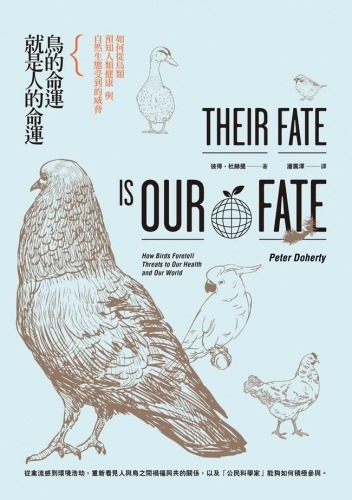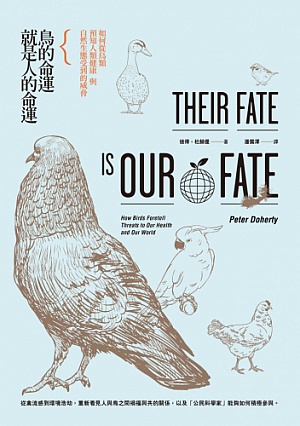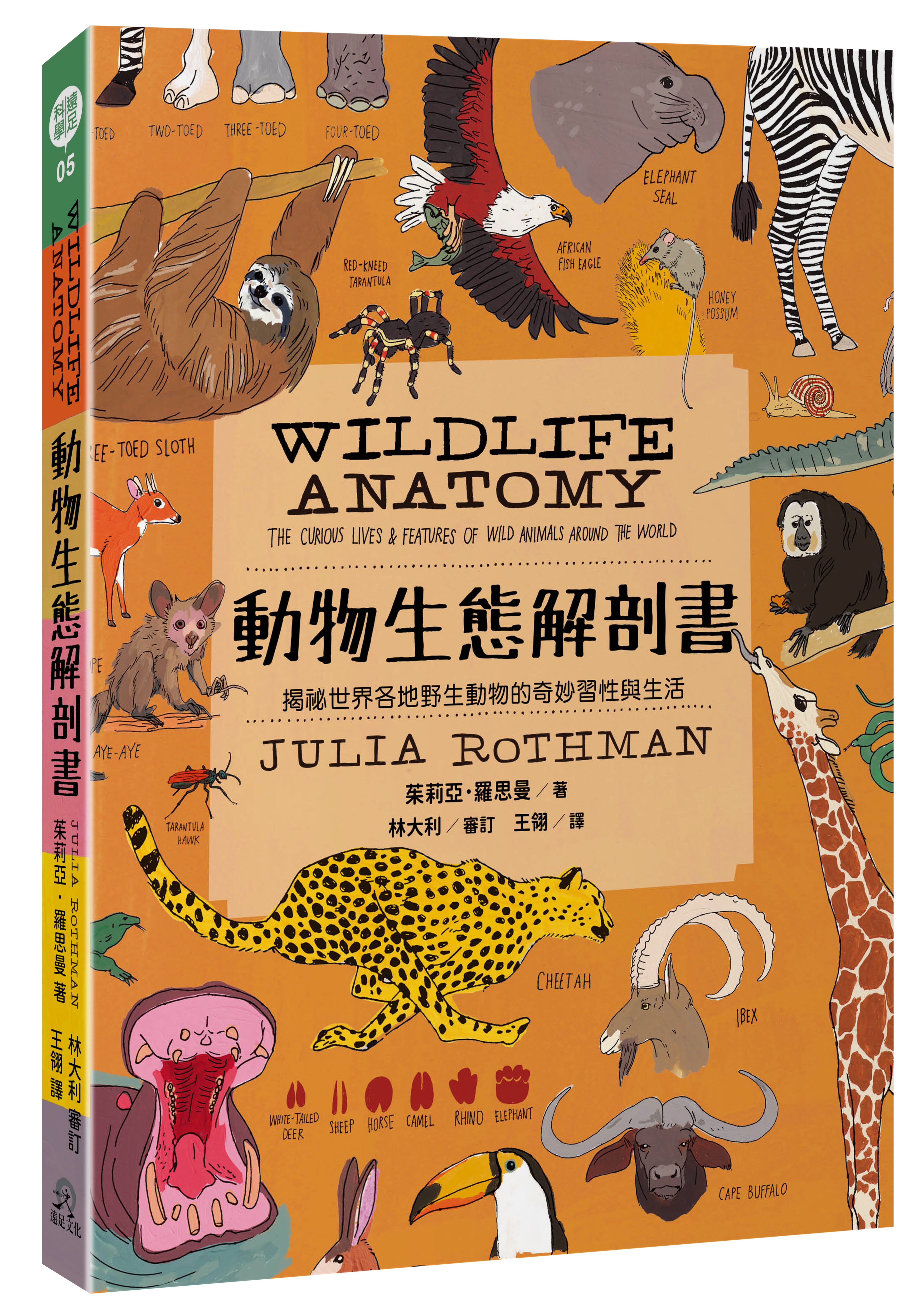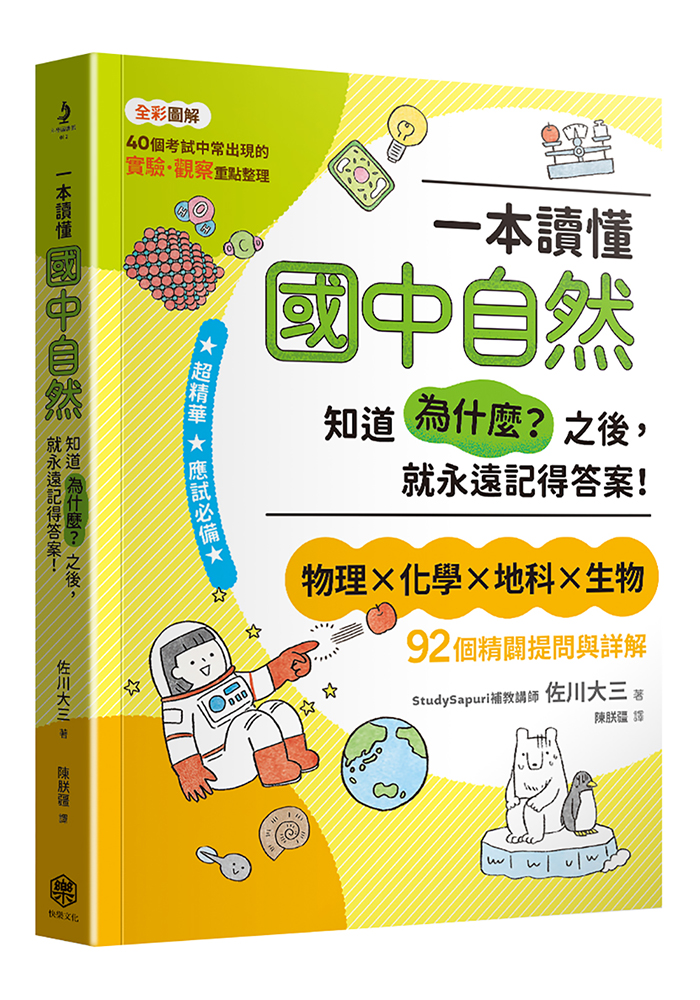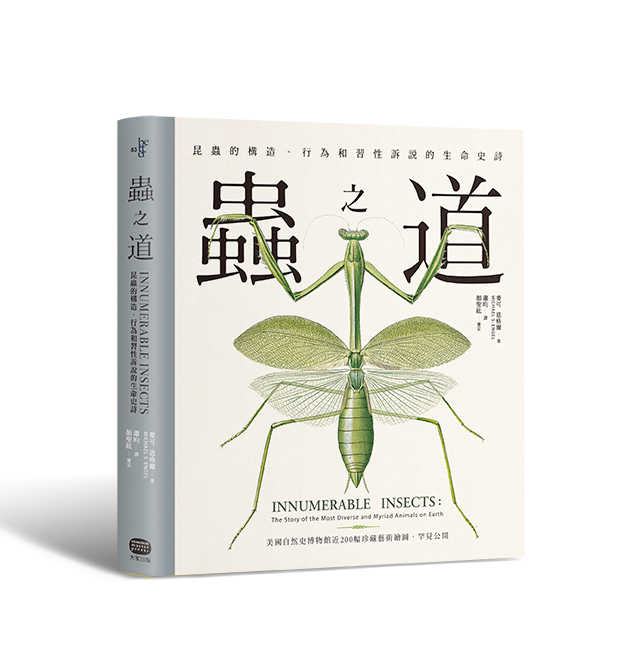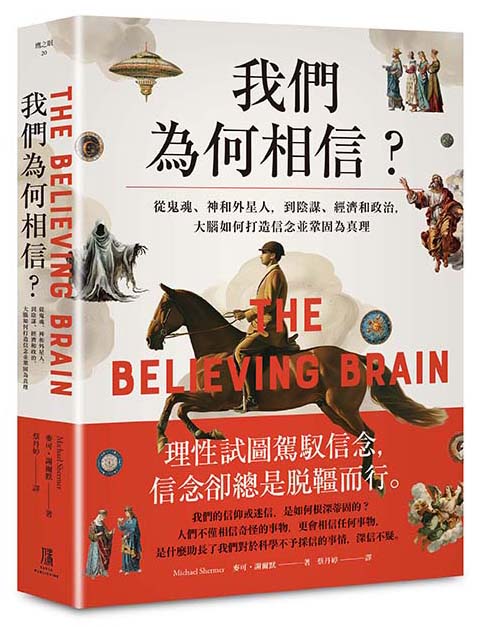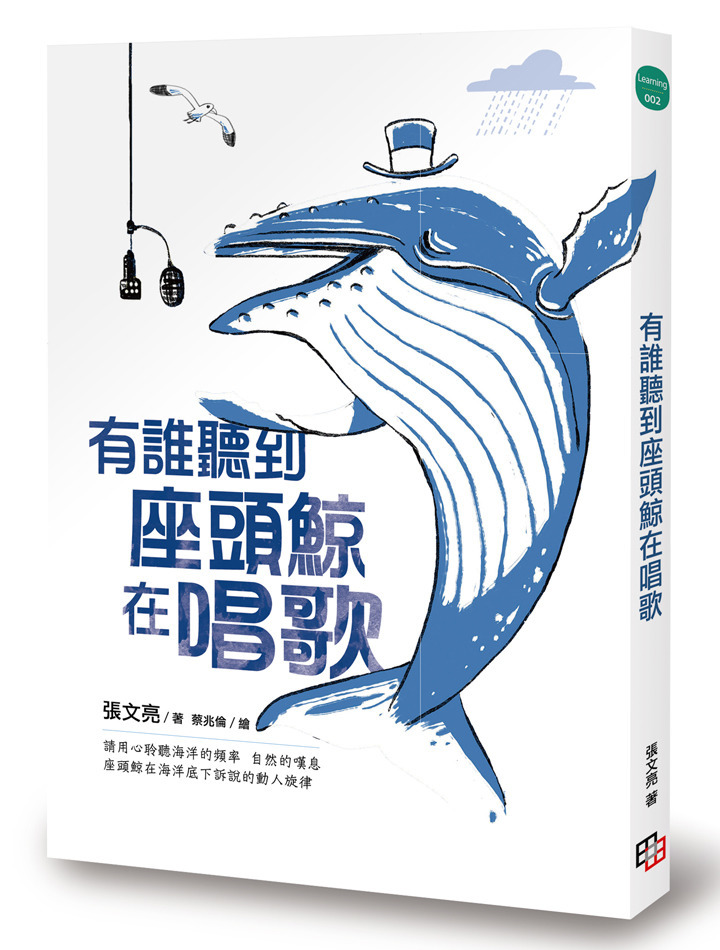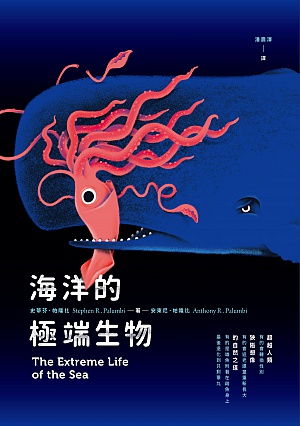從禽流感到環境浩劫,重新看見人與鳥之間禍福與共的關係,以及「公民科學家」能夠如何積極參與
人、鳥、病毒與環境的疾病生態學
在過去,工人會帶著金絲雀一起進到礦坑工作,原因是這種小巧的鳥兒對有毒氣體非常敏感,周遭空氣稍不對勁便會鳴叫甚至死亡。
這些金絲雀的功能是讓人類能夠早一步發現危險。現今的礦坑已經不用金絲雀來示警,但隨著人口暴增與大規模養殖的興起,影響到流感病毒、野鳥及許多哺乳類動物之間的平衡,人類與鳥類之間的關係卻比以往更加緊密。自從一九九七年香港爆發人類感染H5N1禽流感疫情以來,每隔一段時間便在世界各地出現人類感染變種禽鳥病毒的事件,人鳥之間禍福與共的程度愈來愈高。
鳥就像哨兵,是人類健康與地球生態的預警系統,牠們會對空氣、海洋、森林及草原進行取樣,如果自然環境遭到危害,頭一個明顯受到影響的就是鳥類的健康與數量。
本書作者杜赫提是一九九六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研究傳染及流行性感冒數十年,並熱愛觀察鳥類生態。他以各種故事和例子說明人跟鳥之間在生態上和健康上的關聯,用平易的方式解釋醫學和生物學的相關知識,以及我們這樣的普通公民可以做什麼。
彼得.杜赫提 Peter Doherty 諾貝爾獎得主,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系教授,兼美國田納西州孟斐斯市聖猶達兒童研究醫院的生物醫學研究譚莫講座(Michael F. Tamer Chair)。他在免疫學上的先驅研究讓他與辛克納傑(Rolf M. Zinkernagel)共同獲得了一九九六年的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次年,他被選為澳大利亞年度風雲人物(Australian of the Year),並獲頒澳大利亞最高榮譽勳章(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
潘震澤 臺灣大學動物系所畢業、美國偉恩州立大學生理學博士,專長為神經內分泌學。曾任陽明大學生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長,並獲慶齡基礎醫學獎、國科會傑出獎、特約獎等榮譽。現任教美國奧克蘭大學。 近年關心科普讀物譯介,譯有《人體生理學》、《愛上中國的人:李約瑟傳》、《潘朵拉的種子》、《另一個腦》等書,著有《科學讀書人》、《生活無處不科學》,並擔任《科學人》雜誌編譯委員。
人鳥之間:譯後記 潘震澤 「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這首杜甫絕句,為我們描述了一幅聲色俱佳的畫面,也點出了人對於鳥的兩個特性:鳥鳴與飛翔,一向具有的欣羨之情。善鳴的鳥種甚多,雲雀、畫眉、夜鶯與百靈是為人熟知的一些,其鳴叫聲之多樣與動聽,常是口技與樂器模仿的對象。當大地春回,桃紅柳綠之際,要是沒有鶯啼燕語相伴,春光將少了好幾分旖旎。至於喜鵲叫吉、烏鴉報凶,則是人對未來的期待與擔心,而把意義強加於鳥語之上,自是做不得準。詩聖還有一首膾炙人口的名句:「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寫出了人對自由翱翔的嚮往。古今中外,人類模擬鳥類飛行的嘗試從未少過,而於百餘年前終於取得成功,發明了飛機,實現了百萬年來人類的夢想。 這是一本描述鳥類與人類關係的書,作者杜赫提不是文學家,也不是自然學者,而是專研病毒免疫學的傑出生物醫學家,曾獲一九九六年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他是在退休之後愛上了賞鳥,才對鳥的一切產生了研究的興趣,最終則寫了這本知識與趣味兼具的小書。這不禁讓我想起國內的藥理學家張傳炯院士,也是退休後全時投入賞鳥,談起鳥來眉飛色舞,讓人嚮往。 我自己大學念的是動物系,但對蟲魚鳥獸之名,所知無幾;這一方面是個性所致,我對生物構造與功能的興趣,遠比對生物分類與生態來得大,因此研究生涯都在實驗室度過,幾乎沒有任何田野經驗。談到對鳥類的認識,除了大一的動物學與大二的比較解剖學學過鳥類身體構造、大三的胚胎學對雞胚稍有提及外,大四還正式選修過一門鳥類學,由一位沒受過什麼研究訓練的兼任講師,拿著一本發黃的講義授課。整門課下來只記得老師用日式英文講的第一句話:「What is ornithology? Ornithology is the study of bird.」(什麼是鳥類學?鳥類學是研究鳥的學問),其餘則一片空白。 四十幾年前的臺灣,還是克難從簡的年代,不要說帶長鏡頭的單眼照相機了,就連望遠鏡也是奢侈品,因此賞鳥純屬小眾活動。我在臺大念書時聽說東海生物系有賞鳥社成立,還心生羨慕。一直要到後來自己也有能力了,才曉得賞鳥與釣魚這種需要在野外一待幾小時不動的活動,不是自己的菜,也才死了這條心。 因此,我在接下這本書的翻譯工作時,心下有些惶恐,也有幾分期待;一方面擔心自己對鳥的認識不夠,未能做好這份工作,但另一方面,我也想藉此機會補充自己知識的不足。在此我可以說,我的期待並未落空,我從這本書學到了許多之前欠缺的常識;而我更希望透過我的翻譯,國內讀者對鳥與人的密切關係能有所體認,進而對環境保育工作的重要性有更深入的瞭解。 一般人對鳥的認識,大抵接近上述文人墨客筆下所描述的鳥類外觀與行為,以及給人帶來的美感印象,而不會馬上想到鳥類對民生經濟、環境衛生、疾病傳播,以及醫學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性。像家禽養殖在人類社會已有幾千年歷史,提供穩定的蛋白質食物來源(包括牠們的卵在內);鷹隼、烏鴉、鴿子等腐食與雜食性鳥類是大自然的清潔工,幫忙清除野生生物的屍首以及城市居民的廢棄物;禽類也是許多病原菌的帶菌者,不時可能傳染給人,像禽流感已是大眾耳熟能詳的字眼;最後,雞胚是古典發生學與病毒學常用的研究材料,既經濟又實用。 此外,由於鳥類在全球各地分布以及活動的特性(尤其是南北遷徙的候鳥),牠們還是大自然生態健康狀態的最佳指標生物。這本書的澳洲版書名就叫《哨兵雞》(Sentinel Chickens),也是書中第四章章名,指的是將籠裝雞隻刻意擺放在某些地方,讓蚊子叮咬,然後定時檢測這些雞隻的血液,看是否有節肢動物攜帶性病毒感染的痕跡,作為病毒散播程度的依據。還有在有毒氣體感應器發明前,礦工在下礦坑時帶隻金絲雀同行,有預警的作用。再來,自然界鳥類的數量與種類,也間接顯示了生態環境的良窳。 幾個月前,國內有件關於鳥類的研究結果登上了國內外的新聞版面,那是臺師大生命科學系的研究人員利用美國兩所自科學博物館收藏的旅鴿標本,從中抽取DNA定序,並分析其遺傳變異度,推算出旅鴿的有效族群數量,再與旅鴿賴以維生的主食橡實產量做交叉分析,得出旅鴿滅絕的可能原因。巧的是,利用博物館館藏的鳥類標本進行現代的分子生物學研究,在本書第十七章有所提及;而旅鴿從十九世紀上半葉號稱是全球數量最多的鳥種(據估計在三十到五十億之多),半世紀後就遭到全部滅絕的故事,也在第十九章有所介紹。人類的大量捕捉、森林棲地與食物來源的減少,以及傳染病流行,都是可能的原因;新研究則對旅鴿族群數量的天然浮動,提供了新的證據。 像旅鴿這種由族群數量增加過多,碰上食物供應不足所造成的悲慘後果,在自然界許多物種都出現過。如今全球人口已超過七十億人,是一百年前的四倍多;人類若不能從自然界與歷史中學到教訓,有所節制,遲早也會被自身的生殖成就反噬。 國內近二、三十年來,生活條件變好,賞鳥的人也變多了,各地都有野鳥協會的組織成立,大眾環保意識也增強不少;昔日濫捕濫殺過境候鳥(以伯勞鳥最出名)的情事已少見,保護區的設置則增多,這些都是進步社會的表現。即便如此,由人類活動造成生態環境改變,在所難免;尤其是人為氣候暖化造成的影響,更是緩慢而難以讓人馬上察覺。我相信這本從不同觀點來看鳥與人之間關係的書,必能發人深省,讓人開卷有益。 第一章─尋找海鷗:引言 運氣好的話,那一天我們終於將可以看到海鸚(puffin)。十天的旅程已經過了八天,我連一隻海鸚都還沒見著。牠們可不是被其他大批遊客給趕走的,因為我們搭乘的這艘只容八十名乘客的小船,是二○一○年夏季從西雅圖的華盛頓湖,穿越巴拉德水閘來到普吉特海灣,往北到聖璜島,再經過加拿大卑詩省,前往終點站阿拉斯加州朱諾市的第一艘船。位於保護區內陸航道的,差不多就只有我們這批遊客了。 這趟包括參觀冰河及拜訪小型社區等附帶行程的旅遊,對喜歡待在不時會凍著人的甲板上尋找野生動物蹤跡的人來說,還是非常愉快的經驗。船上的每個房間都備有兩具高倍率的雙筒望遠鏡,但那並不能保證我們能看到旅遊指南上所介紹的每一個物種。 不過截至當時為止,我們所看到的海生及陸生哺乳動物已超過原先的期望。一路上我們陸續看見了海豹、海獅、殺人鯨、座頭鯨、多爾鼠海豚、鹿、山羊、黑熊及棕熊。更往北行,我們還看到了仰身浮在海面、只有頭尾像兩個黑色書鎮般突出水面的海獺,順著水流漂過。 在航程初期,我們見到了海鸚的親戚:一隻角嘴海雀(rhinoceros auklet);此外還看到其他海鸚科(alcid)的鳥類,例如斑海雀(murrelet)及海鳩(guillemot)。接下來又看到了鸕鶿(cormorant)、燕鷗(tern),以及各種鷗類(gull)。我是相當晚才開始賞鳥的,所以對我來說,看到這些鳥類大都是既新鮮又有趣的事。在年歲漸長以後才發現新的興趣,是人生的驚喜之一。當然,我已能辨識好些為人熟知的鳥種,像在內陸航道到處可見的白頭鷹(bald eagle)及渡鴉(raven);牠們棲息在有利的位置並保持戒備狀態,不時像到處可見的通勤水上飛機一樣起身飛動,沿著人類居住的水畔迴旋及俯衝。在航道外圍,我們可以一路追著一些飛得又低又快的白色(斑紋)鷹頭;還有一些鷹頭則從原始森林高枝間的鳥巢中探出。有隻一動不動站在裂解浮冰上的老鷹突然起飛,然後朝向冰冷的海水俯衝,又再一飛沖天,腳爪上緊緊抓著一隻大魚。 從古羅馬、拜占庭與帝俄以降,直到今日美國,像神一般強有力的老鷹都是世俗力量的象徵。在阿拉斯加州彼得堡漁港的碼頭,我曾著迷地凝視一隻棲息在附近高桿上的成年老鷹,沒有多久,我發現牠也以同等的專注端詳著我。老鷹的雙眼視覺,加上更敏感以及可接收更廣泛顏色光譜的視網膜,賦予了牠們(包括所有獵禽類)超凡的視覺敏銳度。那隻老鷹看到的我,要比我看到的牠清楚多了。有趣的是,老鷹的象徵大多著重其巨細靡遺的視力,而非其維持環境衛生的能力;對自然界而言,後者可能才是老鷹最重要的功能。在這趟阿拉斯加旅程的初期,我們就從望遠鏡看到了幾隻烏鴉與一群白頭鷹(多屬未成年),將一頭擱淺的鯨魚屍體給肢解的畫面。 當然,做為偶像標誌的白頭鷹只存在於北美;反之,烏鴉則廣泛分布於這個星球,在我住過的世界每一處都看得到。在阿拉斯加見到的烏鴉,種名是渡鴉(Corvus corax),與出名的倫敦塔烏鴉屬於同一種;至於在南半球的澳洲我家後院偶爾可見的小渡鴉,種名則是Corvus mellori。(本書提到的鳥類我大都使用俗名,但在書後附錄提供了牠們的拉丁學名。) 鳥類可做為有力的象徵,像是在北美這塊地區的原住民特林基特人(the Tlingit)將自己分成「鷹族」與「烏鴉族」兩種。內陸航道裡有許多只能經由船隻或飛機才能抵達的小鎮,梅特拉卡特拉(Metlakatla)就屬其中之一,我們在鎮上的社區中心參觀並聆聽了一些有關特林基特人文化的解說。傳統上,鷹族必須與烏鴉族成親,這是防止近親通婚導致遺傳疾病的好法子。然而特林基特人關注的鳥類,還不只是鷹與烏鴉兩種,他們與海鸚的關係有些不同,而且更實際:為了利用現成的資源,特林基特人的祖先會前往海鸚的群居地以取得牠們的肉、皮毛與蛋。 我對海鸚的著迷倒沒那麼功利。由於海鸚有著橘色的鳥喙及矮胖的身材,是種特別可愛的鳥類。牠們的大頭與身軀不成比例,近似人類的小孩;一般認為企鵝出版社就是基於這個原因,使用可愛的海鸚做為旗下童書系列的商標。我在蘇格蘭住過一陣,當地常能看到海鸚,但我卻從來沒碰過一隻。因此,當我們的小船安靜地駛向海鸚的保護區南馬波爾島(South Marble Island)時,我全神貫注,急切等著看到我生平的第一隻海鸚。 突然間,到處都是有著橘紅鳥喙、如假包換的海鸚群集在天空、水裡以及岩島的峭壁上(牠們在壁上挖洞築巢)。太棒了!我們終於進入簇飾海鸚(tufted puffin)的領土。其金黃色羽毛的簇飾,或稱「尾巴」,吊掛在頭部後方的兩側,左右對稱,與較不常見的帶角海鸚(horned puffin)有所不同;後者通常出現在更北邊的地區,長相與做為海鸚圖書商標的大西洋海鸚較為相近。 使用照相機的望遠鏡頭就近觀察這些身軀矮胖且翅膀相對較短的簇飾海鸚,我可以輕易看出牠們不是什麼善飛的鳥類。海鸚起飛得花很大力氣:牠們把頭部朝下,盡全力快速擺動雙翅,並用帶蹼的腳爪拍擊水面,藉以提供額外的動能。海鸚既能潛水又能捕魚,所以在海邊活得十分自在。牠們還能飛翔這點,或許避免了因過度捕獵而絕種的命運;像牠們不會飛的表親大海雀(the great auk),在十九世紀就已絕種。 即便如此,海鸚還是未能避免人類的捕捉。除了提供特林基特人食物來源外,牠們一度也遭到挪威人的捕獵;挪威人飼育了一種擁有六個腳趾的海鸚狗(lundehund),會把海鸚及牠們的卵從巢穴中挖出。自然界的所有物種,都靠食用一種或多種其他生命形式而存活,不論是植物還是動物都一樣。只有當這種關係變得不平衡時,我們才會面臨饑荒以及不可挽回的物種消失等前景,好比我們目前所見許多海洋魚種的情況。 人類擁有足夠的彈性,可以改變自己的維生系統,譬如從傳統的漁人變成紀念品製作者、導遊或是當海盜;鳥類就沒有這麼多選擇,全球海鳥的數目都在持續下降。阿拉斯加州在管制商業捕魚、以維持可存續的族群數量上做得很好,這也是我們沿著內陸航道、一路上能見到這麼多不同鳥類的原因之一。對全球所有的湖泊、水路及海洋進行謹慎而聰明的管理,必須是我們的目標。在尋求食物供應無缺之際,我們必須考慮更廣大自然世界的健全。物種多樣性的喪失,會以無窮的方式影響到我們每個人,從實用與科學到審美等層面。 * * * 對南馬波爾島上以及周圍的海鸚、海獅、北極燕鷗與白頭鷹做了最後巡禮後,我們便往這次航程以及個人發現之旅的終點站朱諾前進。我們搭乘的小船把我們在朱諾放下後,就自個兒踏上回程。 兩天後,我們回到了墨爾本。在勉強撐過飽受時差之苦的一天後,晚上我打開電視,觀看近三週來頭一次的晚間新聞。我發現英國石油公司在墨西哥灣的「深水地平線」鑽油臺發生爆炸、引起大量漏油的事件,仍持續得到大幅報導,不論是電視還是報紙都刊登了鵜鶘(pelican)沾滿油汙的出名相片,讓人看了難過。保育人士關心細菌疾病(好比臘腸菌病〔botulism〕)對美洲褐鵜鶘(American brown pelican)造成的威脅,但與重大漏油事件造成的影響相比,那種危害只能算小兒科;所有海鳥都容易受到水中油汙的傷害。一九九五年鐵男爵號(Iron Baron)在塔斯馬尼亞島北方擱淺時,我人不在澳洲,所以沒有看到沾了油汙的小藍企鵝(fairy penguin)景象,而那次災難只洩出了三百五十噸左右的油艙燃料油。一九八九年埃克森瓦迪茲號(Exxon Valdez)油輪在阿拉斯加的威廉王子灣撞上布萊礁造成的漏油情況要嚴重得多,據信造成了約一萬三千隻簇飾海鸚死亡,但受創最巨的,還屬海鸚的親戚海鴿(pigeon guillemot)。 對此,我們必須更加小心,並重視其背後的科學,否則隨著人類族群增多以及愈形富裕、高消費的生活形態,造成自然棲地遭到剝奪,將無可避免地導致許多鳥種喪失。譬如由於人類的開發,已經使得從堪薩斯州到德州西北狹長地帶、到科羅拉多州東南以及新墨西哥州的沙丘及草原面積減少,這些地區是支援小草原松雞(the lesser prairie chicken,屬於雉科〔grouse family〕)生存的灌叢生態系統,使得牠們的前景堪憂。英國的雉禽類則面臨不同的威脅,將於本書稍後談及保育的努力時一起介紹。同樣的,美國的賞鳥群體也正在盡一切努力,以確保小草原松雞的存活。當然,這種行動措施仰賴志願者的付出;其中要求不多,只是對大自然的熱情以及參與的承諾而已。 隨著人類興建住宅,將大片土地鋪上混凝土,或是為了建造頂級客層的高爾夫球場,而將溼地「重建」等做法,都造成了生物棲地的流失。西太平洋地區賞鳥群體的每一個人,都對亞洲目前發生的事深感憂心:當地正不斷「開發」海岸邊上的潮泥灘,造成娥螺、貽貝一類的生物流失,使得每年從地球這顆小小行星的最北邊到最南邊做遠距離遷徙的鳥種,少了可能的食物來源。 雖然像漏油這種戲劇性事件造成的浩劫顯而易見,但其他問題除非親身經歷,我們可能就不那麼熟悉。像美國奧杜邦學會(Audubon Society)、英國皇家鳥類保護學會(Royal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Birds),以及澳大利亞鳥類生活學會(BirdLife Australia)等組織都在徵召會員,一同監測生物棲地流失及氣候變遷對各種候鳥及留鳥的影響,只不過這種有系統的做法卻吸引不到多少媒體的注意,以致大多數都不為人知。在此次阿拉斯加之旅中,我們拜訪了精采的錫特卡猛禽中心(Raptor Center at Sitka),在那裡看到這些猛禽類在飛翔時撞進高壓電線或被丟棄的捕魚裝備陷住的後果。經該中心治療過的一些鵰、鷹及鴞,其傷勢之重,將永遠不能重返大自然。之前我都不會想到這些,但如今我每次驅車經過鄉間,或是看見垂釣者的釣具被扯斷而遺落在海灘,那些影像都會出現在腦海。減少塑膠袋使用的努力較為人所知,像浮在水面的塑膠袋會纏住海鳥,形成球狀的塑膠袋則會被鳥誤認為食物,而把牠們及其幼鳥噎死。 在鳥類與人類的互動中,更不為大眾所知的一面屬於我的專業領域。我早年的訓練是成為一位獸醫病理學家,之後研究傳染及免疫學將近有五十年,而過去三十年左右我的研究都集中在流行性感冒。大約在四十年前,病毒學家與流行病學家開始認識到:會對人類造成極大危害的A型流感病毒,主要存在於水鳥當中;這個發現對人類及動物疾病來說都意義重大。同時,自二十世紀中葉以來,人類及家禽的數量都有大幅增加,而影響到流感病毒、野鳥與許多哺乳類動物之間的平衡。 多年來,我有幸從研究各種鳥類問題的人士聽到一些動人的故事。身為成功的生物醫學研究人員,早期又受過動物保健的訓練,因此我經常受邀到獸醫學院演講,譬如二○○九年,我頭一次前往知名的南非獸醫學院,該校位於普瑞托利亞市(Pretoria)附近翁德斯泰普特鎮(Onderstepoort)。院長史旺(Gerry Swan)是位藥理學家,他告訴我關於長喙禿鷲(Indian vulture)的神祕死亡事件,以及他和同事幫忙找出解答的過程。此外還有一些有趣但鮮為人知的故事,像是針對鳥類及其胚胎的研究,如何導致我們對人類傳染病及其他疾病(包括癌症在內)的認識出現重大進展。 因此,本書的源起是想探討自然界、鳥類以及人類之間的互動。為了要進入病理學、毒物學以及惡性傳染病等更深層且黑暗的世界,這項探討超越了較為人熟悉的社會與環境主題。很顯然,這大部分反映了人類的活動,對關心這個問題的人來說,我們必須盡一切力量將負面影響降至最低;這一點,專業科學家以及能夠吸引媒體注意環境議題的人士顯然責無旁貸。但不論有沒有受過正式的科學訓練,對於大自然環境裡發生的事,每一個人都可以變成「公民科學家」,做出重要的觀察;這個主題將於本書各章節中一再出現。在此,鳥類扮演關鍵的角色:這些自由飛翔、無遠弗屆的人類親戚,為人類以及共存於地球的其他複雜生物充當了哨兵,幫忙檢測空氣、海洋、森林及草原的健康狀態。許多鳥種在全球遷徙,因此我們有必要大致知曉這個世界從北到南發生了些什麼事。只有當我們花點心思觀察在鳥類身上發生的事,並將這些發現讓人類社會更多人知道,我們(以及牠們)才可能從這些資訊中獲益。我在本書介紹的一些發現,就連最投入的鳥迷都不見得清楚;同樣地,我對醫學界的科學家朋友講述這些故事時,他們也都不曉得,但聽得津津有味。因此,我寫作本書最大的願望,就是能給讀者帶來怡情益智的作用,甚至激發他們採取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