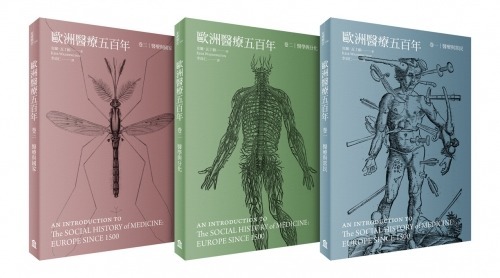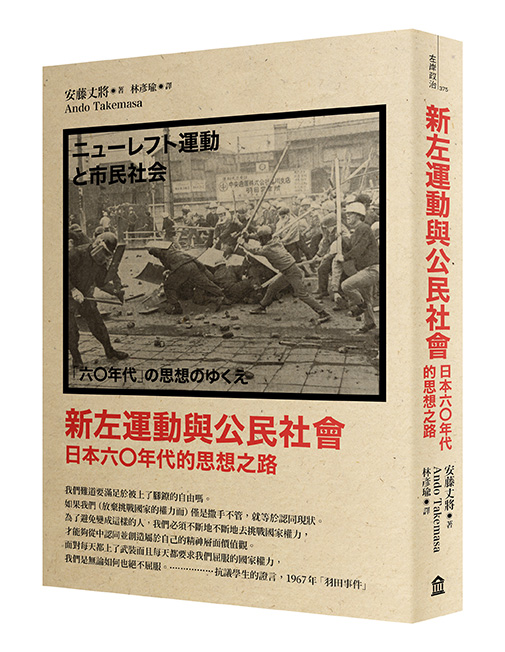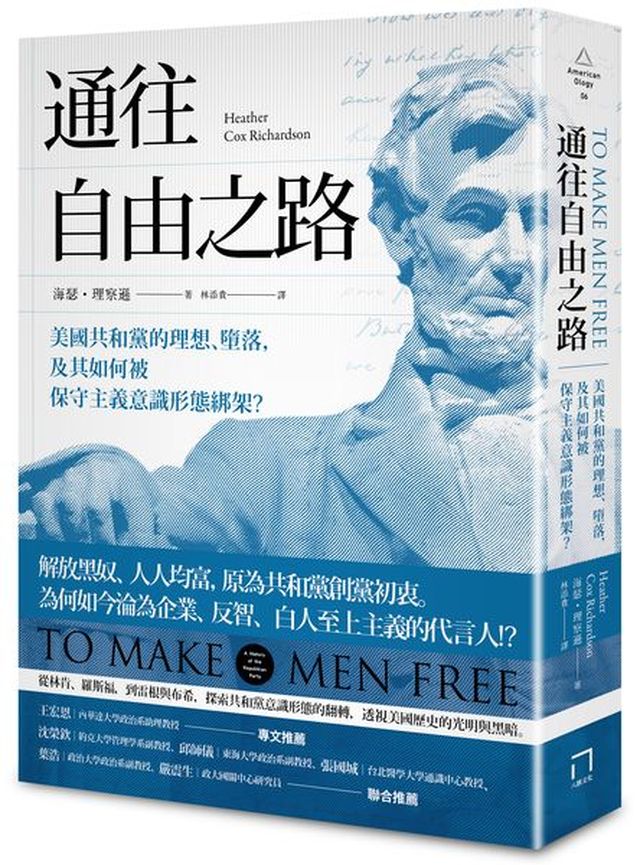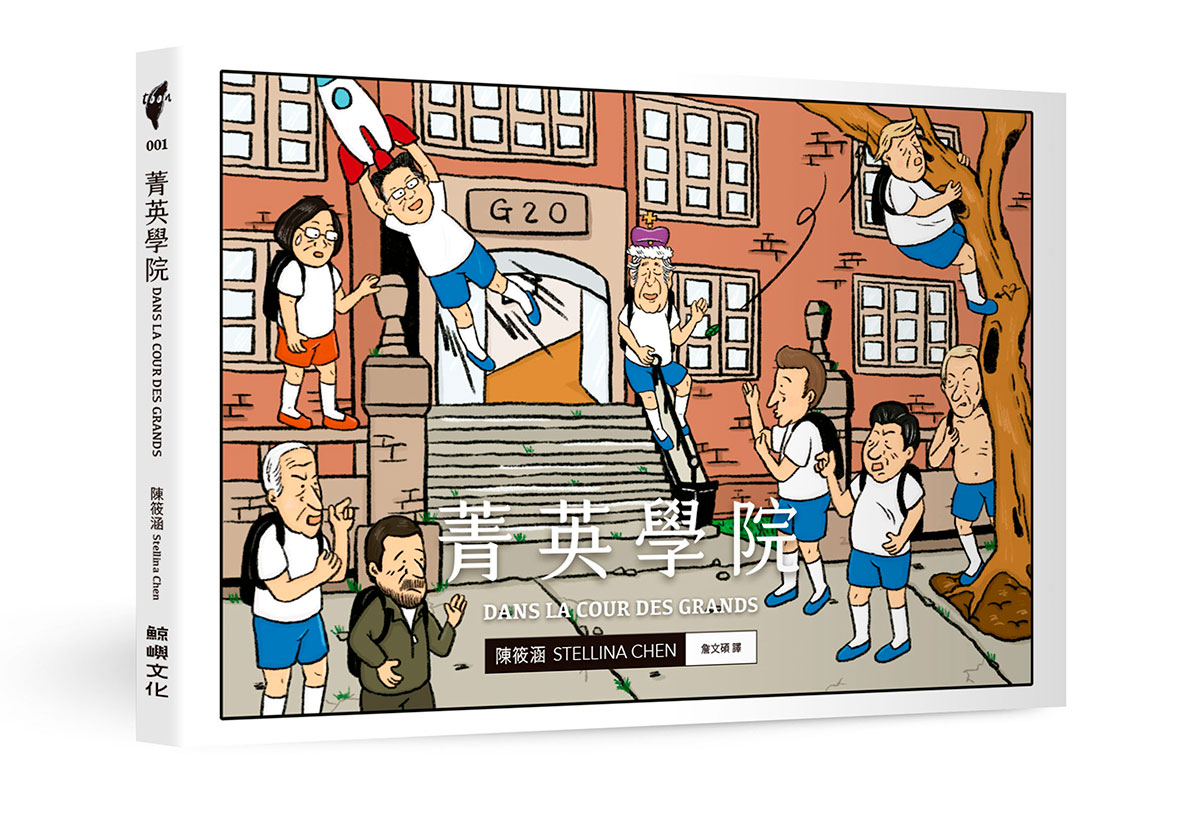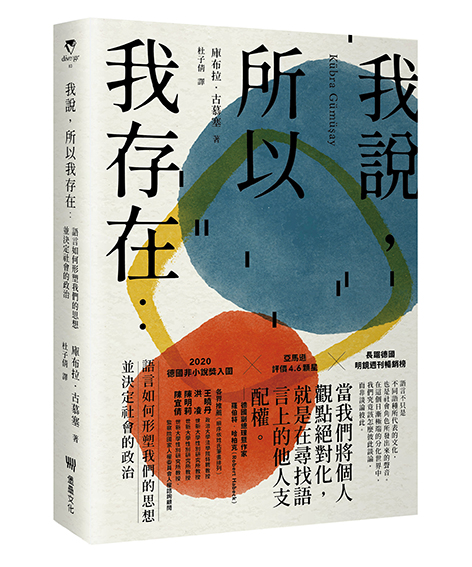詩人濟慈說:「人人都有病。」
但疾病的意義往往超越生物學層面。
500年來,
醫療的行為、體系與制度,
究竟如何受到權力、商業與國家的影響?
過去,醫學總是和「進步」劃上等號。醫界發展出精密的外科手術,輔以各式高科技儀器;研發新型疫苗,逐一攻剋威脅人類生命的傳染病;十九世紀,歐美的船堅炮利,搭配熱帶醫學,躍升為全球主導力量。
不過,自一九六○年代以來,歷史學界挑戰了這樣的看法。醫學並非以線性的方式向前進展,後來看似造福人群的醫學成就,也並非在一推出時,便獲得各界接受。當展開醫學與人類社會的關係圖時,發現醫學並非拉動歷史的唯一引擎,疾病形態、常民觀念、實作、個人行動、醫療人員、機構、社會、文化與政治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這波持續四、五十年的研究潮流也帶來人類社會過度「醫療化」的省思,例如:婦女生產過程的醫療介入是理所當然的嗎?精神疾病的版圖持續擴大是否暗示沒有「正常人」了?但是,作者提醒我們,「醫療化」的批判角度簡化了我們和醫學的關係。我們該如何正視醫療對我們的衝擊,持平地評估醫療的貢獻和轉變?
全套書分成三卷([卷一]醫療與常民、[卷二]醫學與分化、[卷三]醫療與國家),以重要的議題為經,以大量的歷史研究成果為緯,試圖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上,將常見的理論、概念與史學潮流檢驗、琢磨與修正。那將促使我們思索「進步」的意義,對「專業權威」進行批判性的思考。豐富我們對於醫學史的認識,也讓讀者意識到醫學的權威並非不證自明,醫學的改革反映了每個時代。
****************************************************
過去五百年來,把身體失衡和社會失序連結起來,向來是疾病的政治、文化與社會表徵的一部分,不論瘟疫或愛滋病都是如此;疾病的意義常超越其生物學層面。權力關係的微妙變化以及商業考量等因素,也都一直影響到醫療。——克爾‧瓦丁頓(本書作者)
作者達成了不可能的任務:整理、綜合了近四十年來,對歐洲十六到二十世紀醫療社會史大量、多樣而豐富的研究成果,寫成一本精彩可讀的介紹性著作,讓讀者一方面能對現代西方醫療的歷史有宏觀的理解,另一方面又能掌握醫療社會史研究的發展、議題、爭論、面臨的挑戰與前景。——李尚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
【各卷提問】
⊙公共衛生何時進入國家的掌握中,它如何從針對飲用水、污水、都市清潔的環境改善,進展成為針對個人,具有排他性質的管制?細菌學在其中扮演如何角色?為什麼當發展出疫苗血清,可以抵禦傳染病時,仍有人反對接踵疫苗?
⊙醫療的目的常是救助人的身體,但是戰爭竟然幫助了醫學的進展,從外部手術、精神症狀「驚彈症」的判定,到引入DDT和盤尼西林,戰爭如何促展了醫學的發展?
⊙精神病學如何從傅柯所謂的「大監禁」的精神病院時代,轉向抗憂鬱藥物的時代?
☉十五世紀歐洲人便知道採取隔離方式因應瘟疫的大流行,為何考量到貿易與經濟因素,隔離的措施便無法徹底落實?
☉當代性別研究者常認為以男性為主的醫師侵入婦女生產過程,拔除助產士的地位,但新的研究告訴我們一幅完全不同的圖像,在這圖像裡,婦女如何主動邀請男性醫師的參與,藉以標榜身分地位?
⊙16、17世紀,解剖學再度復興的契機是什麼?和當時的哲學、神學、宗教改革有什麼關聯?
⊙19世紀,麻醉法和抗菌法開始發展時,為何沒有立即被外科醫生採用?外科醫生何時開始戴上塑膠手套和口罩,成為我們概念中的醫學化身?
⊙人類如何從生、死都在家中進行,發展成前往「醫院」接受醫療?
克爾‧瓦丁頓Keir Waddington——
英國卡地夫大學醫療社會史教授、
歷史-考古與宗教學院學術發展主任
李尚仁
英國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科學史科技史與醫學史中心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曾獲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著有《帝國的醫師》(第二屆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第七章 外科(節錄)
麻醉常被說成是現代醫學水到渠成的現象,一提出來就廣受歡迎。這並不是事實。麻醉並沒有馬上解決外科醫師所面對的問題:恐懼、技巧、實用、成本和術後照護,仍舊是重要的關切。不同醫院的證據都顯示,在1846年之後,執行手術的數量並沒有戲劇性的增加,也不是所有的手術都在麻醉下進行。醫療期刊記載了許多重大手術,是在沒有使用乙醚和氯仿的情況下進行的。便利性、病人的年齡性別與職業、手術的嚴重程度、地點和成本,都會影響麻醉的使用與否。
麻醉的採用是緩慢的,這反映了世代的差異,但麻醉也具有爭議性,特別是在1846至1860年之間,對於其風險的討論,遠超過對於其好處的討論。公開辯論之初,梅思美術以及透過寒冷來造成麻痺效果,被視為可行的其他選項;以化學方法導致無知覺則遭到公開反對,並提出麻醉對病人帶來的風險問題,特別在刊布了心跳中止引發猝死的報告之後。有些醫師擔心麻醉可能會影響傷口癒合;另外有些外科醫師則擔心麻醉會使得他們的工作不再具有男性氣概。有些批評者擔心,使用麻醉會增加外科醫師對失去意識之病人的掌控,而導致過度或不必要的手術。還有其他的關切被提出,特別是在生產過程中使用麻醉法,擔心它會影響所謂自然的功能運作。反對聲浪在1860年代開始消退。因此,並非一開始就無異議接受麻醉法,它引進的過程受到許多質疑,要到1860年代,病人的需求與菁英外科醫師的支持,才一起減少了反對的聲浪。
麻醉法被認為是現代外科的濫觴,抗菌外科手術則被視為是最後的突破。抗菌外科手術和麻醉法結合,一般認為提供了安全而不受限制的手術前所未有的機會。抗菌法確實帶來改變。術後感染減少,手術的性質與手術進行的環境也有所不同。外科醫師變得更有企圖心,其中有些人實驗新方法並逐步改良,有些人則更為大膽魯莽。
抗菌外科手術的演變,需考量其脈絡。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前,很容易找到骯髒而令人噁心之手術步驟的例子;但過度強調這樣的狀況是不智的。術後的傷口總是會有可觀的交叉感染風險。十九世紀初的外科著作常開門見山探討感染問題,也引進減少壞死的方法。到了1840年代,外科醫師被敦促要採取乾淨的手術作業,和有助於傷口癒合的治療方法;然而到了1860年代,術後感染的程度成為主要關切。英國醫院的死亡率──經常被稱為醫院病(hospitalism)──似乎失控了。好幾種解決方案提出,大致反映了兩個對立理論:接觸傳染論(contagion theory)和瘴氣傳染論(miasma theory),他們分別解釋了感染如何發生與傳播。雖然在實作上,這些傳染理論有所重疊,但它們分別提出了預防術後感染的不同解決方案。
受到接觸感染論影響的外科醫師,其工作假設是:與感染源接觸會散播疾病,因此他們相信必須移除受到感染的物質。維也納的史莫懷哲(Ignaz Semmelweis)基於這樣的觀點,對產褥熱如何在生產後的婦女之間傳播進行觀察。他在1848年宣稱,只要醫生在檢查婦女之前用肥皂和清水洗手,就可以預防這種熱病。雖然史莫懷哲的做法常被認為是無菌步驟的第一個範例,但當時他的影響非常有限。
接受另一方的瘴氣學說的那些人則主張,感染是由空氣中的有毒粒子與不衛生的環境所傳播,解決方案在於環境的改善。衛生運動者已經注意到醫院病房充斥著類似腐敗肉品的噁心臭味,並將之歸因於不健康的環境、缺乏新鮮空氣和過度擁擠。英國護理改良者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在《醫院筆記》(Notes on Hospitals, 1863)推廣的解決方案是,醫院建築應該遵循亭閣原則(pavilion principle),以利清潔空氣的流通。還有些人則強調改善清潔條件與衛生條件以避免術後感染,因此,支持牆壁塗白漆與更嚴格地清潔開刀環境裡的一切事物。
儘管 「清潔派」激起了相當多的討論,但真正主導抗菌法故事的是英國外科醫師約瑟夫‧李斯德(Joseph Lister)。∗歷史學者拜能(W.F. Bynum)在《十九世紀的科學與醫療》(Science and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94)一書宣稱,這是因為較諸前輩,李斯德的抗菌原則更加以醫學科學為基礎;然而,克里斯多佛‧勞倫斯與理察‧狄西(Richard Dixey)則認為,李斯德的聲望主要建立在宣傳之上; 後面這種看法或許更接近事實。這是個大家所熟悉的故事。李斯德在格拉斯哥(Glasgow)發明他的抗菌方法,用消毒劑殺死出現在傷口的感染因子,並在1865年進行他第一次的抗菌手術。他的原則是使用抗菌劑(石碳酸)。李斯德的體系(在1867年首度出版),目標是要排除病菌,雖然李斯德要到後來才使用巴斯德的細菌學說來正當化他的做法。李斯德這樣的說法,使得歷史學者視其方法為病菌學說(germ theory)在外科的應用。
李斯德的做法確實引起相當注意。他透過教學培養出一批弟子,對外傳播其抗菌做法。英國和歐洲的醫師都來拜訪李斯德,親身觀摩他的做法。德國外科醫師特別信服他的方法,還針對過去手術死亡率很高的身體部位,發展出新的手術方法。例如湯姆斯‧比爾諾斯(Thomas Billroth)發展的腸胃外科手術,就大為依賴李斯德的方法。腹腔與胸腔手術變得更為普遍,傳統手術變得更為安全。抗菌法對醫療的影響並不限於開刀房,從1880年代起,藥房開始銷售局部使用的抗菌劑,可在一般科或在家裡使用。針對一般科醫師所出版的手冊,則解釋抗菌步驟該怎麼執行。
傳統的說法有幾個問題。李斯德的聲望和貢獻是複雜的建構產物,他的工作必須放在當時的脈絡中,並考量其他外科醫師的所作所為,而抗菌法的原理與使用方式如何演變也需一併考察。就許多方面而言,李斯德不是一個先鋒或創新的大發明家,而是轉型期人物;例如他使用石碳酸並不是那麼革命性:當時早已有人在使用松節油、酒精和石碳酸來對付傷口感染。李斯德的方法也非毫無爭議,有人批評他太過於專注局部的傷口處理,以及他的做法太過複雜而不實用;清潔派宣稱,他們以更簡單的方法達到相同的效果。雖然這場辯論刺激了外科照護的改良,但反對李斯德的聲浪相當持久。李斯德並不是直接導致病菌學說廣被接受的金光大道:醫師起先抱持懷疑的態度,而細菌學說要到1880年代才站穩腳步。正如麥可‧沃伯依思(Michael Worboys)的《散播病菌》(Spreading Germs, 2000)更為細膩的探討指出,李斯德的觀念和病菌實作(germ practices)有密切關聯。病菌學說的引進,是環繞著李斯德所採取的這些實作以及實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