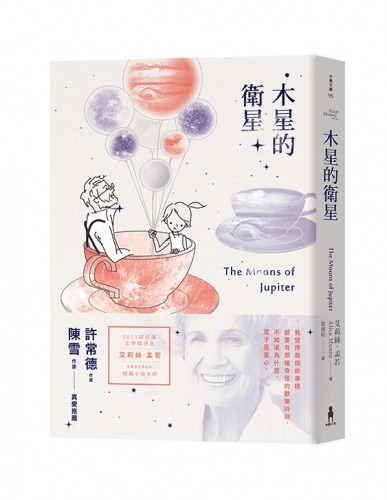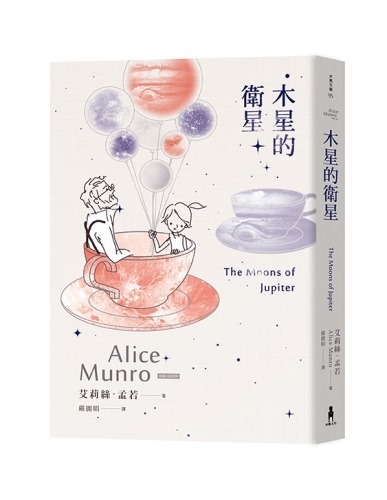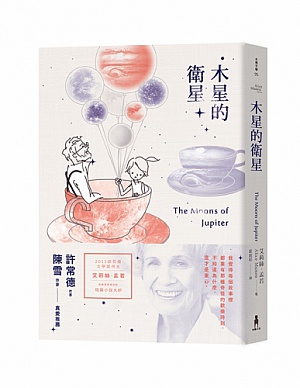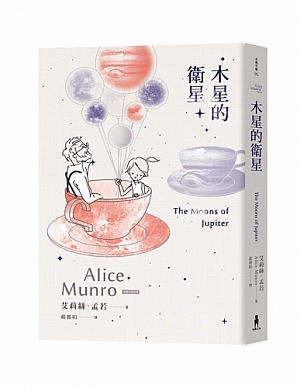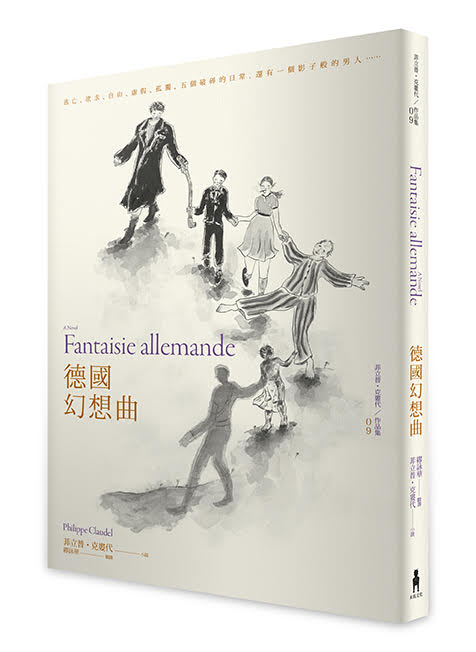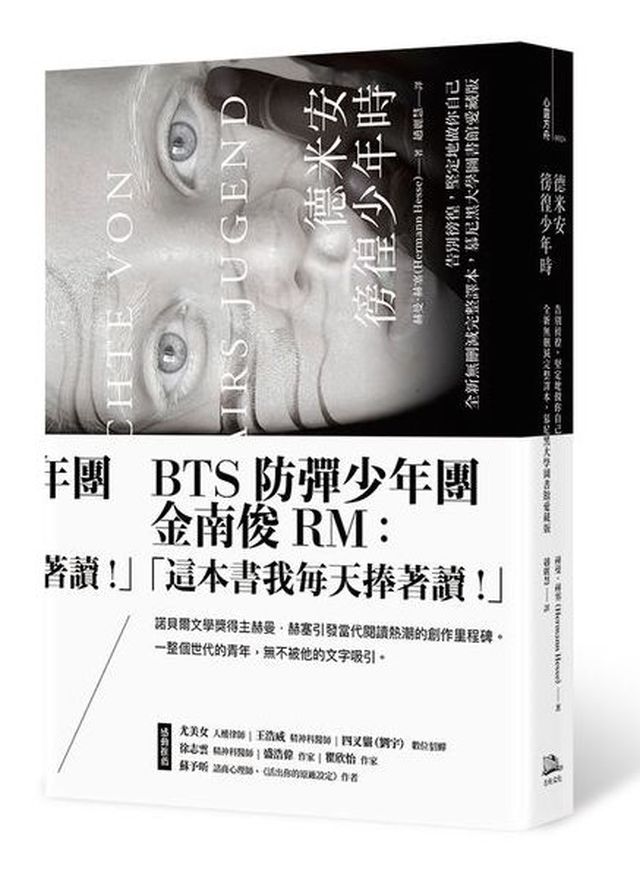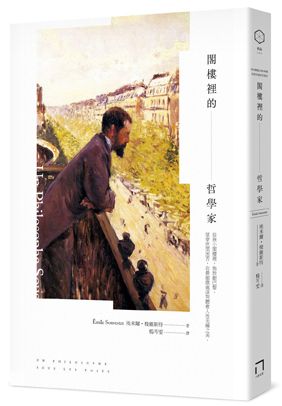作家 陳雪、許常德 推薦
我喜歡艾莉絲•孟若的所有作品,只要有她的中文翻譯本,
立刻找來讀,而且再三反覆細讀。
──作家 陳雪
我覺得每個故事裡都要有那種奇怪的歡樂時刻,
不知道為什麼,這才是重心。
——艾莉絲‧孟若
「我們不怕用愛這個字。我們的生活沒有責任沒有未來,非常自由,可以慷慨付出,一直慶祝也不覺得疲累。我們確實相信,我們的快樂能延續我們想要的短短一段時間。」
在這十一篇深刻、討人喜歡,而且有無盡驚喜的故事裡,發生了琳瑯滿目的事,諸如背叛與勉強,完好或令人哀悼的戀情等等,但真正發生的事情其實是那些隨時間而產生變化的角色們,他們電力十足地向讀者們述說對過去的自己是如何的生氣又抱歉,卻也還有無限的同情。
〈查德利與弗萊明〉:藉由兩個部分,「我」分別描述了母親這一邊的姊妹和父親那一邊的姊妹,如何在同個時代過著截然不同的生活:兩邊的眾姐妹都是未曾出嫁的「老處女」,一邊能過得張牙舞爪、毫不浪費人生,一邊卻如同已死之人——但誰成功、誰又不成功?誰能判斷呢?
〈紅藻〉:療養情傷的莉迪亞搭船前往一座小島,結識了三名出差工人,是截然不同的男子;儘管最後並未發展出實際的關係,卻因為意外得到的禮物而感到一絲溫暖。
〈火雞季節〉:十四歲的女孩到火雞舍打工,初初見識到了社會階級與男女關係的輪廓。孟若在引言中表示,這篇的靈感來自於小時候到旅館打工所見的人事物。
〈意外〉:單身女教師法蘭西絲與已婚教師泰德偷情;天真的法蘭西絲以為鎮上沒什麼人知道,事實上只有她的老母親和泰德語言不通的妻子被蒙在鼓裡。直到某一天,泰德的獨子出了車禍——兩人的關係又將面對何種挑戰?
〈巴登巴士〉:「我」與X都因為隻身到異地工作、伴侶不在身邊,進而發展出了一段愉快的婚外情,然而當X回到加拿大後,從此沒有消息,我則透過朋友才輾轉得知,X很好,而且他的戀人也從沒斷過……
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
艾莉絲‧孟若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溫漢出生長大。高中畢業後,在西安大略大學就讀兩年,之後結婚並搬到溫哥華以及維多利亞,成為三女之母。一九七二年,她返回安大略省西南部,目前和第二任丈夫住在克林頓。
年復一年,她的作品愈來愈廣為流傳。《紐約客》雜誌將她納入卓越投稿人的名單,美國和加拿大種種類型的雜誌也希望能刊出她的作品。挪威和澳洲等遙遠的國家也邀請她去演講,討論自己的作品。
一九六八年,孟若的第一本書《幸福陰影之舞》在加拿大問世,贏得加拿大總督文學獎。一九七一年,《雌性生活》出版,深獲大眾讚賞,接下來則是一九七四年的《一直想對你說》。四年後,大為暢銷,讓她再度得到加拿大總督文學獎。《乞丐女僕》(《妳以為妳是誰?》於英國出版的書名)這部極佳的小說作品入圍英國的布克獎,將孟若推上當代最佳作家的舞台。
嚴麗娟
台大外文系畢業,英國倫敦大學語言學碩士。現任職科技界,喜愛閱讀。
引言
我發覺,我寫的東西出版後,隔絕在書裡面,就很難成為我想談論的話題,更不用說拿來讀了。為什麼?其中一個原因是焦慮。我不能寫得更好嗎?想到這裡也無濟於事——都印到冰冷的書頁上了。還有呢。故事就像從我身上生出來,曾有一度與我相連,不斷長大,現在剪下來了,沒有屏蔽,被拋棄了。我不覺得遺憾,也不覺得後悔──那種感覺說起來很虛偽,我當然一心希望能被別人看見,能出書──而是有點不舒服,不願去看、去盤查。我希望自己能圓熟點,覺得我的想法太天真幼稚了。現在,就來試試看吧。
有些故事比其他的更貼近我的人生,不過都沒有大家想的那麼貼近。與書名同名的故事與父親的死有關。他過世後的夏天,我去參觀奈芙琳天文館,成了故事的引子。一開始寫故事,好多東西從腦袋裡很遙遠的地方跑出來,黏在故事裡。有些你覺得該寫進去的東西消失了;有些則不斷擴張。因此,在故事成形的過程中,你滿懷希望跟惶恐,還常常又驚又喜。如果是某種類型的故事──第一人稱──別人會覺得你不過就把某天發生的所有事情寫下來了。
如果別人那麼想,很好;表示你的故事發揮了效力。其實,故事就是這麼寫出來的。有些來自個人體驗,比方說〈木星的衛星〉或〈田野中的石頭〉──有些則來自觀察──比方說〈訪客〉或〈克羅斯太太和奇德太太〉。這種差距在寫作時變得很模糊,本來就應該這樣。個人的故事無情地脫離了真實。觀察到的故事失去了軼事的優勢,被熟悉的形狀和聲音給入侵。
畢竟,總有希望。
如果要說清楚,〈火雞季節〉的寫作過程或許能拿來解釋。多年來,我試了好多次,一直想寫十九歲那年我當過女侍的旅館。這個故事我一直寫不完。有一天,在父親的文件裡,我找到一張臨時工的照片,背景是他管理的火雞舍內部。照片讓我想到某些類型的苦工,以及努力工作帶來的滿足和同僚之間的情誼,還有要付出的辛勞。我發現,旅店故事的人物進了這個故事……但是,現在我解釋了這個故事,我們就更了解故事的內容了嗎?與性慾或工作有關?與火雞有關?還是與中年女性的住宿或少女的發現有關?想到故事,我就想到瑪喬麗、莉莉和女孩從火雞舍裡出來,外面下著雪,她們勾著手臂唱起歌來。我覺得每個故事裡都要有那種奇怪的歡樂時刻,不知道為什麼,這才是重心。
〈意外〉最早寫出來,那時候是一九七七年的冬天。然後,我幾乎都把時間花在另一本書上。〈巴登巴士〉排在最後,一九八一年秋天寫成。寫這些故事的時候,我都住在安大略省的克林頓。那幾年我去了澳洲和中國,也去了雷諾、鹽湖城和好多地方,但我不覺得旅行對我的寫作有什麼影響。比方說,〈巴登巴士〉有一小部分在澳洲,但主要還是在多倫多皇后街上幾個陌生、骯髒、忙亂的街口,我夏天的時候幾乎都住在那裡。
要記起故事的內容,我得想一想。很奇怪。寫故事的時候,我投入高度的能量,非常虔誠,還有不能說的痛苦;接著我脫身了,故事就在原處變硬定型。我覺得自由了。接下來我又開始組合材料,準備再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