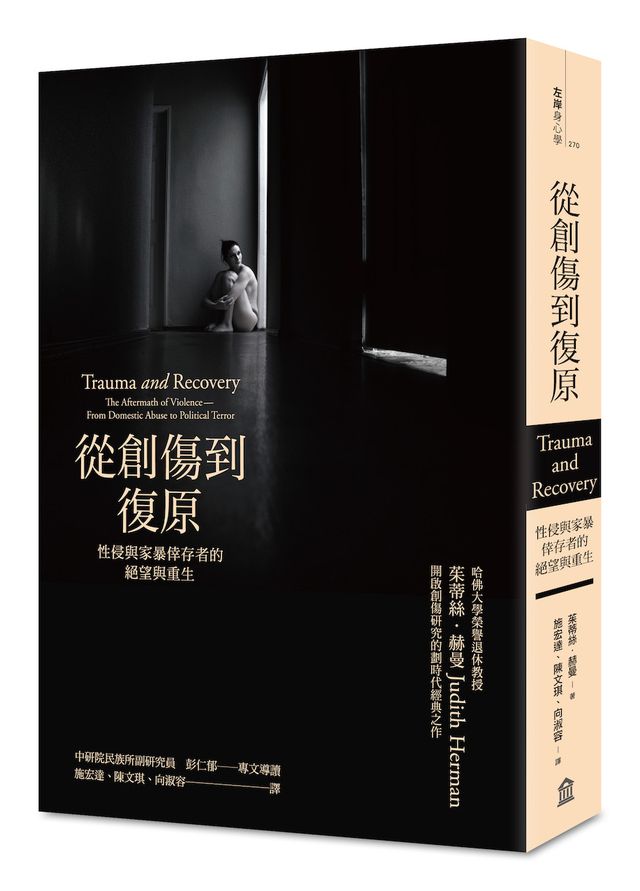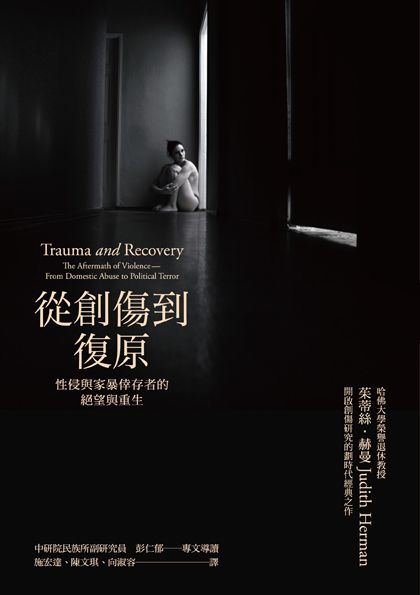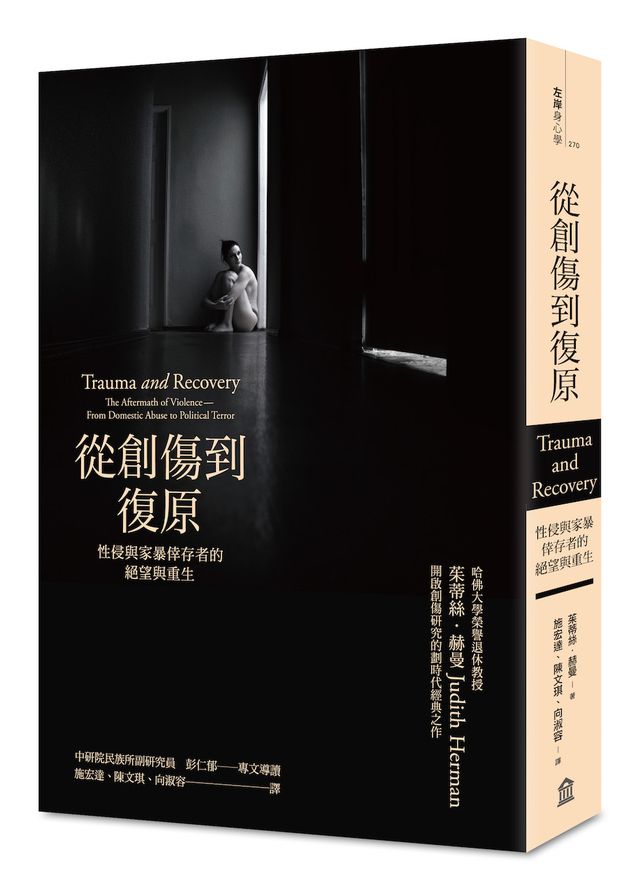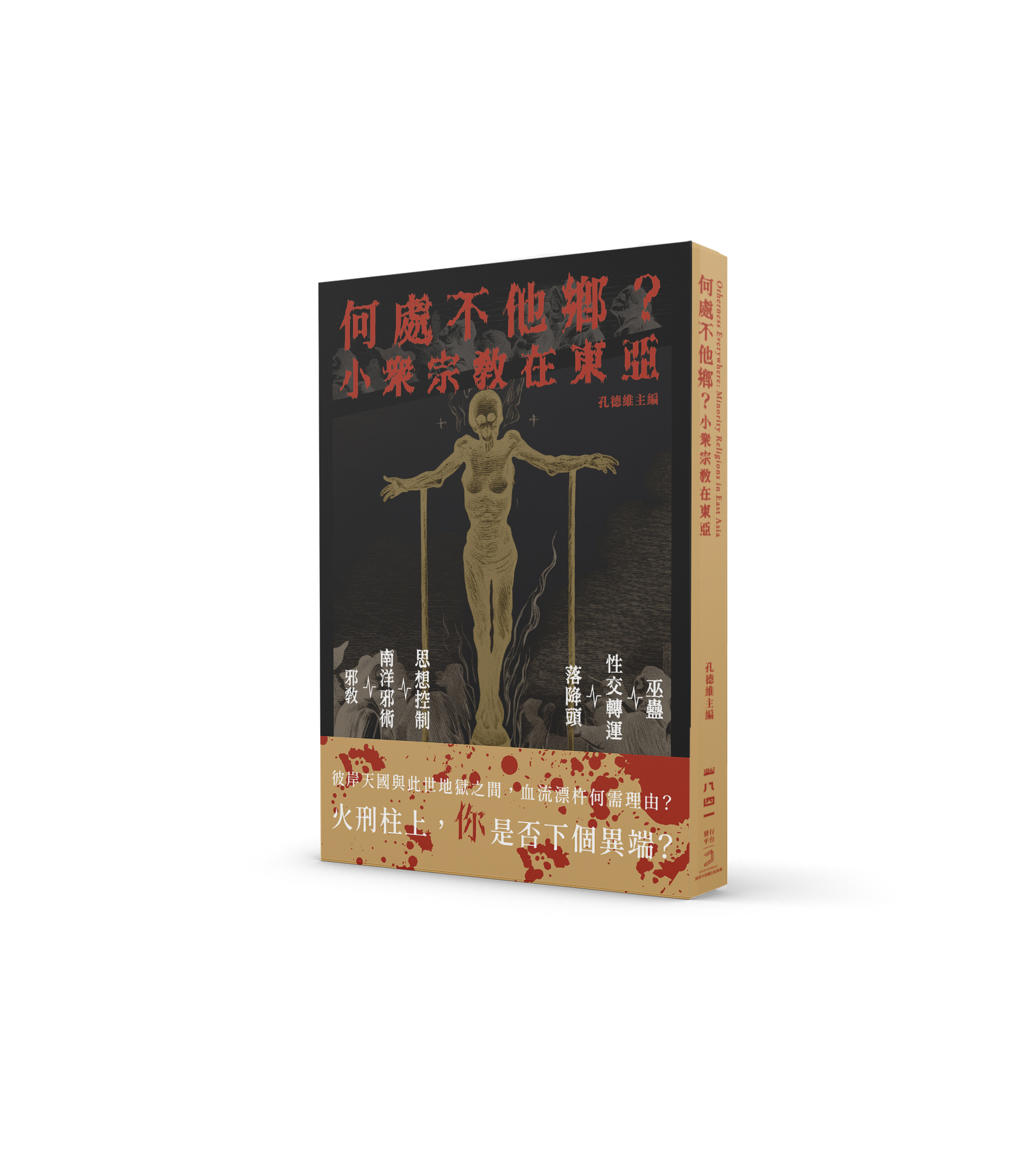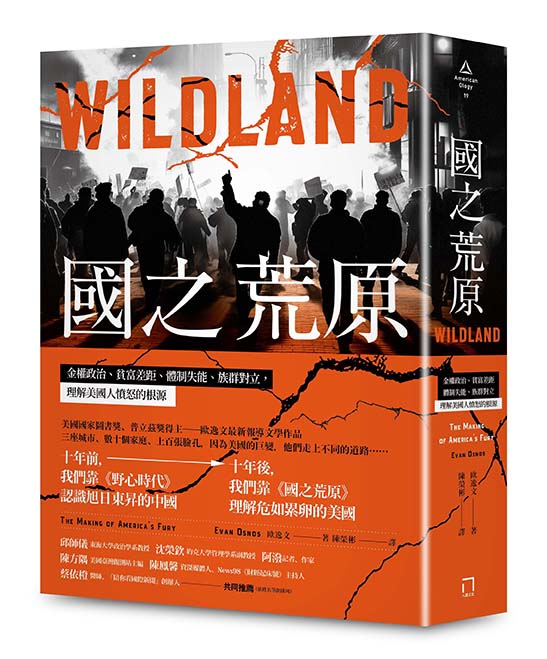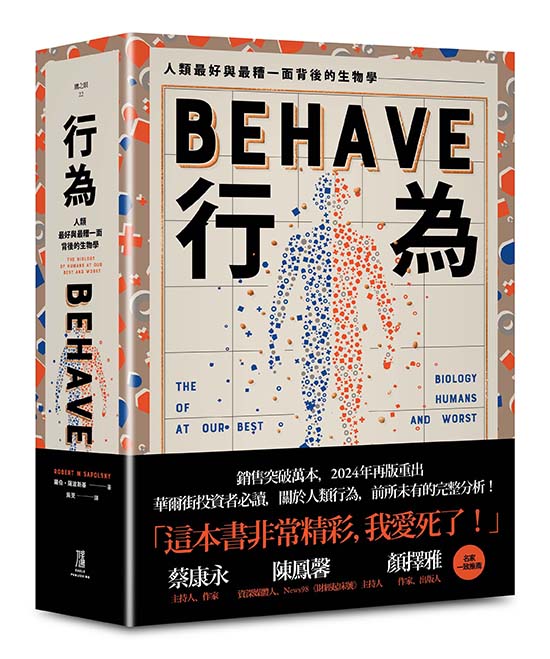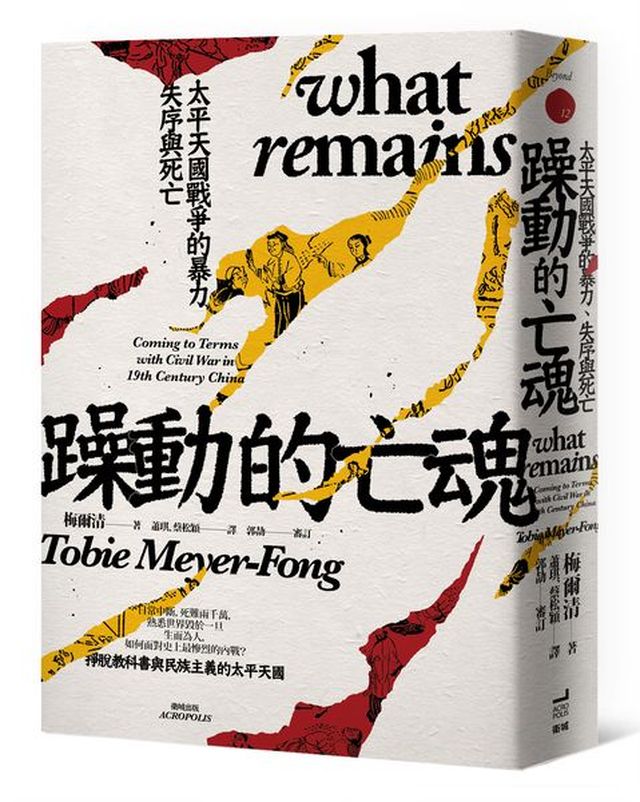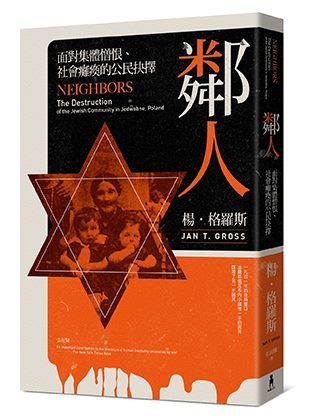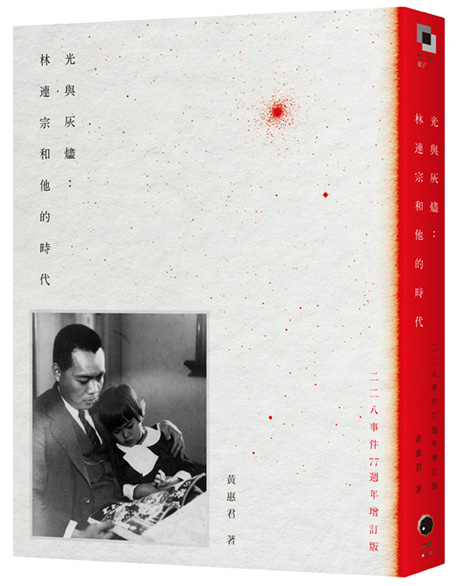哈佛大學退休榮譽教授 茱蒂絲.赫曼 開啟現代創傷研究的經典之作
《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作者范德寇讚譽:「驚人的成就……我們這一代的經典之作。」
如今我們熟知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最早源自十九世紀佛洛伊德與賈內對歇斯底里症的研究,那是學界第一次開始傾聽女性與孩童的家庭故事。過了一百多年,茱蒂絲.赫曼博士對比集中營倖存者、作戰士兵與政治犯的心理歷程與症狀,才發現,經歷家暴與性侵的受害者,其身心創傷等同於人際關係中的傷兵。1980 年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被列入正式診斷,背後的推手,正是那群被政府遺忘的越戰退伍軍人。
在創傷領域,赫曼博士有兩大重要貢獻。第一,她精確地掌握到施虐者與受虐者的情感依附關係。人一定要有互動對象,施虐者理解這一點,所以會企圖隔離受虐者、保持神祕、恩威並施,受虐者自然就在心理上產生恐懼與依賴。對受虐者而言,這些祕密公諸於世之後的汙名與社會歧視比起虐待本身更加傷人,所以往往不願意當下就揭露或擺脫受虐關係。
此外,赫曼博士最重要的創見,就是提出「復原三階段」論:建立安全感、回顧與哀悼,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重建人際連結,不論是哪種創傷的倖存者,首要任務就是在受保護的環境下恢復一般作息,接下來才可以進行煎熬的創傷回顧治療。最後,倖存者走入團體,發現自己的苦痛有人懂,自己的經歷可以啟發別人。她開始覺得自己是個普通人,能過平凡的生活,從前的苦惱只是海水裡的一顆雨滴。她總算走到復原的目的地了,接下來要面對的,就只有當下與未來的人生。
推薦
「自佛洛伊德以降最重要的精神醫學著作之一。」――《紐約時報》
「赫曼連結起作戰士兵、戰俘、受暴婦女和亂倫受害者的世界,對創傷和復原過程的分析令人信服。」――蘿拉.戴維斯(Laura Davis),著有《治療的勇氣》(The Courage to Heal)
「時代的里程碑。」――葛羅莉亞.史坦能(Gloria Steinem)
「本書論及心理創傷和治療對社會的衝擊,無疑將成為經典之作……可說是給倖存者的珍貴禮物。」――米瑞安.路因(Miriam Lewin),《女性書評》(Women’s Review of Books)
「本書解析創傷的本質和復原過程,內容豐富,充滿悲憫之情,每一頁都閃耀著赫曼的洞見。」――莉諾.渥克(Lenore Walker),著有《恐怖的愛》(Terrifying Love)
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1942-),哈佛大學醫學院退休榮譽教授,美國心理創傷研究先驅,曾獲國際創傷壓力研究協會終身成就獎(1996)、美國醫學婦女協會傑出女科學家獎(2000),也是美國心理學會的傑出會員(2003)。
施宏達(前言至第四章):美國派普丁(Pepperdine)大學心理學碩士,輔仁大學食品營養系畢業。曾為劇場工作者和電視節目製作人。
陳文琪(第五章至後記):祖籍江西,生於台灣,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生化學及分子生物學博士。
向淑容(致謝與新版後記):全職譯者、龜速讀者、影集迷。專事書籍與影視字幕翻譯,譯有《鋼鐵人3:電影小說》、《雷神索爾2:電影小說》、《練習8分鐘就靜心》、《野性時刻:國家地理自然攝影新經典》、《文化大革命》、《憂鬱的演化》等書。
目錄
導讀
致謝
第一篇 創傷
第一章 被遺忘的歷史
第二章 恐怖經歷
第三章 失去連結
第四章 囚禁
第五章 受虐兒童
第六章 全新的診斷
第二篇 復原
第七章 治療關係
第八章 安全感
第九章 回顧與哀悼
第十章 重建連結
第十一章 共同性
後記 創傷的矛盾衝突仍未休
2015年新版後記
第十一章 共同性
創傷事件毀壞了個人和群體之間聯繫的恆久基礎。倖存者領會到,自我感、價值觀和人性,都取決於與他人所產生的連結。群體的團結是對抗恐怖和絕望最有力的防衛機制,也最能減輕創傷經驗的毒害。創傷使人產生疏離感,群體則使人重獲歸屬感;創傷為人帶來羞辱和污名,群體則能作見證和給予肯定;創傷貶低受害者,群體則提昇她;創傷摧毀受害者的人性,群體則可以恢復她的人性。
在倖存者的證詞裡,總是一再談到某個重要時刻:受到他人無私寬厚的對待時,連結感都會再度出現。受害者以為已永遠被摧毀一些德行,如信心、正直和勇氣,都會被利他的無私行為再次喚醒。倖存者以他人的行動為典範,開始理解並尋回一部分自我。從那一刻起,倖存者開始與人類的共同性再度產生連結。普里莫.李維提到,盟軍解放納粹集中營後,他如何遇上那個時刻:
殘破的窗戶修理完畢,爐台上燃燒的火開始傳出熱度。每個人似乎都鬆了一口氣。有個囚犯當下提議,每個人都貢獻一小片麵包給我們這三個工作者。大家都同意了。在一天前,絕對沒人想到這種事會發生,因為集中營的法則是:「吃你自己的麵包,如果有辦法,把鄰座的麵包也吃掉。」而且絕不感激言謝。這件事意味著集中營已滅亡,第一次,我們有人開始展現人性。我相信,那個時刻是一個改變的開端,從此,還未死透的我們漸漸由囚犯變回人類。
恢復社會聯繫的起點,就是發現自己並不孤單。除了在群體裡,沒有別處可以體驗到比這個更直接、更有力或更具說服力的經歷。團體心理療法的權威歐文.亞隆稱它為「普同感」(universality)經驗。普同感在心理治療上有深刻的效果,特別是對那些有不堪祕密、覺得自己與他人格格不入的倖存者。受創者因為自己的經驗而感到疏離,因此在復原過程中,倖存者團體所擔任的角色特別重要。受創者在一般社會環境中很難獲得關照,但這類團體可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與了解。遇見與自己有類似遭遇的人,就能解消倖存者疏離、羞愧和被污名的感覺。
對於曾經陷入極端情境的倖存者而言,團體確實有無價的意義,那些情境包括戰爭、強暴、政治迫害、家暴和童年受虐。參與者一再提到,僅僅是和經歷相似苦難的人同在一起,就覺得很安慰。在參與越戰退伍軍人聯誼團體後,肯.史密斯如此描述他第一個反應:「從越戰歸來後,我再也沒有朋友。我認識很多人,也結交很多異性,但從未擁有真正的朋友。那種朋友是我可以在清晨四點打電話告訴他,一想到在春祿(Xuan Loc)發生的那件事,我就想飲彈自盡,或是今天是什麼週年紀念之類的……越戰老兵受到的誤解,只有其他的越戰老兵才能了解。當我開始談論某些事情,這些人完全都懂,當中有一種難以言喻的解脫感。彷彿我從未告訴任何人這些深刻又黑暗的祕密。」
有位亂倫倖存者也是以差不多的口吻,談到自己如何經由參與團體重拾人際的連結感:「我終於衝破那層糾纏了我一輩子的樊籬。我參加一個由六名婦女組成的團體,在她們之間,我沒有任何的祕密。我第一次在人生中真正享有歸屬感。我感到她們接納的是真實的我,而不是戴了假面具的我。」
當團體產生凝聚力和親密感時,接下來上場的就是複雜的相互映照過程。當成員打開心房、把自己伸向他人時,就變得更能接收到他人給予的幫助。她對他人展現的寬容、憐憫和愛心開始產生作用,反射到她自己身上。雖然這類彼此提升的互動關係可以發生在任何關係中,但在團體脈絡下更能發揮得淋漓盡致。亞隆稱這個過程為「適應性循環」(adaptive spiral)。團體的接納提升了成員的自尊,所以彼此變得更能接納他人。三位亂倫倖存者團體的成員如此描述這個適應性循環的過程:
在我看來,參與此團體的種種經驗,是我人生的轉捩點。在受過侵害的女性中,我們很常看到一股力量。發現自身也有那股力量時,我非常震驚。我永遠記得覺醒的那一刻。
我變得更能保護自己,我似乎更「柔軟」了,也允許自己偶爾快樂一下。團體是一面鏡子,我看到自己的鏡像才有這些改變。
我更能接受別人的愛,這是一種良性循環,我因此更能愛自己,然後愛別人。
有位作戰退伍軍人在榮民團體中也體驗到類似的互動:「這是互惠的,我有付出,也有收穫。這感覺真好。這麼久以來,我第一次感到:『太棒了!』。我開始對自己有良好的感覺。」
團體不僅提供機會,讓成員建立互惠的人際關係,還能全體一起賦權增能。成員把彼此當成地位平等的同儕。雖然每個人都遭遇過苦難並需要幫助,但也都對團體有某些貢獻。團體徵用每個成員的力量,用來充實彼此的生命。結果是,團體比個別成員更有力量擔負和整合創傷經驗,成員可利用團體的共享資源,促進個人經驗的整合。
不管是哪一種背景的倖存者團體,我們都能看到其中的治療潛力。有份社區調查顯示,訪談過逃離受暴關係的婦女後,她們皆一致評價,婦女團體是最有效、提供最多協助的管道。精神科醫師約翰.渥克(John Walker)和詹姆斯.納許(James Nash)在作戰退伍軍人的心理治療中發現,許多個人治療效果不彰的患者,在團體治療後卻有極佳的成果。老兵心中強烈的不信任和疏離感,被「同志情誼」和「團隊精神」化解了。德奈理也證實,當主要的治療形式是團體而不是個人時,納粹大屠殺倖存者的預後情況比較好。同樣地,輔導東南亞難民後,莫里克也發現,把倖存者團體納入治療計畫,復原的希望即從悲觀轉向樂觀。
原則上,為倖存者設立團體是極佳的提議,但我們很快會發現,組織成功的團體並非易事。一開始成員充滿期待和希望,也有可能產生衝突、不歡而散,反倒帶來痛苦和失望。團體所帶來的破壞力和治癒力不相上下,領導者也有可能濫用職權、不負責任。在爆發衝突的過程中,成員很容易再次創造原來創傷事件中的各種動力,分別扮演加害者、共犯、旁觀者、受害者和救助者的角色。這種衝突不但會傷害各個成員,還可能導致團體解散。要成功完成團體治療,成員必須找到重心、清楚治療的核心任務,團體也要有完善的結構以保護成員,避免創傷事件重現。雖然不同團體的組成和結構大有不同,但一定要具備以上基本條件,不能有例外。
準備組織團體時,我們很快會發現,沒有適用於所有倖存者的「一般性」團體。每個團體有各自的規模與樣貌,沒有任何團體可以完全照顧每個人的不同需求。不同復原階段的患者也需要不同類型的團體。此外,團體與個人的主要治療任務必須相符合。患者在復原某個階段中適合某團體,帶到另一個階段或許就無效,甚至有害。
治療團體有各種特性,一開始令人眼花撩亂,但只要對照復原過程三大階段的治療任務,就知道作用在哪。在第一階段,團體的主要任務在於建立安全感,焦點放在基本的自我照顧,目標是過一天算一天。在第二階段的團體任務中,焦點是創傷事件本身,重心放在處理過去的創傷。到了第三階段,團體治療的目的,是讓倖存者重新融入一般社群,所以重點放在當前的人際關係。不同類型的團體有其特定的結構,以配合各自專屬的治療任務。
建立安全感的團體
在創傷事件後的初期,團體很少被優先考慮當作首要資源。近期急性精神創傷的倖存者,通常是處於極度的恐懼中,並有潮湧般記憶侵擾的症狀,譬如夢魘和記憶閃現。此時,危機介入的重點在於,如何動員倖存者周遭可以支援的人,因為此刻她寧願選擇與熟悉的人而不是陌生人相處。這不是參加團體的時機。理論上,倖存者會從團體中發現不只有自己有類似遭遇而稍感安慰,但實際上,團體經歷也會令她無法招架。聆聽別人經歷的細節,會觸發她記憶侵擾的症狀,病況會嚴重到她無法帶著同理心傾聽,也無法接受他人的情感支持。因此,對於急性精神創傷倖存者,我們的一般建議是,在創傷事件後數星期或數月才可參加團體。例如,在波士頓地區強暴危機中心(Boston Area Rape Crisis Center),危機介入的措施包括個人和家庭輔導,但不會包括參與團體。危機中心建議,倖存者在考慮參加任何團體前,最好等候六個月到一年。
針對單一創傷事件的倖存者,譬如大規模事故、自然災害或犯罪行為,團體危機介入有時可以即時提供協助。在這些情況下,成員的共同經驗是復原的重要資源。我們也可以舉辦大型團體會議,提供防治教育,提醒眾人創傷的後續效應。人們也意識到大規模創傷事件經常發生,以「危機事件會報」(critical incident debriefing)或「創傷壓力會報」(traumatic stress debriefing)為名的團體會談,已愈見普遍;在一些高風險的行業裡,更是例行舉辦這類會談。
無論如何,舉行會報時,我們也必須遵循基本原則,不可危及成員的安全。有些人認為,受創者的家庭必會支持她,這種想法非常危險。有些人則以為,遭遇同一件可怕事件的人聚集在一起,就能重新振作、團結一致,這也是相當危險的想法。事實上,倖存者檯面下的利益衝突,比較容易會因為該事件而擴大,而不是被當成小事不理。例如,職災發生後,管理階層和基層勞工對事件會出現兩極化的看法。如果事件是源於人為疏忽或蓄意的犯罪,創傷會報反而會干擾、牴觸司法程序進行。因此,辦理大型團體會報的工作者,愈來愈強調這類活動得添加若干限制。警政心理學家克麗絲汀.鄧寧(Christine Dunning)建議,舉行創傷會報時,主辦者得讓流程與形式符合教育功能。因此,在大型公開會議上,參與者應避免講述事件的過程與細節,不發洩強烈情緒,但可以選擇是否接受後續追蹤輔導。
長期、重複的精神創傷倖存者處於復原第一階段時,團體能提供強而有力支持,認可她受過的經歷。但再次強調,團體的首要任務是建立安全感。這個條件沒有滿足的話,成員就很容易嚇到彼此,因為她們都受過恐怖經驗,現實生活也充滿危險。有位亂倫倖存者談到,其他成員的故事令她更加難受:「我原先寄望,參與團體、認識一些有類似經驗的婦女,心情就能輕鬆點。然而,在團體中,最令人痛苦難受的,是領悟到我不但沒有放鬆,恐懼還倍增。」
因此,第一階段的團體工作應該具有高度的認知意義和教育意義,而不是探索事件和個人本身。團體應該要成為討論的場域,成員可以交換創傷症候群的資訊,找出症狀的共同模式,分享自我照顧和自我保護的策略。組織團體時,基本出發點是要幫助倖存者發展力量和適應能力,我們也要提供成員適當的保護,避免她們被排山倒海的回憶和感覺淹沒。
許多不同類型的自助團體都採用匿名戒酒會的模式,以此結構來保護成員。這些團體沒有將焦點放在探索精神創傷,相反地,它們提供認知的架構,以幫助成員理解創傷的後續併發症狀,譬如物質濫用、飲食失調和其它自毀行為。團體並且提供一套指引,幫助倖存者賦權增能,恢復與他人的連結,這套指引一般稱之為「十二步驟」(twelve steps)。
這些自助方案都具有濃厚的教化意味。會談過程中,成員也許能體驗到強烈的情感,但團體不鼓勵宣洩感覺和敘述故事細節,那不一定對他們有幫助。工作重點在於,經由各個成員的證詞去歸納出普遍原則,從同一套指引流程中成長。成員間強烈的凝聚力並非創造安全氛圍的必要條件,基本上還是得靠匿名和保密規則,以及教育方式。成員間不會正面衝突,但也無法彼此提供高度的個人情感支持。在這類團體中,倖存者分享日常經驗,有助於減低羞辱感和疏離感,加速解決實務的問題,並逐漸建立新希望。
為了保護成員的安全,以防被領導幹部剝削,這些自助團體在傳統的十二步驟中精心加入防護措施。權力屬於組織與全體成員,而不是領導者,領導工作則由成員志願輪流擔任。成員同質性要高,也就是說所有參與者都有明確的共同問題。然而,多數團體並沒有設定明確的資格或出席率;團體範圍有彈性又有包容力。它們不會指定參與者必須定期出席或發言。在這種彈性安排下,成員可以自己調整投入參與的程度。如果你只想看看其他有類似經驗的人,可以自由地只來一次,默默觀察,然後隨意離開。
傳統團體在十二步驟中所設立結構性的防護措施,至今一直運作良好,許多團體也爭相複製。然而,某些自助團體仍然容易被領導者把持剝削,或是發展出具壓迫性、怪異的會議流程。在新近設立的團體中,這些問題尤其明顯。它們缺乏豐富的實務經驗,也沒有成熟的十二步驟計畫,無法提供多樣化選擇。參與自助團體的倖存者要切記,必須採納對自己有益的指引方針,其餘不用理會。
在復原第一階段中,還有一種團體稱為「短期壓力管理團體」(short-term stress-management group),對進入早期復原階段的長期創傷倖存者有極大的幫助。再次強調,這類團體的重心也是要建立當前的安全感。團體結構也是以教化為主,重點目標是緩解症狀、解決問題,讓成員學習在日常生活中自我照顧。至於成員的選擇上,這類團體包容性也很廣,任何人都可以參加。當期的數次會談結束後,就可以加入新成員,或是成立新的會談團體。成員不需要強烈積極投入團體,所以不會形成強烈的團體凝聚力。團體幹部採取主動、教誨式的領導風格,當前的任務也有具體的走向,所以成員都得到妥善保護。成員不會揭露過多的自我,也不會針鋒相對、正面衝突。
類似的心理教育團體可以用來處理各式各樣的社會情況。不管是哪種環境,只要當下的首要任務是基本安全感,這些團體就能派上用場,比如精神病院、戒毒、戒酒機構、受暴婦女的收容中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