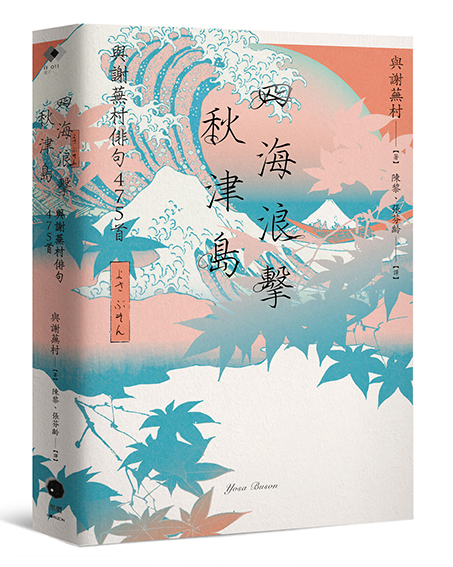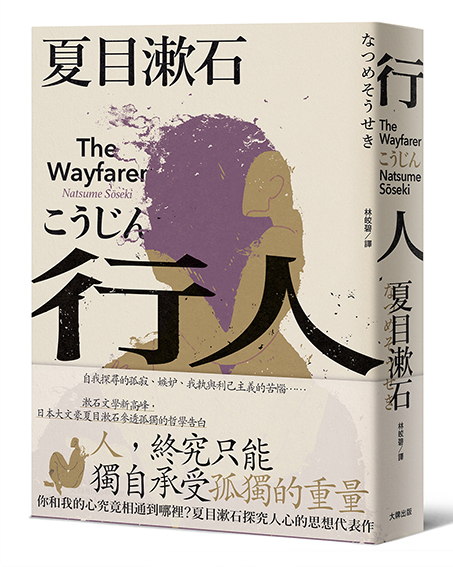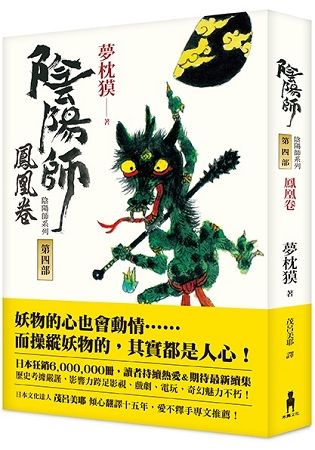啊,悲傷的人總愛笑。
人生如此艱難。
獨自被留下,永遠待在同樣的地方,以同樣的姿態頻頻悲傷喟嘆。
有人說做這種事有什麼用呢?
但那裡有悲傷,有美麗,還有,愛……
《維榮之妻》收錄太宰治十一篇作品,其中晚期代表作〈維榮之妻〉更曾翻拍成電影,並榮獲第三十三屆蒙特婁世界電影節的最佳導演獎。〈維榮之妻〉篇名中的維榮,指法國中世紀的抒情詩人法蘭索瓦.維榮,其一生放蕩不羈,沉迷酒色,命運多舛,更屢次入獄,終遭放逐,常被援以形容無賴、放蕩之人。或許太宰為了強調生命中的荒唐,抑或是投射自己的墮落,而以「維榮」為名,以女性為視角,創作了這篇具強烈對比(妻子的剛毅堅忍對照丈夫的懦弱無賴)的作品。
可是人活著,儘管背負著碰不得的深沉創傷也要忍住,
裝作沒事地活下去。
太宰以敏感纖細的文字,精準刻畫出「無賴」和「懦弱」對抗的心理矛盾,創造出令人著迷的頹廢世界。其以多種形式描述與探索了親愛與背離、懦弱與責任、不堪與諒解,以無可奈何的自嘲與戲謔來面對社會的苛烈──「然而俗話說小偷也有三分道理,我心底深處的白絹也寫滿密密麻麻的小字。……那些小字就像十隻螞蟻從墨汁海爬出來,在白絹上沙沙作響爬來爬去,沾墨汁的腳胡亂印出許多細小的足印,是一種幽微又難為情的文字。」
本書收錄篇中,尤聚焦於「愛情」與「親情」的描寫,看見太宰從千瘡百孔的現實中,匯聚情感的執著與落空。
愛情──
不管是多麼真心的愛情,真到願意掏心掏肺出來給人看,但若只是默默地放在心裡,這只是傲慢,是狂妄,是自我陶醉。……真理不是去感受的。真理是要表現出來的,是要花時間下工夫,去創造出來的。愛情也一樣。若能忍住自己的裝傻與虛無,向對方獻上問候,這裡面一定有愛情在。愛是最高的服務,絲毫不能用來當自我滿足。──〈火鳥〉
我寧可你沒把我放在心上,討厭我,憎恨我,我反而覺得痛快解脫。你把我放在心上,卻又和別的女人上床,等於是把我推入地獄。──〈阿三〉
親情──
家庭的幸福,可說是人生最高的目標,也是榮冠吧。甚至是最後的勝利。但為了得到這個,它卻讓我懊惱地潸然落淚。──〈家庭的幸福〉
當時三十三歲的大哥,正在寫發給鄉下老家的電報,寫下「桂治,今晨四時,逝世」後,不知想到什麼,忽然放掉手上的電報紙慟哭起來。那副模樣,如今依然在我削瘦乾扁的胸中晃動。父親早逝的兄弟們,無論再有錢,依然是可憐的。 ──〈哥哥們〉
全書分為三輯:
※羈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完全無憂無慮的日子只要有一天,不,半天就好,就算幸福的人了。
在〈維榮之妻〉、〈阿三〉、〈櫻桃〉中,女性溫順典雅,逆來順受、無盡包容身旁不稱職的丈夫(父親)。以強力的反差,挑戰世人對於「男人」角色的認知及制約。可這些人物並不見得是自甘墮落,他們的內心往往伴隨著無盡的無奈──「人生如此艱難。渾身上下都被鎖鏈銬著,稍稍一動便噴血如柱。」聚合的表象,卻蘊藏著離散的實相。在理想和失敗之間的縫隙,太宰隱身其中,直指人性的矛盾與掙扎。
※狡黠──貓和女人很像,你若靜靜地待著,她會喚你的名字;你若靠過去,她就逃了。
〈火鳥〉裡的女主角幸代氾濫著感受性,主角彼此辯證著所謂的「愛」──「憐憫與愛情是兩碼子事。理解與愛情也是兩回事。」〈八十八夜〉的笠井一是位天性懦弱的作家,「在卑屈裡活太久,已經忘記自己的語言」,因而渴望荒唐的浪漫。一趟旅行的小意外,卻讓他「徹底被浪漫放逐」。〈美少女〉太宰精湛描寫少女的外貌,讓「美少女」輕盈青春的形象躍然紙上──「很想向少女道歉,比起妳的臉,我居然對妳的乳房比較熟,真是失禮了。」
※悵惘──那副模樣,如今依然在我削瘦乾扁的胸中晃動。父親早逝的兄弟們,無論再有錢,依然是可憐的。
〈父親〉父親在某處為義玩樂,帶著地獄般的心情在玩樂,賭上性命在玩樂。母親終於死心──究竟,「義」是什麼?〈母親〉所帶來的究竟是溫柔的安慰,還是心靈的空虛;〈家庭的幸福〉何以想得到家庭幸福,卻使人懊惱地潸然落淚。〈老海德堡〉以舊地重遊的今昔對照,突出主角心中的惆悵寂寞──「無論走到哪裡,都沒有往昔的氛圍了。並非三島褪色了,或許是我的心乾涸老化了。」〈哥哥們〉細膩描寫兄弟情誼,及失去親人的哀痛。
太宰治
本名津島修治,出生於青森縣北津輕郡金木町的知名仕紳之家,其父為貴族院議員。
1930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法文科就讀,師從井伏鱒二,卻因傾心左翼運動而怠惰學業,終致遭革除學籍。1933年開始用太宰治為筆名寫作。1935年以短篇《逆行》入選第一屆芥川賞決選名單。並於1939年以《女生徒》獲第四屆北村透谷獎。但始終與他最想贏得的芥川賞無緣。
太宰治出生豪門,卻從未享受到來自財富或權勢的種種好處,一生立志文學,曾參加左翼運動,又酗酒、殉情,終其一生處於希望與悔恨的矛盾之中。在他短暫的三十九年生命中,創作三十多部小說,包括《晚年》、《二十世紀旗手》、《維榮之妻》、《斜陽》、《人間失格》等。曾五次自殺,最後於1948年和仰慕他的女讀者於東京三鷹玉川上水投河自盡,結束其人生苦旅。
陳系美
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日本筑波大學地域研究所碩士,專攻日本近代文學,碩士論文《三島由紀夫《鏡子之家》論──以女性像為中心》。曾任空中大學日文講師、華視特約譯播,現為專職譯者。譯有:夏目漱石《三四郎》、三島由紀夫《鏡子之家》、太宰治《小說燈籠》、佐野洋子《靜子》、山田詠美《賢者之愛》等書。
維榮之妻
一
玄關傳來慌張開門聲,吵醒了我。我知道一定是爛醉的丈夫深夜歸來,因此默默繼續躺在床上。
丈夫打開隔壁房間的電燈,發出急促呼吸聲,翻找了書桌的抽屜,也翻找了書櫃的抽屜,不曉得在找什麼。不久,我聽到他咚的一聲坐在榻榻米上,依然氣喘吁吁地不曉得在做什麼。我躺在床上說:
「你回來啦。吃過晚飯了嗎?櫥櫃裡有飯糰。」
「哦,謝謝。」丈夫一反常態答得很溫柔,接著問:「小寶好嗎?還在發燒嗎?」
這也誠屬難得。小寶明年就四歲了,不知是營養不良的關係,還是丈夫酒精中毒害的,抑或病毒所致,竟長得比人家兩歲的小孩還小,走起路來搖搖晃晃,說起話來充其量也只會嗯嘛嗯嘛或咿呀咿呀的兒語,我都不禁懷疑這孩子是不是腦袋有問題。帶他去澡堂時,抱起他光溜溜的身體,實在太小太醜又太瘦,我忍不住悲從中來,顧不得眾目睽睽便潸然落淚。而且這孩子常拉肚子、發燒,丈夫又時常不在家,對小孩的事不聞不問,縱使我跟他說孩子發燒了,他也只應一句:「哦,這樣啊,帶去看醫生就好了吧。」然後匆忙披上斗篷大衣就出門了。我也想帶孩子去看醫生,可是家裡沒錢,只能陪孩子睡覺,默默地撫摸他的頭,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不過這晚丈夫不曉得怎麼回事,不僅變得很溫柔,還難得問起小孩發燒的事。我並沒有特別高興,反倒有種可怕的預感,霎時背脊發寒。我默默地沒有應答,就這樣聽著丈夫急促的呼吸聲。過了片刻,玄關傳來女人的嬌嗲聲。
「有人在家嗎?」
我打了冷顫,彷如全身被潑了冷水。
「有人在家嗎?大谷先生!」
這次語氣有些尖銳,同時也傳來玄關的開門聲。
「大谷先生!你在家吧?」
這次顯然是憤怒聲。
此時丈夫終於走去玄關。
「幹嘛?」
丈夫語氣顯得惶恐不安,答得有些呆滯。
「你還問我幹嘛?」女人壓低聲音說,「你好歹也有個像樣的房子,居然做那種小偷的勾當,到底怎麼回事?別開玩笑了,把那個還給我。不還的話,我這就去報警。」
「妳在說什麼?太失禮了!這裡不是你們該來的地方。給我滾!不滾的話,我才要去報警!」
此時,出現另一個男人的聲音。
「大谷先生,你膽子真大呀!居然說這不是我們該來的地方?真是好樣的!令人傻眼吶!這事非同小可,那可是別人的錢,你開玩笑也要有個限度。一直以來,我們夫妻為你吃了多少苦頭,你不可能不知道吧!可是你居然做出今晚那種無情的事,我真是看走眼了!」
「你們這是勒索!」丈夫說得氣勢驚人,但聲音不停顫抖,「是恐嚇!給我滾!有事明天再說!」
「你別嚇唬人了,先生,你真是十足的大壞蛋。既然如此,我只好拜託警察幫忙了!」
這句話帶著駭人的憎惡,我渾身起了雞皮疙瘩。
「隨便你!」丈夫怒聲喊道,但有種空虛感。
……
我迷迷濛濛快要睡著之際,忽地睜開眼睛,發現清晨的光線已經照進來了,便起身穿衣揹著孩子出門。因為我實在無法靜靜地在家裡待下去。
我漫無目的地走著,來到車站。在車站前的攤商買了糖果給小孩吃,然後一時興起買了到吉祥寺的車票,搭上電車,抓著吊環,不經意看到車廂裡的廣告海報,上面有丈夫的名字。那是雜誌廣告,丈夫在這份雜誌發表了一篇以「法蘭索瓦.維榮」為題的長篇論文。我凝視「法蘭索瓦.維榮」這個標題與丈夫的名字,不知為何悲從中來潸然落淚,霎時看不清眼前的海報。
在吉祥寺下車後,走去看看暌違多年的井之頭公園,池畔的杉樹早被砍光,像要開始興建什麼工程的地景,有種赤裸裸的淒涼,整個景致和以前截然不同。
我放下背上的孩子,兩人坐在池畔的殘破長椅上,我拿出家裡帶來的地瓜給孩子吃。
「小寶,這個水池很漂亮吧?以前啊,這個水池有很多鯉魚和金魚喔,現在什麼都沒了,真無趣啊。」
孩子不曉得在想什麼,嘴裡塞滿了地瓜,股著雙頰,咯咯咯地發出怪笑聲。儘管是自己的孩子,我不免懷疑他是白痴。
然而一直坐在池畔的長椅上也解決不了事情,因此我又揹起孩子,搖搖晃晃地折返吉祥寺車站,逛了逛熱鬧的攤商街,然後在車站買了前往中野的車票,沒有任何主意也全無計畫,彷如被吸入可怕的惡魔深淵般,搭上電車,在中野站下車,照著問到的路線前進,終於來到那對夫妻開的小料理店前。
正面的門還沒開,於是我繞後門進去。老闆不在,老闆娘獨自在打掃店裡。我和老闆娘照面的瞬間,流利地說出自己也很意外的謊話。
「老闆娘,我能把錢都還給你們喔。今晚不行的話,明天確定能還,請您不用擔心。」
「哎呀,這真是太感謝妳了。」
老闆娘顯得有些開心,但臉上依然殘留忐忑的陰影。
「老闆娘,真的啦,一定會有人拿錢來這裡。在那之前,我願意一直留在這裡當人質。這樣您可以放心了吧?錢送來之前,讓我在你們店裡幫忙吧。」
我放下背上的孩子,讓他自己在後面的六疊房間玩,不斷地努力工作。小寶早已習慣一個人玩,一點也不礙事。因為腦筋不好,所以不怕生,也會對老闆娘笑。我代替老闆娘去領他們的配給物時,聽說老闆娘給他一個美國製的空罐頭當玩具,他就在六疊房間裡敲敲打打、推滾罐頭,自得其樂地玩。
中午,老闆採購魚貨和蔬菜回來。我一看到他立刻說出同樣的謊,把之前向老闆娘撒的謊再說一次。
老闆一臉驚愣地說:
「咦?可是太太,錢這種東西,沒捏在自己的手裡之前,都是靠不住的喔!」
出乎意外,他以鎮定的口氣如此訓示我。
「不會的,真的已經搞定了。所以請您相信我,請再寬限我一天。在那之前,我會在店裡幫忙。」
「只要能還錢,什麼都好說啦。」老闆自言自語般繼續說:「畢竟今年也只剩五六天而已。」
「是啊,所以,所以那個,讓我……啊?有客人來了。歡迎光臨!」我對著三個一起走進店裡,像是工人般的客人微微一笑,然後小聲對老闆娘說:「老闆娘,不好意思,圍裙借我用一下。」
「唷,你們雇了一個美女啊。長得可真漂亮。」其中一位客人說。
「你可別誘拐她。」老闆以半開玩笑的語氣說:「她可是身價不斐喔。」
「百萬美元的名馬?」另一位客人低俗地調侃。
「就算名馬,母的也只值一半的價錢。」
我一邊溫酒,不甘示弱地回敬他那句低俗話。
「別這麼謙虛嘛。今後日本,不管是馬還是狗,都是男女平權喔。」
其中最年輕的客人,咆哮般地說:
「小姐,我愛上妳了!一見鍾情!可是,妳有小孩吧?」
「沒有。」老闆娘後面抱小寶出來,「這是我們從親戚那裡領養來的孩子。這樣我們終於也後繼有人了。」
「也有了錢。」一位客人如此揶揄。
「也有了女色,也有欠債。」老闆先是正色低喃,隨後倏地改變語氣問客人:「你們要吃什麼?來個綜合火鍋吧?」
此時,我明白了一件事。心想果然沒錯,暗自點頭,表面裝作若無其事,端酒給客人。
這天或許是平安夜的緣故,客人絡繹不絕,接二連三進來,從早到晚我幾乎沒吃東西,可能是心事重重之故。老闆娘要我歇口氣吃點東西,我也說不用很飽了,然後彷如穿著一件羽衣飛舞似的,輕快地勤奮工作。或許是自我陶醉,我覺得這天店裡充滿異樣的活力,有客人問我叫什麼名字,甚至有兩三位客人要求跟我握手。
可是,這又有什麼用呢?我依然摸不著頭緒,不知如何是好。只是面帶笑容,配合客人的低級笑話,回以更低級的笑話,穿梭在客人之間到處斟酒。後來只覺得,要是自己的身體能像冰淇淋一樣融掉該有多好。
這世上,偶爾還是會出現奇蹟的吧。
到了晚上九點多,一個頭戴紙做的聖誕節三角帽,臉的上半部蒙著怪盜魯邦黑面具的男人,帶著一位年約三十四、五,身材纖細容貌美麗的婦人,進到店裡。男人背對我們,在土石地角落的椅子坐下。這個男人一踏進店裡,我立刻認出他是誰,就是我的小偷丈夫。
他似乎沒注意到我,我也佯裝不知,繼續招呼其他客人。婦人在丈夫對面坐定後,喊了一聲:
「小姐,過來一下。」
「好的。」
我立即回應,走到他們兩人那桌。
「歡迎光臨,要喝酒嗎?」
我這麼說時,丈夫在面具底下偷瞄我,顯得極其吃驚。我輕拍他的肩說:
「要說聖誕快樂?還是什麼呢?你看起來還能喝個一升啊。」
……
早上起床,我和孩子一起吃飯,做了便當,揹孩子去中野上班。年底年初是店裡的旺季,在這裡大家稱我椿屋的佐知,這個佐知每天忙得團團轉,丈夫兩天一次會來喝酒,喝完酒一轉眼又不見了,酒錢都是我付。到了深夜,他又會來店裡探頭,悄悄地問我:
「可以回家了嗎?」
我點點頭,這才準備離開。也曾常常一路愉快地走在回家路上。
「為什麼不打從一開始就這麼做呢?我現在很幸福喔。」
「女人沒有幸不幸福可言。」
「是嗎?經你這麼一說,我也這麼覺得耶。那麼男人呢?」
「男人只有不幸,總是和恐懼在對戰。」
「這我就不懂了。不過,我想一直過這種生活。椿屋的老闆和老闆娘,都是很好的人。」
「他們是蠢蛋啊,鄉巴佬。妳別看他們那樣,其實貪得無厭喔。他們讓我喝酒,終究還不是想賺錢。」
「人家也是做生意嘛,當然想賺錢。可是不止如此吧?你騷擾過老闆娘吧?」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怎麼?老闆發現了嗎?」
「他好像知道得很清楚,前陣子還嘆氣地說,也有了女色,也有欠債呢。」
「這麼說似乎很矯揉造作,其實我很想死,想死得要命。打從出生就在想死的事。為了大家好,還是死了算了。這已經確定的事。可是我卻遲遲死不了。總覺得有個奇怪恐怖的神,阻止我去死。」
「因為你還有工作要做。」
「工作根本不重要。我寫的那些東西,不是傑作也不是劣作。只要人們說好,就會變好,說壞就會變壞。就像呼出去的氣和吸進來的氣。可怕的是,這世上一定有神。有吧?」
「啊?」
「世上有神吧?」
「我也不知道。」
「這樣啊。」
上了十天、二十天班之後,我發現來椿屋喝酒的客人全是犯罪者,我丈夫還算比較輕微的。不僅是店裡的客人,連在路上行走的人,我都覺得他們也隱藏著什麼罪行。譬如有個穿著高雅、年約五十的婦人,來椿屋的後門賣酒,擺明地說一升三百圓。以現在的行情算是便宜的,因此老闆娘立刻跟她買,事後發現是摻了水的酒。連那麼高雅的婦人都得做出這種欺瞞勾當,在這種世上,想活得完全沒有不可告人之事,是不可能的。如同撲克牌遊戲,蒐集到所有負牌,就能豬羊變色變成正牌,這在道德世界有可能嗎?
如果真的有神,出來吧!我在正月的尾聲,遭店裡的客人玷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