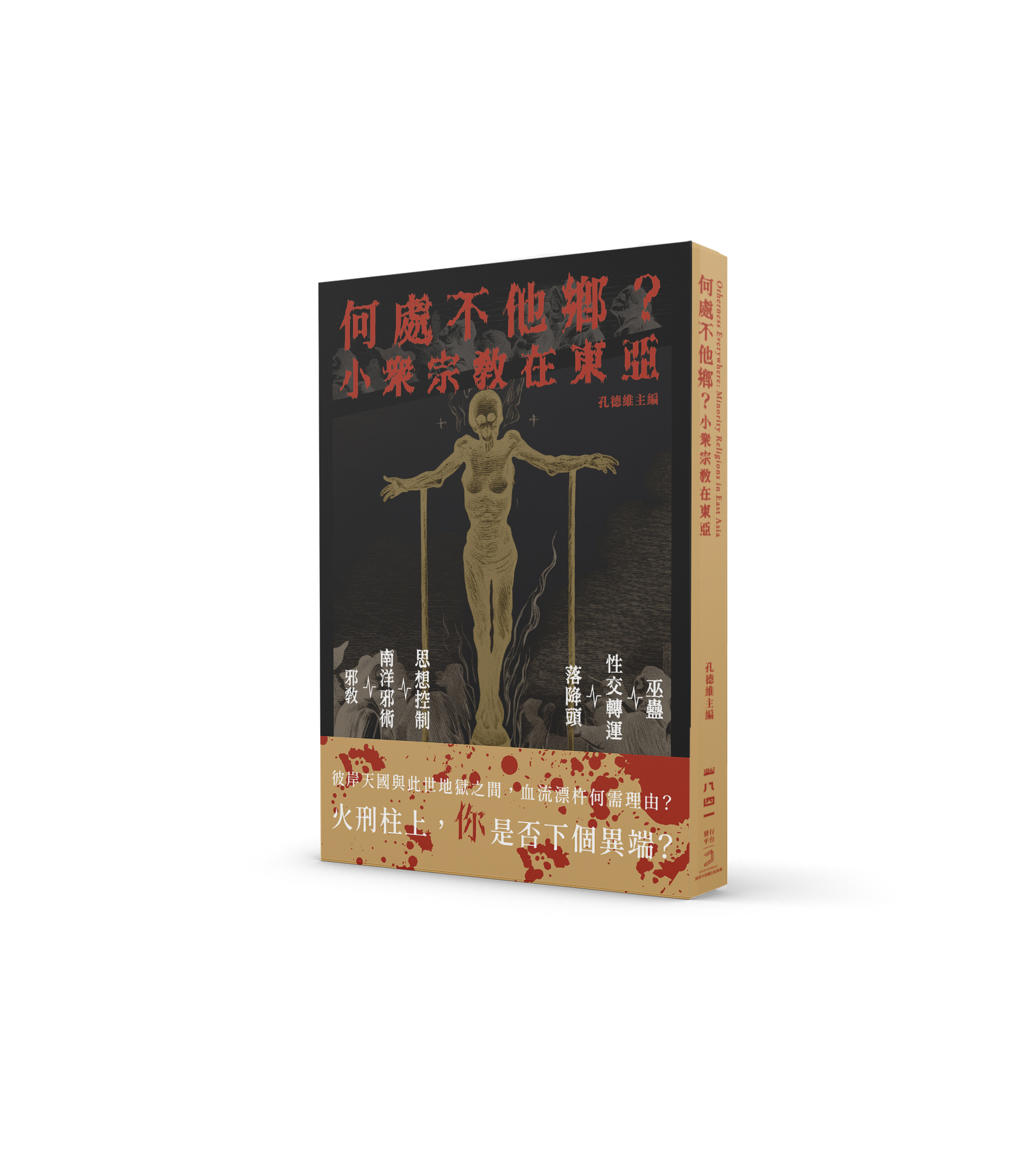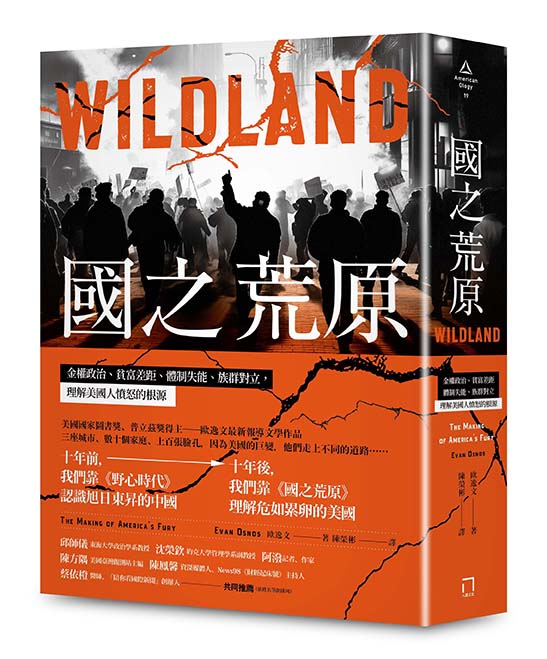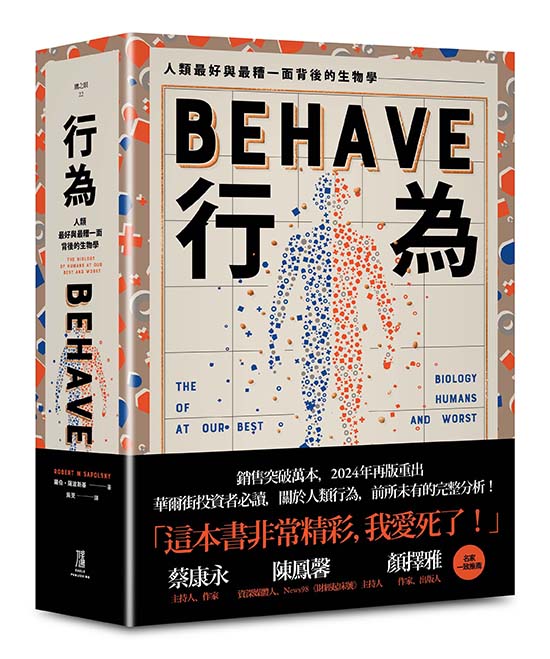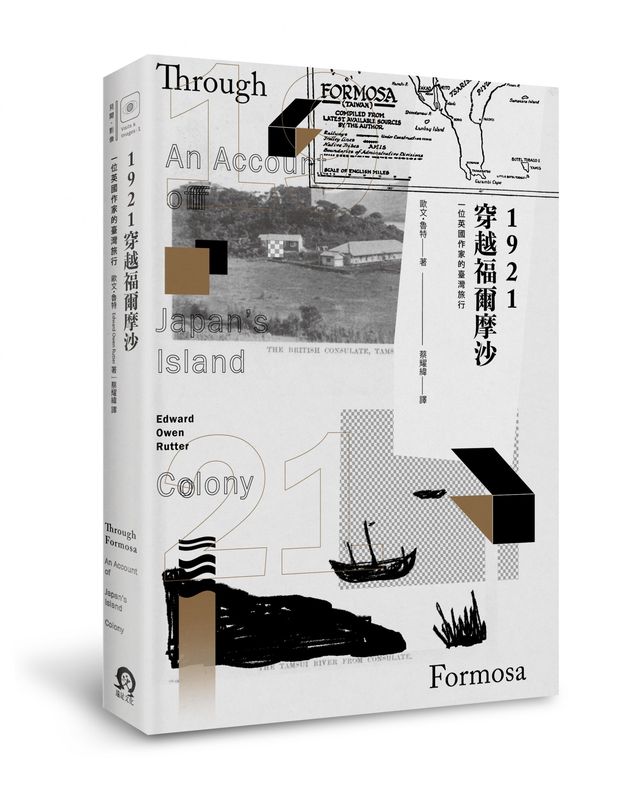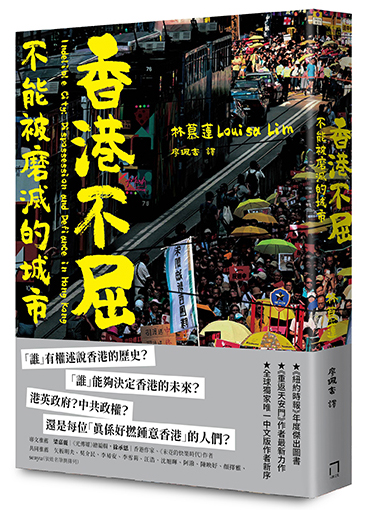曾有一個時代,記者願意捨命,只因深信「真相」能改變世界
她是英勇的傳奇,戰爭的見證者,也是堅毅而無畏的女性
戰地記者瑪麗‧柯爾文 唯一中文傳記
◆電影《私人戰爭》主角的實際人生
◆身經百戰,只為見證真實,傳遞真相
瑪麗‧柯爾文,是歐美家喻戶曉的偉大戰地記者。她曾隻身訪問利比亞狂人「瘋狗」格達費,也在以巴衝突的硝煙中與阿拉法特會面,還獲贈珍珠。她走訪戰地,無懼砲火,關注殘破世界裡珍貴的一絲人性。即使她在轟炸中瞎了左眼、左耳失聰,但仍止不住她凝視真實、報導真相的熱情,之後更以「獨眼」的女俠形象深深烙印在世人的記憶當中。二○一二年,她不幸死於敘利亞的戰火,將畢生都奉獻給了戰地記者這份職業。
在《深入絕境:戰地記者瑪麗‧柯爾文的生與死》中,瑪麗的同事琳賽・希爾遜細膩地梳理了她近乎傳奇般的經歷。她獲得獨家授權,透過研究瑪麗從十三歲起就寫下的私密日記,以及對許多親友的深度訪談,經過多方深度調查,才寫成這本動人心弦的傳記。在世人眼中,她是勇者,是英雄,是戰爭的證人,是一位堅毅而反叛的女性;在這本傳記中,讀者更能看到,她也是有血有肉、時而脆弱、時而迷惘的個人。她因為性別而受到不同的眼光和待遇,也和所有人一樣,會恐懼、會掙扎,僅有平凡的肉身,但她不曾因此卻步,直到死亡都仍體現人性與人道的精神。
本書不僅是一位非凡女性的傳記,也是二十世紀末一系列重要的國際爭端、人道危機的回顧,更可以讓我們看見:敢於深入絕境的戰地記者,曾經在國際大事現場扮演的重要傳真角色,與他們為接近真相而做的人生選擇。書中充滿了故事,也令我們重新思考新聞行業的理想、真相的價值,在今天這個資訊混亂的時代看來更令人動容。透過瑪麗‧柯爾文的一生,或能喚起「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新聞」的省思。
★《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編輯選書
★科斯塔圖書獎(Costa Biography Award)入圍決選
★安德魯‧卡內基優秀獎章(the Andrew Carnegie Medal for Excellence)入圍
★《君子》(Esquire)雜誌與《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2018年度最佳書籍提名
★《衛報》(Guardian)11月書店選書與《星期日標準報》(Evening Standard)11月書單
★ 亞馬遜(Amazon)11月最佳書籍,讀者4.6顆星高度讚譽評價
戰爭不曾發生,除非有人將它帶到你的眼前。瑪麗‧柯爾文,大半生都投入這樣的志業,甚至死在採訪的戰火之中。《深入絕境》不僅是這個知名戰地記者的傳記故事,也透過其經歷敘事讓我們看見她所經驗的戰爭,而她又為何將自己的生命投擲於此。值得注意的是,本書作者琳賽‧希爾遜是瑪麗‧柯爾文相識十餘年的同行,一樣在烽火中堅持真相傳遞,因此,閱讀這本書時,我感覺到的是,這次,她藉著自己的筆所傳遞的,除了瑪麗‧柯爾文冒險得來的報導,還有她從立志當記者開始的學習、思考、方法與實踐。瑪麗柯爾文雖然不在這個世界上,但透過她的報導與被紀錄下來的這一切,她得以繼續活著。而我們都因此而得以學習──如何當一個記者。
──轉角國際專欄作者 阿潑
每個記者作為社會的一分子,身上總是不免帶著時代的印記。柯爾文是一個感性的人,也因為這樣,她會在報導伊拉克戰爭時犯下錯誤。而我一直認為,雖然沒有一個記者能夠做到絕對客觀中立,但是記者需要理性和冷靜,將個人價值偏好和工作區分開來,這樣才能避免因為情感上的偏好,而犯下判斷錯誤。但是同一時間,我也認同柯爾文一直的堅持:記者需要為弱者發聲。要擁有這樣的情懷,才不會對社會不公無意識地視而不見。
在這本書裡面,柯爾文是一個希望能夠平衡事業和家庭的女性,但是最終沒能做到。而這正是很多女性記者,尤其是採訪戰亂和衝突的女性記者所面對的問題。研究顯示,大部分報導戰地的女性記者處於單身狀態,而且和報導戰地的男性記者相比,她們的學歷以及情緒控制能力更高,顯示女性跨入的門檻,要比男性高得多。柯爾文的那個年代,女性要在這個被視為男性的領地站穩腳跟,獲得尊重,她付出的,要比現在的女性記者多得多。但正是因為有她這樣的一批打破了男性壟斷的人,才使得後來者,可以將很多機會視為理所當然。
我喜歡這本書,展現了柯爾文的立體形象。她不再僅僅是一個戰地女記者。她之所以堅守在她的崗位,是因為她的價值觀,她的性格,她對這份職業的了解,她對這個社會的承擔。
──前戰地記者 閭丘露薇
本書非凡地描繪了一位記者的無畏與最終注定的犧牲奉獻……多虧了希爾遜的報導深厚以及熱情洋溢寫就此書,讓瑪麗‧柯爾文完全獲得她應得的評價。
──約書亞‧哈默(Joshua Hammer),《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這本傳記由希爾遜所寫,她認識柯爾文本人,也使用了未出版的報告和多達三百本的私人日記為材料,全書十分能掌握傳主的精神。
──瓊‧李‧安德森(Jon Lee Anderson),《紐約客》(The New Yorker)
宏偉而動人……[希爾遜]捕捉到柯爾文一生中最極致衝擊之處。
──吉爾‧多蒂(Jill Dougherty),《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希爾遜以欽佩之情與同情的理解,描繪了她的同事……記者們渴讀希爾遜這本書,但其他人會嗎?答案是肯定的:憑藉瑪麗的故事,希爾遜打開了許多人不曾窺見的大門。
──艾德‧維利米(Ed Vulliamy),《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深入絕境》是我這幾年來讀過最好的傳記。
──克特‧施萊爾(Curt Schleier)《,明尼亞波里斯明星論壇報》(Minneapolis Star-Tribune)
這是我讀過的關於記者最好的傳記之一。
──查爾斯‧格拉斯(Charles Glass),《攔截》(The Intercept)
一本精彩的書──無疑是一份致敬,同時也講述了一段非凡的傳奇生命。
──簡‧邦納姆‧卡特(Jane Bonham Carter),《週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
琳賽・希爾遜(Lindsey Hilsum)
琳賽・希爾遜是英國第四台新聞的國際編輯。她曾報導過去二十五年來眾多重大衝突和國際事件,包括在敘利亞、烏克蘭、伊拉克和科索沃的戰爭;阿拉伯之春;和盧安達的大屠殺。她的作品散見《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衛報》和《格蘭塔》(Granta)。她的第一本著作《沙塵暴:革命時代的利比亞》(Sandstorm: Libya in the Time of Revolution)曾進入二○一二年衛報首作獎(Guardian First Book Award)的決選名單。
黃楷君
政大阿拉伯語文學系、廣播電視學系畢業,曾任出版社編輯,現為書籍譯者。譯有《手寫時代》、《穆罕默德:宣揚謙卑、寬容與和平的先知》、《時光出土:考古學的故事》、《原始富足》、《漁的大歷史》等書,並曾合著《吹過島嶼的歌》。
kaichunhg289@gmail.com
前言
我們生活的方式,
無論膽怯或無懼,
皆將成為我們的生命。
──謝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
那晚,在貝魯特(Beirut)的晚餐時間只有一個話題:是否該找人口販子偷渡我們通過邊界,進入敘利亞和遭圍攻的霍姆斯鎮(Homs)。當時是二○一二年的二月,革命正演變成內戰。希望推翻敘利亞政府的叛軍,正堅守在鄰近霍姆斯的巴巴阿姆爾(Baba Amr)地區。同一時間,總統巴夏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的軍隊以火砲猛烈轟炸當地。
我們四人已經在記者生涯中冒過許多次險。吉姆・穆伊爾(Jim Muir)從一九八○年代初便擔任BBC的中東記者,儘管蒙受綁架的威脅,仍居留黎巴嫩數年之久。尼珥・麥法夸爾(Neil MacFarquhar)童年時在利比亞長大,受《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派駐中東。我曾報導過盧安達(Rwanda)、伊拉克、利比亞和另外十多個國家的衝突事件。此外還有《週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的瑪麗・柯爾文。她的左眼戴著一只眼罩,那隻眼睛在十年前,被斯里蘭卡政府士兵投擲的一顆手榴彈擊中,因此失去視力。一九九九年,配備槍枝和彎刀的民兵進逼東帝汶的聯合國駐區,即便多數其他記者都搭上最後一班飛機離境,瑪麗拒絕離去。同一年的冬天,她在俄國人轟炸道路時,於車臣的嚴寒山區瀕臨死亡。她總是一次次更加深入當地,也一次次待得更久。
不僅巴巴阿姆爾的轟擊毫無間斷,人口販子還可能綁架我們勒索贖金,或轉賣給聖戰士。對我們三人來說,這已經超越所能承受的危險底限,但瑪麗不以為意。「無論如何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她說。於是就這麼決定了。她將進入戰地。十五個月前,我人在倫敦的聖布里奇教堂(St Bride’s),也就是艦隊街(Fleet Street)上的記者教堂,當時瑪麗在年度禮拜上發表演說,紀念當年喪生的同業。「我們總是必須自問,新聞值得我們承擔多高的風險。」她說。她高高站在讀經臺上,瘦削的身軀罩著一件黑色針織洋裝,眼鏡架在鼻子上,好用她那隻僅存未盲的眼睛讀稿。「什麼是勇敢,而什麼又是逞能?」
當晚在貝魯特的晚餐後,我回到飯店,不安地思考著,究竟是瑪麗魯莽,還是我懦弱。我有不去霍姆斯的理由──我的膝蓋不好,有個編輯認為那趟旅程會太過危險,我還有本書要寫──但那些都只是藉口。瑪麗知道新聞所在,赴湯蹈火也要前往報導。我完成了關於黎巴嫩敘利亞難民的報導後,搭機回到倫敦。瑪麗多花了幾天安排她的行程,接著和攝影師保羅・康羅伊(Paul Conroy)踏上危機四伏的旅程,他們步行、搭乘摩托車和吉普車,甚至一度爬行通過暴雨水溝。
幾天後我收到一封電子郵件,是用衛星電話寄出的。「到巴巴阿姆爾了。這裡簡直是場噩夢,但太令人憤慨了,非常值得。我現在應該要申請伊朗簽證,但我把我伊朗門路的聯絡方式遺留在家中。你有伊斯蘭指導部辦公室(Islamic Guidance Office)那位(相較之下!)親切的女士的電話嗎?」瑪麗已經在計畫她的下一趟旅程。
當週星期六, 我讀到她關於「寡婦的地下室」的報導,和她奉為楷模的著名記者瑪莎・蓋爾霍恩(Martha Gellhorn)的任一篇戰爭報導一樣強而有力。蓋爾霍恩曾經報導西班牙內戰(Spanish Civil War)和諾曼第登陸戰(D-Day landings)。「這是個飢寒交迫的城市,砲彈的爆炸聲和陣陣砲火轟隆迴響……冰冷的雨水填滿坑洞,白雪從沒有玻璃的窗戶飄進屋內。」她寫道,「每個人的嘴上都在問著:『為什麼世界棄我們而去?』」
我以為她已經在返家的路上,但兩天後,我聽說她又回到巴巴阿姆爾。我對她感到生氣。為什麼要再次冒險呢?她寄給我一封電子郵件,說她後悔離開了,而且其他歐洲記者也在霍姆斯,所以她覺得自己也應該待在那裡。當時的情況非常緊急,她必須在星期日她的報社出刊前就發布報導。我們安排了一次Skype通話,讓她替我任職的第四臺新聞(Channel 4 News)做段訪談。我們在訪談開始前聊了幾句。
「琳賽,這是我們見過最糟的情況了。」
「我知道,但妳打算怎麼從那裡脫身?」
她停頓了一會。
「就這樣了。我也不曉得。我還在安排。」
隔天早晨,我醒來時想起一位在巴格達(Baghdad)被綁架撕票的朋友。瑪麗也可能遭遇這樣的不測,我心想。我在上班途中的公車上,接到一位在貝魯特的西班牙友人稍來的訊息,她的記者丈夫也在巴巴阿姆爾。
「我想妳的朋友瑪麗遇上可怕的事了。妳聽說了嗎?」
*****
瑪麗死後的幾天一團混亂。有名年輕的法籍攝影師瑞米・歐希里克(Rémi Ochlik)也不幸遇害。《週日泰晤士報》竭盡全力要把保羅・康羅伊給救出來──他受了重傷,另一名法籍記者艾狄・布維耶(Edith Bouvier)也是。我把我的悲慟和掛念,灌注在廣播節目上談論瑪麗的事蹟,與為《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撰寫她的訃文。我發現自己憶起一九九八年我們初相識的情景,當時衣索比亞和厄利垂亞(Eritrea)之間的戰爭已經爆發。有十來位記者在吉布地(Djibouti),包括瑪麗和我,那是地球上最炎熱的地方。我們看上一架搖搖晃晃的烏克蘭飛機,正在將救援人員和商人從厄利垂亞首都阿斯瑪拉(Asmara)載離。當時的情況並不尋常──所有明智之人都爭先恐後離境,但有「一小群瘋子」試圖入境,他們是記者。有兩名烏克蘭飛行員同意掉頭,送我們回去。一轉眼,瑪麗和我已經走過鋪有柏油碎石的飛機跑道,路面熱得快要融化。上機後,我們坐在一塊。飛機在崎嶇不平的跑道上滑行時,我們注意到有兩個東西猛然飛越窗外──那是兩位飛行員汗濕的襯衫,他們掛在機翼上晾乾,結果忘記要穿上。我們朝敞開的駕駛員座艙門一瞧──沒錯,他們正打著赤膊開飛機。機身突然向上傾斜,堆放在前方的電視採訪設備沒有固定住,沿著走道逐漸往後滑。瑪麗和我捧腹大笑,幾乎快要從座位上跌下來。我們就像兩個女學生在課堂上咯咯笑著。這是我對她最初的印象。當然我過去曾見過她,也因為她的名聲認識她,但那是我們成為好友的時刻。我們笑得停不下來,想著自己可能會從空中墜落紅海而死。
接下來的十四年間,我們會在前往採訪途中,或在帕丁頓(Paddington)附近、特派記者經常出沒的前線俱樂部(Frontline Club)相見。她邀請我參加派對,第一次是在她諾丁丘(Notting Hill)的公寓,後來是她在漢墨斯密(Hammersmith)購入的房子,位於泰晤士河(Thames)的北岸。她穿著一襲黑色的雞尾酒會禮服,姿態優雅,調配著伏特加馬丁尼,屋子裡滿是演員、詩人、政治家和記者。隨著二十世紀末和二十一世紀初衝突事件激增,我感覺我們是共患難的死黨,就像記者團的塞爾瑪(Thelma)和露易絲(Louise)。二○○一年四月,我聽說她在斯里蘭卡中彈。我聯繫上她時,她人已經回到美國,正等著為她受傷的眼睛動手術。「我沒辦法哭,」她說,「但我需要哭,因為我不斷收到泰米爾人(Tamils)的訊息,說要捐贈他們的一隻眼睛給我。」外科醫師發現一枚長六毫米的砲彈碎片抵住她的視神經。她自那時起戴上的眼罩,成為她的代表性標誌,也是她英勇的象徵。
如今她聲名大噪,變成授獎的熱門人選,而且獲獎無數,但她卻日漸消瘦、性格乖僻。我在二○○三年美國入侵後的伊拉克見到她時,她臉上的皺紋似乎更加深了。某個在倫敦的晚上,我們在一群人權運動人士的觀眾面前共同演講。觀眾席中有位認真的年輕女性提問,想知道我們是如何處理報導衝突事件後的創傷。這是個前往戰區採訪的特派記者都討厭的問題──我們真的有必要在某個星期四晚上,在一整個講堂的陌生人面前,坦露我們的心靈狀態嗎?瑪麗和我互使了眼色。
「琳賽和我,我們兩人會去酒吧喝酒。」她用她從未改變的東岸口音,慢聲慢氣地回答,而我們咯咯笑了起來。
有時候事情沒那麼好笑。某次我在倫敦安排了一位伊朗社運人士的採訪,她兩小時後才姍姍來遲,而且還喝醉了,令我勃然大怒。後來我原諒了她,這是當然的,因為所有人都會原諒瑪麗──她擁有一種個人魅力,當你認為她把你看作好友時,會感到雀躍不已。我認識她的方式相當簡單,就如同你認識某個同樣因患難和倖存而心有戚戚的朋友,譬如炸彈在你離開後立即爆炸,或擊中道路另一端的空大樓,而你只差幾碼的距離或幾分鐘就會遇難。對於她的黑暗面,我僅略知一二,如她幾次破裂的婚姻,以及我知道深深折磨她的創傷後精神壓力。
在她逝世後的那週,我找到一張二○○二年的照片,那是她失去一眼視力的隔年。照片裡我們兩人身在傑寧(Jenin)的巴勒斯坦難民營的瓦礫堆中,難民營剛剛慘遭以色列的推土機摧毀。相片裡的瑪麗穿著淡藍色的丹寧襯衫和灰色牛仔褲,眼罩蓋在她的左眼上,一手拿著筆記本,一手拿著筆。我身穿紫色襯衫和深藍長褲。我們看上去滿身灰塵,疲憊又快樂。而那正是我們當時的感受,在一股記者取得新聞的強烈渴望下團結齊心,也很高興遇見彼此。那次相遇留下的幾張照片,是我僅有的兩人合照。
我認識她的時間匆忙而短暫──比如在的黎波里(Tripoli)的晚餐、通過約旦河西岸地區(West Bank)的顛簸車程、在耶路撒冷一起喝酒──如今她卻已離開人世。我對許多關於瑪麗的事一無所知,無論是她對我隱瞞,或我選擇不看的事情。是什麼驅使她在職業和私人生活,都走向這樣的極端?是勇敢抑或魯莽?她是我們世代最受敬佩的戰地記者,她的私人生活也因衝突留下傷痕。而雖然我把她視為好友,我對她的認識卻如此微不足道。
悲慟的情緒沉澱之後,我總是時時想起她。她永遠都在那裡,她的鬼魂激勵我去發掘一切我在她生前錯過的點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