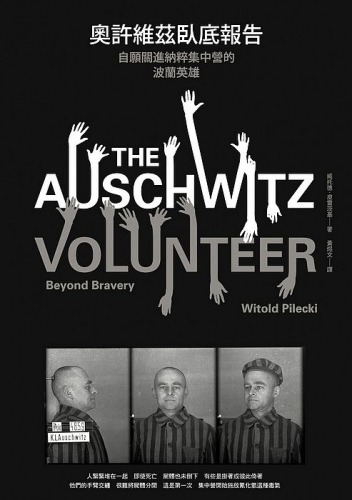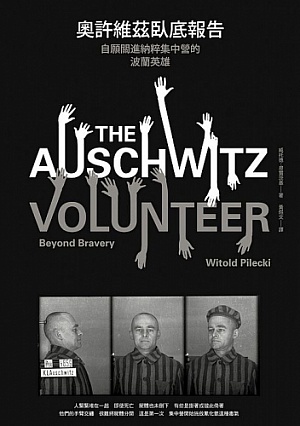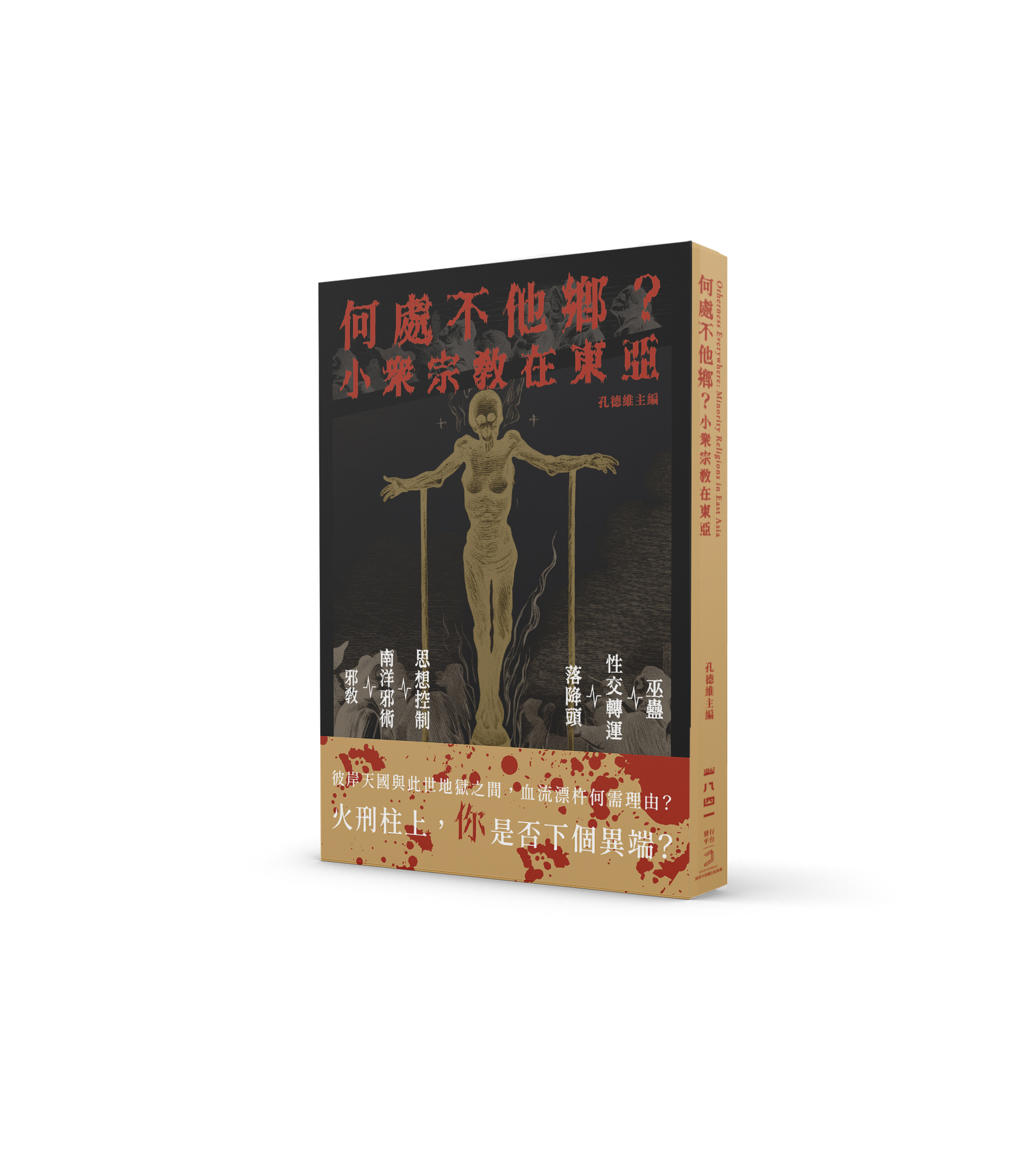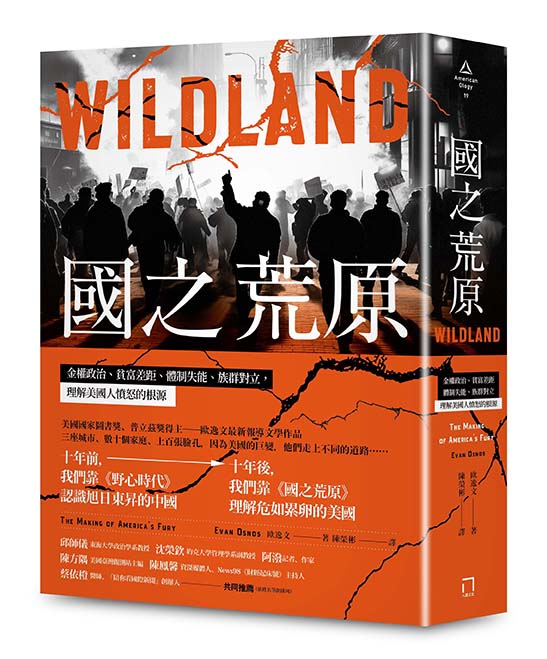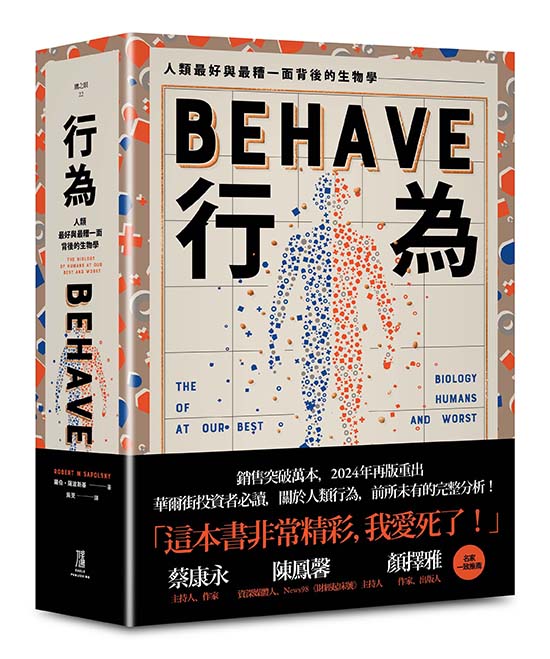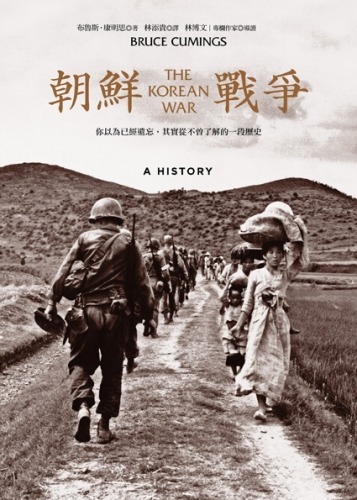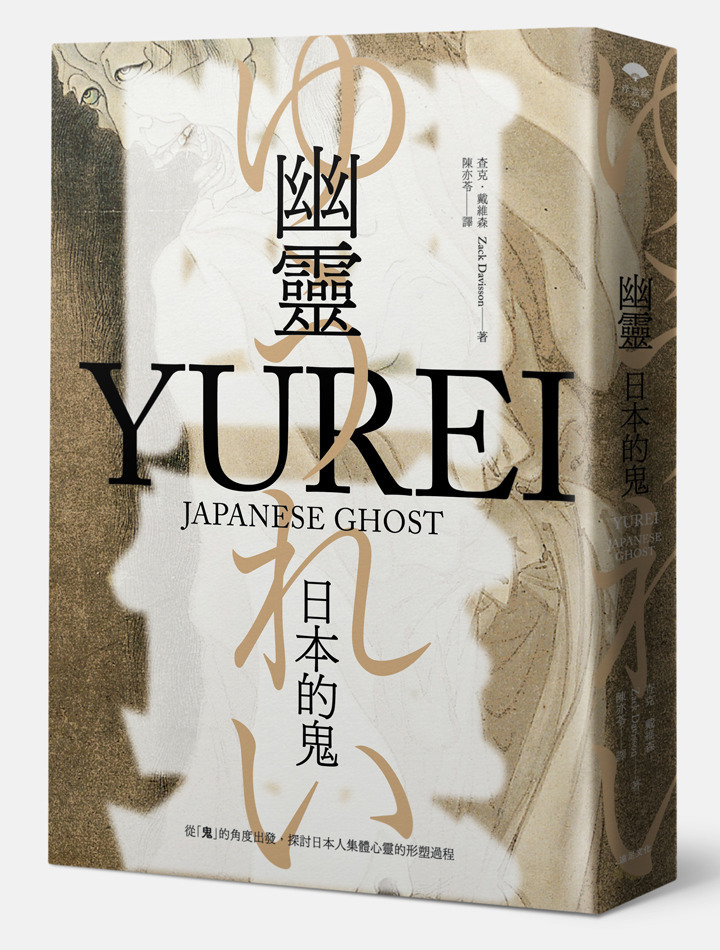作者:諾曼.戴維斯(Norman Davies),英國國家學術院
皮雷茨基其人
一九○一年五月十三日(舊曆四月三十日),威托德.皮雷茨基生於歐洛內茨(Olonets)一個愛國的波蘭家庭裡。歐洛內茨是卡雷里亞(Karelia)的小鎮,鄰近芬蘭邊境,屬俄羅斯帝國管轄。早在十八世紀末,波蘭就已經遭俄羅斯、普魯士與奧地利三國瓜分。皮雷茨基在維爾諾(Wilno,今維爾紐斯[Vilnius])與歐柳爾(Oryol)受教育,因此他年輕時對於被俄羅斯禁止的波蘭陰謀組織已司空見慣,包括波蘭童軍運動。他後來參與了軍事作戰,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年的波蘭布爾什維克戰爭中對抗布爾什維克分子。
一九二一年,由於缺乏資金,皮雷茨基不得不放棄在維爾諾(位於剛獨立的波蘭境內)的史帝芬巴托里大學(Stefan Batory University)美術系的學業,轉而加入國家安全協會(Związku Bezpieczeństwa Kraju)。國家安全協會是個半志願性組織,他在這裡待了幾年時間。皮雷茨基才華洋溢,他會寫詩、畫畫與彈吉他。一九二六年,他奉派到第二十六輕騎兵團,並且晉升為後備騎兵少尉。他一直維持這個軍階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當時他還在奧許維茲集中營裡,但還是晉升為中尉(一般來說,家鄉軍不會對身陷集中營的人進行晉升,這回算是破格)。一九四四年二月,皮雷茨基晉升為騎兵上尉,這也是他最後一次晉升。
一九二○年代,皮雷茨基接管家中小小的地產,他們家的地產位於今日的白俄羅斯。一九三一年,皮雷茨基娶了當地的小學老師瑪莉亞.歐斯特羅夫斯卡(Maria Ostrowska)為妻 ,生了兩個小孩。皮雷茨基對軍事很感興趣,他曾組過一支志願性的騎兵部隊,這支部隊最後被編入正規軍,投入戰場。一般猜測,皮雷茨基在一九三○年代曾為軍方的情報單位或反情報單位工作。
皮雷茨基與他那個世代的許多波蘭人一樣,是擁有強烈愛國心的天主教徒,他在情感上與皮烏蘇茨基元帥(Marshal Piłsudski)的許多觀點一致─皮烏蘇茨基元帥是波蘭實質上的領袖,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他去世為止。皮雷茨基雖然不是特別關心政治,但他可以體會元帥的感受。皮烏蘇茨基對於戰間期波蘭的政治人物與混亂的民主過程深感挫折。
德軍入侵波蘭前夕,波蘭於一九三九年八月開始動員,皮雷茨基所屬的騎兵部隊隸屬於第十九步兵師,該師於九月六日遭德軍擊潰。皮雷茨基於是繼續與其他部隊奮戰到十月十七日,此時蘇聯早已入侵波蘭,華沙陷落,波蘭流亡政府在巴黎成立。他的部隊也就此解散。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皮雷茨基與其他陸軍軍官及幾個平民,一起成立地下軍事反抗組織:波蘭祕密軍(Tajna Armia Polska)。祕密軍的成立原則是愛國主義與基督宗教,沒有特定的政黨屬性,人數成長到八千至一萬兩千人左右。一九四一年年底,祕密軍併入武裝作戰聯盟(Związek Walki Zbrojnej)。一九四二年,武裝作戰聯盟改名為家鄉軍(Armia Krajowa)。
皮雷茨基為了執行波蘭地下組織的祕密任務,自願被德軍逮捕,送進奧許維茲集中營裡。一九四○年九月,他逮到機會,趁德軍在華沙街頭搜捕囚犯時,趁機混到隊伍裡面。九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二日夜裡,他抵達奧許維茲,屬於第二批(第一批在八月出發),他還冒用托馬什.塞拉芬斯基(Tomasz Serafiński)這個名字─塞拉芬斯基真有其人,但皮雷茨基不認識他,此人的身分證件遺留在華沙的「安全屋」(safe house)裡。塞拉芬斯基曾待過安全屋,皮雷茨基也使用過這兒。儘管集中營的處境恐怖,需要持續地警醒求生,但皮雷茨基還是很快找出了被囚的祕密軍成員,做為新組織的核心。
以祕密軍為範例,皮雷茨基在奧許維茲成立的軍事組織聯盟依據的是「小單位」原則,或他自己取的名稱「五人小組」(有時「五人小組」不只五人)。「五人小組」彼此獨立行動,如此當德軍抓住某些成員時,即使遭受拷問,也不可能將整個組織招出來。「小單位」會再招募其他的「五人小組」,而這些「五人小組」又會繼續招募其他的「五人小組」。皮雷茨基在一九四○年十月建立了最早的五人小組,他稱之為「帶頭五人」。
皮雷茨基什麼時候設立第二個「帶頭五人」,這裡面存有爭議。一九四三年六月,就在他逃亡後不久,皮雷茨基說時間是一九四○年十一月;不過在一九四三年年底以及在一九四五年,他又說時間是一九四一年三月。然後在一九四一年五月設立第三個「帶頭五人」,同年十月設立第四個,十一月設立第五個。這些「帶頭五人」的成員是哪些人,皮雷茨基自己的紀錄與其他資料寫的都不一樣。然而,他的組織結構終究起了效果,皮雷茨基一直未被舉發,集中營當局一直不知道他是軍事組織聯盟的主要組織人。
軍事組織聯盟設立之後,立即將奧許維茲的情況回報給波蘭地下組織。一九四○年十月,皮雷茨基的第一份報告藉由獲釋的犯人攜出,最後於一九四一年三月送到了位於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事實上,許多的訊息,如蘇聯戰俘在奧許維茲遭到不人道的對待,以及德國開始在比爾克瑙(Birkenau,波蘭語為布澤辛卡〔Brzezinka〕)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都是由皮雷茨基的組織提供給集中營外的波蘭當局,然後再由波蘭流亡政府將這些訊息告知其他盟國。皮雷茨基在訊息中要求波蘭地下組織進攻奧許維茲,但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皮雷茨基除了從事軍事與自助工作,強調不帶政治立場的他也在一九四一年組織了政治委員會,容納集中營裡各黨派的人士:鑑於戰前難以解決的政治分歧與集中營裡既有的分裂現實,皮雷茨基能成功組成委員會確實是了不起的成就。然而,還是有一些囚犯指控他這麼做不過是為了滿足自我的欲望(一個相當不合理的指控),皮雷茨基於是把軍事組織聯盟的指揮權交給武裝作戰聯盟/家鄉軍的指揮官卡奇米爾茲.拉維奇(Kazimierz Rawicz)中校,此人在集中營裡化名為楊.希爾克納(Jan Hilkner)。
由於有太多優秀的波蘭人被送往別的集中營,而波蘭地下組織又對於他的請求充耳不聞,皮雷茨基於是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利用烘焙麵包的時候與其他兩名囚犯逃亡成功,他打算親自向當局提出請求。當地的家鄉軍指揮官對於他的故事半信半疑,因此不願接受他的請求前去攻打集中營解放犯人。
皮雷茨基後來在華沙的家鄉軍最高指揮部工作,他成為反共臥底地下組織「獨立」(Niepodległość)的成員,這個組織在紅軍抵達時進行運作,而他也在一九四四年華沙起義中有不凡的表現。 皮雷茨基後來又被德軍俘虜,關進蘭斯道夫(Lamsdorf)與穆爾瑙(Murnau)戰俘營,之後他加入了在義大利的波蘭第二軍。他在那裡寫下一九四五年報告,並且開始從事他在波蘭的最後一場絕命任務。
* * *
人在集中營的皮雷茨基以極其驚人的專注力進行任務。他經常談到朋友,卻從未提過自己的妻兒,而從報告中我們也無從得知他在集中營時他的妻兒人在何處,也不知道他在逃亡後是否曾見過他們。他提到家人時,也只是收發包裹這類的瑣事,或是擔心他的親戚會將他贖出來,因為他仍需在集中營裡建立抵抗運動的網絡,而他有時會寫信給家人。
為了進行波蘭的國家生存鬥爭,皮雷茨基不得不面對可怕的道德兩難,其他擁有家庭卻選擇加入抵抗運動的人,也同樣面對此一困境。他們是否該參與一場可能危及家人性命的行動?當然,這當中沒有正確解答,而坐在安樂椅上以事後諸葛的眼光回溯這段歷史的我們,顯然沒有資格評斷他們。他們面對當時的處境,已經盡力做了最好的選擇,我們在提出問題之前,應該以讚揚的角度看待他們。你以為他們只是壓低帽沿,走在渺無人煙的寧靜小徑上而已嗎?
皮雷茨基從事的任務困難多了。事實上,一旦他自願進入奧許維茲,準備在集中營裡組織抵抗運動,他便不可能過著平靜安詳的日子。而這項任務也引領他走向人生的悲劇巔峰,雖然這不在報告的範圍之內,但卻是瞭解皮雷茨基這個人所不可或缺的部分。
二次大戰之後,皮雷茨基與絕大多數波蘭人一樣,反對蘇聯在波蘭強加的無神共產黨政權。因此,一九四五年,皮雷茨基一方面與波蘭境內的反共抵抗組織聯繫,另方面也把波蘭的狀況回報給英國指揮下的波蘭第二軍指揮官弗瓦迪斯瓦夫.安德斯(Władysław Anders)將軍,他此時是西方的波蘭領袖。皮雷茨基的妻兒在波蘭,他也能夠時時去探望他們。安德斯認為共產黨當局已經將矛頭指向皮雷茨基,於是命令他離開波蘭,然而皮雷茨基並未理會這項命令,終於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八日被捕入獄。在獄中,他飽受波蘭祕密警察的折磨拷問,當家人到獄中看他時,皮雷茨基說,與這裡相比,奧許維茲實在是兒戲,蘇聯訓練出來的波蘭人實在是心狠手辣。
皮雷茨基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並準備對波蘭祕密警察成員發動武裝攻擊。皮雷茨基否認這些指控,但軍事法院依然判他死刑,並於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晚間在華沙拉科維奇卡街的莫科托夫監獄,由他的波蘭同胞將他處死。
很難想像有比皮雷茨基的人生終點更可怕的結局。對此,聖保羅寫給聖提摩太的信中有幾句話很適合做為皮雷茨基的墓銘: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皮雷茨基的長眠之處不知位於何地。他在一九九○年代得到平反,現在已成為波蘭的英雄人物。
【選自一九四一年】
德國與布爾什維克戰爭的爆發(一九四一年六月),除了讓我們長久期待的心情獲得滿足與喜悅,眼下對集中營來說似乎沒帶來多少改變。
一些親衛隊員開赴前線。取代他們的是老年人。
直到一九四一年八月,這場新戰爭才影響我們,與其他事情一樣,它帶來的是恐怖的回音。
第一批布爾什維克戰俘,這個時候還僅限軍官,他們被帶進集中營,大約有七百人被關進第十三區(新分區的第十一區)的一個房間裡。房間裡人擠人,連坐的空間都沒有,然後就把房間封起來(我們當時還沒有毒氣室)。
同一天晚上,一群德國士兵在一名軍官率領下抵達營區。
德國隊伍進到房間裡,他們戴上防毒面具,然後丟了一些毒氣罐在房裡,並且觀察結果。
擔任護士的同志第二天去清理屍體,他們說那是一幅恐怖的景象。
人緊緊堆在一起,即使死亡,屍體也未倒下,有些是掛著或彼此倚著。他們的手臂交纏,很難將屍體分開。
從他們的制服,以及施放毒氣時的隊形來判斷,這些人一定是布爾什維克的高階軍官。
這是第一次,集中營開始施放氰化氫這種毒氣。
最早告訴我這件事的人是十九號。
這件事令他感到十分苦惱,他很快就得出結論,這種做法遲早會用在其他人身上,或許就是囚犯。
當時,這看起來仍不太可能。
在此同時,集中營又開始除蝨(一九四一年夏天),之後,所有木匠都被分到相同的營區:第三區一樓。
我們分配到雙層床鋪,因為這時幾乎整個集中營,一區接著一區逐步換成雙層床鋪。
這給予了管理人員與親衛隊員取樂的機會。
新床鋪整潔的維護比在軍官學校更為嚴格,因此出現更多的羞辱與毆打。
然後(九月),有些木匠(包括我)搬到了第十二區(新分區),十月,又搬到第二十五區(新分區,原本的第十七區)。
就是在這裡,十一月時在第二十五區,我在早點名前走到營區前面,刮面的冷風加上雨雪,令人很不舒服,此時我看見了驚人的景象。
我看見,在雙重鐵絲網牆的另一邊,距離約兩百步,有一群完全赤裸的人排成百人隊的隊形。同樣是二十人一排,共分五排,德國士兵用槍托催促著他們快快排好。
我數出有八個百人隊,但隊伍前頭已經擠進建築物的門口,也許有數百人已經進到建築物裡。
他們進去的建築物是火葬場。
這些是布爾什維克的戰俘。
我日後得知,這裡超過了一千人。
顯然,人可以一直保持天真,直到死那天為止。
當時我以為他們是在發內衣與衣物給戰俘,只是搞不懂為什麼要在火葬場,以及為什麼要利用火葬場裡寶貴的工作時間來發放這些物品。我們的同志一天三班二十四小時不斷在火葬場工作,已經趕不上囚犯死亡的速度。
原來,直接將他們帶到那裡,目的是為了節省時間。
大門關上。
從上方丟進一到兩個毒氣罐,然後將扭曲的屍體快速丟進已經燒熱的火爐裡。
直接把他們送去火葬場,只因為一個簡單的理由,那就是奧許維茲沒有準備足夠的空間容納這些戰俘,因此上級下令盡快將這些人解決掉。
日漸擁擠的集中營裡匆促地設起柵欄,把九個營區分配給布爾什維克戰俘。
死亡營的行政單位也隨之設立。
營區發布消息,凡是懂俄語的人,可以在戰俘營擔任室長,或甚至擔任監督員。
我們的組織對於這種做法抱持輕視的態度,同時我們也蔑視提供服務協助殺害戰俘的人。當局只是樂於利用波蘭人來幫他們做這種骯髒事。
柵欄很快就建好了,布爾什維克的集中營於焉完成。
隔開集中營的柵欄,中間有一道門,上面掛了一個大告示:「戰俘營」。
我們日後發現,德國監督員與親衛隊以快速有效率的方式殺死這些布爾什維克戰俘,就跟他們當初殺死我們一樣。一九四一年年底,他們帶了一萬一千四百名戰俘入營(我從總辦公室得知這個數字),但一個冬天過後,人已經殺光了。
倖存的數十人,都是接受了齷齪的任務,在比爾克瑙集中營殺害自己的同志、波蘭人與其他國家的人。此外,還有數百人接受了游擊隊的工作,德國當局讓他們穿上制服接受訓練,給予充足的飲食,然後讓他們在蘇聯境內擔任游擊任務。
這些人住在奧斯威辛小鎮附近的軍營裡。
其餘的人則送去工作,他們必須承受毆打、饑餓與寒凍,最後死亡。
有時在晚上或早上,他們被迫穿著內衣或赤裸著站在營區前幾個小時。
一旁觀看的德國人會奚落這些來自西伯利亞的人理應不怕寒冷。
我們可以聽見這些凍死者的叫喊聲。
這段時期,我們所在的集中營變得比較輕鬆,當局不像過去那樣不斷想辦法要把我們整死,因為他們現在把所有的怒氣與精力全發洩在布爾什維克集中營裡。
集中營早期敲打鐵棒,發出「鑼」一樣的聲響(用來點名與檢閱),此時已改用鐘聲代替,鐘就掛在廚房旁的柱子之間。
這口鐘是從某間教堂搬過來的。
鐘上刻著:「耶穌,瑪麗,約瑟夫。」
過了一段時間,鐘裂了。
囚犯說那是因為它無法忍受眼前的景象。
又搬來一口鐘,很快又裂了。
然後搬來第三口鐘(教堂還有很多鐘),這回他們小心使用。這口鐘於是撐到最後。
教堂的鐘聲有時會喚起許多情感。
有時候,我們在晚點名看著傍晚的景色,若不是殺人的氣息籠罩著我們,相信那會是個令人陶醉的景象。
落日餘暉為天空與雲朵染上絢爛的色彩,然後集中營的警報聲響起,發出恐怖的嗚咽聲,警告所有哨兵不可擅離外安全區的瞭望塔,因為有一兩名人犯失蹤了。
這對我們是個不祥的警告,因為接下來每十名囚犯要挑一人出來受死。而就算不做「死亡選擇」,「懲罰檢閱」也會讓人曝露在寒凍之中,必須忍受冷至骨髓的痛苦。
或者,有時候,我們像禮兵一樣站著,彷彿向受害者致敬似的。他的手被綁住,在絞刑臺旁等待,然後上了套索……突然間,現場一陣死寂,遠方傳來撫慰人心的鐘聲。某個不知名的教堂正在敲鐘。
那鐘聲感覺貼近內心,卻又遙不可及……因為,那是從集中營外頭的世界傳來的……
外頭的人生活、祈禱、犯罪;只是不知他們的罪該如何論處,如果與集中營相比的話。
從一九四一年夏天開始,營方開始施行新的規定,對於在早晨身體不適無法工作的囚犯是否能進入醫院治療進行規範。當早晨鐘聲響起,通知所有囚犯「排成工作小隊隊形」,此時每個人都急忙跑向自己所屬的小隊;然後,虛弱、生病的人則組成一個小隊在廚房旁的庭院站著,接受護士與紀律監督員的檢查。有時囚犯頭子會親自出馬,他們會故意推撞這些犯人來測試他們的力氣。
其中一些人被送進醫院,一些人前往休養區。然而還有一些人儘管已形容枯槁,卻還是每五人一隊被送到田裡工作,並且要求他們快步趕往工作地點,光是這點就足以讓他們死在路上。
然而待在醫院與休養區的人也活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