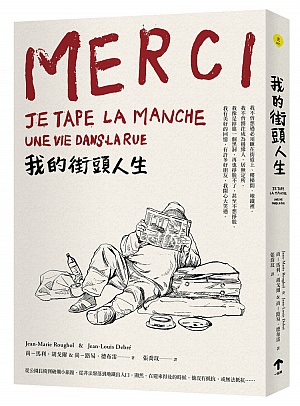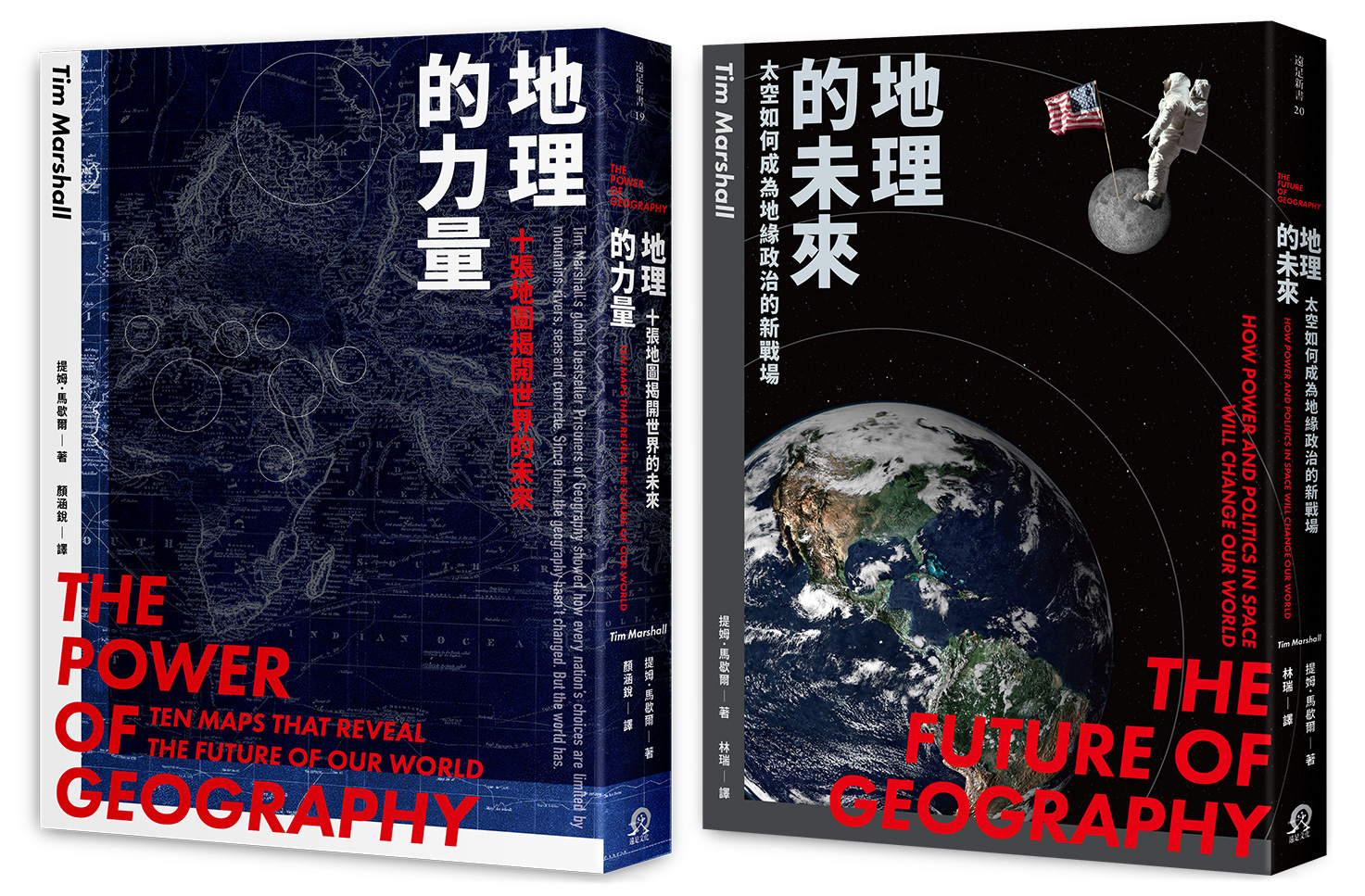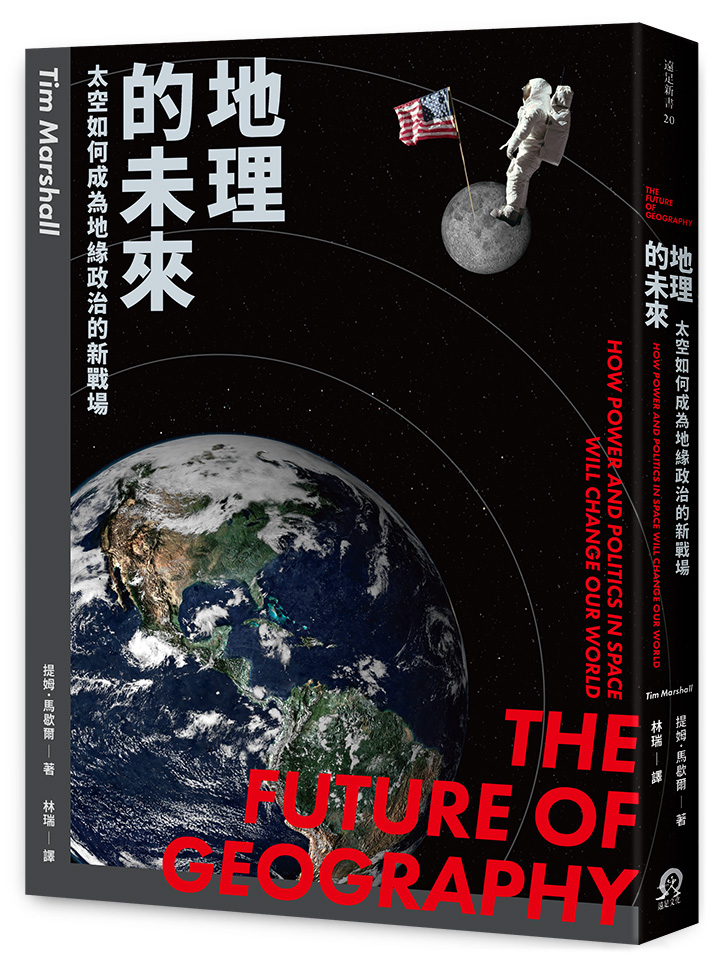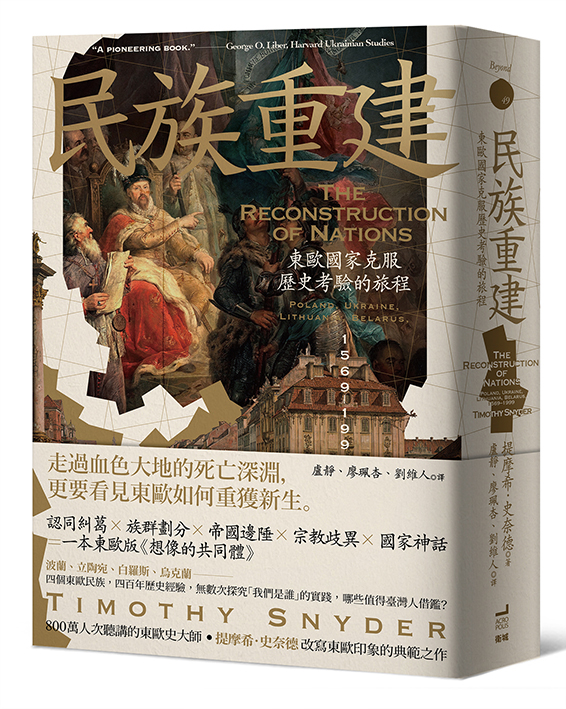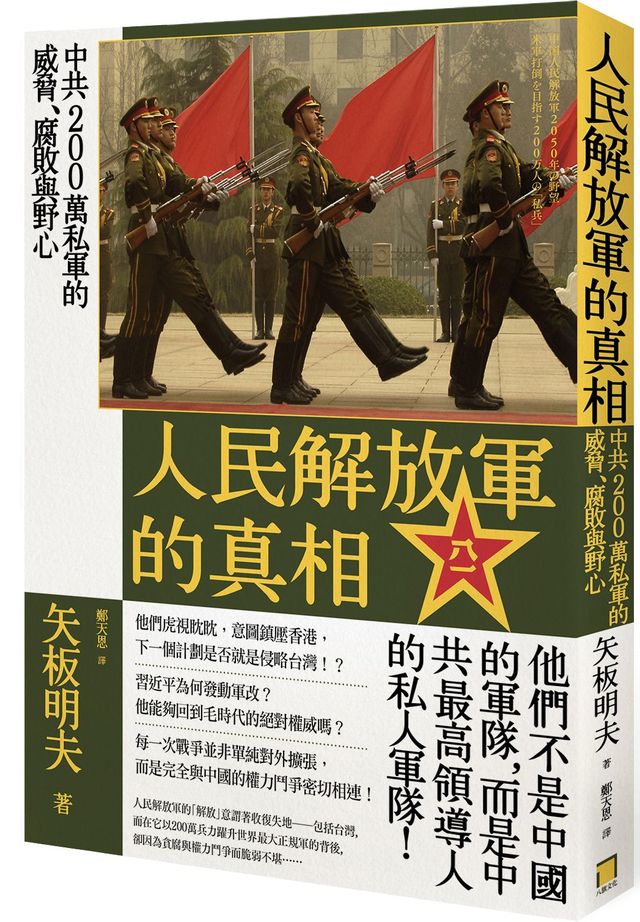前言
他不是名人,沒上過頭條,我們不住在他的世界裡。然而,我們或許曾經走過他的身邊,卻不曾稍加留意,對他視若無睹;甚至在他接近的時候,別開視線或是改道而行;也可能粗魯地朝他手一揮,叫他走開,別來打擾。
他為了餬口,為了求生,向我們搖搖紙杯,期望得到一枚銅板,一點慷慨,一個博愛的舉動。
他四十七歲,至今為止超過二十年──也就是人生將近一半的時間──都在巴黎的人行道上乞討。
現在,他流連於繁華的街區。穿梭於馬勃夫街、蒙田大道的行人,香榭麗舍劇院的常客,行經碧麗熙購物中心 、凱旋門廣場附近的人,都可能從他的身旁走過,或是見到他的身影。
然而,他並非一開始就在這些精華地段出沒。很長一段時間裡,他都在不怎麼樣的街上乞討,在地鐵站出入口或雜貨店門前度過好幾個小時,等候「朝聖者」前來。
他曾經是遊民 ,睡過街邊、地鐵走道、樓梯口,竊占過空屋,待過收容所,住過「黑心房東」 開的旅館。
他見識過夜晚的巴黎,面對過暴力,為了保護地盤而拚鬥;也在街頭結交了一些朋友,經歷了幾段患難相扶的兄弟情誼。
為了生存,他吃盡苦頭。
有個晚上,我將腳踏車停在香榭麗舍大道上的碧麗熙購物中心前。車剛上鎖,他便靠了過來,提議幫我看車,也提到他曾和我女兒在羅伯‧何森 於法蘭西體育場 上演的《賓漢》舞臺劇中合作過。
有些路人認出我來,我們在旁人困惑的注視下聊了一會兒。他們似乎很驚訝,竟然看到我跟乞丐說話,看到我將時間浪費在一個鬍子沒刮乾淨、衣著不如他們稱頭的邊緣人身上。我聽見有位男士走進購物中心之前,對女伴說:「你看到了沒?德布雷在跟那個流浪漢講話!」
這些年來,我就這樣在碧麗熙前的人行道上遇見他,聽他說話多過於對他講話。他教給我的東西,比我帶給他的還多。
有一天,我建議他把自己的故事寫下來,描述自己如何一路步向這種人生。他驚訝地看著我,沒有回答。
我很好奇,想知道他怎麼淪落到如此艱困的生活,尤其是在夜裡,或許他會嚮往另一種命運。我希望他對我敞開記憶之門,跟我談談他自己、他的家人、他街頭的朋友,打開我的眼界,把我帶入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我們通常不願意看見的世界。
人總是將自己真實的一面隱藏起來;而我們每一個人的背後總是有一段故事,一段生命旅程。我很有興趣知道這些事。
我們經常遇上複製人,卻很少碰到異人。對我而言,他就是異人。
為什麼只有名人或是自詡名流的人、政治人物,以及電視、廣播和電影明星能揭露自己的過往,親自動筆或是請人代寫他們的自傳呢?對於「回憶錄」,我總是抱持戒心──無非就是舊事重提,以及滿足那令人無法忍受的自戀情結罷了。難道無名小卒、非新聞人物,或是政壇、媒體和名流圈子以外的人,就沒有耐人尋味的事情可以說嗎?
在那之後,過了一段時間。二○一三年春天,他坦承對此提議很感興趣,他終於有足夠的意願為他的孩子們述說自己的人生。
我建議他將回憶寫在一本簿子上,除了他的經歷、遭遇,還要提及他的日常生活、他在街頭接觸到的男男女女、和他一起乞討的同伴。我囑咐他不要隱瞞任何事情。
「我沒讀過什麼書,一定會有一堆錯誤。」他很憂心地據實以告。
「那不重要,您有話要說,就不要去擔心文體、拼字還是什麼有的沒的,寫就對了。您想怎麼寫,就怎麼寫,就當您在說話,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我們再一起訂正。如果寫得好,我會找出版社出版您的故事。」我當時這樣回答。
說實話,對於自己成了這麼一號人物的「筆」,我深感著迷。
每次見到他,我都會問他這個計畫進行到哪裡了、他是不是動筆了。他總是回答有進展。我不怎麼相信,之後就不再提起這件事了。
有時是他提起這個話題:「我有進展,可是錯誤好多……」
我們的時間概念不同。我很急,他倒是老神在在。最後我把電話號碼給他,讓他寫完的時候可以打給我,然而我不抱什麼希望。
直到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那通電話響起。當時我在憲法委員會的辦公室裡,助理通知我:「有位怪怪的先生找您,說跟您很熟。他的名字叫尚-馬利,還留了個號碼請您聯絡。」
我擔心他是不是發生了什麼意外,馬上撥電話給他。最近我去了碧麗熙購物中心三趟,每次都沒見到他。我問過店門口的警衛,對方說好一陣子沒有在附近看過他。
「我寫完了!」電話一接通,他便劈頭這麼宣布,從聲音裡聽得出一絲明顯的滿足。我們約好隔天晚上七點在碧麗熙前碰面。
那天,他遞給我三大本學生用的作業簿,露出大大的笑容說:「全在這兒了!」
他話很多,顯然非常興奮。他很自豪,也有一點擔憂,不斷提醒我他沒念過什麼書,寫的故事肯定錯誤百出。為了讓他放心,我告訴他,對我而言,重點是搞清楚他過著什麼樣的生活,他為什麼要乞討,之後我們再一起讀稿子。
我讀了他的故事,然後打進電腦裡。我沒有等到全部完成,而是進行了第一本之後,就把打字稿拿給他看。
他很高興,堅持要請我喝杯咖啡來慶祝這一步。我們在馬勃夫街上一間他常去的酒吧裡談了很久。他把經常一起乞討的朋友「老外」、服務生和酒吧老闆一一介紹給我認識。他很開心也很得意,不斷告訴他們「我們正在合寫一本書」。
我多次回到他在馬勃夫街上的據點。前幾次都能感覺到他樂不可支,滿心歡喜,我很替他高興。
我們在人行道上說話的時候,一組鎮暴警察正在執行防恐巡邏任務,看見我和他在一起,隊長問我是否碰上麻煩,需要協助。
我繼續細讀他的故事。這段期間輪到他急了,主動打電話給我。他不懂為什麼我要花那麼多時間謄寫他的故事。我只要打好字,就會把完成的那幾頁交給他。他總是驚訝地盯著它們,點點頭對我說:「很好。」我提醒他還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故事才會流暢可讀,他必須進入自己的最深處,更真誠地挖掘回憶,什麼都不要隱瞞。
接下來的幾個月,我們就這樣定期一起工作。然後有一天,我克服了最初的猶豫,邀請他到皇宮 來寫作。比起在咖啡廳見面,這裡方便舒適多了。
二○一五年一月十五日的傍晚,為了我們在憲法委員會的第一次見面,他提早了至少半個小時抵達,臉上的鬍子刮得乾乾淨淨。他的眼神裡閃爍著好奇,不過顯然深受此地的莊嚴氣氛、牆壁上金燦燦的木板條、閃閃發光的美麗水晶吊燈震撼。我帶他四處參觀:皇宮花園、合議廳、宴客廳、薩瓦的瑪麗-克蘿蒂德(Marie-Clotilde de Savoie)的祈禱室、相傳拿破崙送給手下元帥的地圖桌。
我們面對面坐在我的辦公桌前,手上端著咖啡,握著筆。對我們彼此而言,這是一段難忘的時光。我審問了他很久,替故事裡的幾個段落補足細節,讓內容詳盡一點。他滔滔不絕,在記憶中搜尋任何可能勾起我興趣的事。
在第二次一模一樣的會面接近尾聲時,我把添加了新素材的稿件交給他,讓他從頭到尾重新讀一遍,更正他覺得不恰當的地方。我希望他在沒有我的情況下,獨自進行這項作業。
我們就這樣合作了好幾個月,一週又一週,定期在行政法院、馬勃夫街上的咖啡廳或是其他地方見面,修飾、深入他的故事,並增加更多的細節。我必須為自己安裝上一點耐性,因為我很快就發現到催他是沒有用的,跟隨他的步調,聽其自然比較明智。最後,他為文章畫下句點的這一天來了。在皇宮裡,我終於能大聲念出來給他聽,藉以最後一次向自己確認:我已忠實地呈現他交給我的東西。
這是他的書。
他就棲身在故事裡,這是他個人的故事。他的見證是真人實事。這本書不為譁眾取寵──我已經盡可能監督過了──它將我們拉進這些街友的日常生活之中,路人的反應經常是冷酷、帶著苛責的,但是偶爾也有意想不到的慷慨好施,而他們之間的友情真誠卻總是短暫。
這本書也告訴我們,這麼多年來,街頭世界有多大的轉變,各個幫派又是如何經營,讓乞討有方。對某些人而言,「要飯」成了一項真正的營生手段。
「街頭已經不比從前了。」他語帶懷念地向我保證。
雖然他也夢想過另一種生命,但是他這個人生由他自己來承擔。他曾經試著擺脫街頭和乞討,卻總是重返那個他所鍾愛的獨特世界。
尚-路易‧德布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