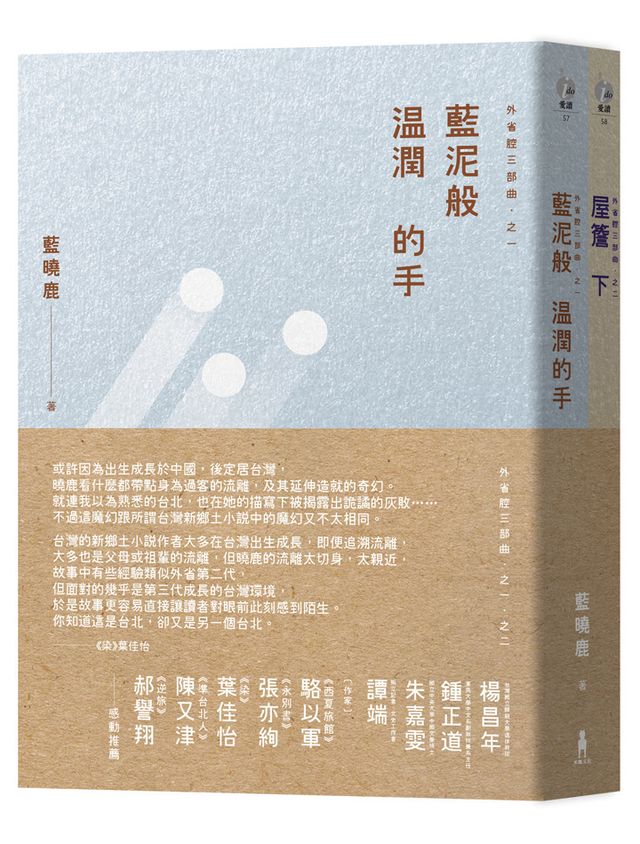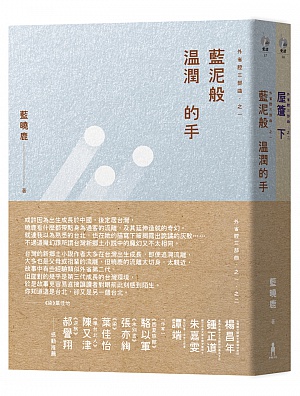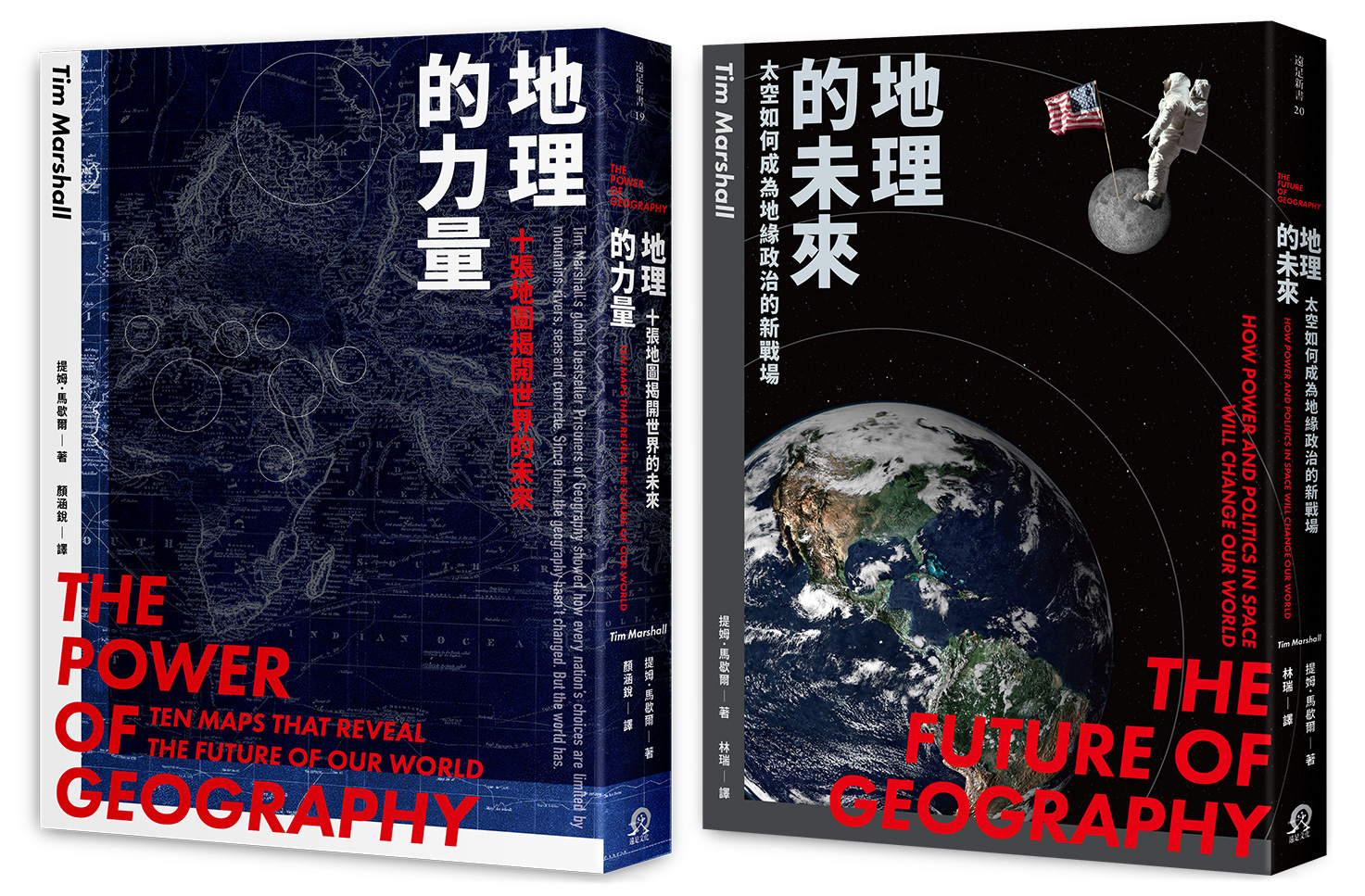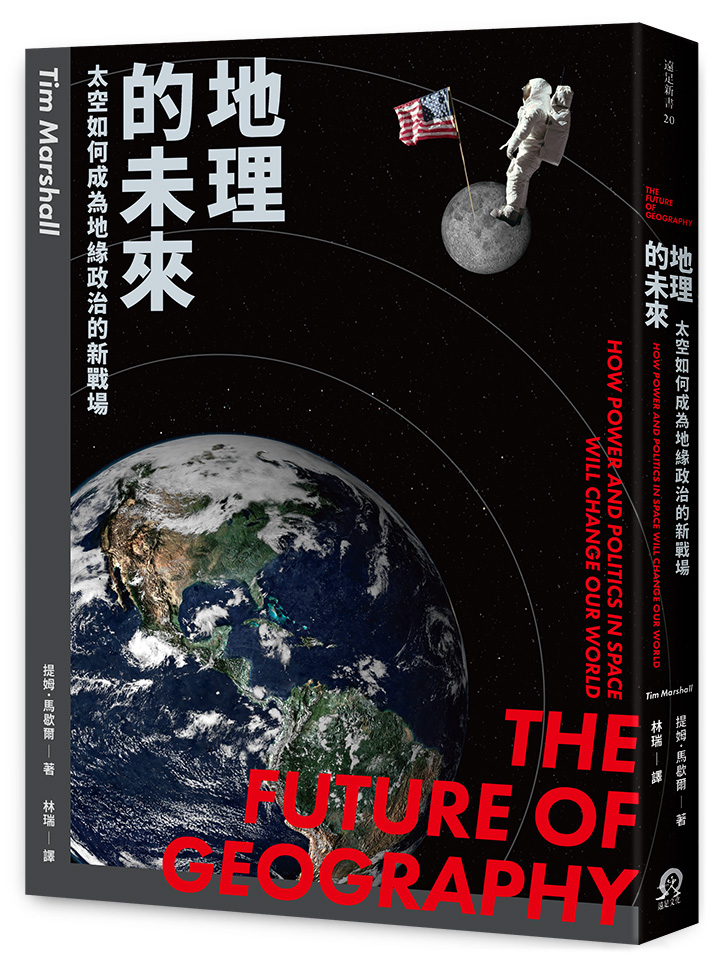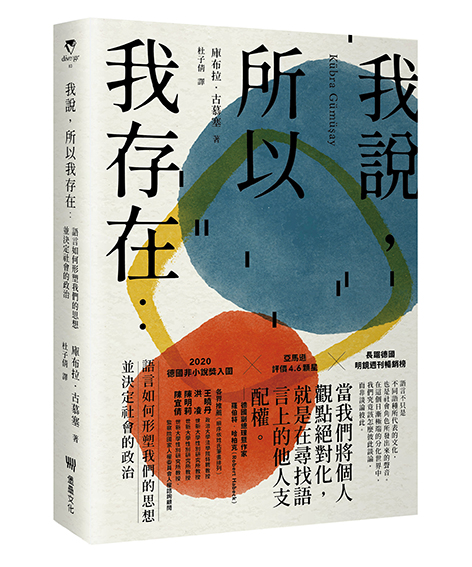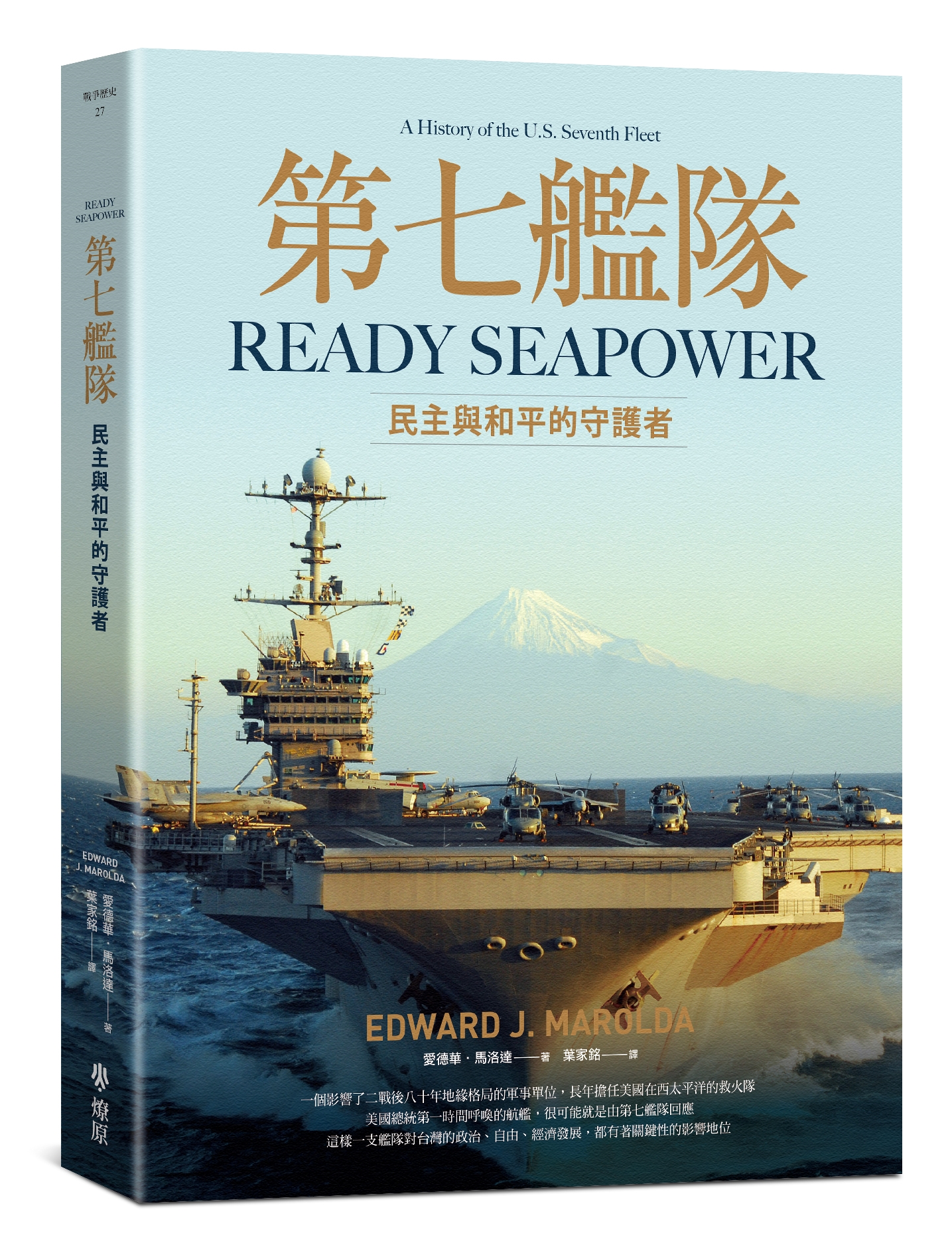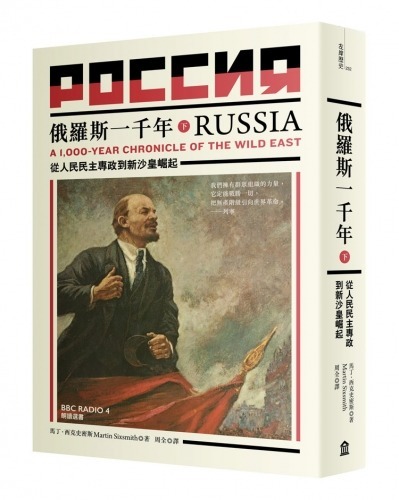《西夏旅館》駱以軍
《永別書》張亦絢
《染》葉佳怡
《準台北人》陳又津
《逆旅》郝譽翔
台灣國立師範大學退休教授 楊昌年
台灣紅樓夢研究學會會長 朱嘉雯
獨立記者、文史工作者 譚端
——感動推薦
或許因為出生成長於中國,後定居台灣,曉鹿看什麼都帶點身為過客的流離,及其延伸造就的奇幻。就連我以為熟悉的台北,也在她的描寫下被揭露出詭譎的灰敗……不過這魔幻跟所謂台灣新鄉土小說中的魔幻又不太相同。台灣的新鄉土小說作者大多在台灣出生成長,即便追溯流離,大多也是父母或祖輩的流離,但曉鹿的流離太切身,太親近,故事中有些經驗類似外省第二代,但面對的幾乎是第三代成長的台灣環境,於是故事更容易直接讓讀者對眼前此刻感到陌生。你知道這是台北,卻又是另一個台北。——《染》葉佳怡
小說最常出現的,是一些「被辜負的人」。這說的不只是個人際遇,還是在積非成是的偏見暴力中,逃竄求存的「新生者」側記:新媳婦、新住民;或兩者都是。在藍曉鹿凌厲又溫柔的字裡行間——這是又冷又爆笑的文學八點檔——峰迴路轉的親情爭霸戰底下,是家庭文明的深度病癥。看懂各式女人的苦,洞見不同男人的痛,還有結構層層的錯。人物非僅有愛有恨,也有色有性。在為德不卒的殘忍黑夜裡,小小的良心未泯恰如流星劃過。也許無人見證,然卻已是救贖。堪稱性別與離散書寫的燦爛新頁。——《永別書》張亦絢
人都有年輕的時候,夠幸運和不幸的話,也有老的時候──當男孩遇見女孩,問的如果是:「我可以買你嗎?」所謂家族,在這本書是一場殘酷的遊戲,人們張揚地鄙夷異族、女性、弱者、窮人,根本不認為自己哪裡錯了。藍曉鹿從地獄把故事帶了回來,而那地獄不在他方,就是我們自己的家庭。——《少女忽必烈》《準台北人》陳又津
她擁有一種我們絕少擁有的,身在其中卻能站在其外凝視的角度,穿透台灣人日常思維框架,把我們的深情、偏執、愚蠢、狡狤和無奈、無力,把我們的血肉靈魂與生生死死用她的文字拓印出來——獨立記者、文史工作者,偵探書屋店長譚端
就理性層面來說,我想寫的不單單是外省人(新移民或老一代的外省人),我想表達的其實是,當生命撥開了表面的包裝,巧克力的膚色還是石雕般的混血白,不管操著湖南的口音還是越南腔的國語,也不管生命的現狀,貴為移民署的官員,還是卑微如拘留中的不法移民,每一個生命的內在其實是共通的。——作者藍曉鹿
☆《藍泥般溫潤的手》
創作源起
這是由一個真實故事發想的小說。一位朋友的遠親長輩獨居家中,後因中風發作,亡故。在長達一個月的時間裡,沒人發現他已經過世了。後來等到發現的時候,他已經成了一個自然風乾的「木乃伊」。由於他沒有直系的兒女,其他旁系親屬有些可以分得遺產的,只想著盡快草率把這個「殭屍」處理了,只叫人覺得心寒。
我想反應一個孤獨老人的生老病死,在老病死三個過程中,一個人去面對的孤單無助,當然老人本身並不是聖人,他曾經做過很多偏差的事,這些事讓他身邊的人一一離開。
孤單躺在地上過世之後,他一邊回憶著過去,一邊期待著一雙溫潤的雙手。生前的最後片刻,他期待著一雙手可以托住他下墜的生命,生命之後,他依然期待著一雙手,安撫死後的他,為他打理後事,讓他盡早入土為安,免得每天被灼熱的太陽炙烤,晚上被地獄般的冷風吹著。
後來他的期盼實現了嗎?請看小說吧。
故事簡介
老人石家琥在家中排行老二,曾經有一段婚姻,後來交往一個女友,並沒有修成正果。
大姊石家珍和母親一樣,個性偏差,自私尖刻。背著家人私下結婚之後,很快又離了婚,回到娘家的大姊和母親每天尖酸刻薄,好像一對齒輪,生活的目的就是把尖利的牙齒卡進對方的身體中,石家每天的日子就在這一對齒輪互咬著旋轉過去。
大弟珀看似有一段完美的婚姻,妻子桂非常漂亮,但表面幸福的家庭早就千瘡百孔的。桂剛來石家時,不習慣這一家人的相處模式,曾一度想要離開,甚至生下了情人的小孩駰。但是珀的寬容讓她不忍離去,又生了珀的孩子驤。看似一家人就要幸福生活下去了,中年之後的珀開始酗酒,石家唯一有妻有子的幸福家庭也被酒精一杯一杯地毀了。
小弟珠從小受到母親的溺愛。他是時裝設計師,普通人在他眼裡都是醜陋庸俗的傢伙。不願結婚。父親過世後,在母親的壓力下,他買來一段異國婚姻。買來的外籍新娘黑糖糕懷孕了,為他生下了孩子。但是珠依然在外過著豐富多彩的生活。黑糖糕離開了。
在小弟每天在外花天酒地的日子裡,琥對黑糖糕產生了非常淡的情愫,這是他自己始終也不願承認的。這份他不願承認的情愫,在黑糖糕還在石家的時候,琥處處為黑糖糕說話;但是在黑糖糕離開之後,琥卻比兩個弟弟更嚴厲地禁止她前來「偷看」自己的孩子。
琥一面在回憶著過去,應該說是琥的鬼魂在回憶著,而他躺在地上的身體也在慢慢發生變化,自然的光和風把他吹乾成了木乃伊……
☆《屋簷下》
創作源起
有回我隨朋友去探望生病的另一位朋友,那位年輕女子當時是輕度憂鬱症,她的公公又有些輕微失智。我們到她家的時候,天色近晚,你們知道的,有些老人家非常節省,這一老一少的兩個病人,坐在沙發的兩端,就著灰黯燈光,一聲不響地看電視。
剎那之間,我呆立在門口,動彈不得,坦白說,其實是悄悄落了淚。在近晚的時光,幽微的公寓空間裡,你感受不到外面的世界。因為我們剛剛經過的大馬路上,正是下班高峰時段,呼嘯而過的機車汽車那些都市文明的噪音,在這裡完全聽不見。這裡就是他們兩個人的世界,你可以感覺到沙發兩端的兩個人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但那種聯繫不是情慾的關係,就是兩個人類個體,各自處在一個極其孤單的狀態下,生出的一種對彼此的慈悲與憐憫。日子久了,這種慈悲與憐憫就瀰漫在公寓裡,好像幽暗的光影下飛舞的纖塵,似有還無,但卻真實地存在著。
故事簡介
在失智前,郭爺爺原本是個攝影師,年輕時懵懵懂懂被國民黨的軍隊帶來台灣,靠著唯一的手藝開了間小照相館;戰時的經歷令他幾乎對生命再不抱熱情,卻因為郭奶奶——當時台南某糕餅店家族舉家來拍全家福照,郭奶奶正是他們最小的千金——而重新感到光明。郭爺爺要求娶郭奶奶為妻,自是答應了許多割地賠款的條件,也不在乎郭奶奶當時早已懷著別人的孩子。
儘管兩人同樣疼愛唯一的男孩,兒子卻嗜賭成性,郭爺爺回大陸老家替兒子娶了個媳婦美華回來傳宗接代,怎料在媳婦生下孫子當晚,兒子又回來討錢並輸得精光。
郭爺爺一氣之下將兒子掃地出門。
郭奶奶自然心向著兒子,同時也為了郭爺爺寧可偏心大陸媳婦,對美華諸多挑剔刁難。
為了養孩子,美華出門上班;中間自然也談過戀愛,卻依舊遇人不淑,不久竟染上憂鬱症。而面對失智情況愈來愈嚴重的郭爺爺,和鎮日對著窗子茶飯不思的媳婦,郭婆婆一肩扛起照顧兩人還有孫子的責任,同時漸漸地發現美華為何會得到憂鬱症,不禁心生憐憫……
藍曉鹿
出生於江蘇。生活在台北。
曾任出版社編輯,翻譯。
二○一四出版第一本非小說創作《拆哪!北京!》,紀錄了在北京大學研讀翻譯碩士時細微有趣的文化觀察。
陸續推出的《外省腔》是小說創作。其實說來小說何嘗不是一種觀察。
觀的本字雚,形擬的是粗大眉毛瞪大眼睛的鳥。
而察字上方是大建物的屋頂,下方是祭,其本意是在大建築內進行祭祀活動,體察神意。
私以為或許這正是書寫的本意:睜大眼睛看周圍的世界,體察其中的深意,從而對人性多一層了解與同情。
專文推薦
廉價生活中的尊貴魔幻◎葉佳怡
曉鹿非常在意身體。無論談婚姻或家庭,總之都是身體的鬥爭。比如性慾、比如食慾、比如氣味,字裡行間活色生香,細節偶爾飽滿得令人不安。
那是在廉價生活中的尊貴魔幻。比如《屋簷下》,一名中年女子某日悠悠醒轉,發現客廳垂掛的滿是蝦皮色簾子,彷彿珍珠沾上貝殼流出的血,之後她才意識到,啊,這可是我的子宮。原來她過度寵愛兒子,導致出現了「客廳就是我的子宮」幻覺,「她就像罹患子宮脫垂症的婦人,把柔軟彈性的、皺褶裡藏著血光的子宮脫垂到了外頭來……」
或許因為出生成長於中國,後因親戚與婚姻的關係定居台灣,曉鹿看什麼都帶點身為過客的流離,及其延伸造就的奇幻。就連我以為熟悉的台北,也在她的描寫下被揭露出詭譎的灰敗。比如委身在大城市縫隙的小代工廠,其中員工如灰老鼠藏匿;移民署中被扣留的女犯,被一網打盡如同即便送命也要去特定海域產卵的雌魚;越南水餃店中因結婚來台的婦女總面對卡拉OK歌本——越南文、印尼、粵語——興奮的異國密語如蛙鳴……身體為了求生被擠壓為動物,卻又因那動物性的粗疏狂野,在資本或父權的制度下踩出了一些迷濛小徑。
不過這魔幻跟所謂台灣新鄉土小說中的魔幻又不太相同。台灣的新鄉土小說作者大多在台灣出生成長,即便追溯流離,大多也是父母或祖輩的流離,但曉鹿的流離太切身,太親近,故事中有些經驗類似外省第二代,但面對的幾乎是第三代成長的台灣環境,於是故事更容易直接讓讀者對眼前此刻感到陌生。你知道這是台北,卻又是另一個台北,裡面藏了因為窮苦而透過台商親戚來台結婚的年輕湖南媳婦,或因為母親迷信而被迫婚姻仲介來台,只為了多換一點好運給姊姊的日本女性。各種邊緣性在她筆下翻出更多皺褶。
對於曉鹿而言,文字似乎是她探索邊緣的舞步,且只有生活能將其收容。她故事裡的角色總因各種邊緣性被擠出看似穩固的體制之外,有時是國籍、有時是性別、有時是階級、有時是憂鬱,一切外在挫折最後全倒灌回那宇宙洪荒也入侵不了的私人生活。她描寫女性的憂鬱時讓我聯想到馬尼尼為,她是因為婚姻而從馬來西亞來台灣定居的華人,兩人文字風格截然不同,但都有一種因為疏離而產生的囈語質地。
於是在囈語中,痛苦是網羅,無論你原本在哪方面佔了優勢,進入生活這支果汁機後全給碎得面目全非。有時你嫌日子吵,有時你嫌日子靜,比如《移民官的情人》(外省腔第三部)有一段,「這張臉就是他們多年婚姻的寫照,他們外面沒有情人,在家沒有家暴,每一個新的日子和過去的每一個舊日子一樣,毫無表情,毫無生趣,讓人打從心底裡,生出厭煩來。」然而等真正毫無選擇的處境蓋下來,你也只能懷念曾經的嫌棄。
但也不完全絕望。這些角色仍像熱愛美食般地投入愛情。《藍泥般溫潤的手》中的男主角幾乎把每一名愛過女性都取了糕點名字,正如《屋簷下》也有一位美華,她在無性生活時特別懷念湖南鹹辣的家鄉味,尤其是那朝天椒濃縮起來的剁椒醬,結果一起生活之人嚐的都是她身體裡的腥羶慾望。雖說愛人如美食看似無情——就算一個人多麼懷念家鄉味,關愛美食的目的仍在於不停品嘗新食物——但或許更接近愛的真諦。
在這些故事裡,愛與其說是現在式,不如說一開始就是完成式。《藍》的結尾有一段,幾乎已死去的男主角在醫院遇見了曾愛過也彼此拖磨過的人,「她套著一件天使藍的無塵衣,朝前朝下往他的世界微微俯下身子;而來自基隆河的風把他雕成一座石像,他朝上朝左,仰望著她的世界。」兩人之前相愛時無法跨越太多障礙,包括國籍、語言與文化,此刻再相逢卻聖潔到幾乎可笑,但真正可笑的其實是人活著即便什麼都不做,只要帶著過多熱烈就能彼此虧欠。於是此生大家各自帶著包袱來搏鬥一場,之後也只能各扛包袱做自己的聖徒,彼此間倘若有過那麼一絲如同對待美食般的愛,那也就好了,食色性也,鴨鵝同命,人生來就是這具身體,死之前也只能轟轟烈烈,廉價也好、魔幻也罷,看來曉鹿筆下的角色都盡力不虧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