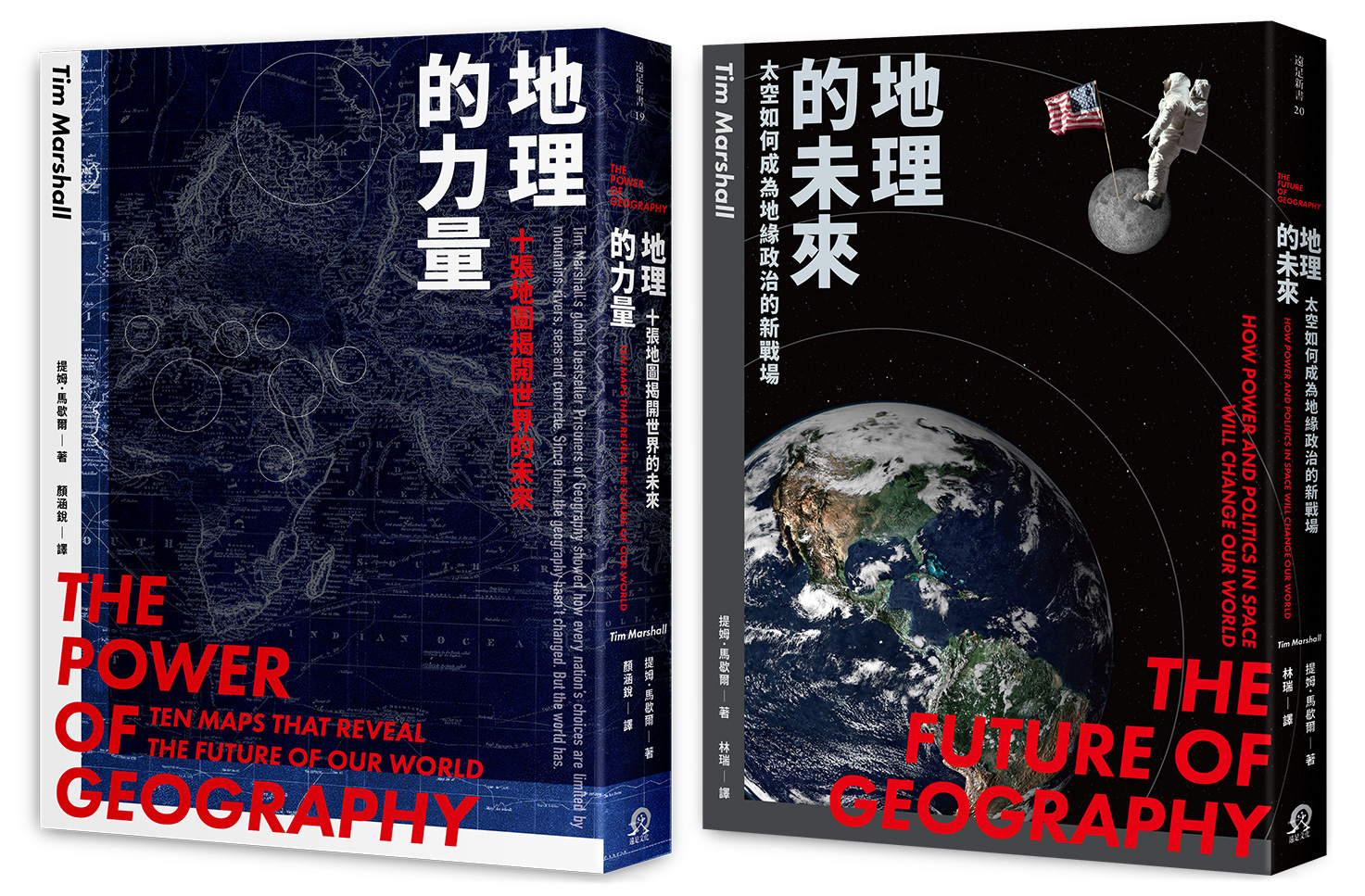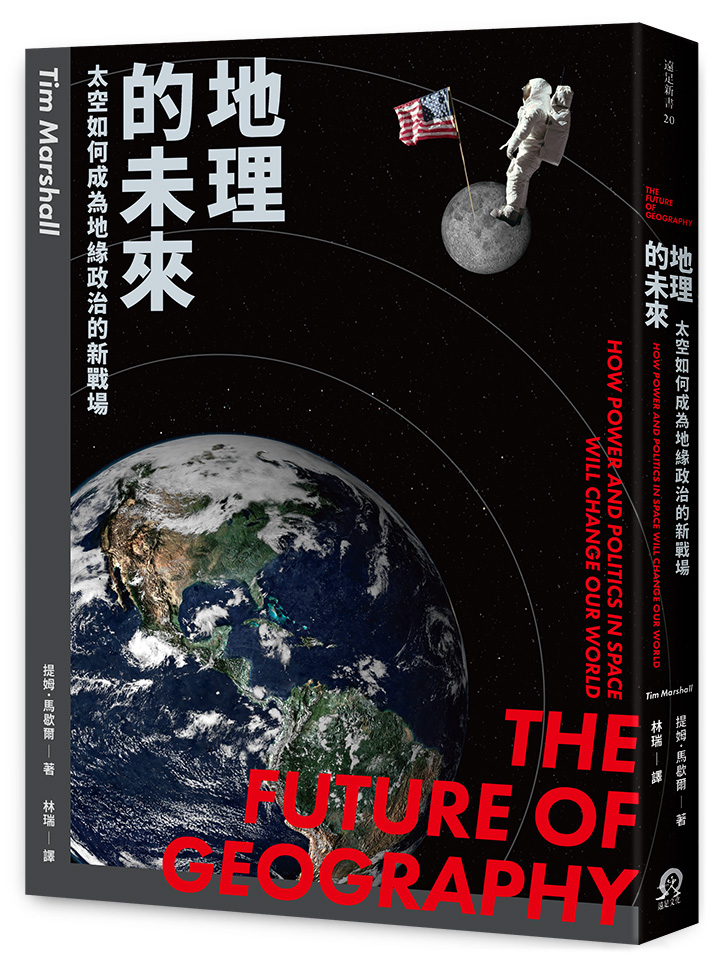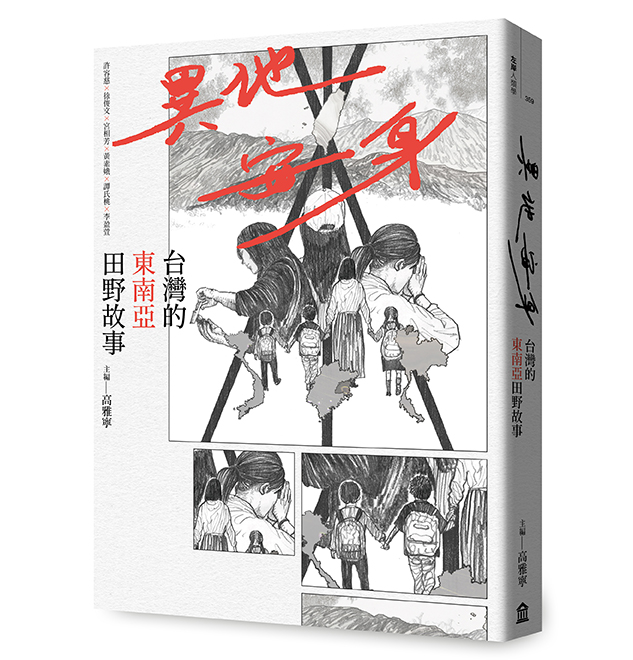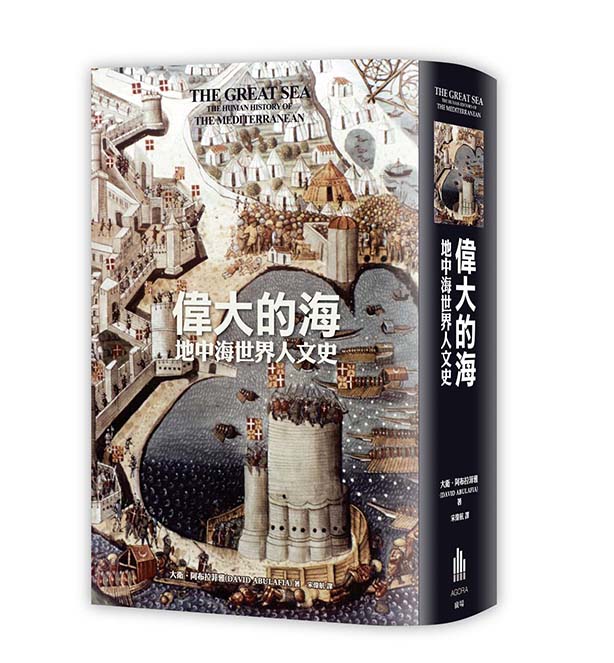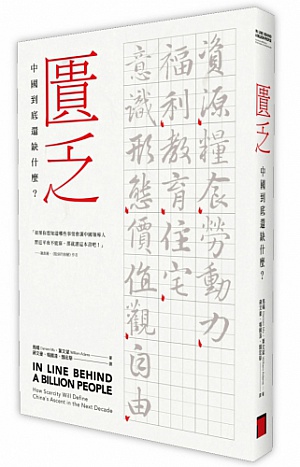「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
唐朝並非純粹的漢人王朝
而是「胡漢統合」的多民族政權
其包容差異的建國精神,正是它留給後世的寶貴遺產!
近十年對唐朝最全面、系統性的經典權威之作
罕見以韓國史學界的觀點,重新解構你所不知道的大唐帝國!
==============================
綜觀中國史,有資格被稱為世界帝國的,排除了從內亞史或新清史的解釋體系下由蒙古人和滿洲人建立的元、清帝國並非純粹的漢人政權後,似乎盛世榮光就只剩下漢唐了。但是,本書作者朴漢濟認為,唐並非單純由漢人所建立的王朝,其本質必須用「胡漢體制」加以理解。事實上,有高達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唐皇室成員具有胡人血統!而唐的多樣性、世界性和開放性也源自於此。
■從「拓跋國家論」到「胡漢統合論」
中國人津津樂道的「強漢盛唐」,是指漢、唐兩個帝國文治武功的盛世榮景。中國史學界的主流看法,也都把唐視為和漢一樣是由漢人主導的中華帝國之巔峰。然而日本東洋史學界,例如杉山正明和森安孝夫均指出:以鮮卑拓跋部為主軸所形成的「代國—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唐」雖是以中國風的王朝名來呈現,但實際上用「拓跋國家」來稱呼更為合適。他們承襲自匈奴以來的遊牧系武人的濃厚傳統及體質,其實是「異族們創造的新中華」。
韓國的資深唐史研究巨擘朴漢濟則提出了「胡漢統合」論。他認為結合胡人與漢人、武人與文人的「胡漢統合」勢力──「關隴集團」,是大唐帝國得以建立的關鍵,也是理解大唐的核心元素;正如同史家陳寅恪對關隴集團的敘述:「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
■「漢化」(sinicization, han-hua)並無法解釋大唐的出現,真正的解釋是「胡族的華化」。而漢並不等於華。
胡族進入中國社會,對中國造成極大的影響。胡族並不執著於華夷之辯,不仇視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相反地,他們想要接受好的那一部分。為了統合、團結境內的所有人,自我改變是必要的條件。從前,胡族的這種態度被稱為「漢化」,但這樣的變化其實不只是單純「漢化」而已,而是更深的 「文明化」,最終產生「中華化」的結果;另外一方面,漢人的胡化也是一種真實的存在,二者形成「雙向同體渦旋互生」的交融模式。而這些以胡漢問題為軸心所產生的種種社會現象,他將之稱為「胡漢體制」。
美國哈佛大學的包弼德(Peter K. Bol)教授也認為,使用「文明化」(civilization)代替「漢化」(sinicization, han-hua)一詞時,意味著少數的胡族跟多數的漢族在中國土地上共存,其最終的目標是達到所謂的「統合」。但必須說明的是,主導這個統合過程的人是胡族,而不是漢人。「中華」或「中華主義」等詞彙的內涵,也不是固執於漢族之物。「中華」也不是民族。然而今天的中國創造出了所謂「中華民族」這個詞彙,是故意混淆「國民」與「民族」而創造出來的詞彙,它在邏輯上並不存在。
綜觀中國史,大唐帝國算是成功的帝國,雖然外族被賦予了相當程度的自治權和平等權,這在唐代以前是不可能看到的現象。但是唐代仍無法發展出像羅馬帝國那樣,漢族與外族同樣適用、一起參與的「市民權」(公民權)概念。和羅馬體制不同,唐代標榜「一君萬民」的皇帝體制是其根本上的弱點。所以,當胡(外國人)被排擠,胡漢之別被強調之時,統合力量自然變得薄弱,這正是安史之亂後出現的情形,也是中國日益邁向純粹漢人社會、強調華夷之辯的宋代的原因。而這也正是當今中國仍有待解決的問題。
■皇帝-天可汗,精彩萬分的大唐帝國留給今日的遺產
皇帝,是南方農耕民(漢人)對於天子的尊稱;可汗,則是北方遊牧民(胡人)對於君主的尊稱。由此看來,接受「皇帝-天可汗」稱號的唐朝君主,其統治的大唐帝國毫無疑問是一個胡漢統合帝國——君主既是農耕民的皇帝,也是遊牧民的可汗。
在秦漢以後的歷代王朝中,除了開國國君,少有皇帝御駕親征,但對唐的皇帝來說,率兵打仗卻是日常的軍事行為,透過遊牧型君主「親征→掠奪→班賜」的領導方式,統御帝國子民。另外,朴漢濟也精闢分析了皇后、太子、太子妃制度,從而解答「為什麼中國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出現在唐朝,而非其他朝代」?在一個像美國一樣富有多元性的「胡漢複合社會」裡,大唐帝國應該如何管理?「大唐帝國的治術和經營」提供了精彩的答案。
那麼,為什麼我們要翻轉傳統的漢人史觀,改從胡人的角度重新理解唐?大唐帝國留給後世的遺產又是什麼?答案是,這是一個「開放的帝國」、「開放的社會」。成為開放社會的必要條件是「機會均等」,而基本條件則是「不靠關係」,讓人民依據實力、技能獲得評價。像高句麗人高仙芝、波斯人阿羅喊,都是因其特殊身分或特殊才能而在唐朝廷中活躍的典型人物。
因為胡漢統合的唐朝廷具備包容差異、海納百川的開放態度,才能造就大唐盛世,這不僅是大唐帝國給予後人的啟示,也是本書的重要結論。細數中國土地上的歷代王朝,不難發現凡是一味追求「漢族正朔」者,終究會遭致覆滅,而強調「胡漢一家」者,則注定走向富強之路;在中國高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此刻,大唐帝國的興衰存亡,更加值得我們借鏡省思。
■為何海外華人學者、日本學者、韓國學者可以理解唐的本質?
八旗文化曾推出華人學者陳三平的《木蘭與麒麟:中古中國的突厥―伊朗元素》和日本學者森安孝夫的《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講談社「興亡的世界史」系列之六)二書。陳三平熟悉漢語音韻訓詁學、精通多種歐洲語文和中、北亞語文,所以他能夠跳出像「木蘭」、「莫賀弗」這樣的漢字形體約束,而從語言上解讀隋唐中國的「伊朗」元素;而森安孝夫借助突厥語、粟特語史料的研究,大膽提出粟特絲路觀、拓跋國家論和「失敗的安史王朝」說,再次刺激讀者對唐代的全新理解。
這兩本關於隋唐的經典著作,與韓國學者朴漢濟的《大唐帝國的遺產:胡漢統合及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構成鼎足,讓學界和一般讀者感到驚艷。這三本書的共同特色都不是以華夷之辯、胡漢之別、中國民族主義的方式認識「中國史上的唐朝」,而是採用不同史料,以不同視角研究「世界史中的大唐帝國」。
朴漢濟更是藉由多民族帝國大唐的混血主義,反思和檢討了單一民族韓國的純血主義的狹隘。他更在本書「結論」中評價了中國政府把高句麗(Korea)解釋為中國地方政權的「東北工程」。他指出,實則「內蒙古—滿洲—朝鮮半島」是彼此接續的北方文明系統,但中國的主張斷絕了比中原黃河文明更早的「遼河文明」與朝鮮半島之間的連結。此外他也批判了主張現在「組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們,其祖先全都是「中國人」,他們所走過的歷史就是「中國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中國」這種官方學說。
朴漢濟最後指出,習近平的中國夢如果要真的獲得成功,多元主義、開放社會的大唐是其最好的範本。不同的膚色、種族、宗教、語言等交雜在一起時,其結果就是形成一個熔爐,並產生出巨大力量。所謂的多樣性,只有在互相尊重彼此的差異時才得以維持,沒有沙子跟碎石而只有水泥的建築物,是不可能豎立幾百年的。
朴漢濟(박한제)
首爾大學東洋史學系博士,畢業後於該系任教多年,現為該系名譽教授,曾任韓國中國學會會長。曾在台灣國家圖書館之漢學研究中心、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機構從事研究工作。投入畢生心力於中國隋唐史研究,其「胡漢體制」的研究主張已成為韓國史學界唐朝研究的代表性理論。
著有《東洋史講義要綱》、《中世中國胡漢體制硏究》、《人生,我的五十自述》、《走去歐亞大陸的一千年》、《朴漢濟教授的中國歷史紀行》、《江南的浪漫和悲劇》、《阿特拉斯中國史》等書。
翻譯|郭利安
台大歷史系畢業,現專職中韓口筆譯,內容力特約譯者。
校訂|鄭天恩
台大歷史所碩士,曾任日文小說編輯,目前為專職翻譯。譯有《人民解放軍的真相》、《文明的遊牧史觀》、《凱爾特.最初的歐洲》(以上均為八旗出版)、《東方直布羅陀爭霸戰》、《珍珠港》等書。
前言
【第一章】大唐帝國的本質和外國人
I. 大唐帝國的本質
II. 大唐帝國的外國人政策
III. 大唐帝國的遺產
【第二章】胡漢融合和大唐帝國的誕生
I. 大唐帝國的出現過程
II. 可汗概念圈向中原擴大,與「皇帝天可汗」之概念
III. 「胡漢之別」的再生與大唐帝國的衰亡
IV. 胡族的華化與中國史的時代區分
【第三章】大唐帝國的經營與治術
I. 大唐帝國的外在特徵
II. 皇帝的日常行為與治術
III. 皇后、太子、太子妃的問題
IV. 胡漢複合社會與整頓制度
【第四章】結論
I. 對於中國「東北工程」的想法
II. 中國會像蘇聯一樣分裂嗎?
III. 最像中國之事物的形成
IV. 中國夢與大唐工程
注釋
〈第一章 大唐帝國的本質與外國人〉
我們可以將中國「魏晉南北朝」(二二○至五八九年)這近四百年的時間視為一段「大唐帝國的形成史」。 大唐帝國最大的特徵,並非如過往的看法那般,只是一種新貴族制社會或是古代社會的完成期,而應將它看作是「胡漢融合」的「世界帝國」(World Empire)。
「大唐帝國」在中國歷史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現今中國人最喜愛的王朝,但若是更深入地看,會發現大唐帝國其實是一個胡人色彩十分濃厚的朝代。如果我們無視或輕視那些全面滲入到唐代社會中的蠻夷與遊牧民族(也就是「胡人」),是絕對不可能徹底了解唐代的。
然而,這部分的研究依然充滿困難。在「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生活的人們所留下的敘述性史料中,幾乎沒有任何跟「胡」有關的的東西,這正是使我們無法正確了解這段時期實際情況的最大難處。對於這段時期的記述,只有在人口上占據多數且掌握文字的漢族文人、史家所留下的記錄而已。相較之下,一二六〇年代忽必烈建立蒙古政權後,對於蒙古歷史的解讀就分為以漢文史料和以穆斯林史料為中心的研究,最近則湧現出許多將兩方史料左右對照後,超越一般立場的研究。
但筆者所研究的這個時代,卻只能完全依賴對胡人帶有偏見和蔑視立場的漢文史料。因為無法突破二分法的界限並以宏觀的角度加以分析,近來對於這時代的研究大多無可避免地產生嚴重扭曲。筆者為了努力還原當時的實際情況,只能盡力去發掘某些稀少且突兀的的資料所代表的意義。
在史料有限的情況下,唐朝因此被許多人認為是由漢族所建立的傳統國家,而比起其他皇帝,唐太宗也被描寫成一位更偏向於漢族的皇帝。然而,當時位於西北方的遊牧民族們卻稱呼唐王室為「Tabugach」,即所謂的「拓跋」,認為唐朝是由鮮卑族的其中一支、被稱為「拓跋」的部族所建立的國家。 如果我們翻開國、高中的世界史教科書,大多寫著「五胡十六國以後進入長城內的遊牧民族,原本都被認為是掠奪成性、毫無文化可言的野蠻人,但最後皆被漢化。」
如果我們就事實來討論的話,筆者的想法是,雖然的確有一部分的胡人漢化了,但漢人也因此胡化,最後兩者出現了「中國化」,如果再說得更正確一些,即出現了「華化」。就這一層面來說,不管是「胡人的漢化」或是「漢人的胡化」,都是真實存在的,這可以說是「雙向同體渦旋互生」的交融模式。
構成本書主題「大唐帝國」的主角,不管是以血統還是文化來看,都具有濃厚的胡人色彩。雖然沒有人會否認「五胡十六國——北朝」的主導者是胡人,但一般都認為自隋代到唐代的所有皇帝,全都是漢人出身。事實上,雖然這些皇帝出於統治方便而冒稱「漢族」,但他們卻並非完全擁有漢人血統。隋朝的楊氏一族雖然成為籍貫在京兆華陰(即現在的西安東部地區)中最高的漢族門閥,但和楊氏同族的楊素 ,在當時卻仍遭到山東地區的門閥(如清河崔氏)的蔑視。
事實上,楊氏因為曾在北周時代被賜胡姓「普六茹」, 再加上他們的妻族也幾乎都是胡人,因此也有學者將他們視為「異民族」。 楊氏以漢人姓氏自稱並假定他們的血統,是為了「形塑國家」(State Formation)而無法避免的選擇。 由此看來,隋皇室和唐皇室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成員都具有胡人血統。
中國文化可以看作是胡漢縱橫交錯而成的產物,若將其比重數字化,當然是華夏民族的傳統文化占有更大的比重。但若是忽視了胡人的要素,不只是中國的歷史,連「中國」本身都無法完整地了解,我們也沒有任何理由採取這樣的立場。最近在中國學術界可以看到許多跟以前比起來更進步和不同立場的見解,例如《五胡興華》 和《另一半中國史》 這兩本書。前者反對傳統史家們主張的五胡入侵中國,使中國帝國和中國文化陷入混亂的傳統史觀,即反對所謂的「五胡亂華」; 後者則主張胡人(即少數民族的前身)與漢族一起開展了中國的歷史,並帶來全面的影響,換句話說,胡人是為「中國歷史的形成」帶來奉獻的重要角色。
筆者針對中國的民族問題以及「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所發生的種種問題進行解讀和分析後,提出了「胡漢體制」(Sino Barbarian Synthesis)學說。所謂的「胡漢體制」,在筆者的第一本著作《中國中世紀胡漢體制研究》的序言中已經提及,那就是在中國中原地區,胡與漢(即「遊牧」與「農耕」)相遇後所產生的各種相互關係。
對於「體制」這個用詞雖然可能會產生誤解,儘管它理所當然地包含了政治體制,但除此之外,胡漢兩個種族在同一地區、同一統治體制內並存,且一邊逐漸形成同一文化時,又一邊產生衝突、反目;這些以胡漢問題為軸心所產生的種種社會現象,我都將之稱為「胡漢體制」。之所以用「體制」的英文「Synthesis」來書寫,是因為我研究的核心與最終的課題,是希望克服胡與漢並立之雙重體制階段,並尋找胡的體制與漢的體制融合後所出現的下一階段之面貌, 這不僅僅是魏復古(Karl August Wittfogel)和馮家昇所提出之「第三種文化」(Third Culture)的意義而已。
筆者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第一次提出此學說,至今已經過了近三十年。其實,究竟要如何定義「漢」,至今仍有一定的難度;而「胡」的定義又是什麼,則是更加困難的問題,所以直到現在,就連列舉出「胡漢體制」的實際狀況都還只是在初步階段而已。所謂的遊牧民族,並非只是單純地定義他們的生活空間是在草原上,他們其實擁有更多樣化的型態。
「胡」這個詞的意義也會隨著時代與地區的不同而有所改變。大致上來說,西漢時期指稱的「胡」,主要仍是指匈奴;在五胡十六國時期,則是用來指稱「匈奴、鮮卑、氐、羌、羯」等曾在中國北方—西北方的草原地區活動過的遊牧民族;自東漢時期起,則開始以胡來指稱包括粟特人在內的「西域人」。雖然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用來稱呼整體遊牧民族的狀況較占上風,但隋唐時期卻漸漸用來稱呼西域國家的人民;此外,突厥、回紇(回鶻)也偶爾被稱作「胡」。這種現象告訴我們,根據時代、區域的不同,「胡」的意義也隨之有了各種變化。
「胡」最主要的意義被認為是指「給予中國強烈衝擊之西北方出身的外人或是異國人」, 且「胡漢」這樣的用詞並非只是像「胡漢」或是「漢胡」這樣,在字的先後順序上出現主從問題而已。 「胡漢」這個詞首次在《後漢書》中作為史料用詞, 雖然在《三國志》及《水經注》等書中也曾經被使用過, 但後來就比較少被使用了。 直到近幾年,不只是中國學者們將之作為愛用的學術用語, 在東亞漢字圈國家中更被廣泛地使用。
一般將唐朝(六一八至九○七年)稱作「大唐帝國」,筆者覺得從大唐帝國這個名稱開始說明才是正確的順序。若我們估算唐朝在中國史所具有的比重或是意義,就會覺得稱其為「大唐帝國」一點也不為過,因為唐朝在中國歷史中不僅占有一定的比重,也被看作是符合「帝國」這個詞的真正意義的王朝。
唐朝是長期統一中國的王朝之一,共統治了兩百八十九年。唐這個名稱是因為大唐帝國的創立者──唐高祖李淵,他的祖父李昞作為北周(五五五至五八一年)的開國功臣,北周武帝於保定四年(五六四年)賜予封地「唐」,即現在山西省省會太原一帶的地區, 於此同時,李昞還受封「唐國公」這個稱號。 在元朝自《周易》中借字作為國號前, 中國王朝的命名原則全是取自建國者或是其祖先的封地名,如同中國歷史上最古老的王朝發源地之一,山西省的堯都(現在的臨汾)一般。
什麼是「帝國」?在西洋史中,「帝國」這個詞在拉丁語為「Imperium」,英語則用「Empire」表達。若用「帝國」來稱呼的話,往往會與近代的「帝國主義」聯想在一起,所以講到帝國時,常帶有下列意義,例如「直接占領他國的領土並支配之,或是運用間接的方法在政治、經濟、文化上行使統治與擴張政策,以實現自身目標的國家」,或是「透過壓倒性的力量征服周邊、擴張領土、無法容納周邊的任何一個政治體與自己處於同等地位的國家」。
然而,所謂的「帝國」,其實更意味著包容多樣性與異質性,不執著於同一性;也就是說,帝國的意義,比起「同化」,更重視「統合」;比起「同意」,更在乎「正義」。 這種意義下的帝國會有著只干涉周邊國的外交、而不直接干預其內政的傾向,因此帝國又可被劃定為「對於支配領域中的統治結構(如制度、組織、人力、情報等)不具有『統一秩序』的主宰國家」。 帝國就是這樣一個多樣的、偶爾帶有相反意義的詞彙。
東亞,特別是在漢字文化圈中,因為將「帝國」視為「皇帝之國」的簡寫,因此是「皇帝所統治的國家」,「皇帝」也成為該世界中獨一無二、絕對性的存在,所以自秦始皇的秦帝國,至最後宣統帝退位的清帝國為止,全部都是「帝國」。但在分裂王朝的情況下,即使被稱為皇帝,大部分也不會將其稱為「帝國」;而就算是統一的王朝,以對外影響力較弱的宋朝或是明朝來說,也不會稱其為「大宋帝國」或是「大明帝國」;而即使元帝國最接近「帝國」一詞的真義,也就是所謂的「世界性帝國」,但與其叫作「皇帝之國」,不如稱其為「蒙古汗國」更為恰當。若以勢力強大這部分來看,「秦帝國」、「漢帝國」、「唐帝國」以及「清帝國」被稱為帝國好像滿恰當的,雖然已經無法知道是誰先開始將「大」這個字放在字首,但比起「大秦帝國」及「大漢帝國」,我們似乎更熟悉「大唐帝國」、「大元帝國」、「大清帝國」這樣的稱呼。
在前文中雖然提到「帝國」是具有兩種意義的詞彙,但在近現代時期,將之擴張、膨脹 並累積成核心詞語的地方,跟漢字文化圈相比,似乎是西方更勝一籌,因為羅馬帝國是這樣,大英帝國也是如此。「帝國」這個詞雖然偶爾會被當作是與「帝國主義」同義的負面詞語,然而將「帝國」與「帝國主義」兩者嚴格區分卻是現在學術界的走向。就像為了世界統一而提出「作為未來計畫的帝國」一般, 「帝國」一詞絕對不是只有負面意義,近來學界也強調帝國作為「全世界統一的中心」、「異質性與多樣性共存的舞台」或是「文明的中心」、「世界秩序的主宰者」等正面的功能及角色。若在中國歷代王朝中,尋找與此帝國意義最相符的王朝,「大唐帝國」應該是最符合上述條件、最不會有人提出異議的帝國。
這些各具不同意義的「帝國」,其興衰在地球上時常出現,包括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波斯帝國、阿拉伯帝國以及大英帝國等。在這當中若要舉出最標準的帝國,古代是羅馬帝國,近代則非大英帝國莫屬。雖然大英帝國也可以拿來進行意義上的比較, 但若要與大唐帝國進行對比,對象應該還是羅馬帝國較為適當。下面三個句子可以簡單呈現出羅馬帝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帝國:一、「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二、「條條大路通羅馬」;三、「羅馬共有三次(以軍隊、宗教和法律)統一(征服)世界」。
(本文節錄自:第一章 大唐帝國的本質與外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