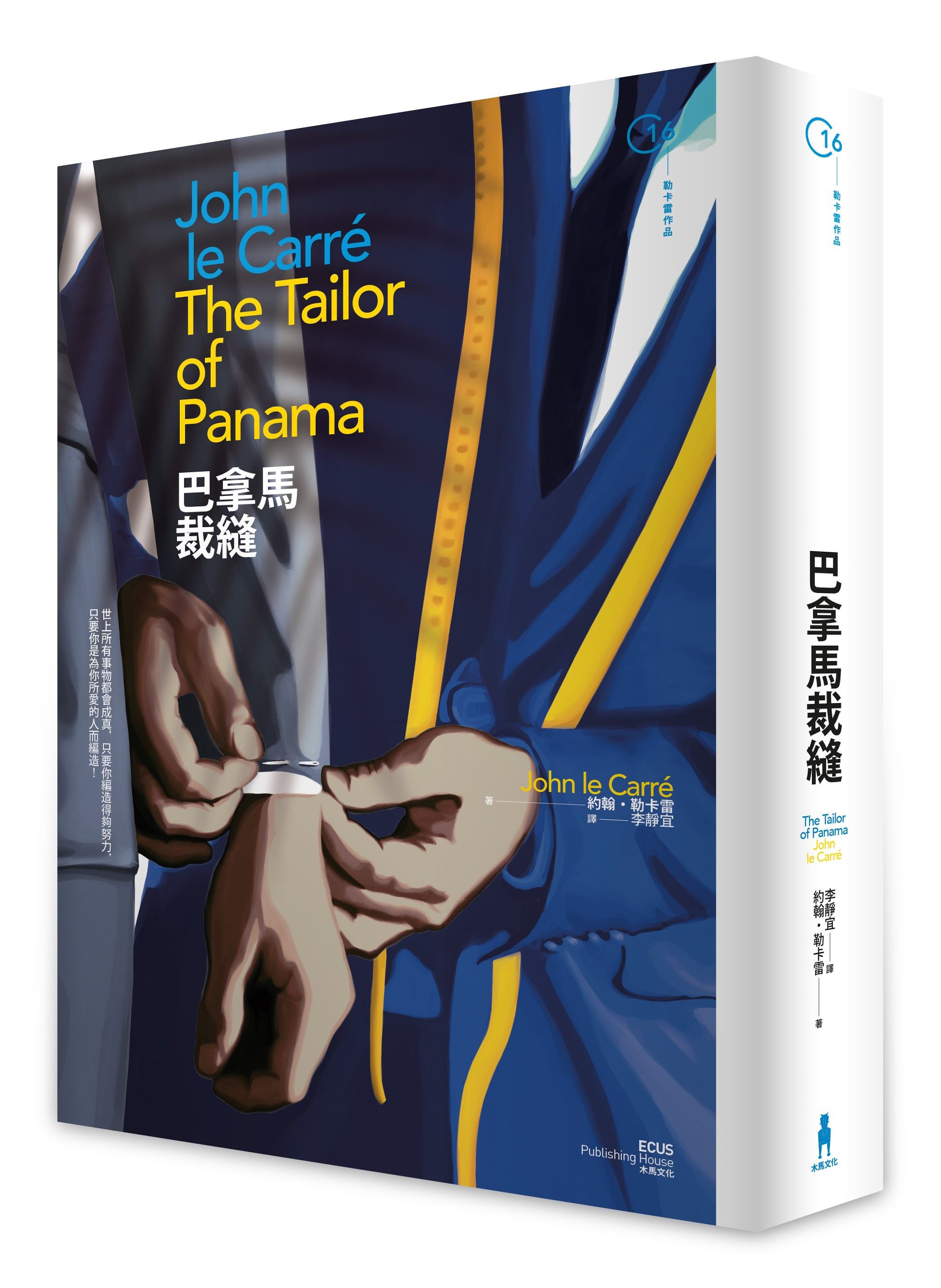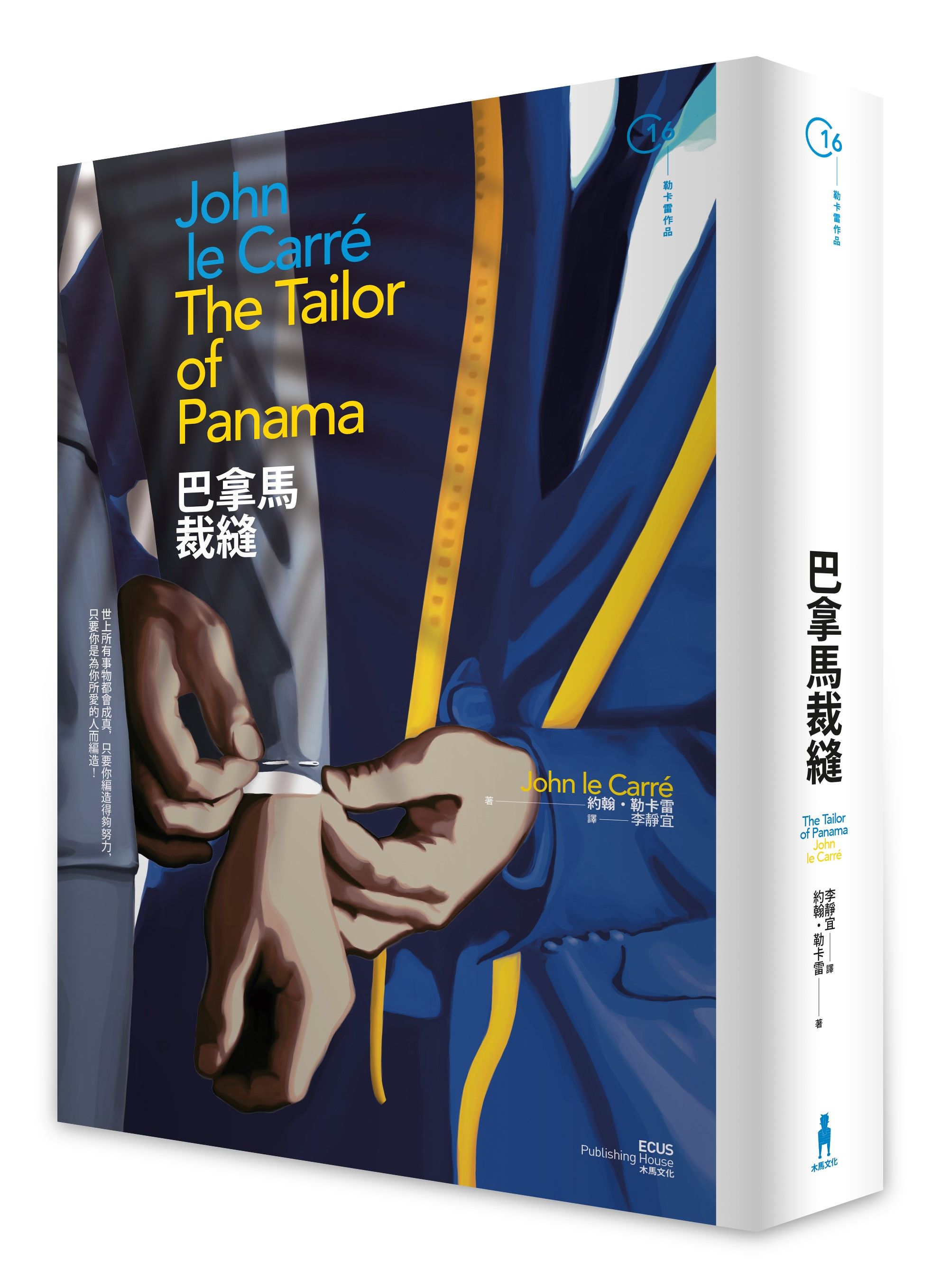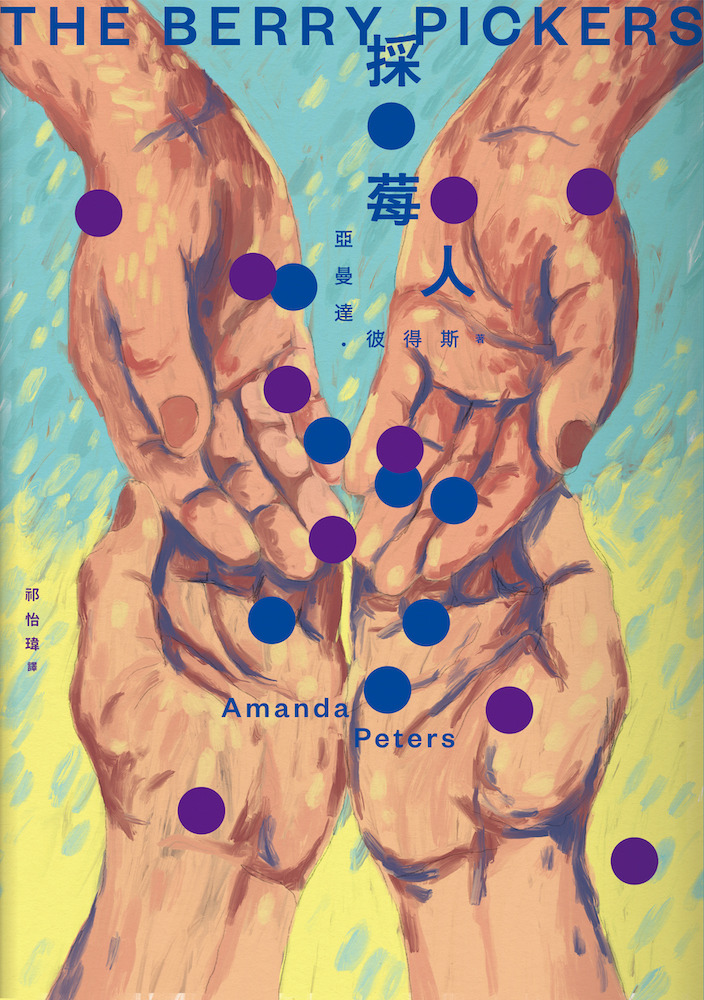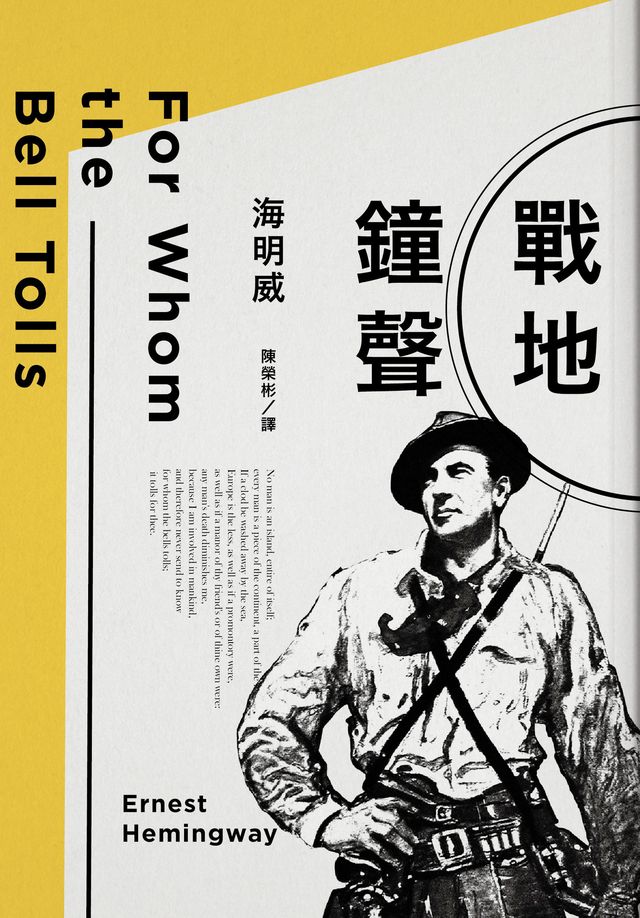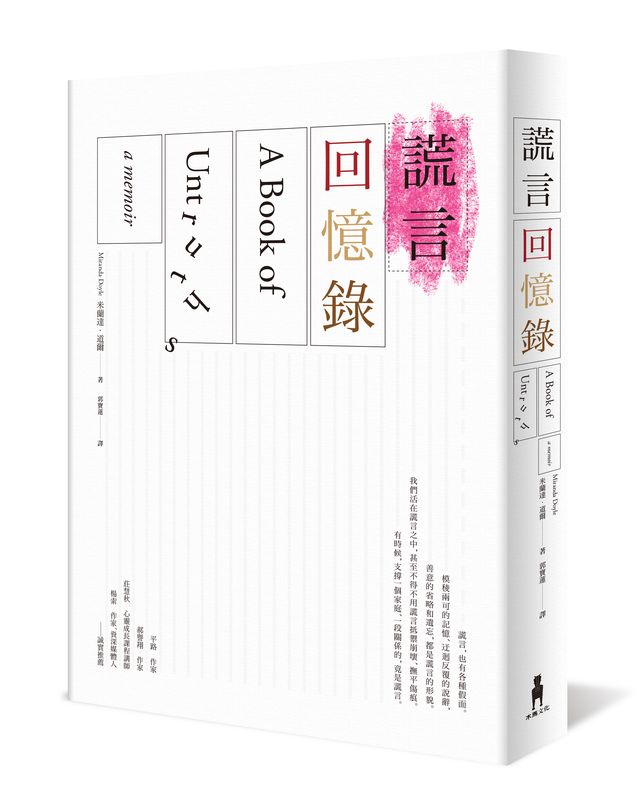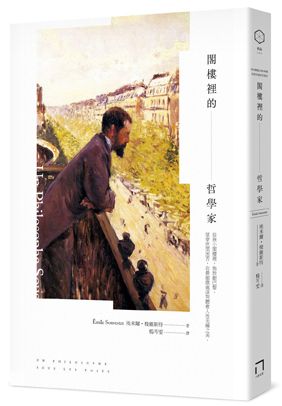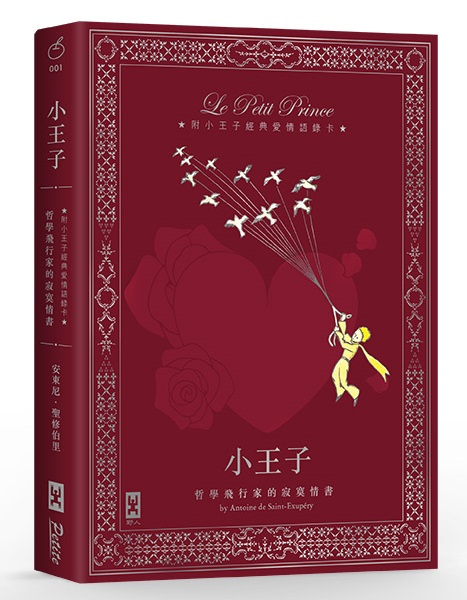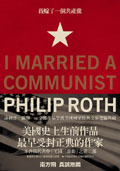「世上所有事物都會成真,
只要你編造得夠努力,只要你是為了所愛的人。」
哈瑞‧潘戴爾,來自英國的裁縫名匠,喜愛在馬勒的旋律中為顧客裁製高級西服。他對客戶所言深諳聆聽守密之道,在巴拿馬當地深受政商名流信賴。儘管事業與家庭美好無缺,潘戴爾內心卻藏著一個祕密。
此時,巴拿馬運河主權移交在即,大國之間角力暗潮洶湧,猜疑與耳語也如伏流不斷。
一個尋常的週五午後,年輕體健、來歷如謎的安德魯‧歐斯納德冒雨衝進店裡要求訂製西裝,潘戴爾的生活從此生變―他驚覺歐斯納德要的是一樁交易,一樁以內幕與隱私、刺探與密謀作為籌碼的買賣。
為了挽救自己瀕於裂解的人生,藏住亟欲洗刷的過往,潘戴爾開始穿梭在虛實之間,以一個個「身分」、一條條「情報」為軸線,織紡出似假還真、龐大複雜到堪稱藝術的「故事」……
只是,當繃緊的線開始出現裂口,潘戴爾能承擔多少代價?
書評
․「勒卡雷的書寫技巧在《巴拿馬裁縫》中完美展現。節奏緊湊,場景描述明快精簡,全文穿插交錯的追憶倒述毫無鑿刻痕跡。」―《紐約時報書評》
․「偉大的間諜小說大師,驚悚、陰謀、驚喜混合交融的佳餚。」―《Book Description》
․「勒卡雷仍然遠遠走在這個領域的最前方,令人驚豔的現代說書人。描寫權力菁英幕後運作結構的功力,堪稱當代文壇翹楚」―《出版人週刊》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
英國著名小說家,原名大衛・康威爾(David Cornwell),一九三一年生於英國,十八歲便被英國軍方情報單位招募,擔任對東柏林的間諜工作;退役後於牛津大學攻讀現代語言,並於伊頓公學教授德文及法文。一九五八年進入英國軍情五處(MI5)工作,兩年後轉調至軍情六處(MI6),先後派駐德國波昂及漢堡,並在任職期間寫下《死亡預約》、《上流謀殺》,以及首部暢銷全球之作《冷戰諜魂》。
勒卡雷在一九六四年離開軍情六處後,即全心投入寫作,作品不僅廣受全球讀者喜愛及各大媒體推崇,更因充滿戲劇懸疑張力,已有十餘部改編為電視劇及電影。
勒卡雷一生獲獎無數,最重要的包括一九六五年美國推理作家協會的Edgar Awdars、一九六四年獲得英國Somerset Maugham Award、James Tait Black紀念獎等,一九八八年更獲頒英國犯罪作家協會CWA終身成就獎,以及義大利Malaparte Prize等,其內斂而深沉的寫作風格更是確立了他在二十世紀類型文學領域的崇高地位。
二○一六年,他以《此生如鴿》一書細膩講述個人經歷,是瞭解勒卡雷其人和其筆下諜報世界、人物及各部作品的精彩回憶自傳。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勒卡雷逝於英國。
李靜宜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博士,美國史丹福大學訪問學者。曾任職外交部與總統府。
譯有《追風箏的孩子》、《燦爛千陽》、《遠山的回音》、《奇想之年》、《史邁利的人馬》、《完美的間諜》、《此生如鴿》、《那不勒斯故事四部曲》、《地下鐵道》、《莫斯科紳士》、《寂寞芳心》、《變調人生》、《迷蹤記》、《荒蕪年歲》、《正常人》、《死亡的重量》、《暗夜》、《倖存之家》等。
臉書交流頁:靜靜讀一本書
內文試閱
第二章 節選
歐斯納德在十點半左右打電話來,沒有激起一絲漣漪。他是新顧客,新顧客照例要轉給哈瑞先生;或者,如果他抽不出空,就請他們留下電話號碼,好讓哈瑞先生立即回電。
潘戴爾在他的裁剪室裡,和著馬勒的旋律,依循棕色紙型,剪裁出一套海軍制服。裁剪室是他的庇護所,他不和任何人分享,鑰匙穩穩安放在背心口袋裡。偶爾,為了享受鑰匙對他代表的意義,他會將鑰匙插進鎖裡,轉動它,把世界關在門外,證明他是自己的主人。偶爾在再次打開門鎖之前,他會以降服的姿態垂下頭,腳併攏站一秒鐘,才重新展開美好的一天。除了旁觀這戲劇性動作的部分自我之外,沒有人看見他這麼做。
在他後面,一間間高度相同、有嶄新照明與電動吊扇的房間,他驕縱過度的各色人種雇工在裡頭縫衣燙裳,以巴拿馬勞動階級通常無法擁有的自由談天說地,但是沒有一個像老闆潘戴爾那般勤勞。他略一停頓,攫迎馬勒樂曲的波濤湧動,然後靈巧地沿著黃色粉筆曲線一刀剪下,就成了哥倫比亞裔艦隊司令的後背與雙肩。這位司令一心一意想藉優雅的儀表和遭解職的前任一較高下。
潘戴爾替司令設計的制服格外燦爛奪目。那條白長褲,已交給遠遠躲在他後面那條走廊房間裡的義大利長褲裁縫師傅;可以服服貼貼抵著座位,適合站而不適合坐。而潘戴爾正在裁剪的這件燕尾服,是白色及深藍色配上金色肩章與穗帶的袖口,金色盤扣與高高的納爾遜式衣領繡著一圈環繞船錨的橡樹葉─這是潘戴爾自己的神來一筆,司令的私人祕書看到傳真的圖樣時表示非常喜歡。潘戴爾從來沒真正了解班尼叔叔說的「目測精準」是什麼意思,但看著圖樣時,他知道自己的確有此能力。
他繼續和著音樂裁剪,拱起背,思緒逸飛遠颺,直到他變成潘戴爾艦長,步下宏偉樓梯,參加自己的就職舞會。這種無傷大雅的想像無損他的裁縫技巧。他一貫主張─這應歸功於他已故的合夥人布瑞斯維特,最理想的裁剪師,天生的模仿者─不管手上裁剪的是誰的衣服,都要讓自己融入其中,成為那人,直到真正的主人來取走為止。
‧
接聽歐斯納德的電話時,潘戴爾正沉浸在出神入化的愉悅當中。一開始是瑪塔接起電話。瑪塔是他的接待員,接線生,會計與做三明治的人,一個頑固、忠心耿耿、黑白混血的小東西,一張歪斜的臉疤痕累累,滿是皮膚移植與拙劣手術的痕跡。
「早安。」她說的是西班牙語,聲音甜美。
不說「哈瑞」,也不說「潘戴爾先生」─
她從來不這麼叫他,只用天使般的聲音道早安,因為聲音和眼睛是她臉上倖免無傷的兩個部分。
「你也早啊,瑪塔。」
「電話上有位新客人。」
「從橋的哪一邊來的?」
這是他們一再重複的笑話。
「你那邊。他叫歐斯納德。」
「叫什麼?」
「歐斯納德先生。英國人。而且愛說笑。」
「哪一種笑話?」
「你對我說的那種。」
放下剪刀,潘戴爾將馬勒轉到幾近無聲,依序拉出一本預約登記簿與鉛筆。在裁剪桌上,眾所周知,他是個執著精確的人:布料在這裡,紙樣在那裡,發票和訂單在另一邊,每樣東西都井然有序。裁剪時,他慣常穿著自己設計縫製的背心,前掩襟後絲背。他喜歡這件背心傳達出的那種提供服務的氣息。
「您的姓名該怎麼拼呢,先生?」歐斯納德再次報上名號後,潘戴爾愉快地問。
對著話筒說話時,一抹微笑滲進潘戴爾的聲音裡,完全陌生的人會立刻感受到自己是對著他們喜歡的人說話。但歐斯納德也有相同的討喜天分,這點很明顯,因為兩人彼此很快就愉悅自如,從他們隨後十足英國風對話的長度與輕鬆氣氛即可印證。
「開頭是O─S─N,結尾是A─R─D。」歐斯納德說話的口氣一定讓潘戴爾覺得特別詼諧有趣,因為潘戴爾照歐斯納德的說法寫下這個名字,三個字母一組,中間還加上一個&。
「順便一問,您是潘戴爾還是布瑞斯維特?」歐斯納德問。
經常碰到這個問題的潘戴爾,雍容大度地把兩種身分都據為己有:「嗯,先生,這麼說吧,兩個都是。很遺憾告訴您,我的合夥人布瑞斯維特已經過世多年了。但我可以向您保證,直到今天,他的典範仍在這間舖子長存不朽,這讓認識他的人都很欣慰。」
在對職業驗明正身畫下句點之際,潘戴爾的話語活力蓬勃,猶如放逐良久才返回熟悉世界的人。它擁有的意涵比你預期的更多,特別在結尾處,頗像協奏曲的樂章,聽眾一直以為就要結束了,結果卻遲遲未了。
「很遺憾聽到這個消息。」歐斯納德充滿敬意地略為停頓後,壓低聲調說:「他怎麼死的?」
潘戴爾對自己說,真古怪,這麼多人問這個問題,但只要想到如此結局遲早會降臨到我們身上,也就不足為奇了。
「喔,他們說是中風,歐斯納德先生。」他用健康的人論及這個問題時慣常會有的聲調,肆無忌憚地回答,「但我說呀,老實講,我會說他是心碎,因為懲罰稅,讓我們在薩維爾街的基業落得悲劇收場。歐斯納德先生,您是巴拿馬這兒的居民嗎?希望這麼問沒太失禮。或者,您只是路過?」
「幾天前才到,打算在這裡待一陣子。」
「那麼,歡迎蒞臨巴拿馬。先生,能否留下您的聯絡號碼,以防我們的線路被切斷?這在我們這幾個區域恐怕是常有的事。」
這兩人,兩個英國人,都帶著烙印般的口音。在這位歐斯納德看來,儘管潘戴爾急切想擺脫他的出身,卻明顯得不容錯認。他熟膩、老練的聲音從沒洗刷掉倫敦東區雷曼街的標記。即使母音正確,抑揚頓挫與連讀音還是讓他露出馬腳。而且就算全都正確無誤,他對自己的字彙也太有野心了。另一方面,在這個潘戴爾看來,歐斯納德就像對班尼叔叔的鈔票不屑一顧的人一樣,因為粗魯又擁有特權而言詞輕慢。但隨著彼此交談傾聽,潘戴爾似乎感覺到他倆之間油然生出了投契之情,宛如兩個遭放逐的人,為了共同的聯繫,樂意將各自偏見先擺到一邊。
「在公寓搞定之前,我會先住在巴拿馬飯店。」歐斯納德解釋,「那地方早在一個月前就該準備妥的。」
「都是這樣的,歐斯納德先生,全世界的建商都一樣。我以前就說過很多遍了,現在還是要再說一遍。廷巴克圖或紐約市,不管您在哪裡都一樣,沒有哪一行像建商那麼沒效率的。」
「您那裡五點鐘很安靜,是不是?五點時大家不會爭相奔逃吧?」
「五點鐘是我們的快樂時光,歐斯納德先生。我那些『午餐時間』先生已經安安穩穩回去工作,而我稱之為『飯前酒』的先生還沒出來玩樂。」他抑制住自謙的笑聲。「把您唬住了。騙您的。今天是星期五,所以我的飯前酒們回家陪老婆了。五點鐘,我可以全心全意地接待您。」
「您親自?本人?你們這些高貴的裁縫,很多是請奴才來做這種粗重工作的。」
「我恐怕算是您心目中那種老派的人,歐斯納德先生。對我來說,每位顧客都是挑戰。我量身,我裁剪,我試穿,而且從不在乎試多少回,只要能讓我做出最好的衣服。每套西裝製作都不離這個原則,我也會監督製作過程的各個步驟。」
「很好。多少?」歐斯納德追問。口氣帶有戲謔,但沒有挑釁的意思。
潘戴爾愉快的笑意更濃了。要是他說的是西班牙語─這已經是他的第二靈魂,而且是最偏愛的─他就毫無困難地回答這個問題。在巴拿馬,沒有人會對錢的事難為情,除非他缺錢。但眾所周知,你們英國上流階級對錢的態度是難以預料的,最有錢的人往往也是最節儉的人。
「我提供最好的,歐斯納德先生。我總是這麼說,勞斯萊斯可不是免費的,潘戴爾與布瑞斯維特也一樣。」
「那麼,多少?」
「嗯,先生,標準的兩件式,一套通常是兩千五百元,但也要看布料和樣式。西裝外套或休閒外套是一千五,背心六百。因為我們傾向用比較薄的料子,所以也會建議多裁製一條褲子搭配,第二件長褲的優惠價是八百。我聽見您嚇得說不出話啦,歐斯納德先生?」
「我以為公定價是一套兩千。」
「以前是,先生,直到三年前。那時候啊,唉呀呀,美金衝破地板,而我們P&B還是得買最頂級的布料。其實我不必多說,我們不計成本,全用最好的,很多都是歐洲貨,而且全部都是─」就在即將說出諸如「相關強勢貨幣」之類的奇言怪語之際,他頓時又改變了心意。「想想我說的,先生,你們上流階級現在穿的成衣─我拿洛夫‧勞倫當基準好了─也逼近兩千,有時甚至還更高。先生,可否容我告訴您,我們還有售後服務?我不認為您能回去一般的服飾店,告訴他們說您的肩膀有點緊,對吧?不可能有免費服務的。您想做什麼款式呢?」
「我?噢,一般的。先做幾套日常西服看看如何,之後再做全套。」
「全套?」潘戴爾語帶敬畏,對班尼叔叔的回憶此時全湧上心頭。「我一定有二十年沒聽過人家用這個詞了,歐斯納德先生。老天保佑。全套。我的天哪。」
再強調一次,這種時候,任何裁縫都會合情合理地收起情緒,回到他的海軍制服上。如果今天是其他的任何一天,潘戴爾也會這麼做。時間預約好了,告知價錢了,初步的社交問候也交換過了。但潘戴爾自得其樂。今天造訪銀行之行讓他覺得很孤單。他的英國顧客不多,英國朋友更少。露伊莎秉承先父遺訓,並不歡迎他們。
「P&B仍然是城裡唯一上得了檯面的,對吧?」歐斯納德問。「替巴拿馬最頂級、最聰明的大戶量製衣服的裁縫師?」
聽到「大戶」這個詞,潘戴爾微微一笑。「我們確實這麼認為,先生。不是自鳴得意,但我們以我們的成就為榮。我可以告訴您,過去這十年並非一帆風順。坦白說,巴拿馬的品味並不怎麼樣。或者應該說,在我們來之前是這個樣子。我們得先教育他們,才能向他們推銷。花這麼多錢就為了一套西裝?他們以為我們瘋了,甚至比發瘋還糟。我很欣慰地告訴您,慢慢地,大家也就接受了,一直到現在仍是如此。他們開始了解,我們不只是把西裝扔給他們,要他們付錢;我們提供維護,修改,我們就在這裡等他們回來,我們是朋友,也是後援者,我們是人哪。您該不會是新聞界的朋友吧,先生?最近邁阿密先鋒報的本地版登出一篇報導,讓我們受寵若驚,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剛好看見了?」
「我一定錯過了。」
「嗯,歐斯納德先生,這麼說吧。要是您不介意,我想用比較嚴肅的態度告訴您。我們幫總統、律師、銀行家、大主教、立法議員、將軍和艦隊司令治裝。我們替能欣賞訂製西服、也負擔得起的人治裝,無論其種族、宗教或聲望。您覺得如何?」
「很有前途,真的,非常有前途。那麼,五點鐘,快樂時光,歐斯納德。」
「五點鐘,歐斯納德先生。我很期待。」
「就我們兩個。」
「又一個好顧客,瑪塔。」瑪塔帶著一疊帳單進來時,潘戴爾這麼告訴她。
但他對瑪塔說話的模樣從來就不太自然,連她聽他說話的樣子也是:傷痕累累的頭部撇向其他地方,聰慧的黑眼睛看著別處,烏黑的頭髮如簾幕般遮住她最糟的部分。
‧
就是這樣。潘戴爾很愉快,被捧得飄飄然,雖然事後他說自己是個自負的笨蛋。這位歐斯納德顯然是個人物,潘戴爾就像班尼叔叔一樣喜愛大人物;更何況,不管露伊莎和她已故的父親怎麼說,英國人比大多數人更像大人物。或許這麼多年來他背棄的那個國家,其實還是個不賴的地方。歐斯納德完全沒提自己的職業,潘戴爾不以為意。許多顧客都絕口不提,其他就算提了也未必是真的。他很愉快,他無法未卜先知。放下電話,埋首繼續做他的艦隊司令制服,直到快樂週五的正午慌亂展開。大家就是這麼稱呼週五午餐時間的。直到歐斯納德進來,摧毀了潘戴爾最後一絲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