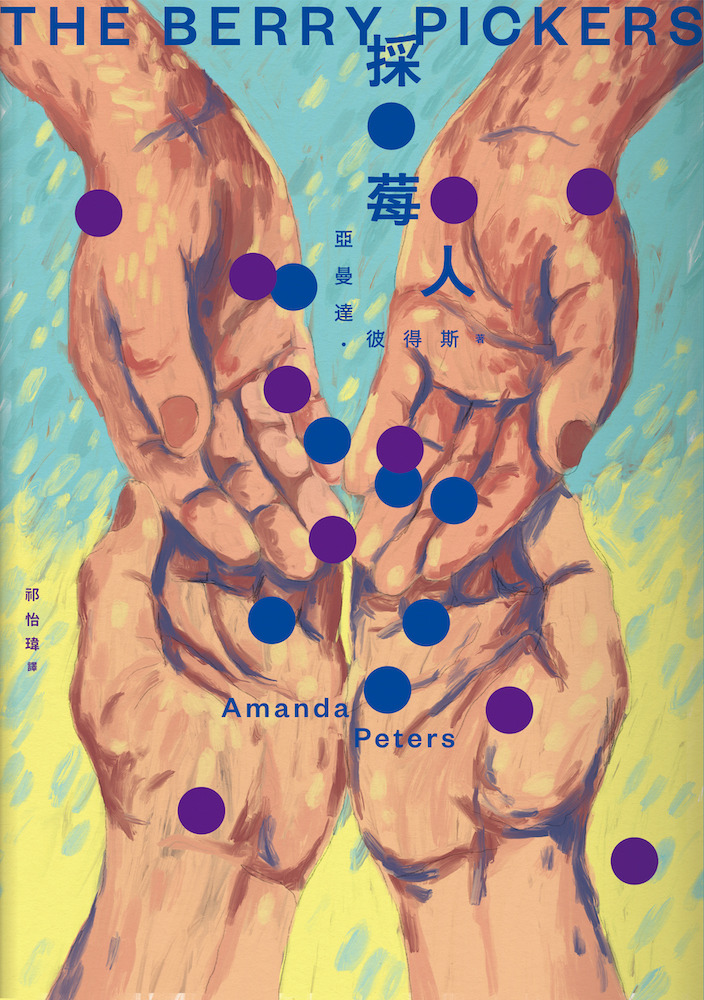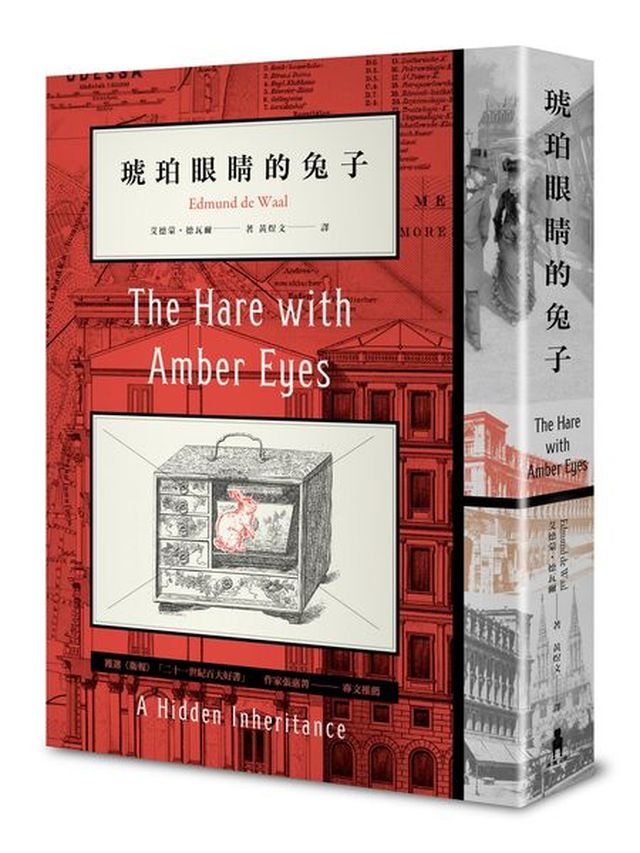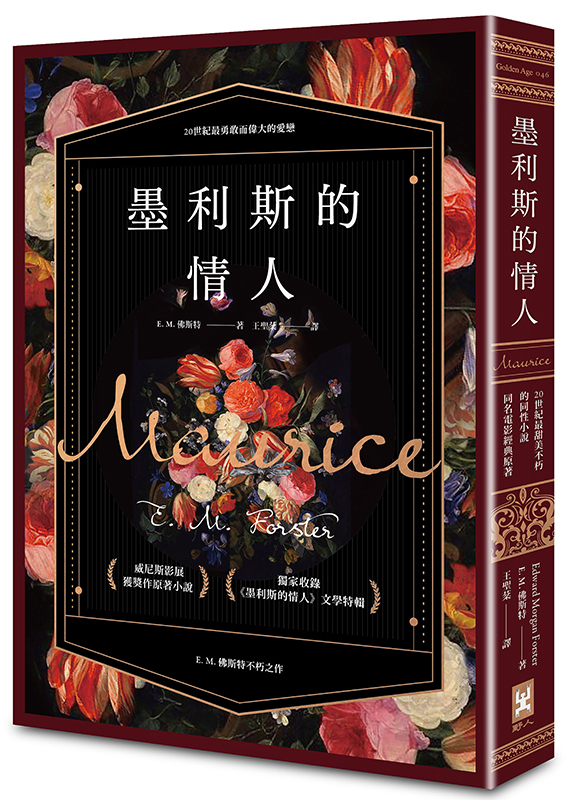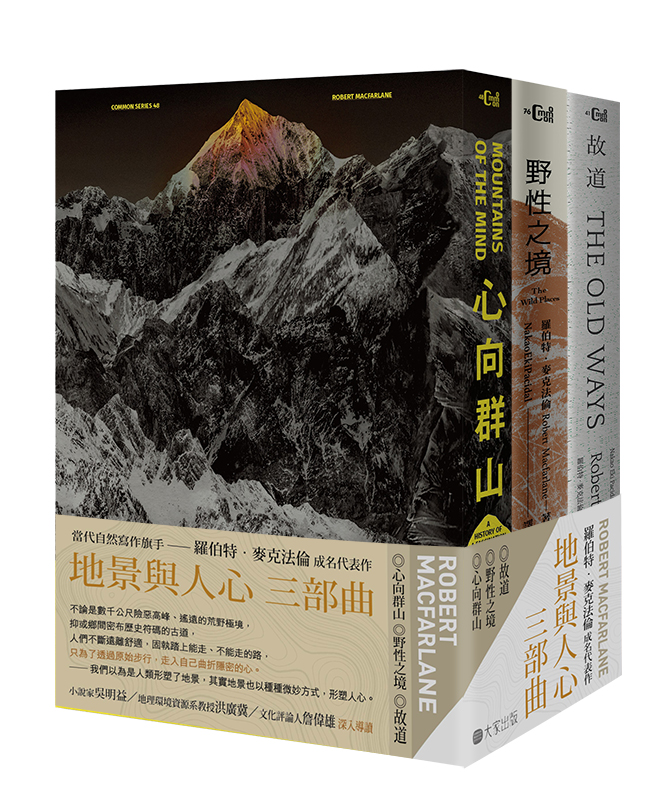哪裡都不去了
時間是各語系的音節,
而你眼裡就是我的歐陸
★法國電影新浪潮代表導演—楚浮(François Truffaut)經典改編原著
★ [ fps ]書系:導演與小說家的跨文本經典對話,精裝首發
★突破傳統文學體裁的全書信體表現,簡白、節制、鋪陳縝密;三角關係的曖昧與掙脫,愛和性的試探、迷亂;二十世紀初的道德難題,二十一世紀觀點再定錨
「不不不、我愛的是他們兩個。」(性是再簡單不過的問題)
楚浮:「大部分我的電影都表達了對一本書的崇敬。」
突破傳統文學體裁的全書信體表現,簡白、節制、鋪陳縝密
三角關係的曖昧與掙脫,愛和性的試探、迷亂
二十世紀初的道德難題,二十一世紀觀點再定錨
兩個英國女孩與歐陸∣無論熾熱與淡泊,每一段情感都有開始與結束,所有人在國籍、語言、信仰種種限制內找到理想,直視自身缺陷並尋找平衡。安娜、米瑞兒與克羅德三人關係之轉變,非典型多邊戀,各別往返書信裡陳述的是對愛(與自我)的推敲、鑿刻與試探,性只是最直言不諱的途徑。英國姊妹自幼教養中,深信有命中注定的另一半,為之奉獻、喜樂;而極具魅力的法國男孩克羅德,成為了兩個女孩的激情燃點,更是視野的拓望者。
姊妹一冷一熱,心緒卻反之一如湍急瀑流、一如悠揚靜水,藉由無數表白,釐清自己,言辭坦然;男孩多情善感,心猿意馬,機運主義地開啟與結束,然則一生擺盪,仍為廣袤之陸。愛情宛若政治寓言,機巧難測,島嶼遙望大陸,大陸渴望更多擁抱。本書以日記與書信體呈現三名青年男女戀情的幽微婉轉,大量言外之意於文字留白處被細膩暈染而出—臆測與假想,歡快與不安。
故事多方隱喻,特別是女性在二十世紀初的舊時代束縛下,所表現的任性與纖細,獲得法國導演楚浮的青睞,轉化為大銀幕影像,以心理寫實的電影語法,描繪三人情愛曲折,讓小說與電影互為援引;反覆的重逢與告別裡,情感中人的念想瞬息萬變,為愛疲於奔命,甚至楚浮與侯歇對結局的鋪排各異,更似一場觀點對奕,讓原已糾纏難解的文本,格外耐人尋味。
作者∣亨利-皮耶.侯歇 Henri-Pierre Roché(1979-1959)
生於法國巴黎,一次大戰期間,從事記者工作,同時是藝術藏家與經銷商,其最為人知是將畢卡索與杜象的作品引薦至美國,對於巴黎藝術和達達運動影響深遠。侯歇於一九五三年以七十四歲高齡完成半自傳體小說《夏日之戀》(Jules Et Jim),法國新浪潮代表導演—楚浮初見本書時驚為天人,約定共同完成電影改編劇本,故事所述之三角戀情衝擊了世俗倫理;而一九五六年出版的《兩個英國女孩與歐陸》靈感則源自侯歇的生活。兩部小說雖出自高齡之手,卻為當時法國浪漫主義注入新鮮的活力。
譯者∣黃琪雯
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法文筆譯組畢業。譯有《爸爸,我們去哪裡?》、《難分離》、《雨傘默默》、《我答應》、《溫柔之歌》、《零公里》等書,以及法語電視影片數部。
米瑞兒給克羅德
第一部 三人行
01 邂逅
02 米瑞兒、安娜和克羅德
03 左岸
04 這裡那裡
05 軍人克羅德
06 克羅德在倫敦
07 小島
第二部 米瑞兒的拒絕
08 隨意地包紮傷口
09 或許
10 克蕾兒
11 分開
12 米瑞兒一九○三的日記
13 米瑞兒的告解
第三部 安娜與克羅德
14 安娜與克羅德重新發現對方
15 安娜、克羅德以及穆夫
16 長吻
17 兩姊妹
18 透過安娜
19 安娜結婚
第四部 米瑞兒
20 那三天
21 漩渦
22 四年之後
23 十三年之後
試閱(一):
01邂逅 LA RENCONTRE
克羅德的日記
一八九九年復活節於都蘭
我坐在鞦韆上,雙手沒扶著鞦韆繩,身旁圍繞著一群孩子。其中一個較年長的,為了替年紀較小的孩子推鞦韆,猛然拉了一下繩子,使我往後倒。為了不負自己「鋼腿」的美名,我努力想站直身子,雙膝卻發出喀擦的聲響,一陣尖銳刺骨的疼痛,讓我無法起身。當疼痛感褪去,勉強行走。隔日膝蓋腫大如瓜,也無法彎曲了。
醫生宣告我的韌帶斷裂,必須臥床六個星期,而且膝蓋可能就此變得脆弱。
虛榮心讓我得到了懲罰。我跛著腳返回巴黎,躺臥在床並且拚命閱讀。
一八九九年五月十五日
我的法國朋友來看我。有一天,當我拄著拐杖經過克蕾兒(我的母親)的會客室,看到一名年輕英國女孩。克蕾兒向我提過她,印象頗佳。我向她點個頭,正猶豫要不要進客廳,她坦率的微笑鼓勵著我,於是我走到她面前自我介紹。和其他的法國朋友比起來,她的容貌略微遜色,較不活潑,卻有一種敏感堅定又富有責任感的神情。克蕾兒進入會客室,建議我們可以交換語言。安娜‧布朗和我一樣都是十九歲,戴了副夾鼻眼鏡。當她第一次拿下眼鏡,彷彿見到她的裸體似的,讓我有著靦腆中帶點有趣的感覺。
我躺了一個多月,學校和畫室的事都拋得遠遠的。安娜‧布朗時常來看我,我們一會兒用英文交談,一會兒用法文。她讓我對她的國家產生了極大興趣。對我而言,那是個難以理解、充滿矛盾的地方:個人謙遜修養與民族尊嚴、因循守舊與莎士比亞、聖經與威士忌,看似相互矛盾卻又並存。
她每次都能繼續聊起上回未完的話題,而且總坐在離我的床兩步之遠,從不再靠近一些。
某天一名四歲小女孩進來打斷我們的談話。她將她的洋娃娃交給我,向我告狀,說她的小女兒如何不乖。我掀起洋娃娃小小的裙子,在小屁股上打了幾下。
安娜‧布朗紅了臉,顯得很不自在。當晚她告訴克蕾兒,一位英國紳士,即便對一只洋娃娃,也絕不會做出這種動作。
安娜熱衷雕塑,為此貢獻所有心力。由於剛到法國,所以不了解歐洲藝術。
她問我:「你熟悉英國畫家嗎?」
「我知道一些。伯恩・瓊斯、泰納、還有瓦茲畫的〈希望〉:一位年輕女孩矇著眼睛坐在地球上,傾聽豎琴最末端的弦發出聲響……」
「天啊,那是我最喜歡的一幅畫!」
六月二十五日
經過一段時間的抗拒,她和我一樣,喜歡上羅丹雕刻的〈巴爾札克〉;又經過另一段時間的抗拒(我真喜歡這些抗拒),她陪我到喜劇歌劇院兩次,聽夏邦泰的歌劇《露易絲》。
對於劇中人物露易絲和朱立安還沒結婚就同居,她感到遺憾。我對她說,他們倆若非放棄這段感情,就是繼續下去。
安娜回答:「面對這種無所適從的情況,必須能犧牲自我。朱立安應該等到露易絲成年。」
「總要有人能超越法律。」我回答道。
「或許吧!如果真是那樣,那些人就要有犧牲奉獻的準備。」
我從朱爾・拉佛格的〈傳奇美德〉一詩中,摘了幾個段落念給她聽,在哈姆雷特洗手的那段情節時,她瞪大雙眼,作勢欲嘔。
她對我說:「我來這裡是想了解你們的國家和藝術。如果你要比較兩個國家的不同,那麼你也應該到我那裡,換我來向你介紹我的國家。和你們比起來,我們那裡的人比較封閉、拘謹,不過自有表達明理和異想天開的方式。」
「舉個例子來聽聽吧!」
安娜從她的學校、家人當中,找了幾個很有趣的例子,讓我起了想要跟著她去英國的念頭。
克蕾兒以讚許的眼光來看待我和安娜的友情。她會帶安娜上劇院、參加晚宴,而且每個星期都寫信給布朗太太,告知安娜在法國的近況。
我刻意讓安娜知道我欣賞她。不過,並非基於想和她有什麼曖昧的心理。她對我說:「我只是個普通的英國女孩。你應該認識我姊姊米瑞兒的,她大我兩歲,一直都是我的榜樣。由於米瑞兒有一頭金髮,當她還小的時候,人家都說她是一朵『黃花毛莨』,而她的燦爛笑容,為她贏得了『旭日光芒』的稱號。她比我活潑開朗,也比我懂事,集所有優點於一身。每場考試都能隨心所欲拿到好成績,也會將莎士比亞的戲劇搬上舞台,並且扮演主角奧菲莉亞,在我們村裡很活躍。我們姊妹一點都不相像,我只懂雕塑而已。我很想念米瑞兒,想跟她一起聽你說說話。」
安娜給我看米瑞兒的畫像。畫中的她十三歲,圓臉,有著年輕女先知的神氣,嘴唇緊抿,眉型俐落,眼神認真又帶著幽默。
我心頭一震。
我問安娜:「那她現在長什麼樣子呢?」
安娜回答:「你來看就知道!」
慢慢地一點一滴累積,終於和克蕾兒商量好,我們要一起到英國,和布朗一家人好好度個假。
試閱(二):
02米瑞兒、安娜和克羅德 MURIEL, ANNE ET CLAUDE
克羅德的日記
一八九九年八月於英國威爾斯
青翠嶙峋矗立在海中的小丘、起伏不平的海灘、小港灣、高爾夫球場、三三兩兩不成群的房子。
安娜獨自迎接我和克蕾兒的到來。
當天早上,有人偷走了我們別墅房東菲林特先生的小艇。負責偵察的警員詢問他是否要備案。
菲林特先生表示:「小偷比我更需要那艘小艇,所以我不要備案。」
他的反應讓我非常驚訝。交談之下,發現菲林特先生和我一樣,都是托爾斯泰主義的信奉者,認為擁有私人財富是不應該的,只不過他奉行得比我徹底。
安娜說:「對我們這裡的人來說,這種處世態度是個特例。」她又補充一句:「你明天晚上就可以見到米瑞兒了。」
隔天午餐時刻,我們母子和布朗太太,還有安娜的弟弟亞歷斯以及查理見了面。我和克蕾兒都覺得他們具有英國人的保守謹慎,而且這種態度是根深柢固,難以撼動的。安娜對他們說我們倆相處的事情。這樣也好,不過還是應該要自己判斷,不要以偏概全。
從這兩個男孩的態度看來,那些法寇達(Fachoda)事件的紛擾、英法兩國戰事一觸即發的威脅,皆已不復存在。
安娜突然出現,滿臉驚訝地說,由於米瑞兒眼部疼痛,晚上只能彼此寒暄一下,讓她多休養。想要深入認識,還得等等。
晚餐時,米瑞兒現身了。她比安娜略矮,擁有和克蕾兒年輕時代一樣的柔順金髮,眼睛上纏著一條綠色塔夫綢和棉花混紡的繃帶。她似乎很不舒服,動作緩慢,偶爾會用根手指撐開繃帶,看餐盤裡有什麼東西。她的聲音從喉頭發出,咕噥著聽不真切,背脊挺得直直的,一雙白晰大手顯得十分光滑。
在英國的最初幾天,日子過得平淡無趣。布朗太太分派家事,而每個人準確做好分內之事。
有天傍晚,安娜問我:「晚餐之後你有沒有空陪陪我呢?」
「當然有。」
晚餐之後,我們一起外出。安娜離開家門時,步履緩慢,然後她跑了起來,速度快得猶如自弦上射出的飛箭,對我大喊:「來抓我啊!」
我忘掉膝蓋受的傷,抓到了她。
我們來到了小港灣,她跳上一艘小艇,「人家借給我的。我們到對岸去吧!」
皎潔的月光,漲起的潮水,遼闊的河流。我們各划著一把槳,她在前,我在後。當船底碰到了沙灘,安娜沒脫下草底帆布鞋便跳入水中,我們合力將小艇拉上岸。她朝著村裡光源的方向走去,然後停下來對我說:「今晚我沒有別的事要忙,想要跟你聊聊,就像在巴黎的時候一樣。有些話我想告訴你,卻不知道如何說出口……」
「妳說說看吧!」
「是這樣的,」她一邊說,一邊在較低的岩石上坐了下來,「事情的發展出乎我預料之外。我們的母親互相欣賞,非常合得來。我的兩個弟弟整天不是在沼澤打獵,就是划船釣魚;而你和我也正要開始畫畫。」
「問題就出在米瑞兒身上。有一天深夜她瞞著我母親,拿了一本書做預習報告,要交給老師,那本書談論的是她崇拜的偶像——達爾文,結果她為了這個報告過度勞累而傷了眼睛。目前我們還不知道傷勢有多嚴重。」
「母親認為米瑞兒應該先問過她的意思,也不應該有事情瞞著她,這是為人子女應守的本分。米瑞兒承認自己讓眼睛過於勞累,也承認要為眼睛受傷一事負責。可是她聲稱必須勇於冒險,才能知道自己的極限,而且無需事事都要問過母親。」
「米瑞兒,真有妳的!」我讚嘆。
「母親說米瑞兒只會瞞著她。總之,整個家裡為了這件事弄得烏煙瘴氣。我邀請你們來,卻讓你們過得一點意思也沒有。主要是因為米瑞兒一直是家中的活力源泉,現在這個活力源泉卻暫時枯竭,而米瑞兒生悶氣,也讓我心情很沉重,今天晚上剛好可以乘機向你解釋一番。我剛才所說的話,請你一定要轉達給你母親。」
「一言為定。」
「然後……然後……」安娜沒有將話說完。我們陷入一片靜默當中。
我想握住她的手。我聽到安娜的聲音彷彿幻音般遠遠地傳來,在我腦海中說著:「然後……快點抱住我吧!」
我為自己有這種輕浮的念頭感到自責。我對她說:「當然我們都因為米瑞兒發生的事情而感到難過。我還不認識她,不過我向妳保證,當我看到她的雙眼之後……」
「那時一切都會不同了!」安娜說完,跳下岩石跑向水邊。
潮水已經消退,我們划著小艇前進。水流將我們推向海洋,而我們愉悅地往相反方向奮力划動,不讓小艇滑向海上。最後我們偏離方向,在一片淤泥地靠岸。
隔天一同前往懸崖高處去作畫。
我對安娜說:「我耐心等著米瑞兒康復。儘管沒能見到她,但我還是很開心能來這裡。今天下午一起去那個荒廢的城堡看看吧,妳覺得如何?」
她猶豫了一下,回答我說:「好的。」
那座老舊的城堡從高處俯視整個港灣。城堡裡有個鏡子迷宮,如果在裡面迷了路,可能永遠都走不出來。進入迷宮之中,只有我們兩人,單獨面對著無窮無盡的鏡中影像。我們在迷宮中漫步、迷路,有時相距只有兩步遠,卻瞬間自對方眼前消失,就算聽見對方聲音,也找不著彼此。我們迎面碰上對方之後,便一同前行。我開始想要離開這裡到外面去。安娜拉起我的手放在她肩上對我說:「別放開,讓我來找離開的出口。」她用涼鞋的鞋尖碰觸鏡子底端試著探路,樣子像個舞者,又像是善良溫柔的嚮導。這座迷宮適合接吻,就算在英格蘭,要親吻也應該南下到這座迷宮來。五分鐘之後,我們走出了那裡。
亞歷斯與查理教我和他們一起玩板球。草皮上除了安娜之外,共有十多個球員,不過我很遲鈍,總是搞不懂遊戲規則。亞歷斯拿筆記下每個人能將球投得多遠。我可以擲到八十一碼的距離。「這個距離算是不錯了,尤其對一個……」查理停了下來,沒繼續說下去。
亞歷斯接著說:「世界紀錄是一百三十碼。」
我們也打網球,只不過這兩個男生心中只想著打獵和釣魚。我們還一起除草,看著綠草硬生生自機器中噴出。
我們到海中游泳時,米瑞兒也會跟著去,不過她需要安娜攙扶帶路,像個盲人一樣。我們在海水中裸泳,男女分開約莫兩百公尺的距離,誰偷窺就會遭到驅離。儘管我的好奇心繞著女孩們打轉,但我還是挺喜歡這種不得不遵守的誠實。
漸漸的,米瑞兒在屋內走動次數越來越多。只不過我目前見到的她,並非安娜先前描繪那般優雅。在我眼中,她是一個逐漸痊癒的病患。她拆下了繃帶,換上大大的深色眼鏡,從鏡片中我看到她的雙眼腫脹無神。她拿著高爾夫球桿,在沒有球、雙眼無法視物的情況下練習揮桿,動作柔軟迅速。
夜晚時,我們一群年輕人聚在客廳玩猜謎、大風吹遊戲還有即興表演。米瑞兒輸了遊戲,我們罰她當場表演「奧菲莉」的一幕戲。閉著眼表演的她,散發出無比的光芒。
我和安娜常常在一起,周遭的人開始用一種意有所指的眼光看著我們,認為我們像是一對互相照顧、互相調侃的情侶,甚至房東菲林特先生也是這麼想。我和安娜總是清晨便提著折疊畫架,一同出門去作畫,順道繼續語言交換的課程。安娜有時會抱怨連連,等她發現這一點之後自己也覺得好笑。現在我好像有了個姊妹,感到非常高興。
一八九九年八月十五日
安娜對我說:「我邀米瑞兒明天和我們一起去。她雖然不能畫畫,但是可以散散步,享受一下山頂吹來的徐徐微風。」
安娜在前,米瑞兒緊跟在她身後,我則是押後,三個人就一個緊接一個,隨著綿延的山路往高處爬。米瑞兒戴著一頂帽簷寬大的綠色遮陽帽,說話聲音聽起來很熱情,字字句句清楚。她每走一步路,髖部會跟著扭擺,特別的姿勢,讓她每個步伐都顯得穩健堅決。不過對其他人來說,這種姿勢也許讓人覺得惹火。她這麼活潑的樣子,我還是第一次見到。她將濃密的金髮盤起,梳成一個髮髻,露出白皙的頸子,我私下給她一個「脖子姊姊」的稱號。
到了山頂我們坐下來。米瑞兒對我說:「安娜時常提起你的事情。當我眼睛還沒受傷的時候,她會讓我看你寄給她的書。那些書的內容我並沒有完全了解,論點也並非完全贊同,不過,整體而言,你讓我們大開眼界。我和安娜應該要如何謝謝你呢?」
「我想要揭開英國風土人情的神祕面紗。當然,對一個法國人而言這不是件容易的事,還好有安娜的指導。」我回答她。
安娜說話了:「米瑞兒比我更能幫上你的忙。」
米瑞兒回答:「或許是,也或許不是吧。只要你有心一定可以做到的。你教我講法文吧!我現在已經會照著字念了。我和安娜就負責讓你的英文更流暢,你覺得如何啊?」
「樂意之至!」
「那我們馬上開始吧!想要知道你發音上有什麼問題嗎?來,就是這些。」
米瑞兒滑稽地模仿我的腔調,慢慢說話,向我解釋清楚問題何在,然後要我重複念整段句子直到發音正確為止。
「至於我的法文發音如何,我念這篇〈狼與羔羊〉的寓言故事給你聽聽看。我念完之後,輪到安娜,接下來輪到你。」
米瑞兒開始嚴肅地誦讀起來,不過她忽而模仿大野狼發怒的語氣,忽而模仿羔羊天真的口吻,讓朗誦過程生動有趣,而她那令人無法理解的發音,也讓人忍俊不住。安娜和我不禁大笑起來,米瑞兒自己也是。安娜重新念一次這個寓言故事,口音就像是個已經巴黎化的英國女孩。最後我再一個一個音節分開念了一次。這是我們三人一同學習的開端。
一八九九年九月五日
安娜先前提過,米瑞兒樣樣拿第一。在三人當中,果然米瑞兒的學習力最強,這都要歸功於她的創造力和活力。我和安娜毫無保留地接納她的加入。「在我加入之前,已經開始注意你們了。」米瑞兒這麼說。從此我們變得形影不離。
我喜愛她們的謙遜和運動方面的表現,也從不道人長短。米瑞兒說過:「當我們有機會為別人服務,就別想著享受清閒。」她有時會引用聖經的語句,安娜會引用法國詩人魏倫的詩,而我則是會引述唐吉訶德那愚蠢的忠僕——桑丘所說的話語。
有一天,安娜有事走不開,米瑞兒問我是否可以陪她出門。她和安娜一樣,也想去城堡迷宮走走。安娜對她說:「可別指望克羅德帶妳走出迷宮。」然後我們兩人往城堡方向出發。
這一次我開始摸索出走迷宮的訣竅,也猜想到利用鏡角的可行性,不過我還是故意讓自己在裡頭迷路。我們在鏡子反射的影像中迷失了方向,無論往哪個方向小步前進,依然會迎頭撞上鏡子,彷彿置身萬花筒中。我們開始失去了耐性,米瑞兒對我說:「把你的手給我。」然後她用飽滿結實的手拉著我;另一隻手,則是手指往後翹起,露出了手指渦,迅速拍打著鏡子。隔著一個月重新上演的相同情境,讓我不禁為她們兩姊妹的異同之處而感動,也因她們都視我為兄弟而歡喜。這一次,米瑞兒比安娜花了更少的時間便帶我走出迷宮。
某天早上,我和米瑞兒兩人沒披上斗蓬風衣,就登上小山丘的頂端。突如其來的一場大雨,讓我們只得暫避於岩洞中。岩洞貼近地面,約二步寬,上覆有草皮如毯,草色泛黃。我們必須緊貼對方身體,以免淋溼。雨勢稍緩,但持續下著,而岩石讓人坐得很不舒服。我們玩起了史前穴居人的遊戲,假裝有穴居人對我們提出成千上萬的問題。不過,我不敢逾矩談論到假若我們有小孩的話題。
雨後天晴,我們不情願地下了山。在山上耽擱太久,趕不上午餐。布朗太太憂心忡忡,倒是安娜一點兒也不擔心。
米瑞兒和安娜渴望了解巴黎的風土人情,她們說服母親將島上的房子出租,而後一起到塞納河左岸生活八個月。兩個弟弟就留在學校,放假時再到巴黎會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