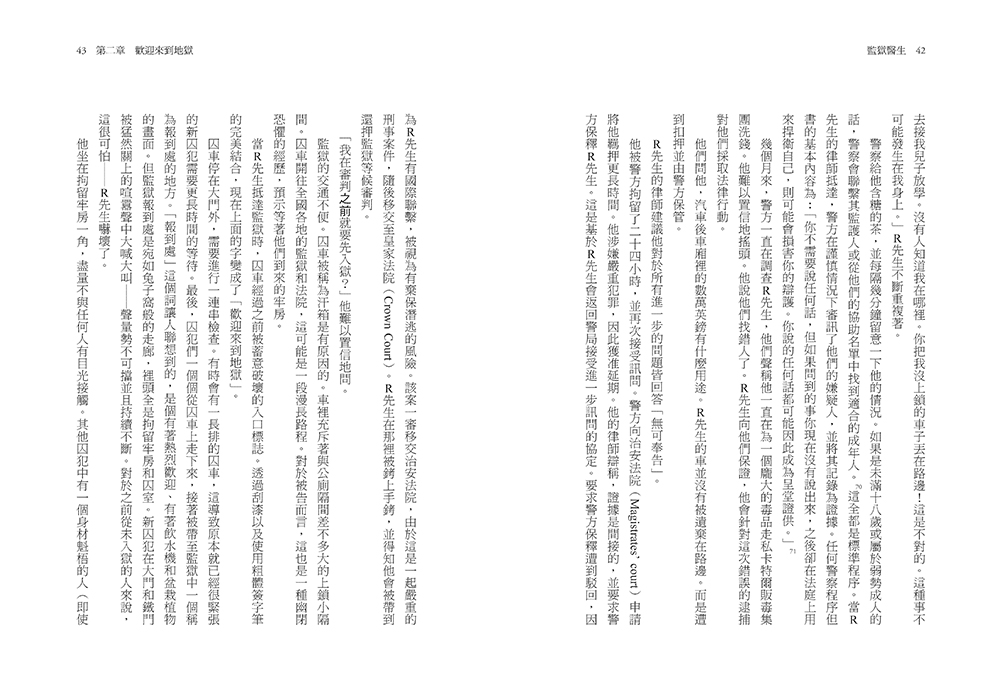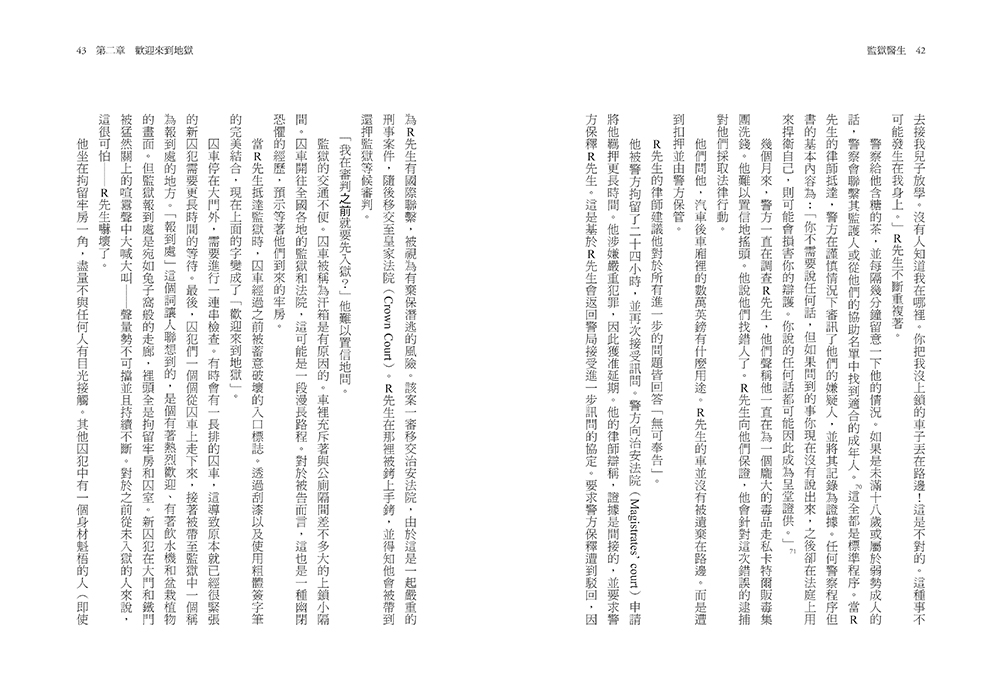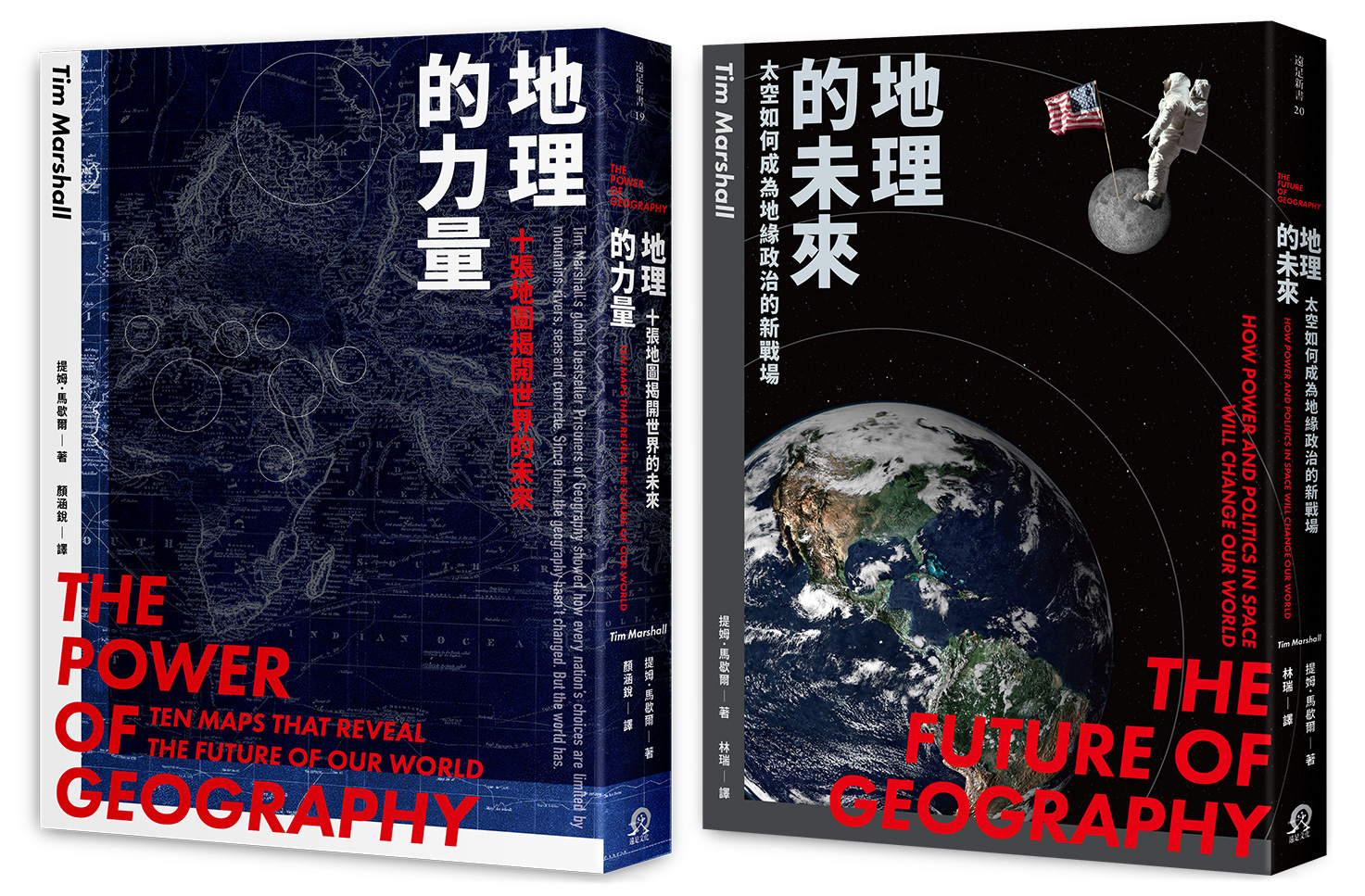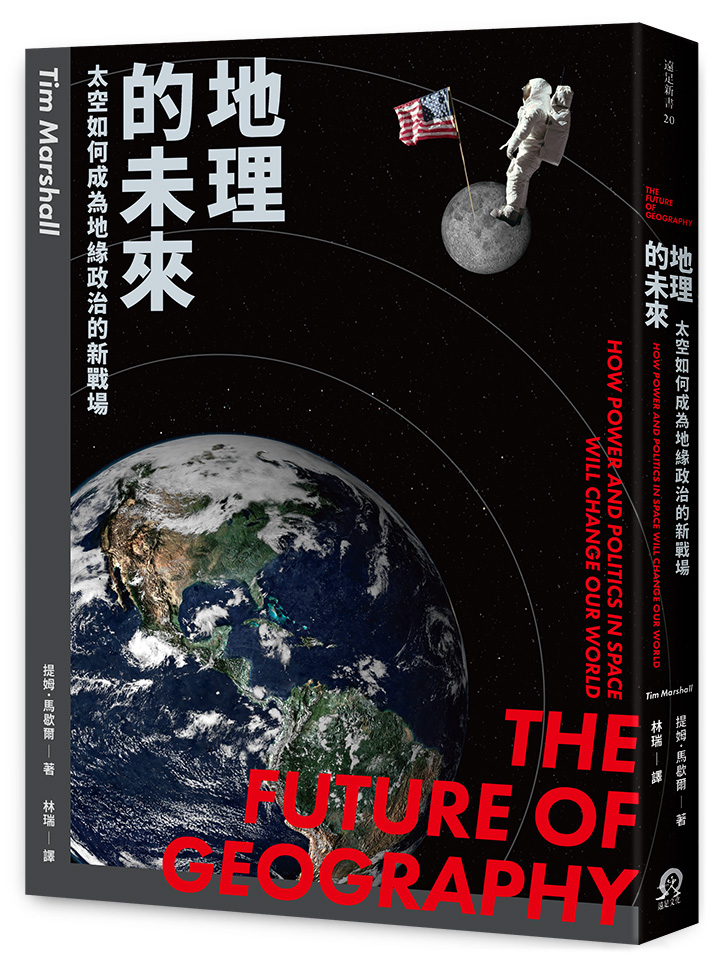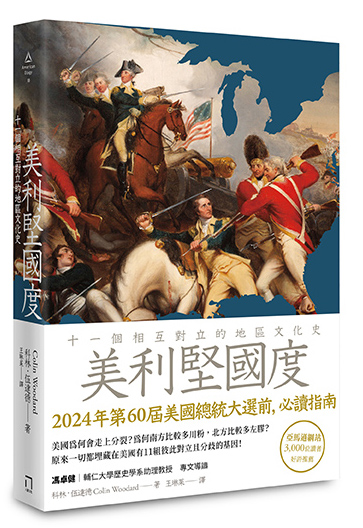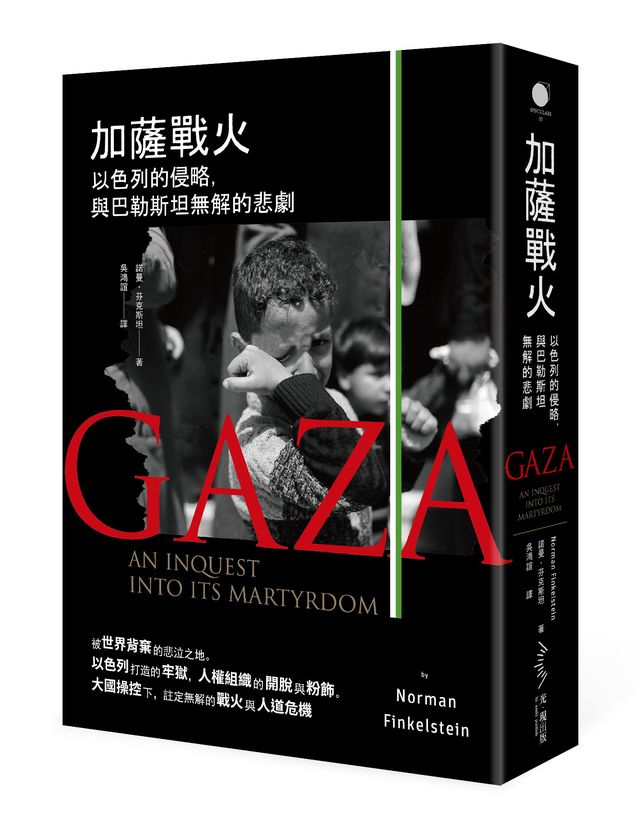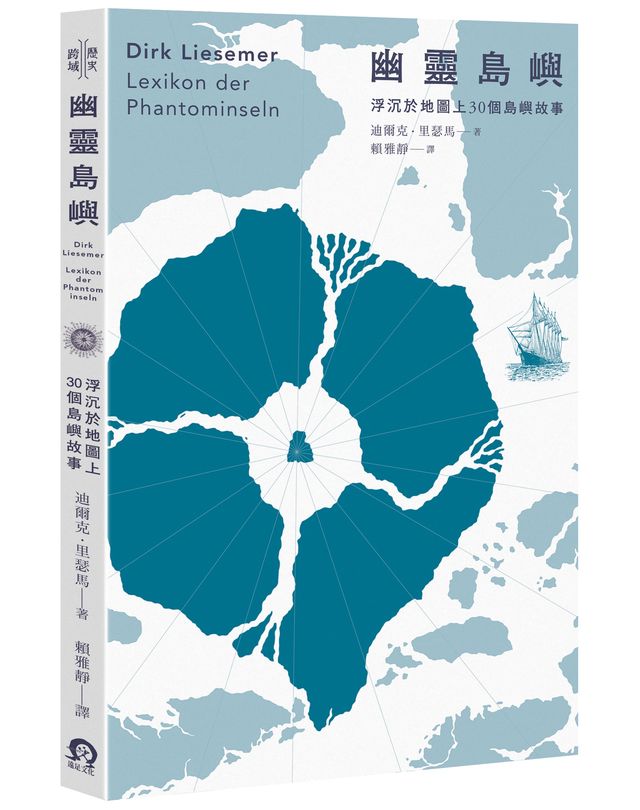在圍牆之後,他們是罪人,是病人,更是一個人─
一位監獄醫生在監獄之中看見的,那些被遺忘者的痛苦與生死……
當前全球的監獄系統普遍面臨著各種挑戰,包括人權問題、過度擁擠、缺乏醫療保健等等。然而,這些問題的影響對囚犯和監獄工作人員同樣巨大,而尤薩夫這位在監獄中照顧所有人健康的監獄醫生,就在這鐵幕圍牆之中,親眼見證了無數由此而生的悲劇與問題。
在書中,尤薩夫分享了他從一個初來乍到的新手到一個經驗豐富的醫生的轉變,並且描述了他在監獄系統中的工作經驗和所面臨的挑戰。他從一個監獄醫生的角度,細緻描繪了監獄醫療保健的現實,以及他如何應對各種困難情況,包括囚犯的心理健康問題、毒品成癮、自殺等等。
他親眼看著這些被奪去名字與尊嚴的人們在牢籠之中痛苦、受盡折磨,在渺小見方的囚室內,寒冷卻沒有暖氣貌似理所當然,受苦而無力拯救就像例行公事,藥物需要控制以避免被囚犯拿去交易,為囚犯看診需要隨時緊盯出口位置以及緊急鈴避免憾事發生,這一切衝擊著他對於成為一位醫生的應有的信念。
在這裡,他們不相信醫生,整個體制也告訴他們絕對不要相信囚犯,但他卻從未放棄過他們,也從未過問他們所犯下的罪刑,因為在犯人這個身分之上,他們也是人,是病人,也是他需要救助的人。
尤薩夫透過自身親眼所見的種種故事,刻劃出令人難以忘卻的無數生死與苦難,讓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監獄系統中的挑戰和困難,進而反思和探討如何改善監獄系統。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認識監獄系統中包括囚犯、監獄工作人員、政府等等的各方利益關係。此外,尤薩夫更點出了監獄中存在的種族不平等和性別歧視,這些問題對囚犯和監獄工作人員的影響非常深遠。
對許多人來說,在監獄圍牆之後的人們是犯罪者,他們觸犯了法律,更甚者有些還剝奪了他人的性命,他們甚至不應該擁有人權,或應該要剝奪屬於「人」的某些權利當作懲罰。然而對於身為醫生的尤薩夫來說,不論在圍牆之內或圍牆之外,他們都與你我相同,都是活生生的生命,不應該因此刻意的遺忘他們,並且對他們在其中的遭遇不聞不問,甚至認為他們都活該如此,因為生而為人,我們都應保有良知與人性。
李茂生 | 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兼任教授
邱瑀庭 Jessie | 小太陽社工師
張誌閔 | 諮商心理師
黃明鎮牧師 | 台灣更生團契總幹事
法律白話文運動
感動推薦
沙赫德•尤薩夫醫生是一名全科醫生,服務於監獄、藥物濫用和遊民社區。他入圍了2016年巴斯極短篇小說獎(Bath Flash Fiction Prize),並獲得了2017年的Faber & Faber FAB Prize。同時,沙赫德也獲得並參與了2019年西米德蘭茲郡的204室寫作指導計劃和Middle Way Mentoring計劃(一項為期兩年的專業發展計劃,主要針對位於中部地區的黑人、亞裔、少數族裔 〔BAME〕 之作家)。
李伊婷
1980年生,高雄人。
曾任職文創產業國外行銷
現為自由工作者及譯者。
譯有小說、心理勵志、醫療保健、商業、運動等多種書籍。
譯作有:《寫作的本事》、《自我提問的力量》、《吃出好心情》、《紅土之王:拉法‧納達爾》、《百倍獲利,複利投資選股指南》、《我睡不著的那一年》、《聖殿騎士懸疑系列之一聖殿之劍》等等。
聯絡方式:stellayiting@gmail.com
前言 :一個壞掉的體系
第一章:罪犯的健康照護
第二章:歡迎來到地獄
第三章:現在醫生可以見你了
第四章:無期徒刑者
第五章:團隊合作
第六章:創傷
第七章:病史
第八章:黑眼星期五
第九章:隔離
第十章:脆弱的監獄單位
第十一章:佛萊迪•墨裘瑞
第十二章:何人,何時,何地,如何?
第十三章:解放
後記:真實比虛構更奇怪
參考資料
致謝
精彩試閱:
第六章
創傷
警鈴在無線電中劈啪作響。
「D牢區急救代碼,刺傷。奧斯卡一號前往。飯店三號前往。指揮部叫了救護車!」
就這麼開始了。
我們使用北約音標字母(NATO phonetic alphabet)溝通。飯店是健康照護,奧斯卡一號是管理或監獄領導。飯店三號是負責處理所有緊急情況的護理師或護理人員。飯店三號通常是史蒂芬護理師。
史蒂芬護理師危機處理表現出色:處變不驚,特別令人安心。她被暱稱為納洛酮(Naloxone)女王,擅長用這種藥物把人救活,否則他們會死於鴉片類藥物過量。史蒂芬是一個敏感的氣喘患者,她自己每隔幾個月就需要住院治療。我們所有人都覺得由她照護這些吸食有毒物質的男人實在諷刺極了。然而,她把重達十二公斤的醫療應變包扛在背上開始奔跑,其中有著氧氣瓶,以及她進入未知世界時可能會用到的所有設備及藥物。
在另一天,史蒂芬可能正在回覆紅色代碼(Code Red)。紅色代碼是涉及血液的緊急情況,可能是毆打、刺傷或自殘,所有這些都是時常發生的事。史蒂芬會和一名醫療助理一起趕至代碼處,可能是克莉斯、維多利亞或蘇菲其中一人。他們有幾分鐘時間趕至地點,那個地點可能是監獄中的任何地方。我們所有人幾乎每天都處於從一個緊急情況衝到下一個緊急情況的狀態,根本沒有任何空檔可以寫下記錄。而值得一再重複的是,醫療記錄可以阻止專業律師們在死因裁判法庭上把你撕成碎片。
監獄中一個主要問題是香料。一些囚犯沉迷於香料,為了它什麼事都做得出來,他們甚至為了得到它而任人毆打或羞辱。一個臭名昭彰的人會「以一拳換一口」,讓人們使盡全力揍他的臉,只為吸一口香料。他下巴脫臼過無數次了,總是歪著嘴笑地走來走去。獄警們告訴我,這些攻擊有時會被拍下並上傳到網路上,需要由安全團隊撤下,以免損害監獄的聲譽。我們已經被譽為英國最暴力的監獄之一。
我問史蒂芬,這些人是怎麼在監獄裡取得香料和其他毒品的。畢竟,囚犯進來時都有進行搜身。
「他們在家人來探訪時拿到的,然後擰緊螺絲,或者把它放進他們的監獄口袋裡,」她若無其事地回答。
我一頭霧水。「什麼?」我傻傻地問。
「他們『塞』。」
我搖了搖頭......
「他們把它塞進屁股裡,」史蒂芬直率地說。
「我以為那個叫『打包』?」我回想著。
「同一件噁心的事可以有很多不同說法。有時,假如有人被懷疑藏帶毒品但他否認,其他囚犯會給他挖湯匙。」史蒂芬說,對於我不了解監獄術語似乎感到很有趣。當她說挖湯匙時,我腦中的畫面是一對熟睡的情侶保護性地、充滿愛意地交疊在一起。
「不是你想的那樣,」她說,彷彿讀到了我的心思。「在監獄裡,挖湯匙指的是他們真的會把湯匙插進某人的屁眼裡,然後四處挖找包裹。這會導致內部損傷,我們第一次聽到這件事是有人造成紅色代碼,而他們的肛門大量出血。我們必須排除強姦情況並且召集鑒識小組進來,但十之八九是挖湯匙造成的,但這仍被歸類為性犯罪。」
我震驚地用手摀住嘴,一臉難以置信的誇張表情。
最兇狠的攻擊,比捅傷(或以監獄自製刀片刺傷)和用裝有鮪魚罐頭的襪子毆打更糟糕的,就是被糖水攻擊。把一大袋糖加進一壺水中並加熱,把這種熔化的糖漿潑到人身上時,會灼傷每一層的皮膚和細胞組織,這比一般的熱水燒燙傷更嚴重,會導致永久性毀容。如果把糖水潑在臉上,可能會導致失明甚至死亡。被糖水燙過之人的慘叫聲仍是我揮之不去的噩夢。
糖水襲擊的受害者總是傷勢嚴重,無法在側翼樓得到照護。這些可憐的人,失明、慘叫、驚嚇地顫抖不止,必須被護送至門診部。把濕潤和冷卻藥膏輕輕敷在他們紅腫的傷口上。我們一邊極其小心地照顧他們,一邊表達歉意,因為我們知道他們正承受著難以忍受的痛苦。我們極其謹慎地照護這些人,也說著安慰及安撫的話語,然而在極度痛苦的尖叫聲中,這些話他們幾乎聽不見。
除了急救代碼和紅色代碼,每一次牢房火災也會召集醫護人員前往。僅僅在二○一一年,英國監獄就發生了將近一千起牢房火災—這個系統是一個積極的地獄。牢房火災可能是你在獄中目睹過最痛苦難忘的事件,而你永遠不會忘記第一次。我的第一次在某天早上來臨了。
一個無線電呼叫傳來,要求醫生緊急前往牢房區。這絕對不是個好預兆。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向那個地點。我順著燃燒的氣味和側翼樓上鳴響的煙霧警報器前進,直到我看到一群獄警,個個身材魁梧的男人,以能在健身房裡忍受多少身體上的疼痛而自豪,相互扶持地蜷縮在平台角落。他們無聲地哭泣—顯然處於震驚狀態。我急忙趕到那間牢房,看到整個牢房被黑煙吞沒,仔細一看,我可以看到床墊上燒了一個大洞,地板是濕的—但病人不見了。
我很困惑。然後一名獄警介入指引我。原來,每個牢房都裝有一個撒水設備,這是一個可以拆卸的圓孔,在無需打開牢門的情況下,軟管可以穿過圓孔,但這會有回燃和進一步擴散的風險。監獄是一個火藥桶,火勢可能會從一個牢房蔓延到另一個牢房。獄警們已經透過門上的孔洞撲滅了火焰,但牢房裡仍籠罩在有毒煙霧中。獄警們小心翼翼地把這名男子抬到鄰近的一間空牢房接受治療。在搬移過程中,他燒傷的皮膚在獄警手中如紙片般剝落,露出燒焦發黑的肌肉。可以理解,獄警們因目睹這一切而感到崩潰。
我跑到新地點協助我的同事,他們已在努力救治,因為病患的靜脈嚴重受損,他們正盡力尋找他身上任何沒有被燒傷的區域以便注射止痛針。一眼望去,我估計他至少有百分之六十的燒傷面積,並且有嚴重脫水、休克、感染和死亡風險。終於,我們在他的腳上找到一小塊沒有被火燒傷的皮膚,我固定了一根珍貴的針頭,為他注射嗎啡和液體。護理師們告訴我,這個人在痛苦哭喊中跟他們說了一些事發經過。他一直在吸食香料接著失去意識。他把點燃的捲菸掉在自己身上。當他身上的纖維衣物著火,置身在火焰中時,他恢復了知覺。
空中救護車在幾分鐘內抵達,他們把他送到當地的燒傷中心,幸運的是,距離只有幾英里遠。接下來的幾天,我們都想著他的情況如何,但沒有任何消息。終於,在一週後,所有在當時參與照護他、奮力維繫其生命的人員—官員和健康照護人員—都被叫到教堂,我們被告知那名病患因傷勢嚴重而死。典獄長和一名健康照護代表必須親自向他的親屬通報這個消息。他們悲痛欲絕—他留下一個年幼的家庭。
除了香料的危害外,火災的風險也總是很高,因為男人們有時會用沸騰的水壺互相攻擊,這可能會導致電器走火。二○一五年,監獄禁止吸煙和打火機。但這些人很聰明,可以拆開水壺取出電線,輕鬆點火。
香菸常被私帶進來並以高價出售。當囚犯用光時,他們會抽塗上香料、煤焦油洗髮精或任何他們能找到的其他化學物質的白紙。香蕉曾一度被禁止,因為囚犯過去常常偷香蕉皮,他們把香蕉皮曬乾並吸食,誤以為吸食香蕉皮會讓人自然嗨。囚犯有時甚至會吸食燃燒的塑膠來得到快感。無論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他們都試圖忘卻一切。
沒有人想死在獄中。我們竭盡所能挽救生命,讓犯人在服完刑後能夠回家。如果有人看起來很沮喪或沉默寡言,我們分析他們的精神狀態,並詢問他們是否有任何自殘念頭或計劃。In-reach心理健康服務團隊每天都會收到許多這樣的轉診。迪恩特別擅長讓人們在情緒問題上對他坦誠以待。他幾乎是不停在監獄裡跑來跑去,從一場心理危機到另一場心理危機,並做出實質的改變。有些人會以割傷或摳抓自己來應對焦慮,也就是所謂的「切割」。他們的身體在康復的各個階段皆佈滿傷疤—但他們堅信這只是一種應對機制,他們實際上並不想死。有一度,在差不多一千出頭的人口中,大約有七十人加入了ACCT照護計劃。這是一個可怕的統計數據。
史蒂芬因一天處理三十件急救呼叫而受到典獄長的嘉獎。那段期間,監獄裡有危險的鴉片類藥物吩坦尼(fentanyl)滲入。它起效迅速,囚犯們把它與香料混在一起吸食。許多人會立刻中止呼吸或癲癇重積狀態。儘管給了雙倍劑量的鴉片類解毒劑納洛酮,但有些人仍然沒有反應。他們不得不被轉往外部醫院,在那裡還需要靠人工呼吸器維持生命。史蒂芬在十二個月內救回了二百八十七條人命,典獄長給了她一張五十英鎊的消費券和一張「感謝卡」。授勳一枚官佐勳章(OBE)會更適合。她是個真正的英雄,謙虛到不願接受祝賀。
「這是我份內之事,」史蒂芬說。
如果史蒂芬正在處理一個急救代碼,而無線電中又傳來另一起緊急情況,那麼飯店四號或輪值表上下一位有空的護理師就會出勤。如果又傳來另一起緊急情況,接著又是另一起,那麼無線電呼叫會要飯店全員出動。如果這是一起非常嚴重的急救事件,而飯店需要支援,他們會呼叫醫生—這代表情況正在急速惡化。於是我會終止任何問診,向我的病患道歉並請他們離開,鎖上身後的房門並開始奔跑。
我們把每一次急救視為一場戰役,奮力把我們的病人從死亡邊緣拉回。有時,一個狹小的牢房裡會有四五名醫護人員。一些牢房被非正式地當作側翼樓商店使用,所有備用的空間都堆滿物品。其他的則是相對空無一物,牆上只有塗鴉和半裸的海報。在這個監禁空間裡,我們必須相互翻過越過,對一個人進行急救,使他起死回生。每個牢房都是一個完整的世界,家人的照片由上往下俯視著我們。萬用黏土(Blu-Tack)和口香糖在監獄裡是禁品,因為它們可以用來堵住鑰匙孔。如果有囚犯拿到一串鑰匙,他們可以用口香糖做模具,複製鑰匙並逃脫。這聽起來很荒謬,像電影裡會出現的東西,但它是可能的。於是,親手製作的父親節卡片,只能用牙膏微弱地固定在牆上,因擾動的空氣而飄動。笑容滿面的幼兒、父母和伴侶在我們工作時看著我們。我盡量不去看那些家人的照片,他們的表情似乎在懇求我把他們所愛的人帶回來。我們都知道,在這個狹小空間裡,生命是一件非常脆弱的東西。它可以像吹熄蠟燭或點燃香菸那般容易被剝奪。有時只需要一顆直徑只有幾公釐的藥丸。
讓一個人起死回生是件極其累人的工作,我們需要輪流按壓胸腔,力道要足以讓這個人的心臟重新跳動。給予氧氣,要把他萎陷的肺部充氣。我們用自己的手搓揉那雙冰涼的手,看著他的血液循環開始漸漸漸停止。死亡的藍墨色首先會聚集在指尖,然後向上延伸至手臂。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會指示是否需要電擊。我們在狹窄的空間裡盡可能地後退,看似毫無生氣的身體在堅硬的地板上劇烈抖動。我們的手放在他黏濕的胸膛上,為他的心臟和肺部復甦。整個過程,我們呼喚著躺在面前的這個人。我們求他回到我們身邊。我們告訴他,他是被愛的。即使過了三十分鐘,我們還能幸運地把隱藏在皮膚下的死亡藍色斗篷慢慢拉開。血液循環的紅潤溫暖從他的臉蔓延到指尖,直到他終於急促地喘起氣來並睜開眼睛。
「歡迎重返人間。」史蒂芬氣喘噓噓地說,用戴著手套的手背抹過濕漉漉的額頭。
「你差點讓我心臟病發!」克莉斯捂住自己的胸口跟那人說。
「對不起。」當我們將他擺放至復甦姿勢時,他低聲說。
如釋重負的浪潮席捲而來,因為我們戰勝了死亡—這一次。而後我們笑了笑,互相祝賀。又一條寶貴的生命得救了。一個已經因監獄分離而緊張的家庭免於破碎。我們不期望感謝;保護患者是我們的工作,也是我們來此工作的原因。這些緊急情況帶給我們的身體及情感上的耗損不是我們談論的話題。正如史蒂芬所說,這是我們份內之事。
有時,我們會持續急救一個小時,直到病人甦醒。除非是非常明顯已經死亡,否則我們絕對不放棄。如果他們持續使用香料,他們一恢復過來就會變得偏執和暴躁,他們會攻擊我們。他們摑我們巴掌、踢開我們,因為他們仍受到毒品的影響。我們要護著自己的臉以免受到攻擊。我們在退到安全距離之前還要邊收回設備,並在幾分鐘後再次查看患者。我們可能需要坐在牢房外的地板上休息,靠著冰冷的牆壁。史蒂芬會使用她的氣喘吸入劑。正當我們仍氣喘噓噓、汗流浹背時,另一個緊急呼叫又傳來了。我們打起精神,再跑向下一個急救現場。
急救代碼其中讓人持續感到挫折的一點是,反覆收到呼叫來搶救同一個人。哈里遜先生就是履犯者之一,他最近一次入獄一開始就在報到處使用香料而倒下,而他的行為一直持續著相同模式。他的毒癮並沒有減輕。自搖擺六十年代以來,他一直留著長髮,而現在白髮蒼蒼,使他看起來像是另一時代遺留下的產物。他吹噓沒有任何一種毒品是他沒試過的。他告訴我,他年輕時長得很帥,非常有女人緣,環遊世界到處都有他的孩子,從事毒品交易賺到巨額財富。他描繪著各種放蕩的迷人生活,並細數出他所結識的過氣搖滾明星。他說他曾探索過南美洲的叢林,那裡的一位薩滿巫師給了他死藤水,一種死亡率極高的迷幻藥。
「我差點死了,兩次。」哈里遜先生語帶驕傲地說,好像他堅不可摧似的。我禮貌性地笑了笑,但一個字也不相信。
哈里遜先生仍然舉止得體,彷彿他對女人毫無招架能力似的,他拔掉假牙向護理師送飛吻,護理師們會好心裝出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稱他是號「人物」。他總是因海洛因相關罪行而不斷進出監獄。他也是出了名的監獄白老鼠,無論他同意與否,監獄毒販都會用他來測試新一批毒品的濃度。如果D牢區出現緊急呼叫,我們都猜想那很可能是哈里遜先生,而且通常是準確的。每次我們把他從懸崖邊拉回來時,我們都會告訴他,他還活著是多麼幸運的事。
「這不叫活著。」我們離開時他曾經這麼說過。作為一個自豪的毒品行家的逞能,只讓他肋骨酸痛,喉嚨因插管而破爛不堪。史蒂芬和我都一反常態地啞口無言。
通常她會講個笑話,而我會給囚犯一個我給自己的建議。「在一天中找到你最喜歡做的三件事—可以很簡單的像是吃好吃的食物、聽有趣的東西、見你喜歡的人。這三件事代表著這是值得度過的一天。」
但這次我沒有這麼說。相反地,我感到悲傷。感覺好像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收拾每個人悲慘人生所留下的爛攤子,而這只是為了讓洪水再次決堤,或者在深深的傷口上纏上繃帶,然後在傷口未癒合時感到驚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