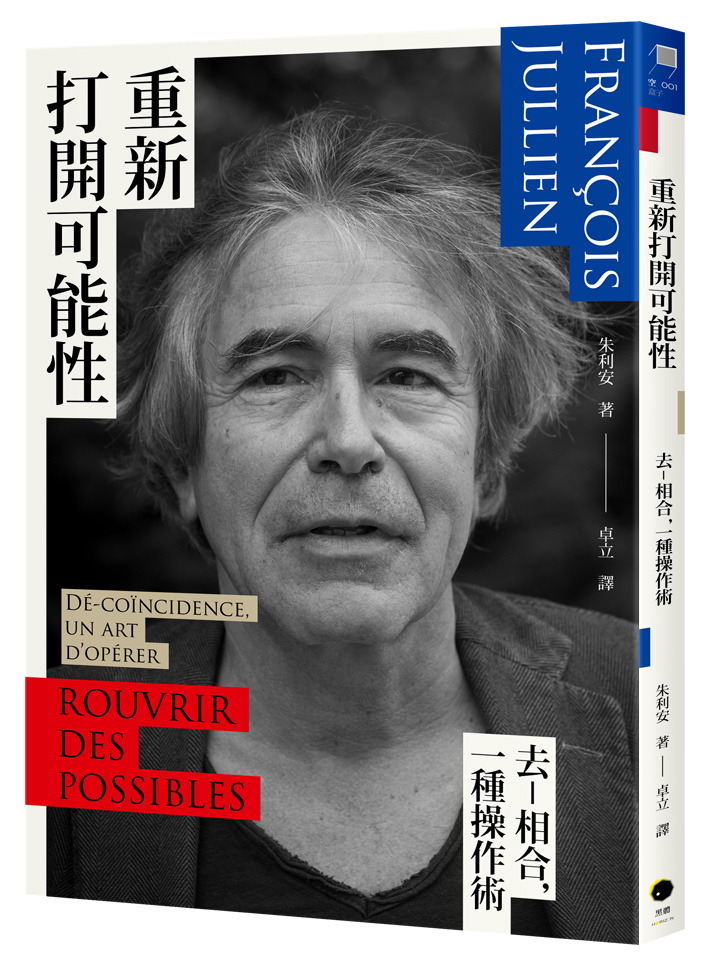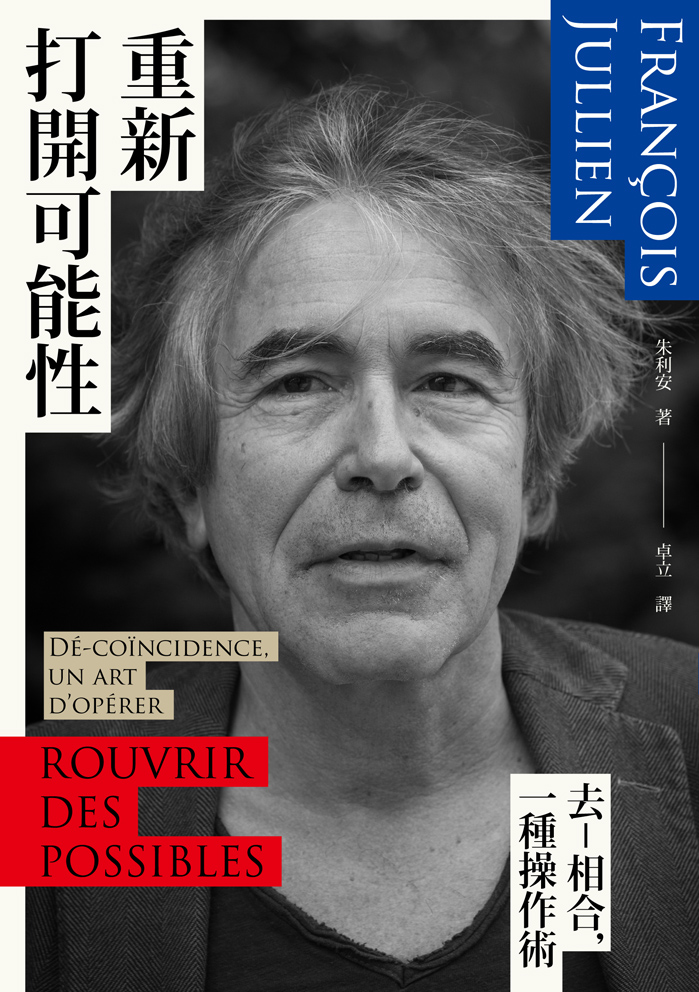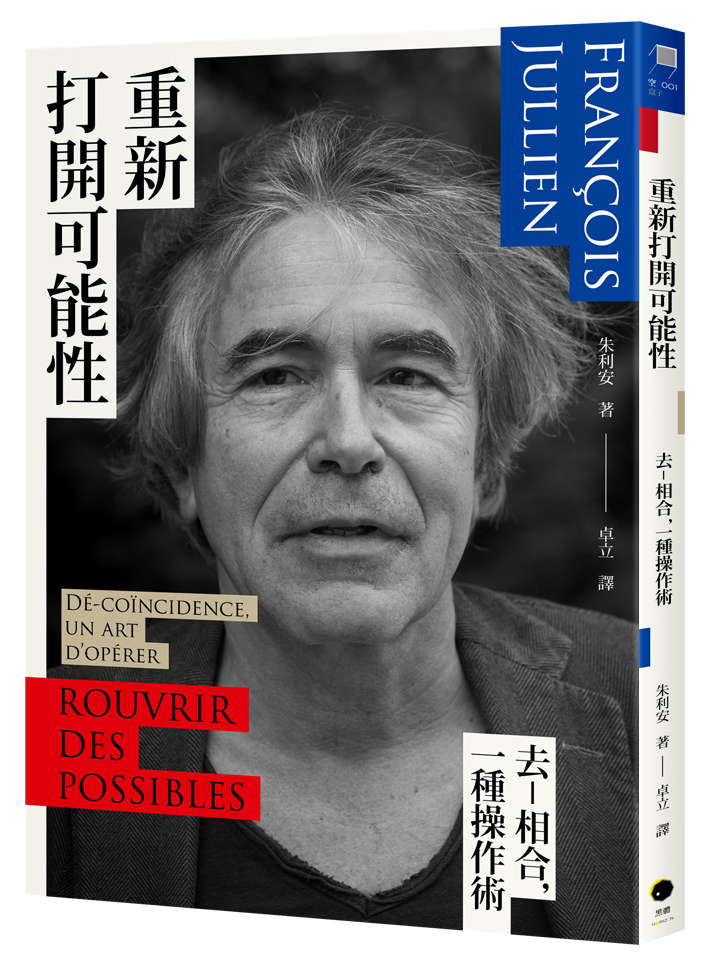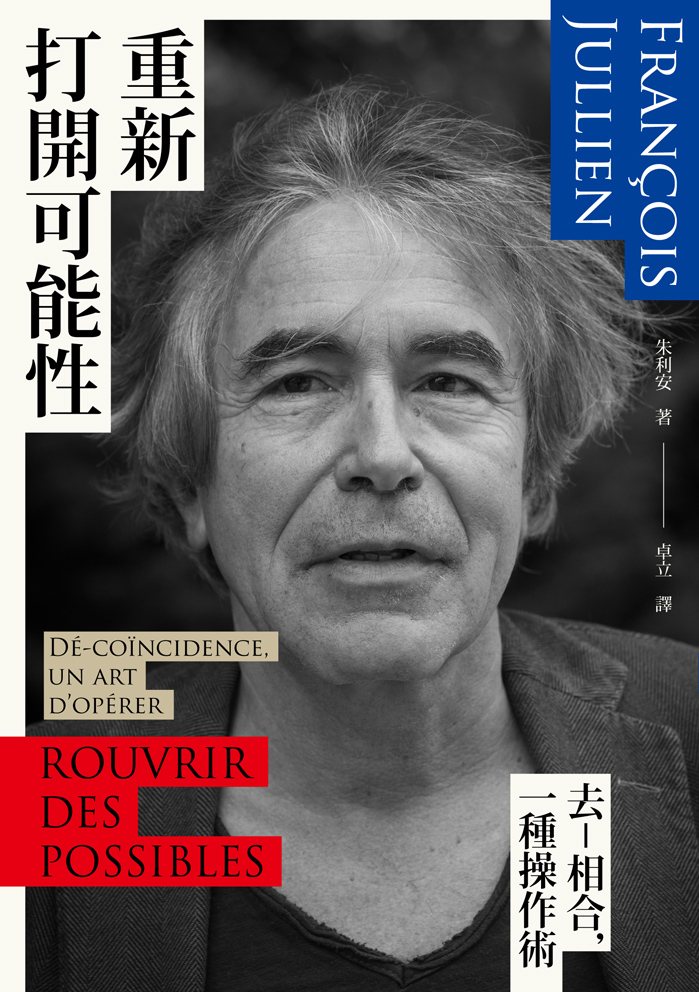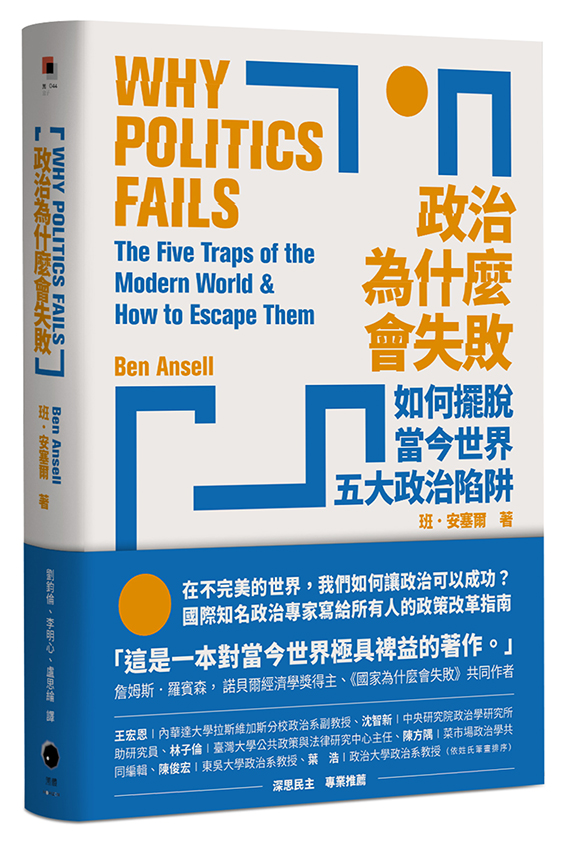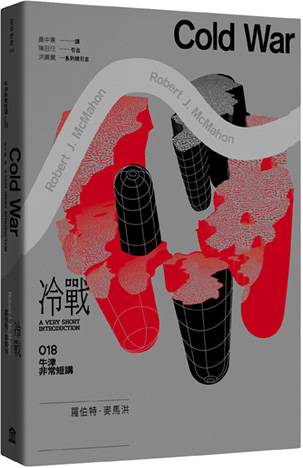法國哲學家和漢學家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所建構的哲學思想概念不僅對世界有深遠的影響,在其他領域如藝術創作、企業管理、精神分析也引發廣大的迴響。近年朱利安構思一種共通的概念,穿越美學、倫理及政治領域的經驗,一起形構人們對當代世界的投入,因此他大力提倡「去-相合」(dé-coïncidence)概念。
當事物相符相合,也就是這些事物完全貼合或全然對應,完美地互相扣合,即「相合」(coïncidence)於最初幾何學的意涵。這樣的符合當然令人滿意,它合法合理堅持其相符,同意自身,憩息在它的相合裡,而且固定不變。然而,它不再脫離這個狀況,逐漸陷溺其中、硬化而貧瘠了;也就是說,它不再發揮任何作用,變得呆滯了。此時,「合拍」(ça colle)表示符合變得像一種黏膠,人們無法跳脫它。「相合」便從先前的正面逆轉進「正面性」,固定了、不發揮作用,而且變成貧瘠的正面。
相合就是死亡。相合是沉溺萎縮(enlisement),「去-相合」是推動(promotion)與脫展(dégagement)。因此,我們必須與這種硬化了、不再活動且造成阻礙的符合拉開一個「間距」(écart),使自我封閉並阻礙任何發展的事物產生裂縫,也就是使其與該情況做出「去-相合」,才能重新打開可能性。
以藝術為例,一位藝術家只有當他與已完成、被認可且被頌揚為「藝術」的藝術做出「去-相合」時,他才是確確實實的藝術家。只有在與已經被思考過的內容且這個符合的內容被看作「真理」的事物做出「去-相合」,我才真的進行思考。
從生存的觀點來看,我只有與已經活過的、與我當今擁有的相符生活做出「去-相合」,我才真的在生活。與我當今的相符生活做出「去-相合」,也就是說,我使現在如此適合我的生活方式、我正要安頓於其中的生活模式「產生裂縫」,這是為了在我的生活當中重新打開可能性。
就倫理而言,我只有與自己做出「去-相合」,才能「遇見他者」。否則我只是與他擦肩而過,或者把他同化成我想要的模樣。
在政治方面,一旦一個理念變得相合性的,亦即被眾人所集體消化和吸收,就不再被人質疑,不再被人擔心,也就會變成意識型態性的。
在朱利安的構想中,「去-相合」的操作方式可說是有別於批判、逆轉這些戲劇性的風格,而比較是一種存在於內部、以小小間距逐漸打開並默默產生的轉化:在已穩固的相合狀態內部,透過持續的小「間距」、逐漸操作的小小移位,暗中在內部拆解該相合狀態,促使它產生裂縫,以此使它受損。
二十世紀末,「差異」(différence)概念在法國最重要的思想家主導之下主宰了法國思想,本書最後的註解也對「去-相合」概念與「差異」概念之間的關係提出扼要說明。
在今天,我們正遭受哪些新形式的物化?市場以及強加給人們的科技應用,聯手強迫全世界接受它們的相合。我們都變成相連、交流且消費的主體,我們的生活大都花在勾選事先設定的合適選項。這樣的「相合」繼「信仰時代」來到了,我們知道如何使它產生裂縫,與它重新打開間距,以便在我們的生活裡再次打開新的可能,亦即重新找到主體的主動性。
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
法國哲學家、希臘學學家和漢學家,其名曾被譯為于連或余蓮。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1974年取得法國大學教師資格,1975-1977年至北京大學和上海復旦大學學習中文和中國思想。1978-1981年擔任法國漢學中心香港分部主任,1985-1987年在東京擔任日法會館駐地研究員。1978年取得高階博士學位,1983年取得法國國家東亞研究博士文憑。
他曾擔任以下要職:法國漢學學會會長(1988-1990)、巴黎迪德羅大學東亞研究部主任(1990-2000)、巴黎國際哲學院院長(1995-1998)、當代思想研究院院長以及葛蘭言研究中心主任。他曾是法國大學研究院資深院士(2001-2011),2011-2022擔任巴黎人文之家基金會「他者性講座」教授。
2010年,朱利安因其政治思想研究成果榮獲德國漢娜.鄂蘭獎(Prix Hannah Arendt);2011年因其整體作品榮獲法蘭西學院哲學大獎。法國國內和國外(德國、阿根廷、臺灣、中國、越南等)曾舉辦過多場有關朱利安思想的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0年9月,朱利安成立「去-相合協會」,吸引各行各業人士參與。其著作等身,是最多被譯成外文的當代思想家之一;至今他已出版40多本論著,被翻譯成28種語言。
推薦序 去-相合的操作
作者序 遇見他者
第一章 明天不再歡唱了
第二章 相合即死亡
第三章 發揮作用的去-相合
第四章 去-相合倫理
第五章 相合是意識形態性的
第六章 當代法文相合性詞彙
第七章 去-相合的政治資源
第八章 去-相合的操作模式
第九章 去-相合的命運
第十章 去-相合與哲學
第十一章 革命,創新或重新變得可能
第十二章 什麼樣的投入?
關於差異和去-相合的註解
第一章 明天不再歡唱了
最近全世界發生了一場悄然無聲的革命,徹底改變了我們和政治的關係。我們越來越難以對將來(avenir,來自法文 “à venir”,指將要來的、將來到的,有相信事情會來到之意)做出一份理想城邦的藍圖。然而,自古希臘人以來,我們學習形構更好的想法,然後設法使其落實於社會當中。大寫的歷史,尤其在歐洲,過去的確被「理想性」(idéalité,即一種精心策劃的善的形式,既是理念性的,也作為理想模式)承載著,該歷史也與我們的慾望緊密相連,也就是我們的生活(生命)想要投入其中。但今天這情形很難做到,因為兩個原因。首先,我們必須先做出「隔離」(isoler),才能進行「模式化」(modéliser)。然而,今天全球化的世界之特質就是沒有任何事物可被隔離開來,因為一切都「相連」、相接相交,所以是「複合體」。從此越來越難建構一種大家共享的理想性,至少就全球層面而言。即使我們更透過模式化和技術模擬來操作,我們反而不再有能力策劃出一種公共的善;這甚至是我們的時代最大的悖論。人工智慧在各領域獲得最大的功效,但我們再也無法為人類提出任何偉大的計畫。我們確實儲存了更多的「資訊」,它們越來越精準且網狀相連,但這些資訊卻幾乎無法為我們的慾望畫出形狀。它們甚至可能阻礙我們的慾望,並使其晦澀難懂。我們因此觀察到人們對政治的冷淡,宏偉的革命時代也一去不復返;我們只看到零星發出的拉緊報、對暴力的抗拒或恐慌。
其次還有這件重大事實,即我們再也不相信將來了。至少傳統上歐洲人相信未來(futur,指對將來是否發生的事情沒有把握)引領著人們,未來因此與上述的理想性並肩同行,在過去兩者一起帶我們奔向比今天更好的未來。歐洲在宗教上認為人的歷史發展會走向救恩(事實上,此想法從未世俗化,而進步的意識形態就是其發展頂峰),但現在這種主張也無法說服我們了。當今我們不再能確定明天會「燦爛無比」或更快樂。我們只確定地球本身著火了。此外,甚至「自然」也不再能讓我們安心了;我們過去面對歷史上的重大災禍時就退守於自然當中,在其中找到庇護,而且自然恆常的週期性、季節的更新及收穫都讓我們放心。我們已窺探到地球上多處遼闊的地區很快會變得不適合居住,假如這種演變最後成真呢?儘管種種資訊及其應用算法的繁衍越來越干擾人,甚至使人異化,對我們而言,世界整體上似乎越來越不確定。我們從未像現在如此確定地掌控世界,但同時,我們也從未如此擔憂這個世界會逃離我們的控制。我們在這個世界裡畫不出任何未來的願景,這也是為何將來對我們無言了。我們過去認為人類歷史合理地會走向一個更完美的社會,而今該歷史的合理性卻不再強加給我們的思考,換句話說,明天不再「歡唱」了……(未完)
關於差異和去-相合的註解
一九六○年代左右,尤其在法國,出現的「差異」概念(différence),在二十世紀末曾經是最重要的哲學概念。差異這個字被索緖爾(Saussure, 1857-1913)的語言學理論用來界定辨識語言符號,於是差異概念使「存有本體」的核心產生了「裂縫」,而暗中從旁引入一種與存有本體論去-相合的操作。語言符號本身只有在語言的對立網絡當中,透過與其他符號的差異,才有價值。在這個語言理論裡,存有本體的基座被拆除了,建立在同和一(du Même et de l’Un)的同一本體性機制上的形而上學也因此被推翻了。此後,德勒兹(Deleuze, 1925-1995)的《差異與重複》(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與德希達(Derrida, 1930-2004)所推出的「延異」(différance)概念都賦予「差異」極大的重要性。傅柯(Foucault, 1926-1984)在《詞與物》(Mots et les choses)裡認為,人文科學不可避免地被壓成把人當作「同」的形象來處理,一些「反科學」(contre-sciences)則被視為唯一被拉回到差異遊戲的無意識論述打開了一種「純語言理論」。如傅柯在《知識的考掘》(L’archéologie du savoir)書末所說的,那是關乎拓展一種人們無法重新拉回到獨一的差異系統的散射(dispersion),此散射也不能被帶回到(時空)絕對參考軸。「考掘家」傅柯的論述目標是要「製造」差異,並把它們建構成(研究)客體(對象),但絕不會讓它們再次被導入任何可能整合它們的目的論裡。
在這篇「註解」裡,我並不想重新質疑「差異」這個曾經撼動思想和知識根基的強大創新概念,我只想以最簡短的方式探察差異概念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推翻形而上學(或說我們能否用「推翻」這個動作來脫離形而上學);我還想問差異概念的政治效能,即相較於其他的經驗場域,我們如何在差異概念裡建構政治理念(le politique),它能打開什麼視野,以及它能帶來何種投入。由此我們肯定會問去-相合與差異之間的關係如何;既然我們看到,我們過於膚淺且惡意地稱之「六八思維」(pensée 68)在差異哲學裡大大發酵,那麼在面對當今的世界及意識形態的新局勢之現狀時,該現象是否還存在?
使我與變成上一代哲學家重要相合的差異概念做出去-相合的原因是,我不得不從我在中華與歐洲之間所開闢的思想工地上出發來思考文化多元性。在多種文化的關係當中,意識形態性的相合確實是從「差異」的角度來看待「多元」(divers)。然而,不管我們是否願意,即使差異概念多次被重新應用,但「差異」仍然與認為其底下存有某種同一存有本體性的想法配對,該同一存有本體性就因「差異」而被彰顯出來。一九六○年代眾多解放運動都是以「捍衛差異」為名義發起的;這是對於被多位哲人重新加以思考的差異概念所做的扭曲變異?還是此概念本身就非其所願地帶有逆轉進身分認同的宿命裡?無論如何,如果說差異概念可以是用來走出同一存有本體性的邏輯思考工具,但該操作在社會和政治場域裡卻難以為繼。換句話說,差異概念斷成兩半,甚至在知識論上的用途和在政治上的一般用途反而暗中互相對峙。若不探查這種內部矛盾,它的用途就變得可疑。
的確,如果「每一個人」、每一個東西或每一個實體──如德勒兹明顯地要從存有本體論裡解放出來而說的──只是「眾多差異當中的一個差異」(une différence entre des différences),那麼在政治上如何解說這「每一個」(chacun)?「每一個」不可避免地用「存有」(être)來建構嗎?在(並非不食人間煙火)社會方面,語言裡非但用差異來界定個人身分,差異還使個人身分孤立。當我們用差異來區分兩者,一旦我們把其中一個分辨出來,我們便把另一個擱置一旁,只保留第一個的特性,以便得出其定義來做為知識分類。容我這麼說,差異對另一個「棄之不顧」。眾多文化之間也是如此,亦即以差異(或相似)來比較那些文化(可是文化的不同特殊性不可能像我們在自閉的語言功能當中所看到的),我們把它們關進我們所以為的同一存有本體性裡,使它們孤立於自身的文化圈裡。如此做所帶來的後果不可避免地肯定是文化之間的「衝撞」,由於這些文化被改變成堅硬的實體,隨其「差異」而互相對峙,因此阻礙了彼此之間的「間談(對話)」,它們也被用來支撑民族主義。在今天,我們對此現象看得很清楚。
這是為何我提出不同於「差異」的「間距」(écart)概念,並在這兩個概念之間拉開一個「間距」。之前的哲學確實一般把「間距」和「差異」視為同義詞(例如梅洛-龐蒂說:「找出它們的間距或它們的差異」)。多年來我的研究工作就是要驅除並分裂那些被集體同化而不再被反思的(「相合性的」)同義詞,這些同義詞堵塞了人們的思辨,也遮蔽了人們的經驗。首先,簡單地說,差異「標出」一個區分,而間距「拉開」一段距離。間距這麼做就不會整理歸類(ne range pas),這是差異所為,所以差異概念是分類的合法合理工具。間距概念反而「打擾歸類」(dé-range)。(語言表達上、行為舉止上……)「做出偏離」(Faire un écart)指的是脫離人們所期待、符合以及約定俗成的,開始與其做出「去-相合」。此刻要問的是,能偏離到多遠?所以間距概念是有探索性的。文化之間如是,語言之間亦如是。在我治學的第一階段,我試圖在中國語言-思想和歐洲語言-思想之間探索它們的間距能發展到「什麼地步」,以便重新打開思想的可能場域,(但有人卻把我的努力誤說成「文化本位主義」,很可能是因為我所採用的「去-相合」做法對漢學來說過於強烈,以至於它無法被漢學家理解,甚至不能被他們接納)。這一切的努力只試圖使我們哲學上的相合產生裂痕,這些相合自以為它們的推理放諸四海皆準,但其實是種族中心論的;我還試圖由此打擾我們的思想傳統,為了使它脫離其所涵蓋的類別,並使它再次不安起來。(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