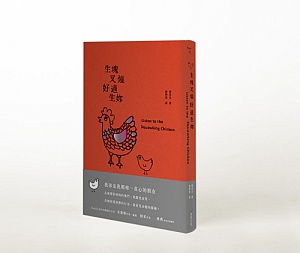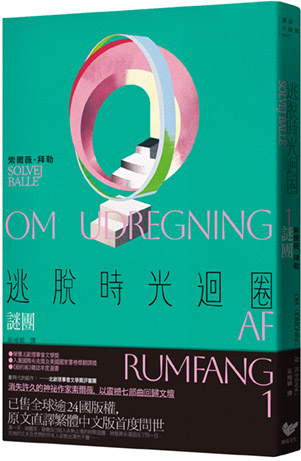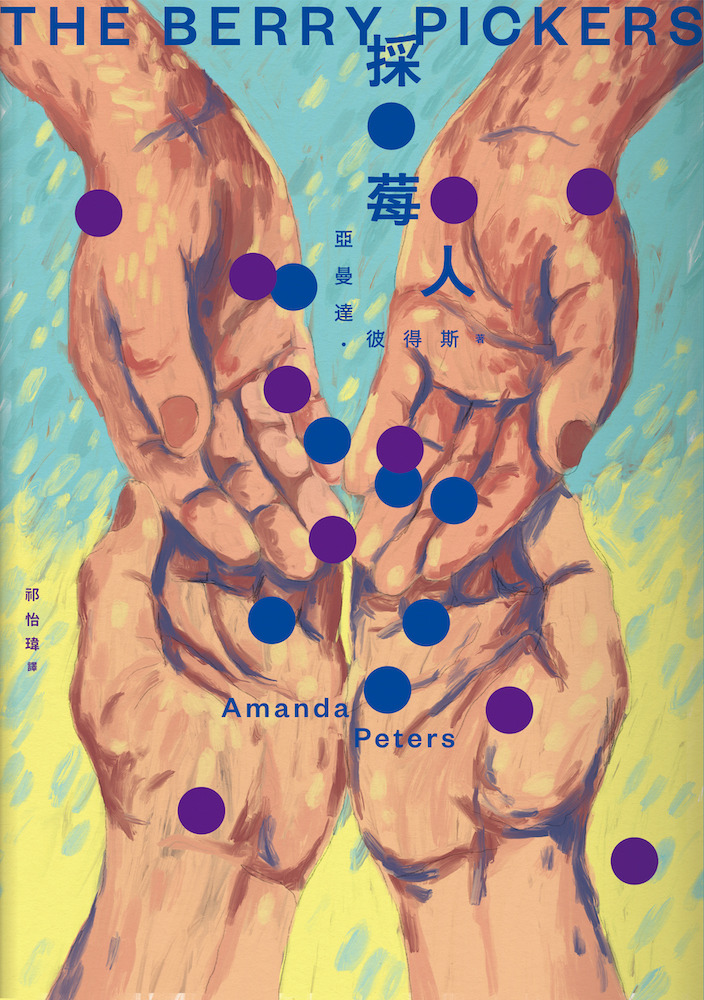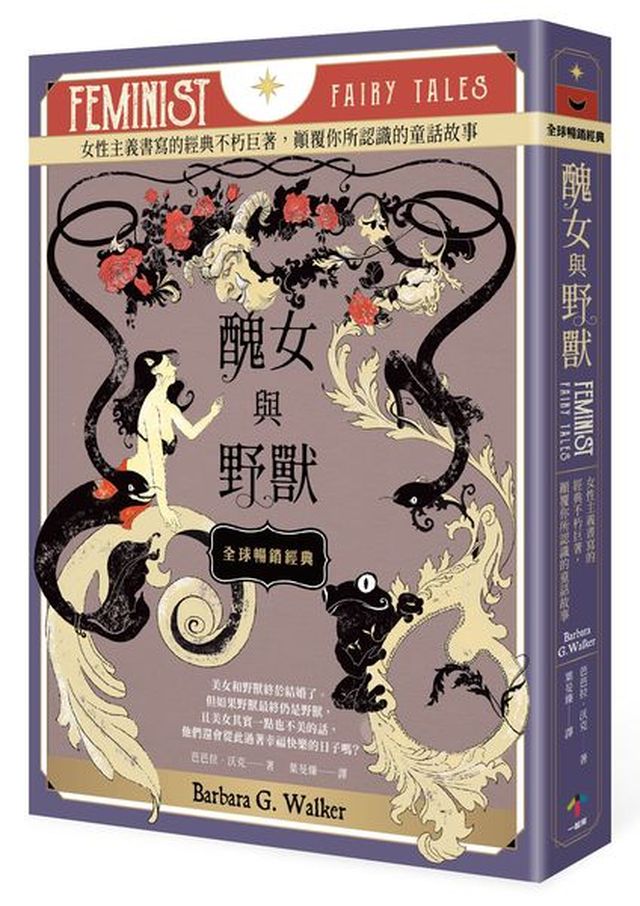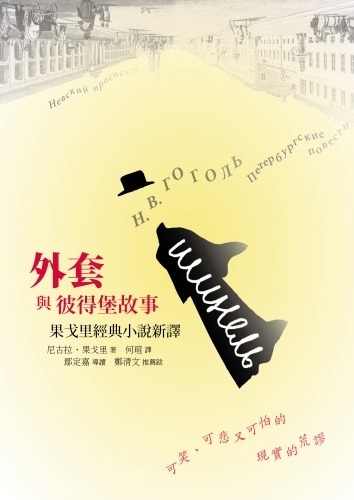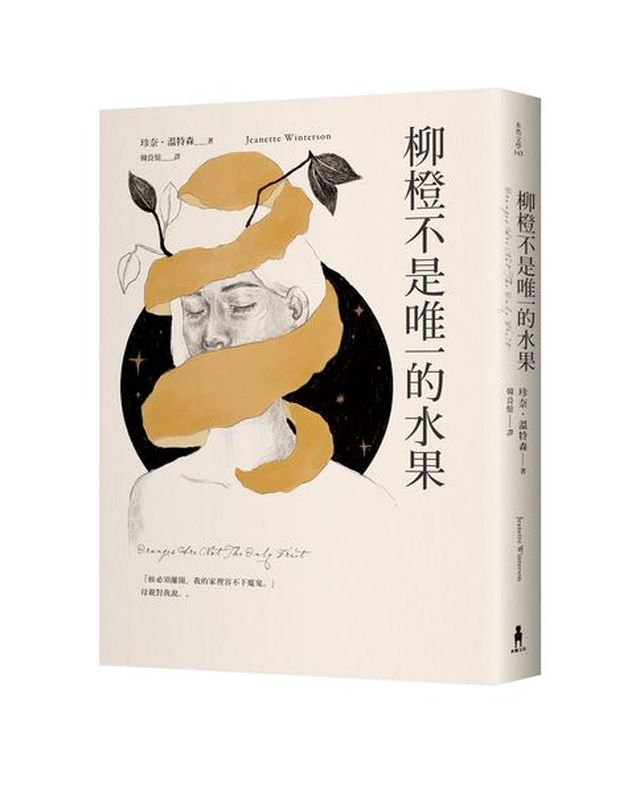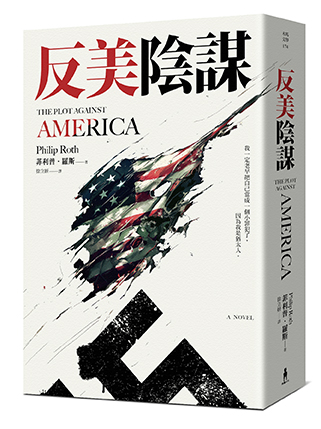我卻是我媽唯一真心的朋友
假鑽亮片羽毛,大嗓門華麗登場,
鬼故事教養法,傳遞麻將桌上的人生課題,
總是嘲笑羞辱,還用算命跟風水勒索我!
可是,在她囂張啼鳴的嗓門,我聽見寂寞,
在她跋扈無禮的行為,我看見未癒的傷痛。
她,是我人生的榮耀。
妳走路永遠都要像大象喔!真正的女人才不會躡手躡腳進房間呢!
如果妳為自己的身體感到丟臉,就是羞辱自己。你羞辱自己,每個人也會羞辱妳。
下一次妳決定要倒貼人家的時候,最好先確定,讓全世界都知道也無所謂。如果妳沒辦法接受,那是妳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
妳為什麼需要這麼多讚美?把事情做好,為什麼妳還不滿足?難道妳每放個屁,我就要開趴慶祝嗎?
幸福要過來以前,難道還要先通知妳喔?還是妳寧可預先知道困苦時期什麼時候會來?我的工作是要教妳做好面對困苦時期的準備。我的工作是要教妳怎樣盡可能避開困苦時期。
我批評你,永遠出自於愛。可是,隨著你逐漸長大,批評你的人並不會愛妳。他們會為了傷害妳而批評妳。我是在替妳暖身,準備面對以後來自妳敵人的批評。
如果妳能把自己最慘的經歷說出口,妳就永遠不會被迫噤聲。
天底下沒有免費的東西。如果起初它們看來是免費的,妳最終還是得付出代價。
漂亮又怎樣?漂亮眨眼就不見了啦。
如果他驕傲到不去尊重妳的父母,那他又會有多尊重妳?
如果妳覺得我犯了錯,那麼妳為什麼不試著做得更好?至少我會搞出爛攤子,都是有理由的。我來自一無所有的背景。我沒什麼本錢可以發揮。妳明明有那麼多可以發揮的才能,卻還是把自己變得一無是處。
妳這輩子都會感謝我的。
加拿大知名八卦網站主持人雷若芬,父母皆為來自香港的移民。她說她的一生皆是母親的精心策劃,一切行動都必得與母親商量,連旁人都流露同情目光對她說「妳被妳媽控制了」。她的母親不曾讚美她的美貌,因為與其「貌美」不如自己獨立自主;不曾以甜言蜜語顯露母愛也吝於給予讚美,因為母親的任務就是協助孩子認識現實的艱險並學習應對;總是在她犯錯時極力羞辱,要她正視自己的錯誤,預防再犯;也在她未犯錯時「預防性」羞辱她,以免誤入歧途。此外,她的母親從不說夢幻的床邊故事,而是以各式各樣香港鬼故事告訴她什「不可以亂撿街上的物品回家」、「不可以在天黑後去醫院」;也告訴她從麻將桌上學習到的經驗,像是「不可以在麻將桌上連打四張西風」,作為人生的指導方針;還以風水與算命,嚴格規定她買房子的價碼、三十歲以後不能剪瀏海、每天早上一定要吃木瓜。
雷若芬的成長過程,是一場與母親的競賽,每當她想耍小聰明──蹺課、約會,卻總是被母親詭異又神準第六感準確預測。她惱羞成怒、她生氣、她想反抗,甚至偶爾想偷懶,不想對母親開出的行為守則照單全收,卻總是再度栽進母親的「陷阱」,最後只得回到母親的懷抱,她的人生總是在母親的全盤掌控中。
母親生病後,為了激勵母親對抗病痛,她寫出了母親的故事。從她在香港掙扎奮鬥的少女時期,頂替不負責任的雙親扛下養家重任,遭到痛苦經歷後浴火重生;移民至加拿大後一人兼兩份工作為了求生存,又因為家族問題而離婚,她呈現了母親精彩的生命。她終於了解,在母親如雞啼般的大嗓門、看似永遠不會感到害羞卻總讓親人尷尬不已的行為背後,是不肯向命運低頭的強悍;母親的多疑與尖銳,是受到多次辜負的防禦。母親用自身的勇敢與誠實,教會她面對挫折;而那些母親做不到的、失去的特質與情感,卻在她的身上更完整地體現。她傾聽母親,理解她的故事,並且學習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因此,雷若芬說:「我全心全意仰賴著她。」
Elaine Lui(雷若芬)
出生於加拿大多倫多,父母皆為來自香港的移民。她經營加拿大廣受歡迎的「雷妮八卦」部落格(http://www.laineygossip.com/),該部落格每個月有將近一百五十萬人次造訪,同時也主持加拿大電視台的娛樂節目。並於2013年受邀至TED演講,分享自己長期從事八卦行業的觀察與想法。她與先生、兩隻米格魯現居多倫多。本書為她的首部著作。她的推特:https://twitter.com/LaineyGossip
謝靜雯
荷蘭葛洛寧恩大學英語語言與文化碩士。非小說譯作有《最後的演講永不完結:送別蘭迪,擁抱新夢想》、《這堂課:愛過的人教我的事》、《生還者希望你知道的事》、《死亡的益處》、《一隻貓,療癒一個家》、《莫札特與鯨》、《預知生死的貓》等。其他譯作請見:http://miataiwan0815.blogspot.tw/
【書摘】
(節錄)
1.〈學大象走路,學雞咕咕叫〉
如果世界是以靜音模式來運作,你會覺得我媽看起來跟任何華人女性沒有兩樣——比平均身高矮了點、骨架細小,但穿著品味相當可怕。想像一下全身上下佈滿假鑽的模樣,如果不是假鑽就是亮片,要是沒有亮片就有羽毛,有時三種還會同時出現。她最愛的裝扮就是牛仔褲套裝,背部跟整條褲腿都縫綴了鑲有假鑽的布片。她會刻意將衣領翻高,最後再用一雙金銀混色的COACH 運動鞋,來替這套華人婦女版的貓王打扮做個收尾,這就像糟糕透頂的歌曲裡,會有那種讓你無法抗拒、一聽就琅琅上口的魔音段落。
我們結伴出門吃港式飲茶時,當天要是我福星高照,外頭會是一片豔陽天。她會戴著墨鏡走進餐廳,整顆腦袋藏在亞洲人常戴的巨型遮陽帽底下。大家不禁納悶,她是電影明星嗎?還是在賭城搜刮了捐獻箱的遊民?等她終於摘下墨鏡跟帽子,就會露出那張漂亮到近似裝飾品的臉蛋。換句話說,單從外表看來,我媽看起來人畜無害。
只消把音量轉大,天地就為之變色。只要一聽她講話,你就永遠忘不了她。重點在於她的嗓門。她在香港的成長期間,那副嗓門替她掙得了「倀雞」[1]咕咕雞的綽號。沒錯,她的音量刺耳至極。你無法想像那麼響亮的聲音會這麼毫不費力又毫無預警地冒出來。咕咕雞不會給你時間好好適應她的高分貝,她的音量只有一個等級,而且是全面進擊。此外,還有語氣的問題——銳利、尖刻又急促,不是那種降落之後會留下一片靜寂的轟隆呼嘯,而是會侵襲心靈的哀鳴警報,有點像是灌注大腦、造成永久傷疤的酸劑。
媽大多用廣東話(香港主要講這種漢語方言)跟我交談,偶爾為了誇大效果,而摻入一點殘缺的英語字彙。
這裡有個例子。下面的句子除了一個例外,用的全是廣東話。看看你能不能聽懂她的意思:「我不喜歡這件毛衣。喀里[2]好差。」什麼是「喀里」?提示:「喀里」不是「衣領」(collar),「喀里」指的是「品質」(quality)。
媽不只會用「喀里」形容無生物跟服飾,也會拿來形容人。有一回我們去買吸塵器,銷售員對她很不客氣。「他有什麼『喀里』啊?竟然用那種態度跟我講話!」翻譯為:「這男人沒資格那樣對我說話。」
她不得不說英文的時候,動詞時態就會出紕漏。我刻意忽略這個問題,不主動去糾正她。我讓媽到處去跟人說:「我好刺激(exciting)唷。」
她真正的意思是她好興奮(excited)。從她嘴裡跑出來的句子,娛樂效果高多了,尤其想想她嗓門有多大。
媽不知道要怎麼低調講一通電話,更不曉得電影開演之前該怎樣在影廳裡悄聲對話。她不只在生理上缺乏輕聲細語的能力,也從來就不想要輕聲細語。媽的理念是高聲說話、大聲走路。拳王穆罕默德‧阿里像蝴蝶一樣飄飛、如蜜蜂一般刺擊;但媽走起路來像大象,跟雞一樣咕咕叫,而且她向來教我有樣學樣。看到有人鼓勵女生輕聲走路跟說話,媽就覺得心煩。
某次在我姑姑家的家庭聚會上,媽就把這點攤開來講。當時是晚餐時間,我們都被叫到餐桌那裡。我表妹麗茲在樓上,我們聽到她腳步很重地下樓,砰砰砰一路走到廚房。她爸大喊:「麗茲,走路別那麼大聲!走路要淑女一點!」
媽對這個姑丈本來就沒什麼好感。她淘氣地轉向我說:「我阿爺從前都交代我,走路要跟大象一樣,才能把鬼嚇走。阿女[3]啊!妳走路永遠都要像大象喔,真正的女人才不會躡手躡腳進房間呢!」
華人傳統意在培養可愛又雅致的女生。笑容要拘謹,要是笑出聲的時候要記得遮嘴,彷彿大笑表示妳太愛社交,不僅有失優雅,對女性來說也不體面。在華人文化裡,女性常被當成幼兒看待,也時有被物化的情形。男人在談正事的時候,會要求女性離開現場,也不會有人想徵求她們的意見;要是她們提出意見,就會害男伴覺得難堪。大家教女生不要表現出粗魯的樣子,教她們舉手投足要秀氣、性情要溫柔。永遠不該語出冒犯,華人「好」女生永遠不會出口成髒。在西方社會,聽到有人亂飆髒話會挑起強烈反應,但在華人文化裡會惹出更大的爭端。在那個文化裡,髒話用得很節制,而且使用者通常僅限於男人,以及咕咕雞。媽從來不遵守「僅限男生」能罵髒話的性別限制,她想罵就罵,隨口都能拋出F開頭或C開頭[4]的髒字,尤其是在跟人吵架。對媽來說,沒有謹言慎行這回事,她的雙腳跟嘴巴永遠也辦不到。
這隻咕咕雞不管到哪裡,從來不曾輕聲走路,也從來就不怕被人聽到。她這個世代的亞洲婦女,很多人都輕聲細語、舉止拘謹,但是我媽不一樣。即使周遭的人都相信女性應該柔和謙遜,她依然總是搶先提出意見、搶先暢所欲言。在她所成長的社會裡,傳統文化鼓勵女性表現得屈從恭順,但我媽從來就不是縮在角落、隱藏想法的那種女性。
多年下來,有些人覺得她的態度、聲音跟儀態惹人生厭,而比較喜歡那種愛組小圈圈、溫順過頭而不會跟男人對嗆的女性。可是,從年少時期在香港跟幫派份子同桌賭博,一直到在多倫多教中年猶太主婦打麻將,媽不管在什麼環境裡,向來都是自信滿滿。無論如何,她的咕咕雞態度始終如一:她相信自己可以融入任何地方。對我來說,她總是主場事件;不論時空如何,她都會霸佔焦點,她是終極的搶戲高手。
媽從位於香港西邊的城鎮元朗起家。當時,香港的活動大多集中在半島南區的九龍。在媽成長期間,九龍是「市中心」,是個光鮮亮麗的大城,對比之下,元朗是純樸的鄉下,得坐一個多鐘頭的公車跟火車才能抵達九龍。當年的元朗,公寓大樓還在陸續興建中,居民大多住在樸素的石屋或木屋裡;房子在幾個村莊裡聚集成群,跟元朗主要道路相隔十五分鐘的步行距離,那是一條通往幾家在地酒吧、餐廳跟露天市場的石鋪街道。在那個年代,住九龍的人都把元朗的居民當成鄉巴佬。但是,咕咕雞從來就不覺得自己是鄉下人。雖然她在元朗出生,卻總是端出來自九龍的架子。巧的是,隨著她邁向成人之路,元朗這個區域也漸漸都會化,彷彿是她用念力要它成長茁壯、變得更能跟世界接軌似的,彷彿這樣它才配得上她。
咕咕雞是那種困居小池塘、橫衝直撞的典型大都市女生,而那個小池塘從來就不把女生當一回事。不過,一九六○跟七○年代的元朗,在女生中只有她有那種膽量,敢跟男生坐下來玩骨牌跟打麻將。她常常把他們打到落花流水,贏得了他們的敬重。她的作風凶猛,有些男人還因為不想跟賭技相當、罵人更兇狠的她有所牽扯,最後竟然還開始躲她。媽所處的社群不鼓勵女性自我肯定,她卻反其道而行;每當有女性不懂得為自己挺身講話時,媽就替她們咕咕發聲;有個朋友拖繳保護費的時候,自願去找當地「三合會」(華人黑手黨)的老大協商的,就是我當時還年輕的媽。
咕咕雞在一九五○年出生,是六個孩子當中的老大。她的雙親沒有穩定的職業,有一搭沒一搭地工作著,在她人生的頭幾年裡,都把她留在老家的村落裡,由祖母帶大。媽的母親在各個餐廳進進出出,負責洗碗或包餃子;她父親則替當地的幫派打點零工,在客戶遲交保護費的時候去討債。他們把賺來的錢都花在麻將桌上,結果大多數時間都陷在欠債的狀態裡,但是偶爾也能夠過得好一點。媽的父母在特別春風得意的那段時間裡,回到村裡的老家吹噓炫耀。她們祖孫倆很親,她把祖母當成「真正的」母親,也就是培養她人格的人,所以她並不想離開祖母身邊。可是,既然父母的手頭現在寬裕起來了,繼續住在村裡而不跟父母同住,感覺就是不合體統。
賭博的好手氣從來就不會持續太久,而且家裡總是有新生兒來報到。媽每天放學之後就要照料弟弟妹妹,父母則因為前晚徹夜打麻將還在補眠。可是她很愛上學,即使她父母從來都不支持她唸書,她也記得自己當年是個伶俐又認真的學生。她只有趁家裡的小孩都就寢、父母出門上賭場之後,才有時間唸點書;又因為父母禁止她「浪費」電,所以她得到街燈下面去讀書。(西方的祖父總是喜歡說:「我當年上學一趟,就要跋涉十英里的路程,雪都積到膝蓋這麼高了。」我媽這種狀況,就是那種比喻的華人版本。)
不久,她不得不輟學。她才剛上十年級,父母就注意到她出落得相當標緻,可以開始去當服務生替家裡賺點錢了。於是媽被送到當地一家不大可靠的夜店,平日的來客大多是在地幫派的小嘍囉,他們對她的幽默感、神氣活現、老娘我最大的態度越來越有好感,會用豐厚的小費來對她表示心意,也會在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多多關照她。
差不多在這個時候,她母親跟男人私奔了。媽的父親跑出家門,開始一連失蹤好幾天,狂喝酒狂打麻將。媽必須仰賴鄰居的幫忙,有時也要靠她的幫派死黨,才有辦法照料五個弟弟妹妹。幾個月之後,她的母親被情人拋棄,懷著孩子回到家裡。媽的父母復合了,要求她替他們保密,而媽也幫忙母親撐過墮胎的休養時期。在我外婆的復原期間,媽一邊照顧弟弟妹妹時,一邊扛起家務,還得向那些對她家表示好奇的鄰居跟親戚撒謊編藉口。多虧有長女盡責的付出,我外公外婆才能若無其事地繼續生活。媽很高興自己是父母的好幫手,她毫無怨懟地順從父母的要求,認為經過這番磨難之後,他們會很感謝她。
可是,不久之後的一個晚上,媽在下班回家的途中遭人強暴,她的那些人脈都不在身邊。她的衣服被扯得破爛,嘴巴淤青、手掌割傷。當她踏進家門的時候,父母卻不曾表示同情。既沒有主動說要報警,更沒有幫忙她清理身體。媽既羞愧又心灰意冷,於是當晚吞藥自殺。她記得在昏昏沉沉之際,聽到父母在討論要不要幫她一把、要不要帶她就醫。他們最後決定不要,為了省錢也為了保住顏面,因為媽是唯一知道他們所有秘密的人──知道她母親的外遇跟墮胎,知道她父親愛拈花惹草而且還酗酒,知道他倆積欠未還的債務。她要是走了,就不會有人知道這些事。就在當天晚上,我媽咕咕大叫起來。她硬逼自己開始嘔吐,吐完之後,扯開嗓門發出尖銳刺耳的叫聲。
幾年之後,媽帶我回香港,大家老會跟我提起媽開始尖叫的那個夜晚,就像一則傳奇似的,烙印在眾人的記憶裡──她的尖叫聲傳遍了元朗,她使勁又激烈地尖叫著,彷彿像要召喚神祇來審判她的父母,像要指出父母的罪孽。結果他們那晚沒上賭場,而是躲在家裡閃避鄰居,他們知道別人會認定他們有罪。媽放聲尖叫,是為了遺忘自己受到的侵犯;她放聲尖叫,直到父母的背叛在她心中留下的傷口,結成了疤痕,永遠轉變了她的靈魂;她放聲尖叫,是為了宣布自己的重生。
翌日早晨,她跟父母說生活模式應該要改變了,而也真的改變了。從那天開始,她只要用奇怪的眼神看他們,他們就會趕緊屈服退讓。就是在那個時候,她開始掌控自己的人生。當時她十五歲。
你知道嗎?鳳凰是某種會按照固定循環、成長蛻變的鳥禽。媽就是在成長蛻變,她搖身長成了咕咕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