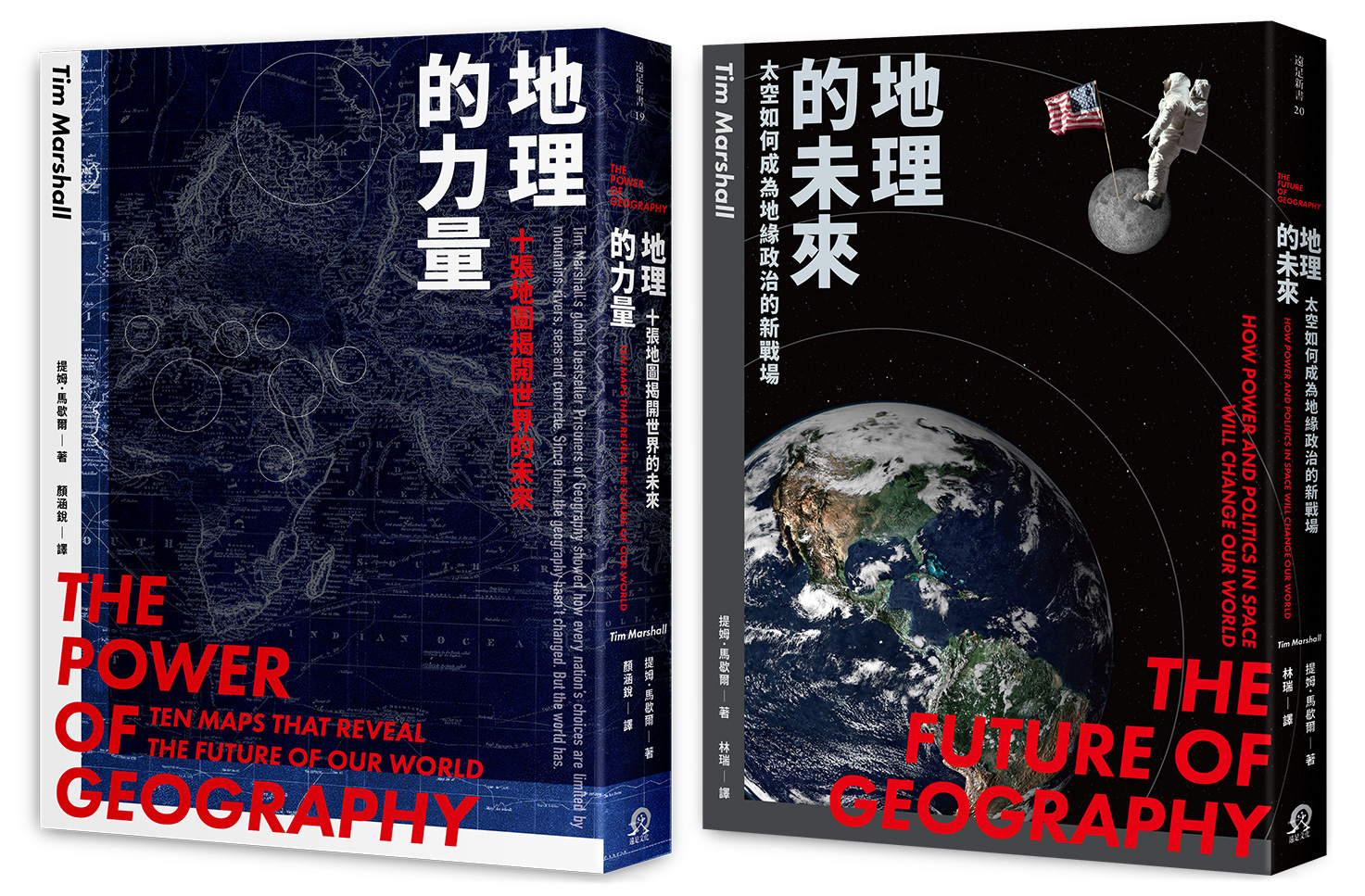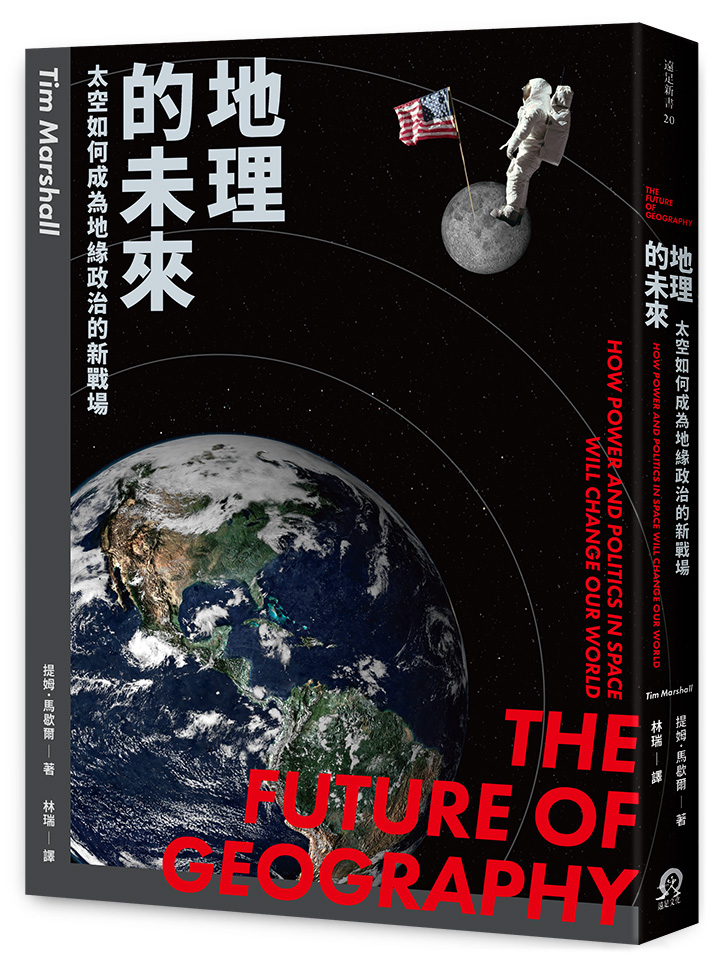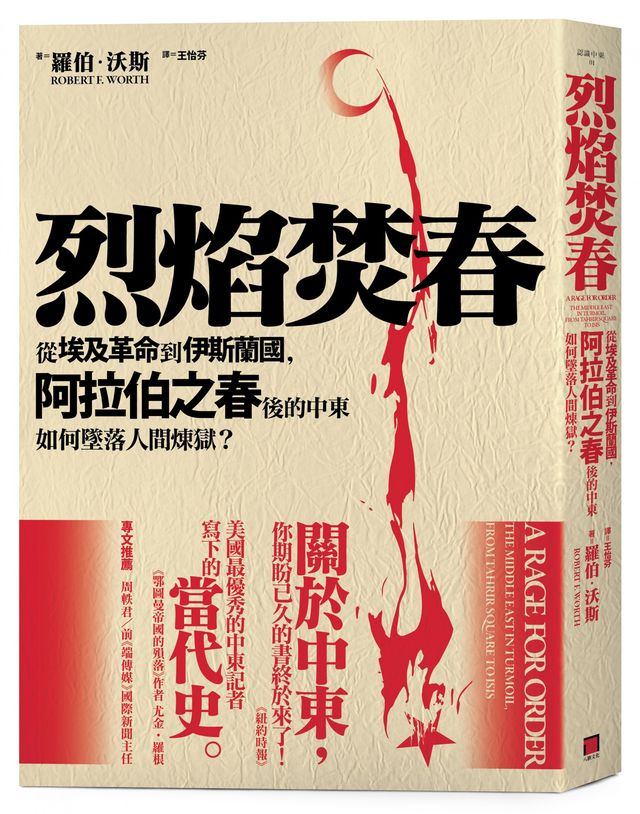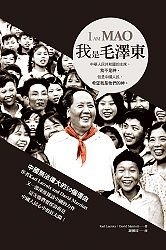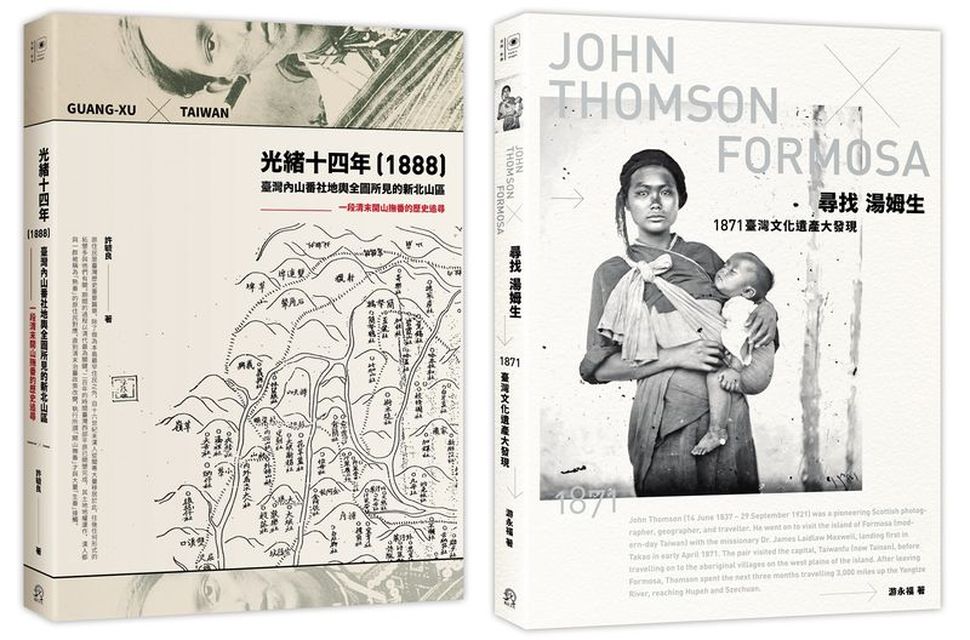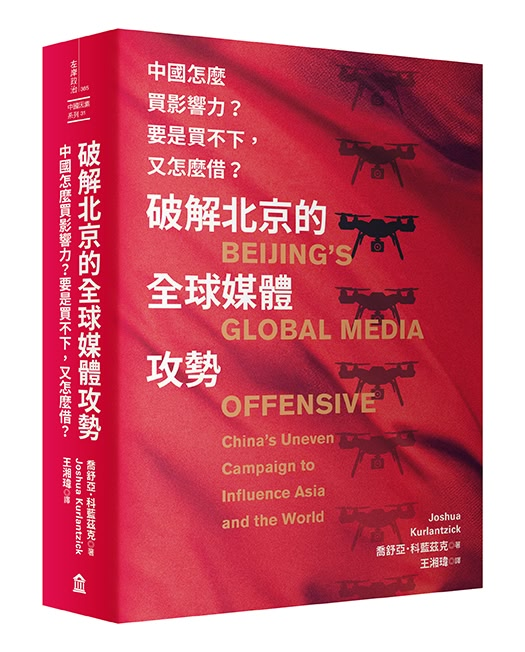div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LINE-HEIGHT: 14.25pt; TEXT-INDENT: 19.6ptstrongspan style=FONT-SIZE: 10pt; COLOR: #111111作者nbsp;/span/strongspan style=FONT-SIZE: 10pt; COLOR: #111111何偉/spanspan style=FONT-SIZE: 10pt; COLOR: #111111Peter Hessler/span/div div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LINE-HEIGHT: 14.25pt; TEXT-INDENT: 19.6ptnbsp;/div div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LINE-HEIGHT: 14.25pt; TEXT-INDENT: 20ptspan style=FONT-SIZE: 10pt; COLOR: #111111出生於密蘇希里州哥倫比亞市,普林斯頓大學主修英文和寫作,牛津大學英國文學碩士。1996-1997年他以「和平工作團」身份在四川涪陵教書,自2001年起才成為《紐約客》首位駐中國記者,在此之前他只是《華爾街日報》駐北京辦公室負責剪報。新世紀開始,他也是《國際地理雜誌》、《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的長期撰稿人,保持著自由作家的身份。 /span/div div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LINE-HEIGHT: 14.25pt; TEXT-INDENT: 20ptspan style=FONT-SIZE: 10pt; COLOR: #111111何偉是全球著名的旅遊觀察者,他也多次獲得美國最佳旅遊文學獎。他所著《甲骨文》曾入圍2006年美國國家圖書獎非小說類最佳作品,《尋路中國》則獲得/spanspan style=FONT-SIZE: 10pt; COLOR: #1111112010/spanspan style=FONT-SIZE: 10pt; COLOR: #111111年度經濟學人、紐約時報等好書獎/spanspan style=FONT-SIZE: 10pt; COLOR: #111111。這兩本書和他根據涪陵兩年所寫成《消失中的江城》(奇里雅瑪Kiriyama環太平洋圖書獎)構成了他1996-2007十年的「中國三部曲」。/span/div div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LINE-HEIGHT: 14.25pt; TEXT-INDENT: 20ptspan style=FONT-SIZE: 10pt; COLOR: #1111112010/spanspan style=FONT-SIZE: 10pt; COLOR: #111111年,何偉來到埃及,學習阿拉伯語,參與當地的生活。我們相信不久就會看到他的新作。而他預告在五年後再度回到中國,繼續書寫新的中國傳奇。/span/div div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LINE-HEIGHT: 14.25pt; TEXT-INDENT: 20pt div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LINE-HEIGHT: 14.25pt; TEXT-INDENT: 20ptspan style=FONT-SIZE: 10pt; COLOR: #111111 divstrongspan style=FONT-SIZE: 10pt作者說明/span/strong/div divnbsp;/div divspan style=FONT-SIZE: 10ptnbsp;nbsp;nbsp; /spanspan style=FONT-SIZE: 10pt本書描述我在涪陵的生活,穿插的隨筆著重於當地的風景、歷史和人民。這些隨筆都是我住在涪陵時寫成的,我利用這個架構讓讀者認識一個外國人在涪陵這樣的小城所扮演的兩種角色。有時候,我是一個觀察者,有時候我深入當地的生活,這種距離感和親密性的結合是塑造我在四川的兩年生活的一部分。/span/div divnbsp;/div divspan style=FONT-SIZE: 10ptnbsp;nbsp;nbsp; /spanspan style=FONT-SIZE: 10pt由於涉及敏感題材,我更改了幾個人物的名字和其他辨認特徵。除了幾個為人熟知的名字mdash;mdash;例如Yangtze(長江)和Hong Kong(香港),我採用羅馬拼音將大多數的中文名字和字詞譯成英文。/span/div divnbsp;/div divspan style=FONT-SIZE: 10ptnbsp;nbsp;nbsp; /spanspan style=FONT-SIZE: 10pt這不是一本關於中國的書,而是一本關於一段短暫時期裡的中國一個小地方的書。我希望我捕捉了那段時光和那塊土地的豐富內涵。我熟悉那個地方,熟悉污濁的長江,以及過度耕種的青翠山丘。但是,界定那段時光是比較困難的。涪陵位於長江中游,也處於歷史之河的中游,有時你很難看出事情從何而來,或者朝何處去。但是,這個小城和它的居民總是生氣勃勃、精力充沛、充滿了希望,而這就是我最終的主題。本書的目的不在於探索起源或目的,而在於記述在這條大河的心臟地帶生活兩年的點點滴滴。/span/div /span/div /div
div style=TEXT-INDENT: 20ptstrongspan style=FONT-SIZE: 10pt譯者/span/strongspan style=FONT-SIZE: 10pt吳美真/span/div pspan style=FONT-SIZE: 10ptnbsp;nbsp;nbsp; /spanspan style=FONT-SIZE: 10pt雲林虎尾人,政治大學西洋語文學系畢業,紐約大學英美文學博士班肄業。曾任大學兼任英文講師及國內多家出版公司譯者,譯作包括《美德書》、《鋼琴師》、《微物之神》、《大洋洲的逍遙列島》等近七十本,近年來一直為基督教以琳書房譯書。/span/p
作者原序 回到涪陵 我在四個月內完成《消失中的江城》的初稿。我沒有理由寫得這麼快,沒有合約或截稿日期催促著我。我原本可以慢慢來,享受久違的美國生活。但是每一天,我早早動筆,晚晚收筆。記憶驅使我加速寫作,因為我擔心會失去涪陵生活的即時感。此外,未來也驅策著我:我想記錄我對於一個即將面臨巨大變化的城市的印象。 在過去二十年,這種轉變感——經常的、無情的、勢不可擋的變化感——一直是界定中國的一個特色。你很難相信中國曾給人恰恰相反的印象:根據十九世紀德國歷史學家里奧帕德‧范‧蘭克 (Leopold von Ranke) 的說法,中國是「永遠停滯不前的民族」。現在,這是一種最不正確的說法,而作家所面臨的一個挑戰就是:筆根本跟不上改變的腳步。在《消失中的江城》的第一章,我寫道: 涪陵沒有鐵路,這裡向來是四川省一個貧窮的地區,而道路路況十分惡劣。如果你想去哪兒,你得搭船,但是你多半哪兒也不去。 但是,當本書在二○○一年出版時,一條通往重慶的超級高速公路已經完成了,幾乎再也沒有人搭船沿著長江前往涪陵,而一條鐵路幹線正在興建中。涪陵欣欣向榮,來自終將被三峽大壩淹沒的低窪城鎮移民刺激它的成長。我以前經常去用餐的小麵館的經營者黃家已經開了一間網咖。我教過的學生分散在全國各地:西藏、上海、深圳、溫州。但是《消失中的江城》——一部永遠停滯不前的書——並沒有提到這些。 一九九九年春天回到中國後,我一年至少去涪陵一趟。由於有了高速公路,現在去涪陵比以往容易多了,而我在北京的作家新生活使我可以自由旅行。我經常去拜訪涪陵,然後沿長江順流而下,前往三峽的核心。 在我加入和平工作團的那兩年,三峽大壩一直像是一個抽象物——一個模糊的應許、一個遙遠的威脅。但是每次我回去,它就變得稍微更加具體。到了二○○二年,移民城已大有進展,地貌明顯地劃分成過去和未來。江岸附近,舊的濱江城鎮和村莊幾乎沒有任何改善的跡象。儘管中國其他地方都在一股腦兒地進行興建,在江水必然會上漲的地方建造任何東西是沒有意義的。當局任由這些低窪城鎮和村子衰敗,直至一切都荒廢了:破損的磚、骯髒的瓷磚、佈滿塵垢的街道。注定毀滅的城鎮和新城形成一個對比,新城是由水泥和白瓷磚建造而成的,高高座落於河流上方的山丘上。每當我搭船朝長江下游而去,我可以在一系列的水平帶狀結構中,一眼看出地貌的演變史:江邊屬於過去的陰暗村落、一段將被水庫淹沒的綠色農田,以及上面高處一簇簇展望未來的白色建築物。 我在水壩完成之前的最後一趟旅行是在二○○二年秋天展開的。我和一位朋友帶了帳蓬和睡袋,沿著將近一百年前鑿在江邊峭壁上的古老小徑徒步旅行。天氣好極了,而小徑上的風景令人屏息。有時我們高高位於長江上方,我們所在的峭壁垂直落入三十公尺下的江水之中。每走一段路,我心裡就想:這將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這條小徑。 我們朝長江上游前進,而且不急著趕路。在小徑走了一星期後,我們參觀了正被拆毀的濱江城鎮。舊城巫山剛剛被拆除,我漫步於瓦礫中,拾荒者在那兒揀拾任何可能賣錢的東西:磚和鐵絲、草和木頭、釘子和窗框。一群人聚集在一堆營火旁邊,周圍是一棟大型建築物的破牆。然後,我認出了一塊半毀的招牌。原來他們正在紅旗旅館的大廳紮營,一九九七年我第一次前往長江下游時,曾住在這間旅館。 所有我最喜歡的濱江城鎮都處於各種不同的毀滅階段。大昌的四分之一已消失了,裴市只留下回憶,大溪已走入歷史。有時,我在拾荒者搜刮過後經過一個村子,在寂靜中,我審視留下來的東西。在大溪,我看到一張加了相框的富士山照片,照片的前景是一大片盛開的櫻花。在清市,我經過了一張墊料加厚的紅椅、一個舊的籃框,以及一塊殘破的石碑,其上的刻文是上個世紀完成的。一棟被拆去屋頂和窗的房子仍然有一扇閂上的門。在裴市,我向一對夫妻買礦泉水,他們所住的臨時棚子完全是由揀來的門和窗框搭成的。也許這是一個道教的謎語:住在一間由門搭成的房間意味著什麼? 當我到達涪陵,舊城區大部分已被拆毀,新建的住宅區擠在高高的山頂上,城市龐大的堤防差不多已完成了,而烏江對岸的師範專科學校也正在擴張和改變。老幹部們已退休了,新幹部對外國人比較開放。幾年前,我和亞當抵達涪陵時,最先迎接我們的那位友善的年輕人亞伯特現在已是英文系的系主任。當我去他的辦公室拜訪他時,他拿出我一年前送給學校的精裝本《消失中的江城》。 「你可以看出許多人讀了這本書,」他說。書的封面已經破損,且沾滿茶漬,翹起的角落已經難以壓平,翻書的手指留下了髒兮兮的灰色痕跡。在我手中,這本書顯得十分沈重,像是一個手工製品。我怎麼可能寫出一本看起來如此陳舊的書? 就某方面而言,改變的步調似乎讓當地人比較容易接受這本書,因為這本書所描繪的世界已經顯得十分遙遠。我的中文家教老師孔明在暑假時把這本書讀完了,他藉著字典一字一字地讀,因為他的英文不太好。他告訴我,當他讀到許多勾起美好回憶的部分時,他笑了。在我拜訪涪陵期間,當學校的官員在當地一家餐館設宴款待我時,他們把我對於昔日宴會的描述取笑一番。「我們不想讓你喝太多酒!」一個幹部說:「你在你的書裡提到我們強迫你喝太多酒。」 「那不是一個大問題,」我說。 「我們當然不想再那樣做!」另一位幹部說。但是另一個人插嘴:「你要不要再喝點白酒?」 在那幾天,我在城裡逛,拜訪老朋友。在銀行那兒,我特地去看錢曼麗,那位我住在涪陵時,唯一與我「約會」過的漂亮年輕女人。那是一個短短的插曲,因為約會一小時後,我就發現她已經結婚了。現在,她已經有一個兩歲大的孩子。她說了每次我回到涪陵時一定會說的話。 「你不認得我了,對嗎?」她問:「我比以前胖多了。」 我說:「妳看起來和以前一模一樣。」 「老實說,」她說:「我變胖了,對嗎?」 當書中一個人物變胖時,作者該怎麼辦?「妳看起來很好,」我回答,然後就不再說什麼了。 當三峽大壩的第一階段工程完工,而閘門終於關閉時,我回到巫山。那是在二○○三年六月,在《紐約客》裡,我發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一個家庭對於河流上漲的反應。他們已經盡可能地等待了,等在江水上漲之前採收了蔬菜。 二○○三年六月七日。 傍晚六點十三分,當周家終於將電視、一張書桌、兩張桌子和五張椅子搬到路旁的南瓜田裡,我在江邊立起了磚柱。在新的巫山地圖上,這一片水域叫作滴翠湖。但是,這些地圖是在湖出現之前印製的,事實上,水呈混濁的棕色,而所謂的湖其實是長江的一個入口,在過去一星期,這個入口已漲到三峽大壩後面。周濟恩下一回從他家的竹架棚屋出來時,他的背上扛著木造的碗櫥。他是一個個子矮小的男人,有一個漂亮的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女兒。最近之前,他們一直住在龍門村。新的地圖上並沒有這個村子。接下來,周家的一個朋友抱著周家那座以電池供電的時鐘走出來了。和我的腕錶一樣,那時時鐘指著六點三十五分。磚柱周圍的水已經上升了五公分。 看著江水上漲就像追蹤時鐘短針的進度──幾乎是無法察覺的。 沒有明顯可見的水流,沒有奔騰的水聲,但是每過一個小時,水就上升十五公分。這種變動似乎來自內部,在某種程度上,對於江岸活動範圍逐漸縮小的每一種生物而言,這是一件神秘的事。甲蟲、螞蟻和蜈蚣從江邊成群呈幅射狀散開來。水包圍住磚柱後,一群昆蟲狂亂地爬上乾燥的柱頂,在牠們的小島被水淹沒時,拚命地試圖逃脫。 有一個多星期的時間,水以每小時十五公分的速度上升。這些細節吸引我,直至我把相機的焦距調準了,把鏡頭縮小了:我分分秒秒注意著磚柱上的昆蟲的動靜。當一切都結束時,我登上船,離開巫山。河流已變成湖。 自此我就不曾回去了。這不是我的計畫,而我不確定我為什麼耽擱。也許這是因為我想完成我的第二本書,而我擔心舊地重遊會讓我分心。或者,也許三峽大壩的不可改變性讓我感到難過。 但是,我看得出對異國產生懷舊之情的危險,當這個地方曾被稱為「永遠停滯不前的民族」的家鄉,這種懷舊之情尤其危險。如果當你看到一片地貌改變了,讓你認不出來了,你會感到難過,那麼,當你待在一個不會改變的地方,你會感到更難過。我以前的學生威廉‧傑弗遜‧佛斯特畢業後離開偏遠的家鄉,就像中國各地一億多個鄉下人一樣。他變成一名移居者,前往東岸繁榮的城市,當一所私立學校的英文老師,步上成功之途。有一年,在假期中回去探望父母後,他寫給我一封有關他的家鄉的信。威廉那一代的人幾乎都離開了,他的村子顯得死氣沉沉。 回到家時,一切都一如往昔,道路依然崎嶇不平,人們都變老了。我感到很難過,因為我找不到以前認識的熟人或朋友。 對於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如果不選擇經常性的改變,就得選擇貧窮、惡劣的道路和慢船。我是一個在一九九六至一九九八年期間學會喜愛涪陵的外國人,所以,我很感激有機會為那兩年留下紀錄,而我懷念我認識的地方。但我也因為大部分的涪陵人對於未來感到十分樂觀而心懷感激。再度航行於長江之上將是一件愉快的事,即使舊日湍急的水流已成回憶。 ——二○○五年十月於北京 作者新序 重新踏上長河 我覺得中國有兩個地方將永遠是我的家。一個地方是北京以北的三岔村,自二〇〇一年起,我在那兒一直擁有一間房子。另一個地方是瀕臨長江的小城涪陵,自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八年,我曾以和平工作團志工的身份住在那兒。有時候,我稱涪陵為我的老家,我想這是一個玩笑,但就許多方面而言,我是當真的。涪陵是我開始學習認識中國的地方,也是我成為作家的地方。在那兒住了兩年就像一種新生,因為這個經驗讓我變成一個新人。 去涪陵之前,我寫過幾篇報導──多半是為美國報紙所寫的遊記。但我沒有出版過長篇故事或書,也沒有做過新聞工作。當時,我知道我想要成為一名作家,但我不確定我會寫小說或非小說。其實當我抵達涪陵,我仍然認為自己最適合寫小說。在我住在涪陵的前幾個月,我寫了一篇以我生長之地密蘇里為背景的短篇小說。我想那是我在二十幾歲時,較出色的短篇故事創作之一,然而,這個經驗沒有帶給我滿足。寫完這篇故事後,我心想:我現在住在長江江畔這個不尋常的城市,所以,為什麼我要寫一個以密蘇里為背景的故事?突然之間,我感覺我的寫作前途的一大部分就在中國。 當時,我的計畫是在涪陵盡我所能地學習,然後,當我離開和平工作團,我希望我能夠成為一家美國報社或雜誌社派駐在中國的記者。我並沒有計畫寫一本書,因為我認為我太年輕了,而且對於中國所知不多——我在涪陵只住了短短的兩年,因此,嘗試寫一本有關這個地方的書,似乎顯得頗為冒昧。然而,當我在涪陵生活和教書時,我的確作了詳盡的筆記。這是一個十分豐富、但也充滿了挑戰的經驗。我經常覺得吃不消,而寫日記是有幫助的。夜晚時,我經常花幾個小時寫作,嘗試處理發生在我周圍的一切。我摘錄學生的作業,記下發生在城裡的事,描述學習中文的經驗。我總共記了數百頁筆記——由於沒有別的事可做,寫這麼多並不難。當時,涪陵這個地方沒有網路連線,所以,我很少和住在美國的人聯繫。我的薪水一個月只有一千多塊人民幣,所以我不常旅行,從來沒有去過北京或上海這類的大城市。我打不起國際電話,所以,在那兩年當中,也許我和我父母說話的次數不到十次。除了亞當‧梅爾,我很少看到外國人。在那段時間,涪陵就是我的生活重心。 當然,這個城市瞬息萬變——當時,甚至中國也在迅速發展著。在涪陵住了十八個月後,我終於可以申請到網路連線。突然之間,我可以重新和我在美國的朋友聯繫,而這些朋友包括約翰‧麥克菲(John McPhee),他是我大學時的寫作老師。我寄給約翰一封電子郵件,向他解釋我希望成為一名駐中國的記者,而他回給我一封長信,他寫道: 涪陵本身就是一個作品,而且將自然而然地成為一個作品。涪陵是一本書。我認為你應該決定寫一本書,說出自己的故事,明年夏天開始認真地寫,或者這兩年結束時開始寫……只要寫一封六、七萬字的長信,你就有一本值得一讀的書了。 那是我第一次開始認真思考寫一本有關涪陵的書。我幾乎立即想到這本書的書名——我決定這個書名就是River Town。我也開始思考這本書可能的結構。我規劃章節,並決定在我住在涪陵的最後六個月,我會盡可能作研究。我有一個長長的春節假期,原先我計畫去旅行,但我選擇留在涪陵作研究,並記筆記。假期結束後,我繼續邊教書邊思考我要寫的書。在我的記憶中,我在涪陵的最後一個時期,將是我生命中最喜歡的時期之一。在這個城市,我感到十分自在;經過起初困難重重的調適後,我學會的中文已足以讓我和別人溝通,而我也交了一些好朋友。我喜歡和我的學生、我的中文老師以及黃家在一起,後者經營一家小麵館,我經常在那兒用餐。多半時候,我有了一種目標感:我決定以這個地方和這個時期作為我的寫作題材。我相信這是中國一個重要的時期,我也深信像涪陵這樣的小地方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當時,外國人往往忽視中國內地,而記者常常不重視來自鄉下的人,認為他們只是純樸的窮人。然而,幾乎我所認識的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背景,而這包括我的學生、同事、經營餐館的朋友,以及我的一位中文老師。這些人的生活複雜而多彩多姿,所以我感覺外界長久忽視他們是錯誤的。 在涪陵,我仔仔細細地作筆記,也為我要寫的書規劃結構,但是,我一直到離開中國才開始寫作。我回到我父母位於密蘇里的家,我已經多年沒有住在那兒。我在我中學時期使用的書桌前坐下來,這個房間的裝飾仍然和我小時候一樣,這讓我感覺很奇怪,因為我已經二十九歲,擁有兩個大學學位,但我單身,而且沒有工作。事實上,除了在和平工作團教書,我從來沒有任何工作。我沒有什麼錢。在美國,快三十歲了還和父母住在一起,尤其又沒有工作,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所幸的是,我向來和家人非常親近,而且我對我的寫作計畫充滿信心。雖然如此,我為我的未來感到憂心,耗了一番極大的努力後,我才掃除憂慮,坐下來寫作。 然而,一旦開始寫涪陵的故事(即使只是在第一個寫作階段),我就明白情況不同了。我寫得很順利,感覺一切都歷歷如繪。當我重讀幾個段落,我感覺它們妙趣橫生。我明白我的寫作聲音完全改變了,彷彿我的音調變深沉了,彷彿我有了一種新的信心,而我的文筆和幽默也顯得渾然天成。部分原因是我在乎我的題材,但這種情況也反映了一種新的成熟度。我明白涪陵的挑戰迫使我成長,而這種新熟度讓我的寫作有了新的深度。 我振筆疾書,一天寫五、六頁。在那段時間,除了寫作,我幾乎什麼也不做。我會在早上寫作,中午時,我會去外面跑個十幾英里。下午和晚上,我繼續寫作。夜晚時,我夢到涪陵,有時候,我幾乎流著淚醒來,因為我太想念那地方了。 我在四個月內完成《消失中的江城》的初稿。在那段期間,我也寄求職信給美國各大報社和雜誌社。我的計畫仍然沒變——我認為我會開始為一家報社或雜誌社工作(也許是在美國),最後,他們會派遣我以記者身份去到中國。但是,我旋即明白,沒有人對我有興趣。事實上,我甚至沒有收到任何個人回函,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費城詢問報(Philadelphia Inquirer)、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時代雜誌和新聞週刊都拒絕我。只有洛杉磯時報給我一封個人回函,一位編輯告訴我,他喜歡我的作品,也對我的中國背景有興趣,但是,我缺乏正式經驗,他們不能雇用這樣的人。他建議我在美國一家小報社找一份工作,如果我從那裡開始,我可以工作幾年,證明自己的能力,然後,也許我就可以在一家大報社找到工作。之後,我可以賣力工作,再度努力證明自己的能力,也許幾年之後,我會以記者身份被派去中國。我至少需要六年才能夠回到中國。 就在我即將完成《消失中的江城》,我收到了最後的拒絕信。此時,無論就心理或身體而言,我已經精疲力竭。寫這本書的最後幾章時,我嘗試忽視拒絕,強迫自己專注於涪陵。然而,完成這本書時,我就崩潰了。我陷入極大的沮喪之中,突然之間,我明白我已經二十九歲了,卻仍然前途茫茫,無法以記者身份回到中國。至於《消失中的江城》,我相信這是一本很糟糕的書,沒什麼價值,就像小孩寫的東西。我完全迷失了方向,再也無法以正確的眼光來看自己所做的事。後來,我得知許多作家振筆疾書一段時間後,都曾有過崩潰的經驗,就像有時候,有些母親經歷漫長的懷孕期之後,可能得到產後憂鬱症。 在一個月的大部分時間中,我覺得十分沮喪,幾乎無法做什麼。書的手稿就擺在那兒,我不會把它寄出去。但是最後,我開始恢復了,終於把它寄給經紀人。然而,幾乎所有的經紀人都拒絕我,只有一個叫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的年輕經紀人告訴我,他喜歡這本書。他把這本書寄給出版商,有幾家給他正面的答覆,但是,他們擔心美國讀者對於中國缺乏興趣。其中一家出版商說:「這是一本好書,但我們不認為美國人會想讀一本有關中國的書。」這話令人難以置信,但這就是一九九九年初期市場的情形——美國人尚未明白中國改變了多少,也不明白中國變得多麼具有吸引力。 但是,威廉找到了三家願意出價購買本書版權的出版公司,而我和Harper Collins簽了約。那不是一大筆錢,但那筆錢讓我還清大學助學貸款,也讓我對自己的寫作能力重新燃起信心。突然之間,我明白所有那些報紙或雜誌編輯都大錯特錯了。他們不明白我的作品價值,也不明白雇用具有中國背景的記者是多麼重要。所幸的是,並非只有他們才是重要的,他們無法掌控我的生命。我可以靠自己回到中國。 而我就是這麼做。一九九九年春天,我買了一張到北京的單程機票,而我就在那兒當起自由投稿作家。最初幾個月,工作很難找,但是後來,指派工作開始出現了。不久,我就忙得不可開交。在二〇〇〇年,我有幾個空檔,於是我開始為《紐約客》(The New Yorker)和《國家地理雜誌》寫文章。不久,許多以前拒絕我的報社和雜誌社就開始寫信問我,是否想要一份工作。但是為時已晚,我喜歡自己工作所享有的自由,也喜歡選擇自己的寫作計畫。關於我要如何描繪中國,我有自己的許多想法。以前,我認為找工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而現在,我再也不必為這件事傷腦筋。現在,我永遠會感激那些在一九九八年拒絕我的編輯。回想起來,這是我碰過最好的事情之一。 《消失中的江城》已經出版超過十年了。出版商沒有料到,它會成為美國最暢銷的書之一,而且這本書持續受歡迎。事後看來,我很幸運能夠在美國人和歐洲人開始重新發現中國之際出版這本書。今日,我們很難想像有哪一位編輯會說,讀者對於中國沒有興趣。對於外面世界缺乏興趣常常是美國人的問題之一,但中國是一個例外。一個經常讓我印象深刻的事實是:許多美國人對中國充滿了興趣,而我尤其高興看到,許多美國年輕人在學中文。《消失中的江城》往往是他們所閱讀的書之一,而我很高興這本書有助於讓美國人和其他國家的人認識中國。 當我寫《消失中的江城》,我不確定涪陵人對這本書會有什麼反應。當我修訂這本書,這是我最掛念的事。我改變大多數書中人物的名字,但我擔心那些人會覺得受到侵犯。我知道中國人對於外國人如何描繪他們往往非常敏感,我明白這種敏感性——我不喜歡一九九〇年代後期大部分外國媒體所描繪的中國。我相信這些描繪顯示出他們不了解中國,而且很少全面性地呈現中國人。在那些描繪中,一切似乎顯得灰沉沉而憂傷,缺乏我在涪陵時深刻感受到的幽默、生氣和活力。我希望這本書不一樣,但我不確定中國人會同意這個看法。我想也許他們會把這本書,斥為另一本充滿偏見、不了解中國的外國人所寫的書。 結果,我在中國住了十年以上,寫了三本書,也為《紐約客》和其他雜誌寫了許多報導。但是在這段期間,我的作品很少在中國出版。我從來不喜歡這種情況;只為了專家而描寫一個地方似乎是不對的。然而,因為種種理由,我的書無法在中國出版,而我為雜誌寫的報導沒有被翻譯出來。 這一切因為台灣而開始了有不同。二〇〇一年,我第一次到台灣,去採訪石璋如,他是在二戰前曾於安陽發掘出許多重要遺址的考古學家。我刻意安排了這趟旅程與台灣立法委員選舉的時間重疊,這樣一來我便可以淺嘗到台灣政治的滋味。對來自大陸的人來說,這是一種啟示──我能夠簡單地打電話給一個政治人物安排訪談,並且可以毫無畏懼或擔憂展開一場有趣的對話,這令我感到驚訝。這讓旅行讓我對台灣更有興趣,包括它的歷史和它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當我在寫《甲骨文》的時候,我有關於台灣的一大章:〈選舉〉──我希望這本書不只是關於人民共和國。這本書隨後在台灣譯成了中文出版,某部份原因是他探觸到了台灣議題,而反應也不錯(我時常能從我太太的家人那邊口中得知台灣對此書的反響──我的岳父岳母皆是生長在台灣,後來移民到美國)。 然而,我的作品能在大陸出版則是過了許久以後,大約是在二〇〇七年,我開始注意到中國大陸翻譯出許多外國故事並登在網路上。與此同時,中國出版商也開始展現出對外國作家更高的興趣。在2011年,我的其中一本書《尋路中國》(Country Driving)在大陸出版,我不知道讀者的反應如何,不過去年春天回到中國,我同意發表幾次演說,並接受一些訪問。但說老實話,我當時以為中國人對於這種書不會有太高的興趣。 結果,這趟我兩年多來第一次的中國之旅讓我大開眼界。我所參加的每一個以本書為主題的活動都擠滿了人,而我遇見的人都是十分敏銳而細心的讀者。整體而言,他們提出的問題,比我在美國類似的場合被問到的問題更加尖銳、更加洞察入微。當我發現中國讀者和這本書產生聯繫,我感到很興奮。他們明白我為什麼有興趣描寫三岔和麗水這種「無關緊要」的小地方,也明白為什麼我如此在乎普通老百姓——農民、移民和小企業家。 過去幾年,我感到中國人對於自己的社會產生一種新的好奇心。我認為這一點反映了某種發展階段的現象。經過二十年的快速經濟成長,現在的中國有更多受過教育的人,而他們的經歷十分豐富,所以,他們很想評估他們的國家處境以及未來的方向。他們遠比我所記得的一九九〇年代的中國人更能認同我的書。當然,網路幫了一個忙,但是,他們也和外國人有了更多的接觸。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有了一種新的信心。我認為這是他們對於「尋路中國」的反應中,最令我開心的一點。中國讀者對於本書所持的態度,大致就像美國、英國或歐洲讀者對於本書所持的態度。他們看出自己的文化的複雜性,也明白為什麼一個外國人想要將探索重點放在幾個特定的地方。他們明白,沒有一個人可以對中國作出最後定論。一個外國人的觀點是有幫助的,而一個中國人的看法也是如此。同樣地,聆聽男人的看法和聆聽女人的看法一樣重要。在一個複雜的國家,盡可能聆聽更多人的看法是有用的。我希望我的書有助於讓人們理解這個迷人的國家。 在那年春天的中國之旅中,我也回到了涪陵。現在,這個城市比我以前住在那裡時大了一倍,而且在許多方面已經讓人認不出。當我在那裡教書,我們得搭長江的船去重慶或其他大城市,而現在,那裡已經修建了好幾條公路和鐵路。我任教的學院的學生已經從兩千人增長到將近一萬四千人,這一點反映了中國各地高等教育的迅速發展。長江也改變了,我曾在我的書裡描述白鶴梁,描述我在一個冬天如何站在那兒注視著其上可以追溯至唐朝的刻文。今日,由於三峽大壩的興建,白鶴梁已經沉到水面下一百三十英尺的地方。但是,我仍然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古老刻文,因為這個城市有了一座嶄新的水下博物館,這個興建計畫花了一億三千兩百萬人民幣,在一九九〇年代的涪陵,花這一大筆錢是不可思議的。 城市的一些改變讓我充滿懷舊情緒,甚至讓我覺得有些憂傷,因為我記憶中的城市已經消失無蹤。但是,基本的精神仍然在那兒,而隨著時間的流逝,我愈來愈感激我有機會於一九九〇年代後期住在涪陵。我相信那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時刻,而涪陵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地方,一個一切都瀕臨改變的城市。 我很感激曾在台灣幫我安排翻譯出版的tk,也很感激我以前在涪陵的同事李雪順,他在中國翻譯了此書。這本書能在台灣海峽兩邊都被閱讀到,對我來說意義重大。 我永遠感激我在涪陵的朋友,在我住在那裡的兩年,他們非常開放,也有著極大的耐心。我仍然和將近一百位以前的學生保持聯繫,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樂事之一。過去幾年,我看著他們成長,而現在,我經常收到他們的來信。我也和其他幾個好朋友保持聯繫,而回到涪陵(像去年春天那一次)令我感到非常興奮。我期望未來還有機會重返涪陵。我不知道這個城市會經歷什麼變遷,但我知道它將永遠是我的中國老家。 二〇一二年二月於埃及開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