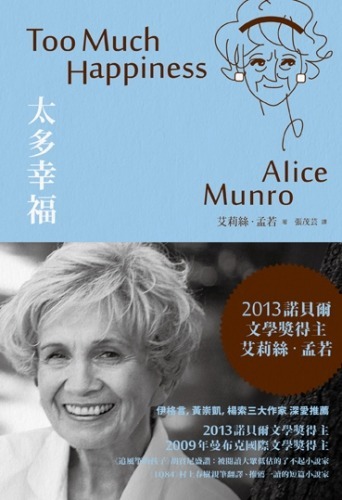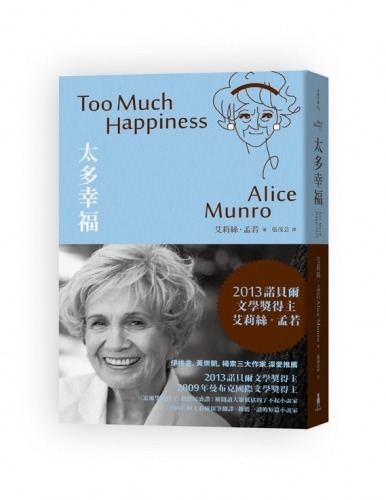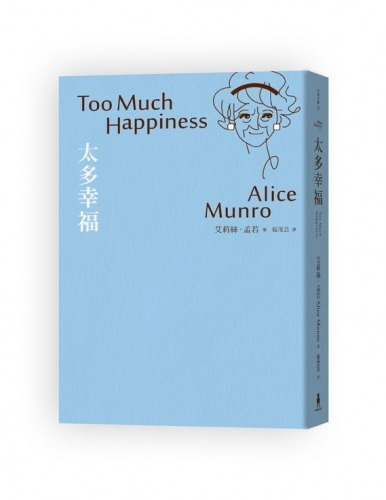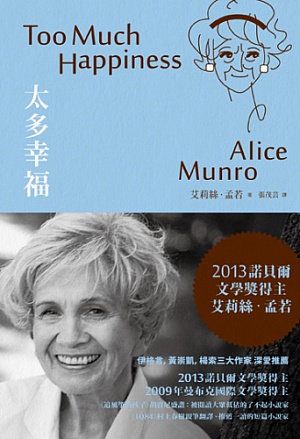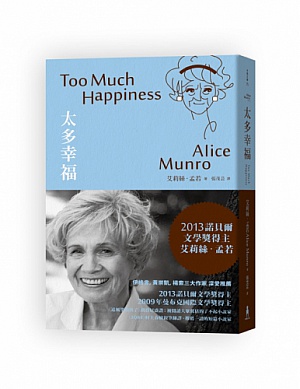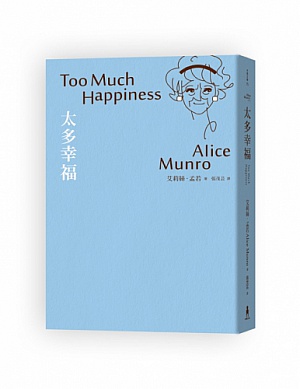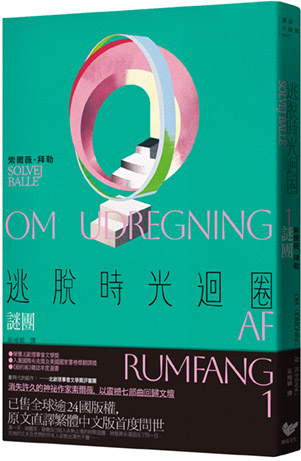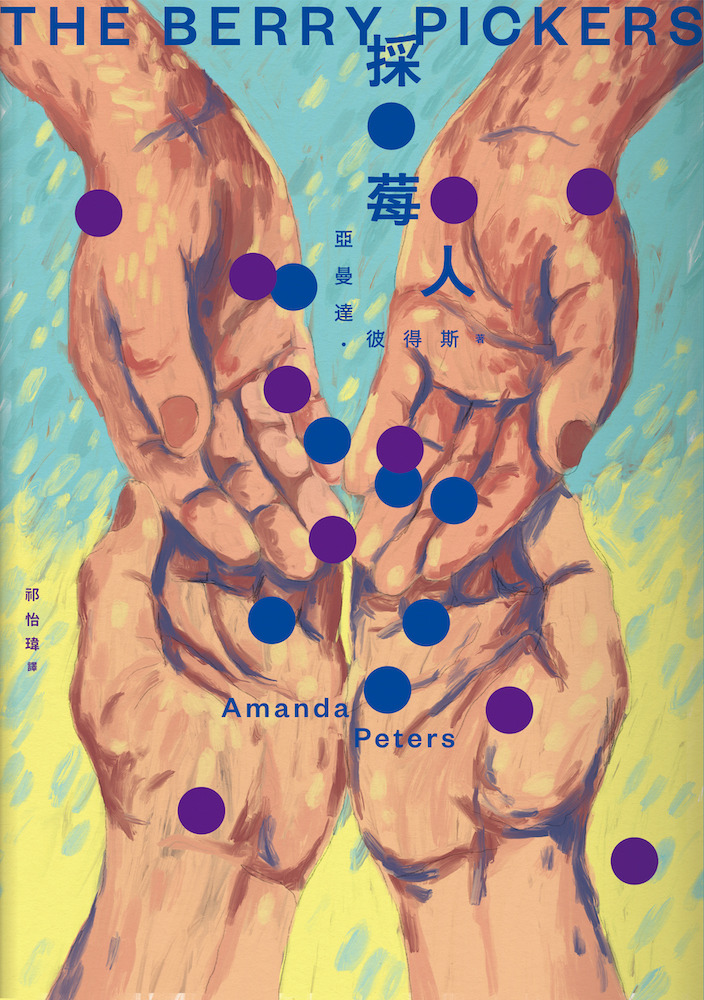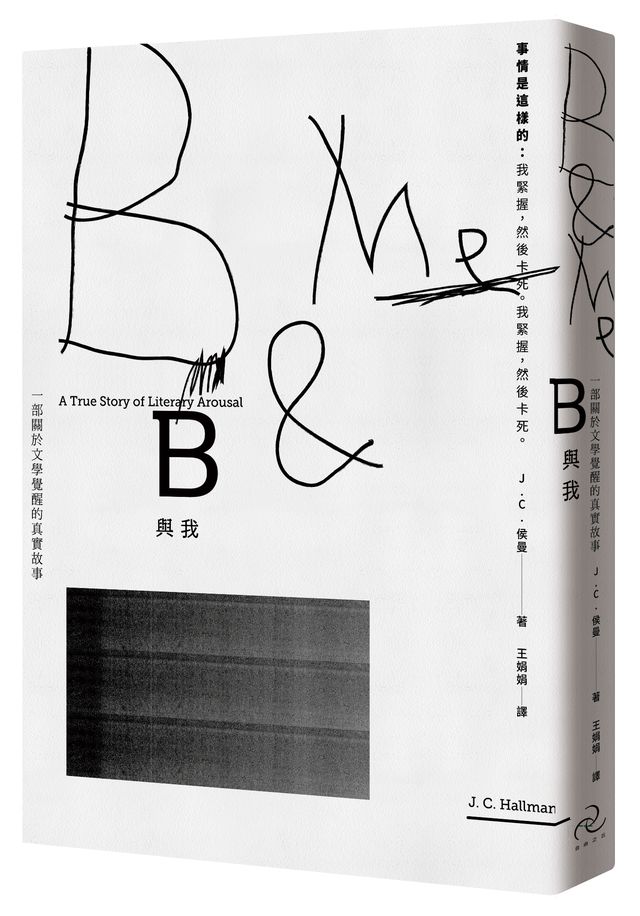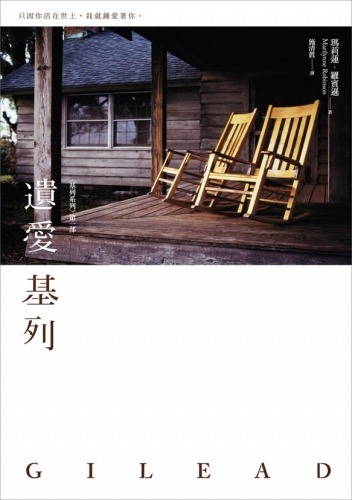自由基
大家起先常打電話給妮塔,看她是不是太傷心、太寂寞,有沒有食不下嚥,或是喝過了頭(她以前葡萄酒喝得多,很多人都忘了她現在必須滴酒不沾)。她叫他們別再打來,但語氣既未強忍傷痛,也沒故做開朗;既未魂不守舍,也沒六神無主。她說她不需要別人幫忙買菜,她正忙著一一處理手邊的事。醫生開的藥還夠,要寄謝卡用的郵票也還有。
跟她比較親的朋友大概也猜到了──實際的情況是,她根本沒什麼胃口,別人寄來的弔唁卡也全扔了。住得遠一點的人,她連寫信通知都省了,那些人自然不會寄弔唁卡來,像瑞奇住在美國亞歷桑納州的前妻,和那個住在新斯科細亞省、他已經不太往來的弟弟,她一律沒聯絡。雖然這些人應該比她身邊的人更能了解,她為何沒舉辦告別式就直接下葬。
瑞奇當時曾打電話給她,說他要去村裡的五金行一趟。那時是上午十點左右──他已經展開粉刷露台欄杆的工程,但先得把斑駁的外層刮掉才能上漆,舊刮刀偏巧壞了。
她沒時間納悶他為何不見人影。他在五金行門前的人行道招牌(上面寫著割草機有打折)旁忽地彎下身來,就那樣死了,連店門都沒來得及踏進半步。他八十一歲,除了右耳有點聽不見之外身體都好,而且上星期才去醫生那邊做過健康檢查。妮塔在事後才看到一堆相關報導,很多猝死的人,在猝死前都剛做過健檢。她說,機率高得有點嚇人,你會覺得最好別去健檢。
這些事情她本該跟她兩個密友說的──維姬和卡洛,兩人嘴巴都有點壞,兩人都和她差不多歲數(她六十二)。不到這個年紀的人,會覺得聊這種事不妥當,也未必真能體會。起先她們還一副迫她吐露心事的樣子,雖不是真的要她講喪夫之痛的心路歷程,但她真的很怕她們說不定哪天心血來潮就會發難。
她一開始安排瑞奇的後事,想當然耳,很多人都疏遠了她,只剩下可靠的老朋友。她選了最便宜的棺木,而且要求立刻下葬,什麼儀式都沒有。殯葬業者說這樣可能會違法,但她和瑞奇早就都問清楚了。他倆大概一年前就有了準備,那時醫生診斷她的病情已經到了最末期。
「我怎麼料得到,這會兒居然被他搶先一步?」
大家沒指望傳統的告別式,但還是希望多少要有個場合,讓大家歌頌生命的美好、放點他喜歡的音樂、大夥兒一起握著手,輪流說點關於瑞奇的故事,誇讚他多好多好,也免不了用他的小毛病和犯的小錯開點玩笑。
也就是瑞奇說過讓他想吐的那種場景。
所以瑞奇的後事很快就辦妥了。事情剛發生時的不安、層層包圍妮塔的溫情,也逐漸淡去,雖然她知道有些人還是會說很擔心她。維姬和卡洛倒沒這麼講,只說假如她想現在一走了之,就是個自私的混帳婊子。她們說會帶伏特加來給她補一補。
她說沒打算這麼做,雖然她看得出這之中的某種邏輯。
她的癌症目前正在緩解狀態——天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反正不是「撤退」,也不是什麼好事。她的肝是最主要的關鍵,只要她遵守小量進食,應該不會有大問題。問題也只有在她提醒朋友說她不能喝葡萄酒或伏特加時,朋友覺得掃興而已。
去年春天她做的放療還滿有用。現在是仲夏。她覺得她的黃疸現在看來沒那麼嚴重——但也可能只是她習慣了。
她早早起床、洗澡,手邊有什麼衣服就穿什麼。不過她確實有穿衣服、有洗澡,還會刷牙梳頭。她頭髮長回來不少,臉旁的毛髮仍灰白,後腦勺則是黑色,一如以往。她會塗口紅、描眉毛,儘管眉毛現在有點稀疏。她又看了一下自己的腰和臀(誰不愛豐臀纖腰呢),比照之前的模樣,哪怕她心裡明白,現在最適合形容她身體各部分的詞,應該是「骨瘦如柴」吧。
她坐進她習慣坐的大扶手椅,身邊是成堆的書和沒拆封的雜誌。她小心翼翼啜著馬克杯裡沖得很淡的花草茶,這現在成了咖啡的代替品。她一度以為自己少了咖啡就活不下去,結果發現自己真正喜歡的,其實是手裡捧著暖呼呼的大馬克杯的感覺。有杯在手,可以幫助她思考,不管她腦裡想什麼,無論幾小時,或幾天。
這是瑞奇的房子。他和貝蒂還是夫妻的時候買的。原本只是買來週末度假用,冬天就完全封起來。裡面有兩間小臥室、一個有單面斜屋頂的廚房,離村裡半哩路而已。不過他很快便展開改建工程,不僅自己學了木工,還加蓋了兩面側翼,一邊是兩間臥室和浴室,另一邊是他的書房。原本的屋子就這樣搖身一變,成為一個結合客廳、餐廳和廚房的開放式空間。貝蒂的興致也被勾了起來──她一開始還說實在搞不懂他幹麼買間破爛屋,但一點一滴化腐朽為神奇的工程,總讓她興致勃勃,還給兩人買了同花色的木匠圍裙。她之前的幾年一直忙於寫食譜、出書,這些都告一段落之後,她需要投入新的工作。他們沒有孩子。
貝蒂還跟別人說,她覺得當個木匠的好幫手,等於又在生命中找到了位置,她和瑞奇也因此變得比以前更親,但同一時間,瑞奇卻愛上了妮塔。瑞奇在大學裡教中世紀文學,妮塔則是教務主任辦公室的人。他倆頭一次做愛,是在一堆刨木片和鋸斷的木條裡,日後變成了中央的大客廳和挑高天花板。妮塔把她的太陽眼鏡忘在那邊──她不是故意的,但從不丟三落四的貝蒂,自是不會相信。接下來當然是老套而磨人的一哭二鬧三上吊,最後的結局是貝蒂去了加州,後又搬到亞歷桑納州;妮塔則在教務主任的建議下辭了工作;瑞奇因此無法升為文學院院長。他選擇了提前退休,賣掉市區的房子。妮塔沒有接收貝蒂的木匠圍裙,卻在一片混亂中開開心心看她的書,用電熱爐做簡單的晚餐,不時散長長的步,探索周遭的一切,帶回長短不齊的虎百合和野胡蘿蔔花束,放進空油漆罐權充的花器。她和瑞奇安頓好之後,有時想起自己不知怎地一下子就成了那個年輕的新歡、得意的小三,活躍歡笑、蹦蹦跳跳的天真姑娘,不免多少有點汗顏。她個性其實一板一眼,是個笨手笨腳,在別人面前就不自在的女人(她早已不是女孩)。她能一一列出英國所有皇后(記得住國王很不錯,但背得出皇后是本事),對三十年戰爭倒背如流,卻不敢在別人面前跳舞,而且和貝蒂一樣,怎麼都不肯學著上梯子。
他們這屋子的一邊有一排雪松,另一邊則是鐵軌的路堤。這裡火車的流量並不大,現在一個月大概只有兩班車。鐵軌間長滿了綠油油的雜草。她快邁入更年期時,有次曾跟瑞奇開玩笑,說兩人可以到那邊去做愛——當然不是在枕木上,而是枕木旁狹窄的草堤上。於是他們真的爬下路堤,喜不自勝。
每天早晨她坐在自己慣常坐的位子時,總會仔細地把瑞奇不在的地方想過一遍。他不在小浴室,那裡仍擺著他的刮鬍用品,和一些治小病不管大病的處方藥,他始終捨不得扔。他也不在臥室,她剛剛整理好了才走出房門。他也不在大浴室,他只有想泡澡的時候才會踏進這裡。他也不在廚房,去年這裡幾乎成了他的地盤。他當然也不在刮漆刮了一半的露台,作勢在窗口調皮地偷窺──他們剛同居的時候,她很可能曾在窗前假裝要跳脫衣舞。
他不在書房。這裡是最看得出他已不在人世的地方。起先她覺得有必要走到書房門前,打開門,就那麼站著,掃視那成堆的紙、奄奄一息的電腦、散落四處的檔案、向上或朝下攤開的書、書架上擠得滿滿的書。現在她已經練到只在腦中想像就夠了。
就這陣子,她總會有一天踏進這書房。她一直覺得這是種侵犯,但她總得侵入亡夫已死的心靈。她之前從沒有過這種念頭。她總覺得瑞奇十足俐落能幹,那麼健壯、那麼真實地存在,所以她始終相信(雖然很沒道理)他會比她長壽。結果到了去年,這念頭就一點都不荒謬了,但她覺得,他們倆心裡都清楚這是必然的結局。
她打算先整理地窖。那確實是個地窖,不是地下室。泥土地上鋪著木板做的步道,小小的頂窗布滿骯髒的蜘蛛網。這裡擺的東西,她沒有一樣用得著。只有瑞奇用到一半的油漆罐、存著備用且長度各異的木板、不知是有用還是準備要丟的各種工具。她以前只打開門下來過一次,看看是不是有燈沒關,確定燈的開關都在,而且旁邊都貼了貼紙,寫著哪個開關控制哪盞燈。她上樓後,照例把廚房通往地窖的門閂上。瑞奇以前常笑她這個習慣,說地窖裡是石牆,窗戶又那麼丁點大,問她覺得有什麼東西能進來找麻煩。
儘管如此,地窖還是最容易先動手整理的地方,比書房容易上百倍。
她已經鋪過床,把自己在廚房和浴室製造的小髒亂都整理好,但她完全沒有來個大規模掃除的衝動。她這個人,連弄彎的迴紋針、失去吸力的小磁鐵都捨不得丟,怎麼可能丟得掉她和瑞奇十五年前旅行時買的愛爾蘭硬幣碟?每樣東西似乎都生出了自己特有的分量與親疏。
卡洛或維姬每天打電話來,大多接近晚餐時分,想必她們以為她這個時候最受不了孤獨。她說她很好,不久就會出關,她只是需要一段時間,就是想想事情、看點書。她吃得下、睡得著。
這些都算實話,但看書那部分除外。她置身自己的書堆中,卻一本也沒打開。她一直都愛看書──瑞奇正因如此,說她就是他要的女人,她可以靜靜地坐著看書,不吵他。但現在她連半頁都看不下。
她也不是把書看完一次就不再看的那種人。《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慾望之翼》、《魔山》這幾本書,她看了又看。她會拿起一本書,想說就讀某個特別的段落吧──結果發現自己欲罷不能,又把整本書重新讀過。她也看現代小說,而且總是選擇小說。她不喜歡聽人用「消遣」這詞形容小說,搞不好還跟人認真爭論過,說現實生活才是消遣。這觀念太重要了,去吵它反嫌多餘。
而現在,非常詭異的是,這一切都消失了。不單是因為瑞奇的死,也因為她滿腦子都是自己的病。她想過,這改變是一時的,等她停了某種藥,做完折騰人的療程,那種魔力又會回來的。
顯然,沒有回來。
有時她想像自己對面坐了個人對她發問,她努力想說出個所以然來。
「我太忙了。」
「大家都這樣講。妳在忙什麼?」
「我忙著注意。」
「注意什麼?」
「我是指想事情。」
「想什麼事?」
「算了。」
有天早上,她先坐了一會兒,覺得很熱,想說應該起來開風扇。她也可以為環保盡一份力,把前後門都打開,如果有風,就會透過紗窗吹進來。
她先把前門的鎖打開。連半點晨曦都還沒透進來,她就察覺門口一道黑影擋住了光。
紗門外站著一個青年。紗門的鉤子是扣上的。
「我不是存心要嚇妳。」他說。「我正在找有沒有門鈴什麼的,還敲了一下門框,可是我猜妳沒聽見。」
「不好意思。」她說。
「我是來檢查妳的保險絲箱。妳跟我說在哪裡就好。」
她往旁挪了一下,讓他進來,又想了一下保險絲箱在哪裡。
「對了,在地窖。」她說。「我待會兒把燈打開,你就會看到了。」
他把門帶上,彎身脫鞋。
「沒關係。」她說。「又沒下雨。」
「還是脫鞋好,我習慣了。是會有點灰塵,但不會留下泥巴的痕跡。」
她走進廚房,想說等他走了再坐下。
他從地窖走上來時,她幫他開了門。
「沒問題嗎?」她問。「你找到保險絲箱了嗎?」
「沒問題。」
她帶他往前門走,卻發現背後沒有腳步跟上來,她一轉身,見他站在廚房裡。
「妳會不會剛好有什麼東西,可以弄給我吃?」
他的聲音變了──有點嘶啞,音調高了幾度,讓她想起某個電視喜劇演員模仿鄉下人嘟囔的模樣。廚房天窗射下的光一照,她才發現他不怎麼年輕。她方才開門時,只注意到他很瘦,因為背光,整張臉是黑的。但她現在看到的身子雖瘦卻很憔悴,完全不是年輕男人的樣子,朝她故做親切地欠欠身。臉長而剛硬,淡藍的眼相較之下很突出。表情帶點玩笑,但藏著某種固執,好像他總能為所欲為。
「是這樣的,我有糖尿病。」他說。「我不曉得妳認不認識有糖尿病的人,不過,糖尿病的人餓了就得吃東西,否則身體就會出毛病。我來這裡之前就該吃東西的,只是因為趕時間沒來得及吃。妳不介意我坐著吧?」
他其實已經坐在廚房桌邊。
「妳有咖啡嗎?」
「我有茶,花草茶,你想喝的話。」
「當然。當然。」
她量好茶葉,放進杯中,插上電熱壺,打開冰箱。
「我沒什麼東西。」她說。「有幾個蛋,有時我會炒個蛋,澆上番茄醬吃。你想這樣吃嗎?我也可以烤點英式馬芬麵包。」
「英式、愛爾蘭式、阿貓阿狗式,我無所謂。」
她在鍋裡打了兩個蛋,把蛋黃弄散,用叉子攪動,又把馬芬麵包切對半,放進烤麵包機。再從碗櫃裡拿了盤子,放在他面前,又到放餐具的抽屜裡拿了刀叉。
「好漂亮的盤子。」他說,拿起盤子端詳,彷彿上面映著他的臉。她要去看鍋裡的蛋時,聽見盤子落地摔成粉碎的聲音。
「喔請原諒我。」他的聲音又變了,變得尖銳,顯然不懷好意。「看看我幹了什麼好事啊。」
「沒事沒事。」她回道,心裡知道肯定有事。
「一定是我手滑了。」
她把另一個盤子擱在流理台上,準備放烤好的麵包,加上塗了番茄醬的炒蛋。
他已彎身去撿地上的瓷盤碎片,拿起其中一片帶尖角的。她把麵包和蛋放在桌上的時候,他把那尖角沿著光溜溜的前臂輕輕往下劃。細小的血珠浮現,起先是零星的幾滴,接著便匯聚成一道血流。
「噢,不要緊的。」他說。「只是好玩。我知道怎麼劃著玩兒。要是我玩真的,就用不著番茄醬了,對吧?」
地上仍有些他沒撿的碎片,她轉身想去拿後門櫃子裡的掃帚來,他卻閃電般一把抓住她的手臂。
「妳坐下。我吃東西的時候,妳就坐在這裡。」他又舉起流血的那隻手臂給她看,然後用盤裡的東西堆成一個雞蛋滿福堡,三兩口吞下肚,而且咀嚼的時候還張著嘴。電熱壺裡的水燒開了。「妳杯子裡放的是茶包嗎?」他問。
「嗯,其實是茶葉。」
「妳不要動。我不要妳接近那茶壺,好嗎?」
他把滾水倒進茶杯。
「看起來跟稻草一樣。妳就只有這玩意兒?」
「對不起。是的。」
「別老說對不起好不好。如果妳只有這玩意兒,那也只有這樣啦。妳根本就不相信我來這兒是為了檢查保險絲,對吧?」
「呃,對。」妮塔說。「我本來是相信你的。」
「妳現在不信了。」
「不信。」
「妳怕不怕?」
她決定把這句話當成嚴肅的問題來思考,不去想成他在嘲笑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