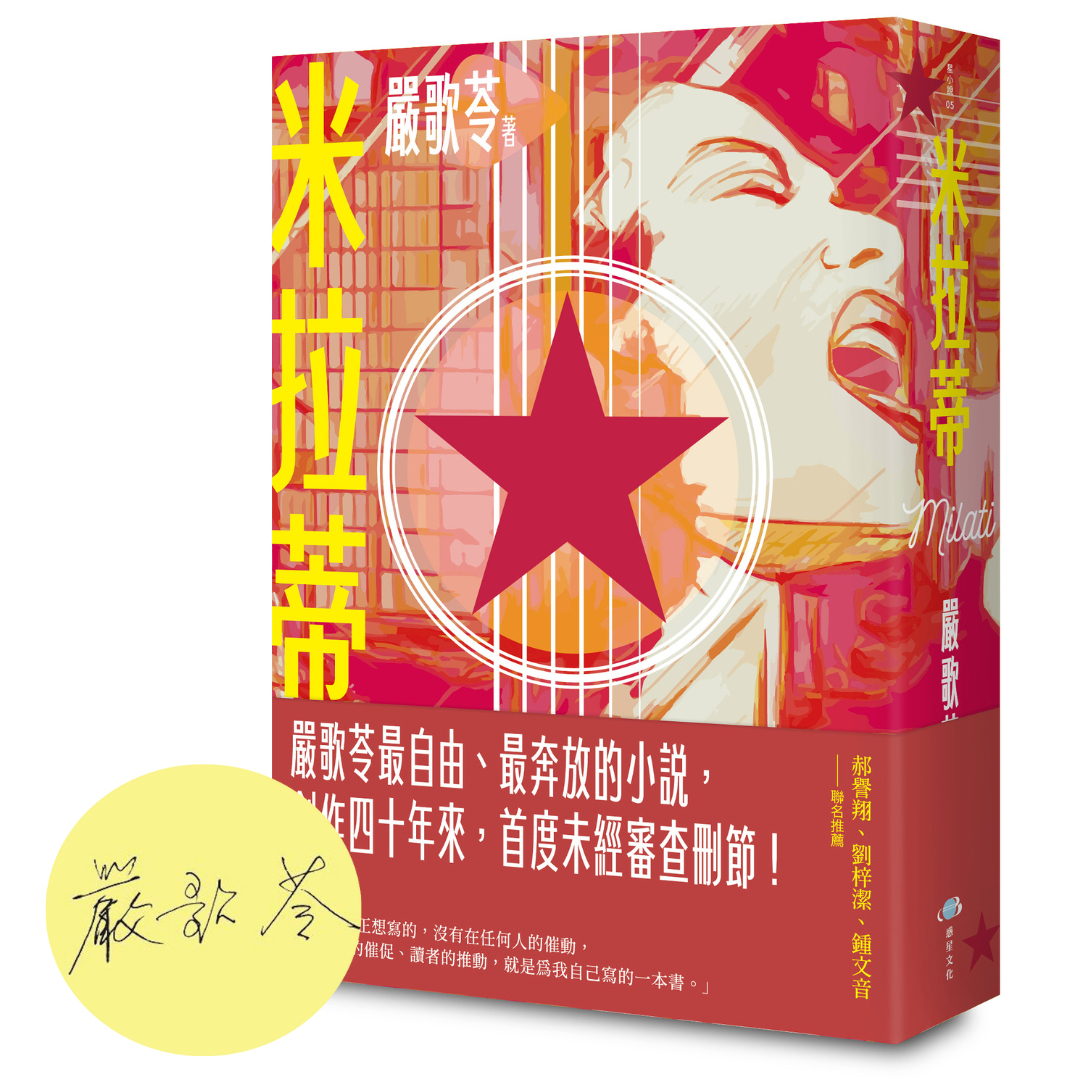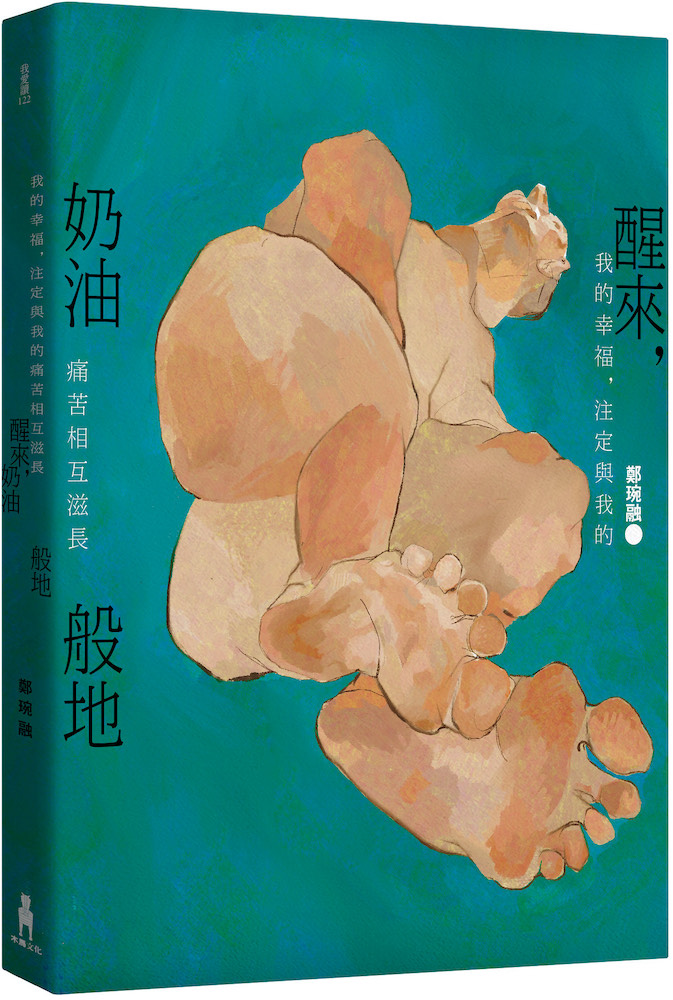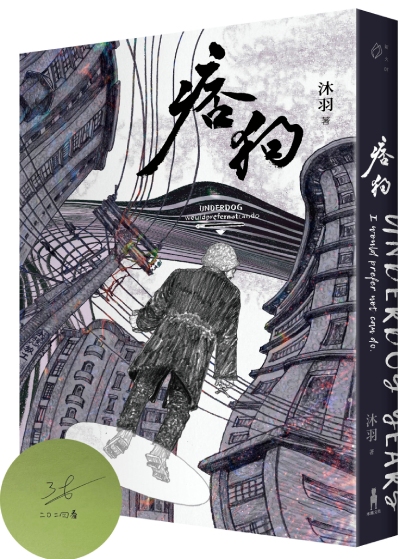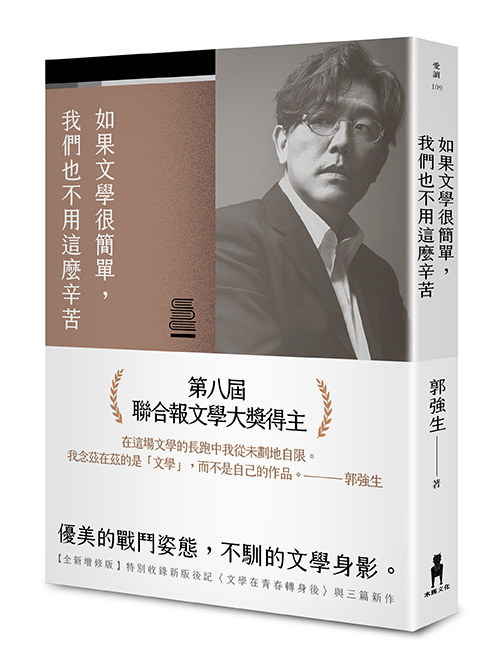「她處理的,其實一直是關於疼痛的記憶。」—黃宗潔
「小說鋪陳的人生處境,突顯了過度簡化的革命語言如何在日常裡失效。」—謝曉虹
《觀火》集結作者蘇朗欣廣受讚譽的得獎佳作與數篇全新創作。以二〇一九年香港社會運動為核心,聚焦於和我們一般,仍為生活煩憂的凡人,在最動盪的時刻,展現出深層複雜、幽微動人的情懷。以及事後面對運動餘緒—從暴動案審訊、疫情到移民潮—如此劇變的世局下,運動或許已經結束,但生活始終繼續,這些人、這些故事仍會被記憶,被書寫。
在不同主張、對立的憤恨、激情中,小說捕捉到最細緻微妙的情感。或是圍困中彼此分享生死與共的煙、或是快意報復後的茫然與內疚感、或是為消失的貓無聲祈禱、寫給離世父親的一封書信、或者母親的一碟蒜泥白肉······在日常事物內斂收束深切的情感。
「觀火」既是本書關懷香港社會運動的主題,也是警醒保持距離,透澈思考觀察運動的本質。
推薦序
或為灰燼或燎原:讀《觀火》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黃宗潔
曉晴突然覺得世上的一切溫和而善良,儘管這種想法如此不合時宜。她幻想著自己的大學,這一間花蓮的風光明媚的大學,在夜裡著了火,焚燃出焦紅色的天空。但是,在台灣,會有這種事嗎?她無法想像。
重讀朗欣置於全書篇首的〈打火〉,心情是複雜的。她筆下那間風光明媚的大學,因為二零二四年四月一場強震引發的大火,已焚燃了一夜焦黑色的天空。看著怵目驚心的新聞畫面時,朗欣是否想起這段文字,或是想起了曾經的,另一場校園裡的火光?無法想像的事成了真實,「不合時宜」的想法彷彿更加不合時宜了?但無論是書名「觀火」二字,抑或這篇帶有若干自身色彩的〈打火〉,隱約流露出的,對於自己看待世界的眼光、自己與世界相對位置的不確定感,始終是朗欣創作時,某種猶疑的起點,此種猶疑,卻帶來了深刻的可能――「不合時宜」的文字背後,是創作者持續思考的證明,也唯有文學,得以保留各種不合時宜。
對於像朗欣這樣一個仍然非常年輕,並且持續在這條道路上前進的創作者,用任何概括式的判斷,將其至今為止的作品化約為某些標籤和特色,顯然並不公平也不可能準確。但「火」與「水」的力量,毫無疑問在朗欣的小說中具有重要意義。《觀火》之前,是《水葬》。《水葬》當中的兩位重要角色,各自有一場「觀火」的生命經驗――
因圍村丁權政策擁有大片土地的「公子」柳志豪,童年時與母親寄人籬下,貧困的他最大的渴望就是一張張的鈔票,某日真讓他等到了,一個狂奔的男人口袋跌出一張又一張的鈔票,竟無人前去爭奪。與眾人逆向拚命撿拾的他抬頭一看,才發覺「大火已在眼前燃燒。火不是紅色黃色的,事後他說,火是黑色的。黑煙籠罩了你的視野,燻得你瞎了,瞎了之後皮膚變得敏感無比,灼熱的空氣從毛孔滲入內臟,你就死定了……」
即使死定了也不曾放手的公子,成年後娶了原本是游泳健將的「夫人」。婚後的夫人慢慢變成一個絕望的女人,在這絕望的婚姻絕望到連丈夫都死去之後,她在廚房裡看著蒸魚的火:
她還特地挪好木櫈,坐在灶頭前等待。沒有人會在廚房裡等一條魚的,……但她選擇留在廚房,等待室內逐漸變暖。……她只是看著,任火猛烈燃燒,當空氣歪曲傾斜,她終於提起鑊蓋,蒸氣一擁而上,黏附在牆壁、器皿、玻璃窗上,霎時四周模糊成一面陳年的鏡子,夫人的臉上也一樣地濕。」
濕氣像是泳池的水,也像是墜落的淚。「總的來說,那就是一生了。」
火的意義是什麼呢?人類學有人類學的解法,精神分析有精神分析的象徵。但在讀朗欣的小說時,我想起的是多年前,美內鈴惠的經典漫畫《玻璃假面》――在我閱讀的那個年代,台版的翻譯還叫做《千面女郎》,女主角北島麻雅和姬川亞弓,則被翻成「譚寶蓮」和「白莎莉」。在這個以兩位少女競爭成為夢幻舞台「紅天女」唯一表演繼承人為主線的故事中,她們最終的考核項目之一,就是「風」、「火」、「水」、「土」。演藝世家的「天才少女」莎莉,以舞蹈表現出火的韻律和動作,燃燒的火、成為灰燼的火;擁有天賦與直覺的寶蓮,則演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江戶時代蔬菜商女兒阿七的故事。阿七因火災到佛寺中避難,愛上住持的侍童吉三,為了再見吉三一面,不惜犯下縱火死罪,那是狂亂的愛戀之火,絕望而難以撲滅的心之火。
《觀火》之中的每個角色,也都有著他們各自的心之火,有些已成灰燼,有些卻仍熾熱,那是火的不同樣態,也是觀者的不同距離使然。而朗欣藉著文字隱微提醒我們的,或許也在於那些看似冷然的面孔底下,未必沒有他們熾熱的曾經。
例如〈旺角賓館〉裡的健與玲,在日常的磨損中,對彼此的期待與失望已瑣碎細微到,以「能否發現家裡熱可可的品牌由雀巢換成了好時」作為判斷指標。但這對看似淡漠冷然一如櫻木紫乃筆下北國男女的情侶,卻是相識於佔領金鐘的活動。不過,朗欣並未停留在「他們也曾有過熱情與理想」這扁平的對照層次,相反地,當兩人從同樣平淡的日常爭執中和好,走在黑夜底下的旺角街頭時,小說是這樣形容的:
他們都知道彼此正在回憶,但默不作聲――一個人在想自己的眼睛遭受到胡椒噴霧,另一個人在想自己看見了別人遭受到胡椒噴霧而飲泣的時刻。他們想動用語言去描述那一瞬間,卻隨即發現自己早就忘記當時的感覺,到底是憤怒、恐懼、無力還是錯愕。
記憶固然不可靠,但連感覺,也是會遺忘的。一如他們連當時承載激情、承諾未來的旅館房間,究竟是四柱床的格局,還是貼滿鏡子?都無法取得回憶的共識。集體與個人的激情,如何安放回仍在繼續、仍要繼續的日常之中?如何看待放回去之後,那些變了樣貌的理想與情感?放不回去的話,又該如何面對歧路的未來?這不只是玲與健的課題,也是《觀火》裡不同年齡、身分的角色,共同的課題。〈十三歲〉裡的明謙體會到的是:「他十三歲,已經很清楚沒有什麼是可以重來。」〈離場〉裡的阿群說服自己:「人到五十好幾,生活本來就是這樣子,行行企企。」〈靈魂通信〉裡仍是少女的「我」,則說出了看似厭世實則早熟的話語:「歷史不也像這樣子的一坑骨灰,不明不白,隨時間過去,終究被壓縮,像堆填區要出口垃圾時不也要先將固體廢物擠壓成一顆立方嗎?」但就算只是一顆堆填區的立方,她也想去看看。「沒有原因。就是想做某件事。必須那樣做,才能安心。」就像〈蒜泥白肉〉裡被嘲笑為「黃絲阿媽」的陳師奶,在事件發生前和發生後,一樣堅持守護著兒子的飲食,要為不自由的他送上一碟蒜泥白肉。
這些掙扎、奮鬥、抵抗,有意義嗎?可能有,可能沒有。關乎我們對意義的定義。但就算沒有,「生活本身多的是沒有意義的片段」。沒有意義,但依然去做,必須去做。無非為了安頓躁動的心。
讀朗欣的文字時,總覺得有著超乎她年齡的蒼涼,當初〈十三歲〉的初稿讓我有點猶疑,裡面角色的話語和思想實在太不像十三歲了。但後來我慢慢發現,那是看似安靜寡言的朗欣,以她同樣超乎年齡的動盪經歷,沉澱而來的深刻感受。儘管那寡言的形象,同樣可能來自於語言隔閡帶來的錯認。記得討論〈靈魂通信〉時已近畢業,她略吃力地組織著當時尚未非常成形的,用這篇文字來思考「未來將如何看待此刻的運動」之想法。我說,不如你用廣東話講吧。瞬間語速快轉不止四倍,那個當下再度提醒了我,我所有觀看的印象,同樣帶著位移造成的偏誤。因此,不要妄下斷語。
不要妄下斷語,或許也是朗欣對自己小說的期許。她在畢業作品的摘要裡寫下:「身在台灣書寫香港,可以是作壁上觀、事不關己,卻也可以是保持距離,重新透澈地思考、想像、觀察運動的本質。」正因為退了一步來看,才看得到火的更多形態。或為灰燼或燎原,各有因緣與苦衷。看似同路人,可能純屬巧合;形同陌路的,卻未必不曾擁有同樣的想望。她下筆慎重,有時慎重到帶點疏離,但那是因為她深知「不論個人的絕望對世界而言如何不必要,它都是非常真實,不可忽視的,它是扎在體內的一根刺,細得無法拔除,又隱隱作痛」(《水葬》)。《水葬》也好,《觀火》也好,她處理的,其實一直是關於疼痛的記憶。
蘇朗欣
一九九四年生於香港,現居花蓮。
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東華大學華文所(創作組)。曾獲鍾肇政文學獎、臺中文學獎、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等,曾入選《九歌111年小說選》。著有中篇小說《水葬》(水煮魚文化)。
推薦序:或為灰燼或燎原—讀《觀火》 黃宗潔(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推薦序:人心即火—序蘇朗欣《觀火》 謝曉虹(作家)
打火
十三歲
時間之外
旺角賓館
離場
靈魂通信
SIDE TRACK
蒜泥白肉
水與灰燼
致謝
打火
後來曉晴再見到智洋已經是十月。期中考最後一天,人潮湧出學院,曉晴在停車場裡尋到自己的單車,轉身一瞥,居然見到智洋在吸煙區抽煙。
智洋不高,戴眼鏡,頭髮削短,上掛一個殘破帆布袋,全身上下質樸無華。他倚坐在吸煙區的鐵椅上,左手搭上褪色的扶手,右手輕輕夾著剩下一半的香煙,擱在生鏽的鐵桌邊緣。桌子正中央是煙灰缸,已盛滿灰燼。香煙燒到盡頭,智洋目視星火散落,曲起指頭把煙頭彈入缸中,手勢俐落。
第一次見證那場面,曉晴愣住一下。
真想不到他會抽煙,她想,那麽乾瘦、無趣的一個男生。
然後她垂下眼眉,把背包塞進菜籃,轉身面向台灣同學,一邊跨上單車,一邊用流利的普通話談笑—從小看大陸綜藝學來的。
來台兩個月,作為港生的曉晴絲毫不認為跟台灣人之間會有任何溝通困難。對她來說,國語和普通話分別只在前者語氣溫柔,後者多捲舌音,僅此而已。她輕鬆融入環境,足跡遍布縱谷許許多多的什麽步道什麽湖什麽潭,她有自信自己去過的景點比得過本地人。所以,這次她們想去更遠的地方,慶祝順利熬過考試,要去瑞穗?玉里?要不往更南闖,台東三日兩夜?好啊,不然去墾丁,享受陽光海灘?
她夜裡躺在宿舍狹窄的單人床墊上,開始策畫一趟墾丁之旅,滑動手機查看海岸邊緣的民宿指南。
但智洋輕輕吐出的煙霧彷彿留在眼角,似有若無。
曉晴跟智洋兩個人,一個讀大學部,一個是研究生,幾近沒有相接之處。之所以認識,是因為疫情肆虐,初來乍到,每個人在機場都得先買一張電話預付卡,方便政府追蹤防疫,唯獨未滿十八歲的曉晴不能買,推拉折騰好一陣,最終找到二十四歲的智洋代辦,兩人才在五十幾位新生裡相認。
十四日隔離結束,新生們從宿舍魚貫離開,那陣時單車已經一輛伴著一輛停在樓下,港澳會的學長姊在停車場邊守候,手裡提著塞滿紙鈔和硬幣的文件袋。
當初港澳會迎新LINE群裡,學長千叮萬囑一定要買單車,不會踩的馬上去學,不騙人—畢竟這間東部大學校園廣闊是出了名—並隨訊息附上一張捷安特產品目錄。新生們慌了,趕緊下單,由學長代為訂購,聽說有特別折扣,結果還是一輛四、五千台幣,群組裡還有人猜疑是不是有詐?但得不到任何回答。
現在終於摸到車子,曉晴拍拍座墊,跨坐上去,在隔離宿舍門前的迴旋處繞兩個圈,感覺不錯,才付錢付得心甘情願。
「同學,你的車呢?」學長朝著曉晴背後發問。
她轉身,發現是智洋—她不記得他的長相,卻認得一對黑框眼鏡,還有身上洗到發白的格紋襯衫—他搖頭,說:「沒買。」
兩人對上眼。已經不可能裝作不曾遇見,唯有尷尬地搭話。
曉晴勸他不如乾脆添置一輛車,一邊給他看看手上的淑女車。智洋雙手抱胸,望著她,嘴角歪歪斜斜向下垂。道路兩邊栽滿了兩人都不認識的樹,夏日陽光穿透枝葉,在智洋的窄臉上打出交錯的光影,其中一片落在他的右眼。他眨眨眼,一直搖頭,堅持走路。
曉晴不服輸,糾纏好久。到最後,智洋才說:「我不會踩。」
她沒想到,忍不住笑:「我教你,當作報答之前辦的電話卡。」
智洋唯唯諾諾,隨便把話題帶過,那張嘴裡沒有流露出一絲鬆懈。
「好吧。」曉晴知道再講便是自討沒趣,於是隨意把話題了結,伸手一指:「那我差不多走了。去那邊。」
事實上「那邊」是哪一邊並不重要,純粹是擺脫對話的藉口°她跨上單車,疾馳而去。
智洋目送她離開,拿著學校派發的校園地圖,轉身走向宿舍。他得走很遠很遠的路才會抵達宿舍。
開學後,兩人就沒再見面。然而那十月的一瞥裡面,當煙霧飄過,在曉晴心中種下了歹念,慢慢地她竟想抽煙。一個人留學,難得擺脫了大人,就想自己當大人,可惜朋友裡沒一個像會抽的,她便不敢問。夜晚在四人宿舍,燈光滅了,曉晴躺在上層床,直到手機用盡電源,仍睡不著,她放空腦袋,想像什麽是吞雲吐霧。
受不了。
於是深夜一個人跑去旁邊的全家,硬著頭皮問:「我想買煙。七星,藍莓。」為了不出醜,還特地上網調查品牌。
大學裡的超商原來不賣煙。
曉晴隨手買了一支瓶裝茶,沿路走回宿舍。她不甘心。難得下了決心—決心像酒後的一瞬昏頭—儘管自己從未真正酒醉—就是這個晚上,她非抽上一根煙不可。她跳上淑女車,一路加快速度,從手把鬆開雙手,感受著輕盈的失重。快要踩到校門了,她在路口停下,左右回望有否機車轉出,這時候發現了一道身影。是智洋。
全是因為那種想像的酒醉,曉晴想,反正她踩過去攔在智洋身前。智洋一頓,猛地後退,狠瞪曉晴,神色警戒近乎凶狠。換曉晴嚇到了,連忙道歉。
「我只是想,嗯,跟你買一支煙。」曉晴說。
「買煙?」
「對,我想抽煙。」
智洋垂下手,尷尬地撥弄衣襬,沒有說話。
兩人陷入沉默,最終曉晴打圓場:「沒關係,我去外面買。」
「不用。」
智洋從格紋襯衫口袋掏出一包煙,抽了一根給曉晴,接著越過她,向校園走。格紋消失於幽深的樹影底下,他似乎還是低著頭,走自己的路。
曉晴拿著煙踩回宿舍,才想起自己沒有火。
那根煙不長也不幼,有一顆紫色的小球在吸嘴底端,煙紙寫著MЕVIUS。
她把煙含在嘴裡,嚐到薄荷的涼。這就是七星藍莓?她一直把玩,直到臨睡前才把煙收進襯衫口袋。卡其色半透明薄紗襯衣,防曬用,明天穿著出門。朋友說好下課帶她去七星潭看海。
隔天上課,要是有空檔,她就到吸煙區徘徊,想問煙友借火,卻又遲疑,昨天的膽色一下子全沒了。來回直到下午兩點才等到智洋,她一見那格紋就認出來,立即迎上去。智洋替她點火,手勢熟練。
曉晴終於抽到平生第一口煙,吸得輕輕淡淡,她聽說要是太用力的話,會頭暈。自問做好了所有防範措施,沒料到還是會暈眩—因為逆風,煙霧撲上她的眼睛,她用力瞇眼迴避,卻因而發昏。她閉上眼,聽見鴿子在上空迴旋,聽見枝葉搖動,聽見智洋輕笑時的鼻音。
這樣的一支煙她吸了很久,直至朋友來電,才出發去太平洋的海邊。
此後借火成為日常,她想像生活是電影《志明與春嬌》,一對男女在小巷交換一口煙,呼出了愛情°智洋不是她喜歡的類型,所以她心裡幻想的是一個高大台仔,會打扮,長著一張明星臉,在同樣的枝椏下突然出現。她其實沒看過那齣戲,和智洋相遇時也不曾談論過什麽愛情。
他們會一起嫌棄學餐又貴又難吃,嘲笑花蓮市區某些自稱正宗的港式茶餐廳,討論最近上榜的香港流行音樂,間或由她哼出一句歌詞,等他和聲—他通常都會和聲,即使每次開始時都害羞而困惑,而且聲音永遠細得幾乎不被聽見。
港澳會的同學若然不在同一個系所裡,幾乎全都在開學不久即各散東西,曉晴的校園生活沒有多少講廣東話的機會—唯獨在這一呼一吸的時刻,她終於使用母語。當舌頭發出倔強的入聲,她感到非常懷念。
到了樹葉枯黃的季節,兩個人已是心照不宣地,總在同樣時間出現在吸煙區。所有事情都成為習慣,因此在這天陰的日子,他們在吸煙區聚頭,當智洋抽出一根煙給曉晴,她仔細看著他連番開合煙盒的食指,突然感受到他情緒的變化。
她把煙遞到唇邊,還沒點火,馬上就察覺到不同。太甜。她仔細看。這不是七星藍莓。應該說,是七星,但不是藍莓,末端的晶球不是紫色而是黃色。
「這是另一個口味?」她問。
「哈密瓜。」智洋呼一口煙。他的嘴裡也有甜味。
「咦,我沒抽過。味道如何?可以先借我試試嗎?」曉晴問。卻又感覺不好意思。轉念想,不過一口煙,為什麽要尷尬。
智洋安靜了一陣,搖搖頭:「我不想。」
「哦。是哦。也是。容易交叉感染。會沾到口水。疫情嘛。」
然而智洋又搖頭,喃喃說不對。
曉晴問:「為什麽你會買這個?你平時每次都是藍莓。」
「以前抽過一次,那時跟我分享的人說是哈密瓜。我一直惦記在心裡。」
「所以就是有跟人分過嘛,女朋友?」曉晴扯開嘴角在笑。
「分享同一支煙對我來說等於分享了生死。」
智洋回答時,眉目低垂。
曉晴笑著說她聽不懂,正想叫他少裝模作樣,但眼見智洋的手凝在半空,煙沉默地燒,幾乎纏纒上指節,她便不再說話了。停頓中,有枯葉飄落地上,在曉晴眼角邊緣。有人走過,踩中落葉,葉片碎開,聲音清脆。
智洋像是突然被挖開了話匣子似地—她以為他身上沒有這東西—滔滔不絕:
「十一月那時候,我在理工大學,每一條路都被封死了。我一個人坐在七仔附近,有個陌生的手足問我有沒有煙。那時學校的七仔所有物資已被搶光,連一包煙都沒有剩下來。我身上本來還有最後一根七星藍莓,但在一次突圍時弄丟了。其實抗爭之前我都沒有抽煙,全都是因為後來壓力太大了。我跟那個人站在七仔爆開的玻璃櫥窗前,都沒說話。這時候另一個手足經過,和我們站在一起,從口袋裡抽出了一根哈密瓜的七星,我們盯著他,他也回望過來。那是他最後的香煙,但他遞過來,我們三個人輪流交換著抽,抽得很慢很慢,直到最後只剩下濾嘴,它自己熄滅了。凌晨五點半,警察打進來,我們的人往學校正門拋出雜物和白電油。當時天空是紅色的。」
智洋無意識地抖了抖煙灰,問:「你有去嗎?抗爭。」「有去遊行。」
她確實有去過一兩場六月的和平遊行,由銅鑼灣出發步行去金鐘,和朋友一起,出門前精挑細選當日的衣著配搭,也不戴口罩。後來事情逐步演變成另一個模樣,此後她對抗爭的認知都來自新聞報導、社交媒體、朋輩分享,但沒有一個朋友會跟她說起在抗爭現場抽煙。
智洋不再說下去,所有的話語彷似頓時煞停,他把煙湊近唇瓣。他總是吞吐輕盈,像在品嚐什麽人間美味;曉晴卻相反,別人一根煙的時間足夠她完成兩根,因為喜歡用力吸,用力呼,吐出來的煙霧特別多,也特別美—她不怕暈眩。已經不怕了。
「那另外兩個人,現在在哪裡?」曉晴問。
智洋還是搖頭,安靜眺望遠山。
搖頭算什麽?曉晴生起悶氣,兩個人之間落得如此尷尬,還不是因為他,是他硬要挑起這種無法輕鬆接下去的話題,挑起了又無以為繼,說一半又不說一半,像把她當成是局外人。
然而,難道她不是嗎?
曉晴沒有辦法輕率回答這個問題。
她坐到鐵椅上,問:「為什麽要來這裡唸書?我在港澳會的學長口中聽過,每年都有香港新生耐不住寂寞,決定退學,不然往北部轉學。台灣這麽大,選擇這麽多。」
兩人一同望山。除了山之外,沒有別的。
曉晴自問在奇莱山下活得很好。她不是那種會因為生活不便就放棄的人。
她已經適應濕潤的空氣,當把書本從架上拿下、發現手指摸著霉菌時,不會再感到驚訝;她清楚鄉郊地方交通不便,下定決心半年後考機車,請台灣人朋友教學,並且習慣了高速中猛風刮面的疼痛。她終於愛上這個地方——
「因為容易考上。」智洋戳穿真相。
見曉晴不答話,他苦笑:「好吧,你就當作是因為我不想再待在石屎森林,那種大城市,那種高牆。我想在花蓮看大山大海。我也喜歡散步。」
「你用走的未免太沒效率了吧,例如,如果你要買煙,由宿舍走到校外的超商要四十分鐘。」
「第一個跟我要煙的手足,說要走下水道逃亡,他彎著身向下爬,誰都不知道他有沒有成功。」
曉晴用力吸手上的七星哈密瓜。澄澈天色下,中央山脈清晰可見,彷彿永恆屹立。是它眺望我們──曉晴有種錯覺。智洋的側臉在霧裡頭隱隱約約,配合著落葉,有種少年憂鬱。曉晴突然覺得世上的一切溫和而善良,儘管這種想法如此不合時宜。她幻想著自己的大學,這一間花蓮風光明媚的大學,在夜裡著了火,焚燃出焦紅色的天空。
但是,在台灣,會有這種事嗎?她無法想像。這裡大概沒有什麼殘破的七仔,只有好山好水。
她沒頭沒尾拋出一句:「你去過七星潭嗎?」
「沒有。」
「去過哪個名勝景點嗎?」
智洋沉默,最後搖頭。
曉晴笑他:「來這麼久什麼地方都沒去過,還說什麼想看大山大海,根本騙人。」
然而話一出口,她就見到智洋的臉色頽靡下來,有如受傷。
曉晴心裡慌了,脫口而出:「不然我們一起去看好了。」為了加強說服力,還拉著智洋動身往校內的公車站出發。沒想到他真的任由了她。
兩人走到圖書館外,查看公車時刻表,好不容易等到一班,對司機一問才發現根本到不了七星潭,終點在花蓮火車站,必須抵步後再轉乘另一號公車,一路上風塵僕僕。智洋小聲嘀咕,不如別去了,卻被曉晴瞪回去,四十分鐘又四十分鐘的車程和等待,彼此默然無語,一個看風景轉眼流逝,一個合眼小憩。
抵達七星潭已經是五點,兩人下了車,望出去,偌大的風景園區裡大部分攤販都蓋上了帆布,也就是說,打烊了,沒有服務。車站只有他們倆。曉晴暗自反省,果真是太衝動了吧?還有回程的班次嗎?反而是智洋望向海,邁步前行,走到一半回身揚手召曉晴過去,似乎沒有了最初的慌亂。不安的人換成曉晴,但她又能怎樣呢,不就只能去看那日落時分的海了嗎。
十二月初,天氣說不上冷,只是天色反覆,剛才在學校還是好好的,到了海邊卻是烏雲一片,雲層低壓似欺身─花蓮一貫景觀─實在說不上什麼好天氣。然而智洋似乎非常滿意眼前陰翳的七星潭,他坐下來,伸長雙腿,兩隻手壓在鵝卵石上,支撐身體,呼出一口嘆息。曉晴猶豫兩、三,最終也跟著並肩而坐。石灘凹凸不平,久坐,屁股開始痛,她將包包墊在地上。眼前水花翻來覆去。岸邊,每隔一段路就有一小撮一小撮的人,全都捲起褲管,穿著人字拖鞋,水來時驚呼,水退了又回到原來的位置,踩踏在被海水吞吐過的砂石上。在智洋和曉晴右方,有一對情侶帶了單眼相機和腳架,三根支架插在石頭的隙縫中,他們校正倒數計時,連續自拍十張。每個人都裝備充足,毛巾、遮陽傘、風衣、手套樣樣不缺;唯獨智洋和曉晴手上空空如也,沒水沒雨傘,什麼也沒有。
最多有一包,或者兩包,七星。和打火機。
七星潭的海分成三種顏色:花白的浪,近接的碧藍,到遠方的深藍。也許更遠的地方還會有其他顏色吧,曉晴記得上一次來—便是抽那第一口煙的日子,她乘坐在台灣同學的機車後座,天空沒有半片雲,一切明媚如許,他們大笑,拔足狂奔,撿拾起散發熱氣的石頭往水面擲出—她問過同學,為什麽海會有不同顏色?她從沒見過被分割的海水。同學也許回答了,也許沒有,她沒記住。海水翻起的時候,連綿成一道壯麗的牆,後面的浪會吃掉前面的浪,最終融為一體,直撲到岸上。她維持安全的距離看潮進潮退,並且為之著迷:所有的浪都如此相似,所有的浪都不會相同。
好幾次,浪越來越急進,曉晴甚至相信大水會馬上席捲而至,自己將會和前方倒插在沙地上的一個啤酒瓶有相同下場:當海水湧近,它會顫抖,卻不被帶走—她會被全身上下沖成濕透,但仍在這裡停留。
然而每一次,泡沫頂多只會湧到她的腳趾前沿,便立即爆開,退去。水從未撲上她的肌膚,哪怕一吋半吋。
智洋撿起一塊圓石,起身往海裡拋。石頭沒入浪中,無聲無息。他再來一次。曉晴過一陣子才猜出來,那是彆扭的打水漂。
「你那樣不行的啦。」她說:「擲出去的時候要彎身,腰要扭轉。石頭要旋轉。」 她挑了一片扁平的礫石,在遠離水邊的地方示範動作。
智洋回頭看她。逆光使她無法辨識他的表情。智洋再次抛出石頭,仍然連一次彈跳都沒有發生。他彎腰,挑剔地揀選,撿拾。
天空逐漸邁入澄黃,不過也許是因為天陰,他們沒有遇上期望中的渾圓夕陽。但海仍然美,泛著火一般的光澤,燦爛到刺眼。若是平常時候,曉晴會抓緊短暫的日落時光,拿手機拍照,換好幾個角度,發給朋友家人,但此刻她只是凝望智洋不屈不撓地拋擲的身影。每一顆石子都噗通跌入海中,一切都毫無起息,卻無礙他的興致,假如那稱得上是一種興致的話。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