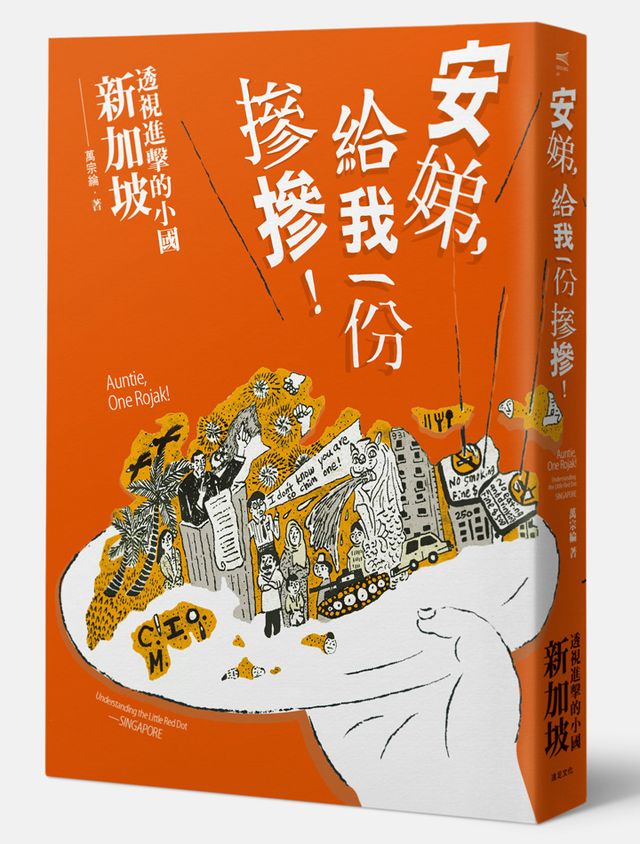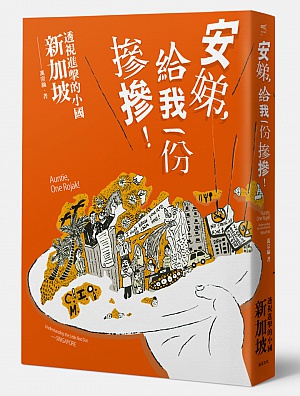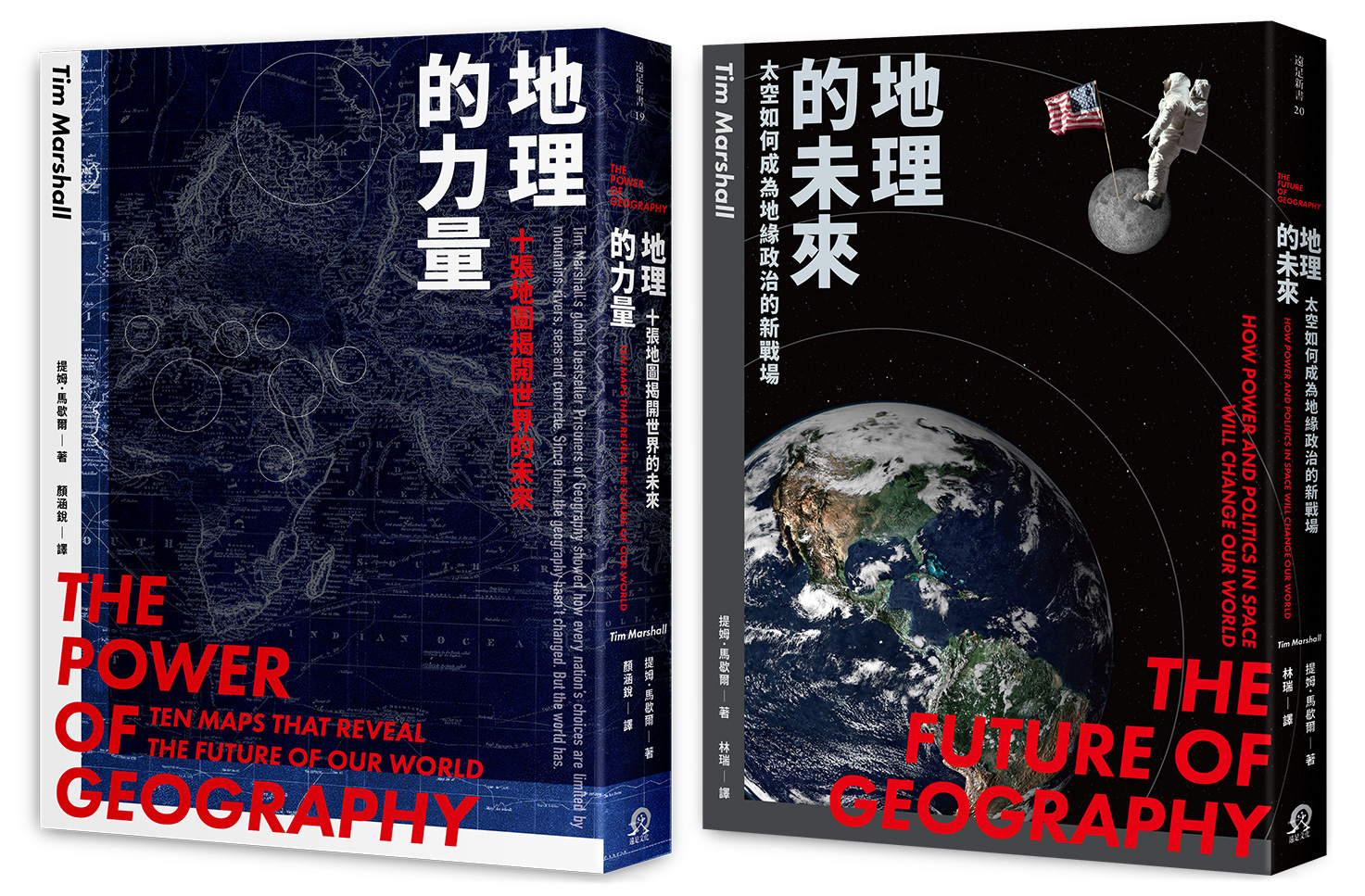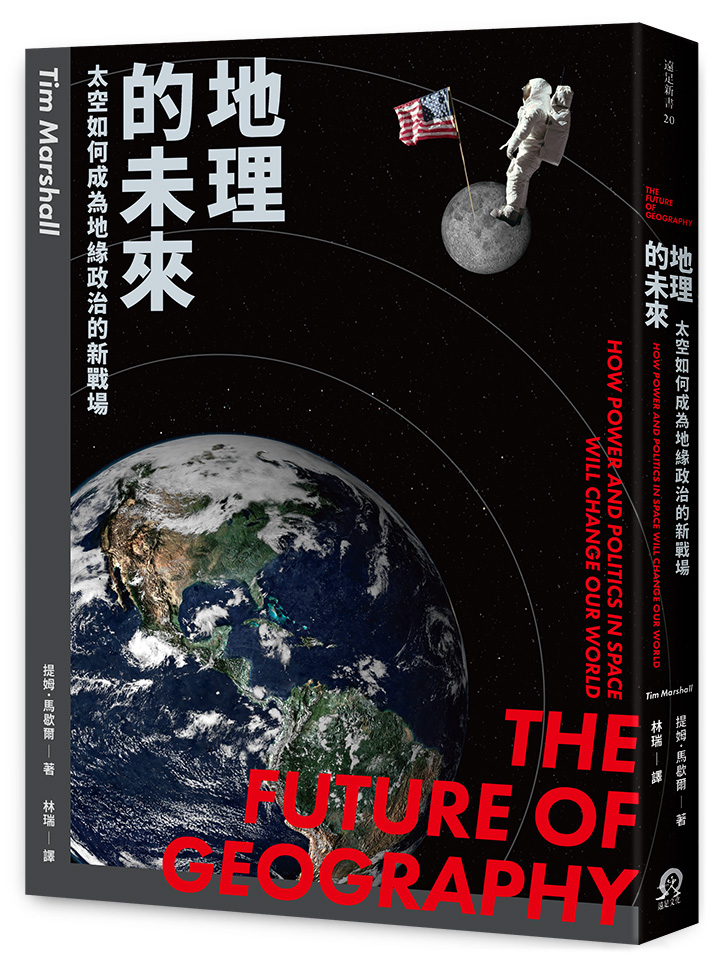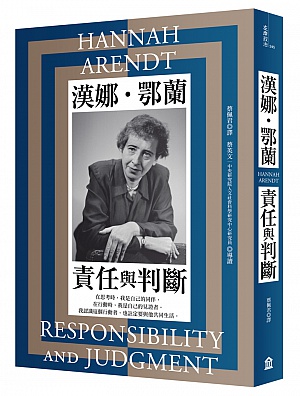摻摻:意指什麼都要、什麼都有、不純粹、混合起來
新加坡國土小歸小,卻蘊含無限大的可能性;
獨立建國短短50年,但鎔鑄各族移民們帶來的悠長歷史文化;
一句「SiNGLISH」便能劃分你我、說華語運動展現李氏政權的務實性格;
小印度、小泰國、小緬甸、中國城乃至甘榜馬來,
不只為滿足觀光獵奇想像,也是獅城內在微縮的種族模型
作者身為社會語言學研究者,不打算提供「柯P」式期待的政經成功模式,
反而引領同為小島國家、擁有多元民族的我們,
穿越語言、種族與領土疆域的界線,珍視複雜性所帶來的層次與韻味
萬宗綸
新加坡國立大學語言學碩士、台灣大學地理系學士,大學時創辦了《GeogDaily地理眼》學術普及網站。關心城市中語言的使用,相信透過探索語言生活能更瞭解一個社會文化,現為《轉角國際udn Global》、《鳴人堂》專欄作家。在旅行中找尋亞洲,在書寫中找尋觀點。新北土城人,最喜歡的小鎮叫卓蘭。
插畫簡介
葉懿瑩 I Ying Yeh
插畫家,作品常見於各報章雜誌書籍等。喜歡繪畫、設計、花草與飲食生活,認為生活中的人事物與大自然是創作時最好的靈感來源。著有《季節禮物:插畫家的台灣旅行記事》圖文作品。
Facebook專頁: I Ying Yeh 葉懿瑩
推薦序
此時此地,向移動致敬
黃舒楣.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助理教授
十一月中甫因會議而造訪新加坡國立大學(當地簡稱國大)亞洲研究中心,回來幾天接到宗綸邀請撰序,正好延續了累積幾日的思考。我翻閱書稿,隨著他記述而重訪他在國大精彩豐富的一年,校園中遇到的那些年輕學人身影原來都有各種跨越國境的不安或心機,在他筆下鮮活立體了起來;已成為景點的小印度和牛車水(中國城)如何呈現了星國CMIO種族模型看似多元實則緊抓界線與刻板印象的管理主義;宗綸筆記還恰好呈現了新加坡建國之父離開之後的小國如何努力適應亞太變局,特殊地緣政治位置而有馬習會般的歷史時刻發生,也唯有在此時此刻此地。
我和這位年輕作者的緣分起自一門課,他是班上數一數二優秀認真的學生。其後他到新加坡求學,一年來他的隨筆線上分享總讓人讀得意猶未盡,兼具語言學與地理學背景的他總能寫到最引人興趣的跨界移動,包括具體的物理界線,以及幽微閃現的社會心理界線──甚至,語言文化實踐總是直接間接模糊且移動了界線,而望眼島嶼四周,可能沒有比新加坡更合適體會移動之地了。如今隨筆成冊真很令人高興。鄭重推薦,但要釐清這不是一本窺看星國崛起的書,不是有關競爭力的教戰手冊,作者書寫新加坡也寫台灣,是能提醒在台灣的人們回看島嶼如何構成、城市如何應珍惜穿越帶來的複雜性,挑戰種種理所當然。
有機會透過留學成為城市生活中的「他者」,宗綸深刻又不失趣味的呈現了語言日常練習攪動的文化衝擊。當語言的混生比一碗囉喏(Rojak)還要複雜而美味,人們忙碌著在新式英語、英式英語、美式英語之間切換時的生活政治絕對不只是口音的「精進」,而是邊境的時時重新定義與網絡的重整。如何恰到好處的不準才是最精準的表意。在新加坡,英語的強勢主導,以及華語系中北方普通話意欲取代了南方語言的日常,所呈現不只是帝國殖民語言的持續作用,更是國族界線的統合假象失效。這本書涉及東南亞語言中豐富的跨界實踐,有機會讓島嶼上認識到「台語」不是台灣人獨享;來自不同地方的「印度人」往往只能以英語相會,流動路徑不同也寫出不同的階級跨越,當種族、階級、地方的污名揉寫為特定時刻的禁酒,印度人也不一定能大聲為「印度人」捍衛。
兩周前某夜我和幾位學界朋友坐在小印度某處騎樓下抬槓,禁酒時間馬上就要到了,老闆娘好心來提醒要及時加點,那一刻,只是身處小印度都覺得被深深的懲罰看低,明明是個那樣美好的夜晚。然而有時界線根本如影隨形,銘刻在你身上,吃什麼、如何說話,在在都意欲規訓你成為特定的樣貌。可我們在場幾位與會者,誰不知道在剛落成的國大亞洲研究中心,每層樓都可見來自印度移工朋友們辛勤勞動,或者從事清潔勞務,或繼續著未完成的室內工程裝修細節。如同宗綸告訴我們,星國境內至少三十萬名來自南亞的低技術移工,整個城市國家的大興土木如創造性破壞,沒有他們根本難以運轉,然而營建移工去哪兒容身過夜,在此都是空間政治的課題。沒有這些人的勞動參與城市,哪來研究機構中的高級跨界交流? 更簡單地說,沒有移動,就沒有新加坡這般港口城市的形成,然而我們卻持續的對移動充滿各種偏見,幻想著堅守純正疆域的可能。宗綸以中國同學所謂「無攻擊性」台灣腔調來寫下這本書,其實內勁充滿,正給移動寫下更包容的註腳,以及新篇章的可能。
離開當天,前往樟宜機場路上,司機聽著洪榮宏歌曲,問起才知是潮州人,不過他仍開心地和以閩南語交替華語和我聊天:「你國民黨還是民進黨的啊?」看我張口結舌,他又切入民生政治: 「诶,為什麼說要進口那個核能的東西啊? 我不明白啊? 我們在這邊看了都很生氣嗄…這樣不對嘛,我們不要說針對國家啦,是人對人嘛,自己種的東西你自己吃嘛,不要給人家吃...」
唉,其實沒那麼簡單。日本核能並非東北地方農夫或漁夫搞出來的東西,人民卻總是為國家承受最直接的責任。不過真讓我好奇的是,遠在南洋的他為什麼會生氣而非坐看好戲?
家來自潮州的司機大哥又談,「你們台灣可以發展得很好嗎,對不對?」我其實不確定這是個問題還是評語,「很可惜嗄,那個馬英九如果有李光耀一半就好了啊」,我一時語塞,他又熱切地談論起台灣政治狀況,說個不停。我聽著聽著感覺到一種特別的「鄰里情誼」,有些似乎關聯著這區域中的歷史流動,總藏著些假設性的設身處地同理心,似乎有關這一兩個世紀的東南亞海域浪潮翻湧,誰當年乘的那艘船如果掉了個方向,今天就你我對換的處境。這觸動了我前一夜在新加坡武吉巴督東坊洗頭的經驗,閒聊中,那位替我洗髮的女士笑笑說道: 「我是廈門人啊,以前年輕時在家鄉有個台灣男友,如果感情沒結束,我今天就嫁到台灣去啦」,在她對男友無限懷念中,我聽見的是移動的各種樣態和歷史偶然性,是當代保守國族主義再興無法妥善對待的足跡,是當前政策與理論仍需要突破再突破才能理解的流移。有此記憶猶新,我相信因宗綸跨境求學而有的這一冊,能提供些不一樣的思考起點。四小龍的發展型國家競爭應放在架上了,且隨著宗綸的研究參與移動,來重新理解新加坡的「成就」如何牽動著區域脈動、語言變化與文化活潑創造,畢竟「移動」在當代,時時刻刻在生活日常中蠢動。
現代地理眼看新加坡的豐富與多元
洪廣冀.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系助理教授
談起新加坡,我想不少讀者應該還記得前外交部長、前國安會秘書長、前總統府秘書長與前立委陳唐山的「鼻屎說」與「LP說」。至於這兩個說法的具體內容,各位讀者可自行google,我就不在此詳述──重點是,若我們將這樣的說法與台北市長柯文哲的「八年內超越新加坡」說相對照,顯然的,關於新加坡的「地理學想像」於過去十餘年間有了莫大的變化。不過,做為台灣地理學社群的一員,我想在此強調,與其說這樣的轉變是源自任何對新加坡深刻的認識,倒不如說是同一類地理學想像的延伸。這類想像大概是這樣子展開的:相較於亞洲其他國家,新加坡的國土小,社會相對單純,因此不論政治與社會秩序容易被調理地井井有條。儘管論者對於新加坡的「小」、「單純」與「井井有條」往往有著迥異的評價,任何對地理學稍有涉獵的讀者大概不難發現,這套地理學想像的源頭是粗糙的地理決定論。
之所以以陳唐山的「鼻屎說」與「LP說」開場,除了據此鋪陳一種多少年來瀰漫在台灣社會的地理學想像外,還有另一層含義:陳唐山是台灣大學地理系創設之際時的畢業生,而本書作者萬宗綸則是二○一五年同系的畢業生。在陳唐山的年代,所謂的地理學指的是區域地理,也就是先定出個區域後,鉅細彌遺地、包山包海地描繪該區域中的風土民情(不過,值得指出的,儘管陳唐山畢業自台大地理系,其所屬為地理系下的氣象組,也就是今日台大大氣系的前身。在台大地理系就學期間,到底陳唐山受到多少地理學的熏陶,還有待史家考證)。與之對照,宗綸於台大地理系學習、繼承、乃至於在《安娣,給我一份摻摻!》一書中成一家之言的地理學傳統則以截然不同的取向來處理「區域」此地理學的核心概念。簡單來說,當代的區域地理學主張,相較於傳統區域地理如填色遊戲般地的做法,地理學者應當檢視區域是如何在全球與在地間流竄、激盪與交融的種種力量中浮現:區域不是給定的,等待被社會或文化填滿的容器;區域不是決定性的,更不是限制人類活動與想像力的邊界。由此對照過去十餘年間以種種姿態出現在台灣之公共論述中的新加坡。新加坡的「小」,並不保證這個島國與城市國家的「單純」──遑論「井井有條」。
這樣看待新加坡的方式充分顯示在書名的「摻摻」一詞中。宗綸引述《聯合早報》的定義,指出「摻摻」的意思是 「什麼都要、什麼都有、不純粹、混合起來」。 「新加坡人其實很喜歡拿自己國家很小這件事來說笑」,宗綸進一步指出,「但在有限國土上,這個國家卻試圖蘊含最大的可能性,這是『摻摻』的精神,也是『驚輸』的性格。」我認為,這樣正視新加坡社會的「摻摻性」,而不是試圖在「摻摻」中區辨出種種純正元素──乃至於提煉出某種可移植的、可放諸四海皆準的「發展策略」或「願景」──成為本書最大的特色。換言之,如果各位期待能在《安娣,給我一份摻摻!》 中找到讓新加坡得以成為「進擊小國」的配方,或是作者獨家的名勝或美食列表,本書不會是各位最好的選擇。相反的,如果你對種種難以歸類的現象感到好奇,或者對目前輿論中對新加坡乃至於台灣等島國的歸類方式感到不耐,《安娣,給我一份摻摻!》會是各位最好的選擇。
新加坡的社會語言學
(Sociolinguistics in Singapore)
李星星/蕾貝卡.史妲(Rebecca Starr).新加坡國立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新加坡可以說是世界上研究起社會語言學--關於語言如何在社會中起作用的學問--最令人感到亢奮的地方之一。作為一座孕有豐富寰宇(cosmopolitanism)與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歷史的「全球城市」,這座小而人口密度之高的島嶼上有探索不完的課題。我在這邊列舉一些我與我的同事們最近幾年對於新加坡與其語言所積極追求的研究目標:
- 描述新加坡的方言,包括新加坡英語、新加坡華語、新加坡福建話等等,以及他們的社會語言變異與改變樣態。
新加坡從漢語方言主導的社會迅速轉移至英語與華語主導。此外,隨著英國殖民時代離得愈來愈遠,社會對於英式英語的傾向逐漸衰弱。我們正調查這些不同的社會變遷怎麼反映在新加坡英語和其他本地語言樣態的轉變之中。
- 紀錄並復甦新加坡的瀕危語言,包含峇峇馬來語(Baba Malay)與克里斯坦語(Kristang)
隨著新加坡種族概念隨著時間轉變,以及特定語言--譬如華語--接受政府制度性的支持,某些少數群體使用的語言已經出現可觀的衰退。兩個例子分別為峇峇馬來語--海峽華人(Straits Chinese)使用的克里奧語(creole language)--及克里斯坦語--葡裔歐亞人(Portuguese Eurasians)使用的克里奧語。年輕一代正尋求學習這些語言,某些人則企圖復甦這些瀕危語言。舉例來說,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一位大學生去年起自願教授克里斯坦語課程;現在他有超過一百名學生。在新加坡教幾乎完全滅絕的克里斯坦語是一個大工程,因為這需要在訪談僅存的母語使用者後,發想出原創的教學材料。儘管新加坡的歐亞人在幾個世代以來使用英語,他們正開始珍惜這樣的語言襲產做為他們獨特身分的象徵。
- 調查新式英語(Singlish)的歷史與本質
新式英語,或稱新加坡口語英語,是一個接受標準英語、峇峇馬來語、福建話、廣東話等等語言影響下誕生的接觸語言(contact language)。政府在歷史上一直不支持這樣的語言,因為他們擔憂不標準的英語將會摧毀「新加坡的國際品牌」。然而,許多新加坡一般人卻覺得新式英語代表了他們的國族身分(national identity),因為這個語言混合了許多能反映新加坡多元文化襲產(又指文化遺產)的語言。隨著時間過去,政府也漸漸開始認可新式英語在新加坡文化中的重要性。
- 調查新加坡演進中的語言規劃策略背後之意識形態基底與隱射
新加坡的語言政策總是反映這個國家的務實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價值。新加坡共有四個官方語言:英語、華語、泰米爾語和馬來語,最後一個也被授予國家語言的地位。然而,沒有維持四種語言的學校系統,新加坡選擇貫徹全英語的教育模式,外加雙語教育的政策,要求學生學習符合他們種族的「母語」(mother tongue)。這些政策有許多很重要的隱射,包含在推廣華語的影響之下,新加坡正逐漸對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展開大門。
- 調查在新加坡政府的語言規劃與語言意識形態之下,家庭如何實行家庭語言政策(family language policies)。
雖然有大約74%的新加坡人是華人,愈來愈多的新加坡家長在家中選擇與孩子說英語,英語成為現在最普遍的家庭語言。在孩子的教育優先之下,且根據家長們認為何種語言在經濟上及文化上最為重要,新加坡的家庭形成他們在家中的語言使用策略。
- 調查新加坡新移民如何整合進本地言說社群(local speech community)
自二十一世紀始,新加坡見證了大幅度成長的外國移工,他們橫跨了社會經濟的光譜,從來自西方的高階財金人才,到來自中國的低階人力,譬如公車駕駛。事實上,根據某些估計,現在新加坡的外國人比本地人還多。新加坡人知道外國移工的語言使用樣態些什麼?外國移工又知道新加坡人的語言使用些什麼呢?外國移工的孩子採用新式英語嗎?這是一個我目前個人正在調查的研究問題。
- 從社會語言學的觀點調查新加坡人如何認知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新加坡以自身的世界化和朝外的眼界感到自傲。以媒體消費來說,新加坡人偏好觀看來自其他地方的媒體,包含美國、英國、韓國與台灣。新加坡人也是最頻繁的旅行者,幾乎所有的新加坡人每年都出國。所以,新加坡人知道些世界上其他語言、方言與口音些什麼呢?新加坡人會覺得自己的本地方言比起英國或中國使用的較為次等嗎?或是他們覺得自己使用的同樣有效呢?
- 調查新加坡的語言情境如何連結到後殖民社會和全球化世界中更寬廣的趨勢
作為一個高度發展與全球化的城市,英語被愈來愈多人作為第一語言來使用,新加坡提供一種窗口來窺探世界其他角落可能的未來。新加坡也是廣大後殖民社會中的一部分,這些社會之間在如何處理語言相關議題之上享有某種共通性和差異性。或許新加坡所遭遇的成功與挑戰能供其他在未來會面臨相似情形的國家寶貴的一課。
宗綸是我「社會語音學」(sociophonetics)課程的學生,在那門課裡我們探索語音如何與社會作用在一塊,衍生出諸如族群身分、社會階級、選舉造勢和性別展演等各種面向的議題,這本書的相關章節會是一個好的開始,供華語世界的社會大眾有機會更理解新加坡的語言與社會。
作者序
畫一幅摻摻
「摻摻」是新加坡華語的一個詞,《聯合早報》認為這個詞的概念是「什麼都要、什麼都有、不純粹、混合起來」。
新加坡政府從一九八○年代以來,訴求發展出一種新加坡的國族身分(national identity),他們雖然要西方的現代性,卻也要亞洲的文化元素。儘管口號喊的是「一個新加坡」和「一種新加坡人」,但仔細端詳,裡頭卻是「摻摻」。
新加坡是異質的,同一個新加坡,對於這座島上的所有人感受都不同,正因為這座城市自古以來的流動特性,迎接了各式各樣的人們來到此處,什麼東西最能代表新加坡?是海南雞飯、新式英語、還是《小孩不笨》?是印度煎餅、周末擠滿移工的小印度、還是全世界唯一將泰米爾語作為官方語言的憲法?是市井馬來語、甘榜炒飯、還是馬來語國歌?
這座島嶼,既被稱作星國、又被稱作獅城,主權國家與全球城市似乎是兩個矛盾的大方向,要怎麼在維繫國族身分的同時,又接受來自全世界的人口與資本流動?新加坡政府在當中試圖做到的調和,難道都沒有疏漏嗎?
這是一個面積僅七一九‧一平方公里的國家,約二‧六個台北市大,但香港又是他的一‧五倍大。若講城市,北京、曼谷、上海都比獅城來得大,首爾、東京也沒有小過新加坡多少。
新加坡人其實很喜歡拿自己國家很小這件事來說笑,但在有限的國土上,這個國家卻試圖蘊含最大的可能性,這是「摻摻」的精神,也是「驚輸」的性格。
這本書中之所以少用「南洋」一詞,是因為希望能從我在這座島嶼經歷到的事物出發,像是「南洋」、「中南半島」這樣的語彙,都曾被本地朋友指為過於中國或北方中心,儘管他們可能是老一輩新加坡華人慣用的詞彙,但既然我接觸的多為年輕一輩已經無法再以「華僑」稱之的新加坡人,我將暫時拋開這樣的語言。基於這個緣故,此書也不會對於新加坡政治有過多著墨,除非是在獅城的日子中,跟我親身經歷的事情相關,抑或曾聽過街頭巷議討論過、朋友們跟我提及過。
感謝我的家人,讓我得以有機會透過我在新加坡待的三百多個日子,貼身地描繪這個台灣人好似熟悉卻又不那麼理解的國家,這本書希望以我的第一人稱視角敘述新加坡的複雜面貌,基於我所見到的人事物,肉身地書寫出獅城的摻摻性格,不帶保留。雖然此書並非學術書籍,但仍然基於倫理考量,此書中的人名皆為假名。我將這本書,獻給我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人們,猶如我第二個家的新加坡以及我摯愛的台灣。
內文節錄
獅城Online
「先生不好意思,我需要你的座位打直。」(Excuse me sir, I need you seat to be right up.)帶著新加坡腔的空少叫醒了半睡半醒的我和母親,飛機即將降落樟宜機場,長達四個半小時的飛行其實挺折磨人;根據機長廣播,當地時間與台北沒有時差,現在是早上五點。
從飛機的窗戶望外看,一片綠油油而整齊劃一的地表映入眼簾,我知道已經抵達新加坡上空。
這座城市的另外一個名稱叫做「獅城」(Lion City),根據《馬來紀年》(Sejarah Melayu)的紀載,在公元十一到十三世紀中間,室利佛逝王國的王子從首都巨港出發,因為船難而來到了新加坡,他在島上看見了獅子,於是命名此地為Singapura(梵文:獅子)。不過當然,新加坡那時候不可能有獅子,這顯然只是傳說。
位在新加坡灣區的那一尊魚尾獅(merlion)像,是這座城市名為獅城的象徵,現在是觀光客必遊景點,那一帶也是新加坡最乾淨且現代化的區域。李光耀帶領的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簡稱PAP)政府從一九六三年開始,就計畫要發展觀光業,那個年代是觀光業即將起飛的年代,波音707與747客機接連出現,儘管那時候每年到訪新加坡的旅客還不到一萬人,不過在一九六四年,新加坡觀光部門便希望要有一個標誌(LOGO)來推銷新加坡。
一九六六年,被迫獨立的隔年,新加坡政府採用了當地水族館的英國人館長設計的魚尾獅圖像,設計構想就來自這則《馬來紀年》中紀載的故事,而魚的身體,則是象徵著這裡身為漁村的過去,也代表這座城市親水、面向寬廣大海的特性,說明新加坡是「本土與國際的結合」。
一九七二年,魚尾獅才正式變成雕像,設立在新加坡河口。「魚尾獅文學」也成為新加坡的一大特色,魚尾獅成為新加坡認同的一個具體物質,其中以Edwin Thumboo的英文詩作〈Ulysses by the Merlion〉(魚尾獅旁的尤利西斯)最為著名,也是官方版本的魚尾獅文學,裡面寫道 “They hold the bright, beautiful. Good ancestral dreams. Within new visions. So shining, urgent. Full of what is new.”(他們掌握著光明與美麗。美好的古老夢想,夾帶在新的視野之中,如此閃耀、急迫,充滿著新的事物。)
二○○二年,政府更進一步推動魚尾獅公園,這座公園就位處在填海造地的土地上,魚尾獅像也被搬至此地。
而在打造聖淘沙為遊樂島時,也打造了一座巨大的魚尾獅像,這個魚尾獅像的尺度必須夠大、夠磅礡,由澳洲藝術家設計,達三十七公尺之高。現在,整個新加坡一共有至少八隻魚尾獅。
魚尾獅,不只是一個白色的雕像而已,他是新加坡的代表,是新加坡野心的代言者。這座獅頭魚身的雕像,面對新加坡河的倒影,也被人說是希臘神話的水仙花──是獅城自戀的展現。其周遭的大榴槤和金沙酒店的大帆船,也都是魚尾獅公園營造出的全球化環境,所吸引進來的外資,同樣用了新加坡的符號(榴槤、帆船)。看過電視劇《我可能不會愛你》的觀眾,對於新加坡有了那樣的印象。
就是這樣的自信與自戀,這座島嶼吸引了我。(未完)
武吉士──變裝的城區
出了樟宜機場,媽媽與我搭上第一班的地鐵前往青年旅館的所在地──武吉士(Bugis),我們在這裡預訂了四個晚上,也就是說我必須在這些日子裡租到房子。這個區域的正式名稱是「甘榜格南」(kampong glam)。
二○一五年二月時,我們一家便來到新加坡「考察」,當時對武吉士的印象是一個與台灣夜市神似的長巷,也就是「武吉士街」,裡頭有一家叫做「我愛台妹」的台灣飲食店,令人印象深刻。這次的旅館位在愛麗華街(Aliwal Street),距離蘇丹回教堂非常近,觀光客喜愛的阿拉伯街(Arab Street)和哈芝巷(Haji Lane)都在附近。若單純就現在來看,武吉士周遭是政府規劃的馬來文化區,並設有馬來傳統文化館,講述新加坡三大族群之一馬來人[1]的歷史。
如同其它東南亞城市近年來興起的壁畫風潮,哈芝巷是新加坡數一數二知名的文化創意巷弄,鮮艷而大膽的色彩潑灑在壁面上,畫出極具想像風格的人頭肖像。七彩色盤後面看不見的是此區多文化的歷史,早在英國人來到新加坡之前,這裡便是馬來貴族家庭所居之地,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阿拉伯人、印度人、華人也紛紛到達此地。「哈芝」本身指的就是從麥加朝聖歸來的人,指向武吉士一區濃厚的伊斯蘭色彩。
儘管只有兩百公尺長,哈芝巷在近年來名聲響亮還有其激進的空間意義,在這座島嶼有如此反抗色彩的空間,並不多見。前些年頭,新加坡的都市更新當局(URA)有意移除哈芝巷的壁畫,原因是鮮豔的色彩與周遭色調相對柔和的店屋不太協調,聽聞此事,哈芝巷的年輕藝術家在網路上連署請願,抗議URA是踐踏本地藝術家的心血,最後使得URA改變想法,認為壁畫讓此區活潑了起來,不失為一件好事。
或許是陪我度過了留學生活的頭幾天,武吉士也成了我在新加坡這座城市中,最喜歡的一塊區域。之所以稱作「武吉士」,是來自於早期沿梧槽河(Rochore River)而居的武吉士人(Orang Bugis)所聚居形成的「武吉士甘榜」(Bugis Kampong)[2]。
相對而言,武吉士還算是相對有其鮮明特色與歷史的空間,並未成為密集的高樓大廈,儘管多了幾棟購物中心。
1950至19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武吉士街逐漸成為一個「世界級」的旅遊景點,當時吸引的不只是當地人,還有那些英國政府的軍人以及越戰期間休假來旅遊的美國大兵。許多小販到此兜售食物和貨品,形成獨特的市場文化。不過最知名的──是此處由男扮女的「變裝皇后」以及紅燈區。
彼時特別受歡迎的變裝皇后表演會在公廁的天花板上進行,揉合著酒精,變裝者光著屁股並且拿著點燃火焰的紙張比劃著,將表演推到最高潮。另外一個焦點是所謂「女皇中的女皇」(the Queen of Queens),要從這些變裝者中進行選拔,選出誰是最美麗的變裝皇后。
這些宛如嘉年華的活動在太陽下山後才會熱鬧起來,比如變裝遊行要到晚上十一點以後,要知道,新加坡的日落是相當晚的,大約落在晚上七點半左右才天黑。當時武吉士美食中有道名菜是「牛鞭麵」,據說有壯陽藥的功效,配合著作為紅燈區的此區而紅了起來。那時還是英國殖民時代,直接控制武吉士的是黑幫,街販、變裝者、美軍、英軍、皮條客和黑幫份子共同構成武吉士的夜間景觀。
1995年楊凡導演的電影《妖街皇后》(Bugis Street)就是在重現這樣的歷史畫面,故事講述由越南籍演員姚志麗(Lê Thị Hiệp)詮釋的17歲女孩蓮本如何離開她在馬六甲(Melaka)的女僕生活,來到新加坡武吉士街的小酒店工作討生活,其中就演到她目睹一個美軍士兵發現到服務他的「華人女孩」竟然是個男人後,生氣又失望地走出屋子。(未完)
說一口「新加坡語」
「你們都是怎麼知道要跟對方說什麼語言的呀?」在入住的時候,我順口問了青年旅館的櫃台人員,是個華人女性,因為起初我猶豫不決到底該開口說什麼語言。
或許是因為穿著寫著TOKYO(東京)的衣服,她起初也是跟我講英語,直到發現我的台灣護照,才忽然換成華語。
她笑了笑說:「華人都會說華語,英語是我們的第一語言,華語是第二語言,但只是有的人說得很差就是了。」
但這樣的回答,似乎無法滿足我初入新加坡的文化衝擊。在樟宜機場的地鐵站買EZ-link card(他們的悠遊卡)時,前面一位華人安娣[3]用英語加值,所以我便認為我也應該說英語,但殊不知,地鐵站服務中心裡的安可在跟裡面另外一位安娣說福建話。
這有時令我無所適從,由於新加坡承襲自複雜的歷史背景以及族群多樣性,語言的發展非常異質且蓬勃。新加坡憲法載明,新加坡共和國的國家語言為馬來語,官方語言則為英語(English)、華語(Mandarin)、馬來語(Malay)及泰米爾語(Tamil),分別代表中性語言與三個族群語言。
然而,四種語言並無法說明白新加坡的語言使用。新加坡的華人最早來自中國南方福建、廣東一帶,老一輩新加坡華人能說福建話[4]、廣東話或是潮州話,其中由於福建人為最大宗族群,根據1957年的統計資料,福建人佔了華人族群中的40.6%,達全島人口三成,華人大多能說上福建話,不僅如此,有些老一輩的馬來人或印度人也能說上一些福建話。
「當你去小販中心點餐時,你說英語,你會獲得比較少的量;你說華語,你會獲得正常量;你說福建話,安可安娣會很高興,給你加飯、加菜。」新加坡本地同學修哥這樣叮囑我,修哥平時不說華語的,是發現了我去過越南後才開始跟我說話,他的榮譽學士論文寫的是越南的語言地景。
修哥一跟我說話就是華語,算是開金口了──我在國大認識的本地人,平日使用的全部都是英語,華語只跟親密的家人、或是真的很要好的朋友才說。
新加坡華語聽起來與中國標準普通話或是台灣標準國語有很大的不同,甚至與馬來西亞華語也存在著差異,儘管需要很仔細聽才聽得出不同,馬來西亞人總認為新加坡人的華語說得很差。
不過詞彙上倒是很容易學會。比如說「五十趴」他們說「五十巴仙」,台灣人取了英語percent的第一個音節而已,他們則是兩個音節都音譯過去;「七點十五分」他們說「七點三個字」,指的是長針指到三,也就是十五分的意思。(未完)
嚴刑峻法
在新加坡的幾百個日子裡頭,有個名為「算命先生說我會在新加坡發光發熱」的臉書粉絲專頁總能讓我捧腹大笑,經營專頁的是個在新加坡臉書公司上班的台灣女生。有一次,她拍了一張她從台灣帶了大批口香糖進獅城的照片,讓網友們感到相當震驚──「新加坡不是不能吃口香糖嗎?」
根據李光耀的回憶錄,當他還是總理時他發現口香糖造成非常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有人會用嚼過的口香糖去黏住信箱口、鑰匙孔,甚至是電梯按鈕,那時候是1980年代,新加坡正大量興建高層組屋,口香糖這種東西的特性,讓原本象徵新加坡走向現代化與完美國家的工程,變得骯髒不堪。甚至在地下鐵系統啟用時,也曾發生過零星幾次有人將口香糖黏在車廂門的感應處,造成地鐵公司需要支付高昂的修復成本。
1992年1月,時任總理吳作棟遂而公布禁令──全國禁止販售口香糖,也不得進出口口香糖。如果違法販售口香糖,根據《食品販售法》(SALE OF FOOD ACT)第283章第56-1節,得處以2000元新幣以下的罰款,相當於4萬8千元台幣;而若違法進出口,則可能被判2或3年以下的牢獄,或是罰款10萬(240萬台幣)或20萬(480萬台幣)以下的罰款,視詳細情況違反哪條細項而定。
1999年美國與新加坡展開貿易談判,直至2003年的最後階段,兩項仍待解決的議題就是伊拉克戰爭與口香糖禁令。最終,新加坡允許開放醫療用途的口香糖進口,在符合醫藥法規的規範下,由牙醫師或藥師提供給病人。
換言之,新加坡從來沒有禁止過在其境內嚼食口香糖。而通常小量攜進新加坡的個人用途口香糖,也不會被海關禁止攜帶。
李光耀在2000年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採訪時,曾不諱言地告訴記者,新加坡就是一個保姆國度(nanny state),政府管制一切生活周遭的大小事,從幾歲結婚到買賣口香糖都要管,「但是結果是比起三十年以前我們活得更好、活在一個更宜居的地方。」
走在新加坡的觀光市集裡頭,一些紀念品就直接以 “Singapore is a fine city” 為主題,挪用了 “fine” 的雙關,既表示良好、也表示開罰。新加坡的好,是建立在政府全面性的規範之下。
如果仔細查看新加坡路邊架設的禁止標誌,有時還真會嚇一跳。譬如地鐵站內不准抽菸、不准飲食、不准攜帶榴槤、不准溜滑板、不准溜冰、不准玩滑板車……琳瑯滿目的「不准」,不禁令人好奇到底執法狀況如何,抑或是說說而已?
若你離開新加坡灣區,走到中部老城區或是更西部的地區,便會發現一樣有老人家隨地吐痰、有人亂丟菸蒂,或是路上隨處可見垃圾。其實新加坡的執法並非那麼嚴格,而大多是仰賴「檢舉」,新加坡人說:「法律寫那麼多只是要告訴大家做什麼事都要尊重彼此、想到別人。」
根據教育學者左林(Levan Lim)的觀察[i],新加坡人習慣「被動」,在新加坡的社會中,人們需習慣遵循明確的規則跟界線。因此,由政府來訂定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變得相當重要。當然,這也許是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
換言之,這是一個建立在互相尊重之上的社會,如果沒有人特意去檢舉你,也不會有台灣民間流傳的──「一嚼口香糖就被抓去鞭刑」。更何況本來就可以嚼口香糖。(未完)
雙城記:對望香港
「我們在香港真的是待得快要受不了了。」在香港念書的台灣朋友特地大老遠飛到新加坡來拜訪我。
「我才是羨慕你們在香港的生活看起來比新加坡有趣多了。」我回答他們。
那幾天,我帶他們走訪了小印度、武吉士、牛車水等等旅遊區,吃了著名的印度早午餐Zam Zam,也去了聖淘沙(但沒有去環球影城),他們對於新加坡的印象很好,尤其是充滿美食的小販中心。聽他們這麼一說,倒也開始懷疑起來,到底新加坡和香港比起來,哪個城市我更喜歡?
這個問題不是只是我個人的問題。如同遠走他鄉的學者喬治一樣,許多學者在新加坡到一個階段後,就改而到香港的大專院校去展開另外一段學術生涯,其中原因不乏香港相對開放的政治與言論環境。
新加坡是香港第八大出口市場,也是東南亞國協中,香港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反過來說,新加坡是香港第四大的進口國。儘管兩座城市看起來在亞洲存在競爭關係,但其實彼此的貿易連帶是很緊密的。
新加坡華人社群其實對於香港有著一種情感。我在國大的第二學期選修了中文系的課程「應用中文語言學」,授課教師是李光耀的華語老師周清海。他總是在課程中回憶起他在香港待過的那兩年,說著共產黨對於香港的做法實在操之過急。
2016年2月8日晚上,香港警察在旺角取締無牌小販,雙方發生衝突,隨後本土派組織加入抵抗,演變成一場嚴重的警民衝突,甚至有警察對天鳴槍。隔日香港特首梁振英將這場衝突定為「暴亂」。外國媒體則稱之為「魚蛋革命」。
香港旺角騷亂的隔一週,在應用中文語言學課上,周清海老師語重心長地說著:「語言是動感情的」,倘若不是北京政府的壓迫,香港人在主權轉移前,是非常渴望學習普通話的,而演變至今,香港人對於中國大陸的不滿與反彈,讓香港人失去了精熟兩文三語(普通話、廣東話、英語)的機會。他說,最有條件與前景的,本來會是香港人,不是新加坡。
這是他對旺角騷亂的發想,周清海老師說:「發生這場衝突,我一點也不意外。」台下坐著的大部分是中國留學生,那天課上的氣氛確是怪異。
在早些年,許多人甚至會將香港與新加坡間的關係稱作是「雙城記」,這個詞是由李光耀發揚光大的,意指這兩座城市有非常相似的英國殖民歷史以及種族組成,兩座城市的發達歷程也相當具有可比性。
然而,在《中英聯合聲明》後,當香港的主權確定要轉移給中國之際,港人曾經出現過前所未有的恐慌,因為他們發現他們的未來即將交給一個獨裁政府。那時,新加坡政府曾開放一段期間接受香港居民申請以永有居民身分進入新加坡。
我與來訪的朋友在武吉士的一家手工藝品店遇到港人老闆娘,她讓我們猜她來自哪裡?「馬來西亞?中國?台灣?」都沒猜中。她告訴我們她來自香港。於是與我同行的朋友便與她用幾句廣東話寒暄了一會兒,她的欣喜之情溢於言表。她告訴我們,她就是當年新加坡接收香港移民時申請過來的,她的老公仍在香港,當時隻身帶著兩個孩子來到新加坡扎根,她說她也曾經試圖選擇英國,只不過種族歧視太過明顯,讓她適應不良。新加坡多元的種族環境,讓她覺得很舒服。
阿姨說,「香港跟中國關係真的很緊張,她也不會想回去了。」(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