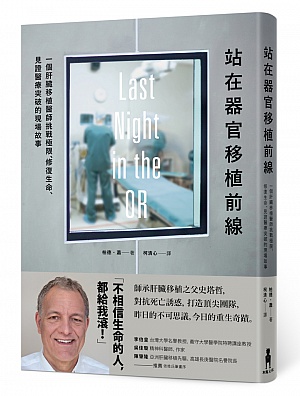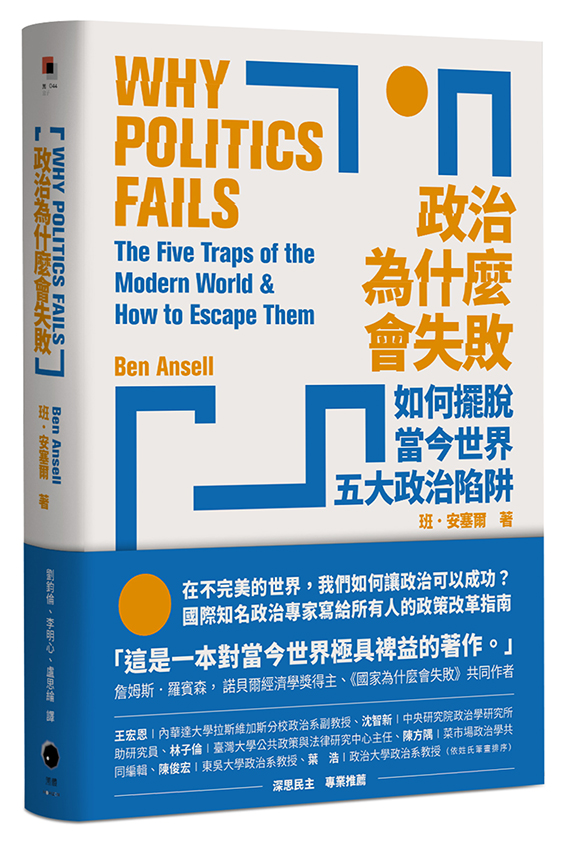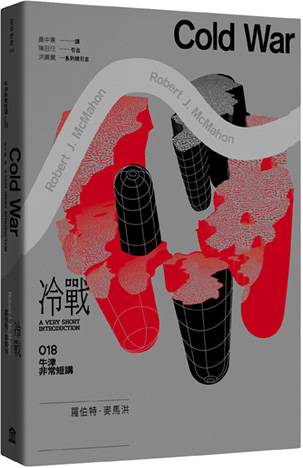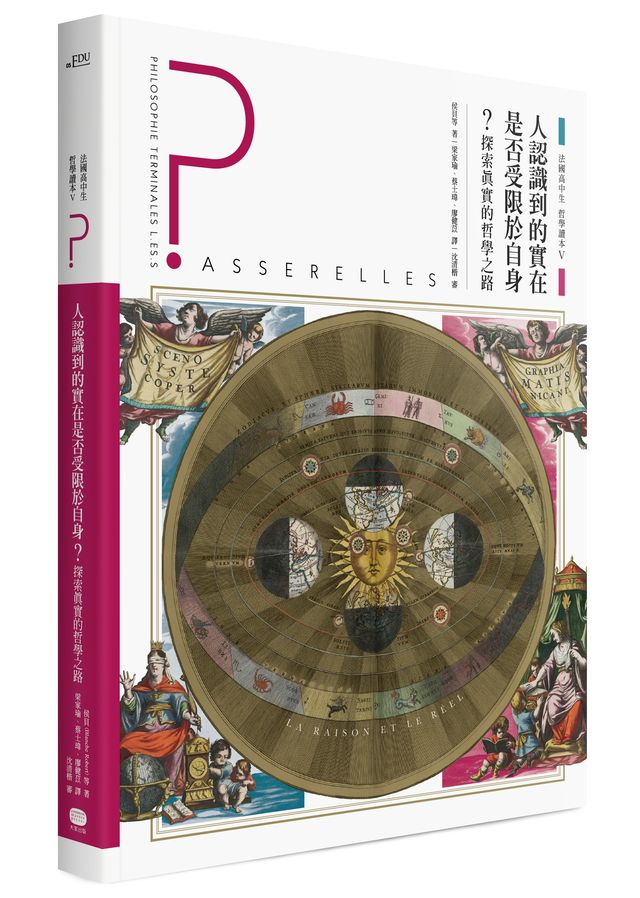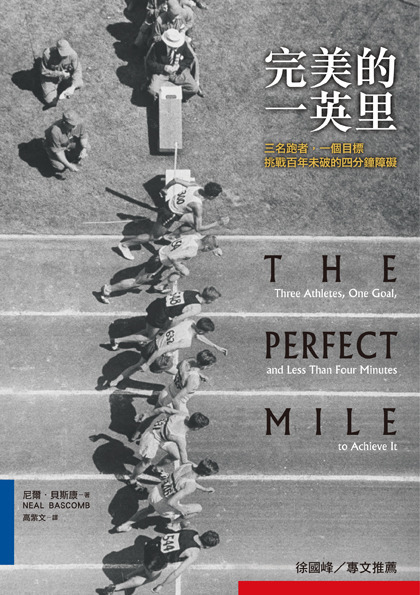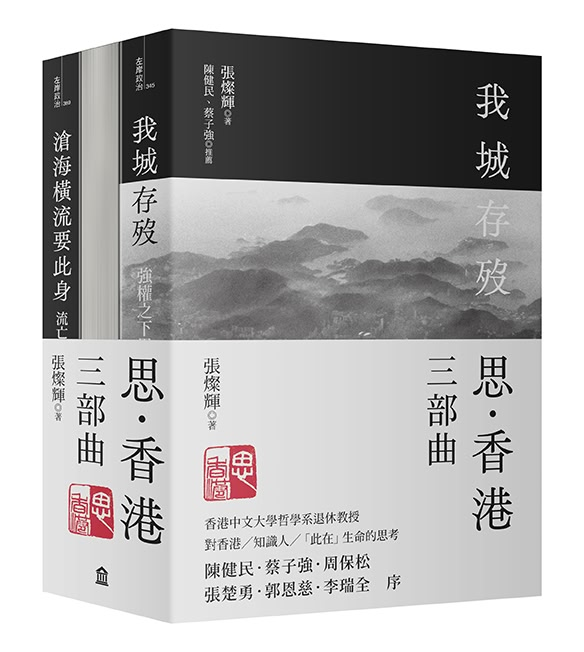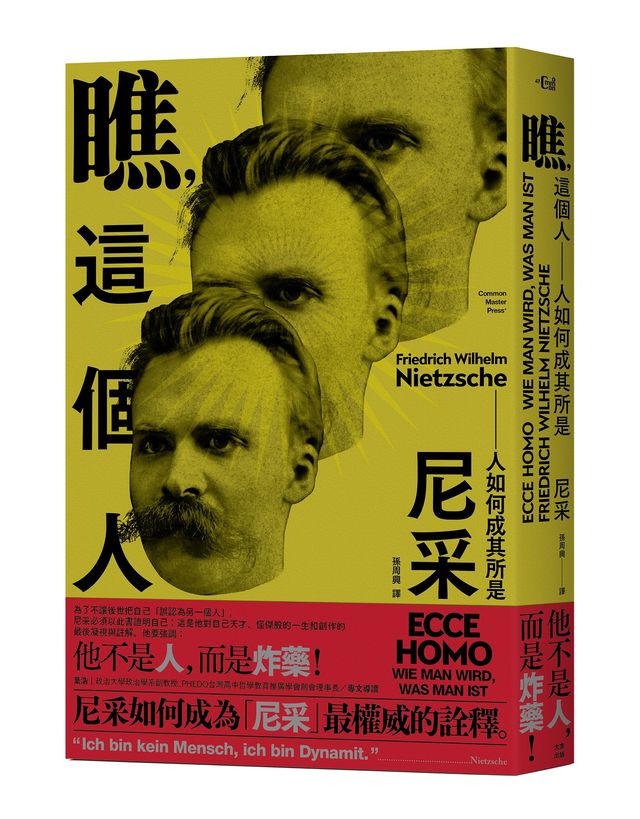「不相信生命的人,都給我滾!」
師承肝臟移植之父史塔哲,
對抗死亡誘惑,打造頂尖團隊,
昨日的不可思議,今日的重生奇蹟。
喜歡葛文德的《凝視死亡》與亨利.馬許的《但求無傷》讀者,熱愛《實習醫生》劇力萬鈞場面的觀眾,千萬不能錯過。器官移植權威柏德‧蕭,在器官移植戰場開疆闢土的外科前鋒,於嚴苛的醫療前線救死扶傷。手術室就是戰場,沒有溫良恭儉讓。
器官移植是二十世紀重大外科突破,一九八○年代的匹茲堡更是肝臟移植重鎮。在醫界同業對器官移植尚有疑慮之際,柏德‧蕭醫師從猶他州到匹茲堡,向全球肝臟移植先驅史塔哲(Thomas Starzl)學習,共同打造頂尖的器官移植團隊。
他們搭直昇機去取器捐者的肝臟,與其他移植團隊競爭時間,分秒必爭摘取可用臟器。手術室則如戰場,有的腹腔乾淨齊整如解剖學教科書,有的則交錯夾纏如遍佈地雷。他們還得摸索移植後的排斥反應,與手術台上的大量出血奮戰。數十小時的燒灼、縫合、填塞、等待,與死亡正面對決,身心瀕臨極限,仍得抵抗棄守的誘惑。一切只為了鬆開夾鉗的那一刻,看著血液注滿肝臟,讓更多患者重獲新生。
從連線頭都剪不好的菜鳥,到成為頂尖團隊一員,柏德‧蕭醫師回顧過往的前線的生活一如飛向星星的火箭,是多數人無法企及的巔峰,更是無法體會的高壓與焦慮。
然而,即使多數患者獲救,卻仍有等不及器官的死者,提醒我們,好好活著有多困難。
柏德‧蕭(Bud Shaw)
生於1950年,為家中長子,成長於俄亥俄州南部鄉間,父親為外科醫師。他於1972年獲得凱尼恩學院的化學學士,1976年獲凱斯西儲大學醫學學位。1981年,自猶他大學醫院完成住院醫師訓練,接著在匹茲堡師事於肝臟移植之父:史塔哲醫師。他於35歲時已成為享譽國際的肝臟移植醫師。他在1985年離開匹茲堡,於內布拉斯加創立移植中心,旋即成為世界上最具名望的器官移植中心之一。他發表三百篇期刊論文,五十篇專書論文,創辦聲譽卓著的期刊《肝臟移植》(Liver Transplantation)。2009年,他自手術室與主管職位退休,目前致力於醫學教育與臨床診療的寫作與教育。他也是三個孩子的父親,目前與小說家妻子蘿貝卡.羅特(Rebecca Rotert)住在內布拉斯加的北奧馬哈。
柯清心
台中人,美國堪薩斯大學戲劇研究所碩士,現任專職翻譯。著有童書《小蠟燭找光》;譯有《我這終將棄用的身體——解剖自我、探索性別、追尋家族記憶的書寫》、《當我們撞上冰山——罹癌家屬的陪病手記》、《白虎之咒》系列、《擁有未來記憶的女孩》、《吸血鬼獵人林肯》、《一刀未剪狂想曲》等數十部作品。
【推薦序】
1.傑出移植外科醫師的省思
李伯皇(台灣大學名譽教授、義守大學醫學院特聘講座教授)
有一天木馬文化來電,希望我能為其新書寫序,作者是柏德‧蕭(Bud Shaw) 教授。他在一九八一年到匹茲堡大學器官移植部,跟隨史塔哲醫師(Thomas E. Starzl)當肝臟移植研究員,一九八五年回內布拉斯加大學設立肝臟移植中心。我在一九八六年到匹茲堡,因此無緣深入認識,只在國際會議和他有數面之緣,但早知他的瀟灑和手術技術,因此我就爽快答應寫序,目的是想進一步瞭解他的人生歷程。
蕭教授在這本書中,以一位充滿自信的傑出移植外科醫師自述其生平歷程,相當生活化,也相當平凡,看不出事業成功的豐功偉績。但在生活化的自述中,卻充滿對移植專業判斷與抉擇的省思。
蕭教授在猶他大學接受外科住院醫師訓練,他的老闆穆迪醫師(Frank Moody)認為要找頂尖人物學習,較有機會成為一位傑出的醫師,所以強力推薦他到匹茲堡跟隨史塔哲醫師學習。書中他花了約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談到在匹茲堡的研修歷程,他也特別感謝岩月舜三郎(Shun Iwatsuki)的協助。所謂嚴師出高徒,他在這一期間的描述相當傳神,也讓我回憶當時在匹茲堡進修時戰戰兢兢的生活,深感心有戚戚焉。
史塔哲醫師是一位工作狂, 在手術台上極其嚴厲,每個步驟皆有固定的操作流程(SOP),手術室彷彿一個工廠。史塔哲後來在描述對蕭教授的評價時,從初見面時認為道不同不相為謀,到後來的讚不絕口,非池中之物。蕭教授是一位相當有主見的醫師,也有自己的堅持,因此後來他選擇離開匹茲堡到內布拉斯加大學建立了自己的移植王國。史塔哲是一位極為積極的醫師,他認為當時匹茲堡大學的肝臟移植一片看好,正值開天闢地的偉大時期,正如已升火待發的登月火箭,必須趁此時多開移植手術,蕭教授卻有自己的看法,認為應持盈保泰,慎選病人,關注病人的預後,這種態度應該與他退休後,轉而專注病人的照護有關。
蕭教授在書中也敘述從事複雜而危險的醫療工作,幾乎夜以繼日投入工作,充分反應當時手術房的場景,令人會心一笑。但也因此忽略了家庭成員關係的經營,雖然事業有傑出成就,但家庭生活卻出現缺憾。蕭教授在書中敘述了他的感受,也看出一位成功的移植外科醫師心中的落寞。
這本書文筆相當流暢易讀,應該是第四位有關從事器官移植醫師的中譯本,讀者可由一位事業有成的移植醫師身上看到一些啟示,拜讀本書之餘個人亦獲益良多,故樂於為之序,與大家分享。
2.敘事醫學典範
吳佳璇(精神科醫師、作家)
《站在器官移植前線》,是美國肝臟移植外科醫師柏德‧蕭(Bud Shaw)六十五歲(二○一五年)時出版的回憶錄。
已經封刀的蕭醫師,打開收納在大腦中,一個個包裹著強烈情緒、甚至血淋淋教訓的記憶盒子,逐一轉換文字。行醫三十年,若沒有這種快速收拾、打包情緒衝擊的能力,是無法追隨任職於匹茲堡大學的肝臟移植先驅史塔哲醫師(Thomas E. Starzl),夜以繼日為命在旦夕的病患,殺出一條生路;更不可能在三十五歲盛年毅然另起爐灶,到當時一片荒蕪的內布拉斯加州,打造另一個移植王國。
然而,「出來混,總是要還」,從本書並未緊貼時間軸的敘事裡,蕭醫師不只一次提及自己罹患淋巴癌,和長期身處高壓工作環境脫不了干係。且抗癌成功不久,恐慌症來襲,讓他開始懷疑,「所謂控制,是否只是一種為了讓自己活下去,而自我創造出來的幻覺」,並領悟到「我總是想像,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但內心深處的真實想法是,自己並不能控制任何事情」……
於是,蕭醫師放下手術刀,提筆致力於非虛構創作(creative nonfiction),讓醫學院學生,以至於千千萬萬讀者,宛若走進通宵達旦生死一瞬間的移植手術室,親歷故事人物的喜怒哀樂。
自從發表於《非虛構創作》雜誌(Creative Nonfiction Magazine)的作品,〈我與艾倫‧哈奇森共處那一夜〉(My Night With Ellen Hutchinson)獲獎,蕭醫師甦醒的文學魂,在小說家妻子蘿貝卡(Rebecca Robert)砥礪下,佳作迭迭。《站在器官移植前線》面世,又是一個里程碑。
不同於編年紀事的尋常回憶錄——其恩師史塔哲醫師精彩的回憶錄《拼圖人》(The Puzzle People)正是一例,蕭醫師以類似精神分析的「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手法編排本書。因此,講完救不回從煉油台上跌落摔破肝臟工人的故事,蕭醫師接著講起十四歲那年夏天,同樣從事外科的父親,幫他搶救遭狗兒偷襲的瀕死鴨群的往事,以突如其來且巨大的無力感,貫穿並連結前後篇章。蕭醫師打開「裝箱」的記憶,經由說故事進行敘事治療的「生命會員重組」(re-membering),從而疏通生命歷程的種種糾結。
相對於近年大興其道,力求「客觀」的實證醫學(evidence based medicine),蕭醫師的故事則是不折不扣的敘事醫學(narrative medicine)。也就是說,這些建構於蕭醫師與患者們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下的敘事,可以作為我們瞭解上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的美國移植醫學發展,以及醫師與病人處境的鑰匙。
不過,強調多元、相對和主體性的敘事典範,向來沒有「標準」的閱讀或解析方法。親愛的讀者們,還是請您速速進入正文,親臨蕭醫師的手術室最後一夜吧。
3. 起手無回的一線生機
陳肇隆(亞洲肝臟移植開創者、高雄長庚醫院名譽院長)
全球肝臟移植開創者史塔哲(Starzl E. Starzl)教授,一九六三年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進行人體首例肝臟移植手術,一九六七年完成存活超過一年的成功首例,一九八一年從丹佛東移到匹茲堡,柏德(Bud)醫師是史塔哲教授在匹茲堡大學早期最賞識、最信任、最倚重的入室弟子。
一九八三年初,我加入匹茲堡團隊和柏德一起師事史塔哲教授。當時肝臟移植還是一項龐大、複雜的手術,一個較困難手術往往要花費二、三十個小時,因為病人都是傳統內外科方法不能有效治療的嚴重肝病,手術過程必須把整個壞掉的肝臟切除,再植入新肝,因此是一項起手無回、不成功便成仁的手術,是帶領著病人在生死間搏鬥的手術。不像換腎,植入的腎臟沒有發揮功能,還可以讓病人再回去洗腎,因此外科醫師會承受比較大的壓力。換肝手術最大的困難是很容易大量出血,因為肝臟是一個充滿血管叢的器官,有綿密的肝動脈、門靜脈、肝靜脈和膽管,是一個非常容易出血的器官;而人體的凝血因子大多在肝臟合成,壞到需要換掉的病肝,通常不能合成足夠的凝血因子;而肝硬化引起門靜脈高壓,造成脾臟腫大,也會破壞血小板,同時在肝臟周圍形成許多側枝循環,這些都是不正常、薄壁的血管,一破裂就造成大量出血。為了避免外科醫師在手術中被噴得滿身是血,當年柏德還設計了特殊的手術穿著,包括從胸腹遮蓋到腳的防水圍兜、高過膝蓋的長筒下水鞋等。
任何領域在最困難、最艱苦的時候,往往是切入這個領域最好的時機,一九八三年期的研究員。我和卡洛斯‧馬格力特(Carlos Margarit)在一九八四年完成亞洲和西班牙首例成功的肝臟移植手術,柏德一九八五年在內布拉斯加創立肝臟移植中心,並在一九九五年成為肝臟移植領域當今最好的學術期刊《肝臟移植》(Liver Transplantation) 的創刊總編輯。二○○九年,柏德從內布拉斯加大學外科主任退休,目前專事寫作與醫學教育傳承。
柏德身高一九五公分,多才多藝、文采洋溢,是我見過手術做得最漂亮,文筆最流暢的美國外科醫師。工作之餘,除了寫作與攝影,他也喜歡冒險犯難的休閒活動,如開私人飛機、潛水等。二○○八年暑假,我們的家庭聚會一起在澳洲租了帆船,圍繞漢彌頓島航行一星期。
我們在台灣開展肝臟移植手術,三十多年來不斷尋求突破與精進,也創立了多項台灣、亞洲、全球的肝臟移植紀錄,並在活體肝臟移植維持全球最高的存活率,目前在高雄長庚醫院已成為例行的常規手術,每周都有三例。我們也秉持醫療不藏私的理念,培訓了三百三十多位外國醫師,也積極協助國內外醫學中心發展肝臟移植高端醫療。在醫援國際,我的理念很單純,醫療是救人的學問,不應該有藏私的觀念。台灣的醫療能有今天,也是因為過去我們有機會到美國、歐洲、日本去學習,今天我們有可以走出去幫助的,或讓別人來學習的,就應該毫無保留地回饋國際社會。我們的經驗也印證了我和柏德的老師史達哲說的:「醫學的歷史通常是昨日認為不可思議的,今日也很難達成的,只要堅持理想不斷努力,明日往往成為常規。」
【內文摘錄】
- 一九八一年,匹茲堡
初體驗之一
那晚我急於展頭露角,患者是來自德州的肝臟外科醫師馬克斯.史汀森。諷刺的是,他染上了肝病,導致最後肝臟衰竭。我們拿著器捐的肝臟從維吉尼亞趕回來時,病人已經躺在手術台上,切開腹部了。尚恩.岩月(Shun Iwatsuki)已刷好手,旁邊圍著六個人幫忙,等我們刷手完畢進開刀房,大部分助理便離開了,但尚恩仍留下來。
史塔哲醫師的心情不太爽,尚恩站在他對面手術台。尚恩曾在丹佛與史塔哲共事,在往後的日子裡,尚恩對我的訓練,重要性無人可比。站在史塔哲右邊的是來自上海的洪醫師(Hong),負責牽引胸廓,以免擋到史塔哲手術,洪醫師雙手齊發,拉住腹部切口的上緣,身體像滑水似地往後傾。不久之後,我才知道,他們稱洪醫師為「人肉牽引器」。卡洛斯.費南德斯.布洛(Carlos Fernandez-Bueno)醫生正在接受第二年的訓練,他也來自丹佛,不過他在秋季前便離開了,因為聲望極高的東岸移植中心,為他開出一個條件好到無法拒絕的職缺。
史塔哲馬上抱怨起來,尚恩像貓似地,默默東推西拉,而且不用一言一語,便能指示洪醫師或卡洛斯幫忙,我還以為他們有心電感應,其實他們只是在極力安撫憤怒的老闆罷了。我在這個新世界顯得如此無用武之地,我已開始懷疑自己能不能撐下去了。
尚恩切開的口子像擺平的賓士標誌,從胸骨向下劃出的垂直短切口,與橫跨腹部兩側的倒V長切口相連。除了當晚稍早,在維吉尼亞器捐者身上看到的之外,我從未見過人體切得那麼大。
我瞥見埋在橫隔膜下的肝臟,那是一顆枯縮成團的黃綠色腫塊,在原本的空間裡顯得過小,而且呼吸器每次啟動,把橫隔膜往下推時,肝臟就在血水裡唏哩嘩啦晃動。
血水似乎湧自四面八方,腹部切口下面皮膚是一層半透明的濁黃色物質,碩大的藍色靜脈從肚臍向外延伸,我看到切口劃過其中一些靜脈,當史塔哲開始移除切口邊緣的紗布時,那些血管便源源流出或黑或紅的血。
史塔哲拚命瘋狂止血,從刷手的技師手裡拿起一把又一把的持針器,用絲線縫綁血管的開口,再讓卡洛斯、洪醫師、尚恩接續抓起線頭,打好穩妥的結。我一逮住機會,也拿起線頭,可是打到第二個單結,就把縫線扯斷了。
「媽的。」史塔哲說著在我扯斷的地方補上一針,但這回我又扯得太用力,縫線劃破了組織,血汨汨湧出。卡洛斯拿起紗布壓住傷口,然後閃身讓史塔哲再縫一針,親自打結。史塔哲在同一個斷口上又補強了兩針,由卡洛斯和尚恩各綁一針,才終於把血止住。尚恩對我皺眉輕輕搖頭。
我決定等他們綁好縫線,再來剪線頭,這是我們叫醫學院學生做的事。我是位訓練有素的外科醫生,而且照猶他州的各項標準來看,還是位好大夫。我在不到一個月前,在猶他受完訓練。於是我抓起剪子去剪線頭。
「太短了,媽的。」史塔哲說,「這樣縫線會鬆脫,他會失血而亡,你是想害死他嗎?」史塔哲再縫一針,由尚恩打了四個單結,我剪線頭。
「太長了。」史塔哲抱怨,「尚恩你快來幫我,這傢伙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一九八一年六月三○日,我在猶他大學當最後一天的外科住院醫師,那年我三十一歲,想成為移植外科醫生。肝臟移植之父,或許也是世上最著名的移植醫師,托馬斯.史塔哲,同意讓我跟他的團隊一起受訓。他在六個月前,剛把移植計畫轉到匹茲堡,我在俄亥俄州長大,但從來沒去過匹茲堡,我討厭他們的美式足球鋼人隊,因為他們老打敗我最愛的克里夫蘭布朗隊。
當大家知道我決定到史塔哲麾下受訓時,猶他大學一部分教職員,和我大部分的朋友都認為我錯得離譜。有位私人醫院的資深外科醫生,曾經在紐約擔任移植醫生,這位摩門教徒告訴我,肝臟移植「只是一場對無藥可醫的病人,進行的死前昂貴酷刑」。
我好想嘲笑他們,罵他們疑心而無知,但我自己也擺脫不了疑慮。我對史塔哲與肝臟移植的所有認識,都立基於多年來,他在科羅拉多州研究計畫裡,各種謠傳的災難。不過等到我必須決定去何處接受移植訓練,情況似乎已有了轉變。史塔哲的團隊已開始使用一種新藥,更能有效防範受贈者的免疫系統,攻擊植入的器官了。這種新藥叫環孢靈(cyclosporinA),是移植領域的革命性產品,而史塔哲是美國唯一能使用環孢靈治療腎臟或肝臟移植病人的外科醫生。然後還有法蘭克.穆迪,法蘭克叫我把眼光放遠,應該跟頂尖的醫生一起工作、受訓。穆迪醫師令我覺得,若去別處,就等於背叛他,而且在移植這種真正的醫療前線工作,比安全躲在大後方,更值得追求。
2. 醫海浮沉
自從老爸娶了一名酒鬼,讓她成為我的繼母,而繼母又教我如何當刷手護士的整整十七年後,我第一次有機會從頭到尾開一次肝臟移植手術。史塔哲挑了一個他所說的完美患者——年輕,沒開過刀,肝臟除了缺少一種酵素,可說是完全正常,但這個問題卻足以要了患者的命。整個手術就像對正常肝臟開刀,沒有糾纏不清、隨時準備爆開、血淹腹腔的血管。史塔哲讓我跟尚恩開始手術,他則飛去取新肝臟。
史塔哲回來後,和一位主治醫師在盛滿冰水的腎形盤裡處理新肝臟,處理就緒,他過來看我們是否已準備妥當,尚恩和我拿開紗布,拿起肝臟四處翻動,直到史塔哲說沒問題。他回到準備桌邊,說道:「準備好了就告訴我。」
尚恩看著我夾好止血鉗,確定我剪血管時留下足夠長度,以便接合新肝。我們把舊的肝臟交給刷手護士,花幾分鐘縫合一些小出血點,確保每條血管都留好了接合新肝臟的切口。
「好了,」我說,「請把新肝臟拿過來。」
「是的,」史塔哲說,「馬上就來。」
我聽到後邊地上傳來啪噠好大一聲,我從沒聽過這種噁心的聲音,卻立即辨識出來。
「慘了!」史塔哲說,「我幹了什麼蠢事。」
我轉過身去,看到史塔哲前面地上躺著一副肝臟——就是那副新肝臟。我只覺雙膝一軟,本能地叫護士拿優碘——我們用來刷手和幫患者消毒皮膚的紅褐色液體——以為只要把灰塵弄掉,便能把肝臟救回來,捐贈的器官落地十秒應該沒問題吧?
史塔哲和主治醫師互望一眼,哈哈大笑起來,我以為他們瘋了,直到那位醫生掀開蓋在腎形盤上的毛巾,拿起真的新肝臟給我看。
「你他媽瘋了。」我說。
史塔哲的神情立即一凜。
「好,別鬧了。」他告訴那位醫生,「咱們時間有限。」他拿起肝臟,帶到手術台,硬擠到我和左邊的助手中間。我要了第一根縫線,突然就開始縫合新肝臟了。
我發現自己視線受阻,很難移到我想去的位置,因為史塔哲卡在中間盯著我的每一個動作,用嘴巴指示我縫每一針。
「向左一點,」他說,「不對,少一點,這樣就對了!」
他一直催我加快速度。
「快點,」他說,「現在這裡剛好可以趕進度。」
每個動作,都是趕時間的機會,我覺得房裡愈來愈熱,等到我接完最後一道連結,告訴麻醉醫師可以鬆開夾鉗時,我已渾身溼透,雖然熱,卻又忍不住發抖。我鬆開夾鉗,恢復肝臟血流,看著新肝臟轉成健康的粉色,並開始製造膽汁。尚恩說,那叫黃金膽汁。史塔哲稱讚我表現得很好,誇尚恩是位好老師,然後就離開讓我們去收尾了。手術過程失血很少,花費時間比當年大多數肝臟移植的案例要短。我們將患者推回加護病房時已近凌晨四點,我坐下來寫病歷,感覺自己真他媽的優秀。
史塔哲醫師顯然認為我是他見過最厲害的外科醫師,至少當天稍晚,某位住院醫師是這麼跟我說的。
「你應該聽聽他的口氣,」他說,「史塔哲說他從沒看過有人那樣開刀,你果然厲害。」
果然。
珊蒂說她也聽到了。那晚尚恩告訴我,老闆對手術非常滿意,我想我已經出師了,我將成為匹茲堡大學裡,偉大的史塔哲之外,唯一會做肝臟移植的人,就我所知,匹茲堡大學肝臟移植的數量,比全世界其他地方加起來都多。
3. 下水褲
一九八○年代初期,我們還在摸索凝血及肝臟移植的相關事項。後來我才知道,在匹茲堡大學的早期病例中,馬克斯.史汀森的手術失血量算最少的了。即便如此,在那幾年,有時手術的出血量,仍然顯示我們學習得不夠快速。
當年我們的腰部以下經常泡在血水中,等到我只剩下兩條內褲可用,鞋子就算用漂白水洗過,聞起來仍像是壞疽時,我知道非得想點辦法不可了。
我無意誇大手術的流血量,但到後來我們終於學會了控制,幾乎所有的肝臟移植手術,都不會流失太多的血了。不過即使在初期,偶爾也會有出血量很少的時候,我們在拉開鋪單,請人送推床過來時,麻醉醫師們會互相擊掌慶賀。當時我見識過的出血情況,涵蓋各種程度,從不太多,至大到我們得站到台子上,才能離開地面的積血。有時來觀摩的醫生休息時,因不知自己身上沾了很多血,你可以沿著走廊,一路跟著他的血腳印直入廁所,知道他用的是哪一隔間。
我們使盡一切技巧處理出血,沿鋪單的邊緣折起溝槽,防止血液外溢到我們身上,但鋪單畢竟只是布做的,血液還是能滲透出來。有時呼吸器開動時會把橫膈膜往下推,血液便一波波衝破溝槽。有一陣子我試過不穿內褲,但血液會從我的陰囊往下淌,沿大腿內側向下滴流,堆積在我黏呼呼的鞋墊上。我在手術室裡穿的是舊的膠底高筒帆布鞋,我從讀醫學院就開始穿這雙鞋了,以前幾乎不太洗,雖然橡膠鞋墊四周有點磨損,但大致上還是白的。這雙鞋現在看起來像從醫療廢棄物裡拖出來的東西,我原以為用漂白水泡過之後,應該能除去污黃的顏色和臭味,但效果不彰。它讓我想起學生時期,第一次到醫院輪訓,克里夫蘭榮民醫院腸胃科病房裡的氣味。我從小在養豬場和飼牛場長大,我告訴榮民醫院的實習醫生說,這裡的味道比那裡更難聞,感覺像死亡的氣息,他叫我習慣就好。
我有一條下水褲,我想應該能解決沾血的問題。這是我在猶他州時,買來穿越貝爾河保護區的沼澤,去獵鴨或獵鵝時穿的。我站在及膝的水中,四周都是冰冷的碎冰,射下我第一隻,也是最後的一隻雪鵝,有下水褲護體,我覺得溫暖而乾爽。
下水褲的缺點是只到臀部,如果走在貝爾河保護區,遇到水深高過臀部的地方,褲子就會變得又溼又冷,沉重如錨。替紐澤西的大學生開刀時,浸滿臀部以上的血液,最終都流積在靴子底處了。我本來想買一條高及胸部的下水褲,但價錢太貴了。我跟黛安提這件事,她拿她解剖時穿的圍裙給我看,黛安就是告訴我,可以把腳踏車擺到太平間的那位病理科住院醫師。她送我一件可從胸部遮到膝蓋底下的塑膠圍裙,圍裙很乾淨,但已發黃發霧了,她說應該是甲醛的關係。
圍裙加上下水褲,我就萬無一失了,但這些橡膠和塑膠材質,有時悶得我汗如雨下,熱到差點昏倒。我試著把這樣的裝扮留給出血量可能較大的手術,不過我實在拙於預測。我不記得自己何時開始不再穿下水褲了,但我在一次動完長刀後,因褲子已開始滲漏,且奇臭無比,便索性跟醫療廢棄物一起扔了,雖然它還遠不及我的帆布鞋臭。我在軍用品店買到一雙橡膠鞋,價錢只有耶誕節郵購目錄裡的一半,我把鞋跟的羊毛氈內襯拔掉後,搭配圍裙一起使用。
我們科裡有位從田納西州蓋特林堡來的輪調住院醫師杰弗遜. 戴維斯(Jefferson Davis)。有一天,他協助我們進行移植手術,我切到一根大血管,血液噴到手術台上快一公尺高,濺到他的臉上時,戴維斯竟然把頭湊上去,像熊一樣咆哮起來,他搖晃著頭,彷彿剛從怒叉河中咬出一條虹鱒,令我印象深刻,大夥哄堂大笑,但那是在我們知道AIDS之前的事。
幾年後,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批准一種測試HIV病毒的新方法。一九八五年冬,我搬到內布拉斯加州後,史塔哲打電話給我,說有壞消息,要我坐下來聽。他說他們檢驗過匹茲堡大學肝移植患者留存的血液樣本。
「有些是陽性。」他說,「而裡面很多刀都是你開的。」
「他們可能是輸血時感染的,」我說,「也許我們的風險很低。」
「呃,我們這裡的人都驗過了,」他說,「當然了,我不能告訴你結果,我只能說……」
他遲疑了幾秒。
「我建議你搭飛機到芝加哥或丹佛,找個不可能有人認識你的地方去驗血,除非你不想知道答案。我也不確定你能怎麼辦,不過你應該知道,你的太太或兒子也該驗一下。」
我在匹茲堡的前幾個月,正值冬季。我與來自土耳其的穆奇醫師一起協助史塔哲,為名B肝患者進行換肝手術。當時尚未發明肝炎疫苗,我們都很擔心會被感染。史塔哲說他在丹佛時已得過肝炎,病得很重,差點死掉,他有一位同事因此去世。史塔哲說,這是正常風險。穆奇和我戴了兩層手套,希望藉此降低風險,但是史塔哲在縫合門靜脈時,不小心刺到穆奇的手。手術的空間很小,穆奇把十二指腸拉開,騰出空間讓史塔哲縫針,每次針頭刺穿他的手套,穆奇就跳一下,史塔哲便斥喝要他別動,說他會把靜脈扯成兩段。
B型肝炎的平均潛伏期是兩個月,六十天後,穆奇臉色發黃,差點丟了小命。他休養好幾個月才康復,等他歸隊,聽說新的試驗疫苗出來了,我是第一批簽同意書打疫苗的人。
我從沒做過HIV檢驗,我不確定為什麼,因為通常我對這種事都挺憂心的。我從當時的文獻得知,醫師幫HIV帶原者開刀,感染病毒的機率非常小——與肝炎的感染率完全無法相比。我想過打電話問尚恩那邊的情況,但終究沒打。後來我才知道,當月稍早我在申請辦理人壽保險時,他們已經幫我驗過HIV了,當時檢測HIV還無需經過本人同意。我猜結果應該是陰性,否則他們不會賣我人壽險。
4.控制狂
我是個優秀的外科醫生,全盛時期手術室裡能與我匹敵者寡,其實不管我到底是不是最優秀,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相信自己是最棒的。我認為,那是唯一能支撐我,度過各種困難手術的辦法;也因為那樣,使我擅長教導許多其他外科醫生,做同樣的事。我發展出一套固定流程,堅持那是做肝臟移植的正確方法,除非我看到改善的必要,才會進行更動,而且僅以審慎、有系統的方式去改。我從不害怕改變,但為了維持水準,我堅信改變需源自仔細檢視經驗,而非突發奇想。
就我對其他外科醫師的瞭解,這些都很正常。手術室是我們的地盤,是我們生活中,唯一能頤指氣使發號施令的地方。我們在這裡指揮軍隊、奮勇作戰、在解剖學中贏取勝利。只要我們站到手術台,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並揮灑這種力量,便能取得主導。
我一向自認是優秀的移植外科醫生,部份原因是,我在手術時,便會考慮術後的狀況——並永遠做最壞的打算。在移植手術中,你學會去懷疑,因為任何症狀都有可能是致死的預兆,你得採行必要手段,尋找並摧毀想害死患者的問題。病人印證最壞狀況的次數越多,你的及時行動便往往越能救回患者,你也越覺得自己聰明幹練。在手術室也一樣,雖然比較沒那麼戲劇性。你要說服自己,你可以解決任何問題、控制狀況,你激進的作為雖然具有風險,但你的技術高超。
這辦法通常能夠奏效,若是失效——我雖已盡力了,卻仍失去患者——至少我總能從個人的認知,找到一些事或人去咎責,幫助我解套,讓我維持必要的能力與控制感。
最近,我不再去控制任何事了,我在真實世界還找不到任何能取代手術室的事物。我停止開刀後的幾年,朋友、同事、老師和以前的學生,不斷問我會不會想念手術,我都掙扎要不要老實回答。
我說,我想念外科手術的成果;那種得意——狂喜的感覺——在漫長的奮戰後,我們雖渾身是血,卻充滿幹勁,彼此會心點著頭。
我告訴他們,我想念用自己的雙手,做一件美好事情的感覺。十年前我造了一條木舟,過程非常有意思,但比不上植入一個肝臟,然後鬆開夾鉗,看肝臟注滿血液,轉成粉紅色,然後開始在我眼前分泌膽汁,每個人因此露出笑容,大夥專心致志,參與其中。
我說我想念同袍的情誼,做為小組成員,與大夥合力達成不可能的任務,一群技術高超的同業並肩而戰,盡力而為。這番話往往令對方語塞,有時對方還會哈哈笑著搖頭,彷彿在說:「最好是啦。」或「明明就是混戰一場。」於是我才想起,手術很少非常順利。於是我便不再說了,他們似乎就想聽這種答案,所以那樣就夠了。我若再多說,便沒人要聽了,但那不是全部的事實,或最重要的部分,至少對我而言如此。
二○○五年,我因不想再於夜間待命,而不再接移植手術,但我仍是全職外科醫師,固定會開刀並乖乖巡房。那是我擔任外科主任十二年的第九個年頭,我開始著手一份新的軟體發展計畫。
二○○六年一月的某個週日下午,我在奧馬哈的家中工作,為一次即將到來的說明會寫報告。書房電視上,匹茲堡鋼人隊正在跟印城小馬隊打季後賽,我聽到鋼人隊暫時領先,我應該能及時寫完報告,坐到沙發上看第四節的比賽,若是比分相差過於懸殊,或許我會去騎個車。一切都很美好。
但我開始感到焦慮,毫無預警,我停止撰寫,做了幾個深呼吸,探著腕上的脈搏,脈搏跳得又重又快。我開始有些頭昏,我一站起來,感覺兩腿發軟。我走進起居室,坐到沙發上,卻看不懂賽事內容。我以為自己也許中風或長腦瘤了,或許腦部有顆動脈瘤正在滲血,在球賽第四節開打之前,我就會成為器官捐贈者了。
我知道那很可笑,我都很想嘲笑自己。我看著鏡子,要自己別胡思亂想,放輕鬆。我找到老婆,說我覺得怪怪的。「怎樣怪?」她問,但我又解釋不出來。時值一月,但溫度有攝氏十五度,陽光晴和,因此我覺得應該去騎個腳踏車,騎一下就好,我說,有助我放鬆。
騎了幾條街區,我知道自己錯了,我滿腦子只想到死亡,我所看到的、感覺到的一切,都加深我的恐懼。我痛恨太陽,洋洋的暖意令我畏懼發顫。一名健美的年輕女子穿著短褲和比基尼上衣,在一月慢跑,讓我覺得世界就要完蛋了,若不是對她或其他人而言,至少對我如此。我這輩子做過的一切都了無意義,而我是唯一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的人。我調頭騎車回家,直奔我的臥室,然後鑽到毯子底下。我冷死了,我蓋住自己的頭部,讓天變黑。我側躺著,把膝蓋蜷到胸口,彎著脖子,把毯子撐起來,以便呼吸,等覺得快窒息時,再把頭探出去吸氣。
幾天之後,我又犯恐懼了,這次也是出其不意,橫空殺出,我本來絲毫不覺得有壓力或擔心任何事。接下來一個星期,我又犯了四、五次,我覺得冷,雙腿無力,想到要跟任何人或事物接觸,就令我害怕莫名。要是在工作中犯病,我就叫手下別來煩我,拉上窗簾,把門鎖上。我躺在沙發上,用冬衣外套蓋住自己,抖到睡著為止,等我醒時,便欣然發現恐懼又煙消雲散了。
我不知如何是好,懷疑自己是不是賀爾蒙失調。我想,有可能是我的甲狀腺出問題,或長了怪腫瘤,分泌詭異的物質,害我有這種感覺。有幾次我覺得頭昏,擔心是腦子出了狀況,於是我去看神經科部門主任,問他有何看法。他叫我去做腦部核磁共振、抽血,並寫說他擔心我淋巴瘤復發,生在腦部。檢查結果全都正常,他也不知道我接下來該做什麼,我覺得自己也許該去見精神科醫師,但我不想提出來。
最後我發現自己得了焦慮症,有個朋友出其不意對我坦承他自身的問題。接受治療後,我的問題大多控制下來了,現在已有大幅進步,不過為了治療,我得服用少劑量的贊安諾或安定文。我有幾次被迫取消排定的手術,或請同事代刀。我從不在服藥後做手術,即使只吃了最輕的劑量。我知道應該不會有問題,但萬一出事呢?我才不想冒那種險,無論風險有多低。
我開始懷疑,所謂控制,是否只是一種為了讓自己活下去,而自我創造出來的幻覺。然而「我若不在場做正確治療,患者可能會死」的狂想,一直都是支撐我活下去的重要意念,我畢竟是個外科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