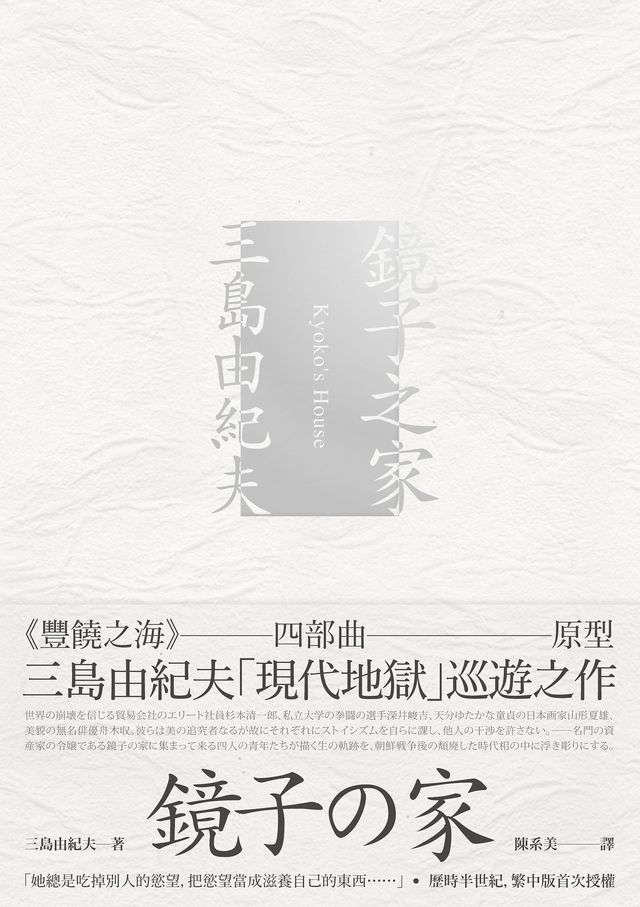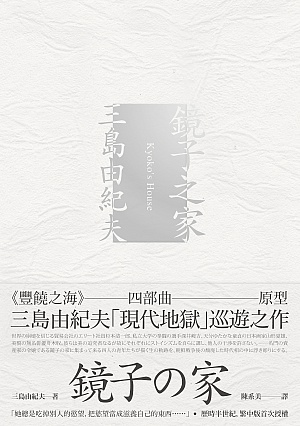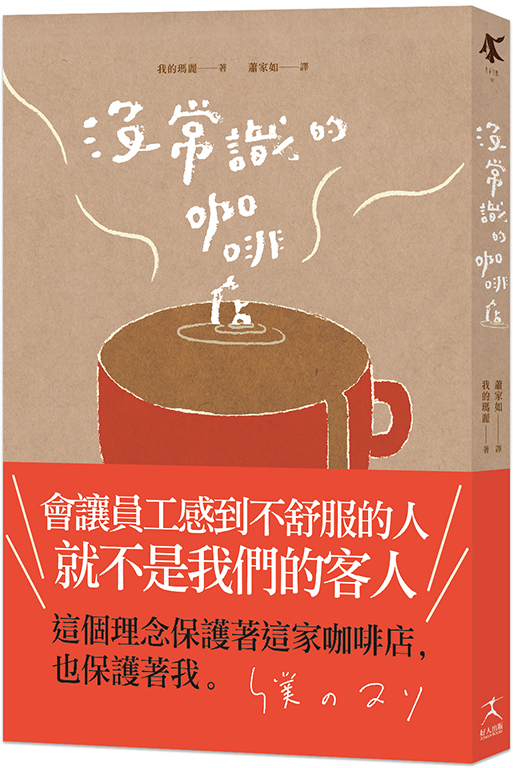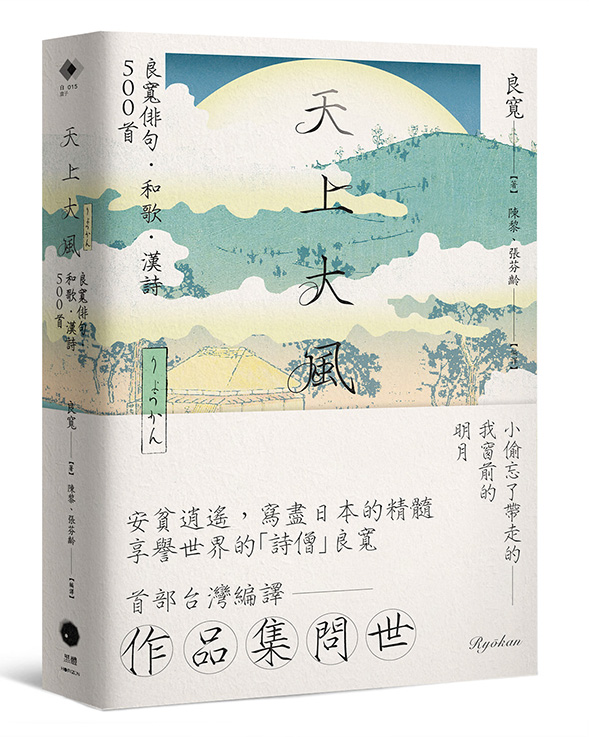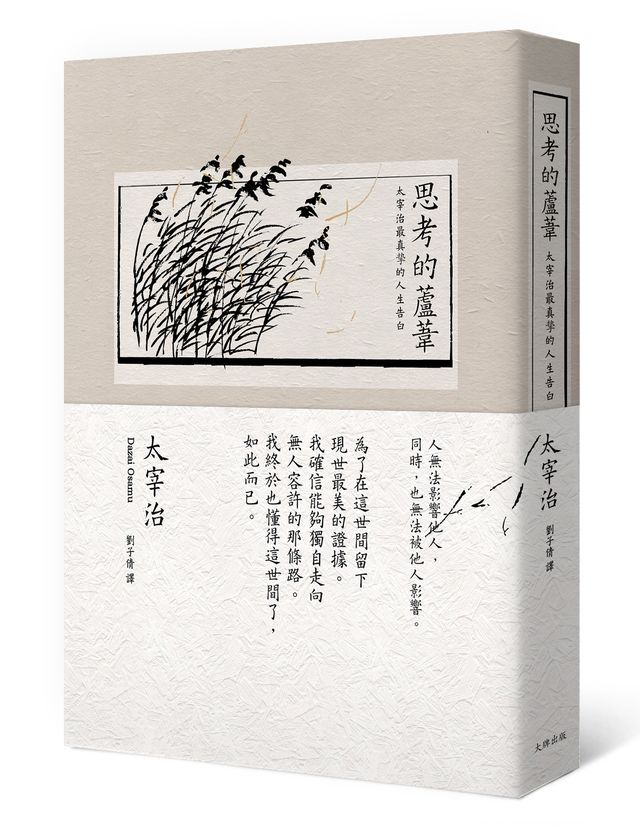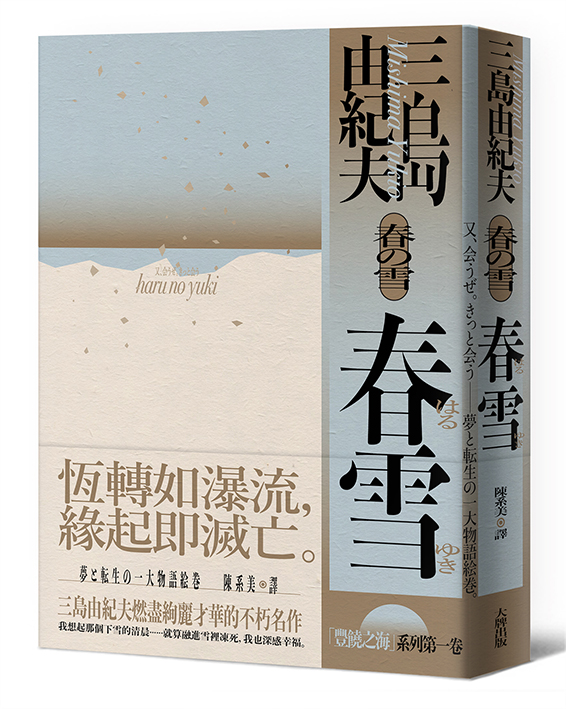從「個人」跨寫「時代」,描繪日常性的野心之作
三島由紀夫最喜愛也最揪心的作品
歷時半世紀,繁中版首次授權
如果將《豐饒之海》視為三島的自我輪迴,
那麼,《鏡子之家》就是作家闡述四個平行的自我,
本書透過鏡子這個女人,演繹出一幅巡遊現代地獄的的圖景。
「她總是吃掉別人的慾望,把慾望當成滋養自己的東西……」
四名青年聚集在鏡子之家,宛如此處即隔世的避風港。
然而所謂庇護,是否也是深淵,他們自始至終只能看見自己的生命,
最後用不同的方式,對抗現實生活中日常性所帶來的虛無。
藝術家氣質的夏雄、崇尚力量的峻吉、追求肉體美的阿收、內斂隱秘的清一郎,
鏡子的魔力,就是輕易地將他們的體悟,飾演成自己的記憶。
他們的意志與挫折,展現一個時代虛無的感情世界。
一九五○年代的日本,因為韓戰爆發而成為美國的後勤基地,帶來空前的「特需景氣」,經濟由此走出困境邁向繁榮,這是非日常的開始,所有人事物都顯得欣欣向榮,獨特而有朝氣。然而三島由紀夫將《鏡子之家》的時間設定在韓戰之後,並且把場景寫在東京與紐約,他認為現代的地獄,理所當然是都市的。而這個令人感到孤獨的地獄,光亮且沒有雜質,人們毫無疑問在此生活,絲毫沒有發現這個非日常的世界正緩慢步向崩解。
「我們來締結一個同盟,無論陷入什麼困境都不可以互相幫助的同盟……」
一九五○年中期,三島由紀夫因為《金閣寺》而達到個人的巔峰,他企圖擴展野心,描繪時代的毀滅,於是寫出了《鏡子之家》。三島將自己的四個分身放在不同的社會階級中,每個人都有明確的個性與觀念,三島像是旁觀者,冷靜地觀察四個人的發展。這些人物的共同交集是鏡子之家,他們避免互相影響,觀察彼此,宛如身處一座璀璨的旋轉木馬,刻意避免糾結。如同三島體內充滿衝突卻又和諧,和諧卻又不斷相互推翻的思想。《鏡子之家》可以說是三島對自我的持續印證,一直到完成《豐饒之海》後,才得以平息。
※特別收錄──【解說】陳系美:三島由紀夫自己最喜歡的小說
三島的青少年時期在戰時及戰後初期度過,戰時不知有明天的世紀末之美,與戰後初期的廢墟之美,深深影響了少年三島。對三島而言,那是個「充滿生死悲劇崇高之美」的時代,隨著戰後復興,整個社會的價值認同逐漸指向「平庸的日常之美」,呈現出一股陰溼、情感化的和平主義女性化性格。因此,三島的悲劇,就在他自小憧憬的生死悲劇崇高之美被時代拒絕,同時也被當下偏向女性化的日常性之美的拒絕中,迸放開來。
三島由紀夫
本名平岡公威,1925年出生於東京。1947年自東京大學法學部畢業,通過高等文官考試,隨後進入大藏省任職,隔年為了專心從事寫作而從大藏省離職,開始專職作家的生涯。
三島由紀夫在日本文壇擁有高度聲譽,其作品在西方世界也有崇高的評價,曾三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也是二戰結束之後西方譯介最多的日本作家之一。
三島對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深為讚賞,他對日本二次大戰後社會的西化和日本主權受制於美國非常不滿。1970年11月25日他帶領四名「盾會」成員前往陸上自衛隊東部總監部,挾持師團長要求軍事政變,期使自衛隊能轉變為正常的軍隊,但是卻乏人響應,因而切腹自殺以身殉道,走上了日本武士最絢爛的歸途。
主要著作有《豐饒之海》四部曲、《假面的告白》、《金閣寺》、《鏡子之家》、《盛夏之死》、《憂國》、《反貞女大學》、《不道德教育講座》等。
陳系美
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日本筑波大學地域研究所碩士,專攻日本近代文學,碩士論文《三島由紀夫《鏡子之家》論──以女性像為中心》。曾任空中大學日文講師、華視特約譯播,現為專職譯者。近期譯有太宰治《小說燈籠》,佐野洋子《靜子》、《我可不這麼想》、《沒有神也沒有佛》,山田詠美《賢者之愛》等書。
序
解說 三島由紀夫自己最喜歡的小說
文/陳系美
《鏡子之家》是讀者花最少心力,便可窺知三島強大的作品,也是三島自己最喜歡的小說。
這部作品發表時,三島曾說:「我在《金閣寺》描寫了『個人』,這部《鏡子之家》想描寫的是『時代』。《鏡子之家》的主人翁,不是人物,而是一個時代。這部小說,並非所謂的戰後文學,而是『戰後結束』的文學。」戰爭結束,連「戰後時期」都走向結束,是多麼可喜可賀的事,但《鏡子之家》開頭第一句竟是:
「大家都在打哈欠。」
因為無聊又平凡的日常回來了。日常是多麼需要珍惜的東西,尤其在經歷戰亂之後。但在三島文學裡,戰後社會的「生」,泛指重複、單調、無聊、平庸、瑣碎、近乎無機質的「現實之生」,亦即所謂日常性或日常生活。三島不願妥協、無法接受,甚至唾棄詛咒的,即是這種充滿日常性的「現實」。
三島的青少年時期在戰時及戰後初期度過,戰時不知有明天的世紀末之美,與戰後初期的廢墟之美,深深影響了少年三島。對三島而言,那是個「充滿生死悲劇崇高之美」的時代,隨著戰後復興,整個社會的價值認同逐漸指向「平庸的日常之美」,呈現出一股陰溼、情感化的和平主義女性化性格。因此,三島的悲劇,就在他自小憧憬的生死悲劇崇高之美被時代拒絕,同時也被當下偏向女性化的日常性之美的拒絕中,迸放開來。
於是我們經常可以在三島的二元對立世界裡,看到「生」與「醜」劃上等號,「死」與「美」劃上等號。
這個令人打哈欠的時代充滿虛無感,甚至成為一道高牆,迫使《鏡子之家》中的四位青年必須面對。因此無秩序根據地的「鏡子之家」像個孤島,成為憧憬非日常的最後堡壘,最後隨著「鏡子之家」的消失,也宣告戰後結束的時代全面來臨。
《鏡子之家》執筆於三島由紀夫三十三到三十四歲之時,描寫時代結束的同時,也是三島青年期最後一座紀念碑,因為他在這時(三十三歲)結婚了。介紹結婚對象杉山瑤子給三島認識的,是他的多年好友湯淺敦子,而湯淺敦子的家,正是「鏡子之家」的原型場所,三島將其作為《鏡子之家》的舞台。湯淺敦子的先生經常出差,寬敞的家裡經常只有湯淺夫人和年幼的女兒,這和《鏡子之家》的設定也有相似之處。其實在更早之前,三島二十九歲時便曾以湯淺母女為材料,寫了短篇小說〈上鎖的房間〉,作中的女主角是位娼婦,而〈上鎖的房間〉就是《鏡子之家》的母胎。
因為是青年期最後一座紀念碑,算是總結算,也算是告別,三島將自己拆為四個分身,拳擊手峻吉、演員阿收、畫家夏雄,與上班族清一郎來寫這部作品。
這時的三島已積極進行肉體改造,勤於上健身房,練拳擊,還曾去日本大學的拳擊社指導拳擊。但拳擊只練了八個月,因為他聽說練拳擊必定導致腦壓上升,破壞大腦機能。雖然只練了短短八個月,但描寫拳擊手峻吉上擂台比賽的場面,仍充滿鮮活的躍動感。峻吉是三島行動家的象徵人物,他只相信行動和有效的拳擊,認為思考是敵人,是一切醜陋的代表。
而美男演員阿收則象徵三島的自戀角色,靠著一張俊美的臉,讓女人供養過活,但三島後來也送他去健身房練身體,誇耀自己的胸圍長了幾寸,肌肉變得多結實,使阿收成為「詩人的臉與鬥牛士的身體」,是肉體的讚美者。但美男阿收,卻碰上醜女清美。從三島的文學脈絡來看,阿收與清美也相當於金閣寺與溝口。然而最讓我震驚的是,譯到清美用剃刀割傷阿收時,日本剛好公布三島自殺前九個月未公開的訪談錄音,聽到三島提到「死」時說:「死是肉體形成之後,從體外進來的。」我一陣鼻酸,這分明在講阿收。難道三島在那時,已如此思考死法?阿收是四個男主角裡,唯一死亡的。日後三島的那把武士刀,也是從體外進來,在三島的肉體形成之後。
至於畫家夏雄,則是最像也最接近三島的角色,代表三島身為文學藝術家極富感受性的一面。但這樣的夏雄,卻槓上阿收所代表的肉體美,並直言:「這麼重視肌肉的話,趁還沒老之前,在最美的時候自殺吧。」這也可以看出三島內心的矛盾與糾葛。然而宛如預言般,阿收在最美的時候自殺了。
清一郎是三島理論家的側面,除了代表上班族對俗世的處世之道,帶著三島的冷眼,偽裝成參與命運的旁觀者之外,也是三島文學脈絡裡,從《假面的告白》以降,戴著「面具」成為「他者」的人物。三島更直言「成為他者是我自負的根本」。因此就在《鏡子之家》的四位青年,面對時代這道異質性的他者高牆時,清一郎想的是:「我要變成這面牆。我要化為這面牆本身。」當其他三人,峻吉、阿收、夏雄宛如成了「獻給虛無的供物」,唯有戴著面具成為他者的清一郎倖存下來。
這樣的清一郎,令人想起芥川龍之介說:「最聰明的處世之道是,既對世俗投以冷眼,又與其同流合汙。」雖然令人唏噓,卻也象徵著三島決定從戰後時代畢業,也是和自己人生和解的努力吧。
然而對《鏡子之家》的女人來說,這道時代的高牆似乎並不存在,即便同樣在鏡子之家出沒的民子與光子,對戰後社會也沒什麼不滿,活得悠遊自得,因為她們是活在趨向女性化的社會吧。這個社會對她們而言不是他者。最明顯的莫過於三島描寫清一郎的這一段:
「他精於塑造自己的形象,而且塑造的方法和世間教的相反。他以奇妙的直覺發現,若想洞悉社會的本質,與其研究別人,不如研究自己才是捷徑。這是女人的方法。可是現在社會對青年要求的,並非當一個男人。」
就連鏡子後來也信起「人生這種邪教」,還對夏雄說「若要像清一郎那樣藐視幸福活下去,女人是辦不到的」。
若將當時的東京,看成一個走向女性化的社會,清一郎後來去的紐約,三島形容它是非常「男性的都會」,而且是「全世界和『幸福』這個字眼最無緣的大都會」,所以清一郎的妻子藤子在這裡過得痛苦。
藉由這些描述,也更能看出三島對於當時日本社會的看法。
《鏡子之家》發表後,雖然成為暢銷書,但當時的日本文壇並沒有給予太高的評價,主要在於這四個主角之間近乎平行狀態,彼此沒有糾葛,只是各自去碰撞時代之壁。可是這本來就是三島的設定。近來日本文壇也重新審視《鏡子之家》,認為這不是缺點,並肯定三島如實描寫了時代的虛無,是三島文學相當重要的作品。
即便在當時不受文壇好評,三島也不氣餒,隔年便開始構思《豐饒之海》,繼續堅持四條線,只是這次不是平行,而是縱接,而且角色設定和《鏡子之家》有異曲同工之處。
「感受性」:畫家山形夏雄與松枝清顯
「行動家」:拳擊手深井峻吉與飯沼勳
「理論家」:上班族杉本清一郎與本多繁邦
「被看者(被觀賞的肉體)」:演員舟木收與月光公主
三島曾說,《鏡子之家》是他自己最喜歡的小說。這話不是在他三十四歲《鏡子之家》問世時說的,所以並非為了推銷自己的作品。他說這話,是在他四十二歲時,距離自決前三年。看來三島是真的很喜歡《鏡子之家》,畢竟他說過,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投進去了。
《鏡子之家》付梓半世紀之後,台灣終於首度出版繁中授權版。我想三島在天之靈也會微笑吧。
內容連載
1
大家都在打哈欠。接下來要去哪裡,峻吉問。
「大白天的,實在無處可去啊。」
「讓我們在美容院下車。」
光子與民子說。她們真是精力充沛。
峻吉和阿收,對於讓她們在這裡下車都沒有意見。如此一來,車上剩下的女人只有鏡子,光子和民子也不在意把鏡子留在車裡。峻吉和阿收以各自的作風,極其乾脆地向她們點頭道別。但她們期待的卻是夏雄的溫柔道別,縱使夏雄並非她們的男伴,而夏雄果然也滿足了她們的期待。
這是一九五四年四月初的一個午後,將近三點。峻吉開著夏雄的車,在市內的單行道轉來轉去。要去哪裡呢?對了,去人少清靜的地方吧。待了兩天的蘆湖人潮洶湧,回到銀座更是人滿為患。
這時應該聽夏雄的意見。
「去月島那邊的海埔新生地如何?我去那裡畫過一次素描。」
大夥兒都贊成,便驅車前往月島。
遠遠便看到勝鬨橋那一帶車流壅塞。阿收不禁納悶地說:「怎麼搞的?難道是出車禍了?」但隨即也明白,八成是到了開橋的時間。峻吉不爽地說:「嘖,海埔新生地就別去了,有夠煩。」可是夏雄和鏡子都沒看過勝鬨橋的開橋情景,很想看看,於是將車子停在稍遠處,大夥兒下車走過部分鐵橋,去看開橋情景。可是峻吉和阿收,擺出一臉了無興致的表情。
橋的中央是鐵板,唯有這個部分會開闔。工作人員拿著紅旗站在前後兩端,被迫停下的車輛擠得水洩不通。人行道前面也掛著一條鎖鏈,阻止行人通行。前來參觀人潮眾多,也有因通行受阻而趁機摸魚的推銷員或餐點外送人員。
鐵板上鋪著電車路線的部分,什麼都沒有載,一片漆黑寂靜。人車在兩旁望著它。
不久,鐵板中央開始緩慢蠢動,慢慢地抬起頭來,接縫處也分開了。隨著鐵板升起,兩側的鐵欄杆與跨於其上的鐵拱柱,與柱上光暈柔和的電燈,全都跟著升起。夏雄覺得這一連串的動作優雅美麗。
鐵板即將垂直時,兩側與軌道凹陷處揚起的塵埃,如輕煙般飄落。兩側無數的鉚釘,各自拖著小黑影。這些小黑影越來越短,逐漸和鉚釘合而為一。兩旁護欄的影子也緩緩改變角度。當鐵板完全垂直時,所有的影子都靜止不動了。夏雄抬起視線,看到一隻海鷗掠過打橫的鐵拱柱。
……就這樣,一面巨大的鐵牆,驀然擋住了四人的去路。
* * *
宛如等了地老天荒那麼久,橋終於恢復原狀後,大夥兒已不那麼想去海埔新生地了。剩下的只有,橋既然通了當然非過不可的義務感。然而每個人都因睡眠不足與旅途勞頓和溫暖的陽光而昏昏欲睡,無法縝密思考,也不適合重擬計畫。既然目的地是海邊,反正盡量往海邊去就對了。大夥兒都靜默無語,似乎心領神會,再度打著哈欠,慢吞吞地走回停車處。
車子渡過勝鬨橋,駛出月島町的街道,又渡過黎明橋。放眼望去是一片平坦的青藍荒野,猶如棋盤般的寬廣柏油路劃過其中。海風拍打著臉頰。峻吉將車子停在美軍設施一角的跑道邊,掛有「禁止進入」告示牌的地方。遠處的美軍宿舍旁有幾棵白楊樹,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夏雄下車看到這片景色,萌生一種幸福感,不禁心想:「我喜歡廢墟和海埔新生地。」但夏雄生性溫和謹慎,不會隨便把感想說出口。他不會因藝術見解堆在心裡而感到痛苦,更何況也無法跟這票人談藝術方面的事,然而這正是夏雄喜歡和他們在一起的原因。
即便如此,他的雙眼也不怠惰地梭巡四周。人工荒野遠處的白色巨船。剛剛駛出豐洲碼頭,煙囪上以白漆寫著「井」字的運煤船。這一切都顯得井然有序,十分美麗。而這片海埔新生地,人工且平坦的幾何學土地,洋溢著春天原野的氣息更是美不勝收。
這時峻吉忽然跑了起來,不停不停地跑,直奔荒野而去。轉眼間身影越來越小。
「因為明天就要開始練習了,這傢伙卯足了勁啊。我很羨慕這種隨時都能把身體動起來的人。」
身為演員,但至今尚未有像樣角色的阿收說。
「他在箱根的時候,每天早上也都練跑呢。真的很勤奮。」
鏡子說。
峻吉停下腳步,回頭看他們三人,三人的身影也是又遠又小。他已經養成每天跑步的習慣,縱使下雨天也不忘在集訓處的道場跳繩二十分鐘。
鏡子這一票人裡,峻吉最年輕。他是拳擊社的主將,明年大學畢業。鏡子的其他朋友,至少都已大學畢業。阿收是,夏雄也是。
生性凡事不拘泥的峻吉,第一次去鏡子之家,是拳擊迷前輩杉本清一郎帶他去的,之後便自然而然成了這裡的一員。他沒有車子,但很會開車,所以被視為瑰寶。由於對拳擊手的好奇心,這些年齡、職業、環境各不相同的人,都對峻吉很有興趣,並且很疼愛他。
明明還很年輕,但峻吉已擁有自己的信條。那就是,即使是瞬間也不思考。至少他是如此訓練自己。
譬如昨夜和民子做了什麼,他今晨獨自沿著蘆湖的環湖公路跑步時,早已忘到九霄雲外。當個沒記憶的人很重要。
……
晚上十點,鏡子家的門鈴響。旅途勞累正準備就寢的鏡子,知道是杉本清一郎來訪時,又坐到梳妝鏡前重新打扮,睡意也全消了。這時真砂子已經睡了。任何時刻都要開心迎接訪客,這是鏡子的家風。
在客廳等候的清一郎,看到鏡子一來便立刻抱怨。
「怎麼,大家都回去了啊?」
「光子和民子在銀座就分手了喔。三個男人來我家,峻吉和夏雄很早就走了。待到最晚的是阿收,不過他在三、四十分鐘前也走了。至於我?我剛才正準備上床睡覺。」
鏡子沒補上一句「要來就先打個電話嘛」。因為不打電話直接跑來是清一郎的習性。此外她也沒說「你喝醉了吧」。因為深夜來訪的清一郎,大多是在應酬酒醉後。而且來這裡的男人裡,清一郎和鏡子的交情最深,她十歲就認識清一郎了,猶如弟弟般。
「旅行好不好玩?」
清一郎問。由於他問得過於漠不關心,鏡子原本無意回答,終究還是開口說:
「還好,普普通通。」
清一郎在這個家的表情,通常是極度不平與極度安心一併出現。這種表情和下班的上班族在酒館裡的表情一樣,但清一郎頑強的下巴與銳利的眼神,那看似意志堅定的臉龐卻背叛了這種表情。他堅信即使是這張臉,或者說在這張臉的保護下,一定能看到世界毀滅。
鏡子為他斟酒後,像是對喜歡高爾夫球的男人要談高爾夫球一樣,為了清一郎,她搬出世界毀滅的話題。
「……可是現在不管跟誰談這種事,根本沒人當一回事。如果現在還是戰爭期間,而且是
大空襲的時候,大家會覺得阿清說得很對吧。或是戰爭剛結束,共產黨說明天可能會爆發革命時,或許還有人會聽。甚至在三、四年前,韓戰爆發時,大家可能會相信。可是現在這種情況……一切都回不去了,大家都一臉悠哉地過日子。說世界會毀滅,誰會相信呢?我們又不是全都坐在福龍號上。」
「我說的和原子彈試爆無關喔。」
清一郎說。然後因為醉意,以昂揚如詩般的語氣,向鏡子詮釋自己的意見。
他的看法是,現在完全看不出任何毀滅徵兆,這無疑正是世界毀滅的前兆。動亂也都以理
性對話解決,所有人都相信和平與理性的勝利,權威再度恢復,開戰前便互相諒解的風潮應運而生。家家戶戶都養奢侈的狗,儲蓄取代了危險的投機,幾十年後退休金的多寡成了年輕人的話題,就這樣洋溢著穩定和煦的春光,櫻花盛開。……這一切的一切,每一項每一項,無疑都是世界毀滅的前兆。
2
隔了一個月,原班人馬再度相聚,大夥兒都很開心。清一郎問峻吉這陣子在做什麼,峻吉說大學聯賽快到了,每天都在加緊練習。然後轉頭跟民子說,他對本月二十四日,白井對艾斯皮諾札之戰的預測,白井可能會勉強衛冕成功,可是無法贏得很光彩吧。……從那之後,民子沒見過峻吉,此刻看他的表情絲毫沒有箱根一夜的記憶,迫於無奈只好跟他比恬淡,充滿善意地說了一句挖苦話。
「反正拳擊忌諱女人吧。」
美酒上桌,只有峻吉沒喝。不知不覺中,女人被晾在一邊,久違的四個男人自己聊得很起勁。但是夏雄很低調,不談自己的任何事情。
「我們的共通點到底是什麼?」
清一郎問鏡子,想把她拉進來聊天。
「大概是,沒有人想得到幸福吧。」
鏡子只遠遠地回了這麼一句。
「不追求幸福,這可是古老的感傷思想喔。」清一郎反駁,「我們即使得到幸福也完全不在乎,即使幸福像青苔纏在身上也不害怕。荒謬的是,人有時會因為無聊透頂的理由,不由得追求幸福。像避開痲瘋病般逃避幸福的傢伙的英雄主義,充其量只是脆弱又窩囊的陳舊貴族主義吧。我們對任何事情都免疫,連幸福也免疫,我希望妳這麼想。」
受到這種鄭重其事的宏論壓迫,鏡子也不再說話,轉而和女人們聊天。
但四個男人也都默默感受到了。我們是站在高牆前面的四個人。
不知道這道牆是時代之牆,抑或社會之牆。然而在他們少年時代,這種牆早已徹底瓦解,在外頭還是明亮之際,可以看到滿地的瓦礫。太陽從瓦礫的地平線升起,也沉落於瓦礫的地平線。將玻璃瓶碎片照得璀璨耀眼的日出,為無數散落的碎片帶來了美。那個相信世界是由瓦礫與碎片組成,那個無限快活、無限自由的少年時代消失了。如今唯一確定的是,一面巨大的高牆矗立在眼前,四個人站在高牆前。
「我要打破這面牆!」峻吉握拳心想。
「我就把這面牆變成鏡子吧。」阿收慵懶地心想。
「我要在這面牆上畫畫。把這面牆變成風景或繁花的壁畫。」夏雄熱切地思索。
清一郎則是這麼想:
「我要變成這面牆。我要化為這面牆本身。」
……沉默中,各自思潮洶湧。在這一瞬間,他們成為熱情的青年。而清一郎本身是青年,卻也很喜歡煽動青年。
「對了,難得大家又碰頭了。」清一郎忽然想起什麼似的說,「接下來不管幾年,我們每次見面時,都毫無隱瞞地暢談所有的事吧。最重要的是固守自己的方法。所以不可以互相幫忙。因為即便是些微的幫忙,都是對每個人宿命的侮辱。我們來締結一個同盟,無論陷入什麼困境都不可以互相幫助的同盟。這大概是史上未曾有過的同盟,也是史上唯一恆久不變的同盟吧。因為歷史已經證明,過去所有的同盟都無效,最後都淪為一張廢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