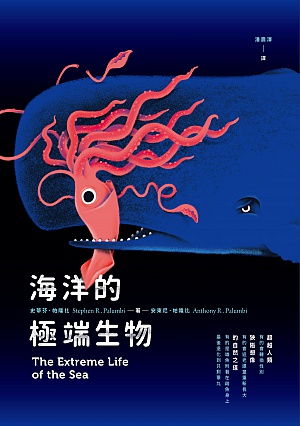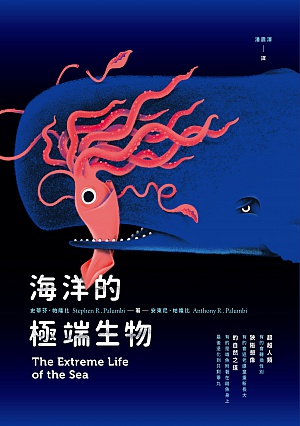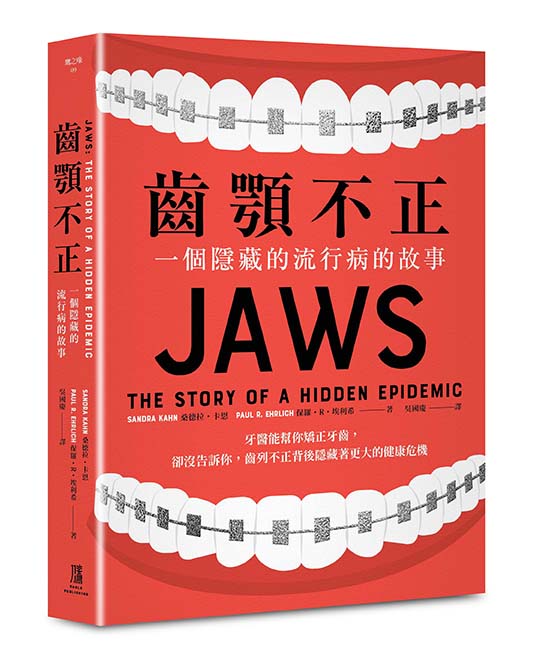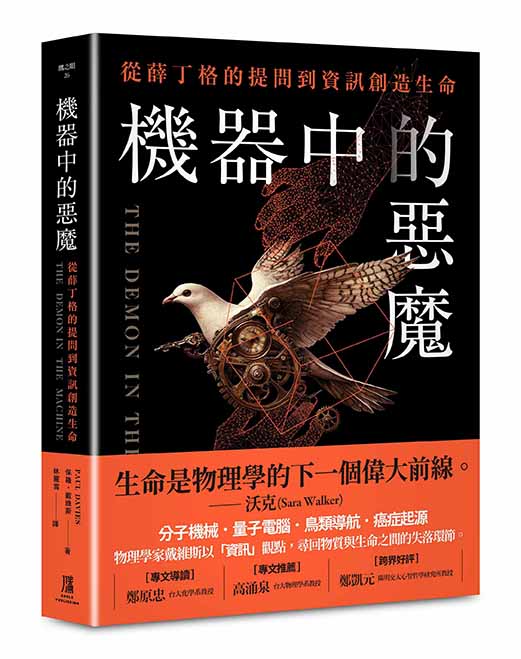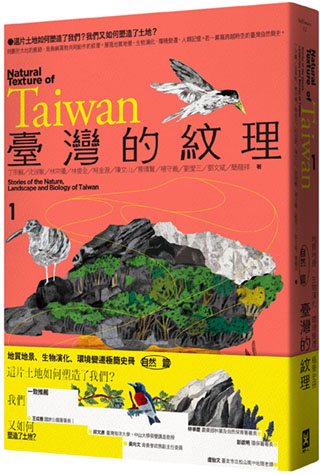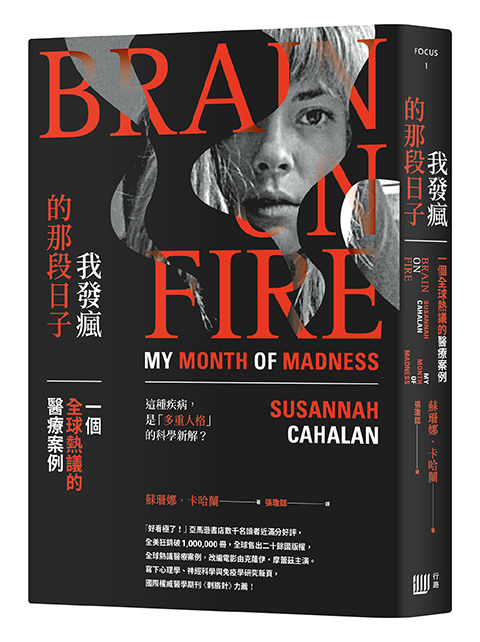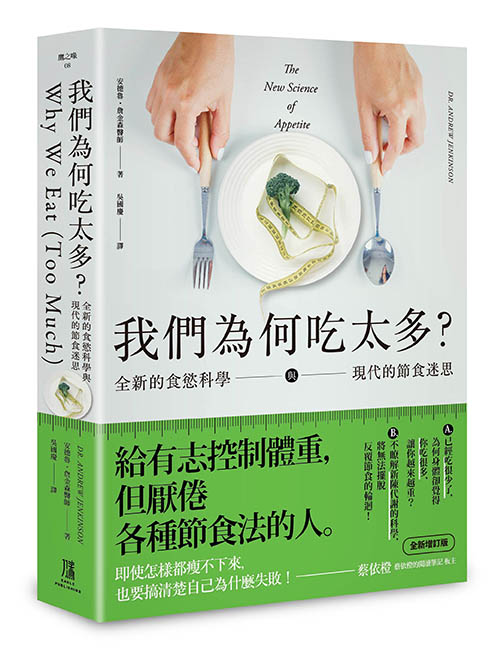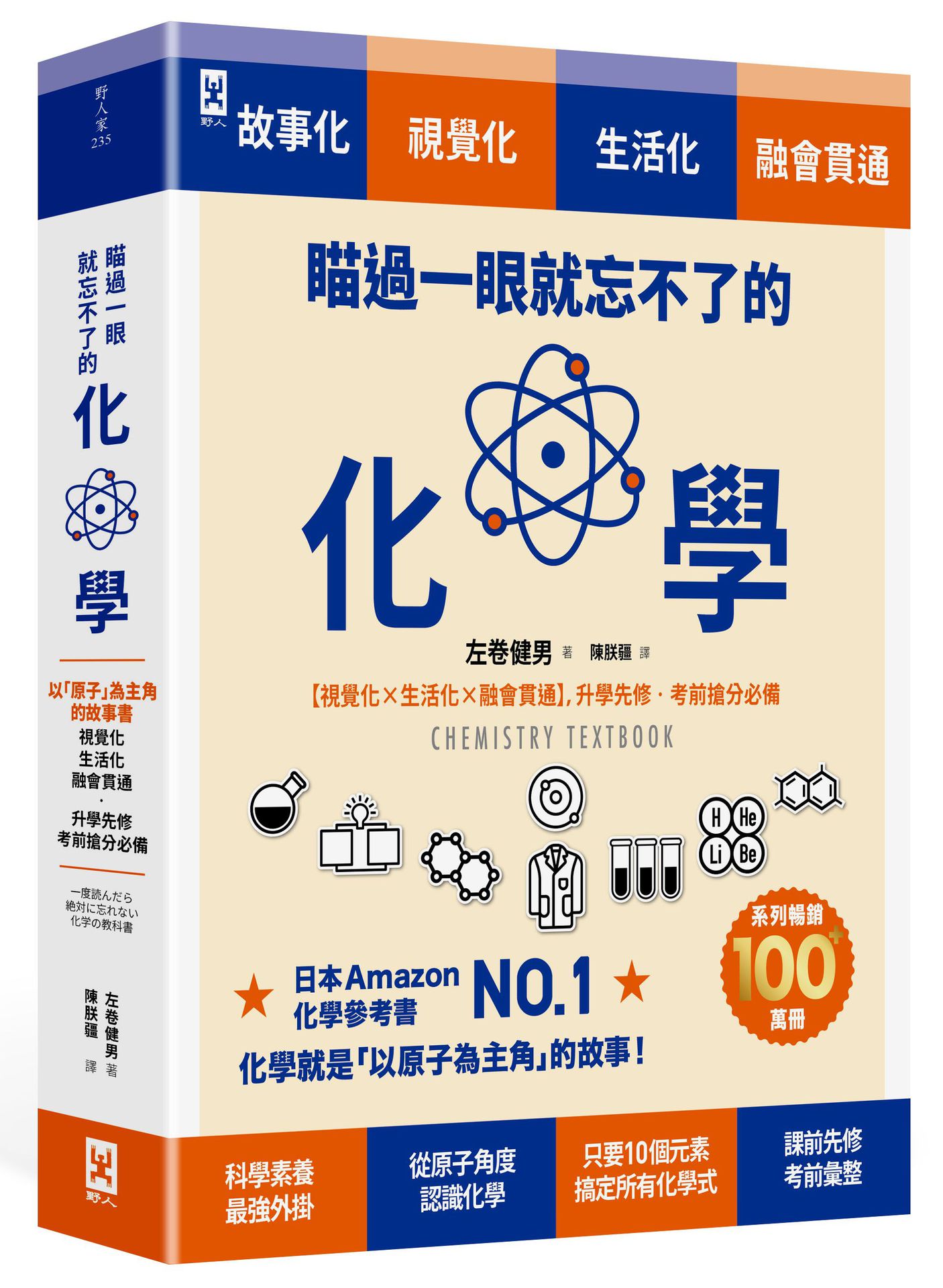楔子 史詩般的海洋
如果你站在海灘上,朝地平線望去,或許你正瞇眼望著落日,或是看著遠方鯨魚噴出的一縷水氣,你能看到將近五公里的距離。如果天氣晴朗,你可能看到二十五到五十平方公里的海面。就許多野生動物的標準而言,這已是相當大的棲地,但全球海洋面積是你望向地平線時所能看到的一千萬倍;此外,在每一平方公尺的海平面下方,平均有超過三公里深的海水。因此,談到海洋最極端的事,其實是它全然讓人難以想像的規模。
在海洋的巨大體積之中(海洋是地球最大的棲地),住了各式各樣的動物、植物、微生物及病毒。的確,海洋孕育了自然世界中最引人入勝且獨特的生物。這些生物佔據了許多不同的棲地,並發展出各式各樣的生存策略;但沒有哪個的生活是特別容易的。從海邊小屋的前方陽台看過去,海洋似乎洋溢著閒適的田園風味,但其中不是過熱就是過冷,微生物充斥,累積了一級又一級的掠食者。
即便如此,極端生物仍靠著奇妙的特化適應,不論是速度、狡猾,還是紅外線視覺,在海洋當中繁殖興盛。美國詩人惠特曼(Walt Whitman)在〈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一詩中的名句:「我廣大無比,我中包含許多的我」用來形容海洋,也貼切無比。漆黑、深邃、充斥異形生物的海洋,讓我們感到畏懼和窒息。海洋帶來的心理壓力,把人的想像力拉回人類與咆哮海洋奮鬥的古老故事。本書的目的是彰顯那些在最極端以及最熟悉的環境中、成功回應了海洋挑戰的物種,也就是那些在海洋當中使用最讓人匪夷所思的生存策略的物種。本書將介紹速度最快、生活在最深、最冷和最熱地點的物種;書裡不但描寫牠們生活當中最微小的細節,同時也包括牠們在海洋當中扮演的角色。
在海平面下方發生的事,要比文學作品描寫的驚滔駭浪航行之旅,或是「鯊魚週」這種製造恐懼的煽情電視節目來得更錯綜複雜、更刺激有趣,也更引人入勝。再怎麼說,除了少數一些大型兇猛的鯊魚以外,大多數鯊魚都算不上極端。只要仔細察看地球任何一塊海面,就會發現迷人且驚人的舞蹈在海洋野生動物當中上演:飛魚疾速穿越海浪前進,快如閃電的鯕鰍(mahi mahi)則在後面追逐;小型槍蝦(pistol-clawed shrimp)射出強大的聲波作為武器,在熱帶珊瑚礁間發出類似遠方傳來的炮竹聲;黑巨口魚(black dragonfish)在海洋深處使用紅外線視覺來偷襲倒楣的過客。生命是一連串反覆循環的掙扎與成功,美麗與醜陋。
過去幾十年間,海洋科學吸引了更多人關注海洋生物;海洋科學使用一整批科學方法和科技儀器來辨疑解難,並得出許多答案。一九三○年,知名的科學家兼探險家畢伯(William Beebe)爬進他的潛水球,下潛進入百慕達的溫暖海水;他只有一個探照燈用來在黑暗中視物,以及一條電話線向海面上的人描述自己看到的東西。如今則有潛水艇、DNA定序儀、機器人化學實驗室,以及小到可以測定藤壺呼吸的呼吸艙。自畢伯的時代以降,我們累積了八十多年的基礎科學知識,要是沒有這些知識,任何重大的生物奧祕幾乎都無法解開。
當你穿戴好包括氧氣筒與面罩在內的潛水裝備、跳進海中,很難預測這些工具會幫助你瞭解什麼,就算是簡單如珊瑚頭白化的問題也一樣。不過有兩樣東西你是必須要具備的,一是面對任何奧祕都感到驚奇,再來就是對任何發現都產生喜悅的火花。本書的目的就是提供讀者這兩樣東西。
當世上最大的掠食生物碰上牠最可怕的獵物
一頭正在覓食的抹香鯨(Physeter macrocephalus)下潛至世界的最底層,在深邃、黝黑的冰冷海水中巡弋。牠孔武有力的肌肉配合溫暖血液的供應,在缺乏氧氣的冰冷海底深處追捕稀罕的獵物。牠不斷重複下潛與升起的循環,在海中一下一上;在每次周期之間,牠在海面上從呼吸孔噴出強勁難聞的喘氣。長壽和巨大的體型給牠帶來耐性:牠放過許多微不足道的小口食物,尋找更有分量的一餐。寬大的尾巴和厚重的肌肉帶來穩定的巡弋速度;比牛眼大不了多少的小眼睛只朝下方,凝視著海水深處。在黑暗中,牠的耐心得到了回報:海面下約莫一公里半,這種世上最巨型的掠食者碰上牠最可怕的獵物。
稱為巨型烏賊的銀色巨獸身長六到十六公尺,有八條短臂,外加兩條末端呈划板狀的柔軟長觸手;後者就像鞭子一樣,可將獵物一把抓住並拉向烏賊鋒利可怕的尖嘴。一般我們在魚市場看到的烏賊,其手臂和觸手上只有普通的吸盤,但深海中的巨型烏賊卻有更精良的配備:有的在觸手尖端帶有可旋轉的鉤子,有的則帶有鋸齒型的吸盤,就像圓形電鋸一般可將獵物的身體撕成條狀。在深海之中,獵物相當稀罕,一旦碰上了可不能給牠們一絲逃走的機會。
我們的雄鯨也抱持相同的想法。讀者可以試想如下場景:一頭四十噸重(譯註:本書使用的噸是美國通用的短噸,合兩千磅,或九百零七公斤,比公噸小)的溫血動物撞上一隻十公尺長、以每秒三公尺速度移動的母烏賊;雖然後者體重只有四百五十公斤,但其中大都是肌肉。這頭雄鯨頭骨前端的作用就像破城槌,或許還會用牠巨大腦部當中的強力回聲定位裝置向前方發出音爆。烏賊停頓了一下,向外伸展並旋轉手臂,就像在黑暗中打開的一把陽傘。兩者相撞的時候,烏賊無骨的身軀吸收了碰撞的力量。牠一面滾動一面反擊,用短臂包住攻擊者的頭部和顎部,觸角尖端的鉤子則在多疤的鯨魚皮膚上畫出長條形的新傷口。對這隻鯨魚來說,這種戰鬥場面早已不新鮮了。
鯨魚感覺到烏賊的手臂落在牠的上下顎之間,於是一口咬了下去,瞬間就咬斷兩隻觸手。烏賊的藍色血液與鯨魚的紅色血液在黑漆漆的海水中混在一起。烏賊如棍般的觸角奮力一擊,打斷了鯨魚一顆牙齒,但絲毫沒有減緩鯨魚的咀嚼。牠的上下顎每開合一次,就造成烏賊又一個可怕的傷害;就算烏賊拚盡全力奮戰,還是毫無勝算。烏賊如刀片般銳利的吸盤邊緣在鯨魚身上撕下一塊塊肉;但就算疼痛,也只是皮肉傷而已。烏賊想逃,但牠半數的手臂不是已經被咬斷,就是只剩殘絲相連;牠用盡力量將水從噴水管射出以求逃脫,但力道還是不夠,因為對手的血液中燃燒著從海面吸入的氧氣,力量實在太強、速度實在太快。鯨魚上下顎的再一次攻擊,造成墨汁與粉紅色碎片齊飛,也就結束了烏賊的性命。鯨魚游離現場,像是調整水平舵那樣調整鰭的角度朝向海面,準備進行下一次換氣;烏賊的殘骸則吊掛在牠嘴邊。
這些史詩記錄在疤痕中,發表在勝利者鯨魚的皮膚上,烏賊在這些傷疤上簽下自己的名字:大王酸漿魷(Mesonychoteuthis hamiltoni)留下平行的長條傷口,巨型烏賊(Architeuthis)則留下近乎完美圓形的傷疤。還沒有人親眼目睹過抹香鯨獵食巨型烏賊的場面,但我們從閱讀鯨魚皮膚的傷疤,以及計算鯨魚胃裡烏賊嘴喙的數目,就可以知道在海床深處,有戰爭正在開打。
這可不是什麼奇思幻想,而是根據一世紀以來的仔細記錄和偶然遭遇所拼湊出來的畫面。此外,還有其他數不清的爭戰與之相輝映,從寄居蟹的連續偷竊行為,到海鞘的生殖器爭奪戰不等。這是古老適應與當下生存之間的鬥爭,這種事每日都在海洋的極端生物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