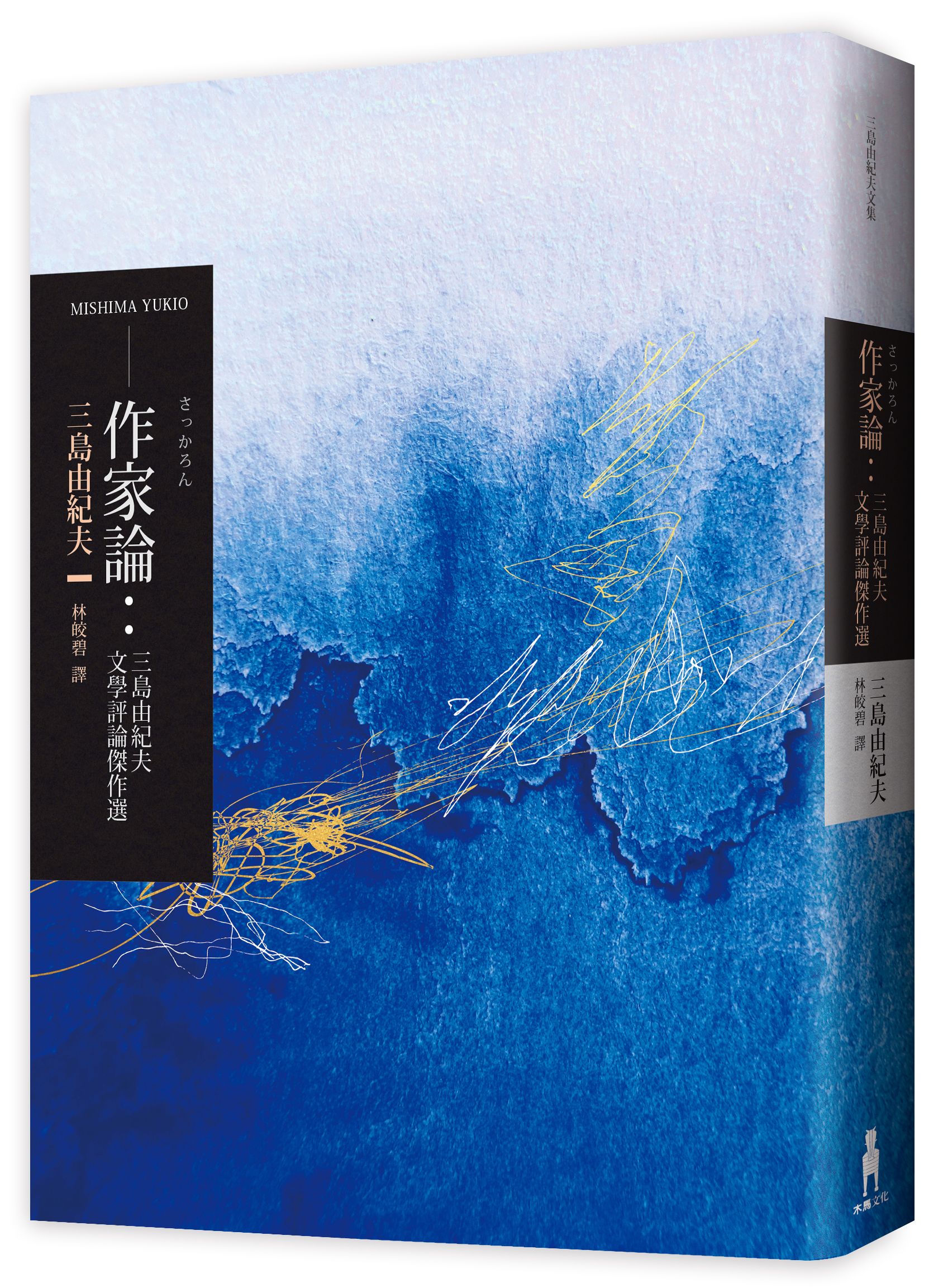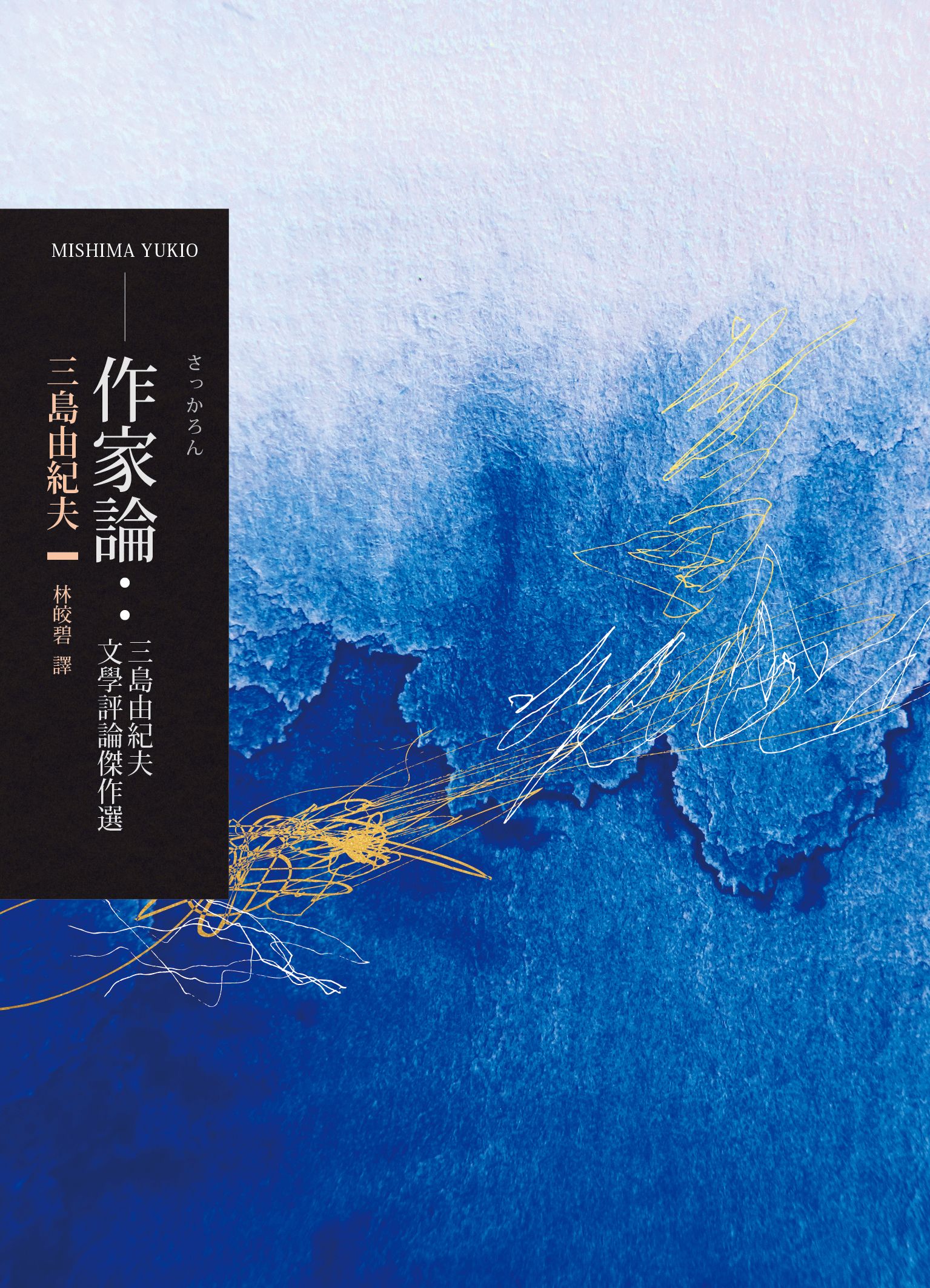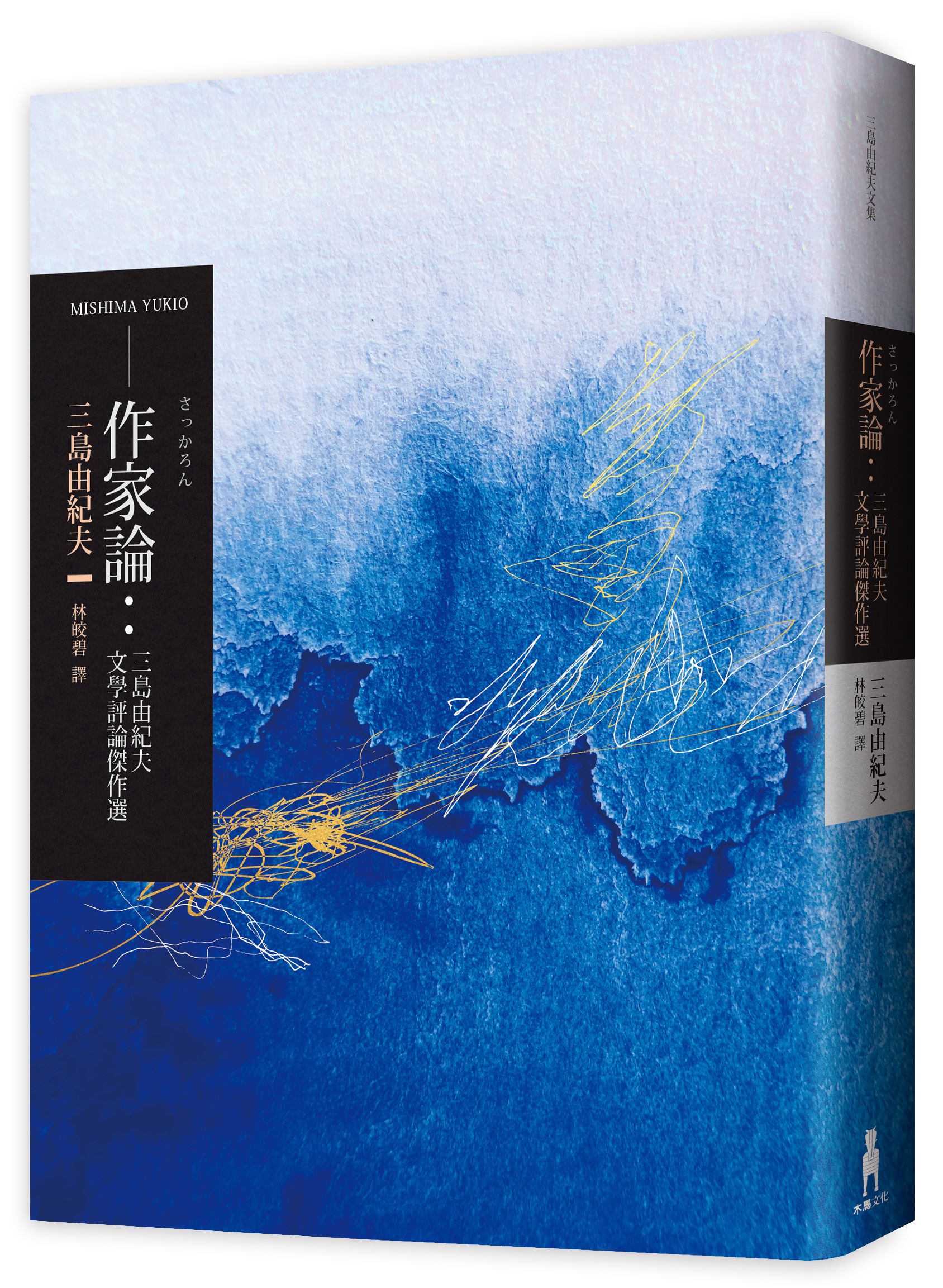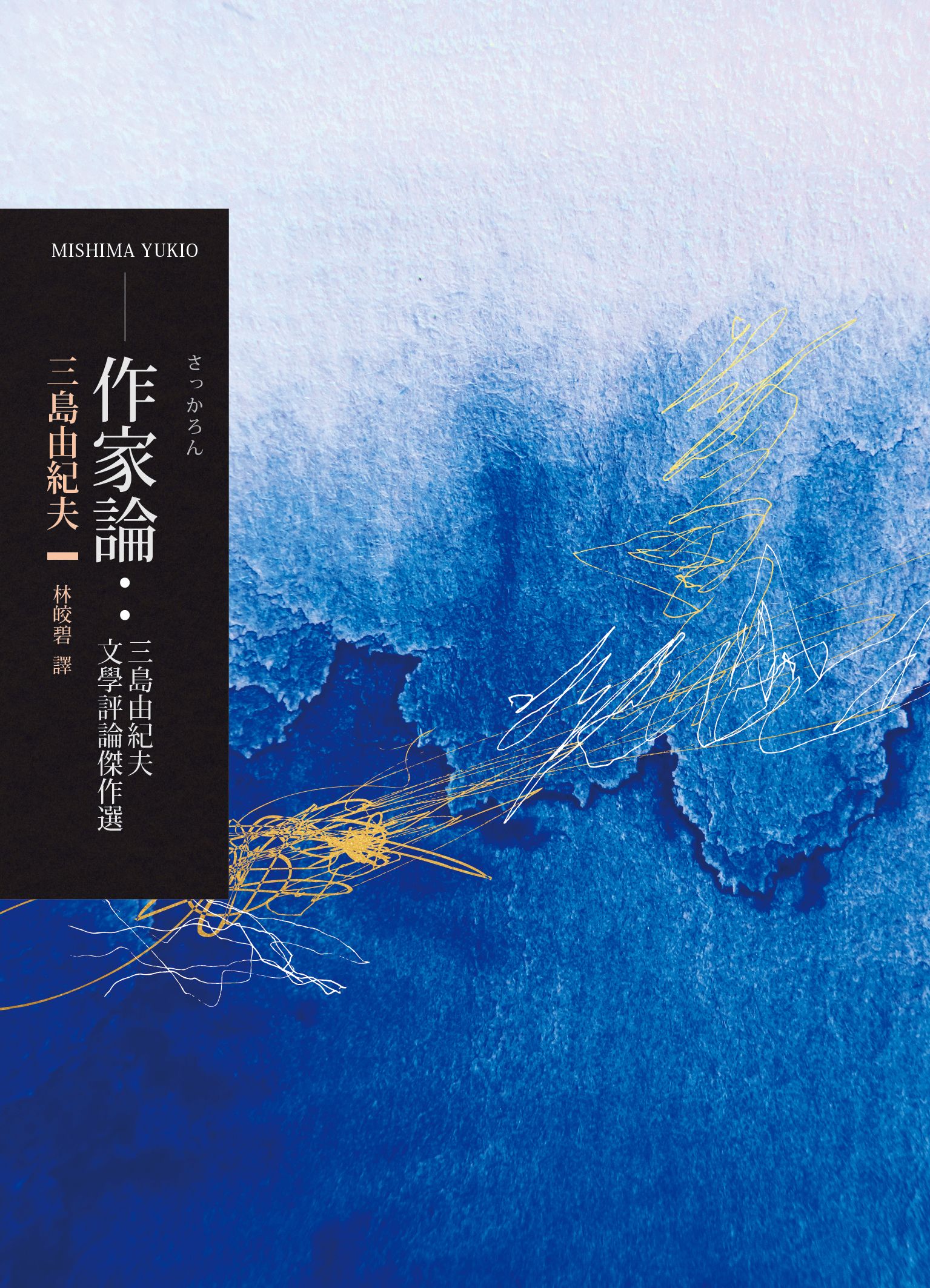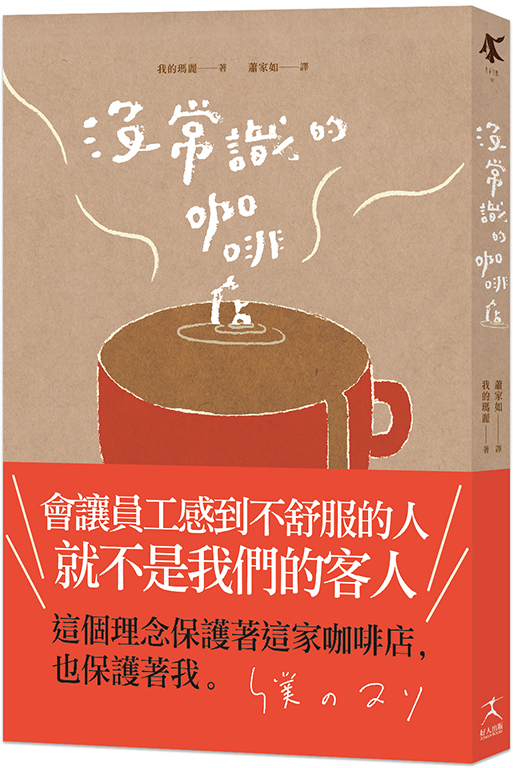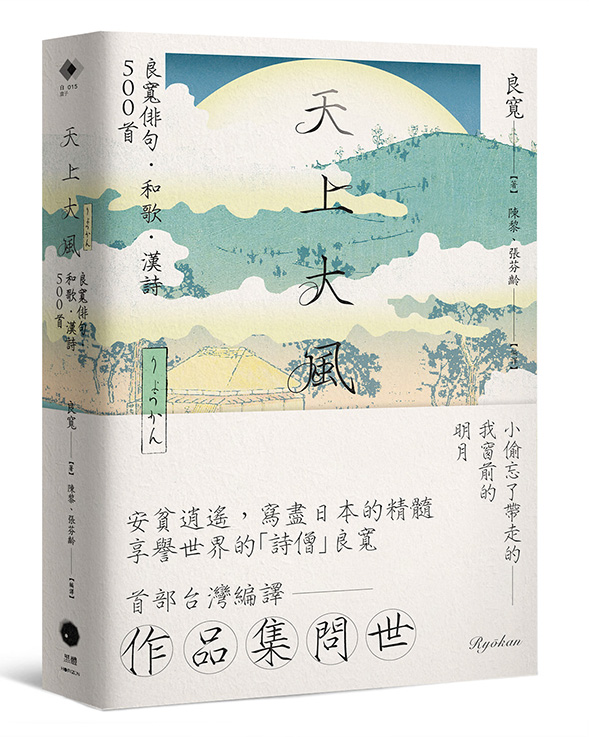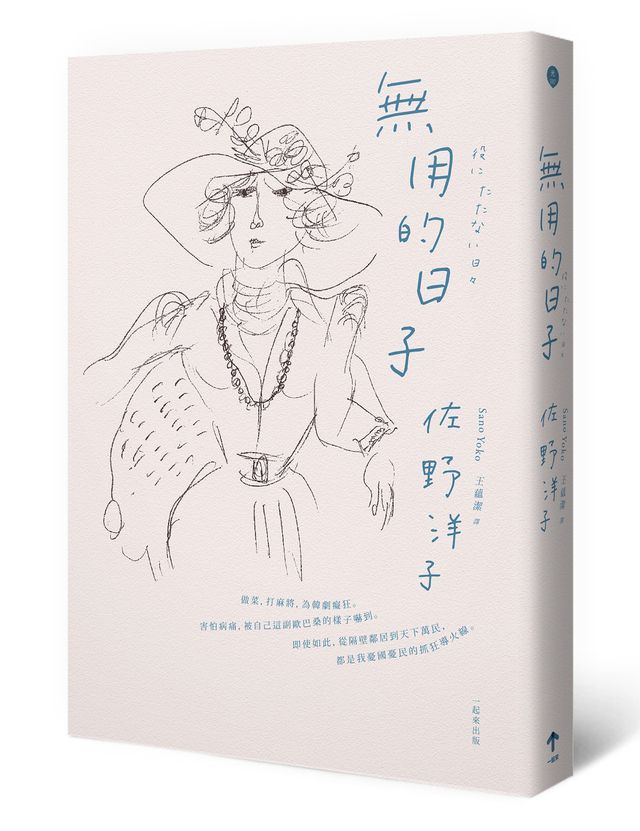「這本書和《太陽與鐵》,為我生涯批評史中的兩大支柱。」
——三島由紀夫
三島由紀夫首度公開一生熱愛的15位日本文豪
「我不讀討厭的作家的書。」————
●備受日本人愛戴的「超人鷗外」的真實形象究竟為何?
鷗外,在失去所有傳說和資產階級盲目崇拜的現代,確實值得以語言藝術家的身分復活。 我相信年輕世代,對於目前充斥在身邊的粗率、雜亂、遲鈍、冗長、懶散、軟弱、下流、可疑的文章,有一天肯定也會感到厭煩,看都不想再看一眼。因為無論任何人,在追求趣味上必然會愈往優雅高尚的方向前進。那時,人們無疑會重新發現鷗外之美,領悟到這才是真正的「帥」。
●明治後日本文學史上的天才泉鏡花,其實有透過作品被美麗女性玩弄的傾向?
鏡花是從明治以來到現在的日本文學者當中,真是罕見的日語(言靈)的靈媒,他的語言體驗遠遠超越他的教養、生活史、時代的侷限。在以風俗為素材的故事裡,鏡花總是固執地保有浪漫主義精神的自我,只追求隱藏在他自我最深處的故事。 那是無與倫比的美麗、無與倫比的溫柔,同時也是充滿無與倫比的可怕之心的熟年美女,和有顆纖細之心美少年之間的戀愛故事。
●從細緻而冰冷肌膚下散發出悚然魅力的川端文學,竟來自棲息在詩人內心深處的日本戰敗命運?
我至今仍難忘第一次讀完《睡美人》的感覺,那像是待在沉沒的潛艇艙房內,感到氧氣一分一秒減少般地喘不過氣。在近代文學中,除了卡夫卡的小說,實在想不出其他堪可比擬之作。小說的場景從頭到尾都在祕密俱樂部的密室裡,是一種精神閉鎖狀態的巧妙象徵。想到這是身為小說家川端先生的地獄,就讓我感到不寒而慄。
森鷗外、尾崎紅葉、泉鏡花、谷崎潤一郎、內田百閒、川端康成、林房雄……從明治、大正到昭和,橫跨三個世代、最終自決而死的日本傳奇作家三島由紀夫,為讀者一一卸下他生涯中敬愛的15位日本文豪的假面,他精讀、細讀文豪們的作品,並將經典文學中精神與美的意識,在本書中做出最生動真實的告白。
推薦
《作家論》與其說是介紹文學諸家,不如說是透過諸家評論這片三稜鏡,反照出作家三島由紀夫的鏡像。
——吳佩珍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二十幾歲的三島由紀夫持續在探索自己的文體,那是拚了命的努力。而在許多年後,他寫下了《作家論》,亦即這本《作家論》可說和其評論集《太陽與鐵》及散文傑作選〈我的遍歷時代〉並稱。
——關川夏央 作家・日本文學評論家
三島由紀夫 Yukio Mishima,1925-1970
本名平岡公威,出生於1925年1月14日,自幼身體孱弱,在出身貴族的祖母溺愛下成長,養成其孤獨、敏感而纖細的個性,及對日本傳統藝能之美的嚮往,帶來一生不可抹滅的影響。
16歲即發表作品《繁花盛開的森林》,展現其美學意識及華麗的文體,被視為早熟的天才。引薦他跨進文壇的恩師清水文雄為其取的筆名「三島由紀夫」從此陪伴他一生。
1947年東京大學法學部畢業後,任職於日本大藏省,隔年為了專心從事寫作而離職。1949年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假面的告白》在文壇嶄露頭角,此後創作不斷,成為日本20世紀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三島不僅在日本聲譽卓著,在國外也享有極高的評價。暢銷作品《潮騷》為其打入美國出版市場;展露獨特洗鍊美學意識的《金閣寺》將三島的文學事業推上高峰。曾三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被譽為是「日本的海明威」,也是日本當代著作譯成英文等外國語版最多的作家。
除了小說、散文與詩詞等文學創作,三島在戲劇方面也展現驚人的才華,寫了許多優秀劇本,致力於日本古典戲劇能樂和歌舞伎的現代化。同時還擔任電影演員,甚至在以自己小說改編的電影中特別演出。
1970年11月25日,三島完成力作「豐饒之海」四部曲最終卷《天人五衰》後,即與四名楯之會青年成員前往自衛隊基地挾持總監,鼓動政變未果,當天便切腹自殺,結束其壯麗的一生。
主要著作有《假面的告白》、《潮騷》、《金閣寺》、《禁色》、《美德的徘徊》、《愛的饑渴》、《女神》與「豐饒之海」四部曲等。
林皎碧
淡江大學東語系畢業,日本國立東北大學文學碩士,專攻日本近代文學。
譯有《作家論:三島由紀夫文學評論傑作選》、《行人:我執與孤獨的極致書寫,夏目漱石探究人心的思想代表作》、《從此以後:愛與妥協的終極書寫,夏目漱石探索自由本質經典小說》、《新戀愛講座》、《羅生門:闇黑人性的極致書寫,芥川龍之介經典小說集》等。
著有《名畫紀行:回到1929的公會堂》。
導讀 文學諸家三稜鏡中的三島由紀夫鏡像/吳佩珍
森鷗外
尾崎紅葉/泉鏡花
谷崎潤一郎
內田百閒/牧野信一/稻垣足穗
川端康成
尾崎一雄/外村繁/上林曉
林房雄
武田麟太郎/島木健作
園地文子
後記
解說 三島由紀夫的「作家論」與「文體論」/關川夏央
谷崎潤一郎
對於母性如此醇化的憧憬,在性慾不經意入侵的剎那,眼前的女人立刻變身為如同《刺青》或《春琴抄》的女主人公般,美麗的肉體中潛伏著一種陰鬱惡毒的魔性,這正是谷崎文學中獨特的女性面貌,實在有趣極了。
不過,仔細觀察這些女人的惡,與其說是女人與生俱來的惡,毋寧說是在男人要求或期待下所產生的惡;這種惡不過就是「男人性慾的投影」,不是嗎?若更深入思考(可能難免會被認為想太多),谷崎文學並不像世人所理解那般完全肯定或解放官能。谷崎在無意識的內心深處還是堅持古老的禁慾精神,甚至認為一切的性慾都是惡,並且把那種惡投射在作為性慾對象的女人的性格當中;因此他筆下的女人就必須惡毒、殘酷,讓充滿性慾卻想否定性慾的男人完成自我懲罰的機制。於是,所有的一切不都是為了讓此機制順利運作,以滿足自我懲罰欲望為目的所構思出的戲劇?而女人不就只是這齣戲裡的一個道具?
不過,女人愈被視為道具,就愈美麗,愈是成為被崇拜的對象;至少谷崎在那樣的戲劇裡,透過崇拜女人的肉體,同時崇拜了自己的性慾——即自己的惡,發誓永遠忠於〈神童〉的主題。這種對於惡的矛盾,絕對不會發生在已濾淨官能愛、「憧憬母親」的世界裡。
在谷崎這種性慾結構之下,衰老不是那麼需要害怕的問題。谷崎的受虐癖打從一開始就和自戀性格缺乏親密感,以致他終其一生不具有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所謂的「陽具自戀」(phallic-narcissism)性格。對谷崎來說,「陽具自戀」雖是必然展開的行動和戰鬥,其結果卻又繫於當中飛蛾撲火般的光榮感,因此不過就是個礙事之物罷了。
《春琴抄》裡佐助刺瞎自己眼睛的行為,雖然微妙地暗示著「去勢」,然而性的三昧境最初即是在跪拜絕對不能性交的愛情中的夢裡實現。如此一來,衰老就不再那麼具悲劇性,毋寧說正因衰老=死=極樂(nirvana),反而很接近通往三昧境的道路。谷崎身為一名小說家,他的長壽果然具有藝術上必然性的長壽。因為這位神童從一開始就走上為達到知性的極限之境而早逝的相反道路。
衰老同時意味著作家思想衰亡的作家,可說相當悲慘;而肉體的衰老若和其思想及感性澈底違逆的作家,也實在很悲劇(想到我自己,不由得毛骨悚然)。連海明威、佐藤春夫都是那般悲慘的作家,我自己先姑且不論,包含林房雄、石原慎太郎也肯定生活在那樣的預感之中。有趣的是,這類屬性的所有作家都隱身在「陽具自戀」人格之下。
谷崎的自戀,完全來自他身為大藝術家和偉大天才的自負。他在所有藝術上的心血,以至創作上嚴格的道德標準,都完全建立在這種自戀性的自我確信之上。
另外,在他的性慾結構裡,性愛的主體就是刺傷自己的雙眼、肉體趨近於零的狀態;愈是處在陶醉和恍惚,對方的美、豐盈和無情也愈發明顯。換言之,性愛的主體若捨棄肉體,體現在性愛觀念本身,愈能提昇眼前之美的純粹。他在晚年作品《鍵》所描寫的衰老,即是存在於以佐助的行動為原點、自然延伸的脈絡上。這種思想在《瘋癲老人日記》中臻至頂峰,肉體在夢見佛足石的恍惚間成為死的一部分,肉體在醫生的冷酷分析下歸零。這部小說的結尾提出醫生的診療紀錄,有人認為是畫蛇添足,我反倒覺得是誤解了谷崎的肉體觀。
崇拜女體,崇拜女人的任性,崇拜女人所有反理性的要素,其實帶有一種難以言喻的輕蔑。谷崎文學與女性解放思想有著一段非常遙遠的距離。他當然不會否定女性解放,不過他感興趣的僅僅在於女性解放後,發育得生氣勃勃的美麗女體而已。
至於「性慾」,崇拜和輕蔑可能更接近它的同義語。不過谷崎的情況不同,這種輕蔑源於他自身的矜持,而那究竟是怎樣的性格呢?那是知性者、觀察者、非肉體的驕傲呢?或只是男人的驕傲?又或是天才的驕傲呢?谷崎在《食蓼蟲》曾引用淨琉璃的一句話:
「妻子的心中住著惡魔,還是蛇呢?」
而這顯然象徵著男人對已無法激起自己性慾的女人不得不展現的冷酷。我必須說這在谷崎作品中相當罕見地呈現所謂「性教養小說」的面貌,也就是圍繞在失去性愛的夫婦及其西歐知識分子的家庭生活;有一名活潑的白人娼妓,也有一名近松門左衛門的淨琉璃中人偶般的老派女人登場,主人公則有如擺盪在西歐和日本之間的鐘擺,終究受到日本式平靜無波的性慾(儘管輕蔑)所吸引,小說於此告終。阿久原是一個最愚笨、最沒有自我的女人,卻因身為女人,而成為最聰慧的女人。
不過這部作品中最精采的寫實場景,還是在開頭數章主人公對妻子性趣缺缺的描寫。男人即使被激起性慾,心情仍搖擺在輕蔑和崇拜的矛盾之間;而男人一旦失去對女人的性慾,將會變得多麼冷酷啊!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一個典型。儘管連精神上的殘酷都繚繞不已,不過原本這種「殘酷」就並非虐待狂式的愉悅,只能名之為貴族式的冷酷。
和這種性冷淡的地獄比起來,世界上所有的事物盡是歡樂和喜慶。對谷崎來說,女人無論如何都是創作那兼具輕蔑及崇拜的戲劇的要素,而且必須充滿生氣、活力和歡笑。若非如此,女人不具任何意義。
相較於室生犀星那般,只要是女人,無論任何女人,都能因發現難以言喻的女人的內心世界而感到愉悅的作家,谷崎絕對不是所謂喜愛女人的作家。抽象概念上的女人、普通及非特定的女人,都無法激發他的靈感。對他來說,女人無論如何要符合他對美的喜好,而且得強烈喚起他的性慾,這時女人才能真正散發出迷人的光輝,極樂淨土才會出現。
最後,我希望所有在日本從事作文教育者務必閱讀他的《文章讀本》。在這本書裡,谷崎毫不偏頗,而是以公平客觀的視角介紹古典至現代各種文章的不同魅力,同時溫和地主張自己的喜好,對於標準失衡的日本作文教育正是一劑最好的特效藥。我自己也有類似的經驗,小學時被迫接受如報告書般單一、務實的錯誤的作文教育;中學時讀了《文章讀本》,才首度踏入文章的廣闊原野,並體驗到一股說不出的喜悅。
川端康成
一
關於川端康成,援用尼采的話來表達也許不太適當。不過尼采在《尼采反對華格納》中,寫到如下有關華格納的話,奇妙地很適合川端文學。
「他真是擅長描寫微小事物的巨匠。」
尼采又進一步如此說道。
「不過他(華格納)不想當巨匠。
他的性格毋寧更喜愛高大的牆和大膽的壁畫。」
後面這句話和川端文學恰恰相反。川端和華格納不一樣,川端先生毋寧更是「想當巨匠」,而且其性格不喜「高大的牆和大膽的壁畫」。他不喜歡大而無當的構圖。
尼采所攻擊的是華格納的觀念和和虛榮心、和「對自身的不忠實」,以及非常莫大的愚蠢的本性。若是那樣的話,川端就是尼采所期待的「華格納的理想版本」:「聰敏」的華格納,了解熟知自己的華格納。
太熱中這種比較其實並不好,不過川端文學中還有諸多令人想起華格納的特質。例如描寫死亡和性愛之間具可怕一致性令人戰慄地合而為一的〈睡美人〉(眠れる美女)中,具有華格納的模糊不清曖昧以及把讀者拉到地底深處的魅力,卻不見華格納常見的龐大風格,取而代之的是以「描寫微小事物的巨匠」的規範,才能從節制中產生緊張感。
川端的聰敏究竟是什麼?肯定任誰都很難以說明這點。若說是和華格納正好相反的聰敏,即忠實於對自我己本身的忠實和了解熟知自己;但在川端眼中,忠實於自我己本身忠實之類其實並並非最高準則,反而像是出自無可奈何。對先生來說,了解熟知自己和拋棄自己簡直是同義詞。
川端的聰敏可歸結於是從結果上的聰敏才可了解的特質,若以此為前提來看的話,我認為其聰敏所獲得的最大成果,就是他不曾會受任何觀念所欺騙吸引一事。
若要列舉那些無法欺騙川端的不被許多觀念數所目吸引,若要列舉,有如百鬼夜行之多:包括了近代、有近代小說、有共產主義、有新感覺派、有自我意識、有知性、有國家主義、有存在主義、有精神分析、有近代的超克(譯註2)、有思想等等。
現存代的的文學家中,即使是暫時也好,是否有人能不被在前述觀念當中的至少一、兩種所欺騙呢?,可是只有川端就連片刻也不曾被任何觀念所騙吸引!
一般說來,雖然聰敏往往會阻礙藝術創作,可是川端的情況不同卻是例外。通常人們冷靜描寫陶醉時,不是把陶醉描寫得出僵硬的陶醉,就是寫得出過度誇張的陶醉,總會陷入兩者之一,可是川端卻學會了體會冷靜同時表現冷靜的心與也知道描寫陶醉的祕訣。由於他不受任何無論觀念所囿都無法吸引他,所以被世人以稱為「小說名人」來稱呼他,可是他的的小說卻從未被和所謂小說的概念、近代小說的概念所累都沒有絲毫糾纏。因此一名讀過英譯版《雪國》(雪国)的美國人,感嘆自己不曾讀過如此獨特的小說,我認為這自是有其道理的。
即便如此,他的作品充滿小說的獨特魅力也是事實。川端闊達而隨興的心性因為和其創作的苦澀為伴的那種豁達精神的投注相悖,在使得每一篇作品中都給予讀者非常精緻、大膽且不可思議的風味而予人奇妙玩味。令人感到滯悶的美麗世界,可以直接和那道悠哉寧靜的心境落差相接合。
川端是最遠離不具威嚇性的特例中的天才,而不過他確實一直保有陰森和純潔的氣息。尤其是戰後的作品中有一股獨特的寒意,那是從細緻而冰冷的肌膚底下所散發的悚然魅力,來源自日本戰敗的命運棲息在詩人的內心深處的日本戰敗命運。
「我不曾經歷西洋風格的悲痛或苦惱的經驗,也未曾在日本也不曾看過西洋風格的虛無與或頹廢。」(〈哀愁〉)
主人公讀了超過半本《源氏物語湖月抄》(譯之後迎向敗戰,而川端在關於獨自說出滅亡的哀痛,還有來自以那種哀痛本身所衍生的哀來慰藉日本人的獨特慰藉的論述之心境後,出現這段大膽的直言的場並非偶然。
所謂「我把日本的山河看作靈自己的精神魂,在你之後活下去。」
這是「獻給橫光利一哀悼詞」的最後一句,之後川端便忠實地身體力行。
後記
收錄在這本書的作家評論,除了已出版的《林房雄論》外,全都是為各種文學全集所寫的解說。我原本並不喜歡依靠解說來讀近現代文學的風潮。自己卻又勇敢接受撰寫解說的邀稿,態度上看似矛盾,實則是反過來利用自己不喜歡的風潮,一來這是再次玩味和重讀諸家名作的機會;再者也是借解說之名來累積作家論的稿件,所以才會接受。因此我寫的解說,以解說來看從一開始就不親切、也不夠完整,上的聯繫是他自己完全合為一致認同,既沒有文學史的敘述,也沒有介紹作家的個人經歷,而是直接緊抓住作品,主要著眼在透過作品,使每個作家的特徵浮現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我會故意以任性的態度,也未必注意到是否公平。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新潮社日本文學《谷崎潤一郎全集》的解說,我為了避免和其他全集的解說重複,把不過是短篇的〈金色之死〉當作焦點,始終就〈金色之死〉進行論述。為什麽呢?因為我打從一開始,就打算採用這本書中評論作家的方法。
把《作家論》當成文學評論來讀的人,也許會質疑我對所有作家都太過肯定。不過以我頑固的態度,一概不接受不喜歡作家的解說邀稿,真是無可奈何。這當然不意味著未收錄在本書的作家我都不喜歡;如果喜歡的作家出了全集,在那之前沒被請託撰寫解說也沒辦法。
如同刑警對待嫌疑犯一般,從最初就以冷淡猜疑的眼神看待諸作家的《作家論》,未必都能夠成為犀利的批評。若是在非讀不可的狀況就另當別論,一般來說,我不讀自己不喜歡作家的作品,只讀喜歡作家的作品。因為是喜歡的作家,他的作品也會讓溫暖的心胸敞開。我相信自己一旦投入作品中,完全就依照作家的引導,以無私的態度在作品中散步,若不如此原本所謂的文學批評也不會成立。有很多偽裝成非政治主義、卻大費心思做出政治主義性的批評。何況是來自意識形態( ideology)的批評,那些就不在討論範圍。
這就是我的基本態度。我從來不曾有過從一開始就積極否定之類的想法。從否定當中挑選出肯定的,這種事倒是有過。而一旦發現從中挑選出的作品有被批評的意義,就到了本書的目的。
另外,本書與可稱作我個人評論的《太陽與鐵》,同樣是我少數評論工作中的兩大支柱。
昭和四十五年十月 三島由紀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