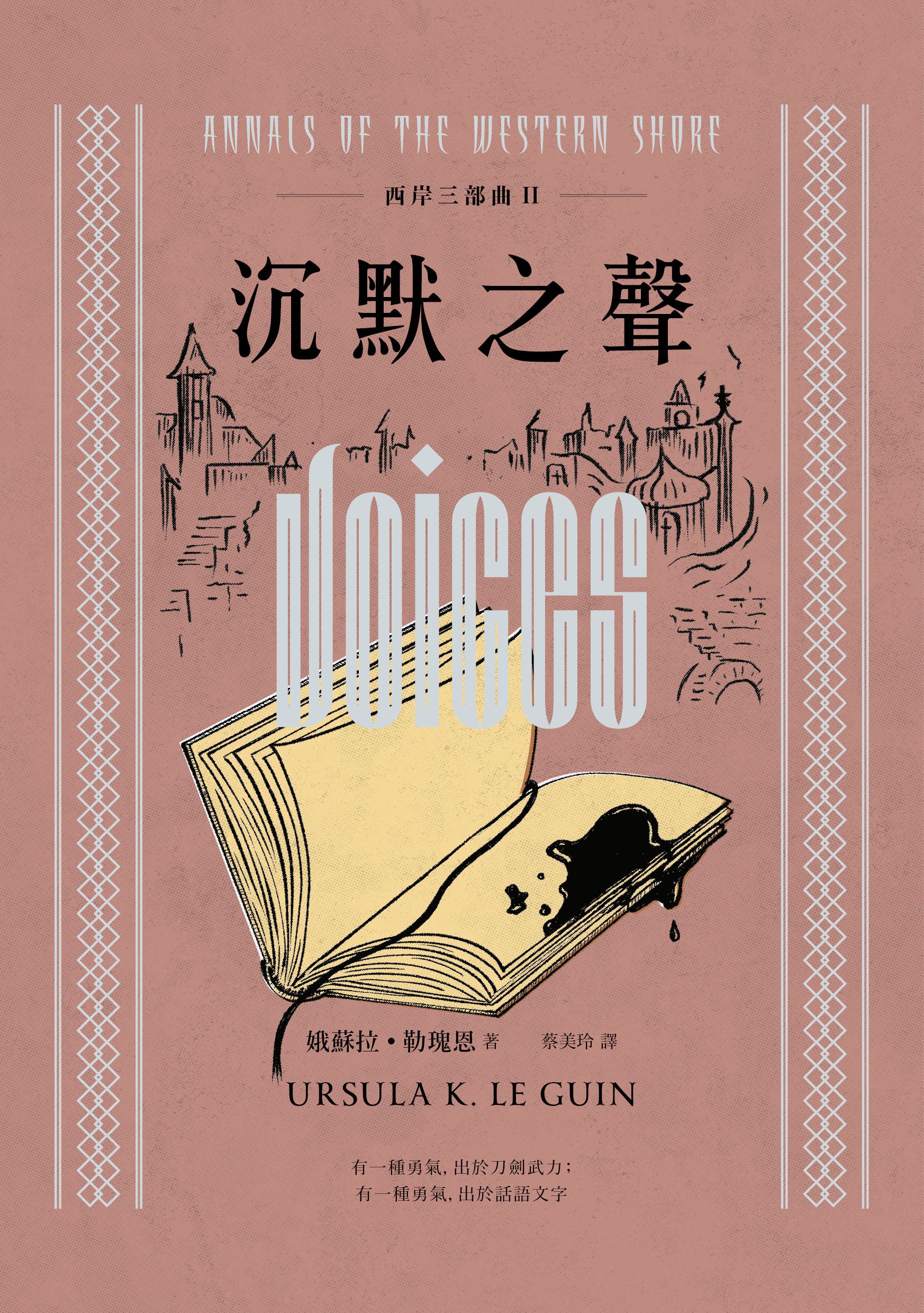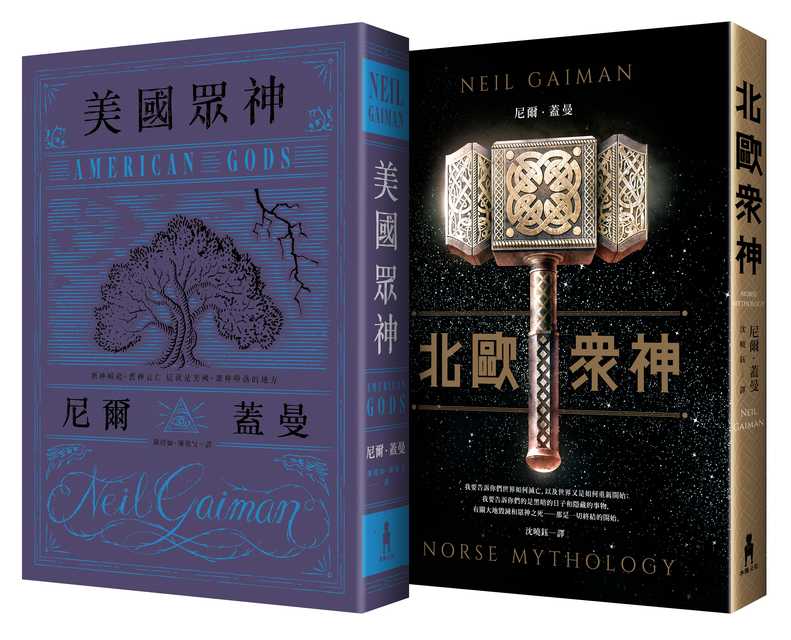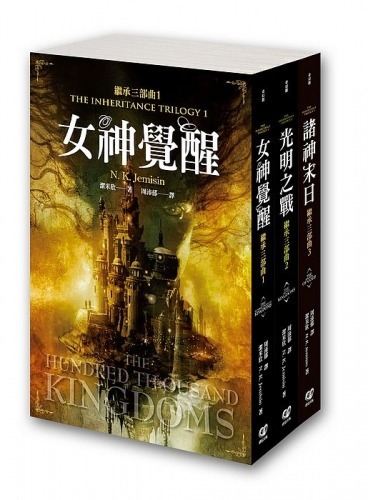未來可以預測,人類則否。
影視化決定!
《星際效應》《西方極樂園》強納森.諾蘭強勢改編
非典型時間旅行,虛擬實境謀殺案;
軀殼與靈魂的哲學答辯,復古與未來的超脫想像。
你我相遇的瞬間,
我們的未來就開始朝不同方向前進。
芙林接下高價打工代班,在虛擬遊戲中監視特定對象。然而,執行任務過程中,那名對象卻以駭人的方式遭到謀殺。由於畫面真實得觸目驚心,她也從未聽過這款遊戲,緊接著又有不明人士追殺她與家人。如果只是遊戲任務失敗,為何會引發如此嚴重的後果?
在困惑中,幕後真正的雇主現身,希望芙林以目擊者的身分協助調查,她才得知一個驚人事實:這名雇主與其企業集團與她分屬不同時空,她所目擊的是一場發生在數十年後、甚至位於另一塊大陸的殺人事件。而她,將透過未來科技,在未來世界以擴充實體的方式現身,揭開這起案件背後的驚人真相!
在可預見的未來裡,我們發現,原因都出在人身上――
那些滅絕,那些死亡,都與人有關。
---
奠定電馭叛客類型的大師吉布森在某次訪問中表示,本書想討論的是科技狂飆後的世界。當技術先進到某種程度,反噬是否成為必然?當他以《神經喚術士》超前眾人,將所有堪稱前衛的概念遠拋在後。而在十數年後,我們的現實才終於追上這位大師的腳步。然而他從未停止思索未來,仍持續對讀者的腦細胞發出挑戰書。吉布森的文字一如他的故事,不受時間、空間甚至文化之限,自由地在綜合交錯的時間軸遊走,更於科幻的硬體架設中填入論靈魂與存在的哲學血肉。當你把神經接入另一具身軀,在鏡中看見的會是什麼?――或說,那真的是你嗎?
各界推薦
科幻迷人的地方在於如何轉化現實生活;每部科幻小說都是對我們當下生活的變形。
――譯者 黃彥霖
吉布森的小說像是在創造未來,而非想像未來。
――《紐約時報》
關於近未來的主題,無人能超越吉布森。
――《華盛頓郵報》
一如吉布森早期開創性的佳作,本書帶有同等耐人尋味、栩栩如生的未來畫面,你幾乎能嘗到、嗅到甚至感覺到,並且在一瞬間深深相信其存在……因為吉布森最擅長的就是描繪深受過去糾纏的未來景象。
――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
吉布森是獨特且天賦異稟的科幻作家,也因此受人崇敬。但他也長於想像各種社會層面與心理層面的情節。《邊緣世界》編織出一個創造力十足且真實得嚇人的未來。
――《星期日泰晤士報》
最精巧且需投入全副專注力的一本作品。回歸舊主題的同時也往前推進,吉布森也持續進行一直以來的實驗,幫助我們以全新視角看世界――就算只那麼一瞬間。
――《洛杉磯書評》
猶如一趟經過精心設計的驚悚雲霄飛車――或十四行詩、或四重奏。而且一旦從車上下來,就立刻想再上去轉個一輪。
――軌跡獎
吉布森能將文句打造出一股獵奇又美麗的氛圍。
――《舊金山紀事報》
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
以打字機創作《神經喚術士》(Neuromancer),卻寫下、定義了科幻文學的「電馭叛客」(Cyberpunk)類型,並創造「網路空間」(Cyber Space)一詞,更拿下科幻文學界三大獎:雨果獎、星雲獎與菲利普狄克獎,創下至今無人打破的紀錄,更暢銷六百多萬冊。
在尚且無人理解電腦或虛擬實境的時代,他的小說打造出近未來的驚人景象。除去躍進未來,他更與另一位知名大師布魯斯.史特林(Bruce Sterling)合作,回溯工業革命時電腦的前身,寫下小說《差分機》(The Difference Engine)。至此算是完全奠定他的大師地位。2014年,他跳脫舊系列,以電玩遊戲的背景創作全新小說,以硬派筆法將政治權謀融入懸疑殺人,並放置在一個絕對科幻的架空未來,佐以穿梭時間的情節,讓讀者墜入他筆下炫麗的科幻世界。
威廉.吉布森目前與妻子一同住在溫哥華,至今仍創作不綴,2020將再度推出新作《Agency》,描繪一個希拉蕊當選總統的未來世界。
黃彥霖
現職翻譯與文字工作,譯有《人類補完計畫:考德懷納‧史密斯短篇小說選》,主要領域為科/奇幻小說、文學、資訊與流行文化。山的初學者。聯絡與指教請寄moonvariant@gmail.com。
白之衡
東吳大學英文系與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畢,從事翻譯工作已有五年,原則上什麼都翻。
相信翻譯是生命中所用語言的濃縮與集合,所以翻譯之餘也要認真吃飯、用心逸樂、好好當人,這樣工作時才不會忘記怎麼說話。
(注意!本文提及故事內容!)
翻譯後記:彷彿一個數項終於平衡了整個方程式
譯者 黃彥霖
以前都以為科幻小說比較接近大眾文學,理當擁有廣大的讀者群才是,不過後來聽從事出版業的朋友說了之後才知道,其實台灣算不上科幻閱讀風氣發達的地方。縱使如此,我知道仍有像是臺大科幻社、中華科幻學會這樣的社群,以及許多獨立的個人(例如科幻翻譯的大前輩卡蘭坦斯或是評論家馬立軒),不斷透過出版以外的各種管道分享自己在這個領域裡的心得、脈絡,讓有興趣的人知道哪裡還有哪些作品可以看。
好多年前第一次聽到吉布森的名字,就是在這樣的管道裡。那是一篇介紹吉布森成名作《神經喚術士》的文章,現在已經忘記名字的前輩仔細爬梳了吉布森的崛起過程,講述他如何與《銀翼殺手》、《阿基拉》一同在幾年裡拓展出整個賽博龐克次文類的疆域。你現在能在網路上找到的吉布森介紹文章想必更多了,或許細數他的得獎史,又或者稱頌他如何神預測未來科技發展云云。不過以閱讀經驗來說,這些都只是背景知識而已,我想應該沒有人在閱讀時會在腦中想這些才是;追根究柢,一位科幻作家之所以能得讀者喜愛,總得作品好看才行。
在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始終震撼於吉布森所展現的「精準」。這個特質也許會影響他的用字選擇,決定他如何掌握、呈現知識和角色,同時更顯現在他如何從看似散落各處的細節裡堆疊拼湊出更大的命題。
吉布森在書裡描述了兩個擁有許多「替代品」的世界,不斷提起「冒牌」這個概念。所謂的「假冒」就是讓表面與實質不對等,是刻意抄襲的複製行為。有時這樣的抄襲是不得不,例如芙林的手機,或者梅肯印的所有東西,甚至包括那些傳輸皇冠,反正只要可以用,是不是正牌又有什麼關係呢?所謂的「真品」一點好處也沒有,只是讓你繼續消費而已。但在奈瑟頓的世界裡,「仿造」代表的意義就不同了,他們假冒為的是獲得更好的生活品質,甚至是為了讓整個社會重返往日榮光(只不過有些人居心不良)。他們有假造的袋狼,有材質表裡不一的衣服布料,對奈瑟頓來說,說謊是工作,甚至是本能,掩飾太平讓鏡頭上好看就好;而無論是廢青列夫、公務員瑞妮或是姨媽簇擁之下的洛比爾,也全都得裝出不屬於自己的那一面。吉布森從各種角度列舉了仿冒的樣貌,敘說為何仿冒有時是種謊言,但同時也在這裡找出了兩個世界的交集:書中這群主角之所以假冒都是不得已的,他們套上冒牌的身分和手段是為了要在權力體制上鑽出一個漏洞,好從中開脫,去保護生活裡一小塊自由的選擇權。
隱私是這小塊自由的其中一部分,而隱私是權力的附屬品,這個道理即便在我們看來也是既弔詭卻又理所當然不過。網際網路曾被視為追求自由的工具,但不過一、二十年而已現在卻彷彿就要翻盤,曾經用來突破桎梏的工具成了另一種龐大的控制體系,讓人到處都得提防自己是不是又被竊聽了什麼。這是反烏托邦類科幻小說不斷演繹的重要元素,而吉布森在此又重新為我們示範了一次:等到時間來臨,連氣候變遷都會站在權力者的一方,除非我們有所作為,否則別奢望整件事會有放緩的趨勢。我們就像恐龍,或像袋狼,只有最能賺錢的那隻會活下來。
科幻迷人的地方在於如何轉化現實生活。每部科幻小說都是對我們當下生活的變形,調動某個變數、左轉四十五度、背對它或面對它。事實上所有的文學都是如此,所有藝術也都是如此。芙林所在的時間點在我們之後,但你可以從科技、社會現象、思考方式,清楚地推敲出他們與我們世界之間的發展脈絡,然後也能看到他們與再更未來的。
翻譯的閱讀不似純粹的閱讀,不能只是挖掘,還得考慮如何隱藏,而為了懂得怎麼隱藏,唯有先把所有細節都挖出來看才行。小時候玩電腦遊戲,手眼不協調,連馬利歐都過不了第二關,只能玩角色扮演型的,而我永遠都想把每條路都走過、打開每個櫥櫃,確定裡面到底有沒有東西。等到後來遊戲裡的世界越做越大,我的下場就是迷失在街道巷弄、草叢和廢墟民宅無主棄箱之間,全都想用滑鼠點過一遍,彷彿在測試遊戲製作者的極限。但吉布森確實有這個能耐。用他自己的譬喻去形容就是,彷彿一組俄羅斯娃娃,打開一個還有一個,讀到讓人疑惑「是這樣嗎……」,但他就是。敘述碎而平淡,因為準確而令人意猶未竟。
到頭來,就是迷人的閱讀而已,把東西擺在適當的位置,讓你將自己像螺旋一樣絞進去,每轉一圈便縮緊一點,每轉一圈都離正確看待整件事的角度更近一些。直到最後,一槍穿越林間空地,血霧在空中突然炸了開來,飄動,吹入風雪之中,彷彿一個數項終於平衡了整個方程式。
=目擊=
攻略遊戲的經驗讓她學會,必須留意任何看起來格格不入的事物。她想再迅速看一眼那個背包,便把鏡頭轉向下方。沒找到。
當她到達三十七樓,那東西突然追上,超越了她。看到那種移動方式後,她不再覺得它像背包,反而比較像鰩魚的卵殼。這種幾近滅絕的動物產下的卵有著黑色的殼,她曾在南卡羅萊納的海灘上看過,外觀是詭異的四方形,每個角落都長了一根歪斜扭曲的角。那東西現在沿著大樓向上滾動,用有黏性的腳不斷翻著流暢的筋斗。她不確定那是角還是腳,但無論哪對在前,都會用它們的尖端穩住自己,翻過身,用剛才抓住物體表面的那對腳,將自己推往更高的地方。
鏡頭跟了上去,她想爬升得快一點,卻發現自己仍然沒有控制權。它再次消失在視線中。也許它有什麼方法可以進到大樓。他曾經看過梅肯列印的那些小型氣動機器人,外型像是巨大的水蛭,它們移動的方式跟它有點像,但比較慢。
芙林的母親把鰩卵的殼叫做「美人魚的錢包」,不過柏頓說,當地人都叫它們惡魔的手提袋。它長了一副危險的外表,彷彿有毒,不過實際上完全沒這回事。
她在剩下的路程中持續留意那東西,然後便到了五十六樓。她發現那個窗臺已經打開,不過窗戶仍是霧面,於是有些失望。她覺得自己錯過了派對,但是或許至少能知道它辦得如何。蟲們似乎不在附近。不管那個像電梯一樣帶著她不斷上升的東西到底是什麼,現在也消失了。她迅速環視四周,希望能出現另一扇窗,可是什麼都沒發生。也沒有蟲。
她回到霧面玻璃前,在那兒等了五分鐘,然後再五分鐘。接著她又巡了一遍周圍。在建築物的另一側,某個她之前沒注意到的格狀溝蓋正冒出蒸汽。
她開始想念那些蟲了。
鏡頭俯視,一輛有著單盞大燈的大車開過,速度飛快。
玻璃消去偏光時,她剛好又轉回了窗前,女人就站在那裡,跟某個芙林看不到的人說話。
芙林停下來,讓陀螺儀將她釘在原地。
房間完全看不出來有辦過派對的樣子,裡頭的擺設甚至完全不一樣,彷彿那些小機器人把所有家具都搬動了一遍。長桌消失,現在放了幾張扶手椅、一張沙發和地毯,燈光柔和。
女人穿著條紋睡褲和黑色T恤,芙林猜想她應該才剛起床,因為女人正頂著一頭亂髮――是那種髮質很好的人剛睡醒時呈現的模樣。
要注意蟲子,她提醒自己,但它們仍然沒有出現。
女人笑起來,彷彿聽到某個芙林看不到的人說了什麼。上次臀部貼在窗戶上的那個人……會是她嗎?她是不是正跟之前親了她的那個男人說話?或者該說,只是試圖想親她?也許他們後來把事情說開了,派對的氣氛又不錯,於是就一起過一夜?
她強迫自己再巡視一遍周邊,緩慢、仔細。她注意蟲子、逃跑的背包,或任何事物。蒸汽都散去,她找不到格狀溝蓋之前所在的位置,這讓芙林有種這棟建築物其實是活的感覺――搞不好還有意識。此時,建築物內的女人位居高處,正在無蟲的夜裡大笑。想到這裡,她才意識到拖車裡有多悶熱,整個人已汗流浹背。
天色更暗。城市裡只有寥寥幾盞燈光,但這些表面空無一片的巨大高樓上則全無光亮。
轉過身,她發現他們正站在窗前向外望,男人的手臂環抱女人。他比她高出許多,像是不想過於強調種族的廣告裡會採用的模特兒,留著深色頭髮以及搭配起來很合適的短鬍碴,表情淡漠。女人開口說話,他亦回應,芙林在他臉上看到的那種冷淡隨即消失。此時站在他身邊的那個女人肯定沒注意到這點。
他穿著深棕色的居家袍。你滿愛笑的嘛,她想。
兩人面前的窗戶朝旁邊滑開了一條縫,同時,窗臺邊緣升起了一根細長的水平橫桿,帶起大片不停顫動的肥皂泡沫。橫桿停止上升後,泡沫隨即變成一片淡綠色的玻璃。
她突然想起自己幫杜懷特工作時遇到的那名納粹親衛隊軍官。窗前男人的臉讓她想起了他。
她曾在珍妮絲和麥迪森的沙發上窩了三天,連去廁所都是抓著當時用的舊手機,衝過去、再衝回來,免得自己錯失殺他的機會。
珍妮絲會端來柏頓幫她煮的藥草茶,讓她配著他留下的興奮劑吞下。那種白色藥丸是在兩個郡外製造的。不能喝咖啡,那時他說。
那位親衛隊軍官其實是名住在佛羅里達的會計師,是杜懷特在遊戲中的對手,但從來沒人殺得了他。杜懷特沒有自己下場戰鬥過,只會將他僱來的戰術指導發出的命令轉發出去。但是,那名佛羅里達會計師的戰術指導就是他自己,同時也是一名冷血殺手。他在戰役中通常都會獲勝,而他只要獲勝,杜懷特就輸錢。聯邦政府已經明定這種賭博違法,但總是有漏洞可以鑽。無論是杜懷特或會計師,他們其實不需要這些贏來的錢,也不在乎自己輸了多少――至少不是真的在乎。但像芙林這樣的玩家,他們的報酬是依據殺敵數以及在每場戰役中存活的時間長度所決定。
後來她漸漸覺得,對那名會計師來說,殺死玩家讓他最喜歡的部分,是他讓他們付出了代價。不只是他擁有的實力更強,而是他們確實會因為輸掉遊戲而受到傷害。和芙林同一小隊的隊員們都用玩遊戲的收入養家活口,也許這就是他們全部的工作。就像她得用賺到的那些錢付給強安藥局,好換取她媽媽的處方藥。而他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一樣的事,一個接一個,殺掉與她同小隊的每個人,還好整以暇地享受著那過程。最後,只剩她獨自一人,小心翼翼繞著圈,逐漸徒步深入那座位於法國的森林與翻飛大雪之中,成為他的獵物。
但是後來麥迪森打給了柏頓。柏頓過來,和她坐在同一張沙發上,看她玩了一陣子遊戲,然後把他看到的狀況告訴芙林。
無論那名納粹親衛隊軍官有多確信自己正在獵殺她,實際情況都不是這麼回事。因為,事實上,一旦她意識到,就會發現當下已演變成她正在、或即將開始追殺他,柏頓是這麼說的。他太盲目了,看不出木早已成舟,看不出他正走上一條無法改變、只能不斷延展的誤途。柏頓說,他能夠告訴她如何看到出路,但會需要她放棄睡眠。他留了幾顆白色藥丸給珍妮絲,並在紙巾上畫了投藥時間表。佛羅里達的會計師總得睡覺吧,得把他的角色留給某個非常聰明的AI操控,但芙林則不行。
後來,珍妮絲開始根據紙巾上記的時間餵她吃藥,而柏頓則會按照他自己安排的時間過來,坐在她旁邊看她玩,然後再把他的想法告訴她。他幫助她尋找看清事情真相的角度,而在這過程中,她有時會感覺到他在抽動,那是觸覺回饋裝置的失靈狀態。妳不能學,柏頓說,這種事沒辦法教,妳只能讓自己像螺旋一樣絞進去,每轉一圈便縮緊一點,往森林的深處逐漸推進,每轉一圈都離正確看待整件事的角度更近一點。到最後,她的一槍穿越林間空地,血霧突然在空中炸開,飄動著吹入風雪之中,彷彿一個數項終於平衡了整個方程式。
那時她正獨自一人坐在沙發上。珍妮絲聽到她發出尖叫。
她起身,走出屋前的門廊,把茶都吐了出來,止不住地發抖。在珍妮絲幫她洗臉時大哭。杜懷特給了她一大筆錢,但她後來就再也不曾替他做步巡前哨,也不曾再看過那殘破不堪的法國任何一眼。
所以到底是為什麼?當她看到這個蓄短鬍的男子把身邊的女人抱得更緊時,這些事又重新湧上?為什麼,當她巡視著大樓的轉角處,她會想要一路延伸到五十七樓,再沿原路折返?
如果這真的不是射擊遊戲,她怎麼會感到自己又變成了Easy Ice?
*
去年萬聖節,里昂把一顆南瓜刻成了岡札雷斯總統的臉。芙林覺得那看起來不像她,也覺得這舉動算不上種族歧視,所以就把南瓜放到屋外的門廊上。第二天,南瓜還在,卻看到有東西在上面咬穿了個洞,並在裡面拉了點大便。她猜應該是老鼠或松鼠。她本來要把南瓜丟到花園當堆肥,卻忘記了,隔天就發現刻在上面的總統只剩下一張鬆弛且皺巴巴的橘色瓜皮,後面的肉都被吃光――而且裡面還有新鮮的大便。她套上通馬桶時戴的手套,把它搬到後面的堆肥上,滿臉皺紋的橘臉就躺在那兒,變得越來越醜,直到完全消失。
當她像躺在搖籃裡似地掛在陀螺儀上搖來晃去,看著那個灰色東西呼吸,還沒有想到這件事。
它現在已經不是灰色,而成了銅黑。它把自己伸直、攤平,銳利的直角都還在,但整片平貼在五十七樓的表面上。大樓表面那些扁平的正方形、長方形全都起了霧,因為冷凝作用滴出汗來,但那東西卻渾身乾燥。它跟建築物之間還有一個手掌寬的距離,扭曲的腳變成了支撐架,讓它能對著她正下方摺疊窗臺所在的那個樓層。
那東西在呼吸。
悶熱陰暗的拖車裡,她的汗突破髮際線,滴了下來。她揮手用前臂反面去擦,可是有些跑進了眼睛裡,刺得痛。
她把四軸機往前推進一點。那東西鼓脹起來,又扁下去。
她對自己正在駕駛的飛行器只有很模糊的概念,知道是架四軸機,但不曉得它的四組旋翼到底有沒有包覆起來,還是全部暴露在外?要是可以看到窗戶裡的倒影,就能知道,可她看不到。她想再往前靠近,看能不能用上次對付那隻蟲時用的方法逼近它,靠近距離以觸動擷圖功能。但如果四軸機的旋翼是外露式,而她讓其中一組碰到了那東西,她就掛了。
那個東西再次膨脹,中間有條垂直線的顏色比其他部位稍淡。
她下方的那兩人正站在護欄旁,女人用手扶著橫桿,男人則站在她身後,貼得很近,也許手正還抱在她腰上。
那東西扁下去。她將自己輕輕往前推近。
它沿著那條垂直線打開,露出一條窄縫,淺白的邊緣稍微往兩旁蜷曲,接著飛出某樣細小的東西,畫了道弧線,消失不見。接著就有個東西在刮她的前鏡頭,是顆模糊不清的灰色逗點。它又刮了一次,長得像隻帶著微型電鋸或鑽石切割器的小蚊子,速度跟蟲一樣快,彷彿不斷揮彈的蠍子尾巴。她的鏡頭上又多了三、四道刮痕。它在試圖摧毀她的視線。
她迅速抽離、後退,再拉高,而劃傷她前鏡頭的東西(不管它到底是什麼),都還在繼續。她找到那個下潛開關,讓四軸機迅速下墜,跌撞了三層樓後再讓陀螺儀抓住、撐起自己。
那東西似乎消失了。攝影機受損,但還能運作。
她快速轉向左方。
急速拉升越過五十六樓時,她從右邊的鏡頭看到男人握住了女人的手,並遮上女人的雙眼。她從五十七樓看到他親吻她的耳朵,說了些什麼。給妳一個驚喜。男人後退轉身時,芙林想像他這麼說。
「噢不。」她說,看著那灰色的東西裂開,垂直的縫隙附近模糊一片。小蟲子的數量更多了。他抬頭一瞥,發現了那東西――他就是在等那東西出現。男人毫無遲疑地轉頭離開,就要走進屋內。
芙林直接往他的頭衝過去。
男人看到了四軸機,屈身躲開,在地上用手撐住自己。芙林的上半身從椅子上挺坐起來。
他一定是發出聲音了。因為女人在此時轉過身,放下手,嘴脣微張。接著,有某樣東西飛進她嘴裡。她整個人僵住。那畫面就有如看到柏頓因為觸覺回饋裝置而發作一樣。
男人用手把自己撐起來,像個從起跑架邁出腳步的田徑選手,穿進窗戶內的門縫。在他進入之後,門縫隨即消失,變成一面光滑的玻璃,再偏光為霧面。
女人沒有任何動作。某個非常細小的東西鑽出她臉頰,在上面留下一滴血珠。她仍張著嘴,更多肉眼幾乎不可見的東西從邊緣發白的縫隙中飛出,衝進她嘴裡。她的額頭凹陷下去,彷彿里昂那顆南瓜總統的停格動畫,它在芙林母親堆肥桶的最頂端待了好幾天,或好幾個星期。當金屬拉絲護欄開始向下降,她身後那片肥皂泡泡似的物質也不再是玻璃了。沒有了玻璃的支撐,女人隨即向後墜去,四肢彎成難以理解的角度。芙林在她身後追了過去。
她完全不記得自己後來有沒有看到更多血,只記得那件黑色T恤和條紋褲翻滾的樣子,一面墜落一面越來越不像人的軀體。以至於當她們經過她第一次注意到灰色背包的三十七樓時,女人只剩下兩片飄盪的破布。一片有條紋,一片全黑。
她想起那些聲音,在到達二十樓之前便拉起機身。她掛在空中,待在陀螺儀形成的無重力狀態,整個人充滿哀傷與厭惡。
「只是遊戲。」她坐在拖車悶熱的黑暗裡,臉頰掛著淚。
她再次拉升四軸機,感覺心裡空蕩蕩,極為難受。她對著不斷飛逝的古銅色發愣,已經懶得再去觀察城市是什麼景象。去他的。管他去死。
當她回到五十六樓,窗戶已經消失,被摺疊起來的窗臺蓋住。不過蟲群又回來了,它們臉上的透明燈泡正對窗戶本來的位置。她根本沒去趕。
「就是因為這樣,我們才連一天好日子都過不上。」拖車裡,她聽到自己這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