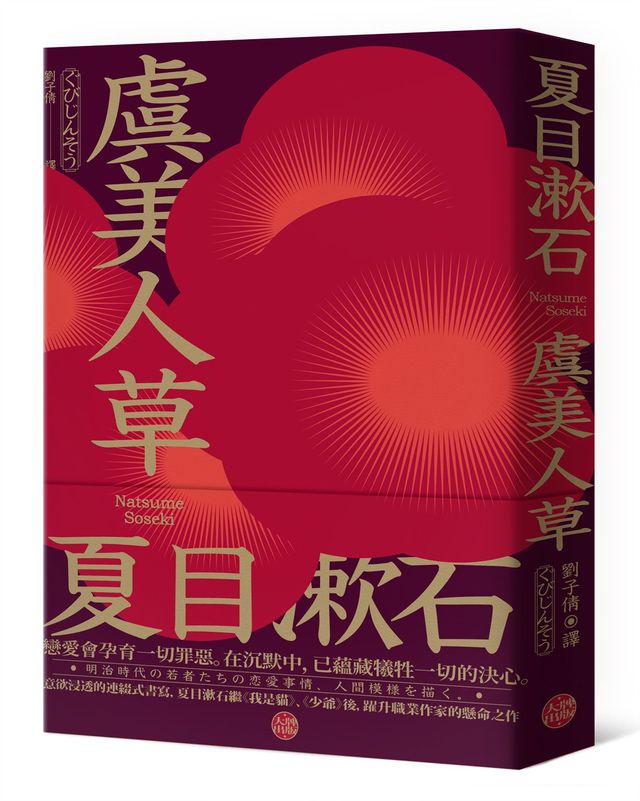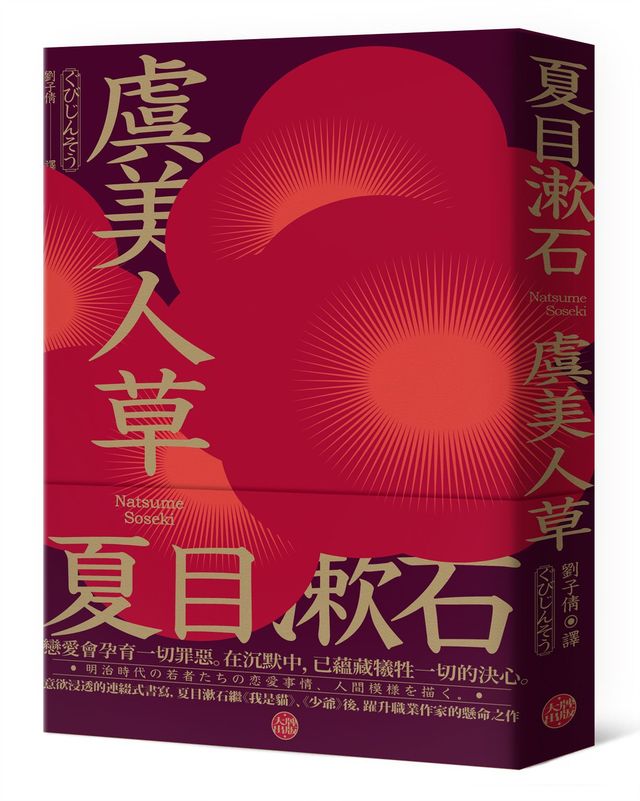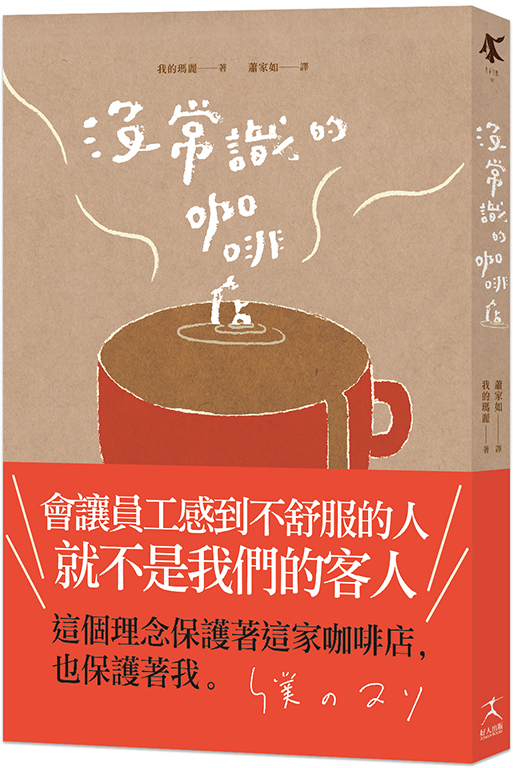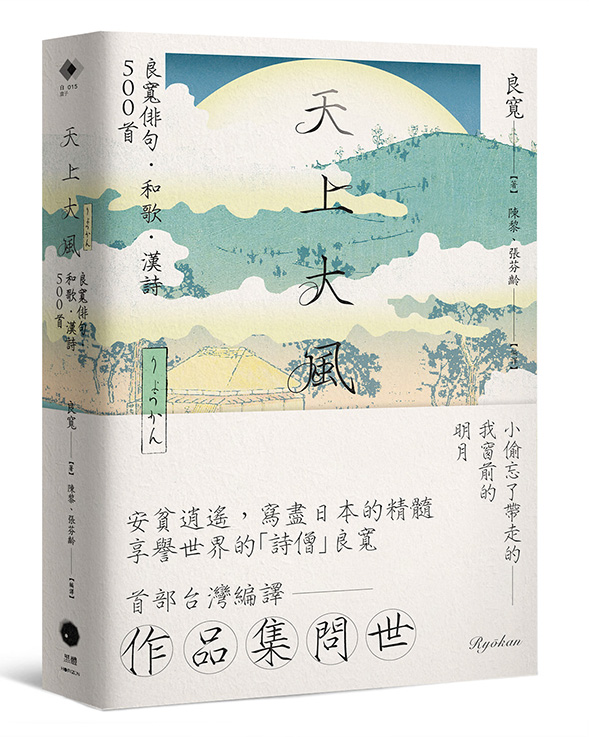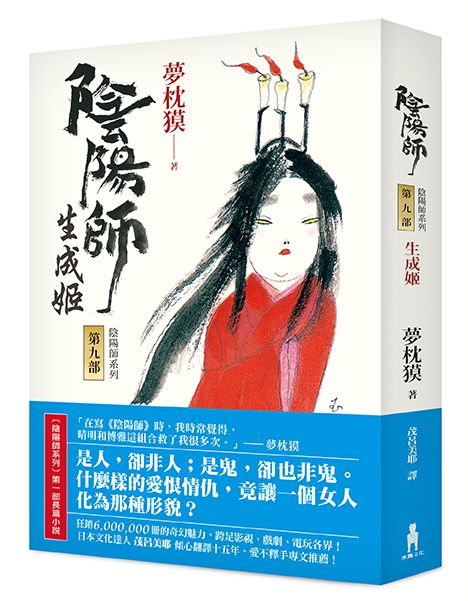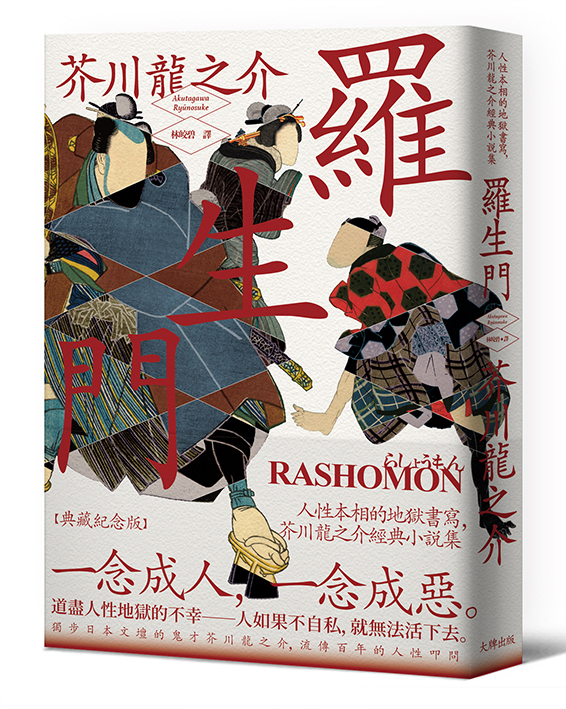戀愛會孕育一切罪惡。
在沉默中,已蘊藏犧牲一切的決心。
★意欲浸透的連綴式書寫,逐字帶你進入「文明人」貪、嗔、痴的色相世界。
★春上村樹一讀傾心的時代傑作──日本國民大作家夏目漱石,繼《我是貓》、《少爺》後,賭上才氣與尊嚴,挑戰文思與寫作技巧巔峰!
倩兮巧笑的女人,
只消轉動黑眸,就能令人意亂情迷……
凡未迷亂者,皆為我執之敵!
「自認生來就是為了伺候男人的女人是最可悲的生物。」
擁有絕美容貌的外交官之女藤尾,向來鄙視那些「賢妻良母型」的女人。
對於父親生前訂下的婚約,這位自詡為新時代的女性並不以為然,
相較於真誠但少根筋的阿一,她更耽溺於詩人小野所給的虛幻之愛中。
當心中的「我執」不斷膨脹,恣意橫行的感官也隨之狂舞,
所有人這才驚覺:生死其實比鄰,悲劇原來比喜劇更偉大……
狗貪香,人逐色。
螞蟻聚集覓甜食,人們聚集貪新鮮。
你是否也是在「色相世界」中不斷掙扎、無法自拔的那個人呢?
明治四十年三月,四十歲的夏目漱石辭去東京帝國大學與第一高等學校的教職,傾全力投入《虞美人草》的連載創作,並以此作宣告自己踏上職業作家之路。這部通篇以白話日文,夾敘傳統駢文、漢詩、和歌和俳句的穠豔大作,不僅轟動文壇,亦是漱石創作生涯中最獨樹一格的小說作品。
漱石以魔性般、妖豔卻帶有致命毒性的罌粟花(即虞美人草)為題,描述新舊更迭的時代潮流中,三對價值觀殊異卻又彼此羈絆的男女,在繽紛熱鬧的「色相世界」所發生一連串的情感糾葛與衝突。
「生死因緣無了期,色相世界現狂痴。」作為一個時代的切片,小說不僅生動地臨摹出女主角──藤尾喃喃自語般的愛欲獨白,以及他人與其「我執」衝撞時的機鋒對談,藉由那些在「色相世界」中不斷掙扎、卻無法自拔的文明人們,漱石亦有傳遞所謂西方文明帶給當時日本社會繁華假象的況味。
如同早已洞悉色相世界的虛幻與真實,哲學家也是藤尾同父異母的哥哥──甲野欽吾在日記上寫道:「悲劇終於發生了。我早就料到會發生這種悲劇。但我只能任由意料中的悲劇發展卻袖手旁觀,因為我知道,對於造孽的罪人所為,我完全無能為力……」
▋夏目漱石
本名夏目金之助,1867年出生於東京。1893年自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系畢業。1899年赴英國留學三年,專攻十八世紀英國文學,回國後開始文學創作。1905年發表小說《我是貓》,大受好評並一舉成名。
1907年他辭去東京帝國大學和東京第一高校的教職,進入朝日新聞社,正式成為職業作家,而《虞美人草》便是首部於報紙上連載的長篇小說,亦是其作品中承先啟後的重要轉型之作。
夏目漱石自幼學習漢文,對東西方的文化均有很高造詣,其作品風格更融合東西方文化的精華,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被稱為「國民大作家」。代表作有《我是貓》、《三四郎》、《從此以後》、《門》、《心》、《行人》、《草枕》等。1916年因胃潰瘍惡化辭世,享年四十九歲。
▋劉子倩
政治大學社會系畢業,日本筑波大學社會學碩士,現為專職譯者。譯有小說、勵志、實用、藝術等多種書籍,包括三島由紀夫《憂國》;川端康成《伊豆之旅》;谷崎潤一郎《春琴抄》、《痴人之愛》、《陰翳禮讚》、《瘋癲老人日記》;太宰治《女生徒》;夏目漱石《門》、《少爺》、《虞美人草》;宮澤賢治《銀河鐵道之夜》等日本文學作品,皆為大牌出版。
這是個彷彿以豔紅包裹三月的白晝暖陽中,萃取春天的一點濃紫,鮮明滴落在天地沉睡中的女人。讓夢的世界比夢更鮮明的黑髮,在凌亂堆疊的鬢上,插著一根細長金簪,簪頭鑲嵌用彩虹貝雕刻得栩栩如生的紫羅蘭。安靜的長日,心魂彷彿已飄向渺遠世界,但女人的黑眸一動,觀者就會立刻回神。半滴暈染中,偷得瞬間短暫,形成疾風威力的,是在春光中壓制春意的深邃眼眸。溯著這眼眸窮極魔力之境時,桃源化為白骨,再也無法回歸塵寰。這不是普通的夢。在模糊的廣袤夢境中,一顆燦爛的紫色妖星逼近眉睫,彷彿在命令人至死都得看著它。女人穿著一襲紫衣 。
女人在這安靜的午後,靜靜抽出書籤,在膝上閱讀沉重的燙金書籍。
「……跪在墓前說。我用這雙手──用這雙手埋葬你,如今這雙手也失去自由。被捕後身在遙遠異鄉雖無法親至,但請記住,這雙手只為你掃墓,這雙手只為你焚香。在有生之年,莫邪 也難以讓我們分離,唯有死亡是殘酷的。羅馬的你被葬在埃及,埃及的我,將被葬在你的羅馬。你的羅馬──無視我的深情,拒絕憂心的我,你的羅馬,無情的你就是羅馬的化身。然而,若真有情,羅馬之神對於我將被活生生遊街示眾的恥辱,必然不會在雲端之上袖手旁觀。必然不會讓我成為你的仇人的戰利品。必然不會拋棄被埃及眾神拋棄的我。我的性命是你復仇的遺物。我向慈悲的羅馬之神祈求。──請藏起我。請將你我永遠藏在不會受辱的墓底。」
女人抬起頭。蒼白的臉頰緊繃,隱約化了淡妝,單眼皮底下彷彿藏著甚麼,急於看清她藏了甚麼的男人悉數成為她的俘虜。男人目眩地半張開嘴。在嘴巴失守時,此人的意志必然已成為對方的獵物。當女人的下唇刻意流露性感風情,卻又不明確開口的瞬間,被她襲擊的對象必定招架不住。
女人只是如鷹隼自長空搏擊般眨動了一下黑眸。男人默默笑著。勝負已分。與口舌如飛的冒泡螃蟹做烏鷺之爭 是最拙劣的計策。風勵鼓行之下被迫訂立城下之盟是最平庸的計策。含蜜吹針、強灌毒酒甚至不能稱之為計策。最高之戰不容彼此交談一語。拈花一笑,即便並非此去八千里,也終究不言又不語。在躊躇的剎那,趁虛而入的惡魔,正中下懷地寫下「迷」,寫下「惑」,寫下「迷失的人子」,眨眼便抽身離去。在人間萬丈紅塵的鬼火,用筆尖沾上腥臭的青磷擅自寫下的字跡,縱然用白髮當刷子也無法輕易刷除。一笑就完了。男人不能收回這笑容。
「小野先生。」女人喊道。
「啊?」男人立刻回應,甚至無暇收拾失控的嘴巴。唇角之所以帶笑,是因為半無意識地流露澎湃心潮,任其無所事事流於草書,卻又在即將徹底變形消散之際,煩惱該來的第二波沒來,所以順水推舟的「啊?」就這麼安心地從咽喉滑出。女人本就刁鑽。讓他冒出一聲「啊?」後,半天都沒再發話。
「甚麼事?」男人只好主動又問。如果不接話,好好的默契會被破壞。默契被破壞了會不安。一旦將對方放在眼裡,饒是貴為王侯也會有這種感覺。更何況現在,除了紫色女子之外男人甚麼都看不見,當然會立刻接話。
女人依舊無言。掛在壁龕的容齋 作品,描繪的是小松旁梳著稚子髻的近侍,從以前就一派悠閒。穿獵衣騎褐馬的主人,或許是習慣太平無事的殿中生活,也沒有活動的跡象。唯有男人提心吊膽。第一箭沒射中,第二箭也不知射到哪裡。這次如果又沒中,還得再繼續。男人屏氣凝神盯著女人的臉。細瘦的臉孔湧現期待的表情,雖不知女人過於厚重的嘴唇究竟會說出好消息還是壞消息,卻似乎還是希望得到回應。
「你還在那裡?」女人從容不迫說。這是意外的回應。對天拉開的弓,差點讓射出的葫蘆形羽箭射回到自己頭上。男人渾然忘我,只顧著看女人,相較之下女人從一開始就盯著膝上攤開的書,似乎壓根沒把坐在面前的人放在眼裡。可女人其實只是發現這本書燙金精美,這才從男人的手裡搶來開始翻閱。
男人只應了一聲「對」。
「這個女人打算去羅馬嗎?」
女人面露不快地看著男人。小野不得不為「克麗奧佩托拉」 的行為負起責任。
「不會去的。絕對不會去。」
他彷彿是在替不相干的女王辯護。
「不去嗎?要是我也不會去。」女人總算被說服。小野僥倖鑽出了黑暗的隧道。
「看莎翁寫的作品,非常立體地呈現出那個女人的個性呢。」
小野才剛出隧道,立刻就想跳上腳踏車奔馳。魚躍深淵,鳶舞長空。小野是住在詩鄉之人。
此地有燃燒金字塔的天空,有擁抱人面獅身像的沙子,有藏於長河的鱷魚,有二千年前的妖姬克麗奧佩托拉與安東尼相擁,任由鴕鳥羽扇輕拂如玉肌膚,是好畫題亦是好詩材。這是小野的拿手本領。
「看莎翁描寫的克麗奧佩托拉會產生一種奇妙的感受。」
「甚麼感受?」
「彷彿被拽入古老的洞穴中再也出不來,正在茫然之際,紫色的克麗奧佩托拉鮮明映現眼前。從色彩剝落的木版畫中,就只有她一人燃燒著紫色火焰冉冉浮現。」
「紫色?你經常提到紫色呢。為什麼是紫色?」
「不為什麼,就是有這種感覺。」
「那麼,是這種顏色嗎?」女人說著倏然將半鋪在榻榻米上的寬袍大袖一甩,掠過小野的鼻尖。小野的眉心深處,突然飄過克麗奧佩托拉的氣息。
「啊?」小野頓時回神。彷彿以駟馬難追的速度掠過天空的杜鵑鳥驟然穿過雨幕底層,女人瞬間流露的異色早已收起,美麗的玉手安然放在膝頭。沉靜得彷彿沒有脈搏。
飄過的克麗奧佩托拉的氣息,逐漸從鼻腔深處溜走。小野眷戀追逐不意間從二千年前喚起的影子,心已被誘往杳窕之境,被帶向二千年的彼方。
「那不是微風吹拂的戀愛,亦非含淚之戀或嘆息之戀。那是暴風雨之戀,是曆本上也沒有記錄的大暴雨之戀。是刀刃相向的生死之戀。」小野說。
「生死之戀是紫色的?」
「不是生死之戀為紫色,是紫色的戀情為生死之戀。」
「你是說斬斷情絲會流出紫色的血嗎?」
「我是說愛情發怒時,砍斷愛情的匕首會閃現紫色。」
「莎翁寫過那種事嗎?」
「這是我對莎翁作品做出的詮釋。──安東尼在羅馬與屋大薇結婚時──使者送來結婚的消息時──克麗奧佩托拉的……」
「紫色被嫉妒濃烈渲染吧。」
「紫色被埃及的陽光燒焦後,冰冷的短刀發光。」
「若是這種程度的濃度應該沒關係吧?」話聲未落長袖已再次翻飛。小野被打斷話頭。就連對於對方有所求時,女人也非得打斷對方說話才滿意。先聲奪人的女人得意地望著男人的臉。
「結果克麗奧佩托拉怎麼了?」壓制的女人再次放鬆操控對方的韁繩。小野不得不邁步向前跑。
「她盤根究底向使者打聽屋大薇。那種問話和責備的方式,讓她的性格更生動,所以很有意思。她沒完沒了地追問使者:屋大薇也像自己這麼高挑嗎?頭髮是甚麼顏色?是圓臉嗎?聲音低沉嗎?多大年紀了……」
「這個不停追問的人自己多大年紀?」
「克麗奧佩托拉應該正好三十歲吧。」
「那她跟我一樣已經是老太婆了嘛。」
女人歪頭呵呵嬌笑。男人被捲入妖異的酒窩中有點不知所措。如果認同女人的說詞,會顯得虛偽。但是否定又顯得太平凡。直到女人的皓齒間閃現一絲金光又消逝,男人始終沒有接話。藤尾這年二十四歲。小野早就知道她和自己相差三歲。
這樣的美人過了雙十年華仍待字閨中,空虛地數著一二三,直到花信之年的今日猶未出嫁著實不可思議。春院徒更深,花影酣欄干,春日遲遲的陽光似乎早早將盡,抱琴猶帶幽恨意,是一般錯過嫁期的世間女子常態,將撢拂塵的陣陣空響聽成琴柱彈琵琶,享受本不該有的音色,這就愈發不可思議了。詳情本就無從得知。我們只能從這對男女的隻字片語之間不時窺視,以莫須有的猜測偷偷占卜曖昧不清的愛情八卦。
「隨著年紀增長,嫉妒也會增強嗎?」女人一本正經地問小野。
小野再次啞然。詩人必須了解人性。對於女人的質問當然有義務回答。但不懂的事情不可能答得出來。沒見過中年人如何忌妒的男人,饒是詩人或文人也答不出來。小野是個擅長玩弄文字的文學家。
「是啊。想必還是因人而異。」
為了不起衝突,他圓滑地含糊帶過。但女人可沒這麼好敷衍。
「如果我變成那種老太婆──現在好像已經是老太婆了,呵呵呵──但我如果到了那個年紀,不知會怎樣。」
「妳──妳怎麼可能會嫉妒,就像現在……」
「我會喔。」
女人的聲音冷然斬斷靜謐的春風。遨遊詩鄉的男人,突然一腳踩空墜入凡間。墜落之後也只不過是凡人。對方正從高不可攀的崖上俯視。男人甚至無暇思考到底是誰把自己踢落到這種地方。
「清姬是幾歲變成蛇的?」
「這個嘛,還是得設定在十幾歲才有戲劇張力。大概十八、九歲吧。」
「安珍呢?」
「安珍應該在二十五歲左右吧。」
「小野先生。」
「是。」
「那你幾歲?」
「我嗎──我啊……」
「自己的年齡還得想了才知道嗎?」
「不是──我記得和甲野君是同年。」
「對了,你和我哥哥同年。但我哥哥看起來老很多。」
「哪裡,沒有那回事。」
「是真的。」
「看來我該請妳吃飯。」
「好啊,那就讓你請客。不過,你不是長相年輕。是心態年輕。」
「我看起來像那樣嗎?」
「簡直像小弟弟。」
「真可憐。」
「是真可愛。」
女人的二十四歲等於男人的三十歲。不懂道理不分是非,當然也不知世界為何旋轉為何靜止。她們也不懂在古今遼闊的舞台不斷發展中,自己佔據何種地位,扮演何種角色。只有嘴皮子特別厲害。女人無法應付天下大事,無法與國家周旋,面對群眾時也無法妥善處理。但女人特別擅長一對一的把戲。一對一較量時,獲勝的必然是女人。男人鐵定會輸。被豢養在具象的籠中,啄食個體的小米,為之欣喜拍翅的總是女人。在籠中的小天地與女人競相鳴叫者必然會斃命。小野是詩人。因為是詩人,所以主動將脖子半伸進這個籠中。小野完全沒找到機會鳴叫。
「你很可愛。就像安珍一樣。」
「說我是安珍太過分了。」
男人彷彿要求饒,這次接受了這個評語。
「難道你不服?」女人只有眼睛在笑。
「可是……」
「可是甚麼?你有什麼不滿?」
「我不會像安珍那樣逃避。」
逃不掉只好硬著頭皮接招。小弟弟不懂得見機俐落抽身。
「呵呵呵,我會像清姬一樣追著不放喔。」
男人聽了只是沉默。
「如果要變成蛇,我是不是有點太老了?」
女人射出春天不該有的閃電,穿透男人的心口。那是紫色的。
「藤尾小姐。」
「甚麼事?」
呼喚的男人與被呼喚的女人相向而坐。六帖房間被茂密的樹叢隔開,連路上的車聲都變得幽微。寂寞的浮世,只有二人活著。以榻榻米的褐色鑲邊為界,隔著二尺距離面面相覷時,社會遠離了他倆。救世軍 這時正敲著鼓在市內四處遊行。醫院的腹膜炎病人奄奄一息即將斷氣。俄國的虛無黨 正投擲爆裂彈。火車站有扒手被捕。火災發生。嬰兒即將誕生。練兵場的新兵被責罵。有人自殺。有人殺人。藤尾的哥哥和宗近正在攀登叡山。
連花香都嫌過重的深巷幽室,互相呼喚的男與女,在消逝於死亡底層的春影上,顯然正心動雀躍。宇宙是二人的宇宙。越過脈脈三千條血管湧現年輕熱血的心扉,為戀愛開啟為戀愛關閉,在長空歷歷描繪出不動如山的男女。二人的命運就在這危險的剎那決定。是東還是西,全在身體微微一動之間。呼喚不是小事,被呼喚亦非小事。彼此之間隔著生死以上的難關,不知會是對方先拋出炸彈,還是自己先丟出炸彈,靜止的二人身體恍若兩團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