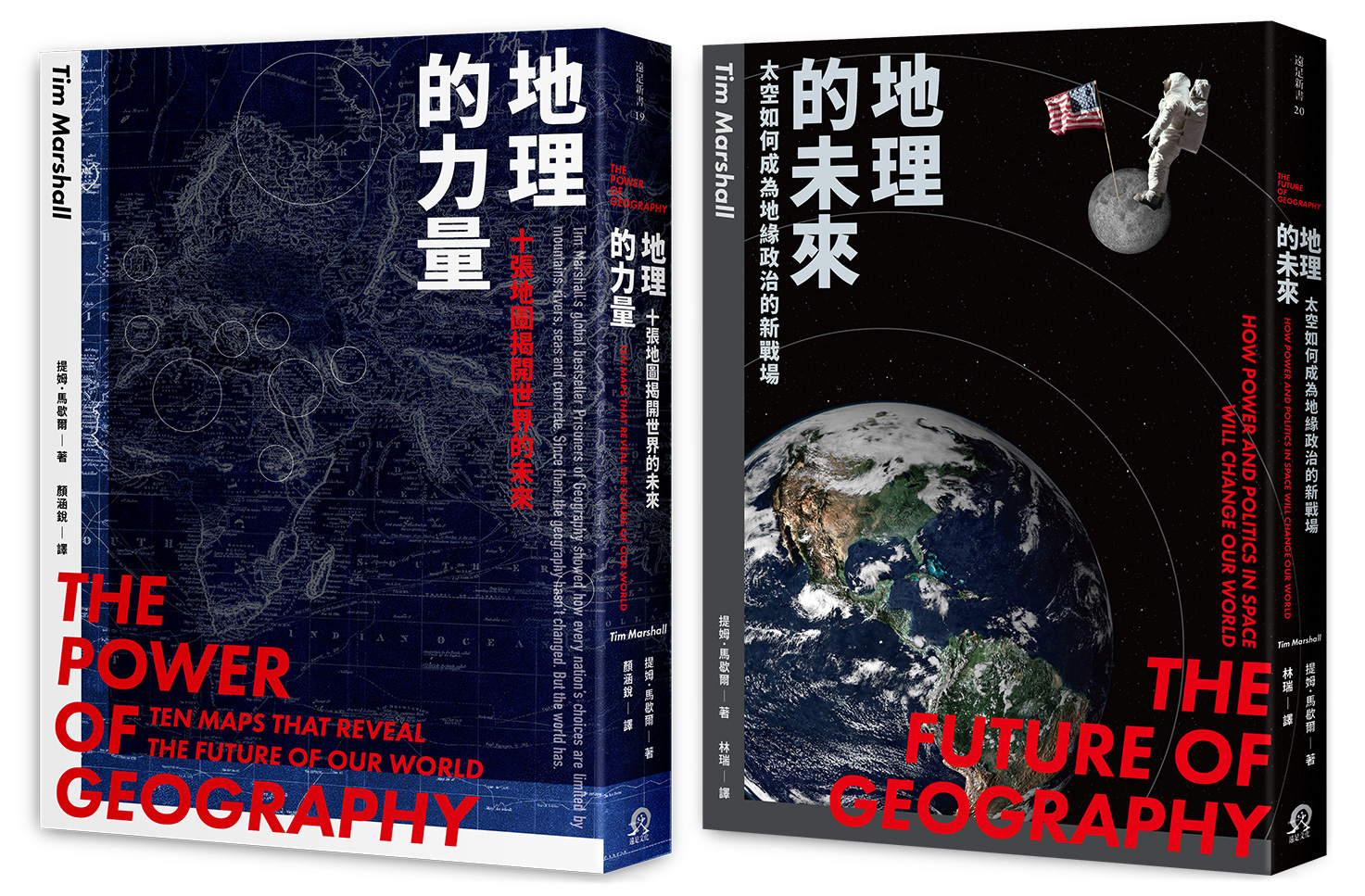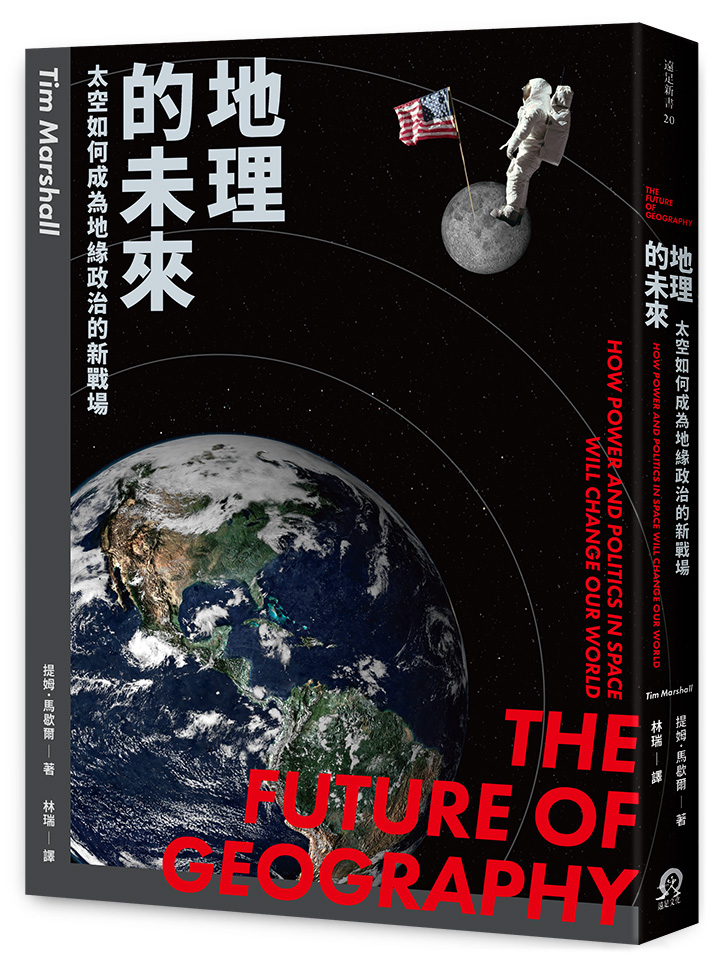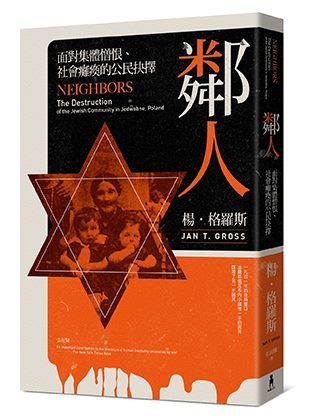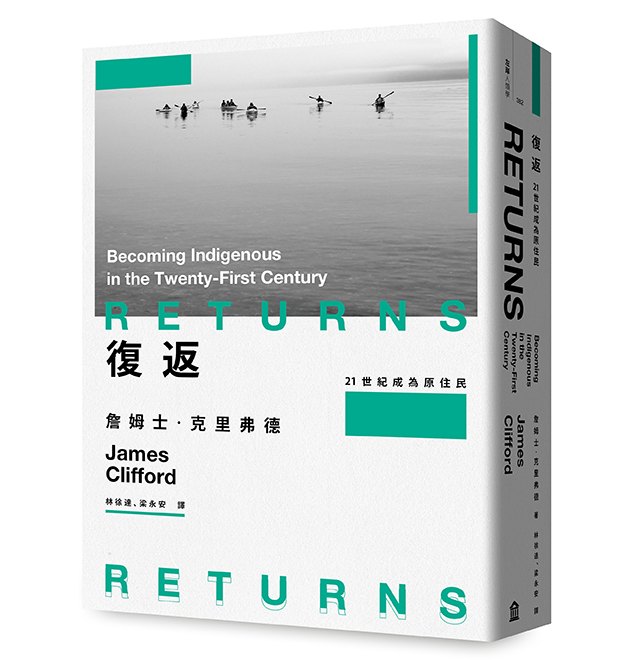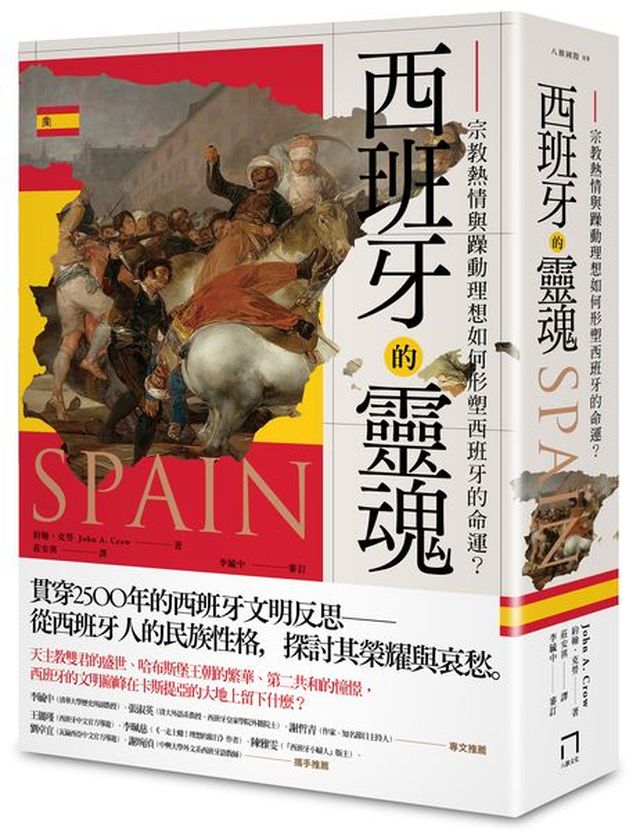★亞馬遜網路書店年度暢銷戰史書籍★
★《華爾街日報》暢銷書★
「我已為我的國家做出貢獻──」
空襲東京、中途島會戰、雷伊泰灣海戰、硫磺島戰役……
她是唯一全程參與二戰的航母,是美國將官的搖籃;
她與日本多次血戰,卻在退役後被拆卸成鋼鐵,賣給宿敵日本!
艦長、飛行員、水手、地勤人員盡忠職守,
面對神風特攻隊的自殺攻擊、夜間惡戰、和時間賽跑的修復工作,
如果沒有企業號,二戰歷史可能從此改寫!
企業號的靈魂,就是美國為太平洋自由而戰的精神!
=======================
1958年的春天,美國航空母艦企業號(CV-6)正在等待最後時刻的到來。它的三角桅杆已被移除並放倒在飛行甲板上,隨後由拖船緩緩拖曳,在數千名群眾的見證下,被送往李普賽特公司的碼頭進行拆卸工程。木製的飛行甲板被擊成碎片、送去焚燒,艦體被切割成一塊塊滾燙的鋼板,龍骨更被分割成數段──歷時兩年,戰功彪炳的企業號軍艦,最終成了兩萬噸、總值僅五十六萬美元的廢鐵。更諷刺的是,它的造價高達兩千萬美元,它遭拆卸後的材料則大多賣給了戰時最大宿敵——日本。
儘管如此,無論是對二戰期間或今日的美國而言,企業號的價值都無法以金錢衡量。她是唯一全程參與二戰的航母,是美國將官的搖籃,甚至可以這樣說:企業號的靈魂,就是美國為太平洋自由而戰的精神!
▋如果沒有企業號,二戰歷史可能從此改寫
在《永遠的企業號》中,美國空戰史權威巴瑞特・提爾曼從企業號建造完成並於1938年下水服役的那一天說起,直到1958年遭拆解為材料出售為止,完整呈現了這艘美軍傳奇航艦的一生。
從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發,一直到日本於1945年投降的期間,在美國海軍迫切需要航艦的艱難時刻,企業號總是在現場,帶領美軍在太平洋戰區東征西討,屢建戰功。例如,在關鍵的中途島海戰,企業號的艦載機領頭擊中日軍三艘航母,造成日本海軍元氣大傷,讓美軍在此役之後開始轉守為攻。在大黃蜂號於聖塔克魯茲海戰遭擊沉後,企業號成為美軍在太平洋戰區唯一一艘可派上用場的航艦,孤軍面對瞬息萬變的數場海戰,以及視死如歸的神風特攻隊所帶來的噩夢。
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企業號,或者企業號在某個更早的時間點就遭擊沉,便可能嚴重打擊美國海軍發動攻勢的能力,使二戰局勢走向出現根本性的變化。
▋艦長、炮手、飛行員、水手,從第一手的口述記錄,見證戰爭中的英雄主義與悲劇性
本書不同於一般戰史書籍,作者提爾曼挖掘官方紀錄、口述歷史,並親自採訪曾於企業號上服役的倖存老兵,以各個人物的奮鬥,提供企業號在太平洋戰爭時最真實、最震撼的作戰歷程。
他帶領讀者觀看損害管制小組在高溫與濃煙中,處理船艦遭炸彈命中後造成的通風問題;下一秒,則置身於俯衝式轟炸機的駕駛艙,看英勇的飛行員推機頭俯衝、投落炸彈、近距離命中敵艦,並在飛機嚴重受損、千鈞一髮之際跳傘逃生。與此同時,他也帶領讀者深入艦橋與太平洋艦隊總部,看總司令尼米茲與企業號性格各異的歷代艦長運籌帷幄,應對戰場上的瞬息萬變。
提爾曼在書中細膩描述,儘管官兵在戰爭期間頻繁異動,企業號掌握的知識、經驗,以及頑強的戰鬥精神,總能完整地保存下來,讓艦上人員一體同心、專注於眼前任務,確保企業號在美軍急需支援的情況下發揮最大效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企業號是美軍首艘嘗試夜間飛行戰技的航艦;這正是源於艦上飛行員為尋求打破現狀的可能,緊盯戰爭發展,同時積極編寫教材、組織「蝙蝠小組」,才可能達成的成就。
▋為自由而戰的美國精神,隨著企業號的到來而深入太平洋地區
二次大戰期間,美國海軍在太平洋共經歷四十一場戰役,其中企業號就參與了二十場。這個記錄在美國海軍中,沒有任何軍艦能與之匹敵。但企業號的歷史地位,不在於它的參戰次數,更在於它所參與的戰役具備相當的特殊性。從珍珠港到中途島、東所羅門海、瓜達康納爾、菲律賓海、雷伊泰灣、琉磺島、沖繩到日本本土,企業號的作戰史就是太平洋戰爭史的縮影,而其無役不與的作戰精神,就象徵美國為太平洋自由奮戰到底的決心。
太平洋戰爭是二次大戰的重大轉折,也讓美國首次將目光轉向太平洋地區,涉入亞太事務。在美中衝突只升不降,海上軍事演習日益頻繁之際,本書帶領讀者重回美國扭轉全世界人共同命運的關鍵時刻。
◎本書初版為八旗文化《企業號的故事:一艘勇猛航艦的誕生與凋零》
★企業號基本檔案★
艦名:企業號USS Enterprise
舷號:CV-6
艦種:航空母艦
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區
服役日期:1938年5月12日至1947年2月17日
標準排水量:19,900噸
全長:809呎6吋
全寬:109呎6.25吋
乘員:227名軍官、1,990名水兵
飛機搭載:97架
★企業號重大事蹟★
- 世界海軍史上航艦VS航艦戰績最佳的軍艦:擊落敵機911架、擊沉敵艦71艘,維持戰績最佳紀錄保持者超過60年。
- 在122艘參與太平洋戰爭的美國航艦中,唯一全程參戰的航艦。
- 美國將官的搖籃,培養出多位將軍以及至少一位國會榮譽勳章得主。
- 生涯共獲得20座戰鬥星、總統單位褒狀、海軍團體褒獎,是至今為止獲得最多獎勳褒揚的軍艦。
- 1944年10月與1945年1月的「台灣空戰」就是在企業號的甲板上發動。
- 1958年,企業號除役,老兵要求讓她轉為博物館的努力落空,但爭取到讓世上第一艘核動力航艦繼承企業號之名,繼續縱橫四海52年。
「本書詳細記錄企業號航艦和她在二次大戰時所扮演的角色。這部氣魄宏達的著作抓住了戰爭的兩面:既有英雄主義的一面,也有悲劇性的一面。本書的核心當然是那艘表現突出的航空母艦,而這樣的軍艦我們有可能再也無法看到了。」──傑瑞‧米勒(Vice Admiral Jerry Miller),退役海軍中將
「本書描述的不是一條軍艦,而是上千名美國水手,他們其中許多人奉獻了自己的生命,從而讓企業號成為致命的武器。作者通過轉述他們的故事,紀念這群二次大戰的水手如何把海軍航空作戰變成美國海軍的利劍。」──史蒂芬‧庫恩斯(Stephen Coonts),小說《闖入者出擊》(Flight of the Intruder)作者
巴瑞特‧提爾曼(Barrett Tillman)
1948年生於美國奧勒岡。著名軍事史專家、空戰史權威,熱愛飛行。第一本著作在十五歲時出版,作品以二戰為主。曾擔任雜誌編輯,自1990年開始專事寫作,目前已經累積超過五十本著作,其中包括十本小說。
提爾曼的作品廣受好評,為他獲得十座寫作獎項,包括由美國海軍尾鉤協會(The Tailhook Association)頒發的終身成就獎。
揭仲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所博士,早年曾在出版社負責軍事叢書的編務,參與過編輯《西洋世界軍事史》套書,譯作有《圖說諾曼第登陸》。現為國防軍事評論作家。
前 言
第一章 未戰先立功(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
第二章 保持冷靜、專注,然後好好地幹上一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五月)
第三章 甜蜜的復仇(一九四二年六月)
第四章 我們一點都不了解這些該死的東西(一九四二年八月)
第五章 作戰的機會來了(一九四二年十月)
第六章 一生中最激動的時刻(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
第七章 漫長而寂寥的旅程(一九四三年二月至十二月)
第八章 如果他們之中有人生還,那可不是我們的錯(一九四四年一月至六月)
第九章 航向二七○(一九四四年六月至七月)
第十章 企業號的能耐也不過如此而已(一九四四年八月至十二月)
第十一章 堅定地活下去(一九四五年一月至五月)
第十二章 企業號,一艘有靈魂的軍艦(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八年)
謝 誌
附 錄
試閱
〈第二章_保持專注、冷靜,然後好好地幹上一場〉
在企業號上,正當海爾賽(William F. Halsey)準備喝下他當天的第二杯咖啡時,一位參謀報告:「將軍,珍珠港此刻正遭遇空襲!」
就連極富戰鬥精神、早已命令特遣艦隊可率先對敵軍開火的「公牛」海爾賽,這時也懷疑消息的真實性。他從座位上站起來大叫道:「告訴金默爾!他們射擊的是我的飛機!」就像此刻在艦上的所有人一樣,海爾賽認為是美國陸軍在朝他的飛機射擊。他直覺地想到要通知他那位海軍官校一九○四年班的同窗好友金默爾(Husband Kimmel)上將,要金默爾下令停止射擊。
不久之後,艦隊收到了一封由金默爾署名的電報,證實珍珠港正遭到空襲,電文內容如下:
發文者:太平洋艦隊司令部
受文者:所有軍艦
內 文:珍珠港遭空襲,這不是演習。
隨後,由加勒荷上尉(Earl Gallaher)所傳回的報告也證實了這個消息。加勒荷是企業號所派出、在距歐胡島約一百五十英里範圍內搜索的偵察機飛行員之一。在他駕機朝歐胡島飛行時,還想著落地後要去俱樂部喝些啤酒輕鬆一下。但此刻他打開無線電報告:「日本人正在攻擊珍珠港,我沒有在開玩笑!」
艦橋上,值更官多塞特上尉(John Dorsett)下令全員就戰鬥位置。十九歲的水兵巴恩希爾(Jim Barnhill)此時正站在操舵室外;他是艦上四個司號兵之一,才剛剛和他的好朋友克萊爾(Calvin St. Clair)交班。聽到艦橋的命令,巴恩希爾舉起手中閃閃發亮的黃銅色軍號,對準擴音器吹出嘹亮的「全員戰備號」;這是一段由三十個斷音所組成的軍號,原本是騎兵部隊通知全體官兵「上馬、列隊」,準備行動之用。在這個時刻,巴恩希爾不禁想起自己正在與家鄉德州斯科鎮(Cisco)相距三千七百英里的地方,參加一場世界大戰。
當號聲響起時,一位快滿三十歲的老兵馬克斯‧李(Bosun Max Lee)立刻大喊:「備戰!備戰!全體就備戰部署。」
語音剛落,李轉身望著在艦橋上值勤的同僚,他們之中大多數都知道李的役期快要結束了。李用一種莊重的語氣,緩慢地告訴他們:「我們在打仗了,我想我恐怕很難活著離開海軍了。」
全艦官兵分秒必爭地奪路衝往各自的部位,往上、往前衝向右舷,或者往下、往後衝到左舷,他們從差不多有膝蓋高的水密門下緣跳過,逐一在各個艙間內移動。官兵們戴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使用的步兵鋼盔,打開彈藥庫,將零點五英寸、一點一英寸和五英寸等口徑的彈藥搬出來,然後開始擔憂這天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第六轟炸機中隊的無線電士克雷格(Claude Clegg)回憶道:「當我來到飛行甲板時,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我以前從未看過、最大的一幅美國國旗在旗桿上飄揚。」接著他聽到艦長的聲音從對講機中傳來艦長:「我是艦長,珍珠港現在正遭到日本人的攻擊。」經由座機上的無線電通訊,克雷格甚至可以聽到一些來自攻擊現場的聲音。
巨幅國旗令艦上所有官兵印象深刻,包括平日十分含蓄的貝斯特(Richard H. Best,綽號「迪克」[Dick])上尉。抬頭看著自己國家紅、白、藍三色的國旗在戰爭第一天迎風招展,這位第六轟炸機中隊的飛行員回憶道:「這是整場戰爭中,最令我感動的時刻。」
炸彈、魚雷和彈藥紛紛送到機庫和飛行甲板上,軍械士忙著替所有飛機裝彈、掛彈。炸彈被固定在無畏式轟炸機的掛架上,紅衣的軍械兵也將炸彈的引信和魚雷的保險絲調整到定位。至於其他人,有的吃力地將重達一噸的魚雷吊掛在毀滅者式魚雷轟炸機機腹下方,有的則從彈藥箱中取出五○機槍的彈藥,再裝入野貓式戰鬥機四方形的機翼中。那天早上,企業號活像個在海上航行的蜂窩,艦上到處都是忙得團團轉的人。所有人都將注意力集中於即將到來的任務上;他們打起精神,強迫自己壓下心頭的懷疑:我們在打仗了嗎?我們真的已經在打仗了嗎?
有些人還是很難接受這個事實。他們想當然爾地認為,這肯定是某個涉及海軍、海軍陸戰隊和陸軍的聯合演習,就連檀香山的廣播電台也參與其中。
一位士官長大步走過某些第六魚雷轟炸機中隊的機組員身旁,邊走邊揮舞手中的百元大鈔,要找人打賭說眼前這一切不過是一場攻擊演習。無線電士格瑞茲說:「沒有人要和他打賭,因為當下我們的想法都和他一樣。」
艦上的無線電通訊室內,操作人員從主通信頻道中,收聽到許多莫名其妙、驚慌失措的呼叫。有些呼叫提到發現敵機,有些則指出空襲正在進行,但他們還是覺得不太合理。誠然,軍艦已經處在備戰狀態下好幾天了,但有誰會在星期天早上發動攻擊呢?
此時,通信網中傳來更多的訊息。無線電士收聽到有人高聲呼叫:「這裡是6-B-3,是美國飛機!請不要開火!」
呼叫者是負責搜索最北方海域的岡薩雷斯少尉(Manuel Gonzalez);他和由韋伯少尉(Fred Weber)所駕駛的僚機在執行任務時,突然遭到六架有固定起落架的陌生飛機攔截。西班牙裔的岡薩雷斯和他波蘭裔的無線電士兼機槍手科扎爾克(Leonard Kozalek),是企業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早陣亡的兩個人。當岡薩雷斯被擊落,韋伯則將座機向下俯衝到離波浪頂端僅約二十五英尺的低空,如果有任何日本飛機打算追擊,看到他這樣也就自動放棄了。
儘管飛行大隊指揮官楊格和僚機塔夫成功穿越密集的自動武器砲火,僥倖地衝進福特島,其他人就沒有這麼幸運了。軍方後來在一架墜毀的零式戰鬥機旁,發現沃格特少尉(John H.Vogt)的飛機殘骸,這二架飛機顯然是在空中互撞了。沃格特和他的機槍手皮爾斯(Sydeny Pierce)雙雙陣亡。
在歐胡島南方的「G區」,由狄金遜上尉和麥卡錫少尉(John R. McCarthy)所組成的分隊,以一千五百英尺的高度通過巴貝爾角時,發現狀況明顯不太對勁:從珍珠港傳來高射砲砲彈的爆炸聲,伊娃島則籠罩在煙霧中。
更糟的是,停泊在福特島旁邊的戰鬥艦列不斷冒出大量濃煙。這天早上,有許多停泊在港內的巨艦慘遭屠宰。
為了更清楚看見發生什麼事,這兩架無畏式向上爬升,但他們立刻就被至少兩架日本帝國海軍的戰鬥機飛行員盯上並對他們展開攻擊。狄金遜率領他的分隊從四千英尺的高度急速下降,卻又迎頭遇上另一批黑色機鼻的日本戰機。敵機開火擊中麥卡錫,使他的座機起火、被迫跳傘。最後,麥卡錫降落在一片樹林裡,過程中摔斷一條腿,但後座的柯恩(Mitchell Cohn)則不幸跟飛機一起墜落身亡。
為了求生,狄金遜只得奮戰,但他成功的機會非常渺茫。他估計至少有三架敵機聯手對付他,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斷轉向,並信任他後座機槍手有足夠的本事,能讓這些零式戰鬥機無法尾隨他的飛機。米勒不斷用手中的單管白朗寧三○機槍進行射擊,同時透過內部通話系統告訴狄金遜他受傷了。但沒過多久,他又報告擊中一架戰鬥機。接著,他用光了所有彈藥,並且再次負傷。
狄金遜用眼角餘光瞥見一架零式戰鬥機已經起火,不過他沒有時間仔細觀察。另一架敵軍戰機從他機鼻前方掠過,他用機首的五○機槍朝對方射擊一梭子子彈。但隨即發現他的飛機逐漸喪失控制,左翼也已經起火,開始盤旋下墜。
當飛機下墜到約一千英尺的高度時,狄金遜解開安全帶、卸下他的無線電駕駛帽,然後通知米勒趕快跳傘。狄金遜費力地從飛機中跳出去;他拉開開傘索,隨即感到繫在身上的傘帶被猛力拉開,降落傘順利張開,讓他降落在一片甘蔗田中。狄金遜落地後,朝遠方地平線上升起的煙霧前進;他在半路上搭了一輛便車前往海軍基地。在這最後一次任務中,米勒雖然沒有弄濕他的腳,卻成為那天早上首批陣亡的美國人之一。
同樣位在歐胡島南方的「F區」,第六偵察機中隊的霍平(Halstead Hopping) 中隊長對整個空襲有清楚的觀察,並以無線電向企業號傳送確認空襲的報告;他在大約在早上八點四十五分落地,正好在日本兩波空襲之間。在霍平四處尋找軍械士時,楊格大隊長和尼可少校則正在向金默爾上將報告。霍平讓自己的情緒跨過戰爭與和平間那個模糊不明的分界線,接受這糟透的事實,然後迅速調整自己並面對它。他說服一位准尉,替他中隊的三架無畏式裝上炸彈。
楊格大隊長用他專業的眼光,親眼觀察日本飛機的第二波空襲。他描述這些前來攻擊的敵機是一種「低單翼、具有固定起落架」的機種,並且說道:「我對這次攻擊唯一的批評,就是他們還是從相同方向進入……然而,由於我們的防空火力欠缺效率,空中也沒有多少飛機與他們對抗,再加上日本人對這種攻擊方式早已演練得非常純熟,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這次攻擊實施得近乎完美。」在未來一年,企業號的官兵還將多次領教此種由愛知時計株式會社(一九四三年成立愛知航空機會社)所生產、盟軍稱為「瓦爾」(Val)的「九九」式俯衝轟炸機所發動的攻擊。
少數企業號官兵眷屬目擊了這次空襲,其中包括珍‧多布森(Jane Dobson),她的先生也參加了今早的搜索任務。由於以前曾見識到她先生所屬中隊訓練的情形,她注意到日機俯衝的角度不如第六偵察機中隊所實施的那麼險峻。後來,她把所看見的情形告訴她的先生克里歐‧多布森少尉(Cleo Dobson)時,後者高興地把她抱起來,不斷地誇讚她是「一位真正的俯衝轟炸機飛行員之妻」。
在這天早上進行偵察任務的十八架飛機上,共有三十六名機組員,他們蒙受極為慘重的損失。除了當天有六人陣亡,他們之中有八人在接下來的幾個月殉職,另有二人被俘、一人因傷成殘,傷亡率高達百分之四十七。
由於同時遭受日本飛機與美軍地面砲火的攻擊,到當天中午,從企業號派出的偵察機中只剩下一半還能服勤。綽號「長釘」(Spike)的霍平仍舊率領九架無畏式自福特島起飛,並編成三支三機分隊,前往搜尋日本特遣艦隊。他們的機隊成扇形分布在一個大約六十度角的範圍內,採三三○轉○三○的航向,先朝西搜索珍珠港西北方,然後再向東搜索珍珠港的東北方。
這些飛機什麼都沒發現,因為此時日本海軍中將南雲忠一早已調轉船舵,率領麾下六艘航艦和其他支援軍艦返回日本。這或許是件好事:這九架沒有戰鬥機護航的無畏式,若真對上了日本機動部隊,肯定絕無生還機會可言。
──
當天上午,企業號的偵察轟炸機有一半不是降落在陸地上,就是已被擊落而無法執行任務。如此一來,企業號若要對任何日本軍艦發動攻擊,就只能仰仗林賽上尉(Eugene Lindsey)的十八架毀滅者式魚雷轟炸機了。
戰爭向來是由混亂主宰的領域,十二月七日那天自然也不例外。一個錯誤的情報指出在東南方發現敵軍航艦,企業號於是立刻派出第六魚雷轟炸機中隊,以及六架攜帶發煙器的無畏式俯衝轟炸機前往攻擊;他們希望這些發煙器所製造的煙霧,能掩護這批慢速的毀滅者式慢慢地朝敵艦接近。六架野貓式戰鬥機也在蒼茫暮色中升空,參與此次任務。
在起飛一小時後,林賽除了下方深灰色的海洋,什麼也沒看到,於是他開始搜索附近的海域。到後來,他們才終於搞清楚,顯然是一架偵察機飛行員將友軍的軍艦與飛機誤判為敵軍,然後發出錯誤的警報。夜幕即將降臨,林賽率領這二十四架轟炸機調頭返回航艦。
赫貝爾上尉(Francis F. Hebel)所率領的戰鬥機,和俯衝轟炸機及魚雷轟炸機失去了目視接觸,於是這位高大、金髮的前飛行教官只得調頭返航。這些野貓式戰鬥機早轟炸機一步抵達企業號,卻接獲命令轉往陸地降落,以便艦上騰出更多的空間,讓這些很少實施夜間降落的飛機有比較高的成功機會。綽號「符立茲」(Fritz)的赫貝爾於是率領這批F4F戰鬥機,在漸深的夜色中轉頭向陸地飛去。
飛行大隊並未接受完整的夜間著艦訓練,但此時飛行員們別無選擇,只能硬著頭皮嘗試。企業號的飛行甲板燈火通明(由於附近可能有敵人潛艦,這是一個很冒險的舉動),已準備好引導返家的「小雞」們降落。負責指揮的是哈登上尉(Hubert B. Harden),一位前偵察機飛行員,現任降落信號官(LSO)。他手中的綠色指示板,讓這些摸黑飛行的飛行員增添不少信心;這批飛行員表現得異常出色,除一架外,其他都安全降落在航艦上。出錯的是一架TBD型魚雷轟炸機,它降落時撞到升起的攔阻網,重達一噸的魚雷從機腹掛勾脫落,導致這個彈頭帶有四百磅高爆炸藥的魚雷就這樣在飛行甲板上滑行──所幸這條「魚」最後還是被甲板上的人員成功制伏。飛機降落後要到那個位置煞車、固定,則由飛行甲板管制官、有著一雙長腿的湯森(William E. Townsend)少校負責。
──
在歐胡島上空,第六戰鬥機中隊正飛進一場混亂中。
在夜色中,赫貝爾機隊的飛行員們看見大火依然在珍珠港四周燃燒,但福特島上的機場跑道燈火通明。飛行員在五百英尺的高度進入起落航線,戰鬥機紛紛放下起落架與機輪準備降落。赫貝爾帶領機隊照往例從機場左邊進入;當他和其他五位飛行員駕機從乾船塢,以及還在持續燃燒、遭受重創、遍體麟傷的戰鬥艦列上空通過,幾艘軍艦突然要求這些入侵者們提供當天的識別信號,但企業號的戰鬥機飛行員哪曉得這些。由於這批飛機未能做出正確的回應,戰鬥艦賓夕法尼亞號的高砲指揮官下令開火射擊。
在今日,此一戰術被稱為「火力接觸」。在賓夕法尼亞號的防空機槍開火射擊後,其他人也如法砲製。為了追瞄在夜空飛行的目標,砲手會發射照明彈照亮天空,然後朝這些野貓式戰鬥機猛烈射擊。
短短幾分鐘內,就有四架格魯曼戰機被擊落。最先被擊墜的是曼吉斯少尉(Herb Menges),他的座機撞進一棟面海的住宅,引燃的大火將飛機燒成灰燼。曼吉斯在艦隊服役了十三個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第一位陣亡的美國海軍戰鬥機飛行員。
幾秒鐘後,艾倫(Eric Allen)中尉的座機也數度遭防砲命中而起火。儘管高度過低,他還是爬出飛機,並拉開他的降落傘,但在下降過程中仍持續遭到射擊,直到落入布滿油汙的海水裡。落海的艾倫身負極重的內傷,一名岸上的水兵又開槍擊中他。這位三年前才從海軍官校畢業、年方二十五歲的飛行員憑著堅強意志力在海面游泳,最後被一艘掃雷艇救起,然後被緊急送往基地醫務室。
其他四架戰鬥機別無他法,唯一能做的就是關掉機上所有的燈、收起機輪,然後加足馬力從持續不斷的防空砲火中衝過去。赫爾曼少尉(Gayle Hermann)座機的普惠發動機被一枚五吋砲彈直接命中,所幸沒有爆炸。赫爾曼置身越來越密集的防空砲火中,只得調轉機頭,迫降在福特島上的高爾夫球場。但在那裡,赫爾曼遭到一群殺紅眼的陸戰隊瘋狂射擊。不過赫爾曼毫不驚慌,他把降落傘夾在腋下,徒步走向第六戰鬥機中隊的機棚。後來,他回到現場,在他那架F4F戰機強韌的機身上,數到了十八個彈孔。
在這個時候,赫貝爾對飛到海軍航空站已不抱任何希望,遂轉頭朝惠勒機場(Wheeler Field)飛去,希望陸軍能對他友善一點。但他的座機因為中彈而嚴重受損,只能在熱帶的黑夜中勉強向東飛行,最後墜落在一片甘蔗田裡。赫貝爾的野貓式戰鬥機翼尖著地,機尾整個折斷、彎到機鼻上方,整架飛機近乎解體。目擊者從殘骸中將不省人事的飛行員拖出來,然後把他送到斯柯費爾德軍營(Schofield Barracks)。
對大衛‧弗林(David Flynn)少尉而言,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不僅是他二十七歲的生日,也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紀念的日子。由於無線電故障,他只得隻身朝伊娃島的海軍陸戰隊機場飛去,但在飛到距機場跑道只剩四英里時,他的座機發動機故障,迫使他在黑暗中棄機跳傘。落地時,弗林摔傷了背,但仍忍痛在野地點起一把火,附近士兵隨即趕到,將他送往崔普勒醫院(Tripler Hospital)。
最後是能力傑出、向來直言不諱的丹尼爾(James Daniels)少尉。他猛踩節流閥朝西南方飛去,躲過濃密的防空砲火,隨後又聯絡上福特島機場塔台,並在塔台指引下順利降落在機場。當丹尼斯從五十英尺高度,從擱淺的戰鬥艦「內華達」號(USS Navada,BB-36)前桅樓附近飛越時,又遭到艦上水兵和附近希甘姆機場(Hickam Field)守軍的猛烈射擊。
丹尼斯回憶道:「不久之後,我的機輪接觸到了跑道。但我落得太後面了,眼看就要撞上二部停在跑道末端的緊急應變卡車──我猛踩煞車,讓飛機在跑道旁的高爾夫球場上整整轉了一圈。」丹尼斯在離赫爾曼迫降地點沒有多遠的地方停下,然後重新啟動飛機,朝飛行線滑行。丹尼斯不清楚究竟是哪一個海軍陸戰隊員幹得好事,只記得一個陸戰隊員舉槍朝飛機掃射,差點打爆他的頭。
從軍官宿舍的窗戶,丹尼斯看到戰鬥艦亞利桑那號的殘骸依舊烈焰沖天。他找到了一支還能用的電話,幾分鐘後就和居住在珍珠城的妻子通上了話。他的結論是:「我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那天,全海軍中最幸運的人」。
次日清早,消息傳來,艾倫因為傷勢過重、不治身亡,而赫貝爾也因為顱骨破裂不幸去世。
在那可怕的一天裡,企業號損失了九位飛行組員和十一架飛機。唯一的戰果,就只有那架與沃格特座機互撞的零式戰鬥機。
──
十二月八日星期一,燃料將盡的企業號和護航艦減速通過歐胡島外海,朝珍珠港前進。當天傍晚,企業號駛入珍珠港內狹窄的水道。艦上每位軍官、水兵和陸戰隊員終於能從高處,親眼目睹港內慘烈的景像。布滿油汙的海水和燃油燃燒所引發的惡臭,清楚說明了一切。
儘管天色昏暗,但悲慘景像依然清晰可見,尤其是那些平日熟悉的船艦的殘骸,格外令人傷心。兩個月前差點與企業號互撞的戰鬥艦奧克拉荷馬號,翻覆在福特島旁。驅逐艦蕭號殘破的船骸還在乾塢內;她在三年半前曾陪同企業號前往加勒比海,進行那次刺激的首航。經常被企業號的轟炸機與偵察機中隊拿來當作練習目標的戰鬥艦猶他號,也被炸得很慘。戰鬥艦亞利桑那號被炸得尤其嚴重,讓第六偵察機中隊的感到特別難過,他從官校畢業後所分發的第一艘軍艦就是亞利桑那號。加勒荷說他「非常、非常地憤怒」。
不過,企業號上的許多官兵這時也感到背脊發涼。因為他們意識到,要不是那個「幸運」的風暴延誤了回程,企業號鐵定也會和這些軍艦一樣,被摧毀在珍珠港內。
(摘自:《永遠的企業號》,〈第二章_保持專注、冷靜,然後好好地幹上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