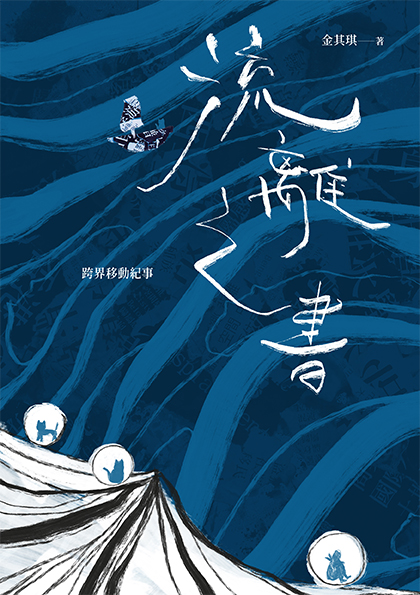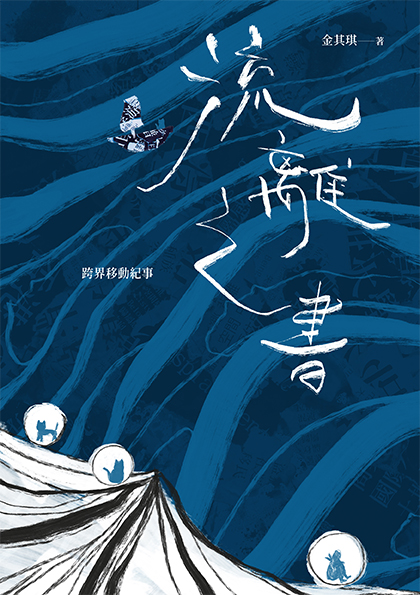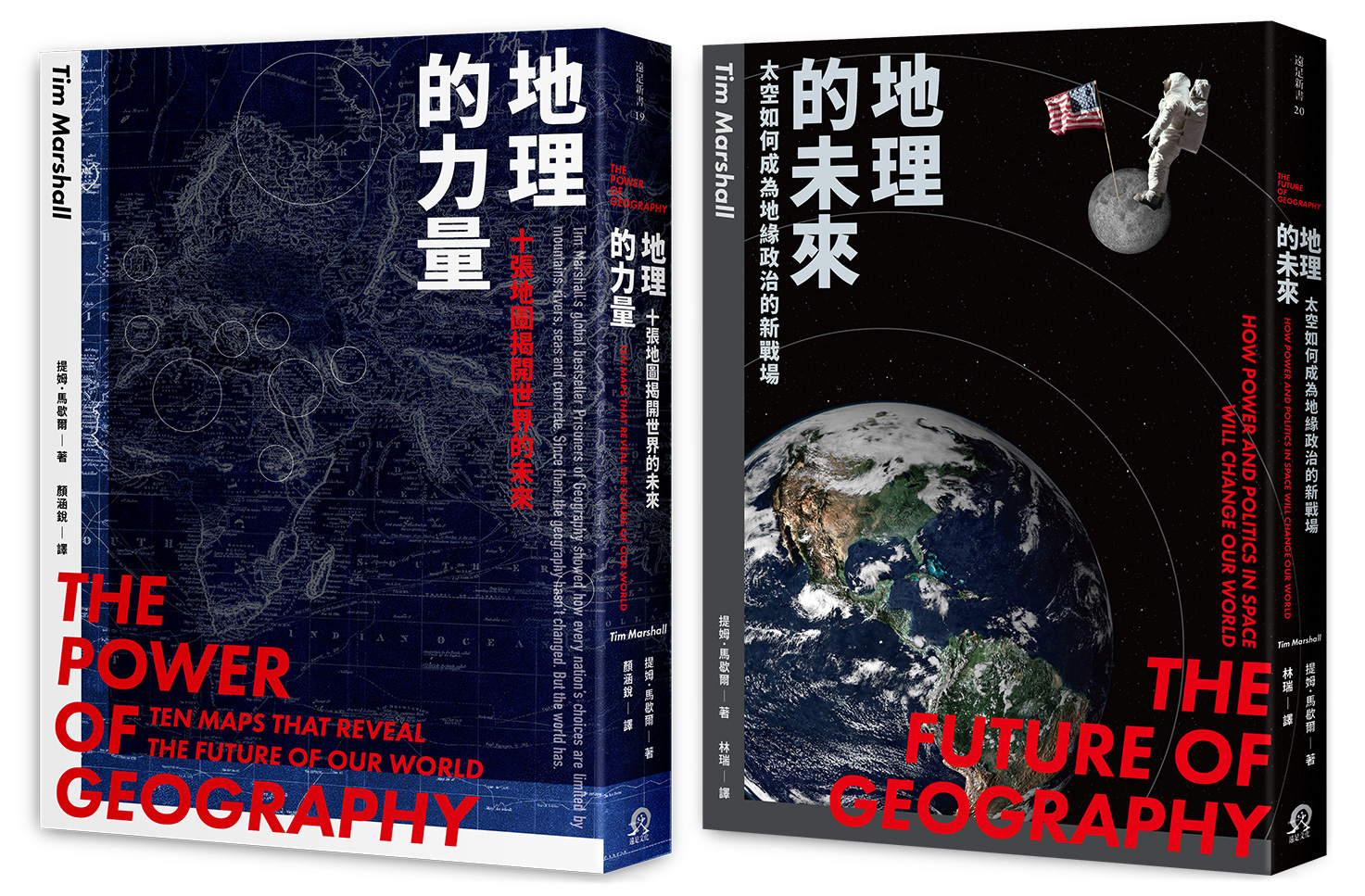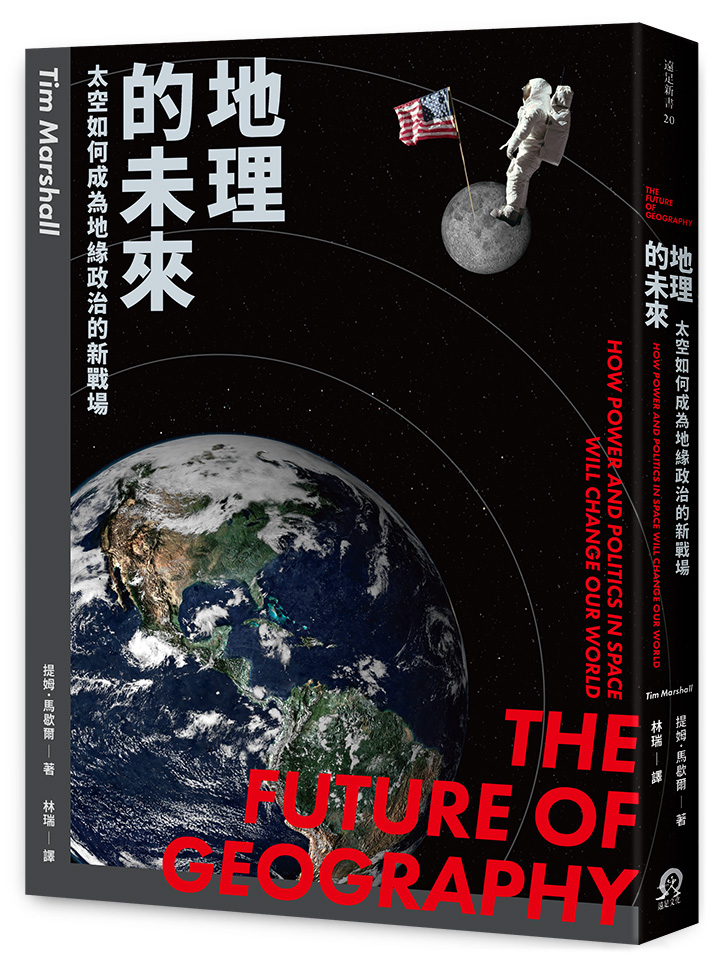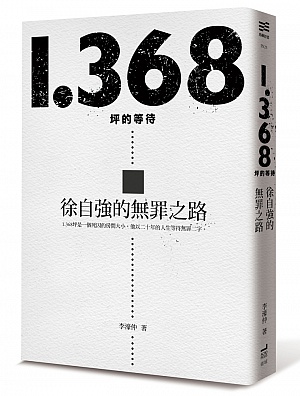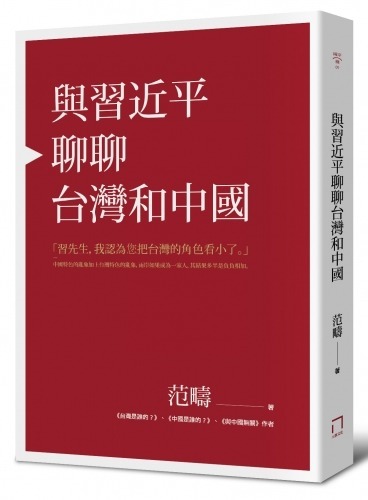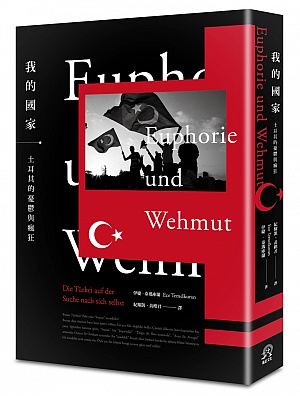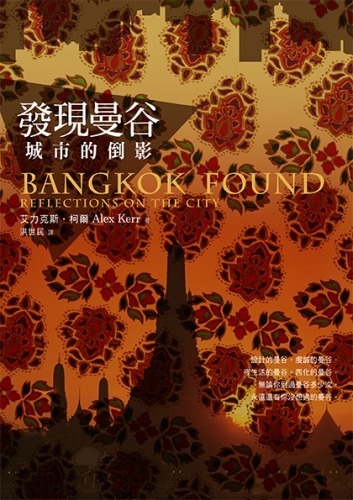「我發現了一種看待人事物的全新方法。緩慢而綿長,允許溫柔與掙扎的方法。」
人類學從來就是一門關乎移動的學科。只是當人類學家遠渡重洋,研究那些往往與自身迥異的陌生族群之後,真正認識的是什麼?「走了那麼遠的路,是不是最終都會透過異文化來認識自己?」人類學也總是在乎能否在地,在遙遠異鄉有另一個等待自己回去的家。人類學家研究親屬、重視關係,但同時為家和家人賦予了更直覺與情感上的定義。
《流離之書》收錄寫作者金其琪17篇跨界移動紀事;她是擁有七年資歷的記者,也是剛入門的人類學學徒;她從中國移動到香港,再到台灣。一路以來,她報導香港馬屎埔農地抗爭、記錄2016年香港大學生間的中港矛盾,文中許多描述已人事全非,但都成了歷史的一部分;她描述了環球大廈週日的菲傭聚會、九龍城的泰國移民、南方澳的漁工,人要花多久時間才能把異地當成家?她寫阿美族祭師從抗拒到接受自身文化的歷程、達悟人如何從大島看到自己的島嶼、學阿美語的猶太人類學家,她寫的是台灣當代原住民,也寫下每一個人企圖尋求身為「人」的自己。
記者和人類學家某個程度是相似的。進入田野地、熟悉報導人(當然,也被報導人熟悉),試圖透過一次次的對話建立關係、看到與理解彼此,然後帶回自己與他者的故事。17篇文章中,7篇關於香港、7篇關於台灣、3篇關於中國,但書中的主題跨越地理上的分界。「土地」書寫具象的土地迫遷、老屋肢解、無家可依,也寫忘記了自己名字的人怎樣找回與故土的親密感;「陣痛」寫的是那些自願和非自願的跨境移動,人們因身分政治而彼此碰撞,移動的海上貨櫃則塞滿走私動物的牙齒;「扎根」書寫在異鄉和面目全非的故鄉創造新生活、新社群的人;「微塵」則是在這個生死常臨的年代,一些像流沙般逝去的故事。
17篇文章呈現的不僅是世界的變化,也讓人在閱讀中發現,人類學如何逐漸滲入一個寫作者的文字DNA,乃至看待世界的方法。
「經歷了多變的生活,讀了人類學並在今年邁入30歲的我,強烈地感覺到自己想用任何文字形式來還原世界本身的混沌。寫得『混沌』比寫得『清楚』可要難太多了。」
「和讀新聞、做記者受到的訓練不同,這種全新的方法緩慢而綿長,充滿速食閱聽者可能錯過的細節,且允許你的筆流露溫柔與掙扎。」
張潔平,Matters創辦人
—————————————————專文推薦
何欣潔,前《端傳媒》台灣組主編
何榮幸,《報導者》創辦人兼執行長
李志德,資深新聞工作者
李雪莉,《報導者》總編輯
杜念中,資深新聞工作者
官大偉,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教授
林益仁,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
容邵武,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高雅寧,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陳如珍,人類學家
傅可恩,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教授
鄭肇祺,台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助理教授
—————————————————推薦
(依姓氏筆畫排列)
金其琪
記者出身的寫作者,人類學與民族學博士生。曾在香港任職《端傳媒》、《明報周刊》,作品獲台灣卓越新聞獎基金會二十週年獎助及多個台港新聞獎項。十年搬家十次後,目前和來自台東的貓咪生活在台北。
EDO
出生於香港。曾以為自己會一直待在東部沖咖啡。喜歡畫畫。經歷過十多次爬樓梯搬家後,現時作品主要以數位為主。
推薦序/張潔平
自序
一、土地 在自己的土地流浪
1、在迫遷的命運裡種一座村莊
2、靈魂的事
3、回到蘭嶼,一個達悟女人的兩種生活
4、飛屋環遊記
5、從深水埗到艋舺公園
二、陣痛 跨界碰撞
1、燃燒的民主牆
2、演「鬼子」的日本人
3、麥高登的非裔廣州
4、走私者的自由港
三、扎根 流離中扎根創造
1、中環折疊
2、九龍城‧泰國城
3、學阿美族語的猶太人
4、在蘭嶼,音樂可以做到的事
四、微塵 生死微塵
1、漁工之死,與他們活過的南方澳
2、中國醫護疫情後心理創傷調查
3、二O二一萬華十日記
4、我們知道老與死的樣子
繪後記/EDO
致謝&原始文章的日期及出處
內文試閱
靈魂的事(摘錄)
找到巴奈.母路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在十月。每年十月,是花蓮阿美族里漏(Lidaw)部落的祭師團體Sikawasay舉行巫師祭的時間,祭師每日都要沉浸在儀式中,不可遠行。年近六十歲的巴奈.母路,是這個僅剩六人的祭師團體中,最年輕的一個。
我是部落的外人,因巴奈.母路引薦,得到祭師們集體同意之後,得以參加兩日的巫師祭。出發前收到這樣的提醒:「你來可以,但記得在儀式前一天晚上開始,直到儀式結束,都不要吃雞肉、雞蛋、蔥蒜、蔬菜、水果、魚類。」即便是觀者,也要守儀式的禁忌。到場之後先mibetik(告靈)喝下米酒,才算跨入神靈的場域,正如阿美族常說的一句:「酒是我們的路。」
以米酒叩門,來到花蓮溪與太平洋交界附近的里漏部落,遇見巴奈.母路的第一個晚上,她不談學術。她是在花蓮做了近三十年田野調查的民族音樂學家,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的副教授。可是兩年前,她的一個決定,讓她可以隨時拋棄這一切,包括學術、理論,乃至這個人間。
阿美語Sikawasay,字根kawas意為「靈」,si意為擁有及承載,say意為「XX的人」,巴奈.母路決定成為Sikawasay,就是「擁有神靈的人」。Sikawasay原本是她的民族音樂學田野,從研究者到自己也成為Sikawasay,我問她何以「下海」,她卻答是「上路」,靈魂的路。
在原漢混居的部落與客家孩子一起長大,她曾是不說族語、努力擺脫原住民身分的台北大學生,在基督教會司琴的「天使」。半生過去,她厭煩了在學術圈過人間的日子,轉身在靈的世界中與Sarakataw(走路之神)相互擁有。
她成為最資淺的第四階級祭師Suday,也成為基督徒眼中的瘟疫與魔鬼,但她不在乎。「我可以不要這個世界了。」還沒脫下黑色祭師服的巴奈.母路喝了一整天的米酒,但不是在說醉話。她選擇去處理靈的事。
穿黑衣服的阿美族
七十三歲的Lali’自前一天晚上開始,就完全沒有吃過東西,下肚的只有米酒。她是巫師祭這一天的主人,必須遵守斷食禁忌。今年的十日儀式中,六人祭師團只來了五人,還有一位年邁的祭師因臥病而缺席。米酒、祭壺、檳榔、荖葉、糯米糕和生薑被擺在地上,儀式從早上十點多開始,一直持續到晚上七點才結束,最後三日還要分別去田間曠野、河海交界,以及海畔進行冷卻祭。
初來乍到的人很難看懂祭師們在做什麼。火焰燃起,巴奈.母路跟在老祭師身後,時而旋轉,又蹲下,像是要鑽過什麼。這是在祭拜這一天的最後一位神靈,Lali’的母親留給她的Lalebuhan(火神)。巴奈.母路解釋她們的動作:「我們先要經過Lalataan(削碎木頭的神),和Tilamalan(點火的神)的路段,過三道門,才能到達Lalebuhan。」
抵達不同的神靈場域需要走不同的路,面向不同方位的吟唱、轉圈、動作組成繁複的儀式。而每位Sikawasay 都有自己的主神,擁有神靈越多的祭師階級越高。優雅的儀式動作配以動聽的吟唱,但原來連祭師的親人都無法知曉其中含義,因為此阿美語非彼阿美語,而是專用於祭祀的靈語。如此艱澀難懂,為何能吸引一個受了完全漢化教育的巴奈.母路呢?
最初,Sikawasay對她來說只是一群穿黑衣服的阿美族。遙遠的記憶中,她大學畢業後,從台北回到花蓮,開始做國中音樂老師。她的部落是花蓮吉安的薄薄社,她常在週末騎著腳踏車,穿過隔壁的里漏部落去海邊。有一天,她騎進了里漏部落的一條小巷子,突然發現了一群穿黑衣服的人。「我說奇怪,阿美族的部落怎麼穿黑衣服?不是應該穿紅衣服嗎?」腳踏車越來越靠近,黑衣人的眼光卻不友善,怕外人影響了儀式的進行。
那時她只知道阿美族有豐年祭,卻從沒聽過這些黑衣人口中吟唱的,像是阿美語又不像是阿美語的,憂鬱深沉的歌。打聽才知道,原來這是巫師團體,Sikawasay。
信仰基督教的家人告訴她,Sikawasay 是魔鬼,不可以碰。她忍不住,硬是要去,卻很不受歡迎。父親是民意代表,大家都知道她是誰家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她來自基督徒家庭。
她回憶,突然加入,「人家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吃了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例如雞肉、蔬菜、魚,可能影響儀式。她儘量保持低調,每年寒暑假都希望能加入,默默在一旁架設小台DV機,一邊做筆記,幾乎沒有聲音。但她被罵過、被轟出來過,甚至有人摔過她的DV機。
沒人眞能轟得走她,她太好奇了。「我會故意找各種機會去靠近她們,聽她們的歌謠,逐年靠近她們。」磨著磨著,老祭師們終於逐漸接受了她的存在。一有了發問和互動的機會,她更是看不過癮,索性連工作也辭掉,大大小小儀式都去看,再讀一個音樂碩士,把所有儀式的聲音都寫成樂譜記下來。
她本來覺得,身為阿美族學音樂的孩子,這樣就已經夠了。可是後來發現不行,因為歌還有歌詞,歌詞也要記下來。記完歌詞,發現還有舞蹈。
為了記下歌詞,她幾乎是從零開始學習阿美族的靈語,一個音一個音拼出來,再去問老祭師是什麼意思。記錄舞蹈的時候,她又發現不能簡單寫逆時針幾圈、順時針幾圈,原來轉圈是「有密碼的」。祭師的旋轉是在虛擬空間裡進行,從人間這個俗世的空間到神聖的空間,都靠不同的速度和旋轉方向來決定。
記錄著記錄著,她自己也結婚生子,碩士畢業,甚至去了福建讀博士,又進入東華大學工作,但始終無法忘記Sikawasay的事。「我的心在那裡,我一直沒有辦法忘記部落的那些,一張張像神靈一樣的老人的臉。」在福建三年,她請丈夫代她去看儀式,用電話給她聽歌謠的聲音。生了孩子,她抱著一大一小的一雙小兒女去,妹妹還是嬰兒,得多帶一個奶媽。她的田野筆記後來成了家庭回憶冊,因為隔幾頁筆記,就有兒子女兒的畫。
她還記得自己第一次看到老祭師和大自然的靈做互動,「那是非常surprise的,就是哇,風一吹,她就說巴奈,你聽,matawa ko bali(風在笑)。」
「那個靈是存在的,她知道風是在哭還是在笑。」她太受感動了,漸漸發現,繁複的儀式背後,是她這個漢化了的阿美族小孩從來沒聽過的,龐大的宇宙架構,裡面住著八個不同方位的一百七十八位神靈,風林山海,無處不在。所以那些固定的、不固定的、部落性的、私人性的二十多種歲時祭儀,包括祖靈祭、慰靈祭、播種祭、田祭、殺豬祭、祛病祭,都是為了與神靈互動。那是充滿意義的。
而最珍貴的是,這居然就是她自己民族的文化。她過去從未發現,甚至在最初二十年的生命中,一直因為原住民受歧視的緣故,不想做一個阿美族。
從林桂枝到巴奈.母路
直到結婚生子,巴奈.母路都還不叫巴奈.母路。她叫林桂枝,受日本教育的母親不會說國語,叫她Kiku(桂子)。她在部落長大,本來以為自己很會聽阿美語,眞的到了山裡的奇美部落才發現,根本聽不懂老人的話。
那又怎樣?年少的她,根本不想當原住民。「我討厭部落。」她說。
那是原住民深受歧視的年代。小時候,老師會因為原住民學生說了族語而體罰,或是罰款。她也連帶覺得部落的人不上進,愛喝酒,於是努力讀書,努力學國語,努力彈琴,就是為了考上好大學,要比部落的原住民「高一等」。到了大學,她努力的方向是西方音樂,跟原住民完全沒有關係,可偏偏遇到一個老師,愛叫她「阿美公主」。
這位老師是台灣音樂家許常惠,難得有一個原住民學生,特別寶貝。可巴奈.母路卻說,「我恨死他了,上課的時候整天對著我說,你們阿美族的音樂怎樣怎樣。」她排斥自己的阿美族身分,「我就覺得我好不容易遠離了,你又要把我拉回去?」
直到一年夏天,她大學剛畢業,老師突然跟她聊起,你知道你們阿美族有個部落的豐年祭,第一天晚上不睡覺的嗎?她覺得太天方夜譚了,豈料一查,卻是眞的。她心裡過不去了:「怎麼總是老師來告訴我說我的文化是怎樣?」一股勁上來,她騎著機車就走到東海岸,一路往豐濱鄉的貓公部落開。媽媽在後面哭著追她:「你不要去啊,你要去哪啊,你一個女孩子去怎麼辦啊!你不怕鬼也得怕人啦,萬一被人強暴怎麼辦啊!」
媽媽當然追不上她,她在晚上十點到達貓公部落,「哇,都在跳舞!」眞的有個徹夜不眠的豐年祭。她覺得自己是學者,就拿著攝影機和錄音機一夜狂拍狂錄,發現全場老老少少,只有她一個女的,大家都看著她。早晨五點半,她就被提到人群中央接受「盤問」了。中央一張長凳放著三大碗米酒,本來是給部落靑年喝,兩個彪形大漢把她提起來,雙腳懸空,押到長凳前,她這才怕了。
「你是誰?」老人家用阿美語問。
「我是北邊的阿美族的小孩。」她用國語答。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林桂枝。」
「你是漢人嗎?外省人嗎?怎麼叫這個名字?你再講一次叫什麼名字。」
這次她用台語答:「林桂枝。」
老人家說:「你不是阿美族小孩,你怎麼一直講別的名字,你媽怎麼叫你?」
「我媽叫我Kiku(桂子)。」她老實回答。
老人家聽不下去了。因為在傳統的場域,無形的靈都是聽族語的,沒有族語的名字怎麼行?「那這樣好了,」老人家說,「我看你神似我家裡一個叫巴奈的老人,叫你巴奈可以嗎?」她就這樣獲得了巴奈的名字。回到家她就告訴媽媽,說山上的老人家給我取名字叫巴奈,可不可以?媽媽說,可以,姑婆就叫巴奈。再加上她父親的名字母路,作為阿美族的巴奈.母路才眞正誕生了。
不過,即便獲得了新的名字,她還是沒能徹底扭轉對部落的印象,直到接觸了Sikawasay的祭師文化。她愛和老祭師們在一起,看她們的臉,聽她們唱歌,哪怕是講最低俗的笑話,都覺得很有魅力。
就算是郊遊,祭師們也隨身攜帶米酒和杯子,如果感應到這段路上有認識的靈群,就會下車祭祀。阿美族的米酒,禮敬無形的靈者,山裡的、海裡的、大自然的、隨處的……她從來沒有發現自己的民族這樣美麗。
「從來沒有人可以這樣,用靈魂的方式去活。」她覺得自己看到了一個民族很細緻的、不為人知的部分,然後也慢慢地,開始看到自己。
她決定眞的改名字,改身分證上的名字,還逼著自己太魯閣族的丈夫也去改回族語名字。她焦急地表達對自身文化遲來的認同,拋棄漢名,「我不知道我為什麼姓林。」她要做一個眞正的原住民。從此,花蓮吉安的薄薄部落,再沒有林桂枝,只有巴奈.母路。
拋掉宗教與學術,選擇「靈的世界」
在貓公部落獲得了名字的那一天,二十三歲的巴奈.母路在人群中央喝下長凳上的三碗米酒,開始不能自控地大哭。那個賜她名字的老人家說,你是女孩子,今天不該出現在這裡。她誤入的是豐年祭的第一晚,阿美族的男人在黑夜中體會母親子宮裡的黑暗,直到泛白的太陽出來,像是初生嬰兒見到母親的臉,大家便歡唱:「太陽媽媽!」女性是媽媽,是太陽,怎麼可以和男性一起出現在黑夜呢?
她回憶自己的哭,覺得是因為靈魂首次與祖靈相遇,誤入了神靈的禁區。做田野調查的時候,她就常夢見已故的祭師們。「在夢裡,有人一直唱,床邊有一堆人跳舞,床的地板都『咚咚咚』,也不知道是醒的還是夢的,半夢半醒。」第二天,她找老祭師解夢,對方不敢明言,只說:「妳最好少夢這些。」
那時候只有大祭師Kamaya最早認定巴奈.母路會成為祭師。那是在二十年前,巴奈.母路抱著她的小嬰兒,帶著奶媽一起去看Sikawasay,做田野調查,大祭師突然對她說:「來來來,進來,衣服脫掉,穿這個(祭師的)衣服。」
她雖然心中有疑惑,還是順從穿上了。直到二○一三年,Kamaya 大祭師去世,其他的祭師們才告訴她:「我們早就知道,她那個時候就想讓你慢慢留下來。」
成為Sikawasay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絕大多數的Sikawasay 都是因為自己或家族有人生病,才不得不履行天職。「神靈喜歡你,才使你生病,要你把靈魂交給祂牽制。」Sikawasay沒有收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能拒絕部落的任何儀式請求,終生禁食雞、蔥、蒜、羊、狐、兔。儀式期間禁食蔬菜和魚類,且不能與異性互動,不碰生水,不可遠遊。
巴奈.母路雖然研究Sikawasay多年,但眞要成為「全職」的Sikawasay,她從一開始就是抗拒的。更何況她出生在基督教家庭,信仰上的拉扯讓她很痛苦。「一邊是我親愛的爸爸媽媽,一邊是我親愛的族人。」她掙扎,也被家族質疑。家人說,Sikawasay是偶像崇拜,神靈一百多個,都是偶像,所以Sikawasay是魔鬼。家族中還有多位牧師,無不反對她和Sikawasay接觸。
多年來,爸媽總幫她解釋,說她只是去做記錄研究。但家族中暗流洶湧。她在家族中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小學三年級,她從單手伴奏開始一直在教會司琴,直到大學畢業,曾是人見人愛的
天使」。可是越接近Sikawasay,家族的人就越是罵她「魔鬼」,「看到我就跟瘟疫一樣跑掉,閃開,眼神都很不友善。」
和基督教不同,Sikawasay的信仰是泛靈信仰,老祭師說,多一個耶穌也可以祭啊,多一個神靈,有什麼不好呢?在困惑中,巴奈.母路又問自己的外婆,才知道原來外婆的母親也曾是部落中很厲害的大祭師,只是從外婆這一輩起,家族才改信了基督教。
她開始慢慢與自己和解,明白泛靈信仰是所有的靈去關照你這個人的靈,而基督教則是從耶穌的靈才看得到所有的東西,本質上都是同一件事。
「哪個宗教都一樣,處理的都是靈的事。沒有一個宗教會讓有靈魂的人與有靈魂的人不和,是不是?」她稱這個決定性時刻為,自己對靈的概念「通了」。從此她再沒有阻礙,可以放下心來,去成為Sikawas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