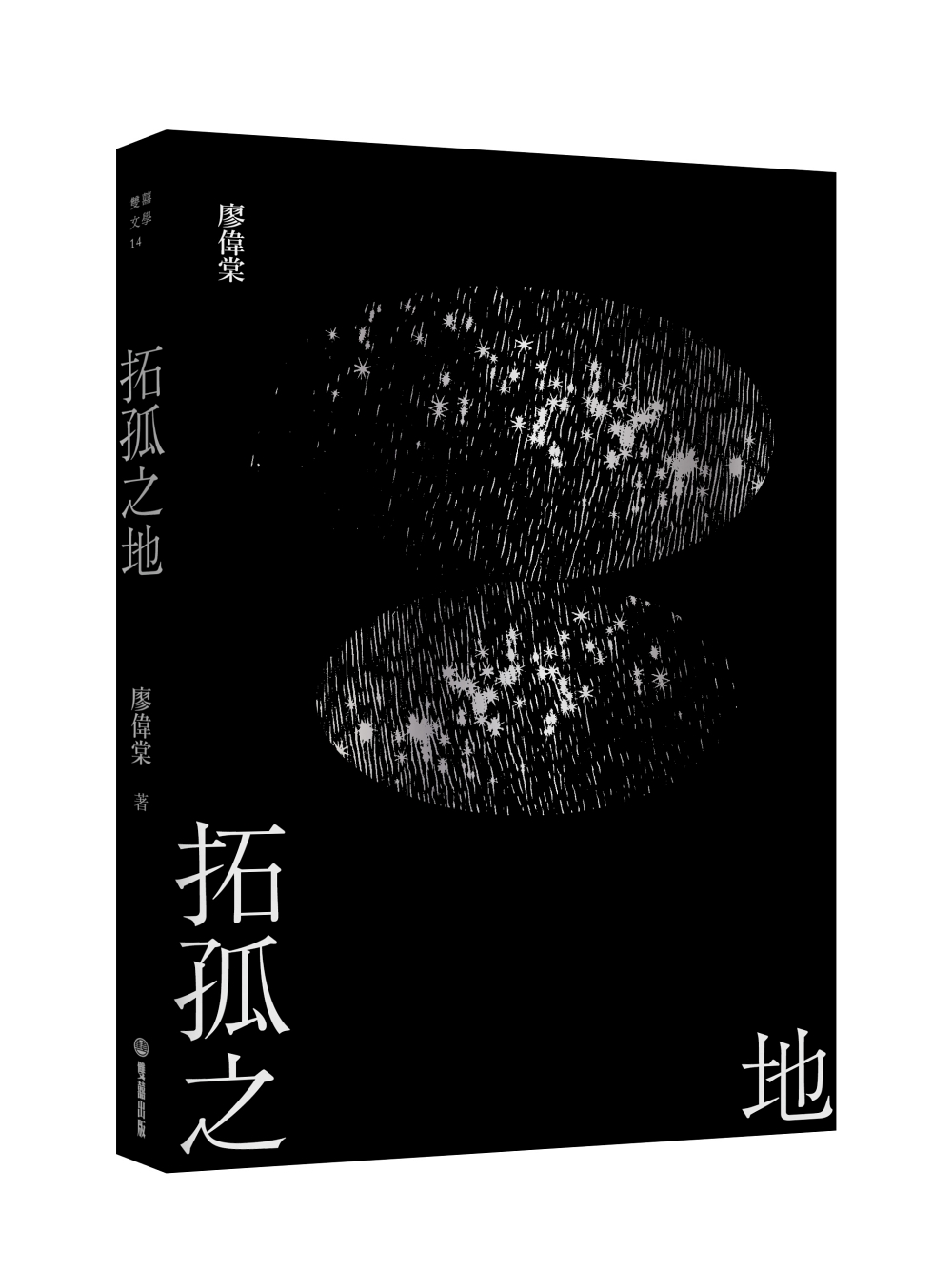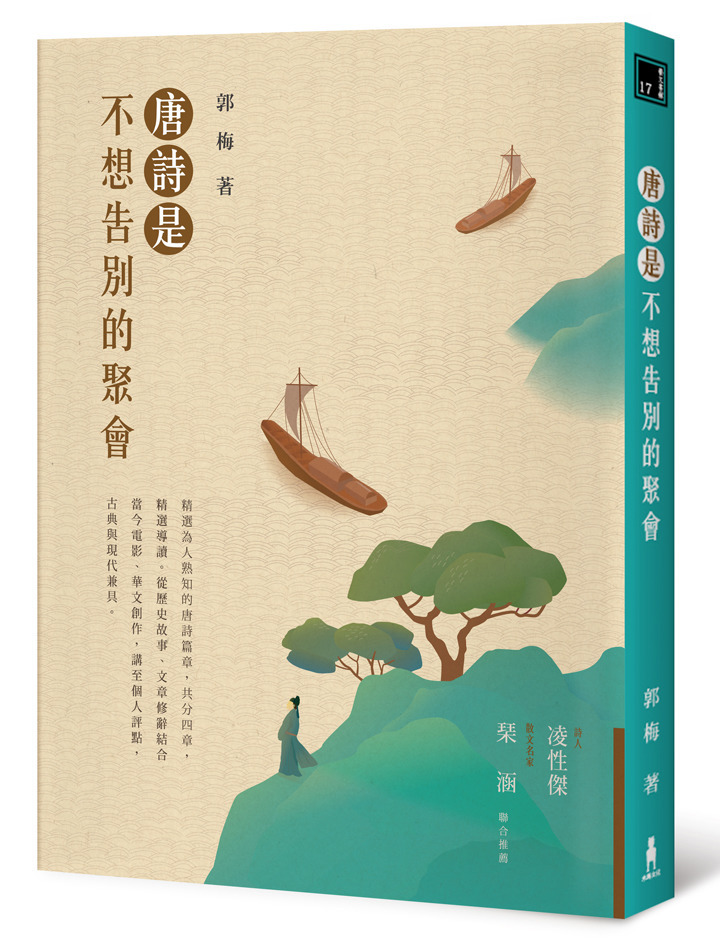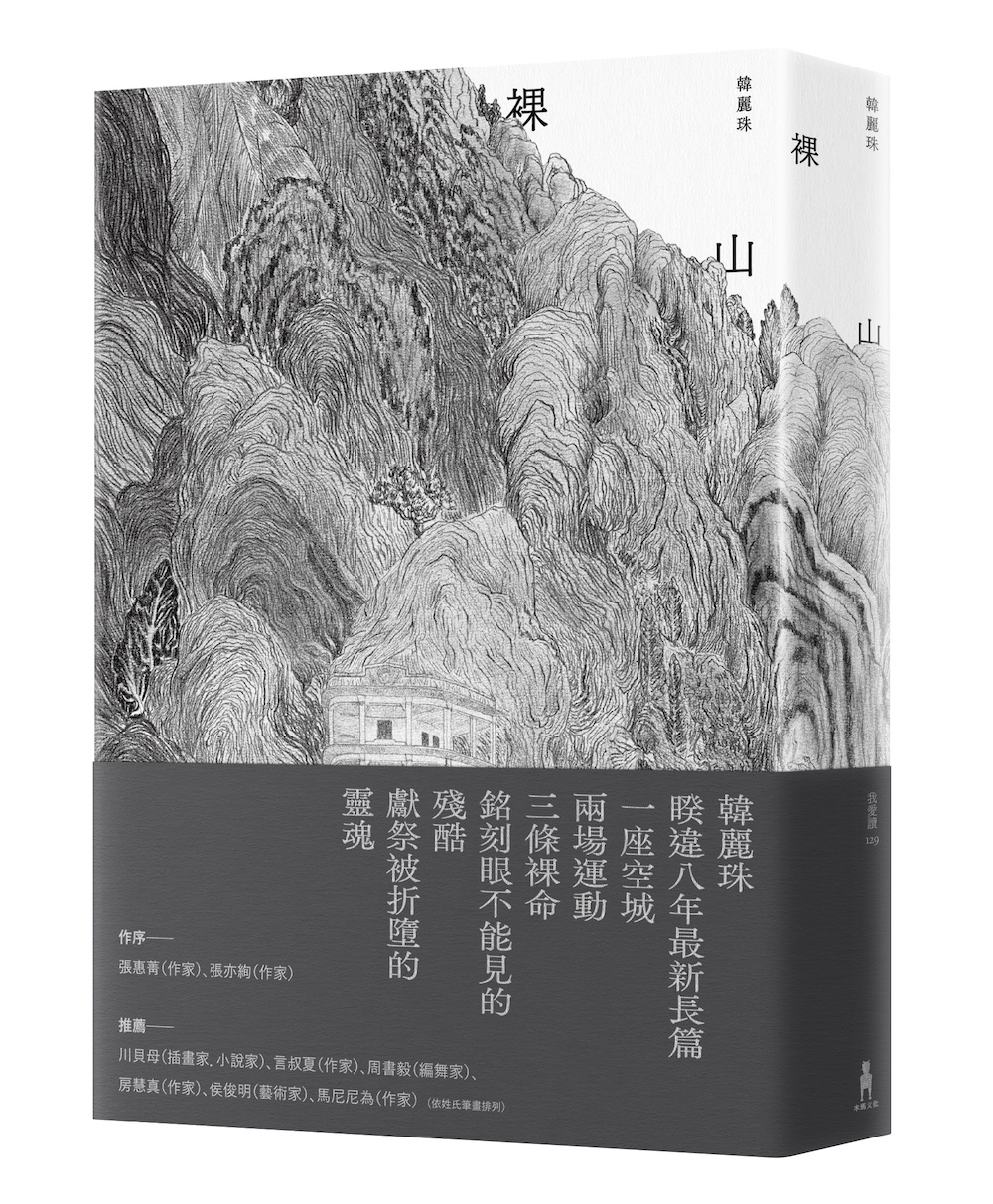好好吃飯,好好看書
時代艱難也引人入勝
長沙—上海—香港:女作家的人生地圖
飲食.離散.文學的況味
「故城,是故鄕的城,是故往的城」
「記憶在這裡發酵,蒸發、膨脹,刻骨銘心。」
——王璞
***
本書為作家王璞的回憶錄《故城故事》,敘述了文革知青一代,流轉多地,成長、讀書、謀生的故事。貫穿其中的,是各種地道吃食的鮮活味道,對書籍、文學與創作的堅執信念,還有多樣活潑的人物記憶。
長沙的童年:在文革批鬥抄家的陰影下,王璞以純摯的目光,看出微妙的人情,舊日的小吃,還有受壓抑的文藝單純曖昧。書中許多地點,現在長沙已不復存在,只在王璞的文學筆下留存。
上海的青春:八○年代的上海,王璞正在攻讀研究所;上海當年打扮、飲食、娛樂潮流的集體回憶,還有大學校園中知識青年生活風景、奇人異事,那個相信開放的希望年代,都是她的親身體驗。
香港的奮鬥:中年王璞到香港轉職謀生,一個知識份子在新移民群體中,與基層人士一起吃剩貨麵包,在報社學習老派傳媒人的功架與作風,並像地道香港人那樣以買樓為人生目標。
因為活過飢餓年代,她練就一手好廚藝;為了專心寫作,她毅然辭去了大學教師的工作。這就是王璞。
***
「只是希望我兒子和兒子的兒子、子子孫孫不要忘記這片土地上曾經發生過了甚麼,不想他們有重蹈那場迷狂的危險。」
「手中那塊餅乾一口咬下大半,誇張地、大力地嚼著,好像那不是一塊餅乾,而是我那長埋心中、業已變質變味、卻仍是嚼不碎咬不爛的上海印象。」
「那些詩行所建構成的虛擬世界,美麗奔放,色彩迷離, 周遭的喧囂與粗野就不再那麼難以忍受了,以至於我對閣樓同事們望向我的異樣目光茫無所覺,對她們含沙射影的議論也置若罔聞。」
「有些人,你明明把他們看得連腳下的塵埃都不如,對他們的行為言語不屑一哂,卻沒法把他們從心裡抹去。」
——王璞
★王璞極擅於說故事,文字活潑生動、敘事節奏流暢。
★不同地方、不同時代的生活與飲食文化在王璞的筆下活現。
★文字中體現王璞本身獨特、敢言的性格。
★記述文革、八○年代中國、回歸後香港獨有的時代風貌與歷史人情。
《故城故事》是一部另闢蹊徑的回憶錄。透過引人入勝的情節、時而幽默的筆觸,傳達背後的心理真實和深層知見。——鍾玲
大歷史和小歷史,融合在文字中,密不可分。——張曉宇
王璞以生動的文字、鮮活的描寫,把我們帶到了記憶深處的場景,還原歷史的真實,見證時代的多變,命運的不測,整部作品充滿非一般的感染力。——周蜜蜜
故園即心園,是寫作者的泉源。然而移動往往是為了讓自我更完整,開闢湧流的渠道。讀王璞《故城故事》,她在港中兩岸多地移動居住,「城」之所以有「事」可追認,「事」之所以依傍著「城」而發生,是因為人情交織其間,無數小記憶縫緊了空間與生命。——楊佳嫻
專文導讀
鍾玲/知名作家
張曉宇/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深情推薦
王安憶(作家)、周蜜蜜(作家)、洪愛珠(作家)、許子東(文化人、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楊佳嫻(國立清華大學副教授)、顏純鉤(資深出版人、作家)、顏擇雅(資深出版人、作家)
(按姓氏筆劃序)
王璞,生於香港,長於中國。五○年代初襁褓中被父母帶去北京,先後生活在北京、東北大興安嶺、長沙、上海、深圳,一九八九年最後一個月年近四十時回到出生地香港。
作過中小學代課教師、車工、電工、鐘錶修理工、編輯。
上海華東師大文學碩士、博士。一九八○年開始寫作。定居香港後作過報社編輯和大學教師。二○○五年辭去大學教職專事寫作。出版的主要作品有:
長篇小說《貓部落》、《家事》、《我爸爸是好人》等。
中篇小說《再見胡美麗》、《西灣河》、《水調歌頭》等。
短篇小說集《女人的故事》、《知更鳥》、《嘉年華會》等。
散文集《別人的窗口》、《紅房子灰房子》、《我想變成一本書》《小屋大夢》、《悠悠我心》等。
長篇傳記《項美麗在上海》。
文學評論:《一個孤獨的講故事人——徐訏小說研究》、《散文十二講》、《怎樣寫小說》等。
推薦語
推薦序一 由真相到真實:序王璞的《故城故事》
推薦序二 母親的記憶之城
第一部 大街小巷——長沙往事
一 家住左文襄祠
二 紫東園
三 西園
四 城門口
五 蘇家巷
六 北正街
七 五星花園
八 通泰街
九 六堆子
十 新開鋪
十一 如意街
第二部 島與河——上海往事
一 畢業留影
二 蘇打餅乾
三 牛仔褲
四 馬蘭頭
五 舞會
六 食堂情意結
七 大食會
八 四月的迷戀
第三部 歸人——香港往事
一 北角那座紅橋
二 紅梅谷
三 九龍灣的星星
四 琉璃街故事
五 香港仔阿潘
六 土瓜灣街市
七 美孚新村買樓記
八 天水圍的月亮
附:南湖渠·父親的日記
後記:我的故城
【推薦序】
推薦序一
由真相到真實:序王璞的《故城故事》
鍾玲/作家
王璞的《故城故事》是一本回憶錄,因為有很多沒有填補的時空,故非傳記體。它表面上看來是寫三座城市。本書分為三部:長沙往事、上海往事和香港往事。連每一部裡的章節,都是寫該城裡某些地點,像是我比較熟悉的香港,她寫北角的紅橋、香港仔、美孚新村、土瓜灣街市等。長沙部分寫的是她少女時期住過或去過的地方。上海主要是寫她讀碩士時的華東師範大學。香港寫她任編輯和在嶺南大學任教時,租賃的和購買的住處。但是三座城市這些地方只是下錨的定點,或者說,是這部作品的架構,王璞要寫的是別的東西。她跟我說過《故城故事》這本書到底講什麼:「所講述出來的一切都只是真相的點滴,只有跟其它許多點滴互相補充,才能拼接出比較接近真實的真相。」
那麼王璞探求和呈現的「接近真實的真相」是什麼?那些真相的點點滴滴應該就是她對該地景物的感受,她跟那裡的人發展的關係和在那裡經歷的事。所謂「真實」應該就是她透視這些感受、關係、經歷所得到的知見。這些真實、知見又是什麼呢?我粗略的看法,「真實」是指:在她少女時期,文革的殘暴和群體的卑俗,帶給她的創傷和恐懼;在她受難期間一些人帶給她的溫暖和她的感激之情;還有,生活艱困時期味蕾帶給她的幸福感以及味覺的發展和盛放。
那些創傷和恐懼是她當時拼命逃離的。長沙左文襄祠的九個院門都是「實心大門」,門上有「厚實沉重的黃銅門環」,文革期間夜晚門環一響,作者的母親會驚恐萬狀地低語:「抄家的來了!」作者多年後還會「從噩夢中驚醒,顫抖不已」。一直到三十多年後作者在香港搬進中產階級的嘉湖山莊,望著窗外一彎明月,想的卻是文革期間的處境:「身為介於革命和被革命之間的『可教育好的反革命子女』,忐忑、愁苦、驚懼、就連月亮看在眼裡也只覺得炫目而恐怖。」可見文革帶給她的恐懼感和創傷穿越歲月如鬼影附隨,這就是本作品的「真實」。
對純真的作者,人心的卑俗和惡意帶來極大的壓力。長沙城門口街市「肥頭大耳」的豬肉佬,對十四歲的作者猥瑣地說黃色笑話,她「頭腦轟地一聲炸了,轉身就跑」。作者透視這件事對自己深遠的影響:「物質世界是如此的鄙俗不堪,我盡量避開它,去精神世界尋找另一塊天地。有時間我就去閱覽室、圖書館」。對純真的作者,封建的偏見也帶來極大的壓力。像她這種追求精神世界的、感性的孤獨心靈,必然渴求一位可以傾吐心聲的知己,她任職代課老師時,竟然遇到了。伊凡是該校的音樂老師,因受過政治逼害,改教數學。他們兩人只要一見面就「狂聊」,「東扯西拉,時不時打斷對方」,有說不完的話。問題出在他是男老師,還有家小。他們除了談話,沒有做別的事,但已經被警告了。他們轉為下班後到街上一邊走,一邊聊,後來被同事看見。最後校長告訴作者學校不續聘她。當時社會嚴厲的男女之防,容不下這種難能可貴的知己之交。在群體有色眼鏡的壓力下,純真的心靈必然受創,這也是作品要呈現的「真實」。
作者承受政治壓力期間,有伸出援手的人,有給予溫暖的人。長沙〈六堆子〉一章描寫好友星星在作者心情極其低落時,拉她到家裡吃飯,星星的媽媽做她愛吃的酸菜炒辣椒和紅菜苔,一家子「嘻嘻哈哈談天說地」,作者感受到「畢竟,這個世界還有點甚麼值得我們活下去的。」星星的媽甚至幫她找到工作。作者透過寫這本書向失散的他們表示感激。書中還出現一位智者,在多次政治運動中逃過劫難,他就是作者的二舅,家族的掌門人,他把銀行事業打理得蒸蒸日上。解放後他卻把家族產業全捐給政府,他的明智和遠見,在於他堅持不出來擔任任何工作,不公開出聲;在於他堅持兒女「都學理工,遠離文字」。他還洞燭政府的宣傳煙幕,知悉歷史的真相,而且文化涵養深。我真的很高興還有這樣的智者安然度過驚滔駭浪。在冷酷殘暴之中,這丁點溫暖和清明的存在也是「真實」。
本作品不時強調的真相是,作者的味蕾自幼發達。長沙〈左文襄祠〉一章就描寫她心目中天下無雙的和記米粉。她甚至進入廚房去觀察米粉「香噴噴」的製作:「老師傅把醬油、香醋、麻油、細鹽、蔥花、香菜末、酸菜末、剁辣椒這些配料一一甩到我們擺放到案板上的大小鍋盆裡,再放上一大勺骨頭湯把這些調料沖開⋯⋯光是看著那種紅是紅綠是綠白是白的顏色就要流口水了」。可以想見這位少女的細心觀察必然發展為精湛廚藝,果然她和先生住在九龍美孚新村期間,常以「四涼菜八熱菜,一湯一甜品」宴客!和王璞交往的這十多年來我嚐過她的手藝多次,兩次是在她位於深圳高爾夫球場旁別墅式的平房,幾次是在她新界傍海的大廈中,每次她都以迅雷的速度烹飪出多盤美味,同時一邊悠然地跟我聊天,至今還記得她書中提過的紅白蘿蔔絲、馬蘭頭炒豆干之美味。
二〇二三年七月王璞由香港來高雄探訪我。本想開車帶她到壽山上看高雄全景,她卻說想去看街市;帶她吃過兩家餐廳,問她晚上要吃什麼?她回說六合夜市,令我滿頭霧水,看了《故城故事》才了解緣由,上海〈食堂情意結〉一章就是談她的吃食經歷。她童年、少年過糧食匱乏的日子,也經歷大饑荒,所以只要有得吃,不論食材貴賤,料理得美味就值得回味。前文說的酸菜炒辣椒就是例子,她說「一輩子吃不厭」!而且進餐的場所不重要,重要的是好不好吃和吃客們的心情。童年大興安嶺的林業局食堂、長沙巷子裡的食堂、華東師範大學食堂,都是她的「懸念」。
作者的「大牌檔情意結」始於她在香港任報社編輯的第一年,九龍灣牛頭角橋下的大牌檔就是她的樂園,因為她在其中享受到幸福,由分秒必爭的寫稿和編報解放出來,輕鬆自在地在攤位前逛;她也感受到人群的幸福:「每個人臉上似乎都有一種自得其樂的喜悅,每個人都好像一名巡遊在自己領地上的君王⋯⋯那些攤主也個個像佔山為王的寨主」。我想食堂、大牌檔的感受是作者呈現的「真相」,而眾樂我樂的幸福感就是她要表達的「真實」。那她在九龍灣大牌檔吃什麼?咖哩魚蛋串、香酥雞腿。哎呀!我知道為什麼今年七月王璞在六合夜市拉著我去鹽酥雞的攤位了!鹽酥雞是香酥雞腿的變奏。早知道我就不說夜市用的炸油可能有問題,不攔她追求幸福了!
寫作技巧方面,必要時王璞會精雕細琢。長沙〈新開鋪〉一章描寫她與知己伊凡最後一次見面的情形。作者被迫離開那間小學後,找到另外一間代課,一次她帶學生去青少年宮表演,在觀眾席中看到他。散場後他們在外面小樹林像以前一樣狂聊起來,他一看錶已經該回家了,他們在人群中走向車站,擁擠的人潮分開他們,雖然隔著人還繼續談話。她上了車,他們分別的一刻應該是刻骨銘心的,所以王璞在文字上下了功夫:「這時我已經擠進了車門,後面立時有好些胳膊、腿、身體擠壓上來,把我壓入車上那堆擠成一團的人眾中。我使勁扭頭往車下看,但這時車已經開動。影影綽綽,我彷彿看見一條手臂在人叢中朝我揮動。漸去漸遠⋯⋯」密集的肢體意象,人群身體的不斷擠壓,不言自喻地傳達其象徵意義:蒙昧的,形而下的群體,阻隔並壓碎了深刻真摯的友誼。
《故城故事》是一部另闢蹊徑的回憶錄,讀者會有深刻的感受。王璞撰寫三個城市的生活故事,透過引人入勝的情節、時而幽默的筆觸,傳達背後的心理真實和深層知見:一方面是文革和卑俗群體帶來的創傷和恐懼的夢魘,另一方面是溫暖的人心和作者稟賦高絕的味蕾,在嚴酷的現實裡兩者都為她帶來一陣陣幸福感。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內容試閱】
四 馬蘭頭
如今,當我坐在這座海邊小屋裡回首華東師大往事,最先湧入腦海的並非傳說中膾炙人口的麗娃河與夏雨島,事實上,在師大的三年中,我沒怎麼注意過那條早已黯然失色的、棄婦一般的河。河水因長年疏於清理,顏色渾濁,氣味難聞,經過河邊時人們往往情不自禁捂住鼻子加快腳步;至於夏雨島,我是後來從那些師大夏雨詩人們的回憶中才依稀想起這名字的。看到他們以那小島為背景的低吟淺唱,我才知道,當年我去食堂打飯天天要經過的那道不起眼的小橋,連接的就是讓他們魂牽夢繫的夏雨島。
我甚至也不太記得那些據說意義重大的活動:講座、研討會、演講會、音樂會、詩歌朗誦會、電影首映式、名人見面會⋯⋯校友們回憶錄中談到的那些當年盛事,我都沒甚麼印象了。或許我壓根就不曾聽聞,更別說去參加了。
伊文說我「自絕於人類」,有點誇張,說我自絕於人群卻是基本符合事實的。我刻意避開人多的地方,盡量把生活保持在三點一線的範圍:寢室、教室、和圖書館。所以回首往事,湧入我腦海的,大都是一些日常生活小景、柴米油鹽之事:食堂裡一毛五分錢一個的肉丸啦,後門外亂哄哄的農貿市場啦,寢室樓傳達室窗口掛著的一塊小黑板啦,每次走過那裡我都會站下來朝小黑板掃上一眼:有沒有我的信?門房阿嬸會把有信者的名字用粉筆寫在上面。字體東倒西歪的,我的名字常常被寫成「㺪」或者「仆」。那倒不都是她文化程度較低所致,雜誌社的編輯們都太忙了,尤其是在退稿信的信封上,筆劃能省就省。
我還清晰地記得傳達室旁邊那道木樓梯,扶手上的油漆早已剝落,但仍然能看出它原先是暗紅色的。還有那永遠陰濕的走廊。靜謐的午夜,走廊裡會驟然響起一道響徹天地的女高音,把我從夢中震醒:「我愛你中國,我愛你中國⋯⋯」、或是「我就是那冬天裡的一把火,一把火⋯⋯」這是對門那位校園歌手約會回來了。那位被愛情沖昏了頭腦又自戀的女孩,以為全世界都跟著她的作息時間表運轉。
我們房間斜對面的公共盥洗室,記憶中最是清晰。年久失修的木門,永遠關不嚴,繞牆排列的水龍頭中總有幾個是壞的,或是沒關緊。失眠的長夜,我聽著滴裡嗒啦的水聲,思想激烈地鬥爭:起不起來關上它呢?結果總是我那「關水關電強迫症」再次爆發,從床上一躍而起,低聲詛咒著衝到對面去把水龍頭關緊。
我會滿懷深情地回憶起我那個小電爐,我在上面煮過多少鍋紫菜蝦皮湯!還有西紅柿炒雞蛋、鹽水蟶子、水煮菜花。那都是當年我的拿手菜。有一次,我甚至在那電爐上燒了一鍋紅燒鴨。多年以後遇見一位同在一幢宿舍樓住過的師大同學,我忘了她是哪一系的,也忘了她住哪個房間,她卻一見面就指著我笑道:「我記得你記得你!你作的紅燒鴨真香!我在走廊那一頭都聞見了。」
我們寢室的室友們常會憶起的則是涼拌菜:涼拌海帶、涼拌黃瓜、小蔥拌豆腐、蘿蔔絲拌芫荽,捲心菜拌紅蘿蔔,對了,還有「馬蘭頭拌豆腐乾」。現在這道菜已成江浙菜的招牌菜式。其實早在八〇年代,它就已經是我們宿舍的招牌菜式了。而且我們的馬蘭頭真是野生的,現採現拌。
第一次跟辛西亞去校園裡採馬蘭頭,是在第二學年開學沒多久吧?天氣還有點冷,我在寢室裡看書還得帶手套。
我戴著手套披著棉衣坐在拉上了帳門的蚊帳裡。辛西亞則端坐在她桌子旁邊,我們各看各的書。寢室裡靜得像沒有人。但是突然,乒乒乓乓一陣響,辛西亞從桌邊站起來 了,衝著我的蚊帳發出邀請:「喂,咱們出去走走好嗎?」
「你是說我?」我從蚊帳裡鑽出頭來,愕然望著她。
辛西亞跟我同系又同屆,我們之間的年齡差距也比伊文小一點,但我跟她的交流比跟伊文少多了。作宿友也快半學期了吧,我跟她見面的次數屈指可數。她是上海人,家離學校不遠,家裡的事又多,她一星期倒有五天是住在家裡的。有時還一連幾個星期不見人影。就算她來了,也只跟我打個招呼而己,因為她跟伊文喜相逢似地時刻黏在一起,嘰嘰喳喳地有說不完的話。她倆一進校就是宿友,在先前那間寢室就結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誼,她們溝通起來甚至都不用語言了:「昨天老馬的課好險⋯⋯差點被她⋯⋯」「那你怎麼⋯⋯」「老辦法囉⋯⋯」這樣一些半截句子加上心照不宣的眼神,就可達至互相的了解,讓本來跟生人一起就沒話的我更加沒話。
那天大概是我和辛西亞第一次單獨相處。伊文好像去了親戚家。我獨自一人在寢室,就沒去教室了。辛西亞卻不期而至。而且,她沒像平時一樣放下點甚麼東西或拿上點甚麼東西就走,而是一屁股坐在她的書桌旁就不動了。
我透過蚊帳朝她瞥了一眼。不知是不是因為寢室的光線不好,我覺得對面那張面孔神色有點落寞,跟我平時看到的辛西亞不大一樣。平時她話雖不多,但算得上是個陽光女孩,總是興致勃勃光采照人。當然啦,世界上所有的好事都讓她佔全了:革幹出身,家境優越,她是家中三姐妹中的老么,肯定受到家中所有人的寵愛。這從她每次從家裡來都帶著菜就看得出來。那些菜都很講究地裝在漂亮的小食盒裡,色香味俱全,一看就是特意精心製作的。
辛西亞高中畢業時,上山下鄉大潮已經過去了,加上她姐姐已經下了鄉,她便得以留在上海分配工作,到菜市場作營業員。這工作雖然普通,卻曾經是我夢寐以求的美差。這還不算,兩年之後中國恢復高考,辛西亞一舉考上華東師大。師大畢業後又一舉考上研究生。這樣的幸運兒還能有甚麼不如意事嗎?
我決定不跟她打招呼。說甚麼好呢,何況,也許她根本就沒發現我的存在。
所以乍一聽她向我發出一起出門走走的邀請,我一時還真反應不過來。
「一起?出去走走?現在?」我又問一句。
「對。現在。」
「去哪裡呢?」
辛西亞淡然一笑:「隨便走走嘛,這麼好的太陽。」
陽光真的很好。當我和辛西亞走出宿舍,站在宿舍前的那片空地上時,我才發覺,春天來了,陽光暖洋洋的。
我看了看錶,下午兩點多。平常這時候,我不是在教室就是在圖書館,要不就在寢室,所以眼前的風景對我來說是全新的:天空又大又藍,對面那個足球場靜悄悄的,除了陽光,闃無一物。那條平時總是熙熙攘攘的林蔭道也人影寂寥。樹葉在風中嘩嘩嘩發出快樂的喧響。昨天那些樹還是光禿禿的!難道春天是一夜之間來到的?
「去哪裡呢?」我又問了一句。
辛西亞也在東張西望著,似乎跟我一樣也被眼前這一片景致鎮住了。「去哪裡呢?」她像回聲一樣重複著我的話。站在陽光下,她的臉色比剛才好多了,雖然有點蒼白。
也許剛才真的是寢室光線太差。這種四顧罔然的神氣使得她像個小女孩,令我奇異地想起一個早已忘卻的場景:多年前的一個夏天,我跟好朋友孫桂琴一道跑在大興安嶺的原野上挖野菜。
「可惜這裡沒有野菜。」我自言自語地道。
誰知辛西亞眼睛一亮,道:「有的呀!前天我還在河邊看到馬蘭頭了。馬蘭頭你知道嗎?」
「不知道。就是馬蘭花嗎?」
那的確是我第一次聽說馬蘭頭這個詞語。後來,每逢我讀周作人《故鄉的野菜》,總會想起當時辛西亞循循善誘的聲音:
「不,不是馬蘭花。馬蘭頭是一種野菜的名字。跟薺菜一樣,是我們江浙一帶最多的一種野菜。三四月天正是馬蘭頭最佳生長期,有時就連我家門口的小路上都可以看到。」
「能吃嗎?」
「當然能了。可以作很多道菜呢!」
我和辛西亞立即作出決定:去採馬蘭頭。有了目標就有了熱情,我們各人手持一根小木棍,像作著發財夢的淘金狂,目不轉睛地掃視腳下的每一寸土地,遊走在校園裡的大小草地,作地毯式搜索。辛西亞可以算是誨人不倦了,她不厭其煩地給我指點哪是馬蘭頭,哪是馬齒莧,哪是車前草,哪是跟它們長得相像的野草。還絮絮叨叨地給我講著馬蘭頭菜譜:清炒馬蘭頭、涼拌馬蘭頭、馬蘭頭蝦皮湯、馬蘭頭炒豆腐乾⋯⋯「涼拌?要不要放蒜末?」我忍不住打岔,涼拌菜可是我的拿手好戲。
「不要。」辛西亞斬釘截鐵道,轉過頭譴責地看我一眼,「涼拌馬蘭頭最忌放蒜末!那會把它們的原汁原味破壞掉。」
原來她竟是個烹調大師,說起作菜來頭頭是道。那些帶到寢室裡給我們分享的精美菜餚,原來都是她親手製作的。
「上星期那盤三黃雞也是你作的嗎?」我問。那道菜給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好吃得要命還不算,那些切得大小均勻的雞塊被碼得整整齊齊裝在食盒裡,上面綠是綠黃是黃地澆著調料。美麗得讓人感到吃掉它簡直是一種謀殺行為。
「當然啦,從殺雞到製作到裝盒皆乃本人親力親為。」辛西亞驕傲地說。
「你還會殺雞?」我驚異地打量著清秀文靜的辛西亞。
「豈止會。本人榮獲過上海市殺雞比賽亞軍,紀錄是從殺到去毛一分鐘四十多秒,記不太清了,總之沒超過兩分鐘。」
活潑潑的太陽暖洋洋地照著,照在我們兩個人身上。還沒走到麗娃河,兩個書包已經裝滿了。馬蘭頭簡直俯拾即是。它們從路邊的小樹叢、從石凳旁邊的青苔上、從我們舉目所見的一徑一石之間冒出頭來,挑逗地、炫耀地在風中搖擺著,以至於直到如今它仍然是我最熟悉的一種野菜。作夢我都會看見它,當然是在美夢裡:那一片平易近人的綠,生機勃勃地從四下裡蔓延,無邊無際,無邊無際的綠,無邊無際的歡喜。
後來,我們就來到了大草地,不記得是一舍前的那片草地,還是理化大樓前的那片草地了。只記得非常開闊,非常非常的開闊。下午最後一堂課的下課鈴聲還沒有響起。四周圍的路上已經有了來來往往的人影,但草地上人還不多。我倆伸展著胳膞、腿,背靠背地坐在草地上。西斜的陽光更加溫和了,也更加明亮。我們坐在那裡看人看天。旁邊放著兩個裝滿了馬蘭頭的書包。兩個鐘頭之前我倆幾乎還是陌生人,現在卻是可以互相倚靠著坐在一起信口開河的好朋友了。
「天好大好高呀!」辛西亞說。
「是呀。」我說。
「相比之下我們太渺小了。是吧?」辛西亞說。
「是的。」
「所以我們每個人的悲歡⋯⋯」
「其實也不是自己所感覺的那樣了不得。是吧?」我搶著說。
「是的呀。」
伊文回到宿舍時,驚喜地發現我跟辛西亞正圍著小電爐熱火朝天地忙碌著,書桌變飯桌,盆盆碗碗的一派青綠,好一頓馬蘭頭大餐!清炒馬蘭頭、馬蘭頭蝦皮湯、馬蘭頭炒雞蛋、馬蘭頭拌豆腐乾⋯⋯辛西亞果然不是吹的,看她切菜的架勢就把我鎮住了,手起刀落,砉然響然,而從刀下綿綿而出的蔥絲和薑絲,用細如髮絲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
二十多年後,有一次我回上海見到辛西亞,她突然說:「你還記得那次我們去挖馬蘭頭的事嗎?」
「記得。當然記得。」
「我應當謝謝你。」辛西亞說,「那天我特別難過,是我好朋友的忌日。一個月前的這天,我去她家找她,明明從窗簾裡看到她的影子,敲了半天門,也沒人來開。後來⋯⋯後來我砸開門⋯⋯可已經晚了,我來晚了,要是我早來一步,要是頭天她打電話給我時我立即過來了,也許她⋯⋯想起這我就特別難過,那天我覺得自己簡直要崩潰了,還好有你陪著我⋯⋯」
我沒有告訴辛西亞,其實我才應該感謝她。那天我遭遇到我的滑鐵盧,三封退稿信從不同的城市寄到。其中有一篇小說本來已經說要發稿了,現在卻來了封冷冰冰的信通知我:因故從校樣中抽下。我開始懷疑自己這麼多年的堅持。
我沒告訴辛西亞這些。有時候,心裡的話太多了,感動太深了,反而不知從何說起,而說出來的,竟都是些廢話和蠢話,例如:「那年我們真年輕。」「沒想到在校園裡也能挖野菜。」「馬蘭頭拌豆腐乾真好吃。」等等。
「你記錯了,」辛西亞拿紙巾擦了擦眼睛道,「那天我們沒作馬蘭頭拌豆腐乾。那麼晚了到哪裡去買豆腐乾呢?後來我就說那不如作馬蘭頭拌肉末。你說那好那好,你不記得了嗎?你說著就自告奮勇跑去食堂買肉丸。」
啊,我也想起來了。馬蘭頭拌肉末,這是我們那天合力創作出來的一道新菜式。說話之間,我似乎聞到了從那盤菜裡飄逸而出的麻油香,我甚至清晰地看到了那一手端著個菜盆的瘦小身影,奔走在那條從食堂到宿舍的路上,忙叨叨的,興沖沖的,好像前面那座燈光閃灼的大樓裡有一大群家人在等著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