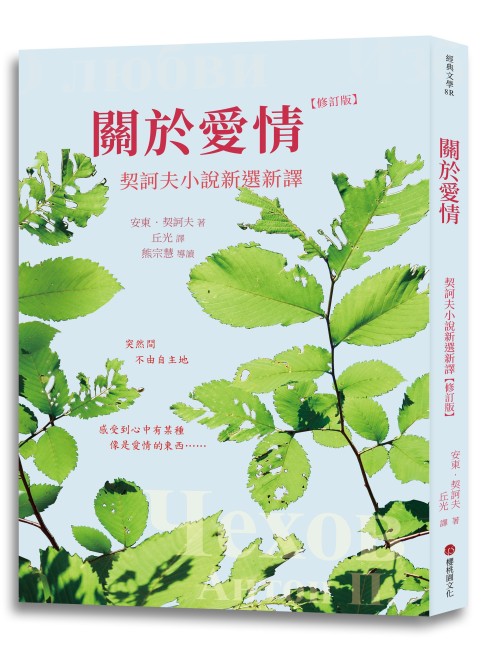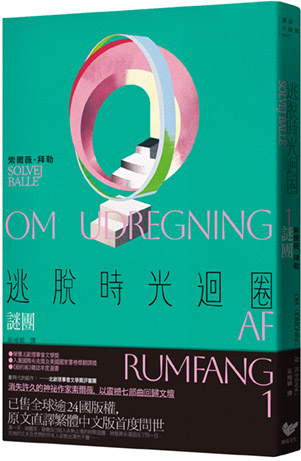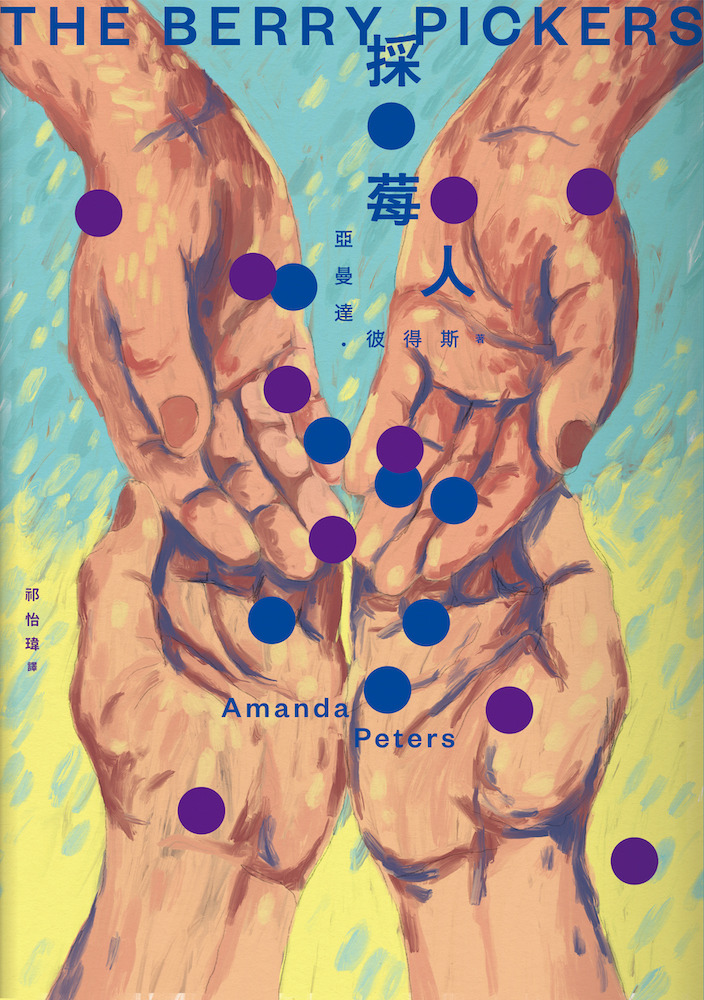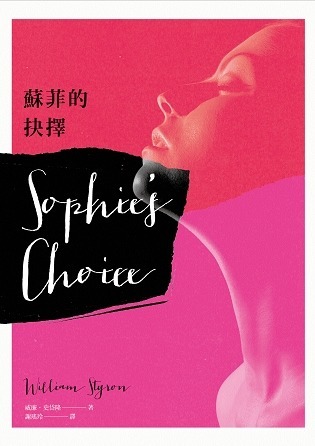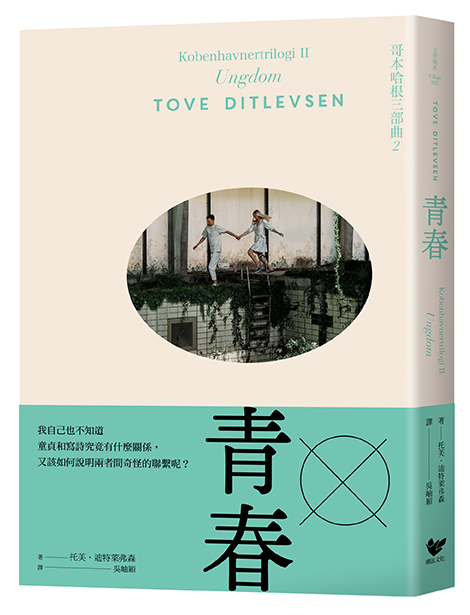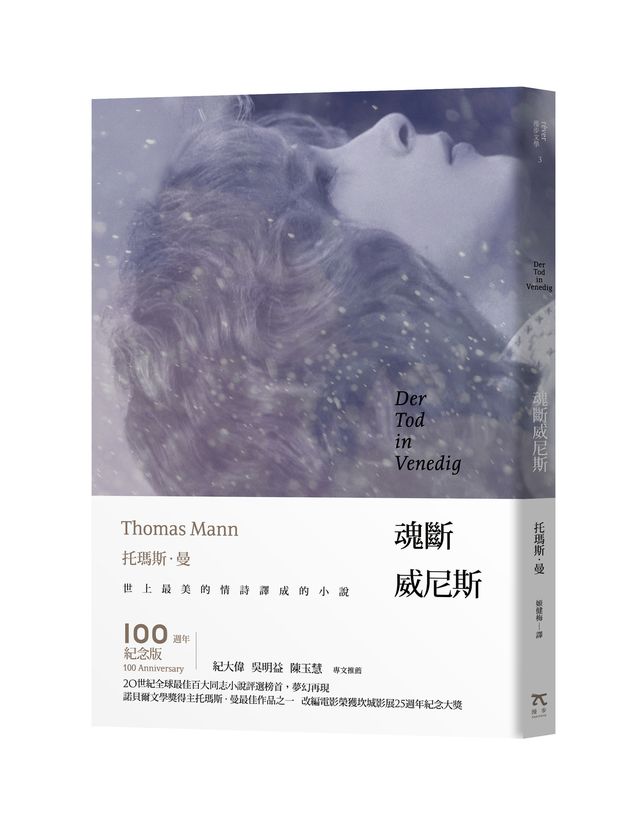本書收錄十篇以愛情為主題的短篇小說,包括審察美與現實衝突的〈美人〉、天真少女幻想愛情紛紛的〈看戲之後〉、中年男子胡想不倫戀的〈在別墅〉、憧憬婚姻卻陷入情欲糾葛的〈泥淖〉、擺布丈夫的妻子〈尼諾琪卡〉、永遠困擾女人的兩種情人〈大瓦洛佳與小瓦洛佳〉、遇見真愛的〈不幸〉、出軌前待解的課題〈關於愛情〉、浪蕩世間找尋永恆眷戀的〈帶閣樓的房子〉、重新發現愛情的奇妙時刻〈情繫低音大提琴〉──契訶夫藉由捕捉男女老少面對愛情時刻的微妙心理,試圖探索愛情是怎麼發生又如何消逝。這些人物往往在感知愛情的那一瞬間,人就變得渺小、糊塗、猶豫了,踏不出那一步,而少數勇於前行的人,離幸福卻往往「還有一段很長很長的路要走」……這些故事告訴我們,在發生愛情到獲得幸福之間的蜿蜒小徑上,人心情感和現實生活是如何糾纏又無端變化。
契訶夫細細描繪出消退的、想像的、看似即將來臨的種種愛情樣貌,有期待、溫馨,也有荒謬、可笑,還有無力、困頓,在故事情節推展中,我們漸漸發現,在愛情的脈絡之下,上演的卻是人心所面臨的困境──
「他已經不能夠再去愛了!就在他喪失對人的信任之後,心中滿是空虛,他便成了厭世的人。生活是什麼?我們為了什麼而活?生活是空想、夢想……是腹語……但是他站在睡著的美人面前,突然間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心中有某種像是愛情的東西。他久久站在她面前,眼睛貪婪地望著她……」──〈情繫低音大提琴〉
契訶夫要說的無非是面對愛情即面對生活,無論最後是童話般的快樂結局?還是永恆難解的僵局?從古至今似乎都一樣費解,然而,最要緊的,是不是誰能夠抓住愛情初湧感動人心的那一剎那,誰就掌握了翻新生活的契機?──契訶夫總是把答案留在讀者心裡。
安東‧契訶夫(Anton P. Chekhov, 1860-1904),俄國小說家、劇作家,他的小說流傳至今讓人一讀再讀,他的戲劇影響世界一再搬演。契訶夫的偉大在於創新了小說和戲劇藝術,在文學上有著承先啟後的地位。或許可以說,他永遠是最新的作家,某種程度上他幫我們在文學藝術上找到了得以重新開始的「零」,他在作品中所探討的問題,使我們看清了新舊生活的交界。
契訶夫出生於俄羅斯南方亞述海濱的港市塔干羅格,祖父自農奴贖身,父親經營小商鋪,十六歲時父親因債務問題帶全家避走莫斯科,留下他獨自在當地生活至中學畢業,除了劇院活動的歡樂時光外,大體上這是一段慘澹的青春少年期,但他從沒怨嘆生活的不幸,而是轉化成未來的文學創作。十九歲進莫斯科大學醫學系,就讀期間為了賺稿費補貼家用,開始投稿短文至幽默雜誌,畢業後持續寫作,漸漸成為職業作家。他雖然沒有正式走上職業醫生一途,但會抽空為平民看病,尤其對當時的鄉村霍亂防疫工作投入最多。
醫學的科學思維也影響著契訶夫的文學寫作方式,他曾為自己的客觀寫實立場辯護:「小說家不該是自己筆下人物的裁判法官,而該是中立的見證人……讀者才是陪審團,自會做出評價。」
把醫學當妻子、文學當情婦的契訶夫,一方面用筆寫小說戲劇,針砭讀者觀眾的心理問題,另一方面用醫術診斷病患的生理疾病,此外,還參與籌辦學校、救助窮困農民等公益活動。而他自己卻在盛年死於肺病,直到死前幾個小時還不忘口述創作幽默故事給妻子聽,讓他現實生活中真正的妻子歡笑。
這就是永遠值得我們一讀再讀的契訶夫。
丘光,國立政治大學東語系俄文組畢業,俄羅斯國立莫斯科大學語言系文學碩士,長年從事俄國文學推介,譯作有:《帶小狗的女士:契訶夫小說新選新譯》、《當代英雄:萊蒙托夫經典小說新譯》、《地下室手記:杜斯妥也夫斯基經典小說新譯》、《關於愛情:契訶夫小說新選新譯》、《海鷗:契訶夫經典戲劇新譯》、《白夜:杜斯妥也夫斯基經典小說新譯》等。
美人
看戲之後
在別墅
泥淖
尼諾琪卡(愛情故事)
大瓦洛佳與小瓦洛佳
不幸
關於愛情
帶閣樓的房子(藝術家的故事)
情繫低音大提琴
【導讀】 契訶夫小說中的幾種愛情 文/熊宗慧
【譯後記】 關於愛情,契訶夫要說的是 文/丘光
【契訶夫年表】
帶閣樓的房子
1
大概六、七年前,那時候我住在T省的一個縣裡,在地主別洛庫羅夫的莊園,他是個年輕人,非常早就起床,經常一身輕便外套四處走,每晚喝啤酒,並且老是跟我抱怨,說他從來沒在任何地方或在任何人那裡得到過同情。他住在花園裡的廂房,而我住在莊園老宅的主屋,一個有列柱的寬闊大廳裡,除了一張我用來睡覺的大沙發外,沒有其他家具,另外還有一張可以讓我擺開帕西揚斯紙牌的桌子。那裡,甚至天氣平靜時,在那老舊的阿莫索夫暖爐裡也好像有什麼東西嗚嗚作響,而打雷下雨時整棟房子會顫動,好像就要迸裂解體,尤其在夜晚,當十扇大窗全數突然間被閃電打得光亮的時候,是真有點可怕。
我命中注定要閒散過活,便壓根什麼事都不做。我會一連好幾個鐘頭看窗外的天空、鳥兒、林蔭道,閱讀所有人家寄給我的東西,或者睡覺。偶爾我會走出家門,到處閒逛到深夜。
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我無意中誤入某個陌生的莊園。太陽已經隱沒不見,夜晚的暗影拖曳在開花的黑麥田上。兩排密植相當高大的老雲杉,聳立得像是兩面連綿不斷的牆壁,形成一條沉鬱美麗的林蔭道。我輕易爬越籬笆,沿著這條林蔭道走,在鋪有一寸厚的杉樹針葉地面上,走起路來很滑腳。那時候寧靜,昏暗,只在高高頂端的某些地方閃動著亮金光芒,還有在蜘蛛網上漫淌著七彩霓虹。針葉的氣味濃烈滯悶。然後我轉往長長的椴樹林蔭道。那裡也是一片荒蕪老舊,腳底下去年的樹葉憂傷地簌簌沙沙,暮色中林木縫隙裡的陰影遮遮掩掩。向右轉去,在一個舊果園裡,有一隻黃鸝鳥嗓音微弱,不太情願地鳴唱,應該也是隻老鳥了。不過椴樹到這裡就沒了;我經過一棟白色房子,帶有露台和閣樓,我面前忽地展開一片風景,那是舊時貴族風格的院子,一池大水塘,附設浴棚,叢叢柳樹綠意盎然,一座村莊落在對岸,高窄的鐘樓上十字架閃耀,映出日落餘暉。這一瞬間,某種親近又非常熟悉的魅力喚醒了我,彷彿我小的時候就曾看過同樣的這幅景象。
在白色的石頭大門旁,有一條從院子通往田野的路,在那陳舊堅固、有獅子雕塑的門邊,站著兩個女孩子。其中年紀大一點的那位,身材苗條、臉色蒼白、非常美麗,滿頭蓬亂的栗色頭髮,一張倔強的小嘴,表情嚴肅,幾乎不太理我;另外一位就年輕許多──大概十七、八歲,不會再多了──同樣身材苗條、臉色蒼白,大嘴,大眼,她驚訝地望著我,我走過去的時候,她用英文說了些什麼,並感到不好意思。我覺得,這兩位可愛的人是我早已熟識的。我帶著這份感覺回到家裡,彷彿作了一場好夢。
在這之後沒多久,有一天中午,我跟別洛庫羅夫在家附近散步,突然間,草地沙沙作響,一輛彈簧馬車駛進庭院來,上面坐著上次見過的其中一位女孩,是那位姊姊。她拿認捐簽單過來,請求援助火災受災戶。她眼睛沒看我們,非常認真又詳盡地解說,在西揚諾沃村有多少房屋遭到火災,有多少男女老少流離失所,因此火災受災戶委員會打算在第一時間採取行動,她現在是其中的委員之一。她給我們簽完名後,便把簽單收好,立刻跟我們告辭。
「您完全忘了我們,彼得‧彼得羅維奇,」她把手伸給別洛庫羅夫,並對他說。「您過來坐坐吧,如果N先生(她叫了我的姓氏)想來看看崇拜他天分的人們是怎麼過生活的,也歡迎光臨,那媽媽和我將會非常高興。」
我鞠躬致意。
當她離開後,彼得‧彼得羅維奇開始談這位女孩的事,依他所說,她出身良好家庭,名叫莉季雅‧沃爾恰尼諾娃,而她和媽媽妹妹一起住的地方,也跟池塘對岸的村莊一樣叫紹爾科夫卡。她的父親曾在莫斯科擔任過要職,過世時是三等文官職銜。儘管家境很好,沃爾恰尼諾夫一家卻常年久居鄉村,莉季雅在紹爾科夫卡自家附近的地方自治小學當教師,月薪二十五盧布。她個人開銷只用這些錢,並對自己賺錢謀生引以為傲。
「有意思的家庭,」別洛庫羅夫說。「或許,我們看看什麼時候去拜訪他們。他們會很樂意見到您的。」
有一次在某個節日的午餐後,我們想起沃爾恰尼諾夫一家,便出發去紹爾科夫卡拜訪他們。他們一家,包括媽媽和兩個女兒,全都在。媽媽叫葉卡捷琳娜‧帕夫洛芙娜,看起來曾是個美人,現在已經虛胖得與年齡不符,氣喘得一臉病容,憂愁,漫不經心,很努力找繪畫的話題來跟我聊。她從女兒那裡得知我可能會來紹爾科夫卡,連忙回想著兩三幅我的風景畫作,那是她曾在莫斯科畫展上看過的,然後她問,我在那些畫裡想要表達的是什麼。莉季雅,或者像家裡都叫她莉達,比起跟我,她較常跟別洛庫羅夫談話。嚴肅的她笑也不笑,問他為什麼不在地方自治機關服務,還有為什麼他到現在從不參與地方自治會議。
「不好喔,彼得‧彼得羅維奇,」她責備地說。「不好喔。讓人羞愧。」
「確實,莉達,確實,」媽媽同意。「不好。」
「我們整個縣都落在巴拉金的手裡,」莉達轉向我繼續說。「他自己是地方自治管理局的主席,把縣裡所有職缺都分給自己的子姪和女婿,為所欲為。我們必須要去爭取。年輕人應該要為自己組織一個強勁的勢力,但您看,我們的年輕人都是什麼樣子。羞愧啊,彼得‧彼得羅維奇!」
我們還在談地方自治的時候,妹妹熱妮雅一直沉默著。她沒加入這個嚴肅的話題,在家中她還不被認為是成年人,而像是個小孩,大家叫她蜜秀斯,因為她小時候都這麼叫自己的家庭教師小姐。她一直好奇地看著我,當我翻閱相簿時,她會跟我說明:「這是舅舅……這是教父」,並用手指指引人像,這時候她會像小孩子一樣肩膀靠著我,我便就近看到她那單薄且尚未發育的胸部、細窄的肩膀、髮辮,以及腰帶緊束的纖瘦身軀。
我們玩槌球和草地網球,在花園散步,喝茶,然後花很長時間吃晚餐。待過廣闊空曠的列柱大廳之後,我覺得在這間不大卻舒適的房子還頗自在,裡面牆上沒有石印油畫,對僕人都稱呼您,在我看來,一切清新又純潔,多虧莉達和蜜秀斯在場,一切顯得體面又舒適。晚餐時,莉達又跟別洛庫羅夫談地方自治,談巴拉金,談學校圖書館。這是一位有活力、真誠又堅定的女孩,聽她說話很有意思,儘管她說得很多又大聲──大概是因為在學校教書的習慣。然而,我的彼得‧彼得羅維奇,他從大學時代以來就養成了一個習慣──把所有的談話都搞得像爭吵,他談話無趣、沒勁又冗長,還有一個明顯的企圖──要人家以為他很聰明又前衛。他邊說邊比劃著手勢,袖子弄翻了醬汁碟,沾得桌布上湯湯水水的,但除了我之外,似乎沒有任何人留意到這件事。
我們回家的時候,天色暗沉又寧靜。
「好的教養並不在於,你沒打翻醬汁灑在桌上,而在於如果有誰打翻了東西你不會去在意,」別洛庫羅夫說,嘆了一口氣。「是啊,美好的知識分子家庭。我落在這些好人之後了,啊,真是落伍!都是事業,事業!事業哪!」
他說,你想要當一個模範的農村地主,就得要做那麼多的工作。我卻想:這真是個難相處又懶惰的小夥子!當他說到嚴肅的事情,就會緊繃地拖長著聲音說:「欸──欸」,他做得也跟他說的一樣──慢吞吞,總是拖拖拉拉而耽誤時限。我真是非常不相信他會腳踏實地,因為我託他去郵局寄的信,他都可以一連好幾個星期隨身忘在口袋裡。
「最沉痛的是,」他走在我身旁喃喃說著。「最沉痛的是,就算你工作也不會得到任何人的同情。沒有任何同情!」……
(本文摘自《關於愛情:契訶夫小說新選新譯》[修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