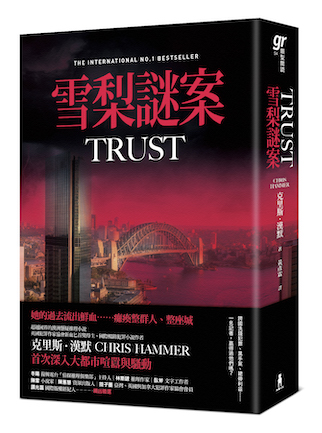回歸最受矚目非裔作家阿迪契的小說原點
一次收藏奠定文學大師地位的兩本成名作
《紫色木槿花》
「這一代最重要且最具創造力的小說家之一。」
非裔天才女作家阿迪契一鳴驚人的處女作
★★不列顛國協作家獎(2005)★★
★★赫斯頓/賴特遺產獎(2004)★★
★★布克獎入圍(2004)★★
★★女性文學獎入圍(2004)★★
從紫色的木槿花,我第一次聞到自由的香氣……
十五歲的凱姆比利與她的哥哥賈賈住在奈及利亞埃努古一座華麗的大宅中,他們衣食無缺,卻活在父親尤金嚴厲管束的陰影之下,時時刻刻都必須遵從尤金規定的宗教戒律行事。尤金是事業成功的商人,對外樂善好施,備受外界尊敬,但在家裡卻有著不為人知的黑暗一面。
當奈及利亞因軍事政變而陷入動盪時,凱姆比利與賈賈被送往恩蘇卡的姑姑家。姑姑家對他們來說猶如另一個世界,書架上擺滿了書本,空氣中瀰漫著咖哩與肉豆蔻的香氣,表弟妹的笑聲迴響在簡陋的屋子裡。在那裡,凱姆比利首次體會到了自由,並遇見了令她怦然心動的阿瑪迪神父……
《紫色木槿花》是阿迪契於二十六歲出版的處女作,一推出就好評不斷,奪下眾多國際獎項,令她成為炙手可熱的奈及利亞籍新世代作家。
這部小說從女主角凱姆比利的視角出發,細緻刻畫了青春期少女的情感經驗、威權家庭的創傷、性意識的啟蒙,乃至她掙脫枷鎖、追求自由的蛻變過程。既是一部動人的成長小說,也反映了天主教與傳統伊博文化的衝突,以及奈及利亞在建國後遭遇的後殖民處境。
《半輪黃日》
當新生的國家被戰火碾碎,他們仍然渴望著愛……
橫掃國際大獎,翻拍同名電影
非裔天才女作家阿迪契書寫祖國內戰的史詩之作
★★全球女性作家最高殊榮「女性小說獎」得主(2007)★★
★★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決選作品(2007)★★
★★「麥克阿瑟獎」得主(2008)★★
★★《時人》雜誌、《紐約時報》年度好書★★
「比亞法拉共和國或許消失了,可是幸好有阿迪契,比亞法拉不會被遺忘。」
一九六七年爆發的奈及利亞內戰,將這個國家撕裂成了兩半。在戰爭前,厄格烏是一名來自貧窮村莊的男孩,他在大學講師歐登尼伯的家裡擔任僕人;歐登尼伯的戀人歐拉娜出身奈及利亞的上層階級,她卻拋下優渥生活,和抱持革命思想的歐登尼伯同居;而理查,一位內向的英國人,則深深為歐拉娜神秘的雙胞胎姊妹凱妮內所吸引,並一步步建立了對伊博族的認同。
隨著豪薩族和伊博族的衝突愈演愈烈,伊博族宣布從奈及利亞獨立,成立比亞法拉共和國,內戰頓時爆發。他們的生活被徹底顛覆,分崩離析,只能在殘缺的愛中尋找希望……
《半輪黃日》是阿迪契在世界文壇奠定地位的代表作,她以細膩無比的洞察力,宏大且充滿野心的架構,將這場被世人遺忘的戰爭,和比亞法拉的國家命運,編織到她筆下栩栩如生的角色和故事中,使讀者為他們的處境時而揪心,時而感動。
這部小說精彩描繪出奈及利亞內戰中不同階級、種族、宗教、族裔、性別的人們的樣貌,也觸及後殖民、傳統文化、道德責任等議題。阿迪契不僅用文字讓比亞法拉重現世人眼前,隨之重生的還有人性和愛。
奇瑪曼達.恩格茲.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1977年生於奈及利亞埃努古市,在恩蘇卡的奈及利亞大學校園裡長大。19歲時到美國,並拿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與耶魯大學碩士學位。她是當代最知名的非洲作家之一,作品已經被翻譯成三十種語言。她的小說《紫色木槿花》(Purple Hibiscus)榮獲不列顛國協作家獎(Commonwealth Writers Prize)以及赫斯頓/賴特遺產獎(Hurston/Wright Legacy Award);《半輪黃日》(Half of a Yellow Sun)獲得女性小說獎(Women's Prize for Fiction)「贏家中的贏家」獎(Winner of Winners);《美國佬》(Americanah)獲得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她還著有短篇小說集《繞頸之物》、文集《我們都應該是女性主義者》(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以及《親愛的伊傑亞維萊》(Dear Ijeawele, or A Feminist Manifesto in Fifteen Suggestions)。她是2008年麥克阿瑟獎(MacArthur Fellowship)得主,2015年入選《時代雜誌》的百大人物。目前在美國及奈及利亞兩地生活。
葉佳怡
台北木柵人,曾為《聯合文學》雜誌主編,現為專職譯者。已出版小說集《溢出》、《染》;散文集《不安全的慾望》。譯作有非虛構作品《向獨裁者說不》、《永遠的蘇珊》;小說作品《消失的她們》、《聲音與憤怒》、《寂靜的緯線》;人類學作品《卡塔莉娜》、《尋找尊嚴》等。
《紫色木槿花》
譯者序 阿迪契的書寫開端:《紫色木槿花》和《半輪黃日》/葉佳怡
推薦序 掙脫成長框架,追尋行動與思想自由/陳之華
砸碎眾神
透過我們的靈魂對話
神的碎片
不同的靜默
《半輪黃日》
譯者序 阿迪契的書寫開端:《紫色木槿花》和《半輪黃日》/葉佳怡
推薦序 一場內戰的創傷裂痕,用世代生命去撫平與和解/陳之華
第一部 六○年代初期
第二部 六○年代晚期
第三部 六○年代初期
第四部 六○年代晚期
後記
《紫色木槿花》
砸碎眾神
哥哥賈賈不再參加聖餐式的那天,爸爸把沉重的彌撒書丟到房間另一頭,砸碎了陳列架上的陶瓷小人偶,我們家就此開始瓦解。當時我們剛從教堂回來,媽媽把沾了聖水濕漉漉的新鮮棕櫚葉片放在餐桌上,上樓換衣服。之後她會把棕櫚葉片編織成一個個鬆垮的十字架,掛在我們用金色相框裱起來的家族照片旁。那些十字架會在那裡待到隔年的聖灰星期三,到時候我們會再把這些葉片帶去教堂燒成灰。每年爸爸都會跟其他奉獻者一樣身穿灰色長袍協助分發聖灰。排在他前方的隊伍總是移動得最慢,因為他會用沾滿聖灰的大拇指用力在每個人的額頭上抹出完美的十字,並用意味深長的語氣、咬字清晰地緩慢說,「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
爸爸做彌撒時總會坐在第一排靠近中央走道那頭,身旁坐著媽媽、賈賈和我。他是第一個領受聖餐的人。教堂的大理石聖壇上立著等身大小的金髮聖母瑪利亞雕像,大多數人都不會在聖壇前跪下領受聖餐,但爸爸會。他會把眼睛閉得好緊,緊得幾乎像在扮鬼臉,然後盡可能伸長舌頭。結束之後,他回到位子坐下,靠著椅背看著剩下的教眾朝聖壇前進,看著他們往前伸的合十的雙掌像一枚立起來的碟子,那正是班奈迪克神父教他們擺的姿勢。雖然班奈迪克神父已經在聖艾格尼絲教堂待了七年,人們還是稱他為「我們那位新神父。」如果他不是白人或許就不會被這樣稱呼吧。不過他確實仍像是新來的。他的臉皮顏色像是濃縮煉乳以及山刺番荔枝切開後的果肉顏色,完全沒有在奈及利亞哈馬丹風吹拂七次後的年歲中曬黑,而他的英國鼻子也仍跟之前一樣皺縮窄小,就跟他剛開始來到埃努古時我擔心他可能吸不夠空氣時一樣。班奈迪克神父在這個教區做出了一些改變,像是堅持用拉丁文誦讀《信經》和《垂憐經》,對他來說用伊博語是不可接受的行為。此外,他希望我們盡量不要拍手,以免彌撒的莊嚴氣息受到破壞。可是他接受人們用伊博語唱聖餐禮中奉獻餅酒儀式的歌曲,他把這些歌稱為本土歌曲,而每當他說「本土」時,原本像是一條直線的兩片嘴唇會從兩邊往下垂,形成一個倒過來的U。在講道時,班奈迪克神父會提到教宗、爸爸和耶穌──就是以這個順序。他會利用爸爸這個例子來說明福音。「當我們讓我們的光照耀在人前,我們回顧的正是基督凱旋回城的那一刻,」他在那週的棕櫚主日如此說道。「看看尤金弟兄吧,他大可選擇跟這個國家的大人物一樣,他大可在政變後坐在家裡什麼都不做,以確保政府不會威脅到他的生意。可是沒有,他利用《標準報》說出真相,就算這樣做會失去廣告收入也一樣。尤金弟兄是為自由而發聲。而我們有多少人為了真相站出來?我們有多少人回顧起凱旋回城的那一刻?」
教眾們紛紛回應「對」或「神保佑他」或「阿門」,但沒有說得太大聲,以免聽起來像那些如蘑菇不停冒出來的五旬節教派教會;然後他們專注聆聽、安靜聆聽。就連寶寶們也停止哭泣,就彷彿同樣在聆聽。在某些週日,就算班奈迪克神父談起所有人早已知道的事,教眾也會認真聆聽,比如爸爸交出了最大筆的聖彼得節奉金以及聖文森.特德保羅慈善活動的款項。又或者他會談起爸爸是如何為一盒盒的聖餐酒付錢,還有那些修道院裡那群「可敬的姊妹」用來烤聖體的新爐子,另外還有班奈迪克神父特別投注宗教熱忱的聖艾格尼絲醫院。而我會坐在那裡,雙膝彼此緊貼,坐在賈賈身旁,努力讓自己一臉空白,免得露出驕傲表情,因為爸爸說謙虛是非常重要的。
爸爸自己也會在我望向他時擺出一片空白的表情,他在獲頒國際特赦組織的人權獎後接受了一場大採訪,當時在照片中就是留下那種表情。那是他第一次允許自己出現在報上的專題報導中。他的編輯艾德.寇克堅持要他受訪,表示這是爸爸理應獲得的待遇,還說爸爸太謙虛了。這是媽媽告訴我和賈賈的,畢竟爸爸什麼事都不太跟我們說。那種空白的神情會一直在他臉上直到班奈迪克神父的講道結束,直到聖餐禮的時刻正式到來。等爸爸領受過聖餐之後,他會坐回去觀察一個個走向聖壇的信眾,並在彌撒結束後向班奈迪克神父回報,而且是憂心忡忡地回報,比如表示有某個人已經連續兩個週日都沒來領受聖餐。他總是鼓勵班奈迪克神父打電話說服對方回到教會,畢竟能讓一個人連續兩個週日沒來參加聖餐禮的事一定是會讓人失去聖寵的致命罪行。所以爸爸在那個棕櫚主日沒看見賈賈走向祭壇時,一切都變了。我們到家時,他把那本裡頭有紅色及綠色緞帶探出頭來的皮革裝訂彌撒書用力拍在餐桌上。桌面是玻璃製的,很重的玻璃,但被拍得抖動起來,上頭的棕櫚葉片也一樣。
「賈賈,你沒參加聖餐禮,」爸爸沉靜地說,那語氣幾乎像是在提問。
賈賈盯著桌上彌撒書的模樣就像是在對那本書說話。「聖餅會讓我口氣難聞。」
我盯著賈賈瞧。他的腦子裡有神經接錯了嗎?爸爸堅持我們要把那東西稱為「聖體」,因為這個詞更能捕捉到其中的那種本質、那種神聖性,也就是基督身體的化身。「聖餅」聽起來太世俗了,彷彿是爸爸其中一間工廠會製造出來的產品──巧克力餅、香蕉餅,就是人們覺得要為孩子買比普通小餅乾更好的點心時會買的那種威化餅。
「而且神父一直摸我的嘴,我會想吐,」賈賈說。他知道我正盯著他看,也知道我震驚的眼神正在懇求他閉嘴,但他沒有望向我。
「那是我主的身體。」爸爸的聲音很低沉,非常低沉。他的臉已經腫脹起來,那些尖端蓄膿的疹子本來就散佈在他的每一吋臉皮上,可是此刻整張臉感覺更腫了。「你不能停止領受我主的身體。那是死亡,你很清楚。」
「那就讓我死。」恐懼已經讓賈賈的眼神黯淡下來,變得像是瀝青一樣的顏色,可是此時他望向爸爸的臉。「讓我死,爸爸。」
爸爸快速在房內望了一圈,彷彿在確認是不是有什麼東西從天花板掉下來,而且是他從未想過可能掉下來的東西。他拿起彌撒書甩到房間另一頭,瞄準的是賈賈。結果那本書完全沒碰到賈賈,卻砸到了玻璃陳列架,那可是媽媽常常擦得亮晶晶的陳列架。彌撒書打碎了架子最頂層、把那些只有指頭大小並扭曲出各種姿勢的米黃色芭蕾舞者陶瓷小人偶掃到硬邦邦的地面,接著彌撒書也落到地上。又或者該說是落到那些小人偶的碎片上。彌撒書躺在那裡,那是本巨大的皮革裝訂彌撒書,裡頭包含一個教會年三個週期的全部講經內容。
賈賈沒有動。爸爸則是整個人左右搖晃。我站在門邊看著他們。天花板上的風扇轉了一圈又一圈,連結在上面的燈泡彼此敲擊。然後媽媽走進來,她的橡膠拖鞋在大理石地板上發出啪—啪的聲響。她已經換掉週日穿的那種亮片罩衫及帶有蓬鬆袖子的上衣。現在只穿著週日以外穿的白色T恤搭配在腰間鬆鬆綁起的普通扎染罩衫。那件白色T恤是她和爸爸參加某場靈修活動獲得的紀念品,「神是愛」的文字就爬在她垂垮的乳房上方。她盯著那些小人偶的碎片看,然後跪下開始徒手撿拾。
唯一打破現場沉默的只有天花板風扇切開凝滯空氣時的呼呼作響。儘管我們的寬敞餐廳連接到一個更寬敞的客廳,我還是感覺好窒息。掛著祖父裱框相片的乳白色牆面感覺逐漸變窄,快要將我壓垮。就連玻璃餐桌都似乎正在朝我移動過來。
「Nne, ngwa。去換衣服,」媽媽對我說,她用低沉以及安撫人的聲音說出那幾個伊博字,但我還是嚇了一大跳。接著她一鼓作氣且毫無停頓地對爸爸說,「你的茶要冷了,」然後對賈賈說,「來幫我的忙,biko。」
爸爸在桌邊坐下,他用邊緣有著粉紅花朵圖樣的瓷器茶組倒出茶水。我等他要求賈賈和我也去嘗一小口,他以前總會這樣做。那是「愛的一小口」,他是這麼稱呼的,因為你會把你愛的事物跟你愛的人分享。來嘗這愛的一小口吧,他會這麼說,然後賈賈會先去喝。接著我會用雙手捧住茶杯舉到唇邊。就只有一小口。茶水總是太燙,每次都燙傷我的舌頭,要是那天的午餐放很多胡椒,我紅腫的舌頭就慘了。但這些都沒關係,因為每當茶水燙傷我的舌頭時,爸爸的愛也同時烙進我體內。可是這次爸爸沒有說,「來嘗這愛的一小口吧」。我看著他把杯子舉到唇邊時。他什麼都沒說。
賈賈跪在媽媽身旁,他把教會公報折成扁扁的畚箕形狀,把一塊邊緣凹凸不平的陶瓷碎片放上去。「小心,媽媽,不然那些碎片會割到妳手指,」他說。
我扯了一下垂在黑色教會頭巾底下的一根玉米壟髮辮,確定自己不是在作夢。為什麼他們表現得像沒事一樣?我指的是賈賈和媽媽,他們怎麼一副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的模樣?為什麼爸爸沉默地在喝茶?就好像賈賈剛剛沒對他頂嘴一樣?我緩緩轉身上樓換掉我週日穿的紅色連身裙。
《半輪黃日》
第一部 六○年代初期
一
主人的腦子有點不正常。他有太多年的時間在海外讀書、常在辦公室裡喃喃自語、不見得每次都回應別人的招呼,毛髮也太過旺盛。厄格烏的姑姑在他們一起走上小徑時低聲這麼說。「但他是個好人,」她補充。「只要好好工作,你就能吃得很好,甚至能每天吃肉。」她停下腳步吐口水,那抹唾液伴隨著一陣咂嘴聲飛離她口中,落到草地上。
厄格烏不相信有誰可以每天吃肉,就連他即將一起住的這位主人也不可能,不過他沒反駁姑姑的說法,因為他已滿懷期待地說不出話,腦中也忙著想像自己離開那座村莊後的全新人生。此刻的他們自從在轉運站步下卡車後已經走了一陣子路,午後陽光灼熱地燒著他的後頸。可是他不在意。他甚至已經準備好要在更炎熱的陽光中走上好幾小時。自從他們經過大學大門後,他看到以前從未見過的街道出現在眼前,這些街道如此光滑,還鋪著瀝青,他真的好想把臉頰貼上去。他永遠無法向他的妹妹雅努利卡描述這裡的獨棟平房是如何漆上了天空的顏色,而且還像衣著體面的禮貌男人站成一排,也無法描述分隔這些房子的樹籬頂端修剪得多平整,看起來就像包上葉片的桌面。
姑姑走得更快了,她的涼拖鞋在安靜街道上發出啪、啪的聲響。厄格烏心想,不知道她是不是也能透過薄薄的鞋底感覺到地面的煤焦油越來越熱。他們經過一個路標,路標上寫著歐丁街,厄格烏用嘴型安靜讀出街名,他每次只要看到不會太長的英文字都會這麼做。他們走進一座住宅區,他聞到某種香甜、猛烈的氣味,確定是入口處一叢白花散發出來的。這些花叢的形狀就像一座座細瘦的山丘、草坪閃閃發亮,許多蝴蝶正在上方盤旋。
「我告訴主人,你什麼事都學得很快,osiso-osiso,」他的姑姑說。這件事姑姑已經跟他說過好幾次,但厄格烏聽了還是專注地點點頭,她也常說他能獲得這份工作有多幸運:她一週前在掃數學系走廊的地板時,聽見主人說需要一名家務男僕來幫忙處理清潔工作,於是立刻趕在他的打字員及辦公室收發員還來不及開口表示可以介紹人之前,就先說她可以幫忙。
「我會學得很快,姑姑,」厄格烏說。他盯著車庫裡的車子看,有條金屬鍊子如同項鍊一樣環繞著藍色車體。
「記得,只要他叫你,你就要說是的,先生啊!」
「是的,先生啊!」厄格烏重複了一次。
他們站在玻璃門前。厄格烏努力克制自己不去伸手去摸水泥牆,但他好想知道摸起來跟母親小屋因為鋪泥時留下隱約手印的泥牆有什麼不同。有那麼一個短短的片刻,他希望自己回到那裡,就在他母親的小屋裡,頭頂上是光線微弱但陰涼的茅草屋頂;又或是身處在他姑姑的小屋裡,那是村裡唯一有波浪鐵皮屋頂的小屋。
他的姑姑輕敲玻璃。厄格烏可以看見門後的白布簾。有人說話,用的是英文,「嗯?進來吧。」
他們脫下拖鞋後走進去。厄格烏從沒見過如此寬敞的室內空間。儘管屋內有看起來幾乎圍成一整圈的棕色沙發、沙發間的幾張邊桌、塞滿書的書櫃,以及放著插有紅白塑膠花花瓶的中央桌子,這個空間也不顯得擁擠。主人坐在一張扶手椅上,身上穿著一件無袖汗衫和短褲。他沒有坐直的身體斜靠著,整張臉埋在書裡,就彷彿完全沒意識到自己剛剛有叫人進來。
「午安,先生啊!這就是那個孩子,」厄格烏的姑姑說。
主人抬眼望向他們。他的膚色很深,像老舊的樹皮,覆蓋在他胸口和腿上的毛髮是一種更為深邃且豐美的黑色。他拿下眼鏡。「那個孩子?」
「那個男僕,先生啊。」
「喔,對,你已經把男僕帶來了。I kpotago ya。」主人的伊博語在厄格烏聽來就像羽毛般輕盈。那是沾染上英文滑溜發音色彩的伊博語,也是常說英文的人說的伊博語。
「他會努力工作,」他的姑姑說。「他是個非常好的孩子。告訴他該做什麼就行。謝謝你,先生啊!」
主人咕噥著回應了,他望著厄格烏及他姑姑的表情有點分心,就彷彿他們的出現讓他想不起某件要緊事。厄格烏的姑姑拍拍他的肩膀,低聲表示他要把工作做好,然後轉向門口。在她離開後,主人重新戴上眼鏡,望向那本書,他放鬆的身體變得更斜了,雙腿也往前伸長,就連在翻頁時,緊盯書本的他也維持著同樣姿勢。
厄格烏站在門邊,他等著。陽光從窗戶流瀉進來,時不時會有輕柔的微風掀起門簾或窗簾。室內除了主人翻頁的紙張摩擦聲外一片安靜。厄格烏就這樣站了一陣子,然後開始慢慢朝書架靠近,就彷彿想要躲進去,接著,又過了一陣子後,他已經坐到地板上,把他那只用酒椰葉纖維做的袋子抱在膝頭之間。他抬頭望向天花板,多刺眼的白啊。他閉上雙眼,試圖用完全不同的家具重新想像這個寬敞的空間,但沒辦法。他打開雙眼,再次遭到全新的讚嘆情緒淹沒,然後為了確保這一切都是真的,他四下張望,同時想著自己之後有機會坐在這些沙發上、需要擦亮這些滑溜的地板,還要清洗那些薄紗似的簾子。
「Kedu afa gi?你叫什麼名字?」主人開口問,他嚇了一跳。
厄格烏站起身。
「你叫什麼名字?」主人坐直身體又問了一次。他的身體充滿那張扶手椅,濃密的頭髮聳立在頭頂,他的手臂滿是肌肉,肩膀寬闊;厄格烏本來想像他是個更老的男人,是個病弱的男人,而現在他突然害怕自己或許無法取悅這個看起來很有能耐的年輕男子,他看起來什麼都不需要。
「厄格烏,先生啊。」
「厄格烏。你是從奧布帕來的?」
「從奧皮來的,先生啊。」
「你的年紀有可能是十二歲到三十歲之間。」主人瞇起眼。「大概十三?」他用英文說「十三」。
「是的,先生啊。」
主人繼續回頭讀書。厄格烏就站在那裡。主人翻了幾頁後又抬頭看他。「Ngwa,去廚房,那邊的冰箱裡應該有你能吃的東西。」
「是的,先生啊。」
厄格烏小心翼翼走進廚房,每一步都踏得很慢。他一看到那個幾乎跟他一樣高的白色東西就知道是冰箱。他的姑姑跟他說過。根據她的描述,冰箱就是個冰冰的穀倉,作用是不讓食物腐壞。他打開冰箱,因為撲面而來的冰涼空氣倒抽了一口氣。橘子、麵包、啤酒、非酒精飲料,許多袋裝和罐裝的食品排列在不同層架上,最高那層上還有一隻閃閃發亮的烤雞,那是只缺了一條腿的完整烤雞。厄格烏伸出手碰了碰那隻雞。冰箱對他的耳朵吐出沉重氣息。他再次碰了那隻雞,舔了一下手指,然後把另一隻雞腿扯下來,一直吃到手上只剩被他吸乾淨的一片片碎骨。接著他撕下一塊麵包,如果有親戚來家裡拜訪並帶這樣一塊麵包當禮物,他一定會非常興奮地跟其他手足分享。他吃得很快,就怕主人進來看見後會改變心意不讓他吃。而當主人進來時,他已經吃完那些食物,站在水槽旁,嘗試回想姑姑曾跟他說過要如何打開這東西,才能讓水像泉水一樣噴出來。主人已經穿上印花襯衣和長褲。他那些從皮拖鞋冒出的腳趾看起來很女性化,說不定是因為實在太乾淨了,而這種腳趾應該屬於一雙總是穿著包鞋的腳。
「怎麼了?」主人問。
「先生啊?」厄格烏用手指向水槽。
主人走過來轉開金屬水龍頭。「你該在屋內到處走走,然後把袋子放進走廊旁的第一個房間。我要去散步,讓腦子清醒一下,i nugo?」
「是的,先生啊。」厄格烏看著他從後門離開。他不高,走路的姿態俐落、活力充沛,模樣看起來就像埃斯古。埃斯古是在厄格烏村子裡蟬聯摔角第一名紀錄的男人。
厄格烏關上水龍頭,然後打開,又關上。他就這樣開了又關、開了又關,最後終於因為神奇的流動水及躺在肚子裡的芳香雞肉及麵包笑了出來。他走過客廳進入走廊。那裡有許多書堆放在三間臥房的書架上及桌上,廁所裡的洗手台和櫥櫃上也有,書房內的書更是從地板堆到天花板,至於儲藏室內,在一個個板條箱裝的可樂和紙箱裝的「首相牌」啤酒旁也堆著許多舊期刊。有些書被打開後內頁朝下放著,就彷彿主人還沒讀完卻又匆忙決定改讀別本書。厄格烏嘗試唸出書的標題,可是大部分都太長、太難了。《非參數化方法》、《一份非洲調查》、《存在鎖鏈》,還有《諾曼第人對英格蘭的衝擊》。他走過每一個房間時都踮著腳,因為覺得自己的腳很髒,而在他這麼做的同時,他逐漸下定決心要取悅主人,為的是能待在這個有肉以及涼爽地板的屋子內。他仔細看過廁所,用手撫摸過黑色的塑膠坐墊,然後聽見主人說話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