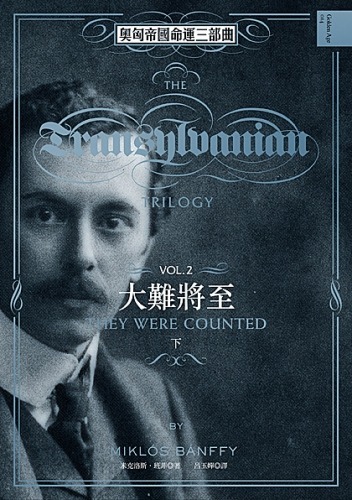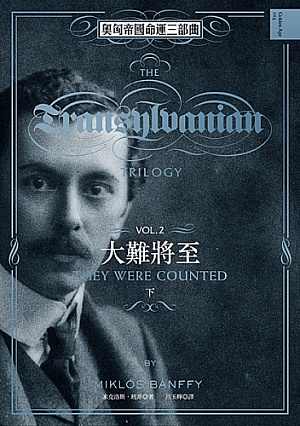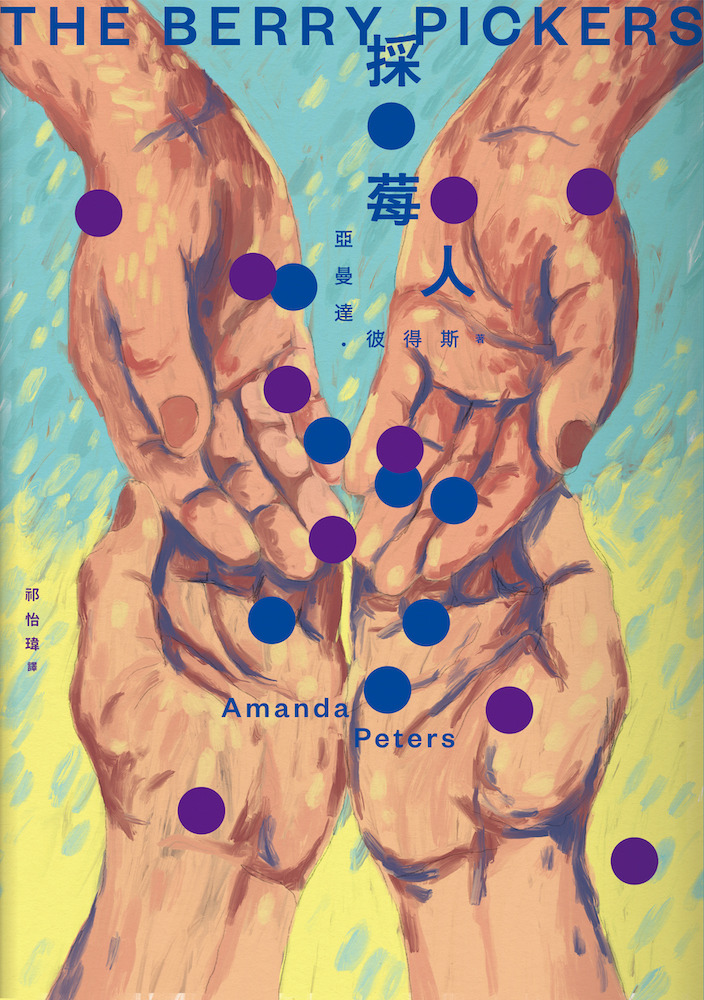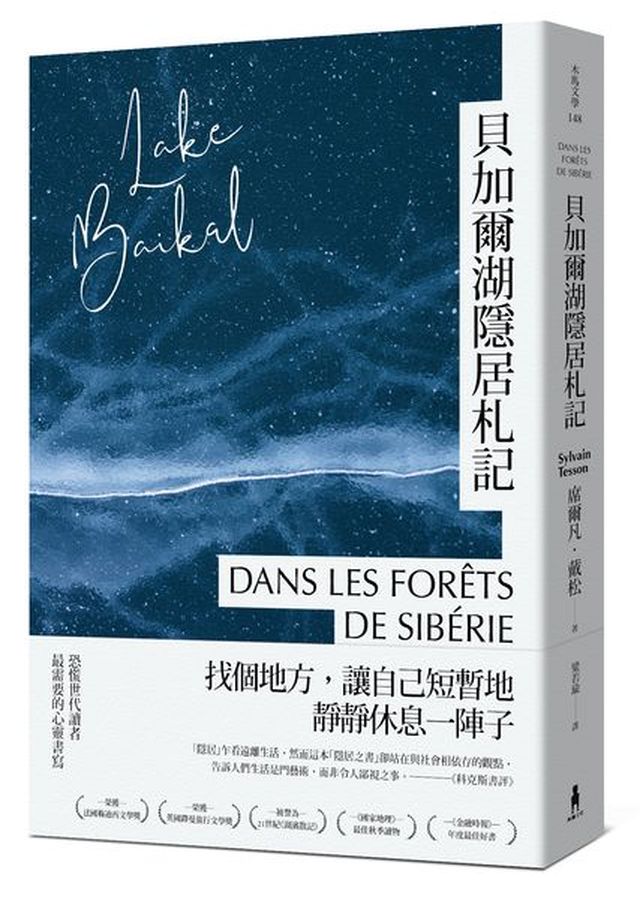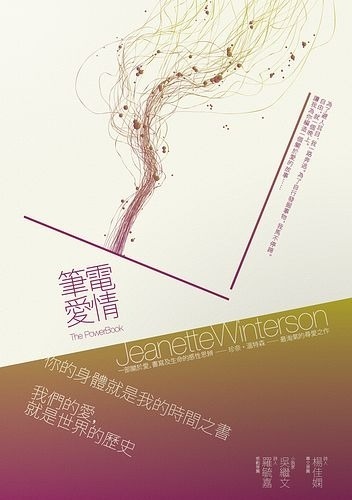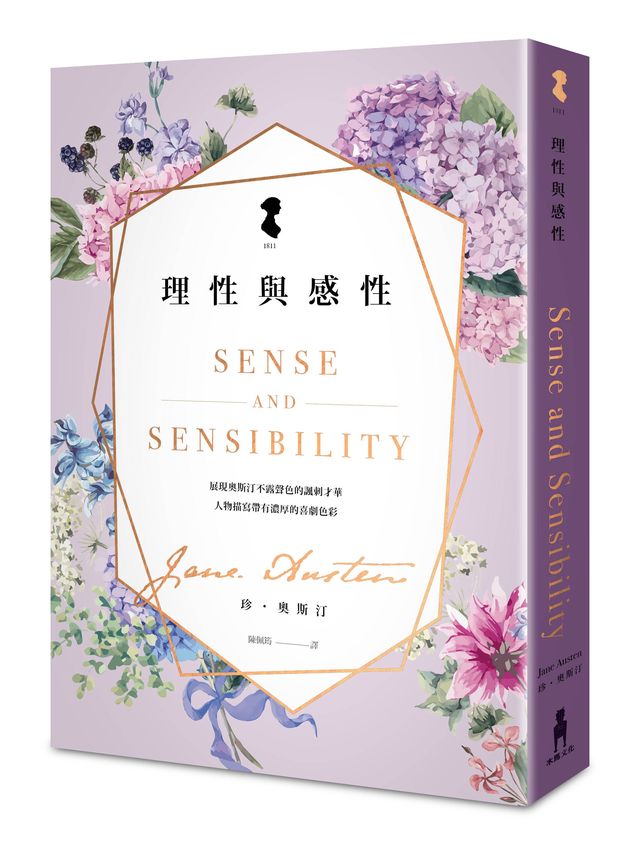失傳近半世紀的匈牙利史詩巨著,
重新出版一舉奪下各大媒體年度最佳小說獎!
被譽為《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妮娜》的綜合體
媲美《齊瓦哥醫生》的蒼茫與壯闊
◆《衛報》1000本必讀小說
◆《觀察家報》年度好書
◆ 牛津威登菲爾德最佳翻譯小說獎
◆《華盛頓郵報》年度最佳小說
出身匈牙利貴族、見證書中歷史場景的班菲,一生享盡榮華、嘗遍冷暖,看盡人世間的愚昧、醜陋和滄桑,終至眼見國亡家滅,無以回天,遂將他對數百年世胄歷史的喟嘆,淬煉為這半自傳的三部曲巨著,作為對國族和一己生平的紀念。
從顯貴夜夜笙歌、朱門酒肉臭寫到繁華落盡、末世滄涼,大時代下的政治角力、階級鬥爭、人性黝暗與淒美愛情,躍然紙上。班菲將當時世界政治局勢的詭變、對奧匈帝國的企盼、貴族的墮落與平民百姓的困苦,全都投射在小說中兩位命運迥異的主人翁身上。
作者行文自然流露貴族的逸趣,節奏悠閒,筆觸細膩,但因思緒縝密敏銳,而致文氣始終飽滿,筆端犀利、明確,字裡行間張力十足,感情豐沛,十分扣人心弦。除了故事的曲折,足堪讀者細細品味其文字世界的豐美。
首部曲《大難將至》
故事從一九○四年開始寫起。首先是一對性格南轅北轍的匈牙利貴族表兄弟登場,揭開存在於貴族間全然不同的兩種生活,在一場場奢華的舞會、賽馬場、狩獵大會、豪賭、愛情、私通中,看到政客故步自封,只顧著與哈布斯堡的奧皇對抗,完全無視歐洲上空籠罩的風暴……
【編輯推薦】
這部匈牙利史詩三部曲出版於1934至1940年間,正值奧匈帝國崩解後,納粹德軍入侵和二次大戰戰火蔓延之際,因此當時只有少數人讀過,然而咸都認為這部作品是20世紀最棒的小說之一。透過口耳相傳,這部失傳近半世紀的文學巨著,終於在九○年代由派屈克.瑟斯費爾德聯同作家親生女兒凱塔琳.班菲–耶倫耗費七、八年的時間,力圖將作家生前欲傳達的匈牙利錯綜複雜的政治局勢和文化,如實展現在讀者面前。英譯版一推出,果然不負眾望,紛紛摘下各大媒體年度最佳小說的殊榮,並獲選牛津威登菲爾德的最佳翻譯小說獎。
米克洛斯.班菲 Miklós Bánffy
生於1873年,卒於1950年,出身外西凡尼亞的匈牙利貴族世家,也是心胸寬大的政治家,身邊除了權傾一時的貴胄,也和藝文界有密切往來,後來甚至無懼社會壓力,娶了演員為妻。他對晚期奧匈帝國的發展影響甚鉅,1916年,他負責策畫哈布斯堡王朝最後一位皇帝的加冕典禮;1920年驅逐匈牙利共產主義領導者貝拉(Kun Bela)後,接任匈牙利的外交部長,期間與美國簽署和平條約,爭取讓匈牙利加入國際聯盟,甚至在二○與三○年代援助羅馬尼亞治下所有外西凡尼亞的匈牙利人。同時間,他也主持布達佩斯國家劇院,以實際行動支持作家與藝術家。1926年他結束公職生涯,返回故鄉,隱居在祖傳的城堡裡,從此全心投入文學與藝術的創作,直到去世。著作頗豐,而其中最為人稱道的成就,正是這部雋永有味的經典三部曲。
英譯者簡介
派屈克.瑟斯費爾德 Patrick Thursfield
生於1923年,曾就讀查特豪斯公學與牛津大學基督教會學院,1942至1946年在英國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服役(聯合作戰任務)。1949年進入《泰晤士報》報社,之後專注於電視劇本的創作,並持續發表藝文及其他相關主題的文章。1971年定居摩洛哥坦吉爾,直到2003年逝世。
凱塔琳.班菲–耶倫 Katalin Bánffy-Jelen
作者米克洛斯.班菲的女兒,定居倫敦。
中譯者簡介
呂玉嬋
以筆譯餬口養心數年,歡迎來信指教:yctranslator@gmail.com。
【摘文1】
拉茲洛不發一語坐在這裡,就跟和私人包廂內狂歡的年輕人在一起時一樣,他仍然覺得自己是外人。他對賭沒興趣,不過身邊有人,又能不受打擾旁觀,依然是愉快的,在賭牌室甚至比在樓下還要自在。在樓下他不由得覺得人家在容忍他,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裡,甚至連客人也不是,而只是與樂隊領班或鼓手一樣等級的人;他們之所以容忍這些人,因為這些討人厭的人不能不存在。他自幼喪父無母,無家可歸,所以有心理準備,認命地接受了這樣的對待,視為天生的命運。不過,自從在席蒙瓦賽宮克拉拉的小房間一隅擁她入懷之後,他的感覺完全變了。現在有哪個名門少爺懷著自私的善意,自以為高人一等對拉茲洛說話,他內心就會立刻湧起恨意與不服。比方說,當晚早些時候,有個人輕浮地說:「哦,好哇,想來就一塊來啊!」接著請他拉小提琴,或讓歌舞劇場來的女孩跳舞,簡直當他是管家,或者花錢請來替他們策畫狂歡活動的人。他覺得忍無可忍,再也不要忍下去。他不值如此,克拉拉捨棄他人,為自己選的、獻上紅脣的男人,絕對不值如此!噢,那一吻的記憶!她的脣溫暖溫厚,令人想起沐浴在陽光中的果子。不過是這麼一個念頭,他便覺得飄飄然。那段記憶幽禁在他心中,他彷彿隨身偷偷攜帶世上最大的鑽石,這極其罕見珍寶夾帶著的超卓魔力,無論是誰戴在胸口,走到哪裡都該第一個通行。拉茲洛靜靜坐在鐵道牌牌桌邊,當晚稍早被迫灌下的過量白蘭地與香檳令他興奮,他覺得血液在體內激烈奔騰,嚷著要求大家遵守這個皇家命令。他面無表情坐在容易激動的登希身旁,表面上謹慎沉默,但內心的憤恨與驕傲的決心正騷動、沸騰。閃閃發亮的桃花心木「鞋」(指發牌盒)現在傳到亞仁諾維克斯手中。發牌前,他把面前整堆籌碼全數推出去,籌碼有的是五百克朗,有的是一千克朗。他說:「Faites vos jeux !(法語:下注吧!)」接著期盼地看看四周,頭轉向每一個方向,尖喙般的鼻子似乎支配著牌桌。從側面看去,他的鼻子弧線極其尖銳,所以大家喊他「黑鳳頭鸚鵡」;又因為他抹了厚厚的髮油,頭髮自額頭高聳,很像黑毛羽冠,讓這個別名更加貼切。暫時無人開口。亞仁諾維克斯又看了看,冷冷的棗黑色眼睛倨傲地尋找願意接受他挑戰的人。他這是故意裝腔作勢,他對自己名賭徒的美名很有把握,希望嚇嚇那群老站在玩家椅子後方暗處的無名旁觀者。即使時候已經很晚了,旁觀人潮依舊不減,亞仁諾維克斯必須無愧自己的名聲,正因為如此,他下的注永遠最高,且從不與人合股,也從不退出牌局。就算他希望換個作風賭牌,現在也沒辦法了,他的原則已經廣為人知,因為他經常向又敬又畏的觀眾解釋他手法裡的智慧。
幾個玩家慢慢把一小堆籌碼往前推,檯面最後約有一萬二千克朗。莊家拿到九點(九點最贏)。
「莊家,二萬四!」亞仁諾維克斯說。他把第一堆籌碼收回來,在面前整整齊齊堆成了兩疊,身子往前傾,把雪茄咬到嘴角,說:「二萬四,誰跟?」
登希面前只剩一個孤零零的五百克朗籌碼,那是輸了一整晚的殘餘賭金。登希暗想,如果現在贏了,那就沒賺也沒賠,要是沒贏的話嘛,咳,總是可以再跟哥哥討些錢,他已經借了好幾次。他敲敲桌面,表示他押同樣的賭注。
亞仁諾維克斯拿到九點,又贏了。登希打了個手勢,要總管拿張借條給他簽。
從這時開始,Ponte(押莊家輸的人)下的注愈來愈小:八千、五千、三千,最後只剩一兩千,而且注下得很勉強。不過他們必須繼續玩下去,若因為有位厲害的賭徒手氣正旺就收手不賭,被認為是可恥的。後來,他們又開始提高賭注,因為大家覺得莊家連贏的局面馬上就要結束了。結果不然。亞仁諾維克斯連贏了十八把。現在下注速度慢了下來,每個人都輸得精光。
「Pour faire marcher le jeu(法語:為了讓牌局繼續)!」奈茲第一面說,一面用精心修剪的長手指推出二千克朗的籌碼。只有他下注,亞仁諾維克斯又贏了。
「十九把……我數了!」裴瑞不安地說,「這傢伙要痛宰我們!」只有他抱怨,雖然一整晚他只是偶爾賭個一百克朗的籌碼,且即使賭注這麼少,他還經常在開賭前收手。不過,他之所以說這句話,是要讓人覺得他和其他人一樣豪賭,他也輸得很慘。
此時,原本在樓下房間的福瑞迪.伍芬史坦加入了這群人。雖然樓梯鋪了厚毯,伍芬史坦沉重的步伐在賭牌室就能聽到,他喜歡這樣走路,因為相信英國上流人士是這樣走的。他已經醉了,敞開手肘,走到拉茲洛的椅子後方停下。
亞仁諾維克斯把籌碼攏一攏,再次往外推出一堆,身子往前傾,一張紅統統的俊臉完全映現在燈下。他說:「四千,誰跟?」
就在這個時候,伍芬史坦粗魯地推了拉茲洛的肩頭一把,說:「起來!我要坐這裡。」這是一句脫口而出的命令,語氣傲慢,沒有「請」或「勞駕」,像沒有教養的主人對貼身男僕說的話。
拉茲洛動怒了。他心想,這人膽子好大,竟敢這樣對我說話!他究竟以為他老幾?沒有什麼能叫拉茲洛站起來,那種話絕對不能!不過,一個念頭閃過,只有加入牌局,他才有權留在原本的位置,否則照規矩必須讓出座位。他把椅子往前一拉,敲敲牌桌說:「Banco(莊家)!」
眾人愕然抬起頭,怎麼也沒料到拉茲洛會加入牌局……而且跟了這麼高額的賭注。不過,Banco這簡單的一個字讓人對他肅然起敬,連伍芬史坦也定住了。
亞仁諾維克斯發牌,拉茲洛熟練地把兩張牌互疊,等莊家說話。莊家說:「Je donne(補牌)!」拉茲洛迅速亮牌,因為他經常看見奈茲第伯爵這樣做,反而不像猶豫生疏的打牌者那樣慢慢攤開。他拿到了六點,因而冷冷地說:「Non(不)!」亞仁諾維克斯拿到同樣的點數。
某個人說:「En cartes(和)!」說得沒錯,但是沒有說的必要。拉茲洛模仿他看過的動作,若無其事地將紙牌精準扔到牌桌中心的皮革容器,那個盤碟有個奇怪的名字,叫作panier,因為玩任何形式的百家樂只能說法語。牌又發下來,莊家再次贏了。
「簽帳,麻煩!」拉茲洛對總管大聲說,總管立刻送上一盤籌碼,以及一張要拉茲洛簽名的紙。他簽好名,把四千法郎的籌碼放在桌上,往亞仁諾維克斯推去。
「想報仇啊?你有這個權力。」亞仁諾維克斯說。
「好啦好啦,起來!」伍芬史坦在他身後說,「我已經跟你說我想坐在這裡!」
拉茲洛轉頭看了一眼,冷靜但咬著牙說:「我要繼續坐在這裡!」
「但我剛才就說了!你那時根本還沒開始玩!這位置是我的!」
「除非說Passe la main(換手),否則沒有人有權坐下,這是規定,你沒說,拉茲洛也沒說,但是他比你早加入賭局。」
伍芬史坦沒答腔,因為奈茲第說話時,讓他的單邊眼鏡片掉了下來,沒有人不曉得,這個動作代表了不可質疑的最終裁定。伍芬史坦走到房間另一頭,一臉不悅地坐下,拉茲洛則欣喜獲得一名高貴人士的意外支持,決定不管之前退出賭局的決定,要繼續玩下去。他簽名借了五千克朗,現在還剩下兩枚五百克朗的籌碼,靠著這些籌碼,他可以偶爾押注,只要贏了一次,就可以立刻把錢還給總管,不會有更壞的情況發生;要是輸了,他總能把欠的五千克朗還掉──先前到達法定年齡後,他已經把舊債還清了,還留下七千克朗備用。這是一記打擊,但他能夠承受,不用負荷過多的壓力。
亞仁諾維克斯在下一局輸了。如果拉茲洛就此收手,他就贏回了先前所輸的每一毛錢,這個想法在他心中一閃而過,但從他的表情看不出任何跡象。他繼續賭下去,面無表情,好像這輩子每一個晚上都在賭牌。他忍受苦楚所培養出的堅忍克己精神此時派上了用場,他的眼皮不會抽動表示贏錢的喜悅,也不會透露輸了還不起的痛苦。他的語氣冷靜、隨意又從容,神色老練。
過了一會兒,他當莊家,不過就在此刻好運似乎轉到閒家的手中。
「有人轉運了哦!」剛才多嘴的人又多嘴,有眼睛的誰沒看到。
拉茲洛做莊連贏了三次,如果他就此打住,他總共只輸大約五百克朗。此刻,他要起身很容易,因為僕人正通知門口有馬車了,這種時候哪個玩家不玩了,即使他賭運亨通,也沒有人會瞧不起他。不過這種事拉茲洛是不會做的。他把兩片一千克朗的籌碼往牌桌中間一推,立刻輸掉了,於是手上剩下二千五百克朗。他繼續賭,下注,贏錢,輸錢,又贏錢,突然手氣旺了起來,贏了二萬五千克朗;一轉眼,又全輸光了。儘管如此,他還是不罷手,繼續坐在那裡賭,時而狂賭,時而小賭。雖然不是特別刺激,但是輕鬆有趣,教人覺得愉快。籌碼似乎只代表數字,不代表價值,不過是一場遊戲罷了。把若干鮮豔的籌碼往前推,有時籌碼留在那裡,有時一大堆被推回面前。有人發牌,有人輸,有人贏,籌碼被移到各自所屬的位置,如此而已。又一次發牌,又一次贏,又一次輸。何必停止呢?如果手氣正順,籌碼在面前累積;如果手氣差了,再簽一張字據。人人平等,只有手氣決定這場遊戲。階級是虛無的,財富是無謂的。你會贏錢,也會輸錢,只有賭品是重要的,就像戲院裡的一齣戲,每個人的角色都已經寫好了,只要照著劇作家的決定去做,多麼愉快的一件事啊!這幾乎是拉茲洛這輩子頭一次覺得其他人歡迎他與他們平起平坐,毫無保留……
拉茲洛終於起身離開牌桌時(他會離開,只是因為已清晨五點,人人都想回家了),他輸了一千五百克朗。他輸光所有贏來的錢,就跟贏到那些錢時一樣滿不在乎。他又滿足又舒坦,甚至能夠在那裡一直坐下去,把籌碼推出去,又撈回來,即使那些彩色小圓片所代表的價值超出他可以負擔得起的金額──這個想法似乎太過虛幻,他根本沒有想到。他把借條從五千克朗更正為一千五百克朗,然後離開賭牌室,慢慢走下樓。
賭場外,雨已停了,人行道結了一層薄霜,水晶似的細針狀晶體在腳底發出微弱的柔光。拉茲洛踏著輕快步伐走上回家的路。
他的心中洋溢著一種異樣的清新感覺,空氣冷冽,但是他脫了帽子,就這樣走回家。在宵夜廳,酒精讓他整個人昏沉麻木,此時刺激的酒氣早已經揮發,他帶著一顆清醒的腦袋,懷著新生的自由感受信步走著。沿路街道昏暗,偶爾的燈火與破曉的微曦勉強勾勒出四周建築的輪廓。
【摘文2】
五月來臨,布達佩斯的社交生活再次活躍起來,不只因為私人或公開的賽馬和舞會,也因為又到了國會會期。政界現在所有興趣都集中在奏章的本質上,從前的反對黨,如今集結起來在國會成了多數黨,將用奏章攻擊譴責提索伯爵強勢統治時期的政策。
公眾強力支持反對黨,老百姓喧喧嚷嚷,對非難維也納的理由很有信心,得意洋洋喊著愛國口號,然而反對黨的領袖卻愈來愈沮喪驚慌,因為解決政府危機一事完全沒有進展。
這就是巴林特抵達首都時的局勢。巴林特每天進國會。在他出席的第一場會議,他們為了奏章起爭執,這一吵,整整吵了兩天。由於史拉瓦塔向他透露了維也納美景宮裡擬定的祕密計畫,巴林特很想支持反對黨的論點,但是奏章與支持奏章的言論所揭示的荒謬、空話及裝腔作勢的盲目愛國姿態,迫使他立刻回頭相信提索,效忠老君主。
在議事廳,不同黨派依然坐在跟冬天選舉後一樣的位置,但是氣氛截然不同了。勝選的反對黨所占據的席位上,原本整合反對黨各個派系的同志情誼與友好關係已煙消雲散,再沒有人相互道賀與親切握手。議員現在面露不滿和不悅,每一個小團體之間的利益衝突讓所有人像勝選前那樣相互提防,分歧隔閡眾目共睹,因為每個團體之間都保持著距離。巴林特厭惡這一切的偽善與齷齪。
頭兩天在窮極無聊中過去了,陳腔濫調後,還是陳腔濫調,每一句愚笨的愛國口號果然不是獲得歡呼,就是遭受揶揄,依哪一方正在國會發言而定。不過,到了第三天,輪到少數民族代表發表見解,這是他們有史以來頭一次的發言機會。提瓦達.米哈伊從他們那一小群人中間站起來,以熟練流暢的匈牙利語反對奏章。他語氣慎重,以穩健而圓融的用詞,說明他所代表的少數民族無法同意,因為就他們的觀點而言,奏章並沒有提及阻擾匈牙利進步繁榮的真正弊害。他提議上呈一份迥然不同的奏章,集中心力在內政問題上,而非與奧皇之間的政體關係所激發的問題。在米哈伊的奏章中,重點會是選舉改革,改革將確保匈牙利政府確實代表所有匈牙利人民,無論種族血緣,這自然必須包括重畫選區,修訂他所代表的少數民族從來就不同意的民族法。米哈伊態度從容,語調冷靜,措辭簡單而直接,他的每一項提議都溫和合理。他特別反複重申少數民族是匈牙利及匈牙利政治制度重要的一部分,他們只要求應該獲得承認上述的地位。米哈伊坐下後,巴林特注意到一件事,讓他覺得很驚訝:這是少數民族領袖的首度發言,在國會居然沒有引發什麼熱烈反應,掌聲稀稀落落。他想了一想,這是自然的,這裡的每個人只有興趣跟提索繼續作戰,其他議題再重要,他們也只有在前首相起身發言時會集中注意力。他還注意到好些議員在米哈伊站起來時離開,直到他坐下才回來。對所有列席者而言只有一件事重要,那就是提索一敗塗地,無論這場戰鬥要付出多少代價,要潑灑多少鮮血,無論整個匈牙利是否因而毀滅!沒有人停下來想一想,提索已經在選舉中受到挫敗,早在一月就去職了,那已經是幾個月前的事。
提索一起身發言,場面立刻騷亂起來。費倫茨.高舒特竭盡所能想讓同黨議員平靜下來,希望他們至少舉止莊重,這是自稱能勝任治理一個現代歐洲國家者的必要條件。喧鬧聲慢慢消失,提索終於能夠發言。
「身為辭去首相一職的人,我已經沒有憲法權利引導議會議事程序……」他開始說。
「一點也沒錯!坐下!滾出去,你這個老傻瓜!」叫囂從四面八方響起,但是提索依然昂首挺立,黑衣身影背對內閣席的紅絲絨,挺著胸膛傲然不屈。提索左手放在臀後,彷彿採取正要決鬥的預備姿勢。他開口說話,右手食指在空中指指戳戳,強調他正在說的話。雖然有同黨議員的支持,他還是給人一種孤單的印象──孑然無依。
他不理會「他煽動農民反對我們」的呼喊,無動於衷繼續說下去,引述數字和數據支持他的論點,發言超過一個小時,彷彿正在與一群通情達理、準備討論國家最佳政策的政治家說話。提索無視紛紛籍籍的干擾,繼續站著,站到他非難的雄渾嗓音結束了他的論點。接著,他坐下。
「厚顏無恥的孬種!替沒人要的人辦事!」一名面色潮紅的「愛國人士」大喊。這句話太過分了,新任首相尤斯特不得不公事公辦申斥那個人,但沒有什麼效用,又有另外三、四個人立刻從「一八四八黨」那幾排跳起來,大叫:「厚顏無恥的孬種!厚顏無恥的孬種!要不要把每個人都罵一罵?」騷動愈來愈厲害,會議只好暫停。
議事廳轉眼人走得一個不剩,議員三五成群聚在長廊,每一群人圍著一名政黨領袖,希望能聽到一兩句話,好在俱樂部酒吧、政黨小聚會與對政治記者說話時,當成自己的意見轉述出去。小議員就是用這種方式達成逢迎大眾的目的。
沒有人好好想想提瓦達.米哈伊的發言,他們認為值得討論的只有提索,他遭受種種叛國指控,從與奧地利人勾結摧毀匈牙利的政治獨立,到和匈牙利亂黨密謀與奧地利決裂。克羅埃西亞人的態度也教其他人失望,議會召開前,人人猜測(報紙也預料)他們會投票贊成奏章,沒人料到他們竟然唱反調。一般的政界人士是如此懵懂天真,他們對發生的事大失所望,便立刻以陰謀受害者自居,眼見之處盡是敵人,不明白國家其實是受到自身利益的支配,掌握利益及發展利益的技巧能力才是一個國家和平繁榮的真正基礎。不信任跟自己意見不合的任何人,這種懷疑心態衍生同黨黨員的分裂,終將導致主導的克羅埃西亞黨瓦解。出席布達佩斯國會這一場災難會議者,沒有一個人預料到,克羅埃西亞黨的變節將替泛塞爾維亞聯合政府開闢道路,而聯合政府最後會順利讓匈牙利喪失德拉瓦河以外的省分。
外西凡尼亞律師西格蒙德.鮑洛斯總結普遍反應,說道:「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崇高愛國的奏章,面對提索、克羅埃西亞人與少數民族一致偏頗的反對,現在完全不可能讓皇帝體恤或平心接受!問題就在這裡,就只有這個問題。是他們壞了整件事,要不是他們,奧皇一定已經讓步了,毫無疑問!奧皇只是太急於擴編軍隊,那是他熱愛的事,就是這群人壞了一切!」
巴林特傷心地聽了一會兒,轉身離去。走遠時,瞥見幾個羅馬尼亞人聚在陰暗角落裡,歐瑞爾.提米森律師也在其中,便走過去打招呼。提米森與在火車上時一樣,和藹可親,看起來心情很好,雖然笑容帶著嘲諷挖苦的味道。他向巴林特介紹其他人,那幾個人態度冷淡多疑,也不說話,巴林特覺得受到監視、懷疑和批評。他提起提索其中一個影響外西凡尼亞的商業論點,以為這可能會成為讓他們結盟的共同利益,他們卻客套回應,顯然不信任他。大約十五分鐘後,鈴聲響起,召喚議員返回議事廳,巴林特沮喪地走開,卻又略微鬆了口氣。
回席位途中,他經過福瑞迪.伍芬史坦的身邊,伍芬史坦向他說:「你怎麼可以和野蠻民族說話?不像話!光是看見他們,我渾身的匈牙利熱血就沸騰了!」
巴林特氣得額頭青筋迸現。「我覺得可以,所以我跟他們說話!有意見嗎?」他對身上一滴匈牙利血液也沒有的伍芬史坦狠狠地說。
「沒有、沒有!怎麼會呢?我只是想……」伍芬史坦迅速弓肩縮背地在他的位置坐下,黑白兩色的套裝與紅色議員席形成強烈對比。
* * *
後來在賭場及其他政治聚會場合,鮑洛斯扼要陳述的觀點再三被人複述,有些小變化,但是主題不變,沒有人談論其他事。在匈牙利以外的大世界,正在發生改變他們所有人生命的事件:俄羅斯暴動、克里特島主權糾紛、德皇威廉二世在不當時機出訪坦吉爾、德國海軍擴編計畫曝光──不過這些事對匈牙利國會議員都不重要,就連離本土不遠的事件,在布達佩斯都未引發關注,例如一位奧地利政治家在薩爾茲堡發表演說,鼓吹匈牙利北部說德語的少數民族叛亂,引發暴民滋事;又或者維也納出現匿名小手冊,顯示與其他歐洲強權相比,奧匈帝國的武力缺乏應變能力。然而,當阿波尼(Albert Apponyi, 1846-1933,匈牙利政治家,自一八八○年代晚期,任聯合反對政黨的領袖)發表演說,支持戴索.班菲(Dezső Bánffy, 1843-1911,作者堂哥,曾任匈牙利首相)的提議,只用匈牙利人處理軍團事宜,以限制由匈牙利人指揮軍隊的要求,想當然耳,每個人傾聽討論,好像這件事攸關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