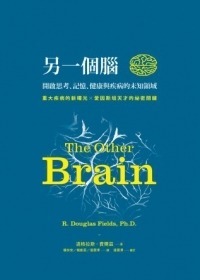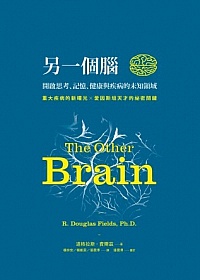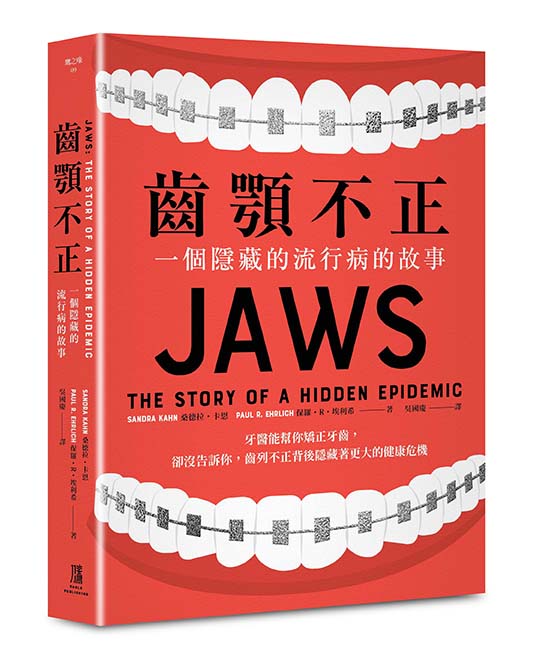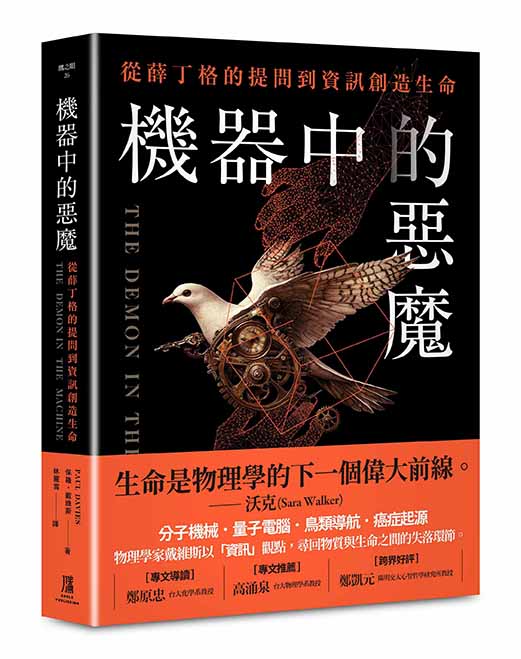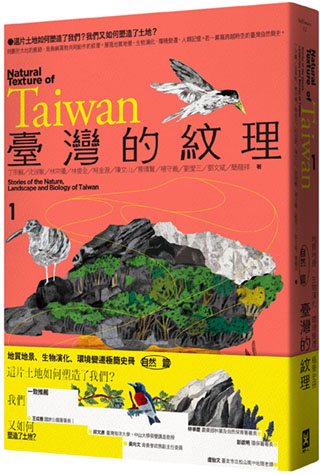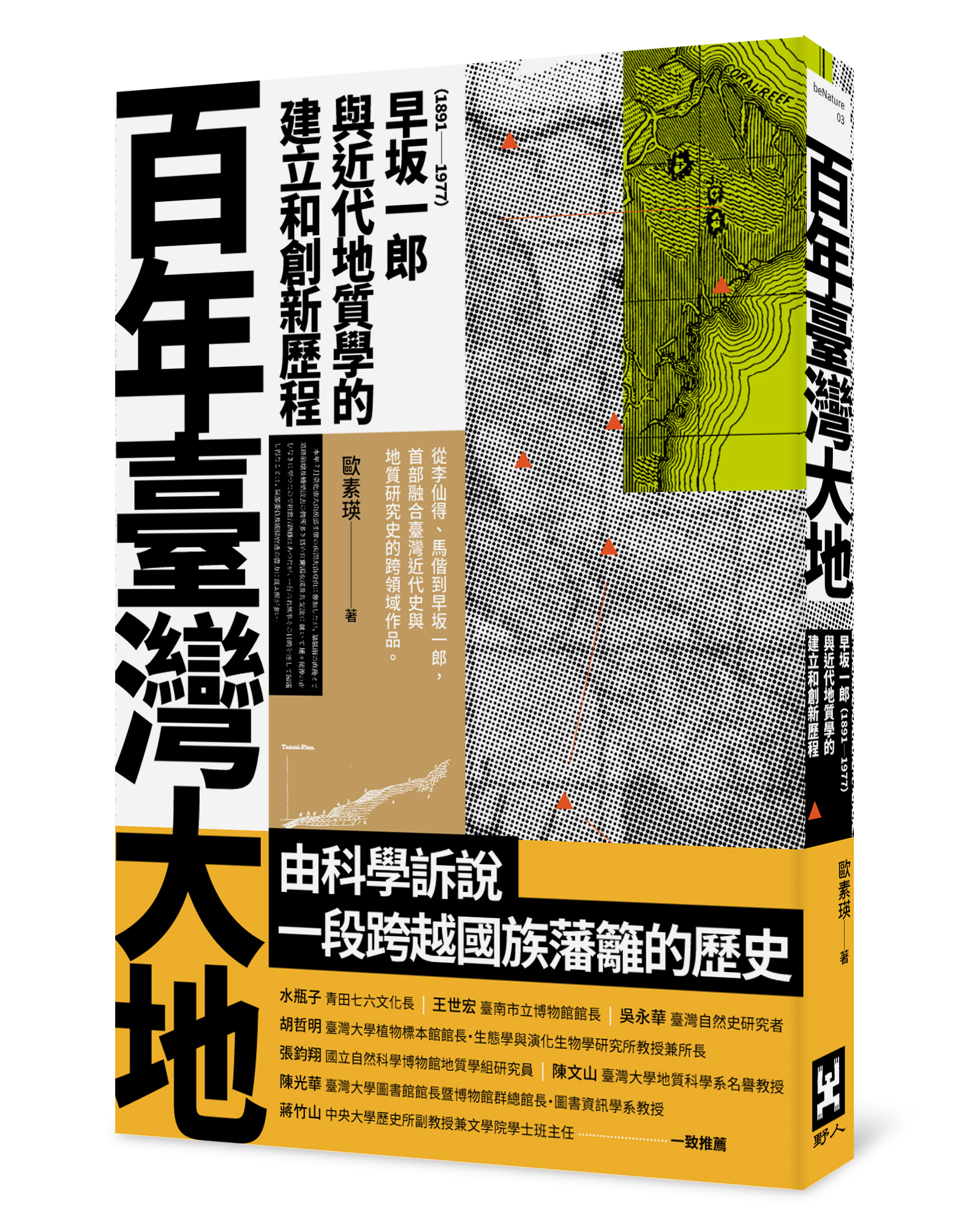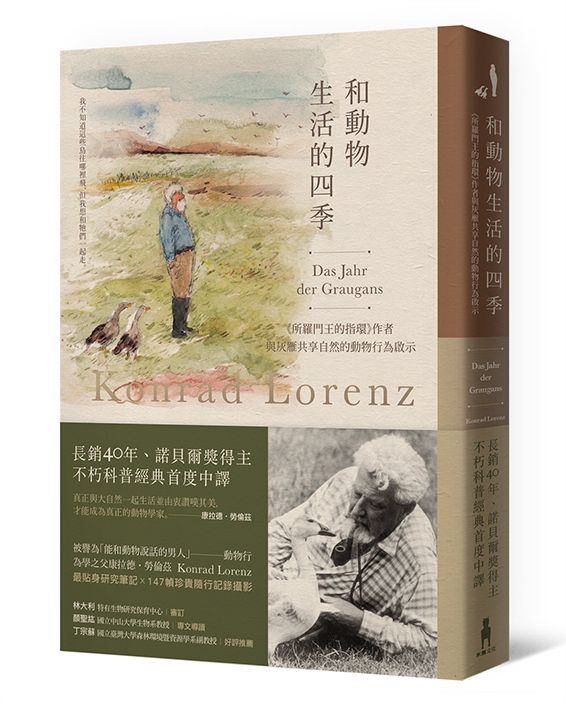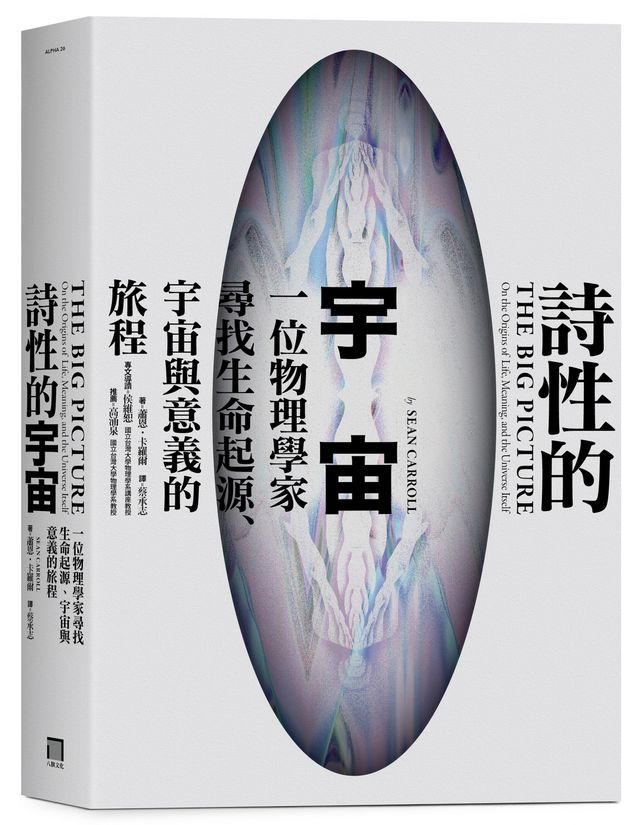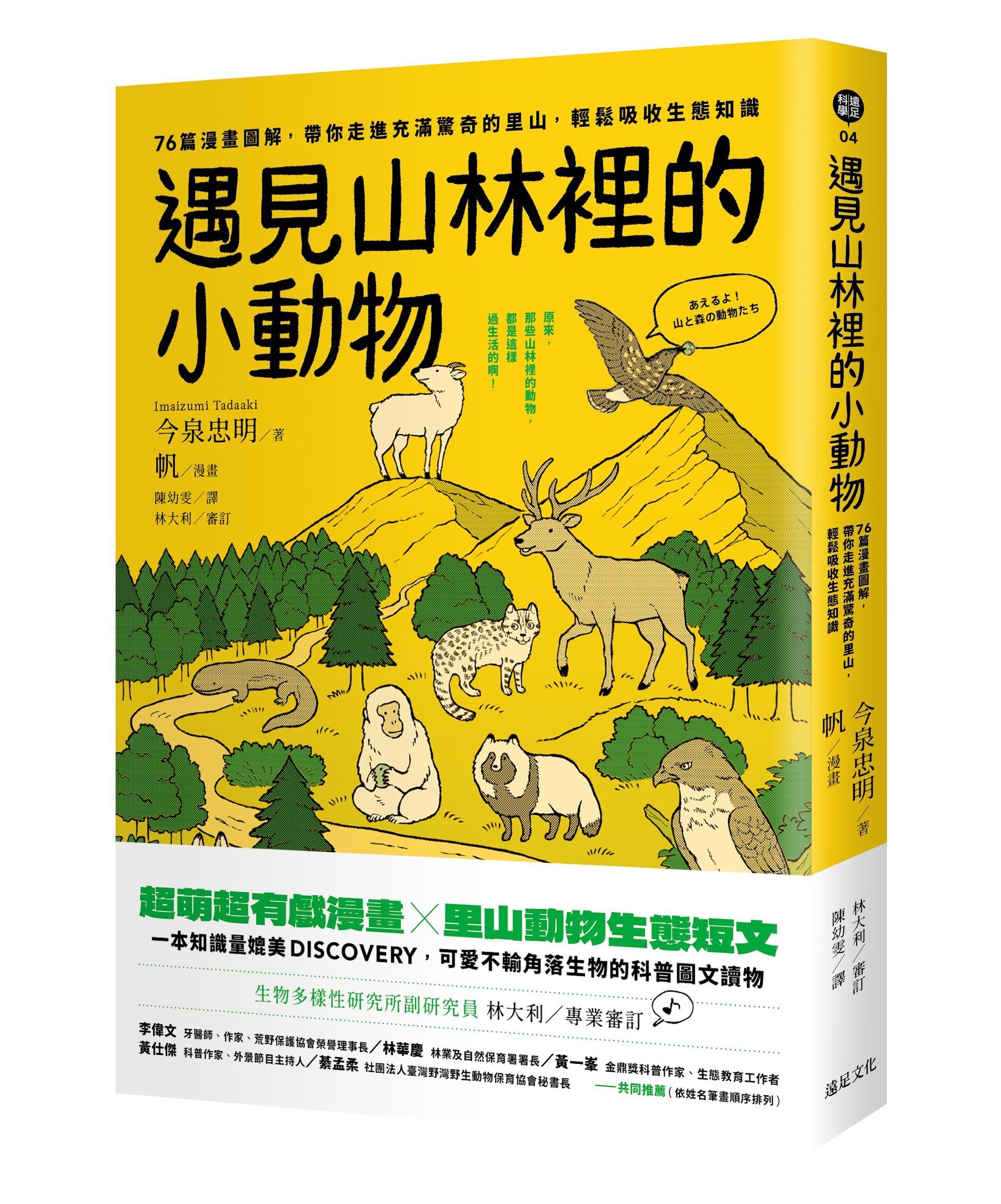前言
人腦中上千億個神經元如何讓我們記得自己是誰?如何讓我們學習、思考,以及作夢?如何讓我們充滿熱情或憤怒?如何讓我們騎腳踏車或瞭解紙上墨跡代表的意義?如何讓我們從一群吵雜的人聲當中馬上就聽出母親的聲音?精神分裂症、抑鬱症,或諸如阿茲海默症、多發性硬化症、慢性疼痛與癱瘓等可怕疾病患者的神經線路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正處於對人腦有全新認識的轉折點;一世紀來的傳統看法,特別是腦中神經元扮演的角色,將因此徹底改觀。一九九○年,科學家擠在暗室的電腦螢幕前看著資訊在奇怪的腦細胞間傳遞;它們不單跳過了神經元,同時還不使用電脈衝的溝通方式。在此發現以前,科學家一直以為腦中訊息只有使用電的方式經由神經元流動。事實上,我們腦中只有百分之十五的細胞屬於神經元;其他稱為膠細胞的腦細胞則一向遭到忽視,被認為只不過是電子神經元之間的填充物質罷了。它們被稱為「管家細胞」,給貶為做家務事的細胞僕人。打從膠細胞被發現以來,它們就遭到忽視,時間超過一世紀之久。
如今,科學家發現這些奇怪的腦細胞也會彼此相互溝通,這點讓他們驚訝不已。這些細胞不但能感知在神經線路中流動的電氣活性,而且還能對其有所控制。這些發現已經顛覆了科學家對於腦部的基本認識。
科學家怎麼可能這麼長時間一直忽視這另一個腦?由於膠細胞不會發出電脈衝,因此神經科學家用來監測神經元的電極探針聽不到膠細胞的傳訊。膠細胞不像神經元那樣以突觸連結成線路;它們不使用推倒骨牌的方式,將訊息一路傳遞下去,而是將訊息以廣播的方式傳遍整個大腦。
這些新發現將如何改變我們對心智的瞭解?當我們探索腦中這塊新領域時,是否能解開精神疾病如何讓人心智失常的奧祕?這項追求是否能找到如何讓腦部從疾病或傷害中復原的解答?
由膠細胞組成的另一個腦的發現就像初升的朝陽,照亮了腦科學當中的每一個層面,同時間影響了所有從事腦部研究的人。這是個仍在進行中的科學故事,其中有意外與轉折、洞悉與困惑、爭議與共識。一路上你會遇到一些真實但有趣的科學家,每個人都不一樣,甚至獨特,但他們都從事著一項最要求合作的人類活動:科學研究。
本書提供的資訊新鮮無比,大都還沒來得及進入教科書。這些資訊將改變你對腦部的認識,並提供重要的知識,幫助你以及你所愛的人維護健康。本書裝滿了神經科學與醫學的最新知識,透過參與其中的一位科學家雙眼,它將帶你身歷其境,親眼見識這一切。
第一章 填充泡泡還是神奇黏膠?
愛因斯坦的腦
劃下最後一刀,他將解剖刀丟入不鏽鋼盤,然後伸出雙手,小心翼翼地從掀開的顱骨內將腦取出。每次手中捧著人腦,總是引發他一連串有關死亡、個性、生物學、靈性,以及個人存在奧祕的澎湃思緒。就在數小時前,造成這位獨特個體的一切特性,都藏在這個重約一點四公斤、表面皺褶扭曲的組織中。雖然這位病理學家已歷經無數次這種感受,然而這回還是不同:眼前不銹鋼檯上躺著的大體,是愛因斯坦;他手中捧著的,正是愛因斯坦的腦。
他在明亮的燈光下詳細檢查這顆腦子。他懷著深沉的好奇注視著它,心想,這個果凍般被本身重量壓得有點塌陷、看來與其他人腦一模一樣的器官,是如何創造出上個世紀裡最出色的心靈呢?突然間,哈維(Thomas Harvey)醫師從這顆腦子看到了他自己的命運與目標所繫。這顆腦注定該是他的。
他小心地以生理食鹽水沖洗腦上的血跡,將其秤重並測量尺寸後,放入剛配好的百分之十濃度福馬林溶液中;他的眼鼻感受到一陣有毒的福馬林蒸氣刺激。在愛因斯坦這位偉人的身軀入土為安後,他那個非凡的腦子就像博物館裡某個特殊的標本,浸在裝滿防腐劑的罐子內,被一位無法抗拒衝動的病理學家據為己有,並藏了起來達四十年之久。這是不道德且違法的瀆職行為,然而哈維卻認為解開這個蘊育著超凡科學心智頭腦的祕密,是他個人對科學以及人類所應負的義務和天職。
雖然這位病理學家自封為那個無價科學瑰寶的守護者,但是該項工作卻遠超過他的能力所及。在之後的四十年內,哈維將切成小片的愛因斯坦腦子分送給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和偽科學家,讓他們用不同的方法去探索愛因斯坦之所以是天才的蛛絲馬跡。
這個超凡的心智所構思出來的想法,超越了其他任何心智的想像能力;就算把相對論完整闡述及說明之後,也還是超越了許多心智的理解能力。這個心智得出了時間本身具有彈性的想法;時間與空間、質量與能量的界線因此變得模糊,彼此之間可以自由轉換;同時,時間可以按照事件而自由壓縮或擴展。而得出這份創見的,靠的就只是思想的力量:那個想像著自己乘著光束前進的心智。
在愛因斯坦的腦遭竊三十年後,有四小片腦塊來到任職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一位傑出神經解剖學家黛蒙(Marian Diamond)手中。她擁有的小試藥瓶內,裝有四片從愛因斯坦大腦皮質刻意挑選的部位所切下的組織。按黛蒙的想法,愛因斯坦的天才都是與他非凡的抽象思考能力和高階的認知功能有關;如果說他的天才可在任何身體構造上看出的話,那必定是在大腦皮質負責這些認知功能的部位,而不會是皮質上處理聽覺、視覺或是控制運動等功能的所在;因為後面這些功能,在愛因斯坦身上並不突出。哈維早已將愛因斯坦的腦皮質切成小塊,並加以編號,然後以賽珞琔(celloidin)這種硝化纖維化合物包埋起來;賽珞琔硬化後,就像是困住昆蟲的琥珀一樣,將腦組織封在裡頭。黛蒙想要檢視從兩個聯合皮質取得的樣本,那是腦中用來分析和綜合資訊的地方。她要求哈維寄給她從位於額頭後方的前額葉區,以及從靠近耳後上方的下頂葉區取下的樣本,同時還必須從腦的左右兩側相同位置都取得樣本;那是因為大多數人的左右兩側腦半球偏重不同的認知功能,就像我們的左右手一樣,各司其職。
前額葉皮質負責規劃、短期記憶,以及訊息的概念化和歸類。惡名昭彰的前額葉切除術就是將這塊區域與腦分離,這麼做可保留病人基本的心智功能,卻失去了從經驗當中進行抽象思考與合成新知的高階認知能力,因此變得溫順。另外,黛蒙還索取了愛因斯坦下頂葉皮質的樣本,因為該部位與想像、記憶和專注力有關。這部分腦區受損的病人,尤其是位於主導腦半球的那一側(通常是左側),會失去識字的能力,無法拼字和計算。醫學文獻記載了一位數學家在該部位的腦皮質受損後,就很難用公式來陳述數學問題。
當黛蒙拿著裝了這四小塊乳白色、方糖大小腦組織的瓶子朝著燈光看去時,她內心好奇、興奮與期待的心情,完全沒有因為研究了一輩子人類大腦皮質的解剖而有稍許減弱;這些可是不同的組織,至少由它們萌生的心智確實如此。如果她能發現這些腦組織創造出愛因斯坦天才的奧祕,那麼這項發現將有助於我們瞭解連結心智和大腦的細胞機制,讓我們曉得人腦如何運作,以及那些心智生病的不幸人士又出了什麼問題。
黛蒙得找到合適的對照組來和這些樣本做比較。某些不確定的因素降低了一些她的興奮之情:雖然她的實驗室裡擺滿了一盒盒從許多不同人腦製作而成的顯微切片,但是愛因斯坦的腦就只有那麼一顆。愛因斯坦那個超級非凡、獨一無二的腦所意味的是,無論她得出什麼樣的結果,實驗都將無法重複。每位科學家在實驗結束時所面臨的惱人不確定性,將因為實驗沒有機會重複而更難克服。從任何數據所得出的結論,都可能發生錯誤,但唯有透過觀察、資料收集以及事實組合,科學才得以進步。要是不去檢視這些組織,會不會更好呢?
科學家面對實驗結果的不確定性,是利用數學方法來測量並計算對照組與實驗組之間的差異,看看出於偶然的可能性有多大。同理,在犯罪現場找到一根金色頭髮究竟有多大意義,可以由族群當中金髮人數的比例做部分評估。
黛蒙與同事決定著手研究這些腦組織樣品的細胞結構。為此,他們得將腦組織切到比一個細胞的直徑還要薄的程度,然後加以染色;這麼一來,他們就能在形成組織的眾多細胞中,分辨出單一神經元的結構細節。這些切片的厚度之薄,就算把十五片疊在一起,也才只有一根人髮的厚度。擺在黛蒙面前的,是一排裝滿鮮艷顏色溶液的玻璃皿,從深紫到閃粉紅不等,後者還會隨光線照射的角度不同而變成綠色,好似浮在水面的油膜一般。在得出一系列的組織切片後,她用非常細的毛筆把它們一一移入裝有染色液的小玻璃器皿中。
隔了一天,黛蒙把切片放在顯微鏡下觀察,陰影從一片迷霧中現身;突然間,聚焦的清晰影像映入她眼簾,就好像飛機準備降落時,穿過雲層後看到的都市全景。她看到的是愛因斯坦大腦某個皮質區的神經元,或許就是那個神經元將想像變成了可行的事實。問題是:它與位於愛因斯坦大腦皮質另一區,好比用來命令手指在紙上寫下數學符號的那些一般神經元,又有什麼不同呢?而這個神經元與她腦中相同位置的神經元,那個正為了思忖眼前的無價珍寶與奧祕,而在自己心緒線路中引發影像和思考火花的神經元,又有多相似呢?像這樣一個在顯微鏡下才看得見的細胞,怎麼可能如此徹底地改變了這個世界?這個細胞與牛頓腦中同一位置的神經元相比,又會有什麼不同?科技的發展是由數以千計的小進步累積而成,但科學進展有時又會出現觀念的巨幅躍進,好比哥白尼的太陽系統觀點,牛頓的重力和運動定律,達爾文的物種演化論以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這種大躍進的例子,伸出雙手十指就可盡數;而她眼前的這個神經元,就來自某個改變了世界的心靈。
經過數日仔細地測量與計算細胞的大小與數目,黛蒙將資料加總起來,並與十一個對照組腦子相同部位取得的數據做比較;這些腦子都來自男性,年齡在四十七歲到八十歲之間。結果是:沒有發現任何差別。
從天才以及從一般人腦中取得的神經元,竟然沒有差別!再者,平均而言,愛因斯坦那個饒富創造力的大腦皮質,與不以創造力著稱的男性腦皮質相比,其中所含的神經元數目是相等的。然而在所有的資料中,倒是有個項目不同:在愛因斯坦大腦的四個部位中,非神經元的細胞數目都高到破表。平均來說,正常的腦組織標本中每兩個神經元會有一個非神經細胞,而愛因斯坦的腦子裡卻有雙倍的非神經細胞;也就是說,大約每一個神經元就有一個非神經細胞。數目差距最大的,是在愛因斯坦主導腦半球的頂葉區:抽象觀念、視覺影像和複雜思考都在那兒發生。這個發現是否純屬巧合?根據對照組樣品的變異範圍,黛蒙計算出這種差異屬於隨機出現的可能性;從愛因斯坦腦中各部位的取樣所得,她發現這種可能性很低。
黛蒙在愛因斯坦和常人的大腦之間,所能看到的唯一不同處,是在這些非神經細胞上。這會是天才的細胞基礎嗎?它們又是如何辦到的?這些稱作「神經膠細胞」(neuroglia)的非神經細胞,究竟是做什麼的?數十年來,這些神經膠細胞就只是被看成腦內的包裹填充泡泡,提供神經元實質依靠或養分供應的結締組織罷了。然而在愛因斯坦的腦中,這種細胞的數目卻多出很多。神經膠細胞與心智功能有關的推測,遠遠超出大多數神經科學家的思維框架。神經膠細胞的拉丁文原意是「神經黏膠」,也就是這個名字將這個框架黏封了一個世紀之久。
心智的盲點:藏在眼前的神經膠細胞
要想真正領會黛蒙的發現有何意義,我們得先瞭解神經膠細胞的一些基本事實,並曉得如今我們對人腦運作方式看法的源起。大多數人對神經系統的印象,是類似電話網路當中的一堆纜線,而且這種印象在過去一百年來幾乎沒有什麼改變。這種觀念根深柢固的程度,讓人很難想像神經系統還會有其他的運作方式,或無從想到這種觀念最初現身時被視為前衛基進;為此而引發的激烈爭議與辯論,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
一八五二年出生在西班牙一個醫生家庭的卡厚爾(Santiago Ramón y Cajal),是個有藝術天分的男孩,擅長繪畫並喜歡當時剛發明的攝影術,只不過這些嗜好追求無法為他贏得一份高薪的職業。在攻讀醫學學位時,他花了很多時間給他父親仔細解剖的大體畫出解剖圖。
卡厚爾三十三歲那年,在西班牙薩拉戈薩(Zaragoza)大學擔任解剖學教授。一八八七年他造訪馬德里時,看到一片神經組織顯微切片,是利用義大利解剖學家高爾基(Camillo Golgi)十四年前發明的技術染出來的,那張影像改變了卡厚爾的一生。他放棄了先前頗受敬重的細菌學研究,轉而擔任巴塞隆納大學正常和病理組織學的主任,並致力於改進及利用高爾基的染色方法,來揭開腦部的細胞結構。過去十四年來,由於高爾基染色法不夠穩定,因此沒有受到重視。這種染色法經常失敗,只不過一旦成功了,結果則讓人驚豔。
這種染色法的化學反應,與卡厚爾深感興趣的黑白攝影術是相通的。由於某種至今仍然不明的原因,僅有少數約百分之一的神經元會吸附上染劑;只不過一旦被染上,整個細胞就都呈了色,好似映照在冬日夕陽背景下的橡樹黑色剪影,所有細節都清晰顯現出來。要是這種方法把標本中所有的神經元都染上了色,反而會變得沒有用,因為裹在任何腦組織切片裡的神經纖維分枝,都將被染成一團無法辨識的糾纏。反之,卡厚爾看到的是清楚顯示的完整單一神經元,有如從岩石中剝離出來的化石一般。
今日,我們傾向於用電腦及電子產品來與腦做類比;但在電子世紀之前,流行的類比是不同的模式。在十九世紀,磨坊和工廠從河流及小溪引水來推動水車,以獲取動力;然後再以運河和小溪把水導入原來的河道。水力學是當時將力量做遠距轉移的最先進機制:只要控制連接供水線和水管的閥門,就可將動力引往需要之處。當時的人認為神經系統也以類似的方式運作:體內的神經就好比是相互連接的水管線,可將力量傳給任何的肌肉。透過顯微鏡,當時的人可在神經內看到數以百計的細管,於是想像它們彼此間都以控制閥互相連接,最終通向腦中的主汽缸。在顯微鏡下,還可看到腦內有數以千計稱作軸突(axon)的微細小管相互糾纏,形成白質區的徑束,在腦組織內穿梭。
這些徑束的源頭落在灰質區內,那是覆蓋在大腦扭曲表面的一層厚組織,就好似從綠花椰菜的主莖分出越來越小的分支,終點是花菜表面無數的綠色小花苞。高爾基染色法將稱作神經元的單一神經細胞給鉅細靡遺地呈現,但是這些構造細節要如何詮釋,卻有兩派科學家持不同看法。高爾基見到從神經細胞本體伸出、可投射至身體遠處的細長軸突,還會分叉並與其他軸突形成無數的連接,於是他認為這些相互連接的神經纖維所形成的網絡,就構成了傳達神經指令或傳導感覺器官輸入訊息所需的路徑。位於神經細胞另一端,高爾基看到了高度分叉並形成有尖細頂端類似小樹根的構造;由於其形狀類似樹,因此稱作樹突(dendrite)。他猜測,這些構造是為了吸取養分以維持神經細胞存活,並提供推動神經能量的動力之需;如今我們已知,該能量是在軸突網路中流動的電流。然而以相同的材料,用上高爾基發明的相同染色法,卡厚爾卻看到了截然不同的東西。卡厚爾提出了一個新理論,也就是如今為人熟知的「神經元學說」。
卡厚爾以一週七天、一天十六小時的狂熱進行工作。他檢視了取自各式各樣以及不同年齡動物的腦組織,還包括腦及身體的所有部位。他觀察過的標本來自人、兔子、狗、天竺鼠、大鼠、小鼠、雞、魚、蛙,以及動物胚胎。他以藝術家精確的觀察力,將神經元的輪廓描繪下來並仔細研究,並逐漸從那些結構中理出頭緒。他觀察到神經細胞類似電線般向外伸展的軸突,雖然可在腦中投射相當遠的距離,但是它們的終端總是落在樹突叢中,也就是神經元上類似小樹根的細小分支。經由某種觀念的飛躍,卡厚爾領悟到每個神經元並不是網上的一個節點,而是獨立的單元!尤有甚者,神經元的功能具有方向性。他意識到訊息在神經網內傳遞,並非像蜘蛛網上的振動那樣,朝各個方向輻射而出;反之,訊息在每個神經元是以單向傳導,就像在單行道上行走的馬車一般。訊息由樹根狀的樹突傳入神經元,指令則經由興奮的軸突,由細胞的另一端送出去。軸突並沒有與其他軸突形成網狀構造,而是來到另一個神經元的樹突。神經訊息以某種未知的方式,通過了軸突和樹突間的門檻,抵達下一個神經元;其過程就像把包裹放在接收神經元的門口,讓後者自行撿起。而前後兩個神經細胞的細胞質,並不像相連水管中的液體那樣是互通的。
介於軸突與樹突間的空隙,稱作突觸(synapse)。藉由控制訊息在軸突與樹突之間每個突觸的通過與否,腦便能以非常複雜的方式指揮資訊的流通,就像電話交換機處理通話一般。
卡厚爾成為二十世紀最出名的神經解剖學家,並與發明了那個重要的染色法、卻不同意神經元學說的競爭對手高爾基,合得了一九○六年的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卡厚爾以驚人的勤奮工作,得出一個又一個新發現;他發表了成卷有關腦部細胞結構的科學論文和專書,直到今日都還是豐富且具有價值的正確資料來源。然而卡厚爾畫作中略去不表的部分,卻同樣顯示出他過人的才氣。
每一個顯微切片中冗雜的細胞結構,經過卡厚爾藝術家的鑑別眼光過濾後,在畫作上呈現出來的都是去蕪存菁後留下的基本資訊。在複雜的腦結構荒野中披荊斬棘前進時,卡厚爾從來沒有畫出像火星運河或精子頭內小人之類的無中生有之物。他非常謹慎小心,從不會把不相干的東西混淆在一起。
在那些他看得清楚、卻總是被排除在神經元畫作之外的東西裡,有一樣就是神經膠細胞。他把這些細胞分開來畫,在多年的研究生涯中,這些奇形怪狀的細胞圖填滿了好幾冊的筆記本。這些細胞讓他著迷,但經由高爾基染色法所顯示的細胞結構,卻無法提供任何功能上的線索。神經膠細胞缺少線狀的軸突,也沒有樹根狀的樹突。在顯微鏡下,這些細胞看起來像是子彈射過玻璃所留下的破洞:圓圈在中央,邊上有細裂痕狀向外輻射所形成的暈輪。卡厚爾稱它們為「蜘蛛細胞」,因為從它們肥大的細胞體有許多原生質腿朝各個方向伸出。其他科學家認為這些細胞的形狀像星星,就稱它們為「星狀細胞」(astrocyte),這個稱呼沿用至今,是我們目前所知四種神經膠細胞之一的名字。不過卡厚爾看到的膠細胞,各種奇形怪狀都有,不一而足。有的像古怪的扇狀珊瑚,有的像沿著軸突串起的香腸。多數的權威學者認為這些非神經細胞是腦內某種形式的結締組織,用來填塞神經元之間的空隙。如果這些怪異的腦細胞有任何高階功能的話,卡厚爾曉得以他所擁有的原始工具是無法解開其中的奧祕。因此他很聰明地將這些細胞分開來畫,並在他的筆記本中以同樣的方式分開處理。他這麼做,似乎是在暗示未來的神經科學家回答下面這個問題:這另一半的腦到底是什麼呀?
傾聽中的膠細胞:揭開卡厚爾的祕密
九十年之後,我坐在一個小房間內,藍色的冷光從電腦螢幕映在我臉上。在我左邊是一張如撞球檯大小的大型不銹鋼桌,桌面約有二十公分厚,碩大的不銹鋼桌腳內有空氣活塞讓桌面懸浮,以提供精準、合乎光學要求且防震的桌平面。這張桌子上擺滿了互相連接的電子儀器,並以鏍絲牢牢鎖在桌上。這些儀器當中的冷卻風扇發出的呼呼聲充溢在空氣之中,間以這些大型儀器內部自動閥和葉門啟動時發出的喀嚓聲。來自隔壁房間一個洗衣機大小冷卻裝置的粗大黑色水管,將冰冷的水在紫外線雷射外圍循環,以降低其溫度,那是這套儀器的心臟。一條表面有皺紋、類似用於烘衣機的管子,則把有毒的臭氧蒸氣從小房間內抽排出去。
在桌子中央,擺著一個以鮮橘色透明塑膠玻璃製作、像櫃子一般大小的盒子,是用來保護我免於紫外線照射的防護罩。盒子內放置的,是這間房中卡厚爾唯一可能認出的東西:一臺顯微鏡。他大概會對這個製造精密的巨型儀器感到驚訝,那有他使用的顯微鏡三倍大,同時他所觀察的腦組織標本是以刀片自己徒手削切的。縱然如此,他應該會認得這顯微鏡的一些基本構造和組件,例如可移動的標本臺和兩個接目鏡,與他曾以孩童般的好奇向內注視的裝置類似。如今接目鏡的功能,差不多就只剩下在調整接物鏡下的標本位置時,讓人匆匆瞄上一眼;標本位置一旦固定後,通往接目鏡的葉門就會關上,把光線轉投至數位相機或是光倍增管,以強化微弱的影像,並將顯微鏡下的景象鮮明地顯示在電腦螢幕上。我則像直升機駕駛般以操控桿控制視野,在顯微鏡下的景觀中遨遊。
經由旋轉類似收音機上的調整鈕,我以光學「切片」的方式將細胞結構由上到下一次一層地剝離。我最先看到的影像是細胞膜上的一點,類似球從玻璃窗上彈回後所留下的汙痕。接著看到的是像用刀子將球頂切掉後,留下的一圈外圍;如此繼續往下一直切到細胞的另一頭。在此過程中,從細胞膜到細胞核的胞內一切微細構造,都給記錄下來。更讓人訝異的是,我用那臺先進光學顯微鏡檢視的細胞還是活生生的;它們取自小鼠胚胎,被分離成單獨的細胞後,在有溫控和供氧的實驗室培養箱中已生長了超過一個月;後者等於是一個人造的子宮。
卡厚爾應該可以馬上認出螢幕上顯示的影像是神經元。事實上,從其特殊的球形,他還可以正確指出那是負責將皮膚的觸、熱及痛覺傳至脊髓的感覺神經元,正式名稱是背根節(dorsal root ganglion, DRG)神經元。但是卡厚爾還是會對這些精確對焦的細胞影像感到困惑,因為那看起來是從薄到不可能的切片上所觀察到的影像。
戴上特殊的鏡片後,我看到的電腦螢幕搖身一變,成了一扇敞開的窗戶,那個單一的背根節神經元懸浮在三維空間中,宛如聖誕樹上的吊飾一般。我以手指觸動滑鼠,可將這個細胞順著任何軸線旋轉,以檢視細胞內最精微的構造細節。卡厚爾肯定會被我的這些動作給驚嚇到。
只不過好戲還在後頭。這是一臺雷射掃描式共軛焦顯微鏡,是我任職的美國國家衛生院下設研究所購置的第一臺。這臺顯微鏡與一般的光學顯微鏡不同,不僅能以光切片顯示清晰的細胞構造,還能顯示細胞的生化和生理反應過程,包括分子在活細胞內及細胞間的移動所攜帶的訊息和指令,從細胞表面的電性訊號到每個細胞的細胞核中心不等。在一九九四年,那是美國國內僅有的幾臺之一,只不過到今天,沒有任何一個主要大學的研究部門裡會沒有這種設備,而且多數大學還會有好幾臺。
來自深處的亮光
二十年前,我在聖地牙哥的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hy)擔任海洋生物學家;每年夏天我會研究一種不為人熟知、叫做銀鮫的深海魚。這種魚隨著深層的冰冷洋流往上游,來到北太平洋靠近華盛頓州聖璜島(San Juan Islands)區域時,會上升到接近水表面;富萊德港海洋研究室(Friday Harbor Marine Laboratory)就座落在聖璜島上。每年夏天,從世界各處來的科學家集結於此,形成一個夏令營社區;在沒有外在干擾下,他們可以終日從事科學研究。某日我們正準備搭乘備有底拖網的漁船出海採集標本時,我注意到有幾位學生拿著捕蝶網在碼頭跑上跑下,他們興奮地將網伸入水中,撈取一種銀幣大小的維多利亞多管發光水母(Aequorea victoria)。這些漂亮的透明生物是富萊德港夏天海域常見的物種,但我不大能理解那些採集者為何會那麼興奮。其中一位學生回答了我的問題,告訴我他們對這種水母發出的生物光感興趣;有好些海洋生物都會發出冷光,通常是藍綠色的磷光。我問道:「哦,那你們是想瞭解牠們如何會發光嗎?」
「不是,那個部分我們已知道了。我們是想萃取那個接住鈣離子後會發光的蛋白質,然後把這種稱作水母素(aequorin)的蛋白質注射到細胞內,好研究鈣的流動。」
我馬上就明白了。電生理學家用極細的電極來研究神經活動:他們在顯微鏡下以微調器將電極精準地刺入希望記錄的神經位置。離子在神經細胞內的流動會產生生物電流,利用電子儀器將這種電流放大上千倍後,科學家便能從示波器的磷光屏幕上看到在神經線路中遊走的神經脈衝訊號,一如醫生在手術房以監視器追蹤病人的心跳。電生理學家想知道這些電流是如何形成並受到調節,他們也想知道在細胞內的眾多離子中,哪些離子形成了電流。這是一項困難的工作,他們的做法通常是在浸泡神經細胞的溶液中更換不同的離子,或是施以藥物來抑制細胞膜上讓不同離子(像是鈉、鉀或鈣等)進入細胞的某些蛋白質通道。
當這些科學家成功地運用這種技術之後,他們就會把水母的螢光蛋白注入神經細胞,然後在顯微鏡下觀察。如果有鈣離子流入或流經某個細胞,他們將會在流動的路線後面看到有綠色的磷光殘留,就好像飛機劃過晴空所留下的凝結尾那樣。這麼一來,科學家就能親眼看到活細胞內的生化和生理活動。他們看到的不只是示波器螢幕上一閃而過、顯示電流變化的綠色線條和光點,而是在三度空間內所發生的即時事件。
一轉眼,二十年過去了,如今我使用的背根節神經元經過一系列的溶液處理,讓它們吸進一種對鈣離子反應靈敏的人造螢光染劑,與從水母萃取出來的螢光蛋白類似。我把這些細胞養在底部配置有鉑電極的培養皿中,這樣我就可以給予背根節神經元微弱的電擊,使其產生脈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