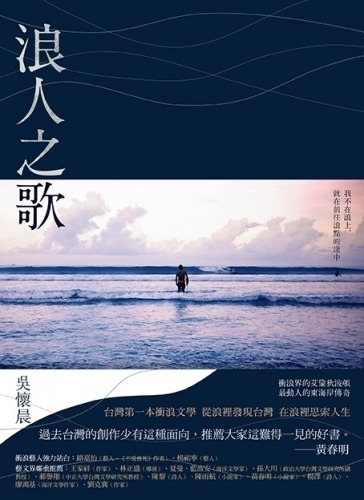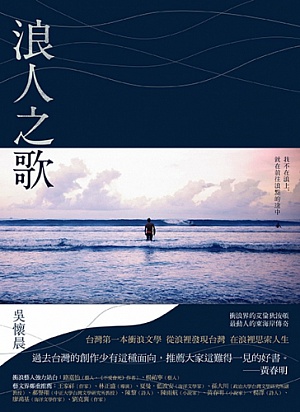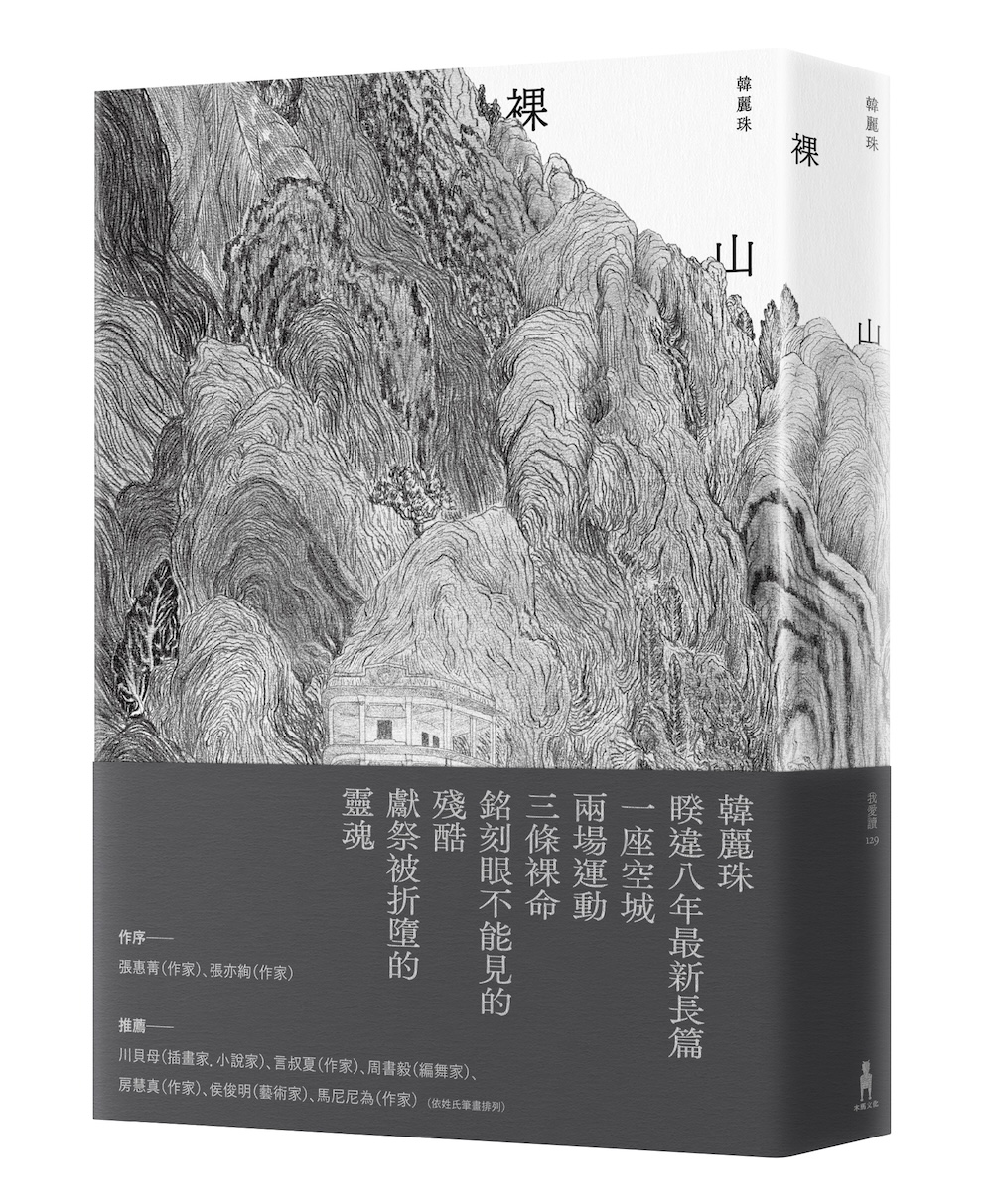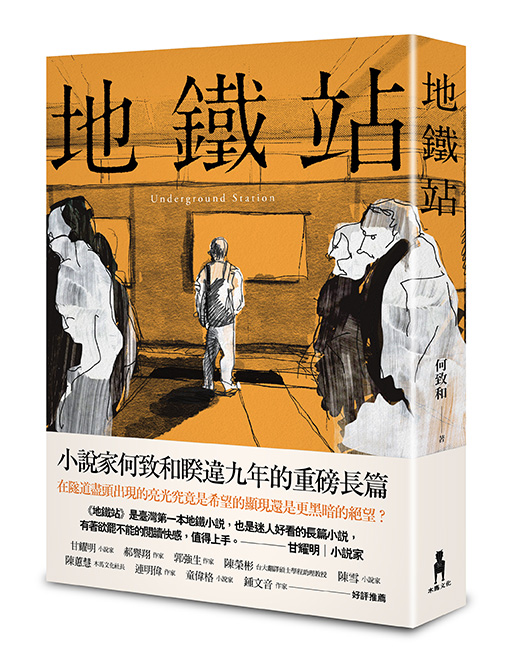自序
孔隆孔隆,身子直往前去;偶爾與另一串列車交會中,背後的車窗玻璃忍不住一身顫抖。總是這樣,夜行列車由北往南奔走而去,右方大山,左首大海,火車離開北方都會後,始穿梭於一條又一條的隧道。幽明交替,意識恍惚中,孔隆孔隆越渡了山與山之縣界。漆黑視野裡,海不可見。但海,總起落在旁。
我總是喜歡這樣獨自一人的長途旅程,闇夜中,沿島嶼東方陸塊,移動在大山與大洋夾縫的狹仄土地上。一夜黝暗,越幾十座月台,幽幽微微穿幾十個小鎮。
每一個小鎮我都指認得出。甚至,每一條鐵道旁淒清的公路,每一處大洋邊的港,轉瞬望眼間,我也都辨認得出。
為何我總是在趕路的當口?那些起於理想,過往年歲中發光的憂鬱?彷彿異鄉行旅,我所直視,我所,合宜於我的一個人,孤獨。
。。。
衝浪第一年,我不知走過屏鵝公路段多少回。
彼時,都是選擇週間的夜晚時分出發。由左營上國道,切88快速路,下屏東南州交流閘口,就進入了國境南端筆直的省道,沿途滿是南方果實熟熱的味,古老泥層蓊鬱,魚塭排列,熱帶。
黑暗公路中,僅有前導的車燈螢亮;常常,樂聲流洩,我就會想起妳。有時只是在風切聲的情愫中想妳,一人凝視著擋風玻璃時。有時,就著車廂的樂聲就哼唱起來。屏鵝公路,聽風的歌,海在那頭等我,在彼時以衝浪為理型的第一年,海即是我最柔媚的情人,我水的女神。
然而,終究瑣碎不重要的這些年就這麼過去了。
每每,背離陸地的方向。青春仍是持續不滅的火種,時刻閃爍我菸草尖端。
。。。
初初衝浪之時,就曾閱讀過一篇文獻。他們說,老海人若衝浪久了,浪裡白條,耳朵長期接觸浸潤海水成分,外耳道會慢慢沈積鈣化,骨質增生,久之,有時一邊耳朵就會塞住,成半聾狀態。
衝浪人的耳朵(surfer’s ear),專有名詞稱作「外生骨贅」(exostosis),或直爽點叫「衝浪耳道狹窄症」。
一隻耳聰,一隻耳聵。我想像一個老海人在管浪中奔馳時半是清明半是神眩的狀態。
衝浪經年,我雖未進階到染此症頭。但我早愜意地,把這醫學案例解讀為一種比喻,可比詩的喻意。
衝浪是一門與自我對話的學問。
一道浪,只容一人在汪洋的背景中飛翔駕馭。
人在外海波浪上奔馳時,觀眾從岸上看去,多只見小米粒的斑點在浪壁上移動。
有時,我坐在外海等浪湧,東部的天地,在在都顯示著舒緩但氣魄的色澤,海與天充滿360度的藍色視野,無限抽象近無以名之。
這中間沒有任何中介。極其純粹之事。在那些無暇的夢幻時光裡,只有一個簡單的靈魂在水中,載浮載沉,無所謂地消磨著在世時間,也許等待了一個時辰的光陰才等到一道好浪。但那就夠了。那乾淨的銷魂時刻,光影於靈魂上移動著造化著──靈魂與浪的本質不過如此。
是的,衝浪是一門耳窩的航道學。耳窩開展出蜿蜿蜒蜒,完美的沿螺旋狀趨進的航道,而若,能隨此路徑緩緩切入,抵達的即是內心;安靜如耳聵的內心。
這些年,我在島嶼的海岸線上來回穿梭,在一個人的車上前往浪點,動線迴旋如耳窩。
端坐浪板,在自己的心頭嘴角鼻腔思念著遠方的女孩,將聲響隔絕在外,將靜默沈積在耳。
浪人在自己的浪壁弧線上,浪板跳躍著、飛翔著。
孤寂的行旅、思念的愛、浪人之歌,原都是迴盪在浸淫海水日久的耳道之內,是在自己的曲折的私密的耳窩中寂寞前進的生命。
我喜歡海邊,以及在海邊遊蕩、鬼混、自在的生命。
。。。
這本書中的篇章大抵成於二○○六―二○一二年,恰是我自己變動最劇烈的人生。然而,書中的心情都是海的,溫柔耽溺的,以致於許多時日光陰後的此在這一刻,只要再浸漬篇中文字,海風的味道就會吹拂出來,潮水彼岸,徐徐的,吹過寬厚的太平洋。
我是一個哲學的研究者,但這些年,也從沒須臾稍離海邊的過活。對自己,此二者是一致的,哲學之堅之礪與海浪的剛硬,皆磨人。兩者,淬鍊都是心智。
在這本集子中,我抹去了大多理論之斧鑿,僅留動作;因為衝浪所經歷的人物及台灣寶島,夠美了,大自然能自然動人。
於是,翻開這本集子,太平洋眾多美麗的海灘便歷歷在目,裡頭除了有自己的海邊生活外,還紀錄下一個個傳奇浪人的故事,這一切,混雜著東部潮湧及海岸山脈下原住民的生息。五六年來寫作的旅程中,有夥伴撤離,有老海人離世,有同好之間的捍格;一切轉瞬即逝後,剩下來的只有浪,仍是千百年來那般弧度起伏的浪。
。。。
本書多篇曾刊載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在此,我要向諸編輯及詩人楊澤,表達我由衷感激。此書順利出版,要向小說家伊格言致謝。而,主編瓊如費心的工作,是本書成就的最後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