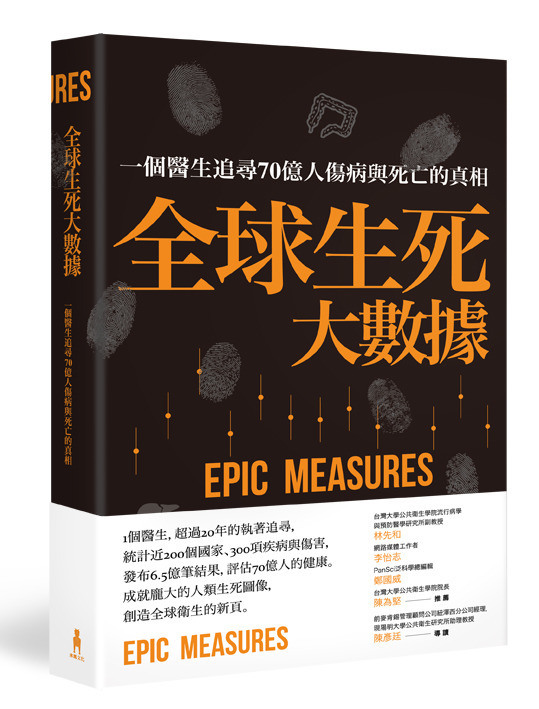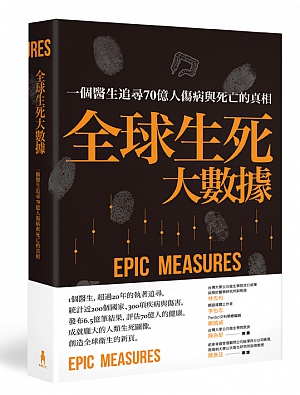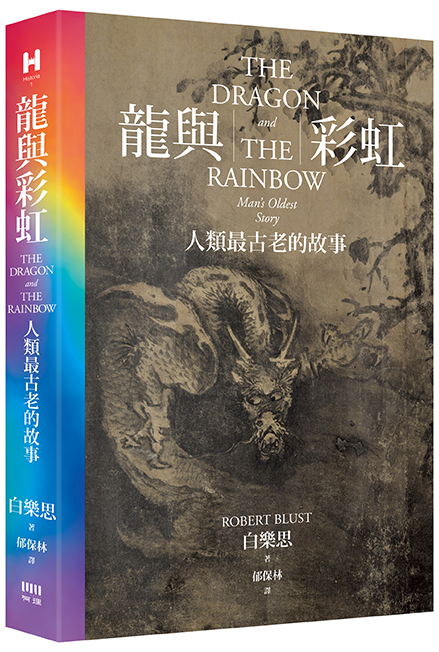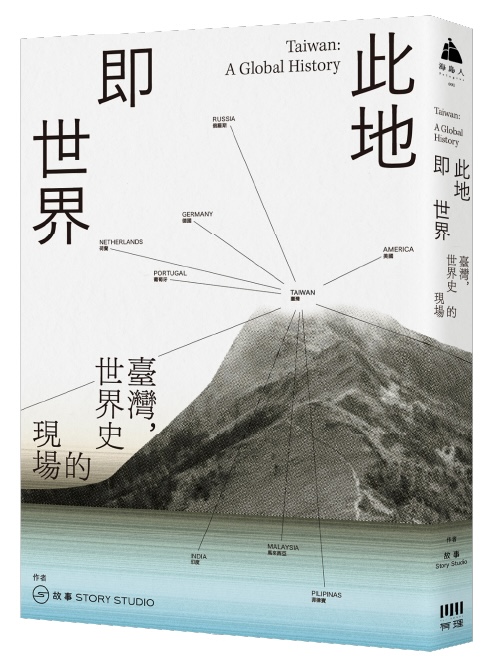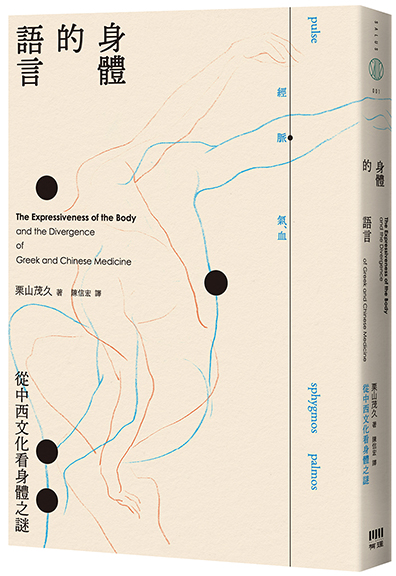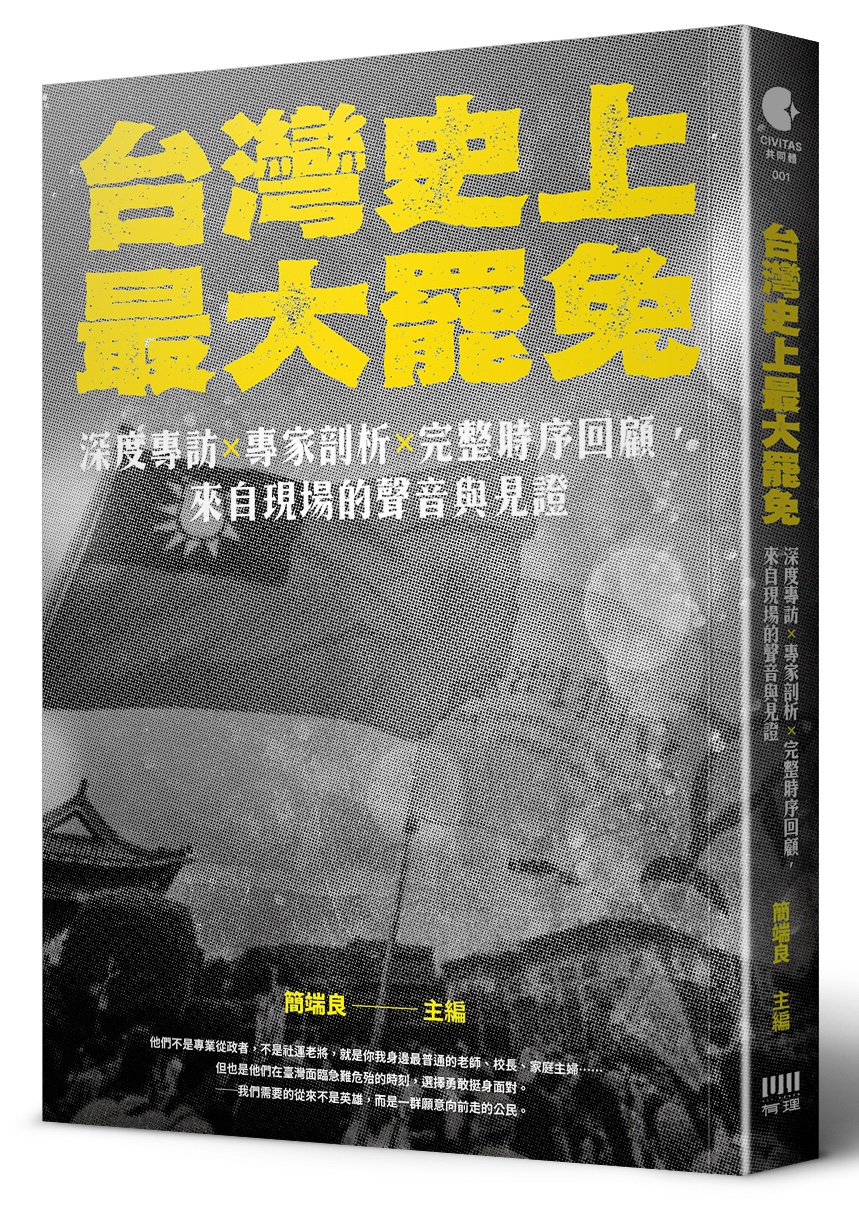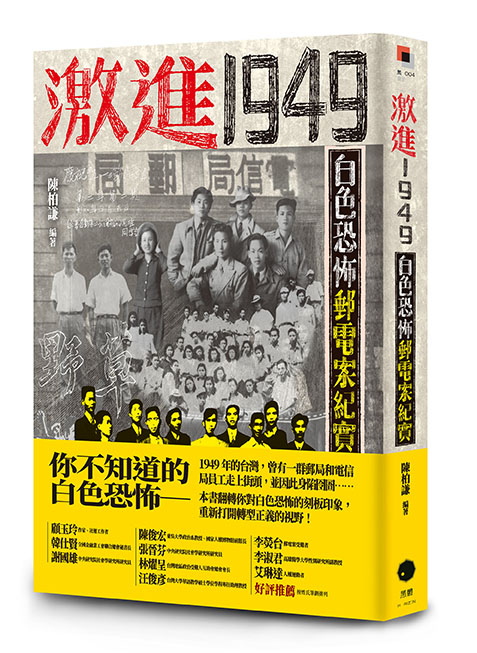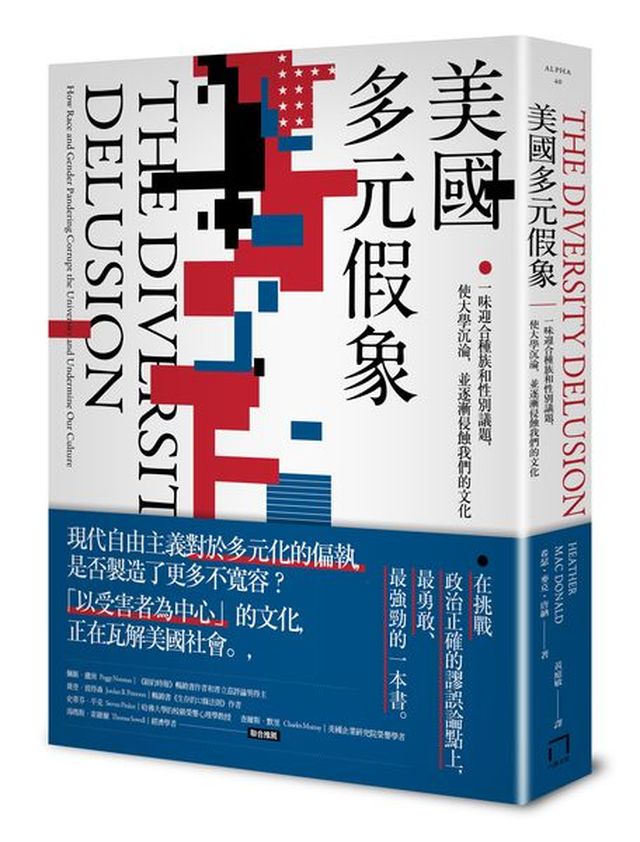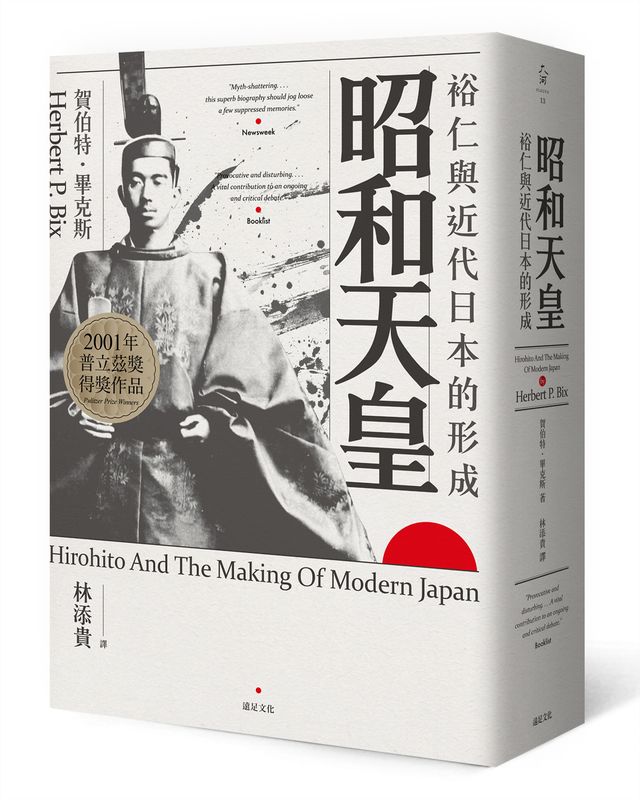統計近200個國家、300項疾病與傷害,
發布6.5億筆結果,評估70億人的健康。
成就龐大的人類生死圖像,
創造全球衛生的新頁。
初始,全球公共衛生研究權威克里斯‧穆雷醫生只是想問:人因何而病,為何而死?
本書跟隨穆雷醫生的足跡,回溯幼年與心臟科醫師父親與微生物學家母親到世界各地旅遊,在撒哈拉沙漠經營小診所,在缺水缺電的惡劣環境下,眼見人類的生存艱難。自哈佛與牛津大學畢業後,他曾於哈佛大學的全球衛生與人口研究所任教,也於世界衛生組織的政策集成部門(Evidence and Information for Policy Cluster)工作。之後受到延攬至華盛頓大學,在比爾‧蓋茲基金會的贊助下,建立了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這是一段漫長又艱辛的旅程。穆雷醫生的童年老是在「背地圖」,當一家子在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原野上的嚮導。他返美後順利進入哈佛大學就讀,在這個有再多怪咖異數都不足為奇的校園,他總是成為奇特的存在。他牢記在非洲的童年記憶,與同學共組「拯救世界」俱樂部。他的執著也帶著他一路累積知識與能力,從哈佛到牛津,也從日內瓦到西雅圖。他追逐知識與真理,帶領被戲稱為「特種部隊」的下屬瘋狂加班再加班,傾盡全力的成果也惹惱一堆官僚組織,激怒一票專業人士,使世衛的各國家代表氣得跳腳想把他趕下台。
他誠實坦率,直言好辯,偉大的願景與企圖心給他過人的耐力,有時卻也因此遭到孤立,最後甚至被世界衛生組織解職的不堪。只是,他從未放棄。即使滿心期待在哈佛的研究中心,因贊助者收手而胎死腹中,他都不輕言放棄。每個階段的殫精竭慮,歷時多年的論戰與研究,最後成為落腳西雅圖、使世人驚艷震撼的「全球疾病負擔」(Global Burden of Disease)計畫——這就是他「拯救世界」的方式。
有些病會致死,有些不會,卻可能讓人痛不欲生,造成失能,影響生活品質。穆雷醫師長期深入研究全球公共衛生議題,戮力發展全球公共衛生的評量指標「全球疾病負擔」,便是為了結合正確的數據,提出新的計算方式。除了統計死亡與平均餘命(Life Expectancy),也有計算失能指標的「失能年數損失」(YLDs)與「失能調整損失年數」(DALYs)等,意在明確呈現那些不致死的病症,如何造成健康的損失,影響餘生。至今,此計畫統計全球將近兩百個國家的各年齡層與性別,超過三百項疾病,67項可能致病致死的風險因子(Risk Factors)。風險因子讓我們理解疾病、失能或死亡或背後的成因,也許是環境,也可能是行為:如空氣污染、吸菸,缺乏衛生設備,缺乏運動等等。
了解導致全球各地區域的健康問題,才可能針對不同地區的衛生需求對症下藥。
例如,在開發中國家,車輛傷害是年輕成年男性第三大健康損失原因。憂鬱症是年輕成年女性第五大健康損失原因。而骨關節炎雖不會致人於死,卻是第九大健康損失原因。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牙齒問題的總損失相當於貧血。在整個亞洲,缺血性心臟病所造成的生命損失年數多過妊娠併發症,神經精神病的傷害多過營養不良。而在中東,傷害造成的健康問題是癌症的四倍嚴重。「全球疾病負擔」便是在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與各地區團體的協助下,蒐集數據,建立資料庫,希望據此改善並促進全球公共衛生的發展。
本書以穆雷醫生為主角,從他的成長故事,描繪對於醫療議題的投注與熱情,並為公共衛生議題帶來大數據的應用。「人為何而死」是簡單的提問,卻牽引了複雜無比的答案──除了呈現巨幅的全球疾病分布,也更能深入了解性別、年齡、區域等因素所造成的差異,進而採取積極改善行動。了解死因,只是一切的開始
大數據是眾人爭先恐後的創新與商機,然而當大數據遇上醫療,呈現了實際存在卻從來未曾如此具象的人類生存圖譜,協助人類改善並過更好的生活。正如比爾‧蓋茲所說:「本書所指出的是,當我們獲得更多正確的資訊,便能做出更好的選擇,我們的作為也能更具影響力。」
【各界好評】
「我們獲得更多正確的資訊,便能做出更好的選擇,也更有影響力。」──比爾‧蓋茲(Bill Gates)
「誰活著,誰又死了?何時,為什麼,多少人?傑瑞米.史密斯撰寫一個執著於數字
的男人和這些數字所訴說的生命戲劇,這個迷人故事讀起來像小說,而且勝過所有的全球衛生教科書或調查。」──保羅.法默(Paul Farmer),「健康夥伴」共同創辦人,哈佛醫學院全球衛生與社會醫學系共同主任,布萊根婦女醫院全球衛生權益部主管
「一旦你了解自己所做的工作可以拯救數百萬生命,你便很難不變得有些瘋狂。本書訴說人們在全世界反對之下,仍然相信該做的事一定可以做到。內容有趣,架構完整,兼具啟發性。就像《社群網戰》一樣,但是更加重要。拯救一百萬人並不酷。你知道什麼才叫酷嗎?拯救十億人。」──漢克.格林(Hank Green)「Crash Course」及「SciShow」製作人及主持人
「一個單純信念經過合理構思與堅決追求之後,可以大幅改善人類生活的動人故事。」──愛德華.威爾森(Edward O. Wilson),哈佛大學名譽教授
「本書是全球衛生的速成課程,混雜一些驚險小說與傳記。讓人驚呼的是,本書主人公完全像個好萊塢角色──聰明但剛硬的科學家,立志要改革我們對醫療照護的看法。了解到真正使人類病痛的原因,總是讓我訝異。」──賈各布斯(A. J. Jacobs),《管他正統或偏方,就是要健康》(Drop Dead Healthy)及《我的聖經狂想曲》(The Year of Living Biblically)作者
2.穆雷,穆雷,穆雷和穆雷
克里斯.穆雷的整個童年都在背地圖。他的父母都是紐西蘭人,也是地球上最熱愛旅行的人。約翰是一名心臟科醫師。安妮是一名微生物學家。他們是在火車上相識的——1943 年還是大學生時,他們在學校放假結束後搭同一班火車回去奧塔哥大學(University of Otago)。1950 年代,他們一起在梅約醫學中心(Mayo Clinic)工作,後來,明尼蘇達大學邀請約翰擔任教授,他們便來到美國。
探險是他們一家人的嗜好。冬天時,約翰和安妮會帶克里斯和他的三個兄姐——琳達,奈傑爾和梅根,開車到科羅拉多州韋爾(Vail)的新滑雪渡假中心。夏天時,他們開車到南加州,在海灘上宿營。為了多看看鄉村,有一年夏天穆雷一家穿越黃石國家公園和提頓國家公園(Tetons);還有一年夏天是去奧瑞岡州,並南下到太平洋沿岸;第三年則是橫越科羅拉多州。沿途為了省錢,約翰開車到深夜,把車停在路邊,搭起行軍床讓大家睡覺。安妮在偏僻的乳牛牧場長大,她教導孩子們接受到陌生地方冒險。「她總是想要看看下個山丘、下個彎道之後有什麼,」約翰說。
1960 年代中期時,克里斯的大姊琳達已經大學畢業,在泛美航空(Pan American Airlines)擔任空服員。這份工作的福利是員工眷屬可以用票價的兩成,以候補方式飛到世界各地。打包好手提箱,有必要時就睡在機場,穆雷一家一有機會便出發,去過泰國、土耳其、黎巴嫩、埃及和印度。有一次,他們飛到了奈洛比,租了一部露營車,花了一個月在肯亞、烏干達和坦尚尼亞旅遊了一大圈。後來,看過奧瑪.雪瑞夫(Omar Sharif)主演的電影《大騎士》(The Horseman)之後,安妮受到啟發,決定他們要去阿富汗。當時還小的克里斯在四十多年後,猶記班達米爾國家公園(Band-e Amir)的藍色湖泊、高達一百二十呎以上的巴米揚石造大佛(後來被塔利班政權摧毀),以及一大堆的頭骨,人家告訴他那是七個半世紀前成吉思汗在該地區征戰的遺跡。
1973 年,約翰的下個學年獲准休假研究。他提議一家人去南非, 那裡是克里斯蒂安.巴納德(Christiaan Barnard)醫師的故鄉,亦即世界上首例成功人類心臟移植手術的實施者。已是高中三年級的奈傑爾不肯去。這也是情有可原。即使他的父親想要在這年進行基礎研究,而不是參與政治,這名長髮的青少年不願住在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國家。高中一年級的梅根和國小四年級的克里斯也是這麼認為。如果他們一家有一整年空閒的時間,他們應該直接去幫助急難的人們,孩子們這麼說。他們想讓自己發揮用處。世上不是有數百萬人迫切需要醫療照護嗎?
受到感動的安妮,著手規畫。「她熱愛沙漠和沙漠的一切,」約翰談起他們早年的旅行。「冒險人生的急劇改變」——由牧場女孩,到實驗室員工,最後成為明尼亞波利斯郊區的全職母親。透過他們的地方教會,西敏寺長老教會,安妮聯絡上美國基督教國際救濟會(CWS)的人員。他們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蓋了一所新醫院,在東非的尼日,不論是當年或現在都是地球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穆雷一家可以去那裡幫忙嗎?
他們一家人坐在廚房餐桌,三個小孩和安妮都在遊說約翰。「這是好主意,」奈傑爾、梅根和克里斯說。「我們為什麼不做呢?」
「我們可以對人類做出貢獻,」安妮說。「小小的貢獻,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一家人一起合作,一起做點事。」
好吧,約翰說。或許這項挑戰對他們都好。他的父親在五歲或六歲時由黎巴嫩來到紐西蘭,挨家挨戶賣火柴,賺個幾毛錢。他的父母都沒有中學畢業。他們經營歌廳式餐館,賣燒烤晚餐給美國大兵,還兩人二重唱,才賺到他的醫學院學費。自己的孩子在富足的郊區長大,卻都不是格外勤勉的學生,令他感到失望。他們想要到尼日服務一年?他心想,如果有任何事可以扭轉人生,這就是了。
這一家人籌錢,飛到英國,待在牛津,儲備未來一年的補給品。他們直接從索利赫爾(Solihull)的工廠用折扣價買下那兩部荒原路華越野車。他們搭渡輪由南安普敦前往法國,開車往南進入西班牙,橫越該國後由靠近直布羅陀(Gibraltar)的地方進入非洲。
然後便進入全球最大的沙漠。
撒哈拉沙漠涵蓋大約九百四十萬平方公里的地區,幾乎相當於歐洲,是德州的十三倍大。撒哈拉三面臨海:北方是地中海,西方是大西洋,東方是紅海。往南,沙漠消失在薩赫勒(Sahel),這個半乾旱地帶向來水氣較多,因此也較多人居住。可是,當約翰、安妮、奈傑爾、梅根和克里斯緩慢地往南行駛了數百公里到尼日首府尼亞美(Niamey)再往東開了一千三百公里到他們被分派的醫院,位於迪法城(Diffa),毗鄰尼日與查德及奈及利亞的邊境,炎熱與乾旱一直沒有消退。人們會攔下他們的車子,他們要來乞討。起初,穆雷一家以為他們要錢。可是, 錢毫無用處。「你有水嗎?」他們問穆雷一家。「可以給我的小孩一些水嗎?」
他們在四月初抵達省府迪法。當地人口約1000到2000人,大多住在茅草頂的泥造小屋。所謂的醫院其實是一間小診所,由義大利人捐贈, 很容易就能看到:兩棟長型、低矮的一層樓組合屋,是這個非常不現代的城鎮裡唯一的現代建築。其中一棟屋子是門診服務,有一個候診區, 檢查室,一間實驗室和領藥處。另一棟屋子是住院病房,男性病患與女性病患各有十張病床,還有護士休息室及手術室。裡頭全部空無一物。
屋面有放置發電機的台座,但機器還沒來。有一個水塔,但沒有水。有一間用品室,但幾乎沒有用品。
外頭,人們聚集在沙地上。那些人是病患。
穆雷一家想要見其他人員:醫師,護士,行政人員。有個政府官員走了出來。原來,先前抵達的另一名醫師看了一眼現場後就走掉了。
他們一家人氣急敗壞。「我們的情況很糟,」約翰說。「我們在這種情況下沒辦法做事。」還是其實他們可以?他們一路從明尼亞波利斯、綑在越野車上運過來的有他們自己的發電機、移動式心電圖機、一台舊顯微鏡、實驗室基本器具,還有大概可以撐上兩星期的醫療用品。他跟安妮在世界另一端的自家舒適廚房餐桌上商量:她想要冒險?現在,她如願以償了。假如他們待下來,約翰將是主治兼唯一的醫師。安妮和十四歲的梅根將擔任護士。十七歲的奈傑爾要維修設備及負責實驗室。還有十歲的克里斯呢?「我是藥劑師兼跑腿小弟,」他解釋說。
不然,他們可以回去他們大老遠來的地方。
「我們討論說,我們能不能在既沒水又沒電的情況下,經營這間醫院?」約翰回想。「我們認為,我們辦得到。」
診所旁邊有一棟醫師的小房子,圍繞著矮樹叢和開著粉紅和白花的馬齒莧。可惜,房子沒有開窗,只有空調機。就像診所一樣,這些在義大利援助的資產負債表上彷彿是給非洲的一大筆預付款。可是,沒有電力,它們都是累贅而已。除非下雨,但很稀少(薩赫勒的旱災是二十年來最嚴重的),他們一家都在戶外宿營。他們搭起床單以維持穩私,掛著蚊帳,打開行軍床,早上時再摺起來收好。起床後,他們看到頭頂上的蚊帳。他們會立刻穿上靴子,並先檢查有沒有蠍子。
數世紀之前,這整個地區都是查德湖,可是旱災及乾燥的氣候造成淺淺的水域縮減,只剩下以前規模的一小部分,最靠近的地方要往東跋涉一百公里。鎮上廣場有一口水井,深達一千英尺,可供大家汲水。當地糧食短缺,是把去年的小米磨成粉。每天早上,克里斯都會聽到捶打的節奏,婦女們將小米加入香料和水,做得像粥一樣濃稠。
人們聽說醫院開張了,有個醫師提供醫療。他們走了數天數夜,自己來看病,或者帶他們的孩子或年老的親人來看病。約翰去找地方行政長官,申請使用水井的許可。獲得同意後,奈傑爾每天早晨都開車去取水。他費力地裝滿自家的金屬桶和一戶人家捐贈的兩百公升圓桶。接著,由於他們一家沒有可用的無線電或者救護車,這名青少年便在地方上漫遊,供水給有需要的人,順便把病重到無法走完這趟路的人接上車。梅根則和母親在早上接待病患。按照父親的指示,她配藥、打點滴、打針或縫合傷口。他們每天都得清掃地板的沙子和塵土,每三天便要拖地。至於電力,這家人完全無計可施。他們僅有的少量燃料,都用來在重要治療時啟動發電機。其他時候,只有在陰涼處和傍晚時才會涼爽,而照明則來自陽光。「如果我們做完醫院的事,我們就會去陪爸爸,」梅根說。當他在做例行性的手術時,她們便拿手電筒照明。
起初克里斯年紀太小,無法直接看護病人,因此曾短暫上過當地學校。那段經驗真是一場災難。克里斯有書卷氣,聰明,是兄姊之中最像學者父親的,他喜歡猜謎,玩「戰國風雲」(Risk)之類的桌上遊戲。這些都讓他不適合被束縛在單間小屋裡「學習」。他們講的語言他都聽不懂。凡是做錯事的學生都會挨打。他被傳染了A 型肝炎,一種經由食物傳染的發熱型病毒,他原已瘦弱的體重掉了將近40%,從89 磅開始,最低降到54 磅才穩住。「克里斯病得很嚴重,」約翰說。「我們束手無策。」他們往西南開了七百二十五公里到奈及利亞北方的大城卡諾市(Kano),尋找補給品和新鮮食品。克里斯的皮膚是鮮黃色。他後來回憶,他使盡全力才沒有在大飯店外昏倒。
等他復原後,他的父母吩咐他去整理診所珍貴的少數醫療用品。在乾燥、有霉味的房間裡,他看到自己的父親瘋狂地打電話,要求所需的設備和盤尼西林等基本藥物。他們獲知,有一批藥在途中了。然後來了一張憑單,上頭用法語寫著:「藥物」(medicament)。太好了。克里斯和他的家人熱切地等候了數個星期。最後,一部滿載的小貨車出現在地平線上了。
他們拉下車斗擋板。上頭沒有藥物。小貨車裝的是數百或數千個橘子果醬罐頭,而且它們都有些撞壞了。這真的很荒唐——「像是荒謬劇場的一幕,」克里斯說。「你真的是哭笑不得,」奈傑爾說。「到底是怎麼由藥物變成橘子果醬的?」是翻譯錯誤?有人想要擺脫發臭的食品?是徹底的詐欺?當權者有人在乎嗎,抑或他們只想打發掉穆雷而已?答案不得而知。但克里斯明白兩件事:有關當局答應某件事,並不表示事情一定會成真;判斷是非的唯一方法是自己去發現。
克里斯開始在病房裡幫忙。炭疽病,結核病,被毒蛇咬而生壞疽的腿,由腳踝上探出頭來的麥地那龍線蟲(又稱為幾內亞線蟲)。「當時, 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已,」他後來說。「這就是我們做的事。那是我還小的時候,我從沒想過那是小孩子不該做的事。」有一天的午飯時間, 克里斯看到醫院外頭有一名老人,倒臥在放空水桶的沙地上。「他很有尊嚴,」克里斯說。「他不想讓別人看出他生病了。」可是克里斯還是個小孩。「他把我拉過去,指給我看他在沙地上吐血了。」這名十歲的男孩跑去找爸爸,告訴他看見的情形。當穆雷一家把病人扛回醫院時, 克里斯一直握著那個老人的手。
約翰診斷他是肝硬化併發症,但不是喝酒引起的,而是血吸蟲病——這種寄生蟲侵入靜脈曲張,造成食道大量出血。這名老人極為感謝克里斯的協助,便請親友送給這個男孩一袋萊姆做為禮物,這是該地區幾乎前所未聞的奢侈品。可是,數日後,這名老人躺在病床上時,身體大量出血。而且,這次出血是致命性。克里斯非常傷心,但是他幾乎立刻就恢復工作。
從早到晚,憂傷的家屬用色彩鮮艷的布裹著生病的孩童從沙漠揹到醫院來,他們年紀和克里斯相仿,或者更年幼。這些孩童瘦到不成人形,只有破爛的衣衫和隆起的胸腔。有的孩子大聲哭喊,其他孩子連哭的力氣都沒有。很多孩子死掉。最慘的是一個極度營養不良的孩子被放在水盆裡,花了一整天才帶到醫院,他的父母是打算緩解孩子發燒。但是,當他們掀開蓋住水盆的毛巾要給穆雷一家看的時候,那個小孩早已溺斃身亡。
克里斯的兄姊對於目睹的景況極為難過。「你可以理解成年人的死亡,」奈傑爾說。「可是,小孩子的死亡——你本身就是那個年紀的孩子——他們和你一樣。」他記得,看見那麼多人死亡,對他的心理產生「衝擊波」。四十年後,梅根談到這段記憶仍舊哽咽。克里斯則像他父母一樣抿住上唇。這成為他一輩子的模式:壓抑負面情緒,將精力發洩到工作上。醫師不哭泣,更不會在病患面前哭。他們必須全力挽救性命。「他的性格變得更加外向,」約翰說。「他變得更加堅定,更加執著。」
3. 迎向全世界
大家都說,在官僚體系裡,什麼事都不准做,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多疑又好辯的穆雷,現在必須熟悉微妙的辦公室政治。舉例來說,凡是敏感的事,一定要當面講,不能用書面,否則會對你自己不利。想要簽署在南美洲舉辦會議的合約嗎?官方流程要填寫四份表格和六周的時間,不然你可以打一通關鍵電話,兩個小時便可搞定。初期, 有個員工去穆雷的辦公室要便利貼。根據規定,某些文具只有主任以上的主管才能使用。「便利貼必須來自於我,或是波士頓,」穆雷說。世衛組織每一份需要簽名的文件,都放在「卷宗」裡。秘書長使用紫色或綠色墨水,執行主任則必須使用其他顏色;單位主管用第三種顏色,普通人員則用第四種。穆雷把他收到的第一份卷宗拿給他的助理說:「我再也不要看到這種東西。」第二天,卷宗又來了,而且堆得更高。「我輸了,他們贏了,」穆雷回想。「那使我驚覺到現實。」
穆雷與法蘭克的上任,對於世衛組織也是一大改變。這個機構從不曾設立過政策單位,只有防治不同疾病的獨立計畫。每項疾病都有自己的專家和評估方法。在那個狹窄的領域內,政策建言係依據成員國送交的、或許可靠也或許不可靠的數據來特製化,而不是全面化。打從第一天,穆雷便宣布,世衛組織將首度自己提出疾病、傷害與死亡的官方估計與預測。他不僅想要複製,更要超越他和同事在世銀與哈佛所做的。「我們必須進行全新的估計,」他說。「我們必須開發全新的方法。」世衛組織將是獨立、公正、創新及廣泛的;它將提供別人缺少的資訊,或是曾經錯誤的資訊。
換句話說,世衛組織現在不單純是政策機構,還是精密數據分析中心。穆雷的部屬和他都一起在世衛組織總部三樓工作,用活動式白色模組牆隔成小房間。他們使用的科技也沒有比一般辦公室標準好到哪裡——穆雷後來回想,「很蹩腳的」桌上型電腦——不過,他要求部屬撤掉瑰麗的成員國衛生報告和非政府機構、聯合國外部機構、個別世衛組織計畫未經檢查的統計,換上直接來自於官方出生登記紀錄、醫院檔案、家庭調查、人口統計評估和金融報告的數據。只要還有人處於疼痛及死亡,政策實證與資訊部門就會像是國際救難客服中心,查出病因並追蹤回應。如果政府及援助團體無法或者不肯提供誠實的估計,世衛組織將代替他們進行,並將數據公諸於世。
跟穆雷共事的人都有個問題,那就是熬夜加班、周末加班及假日加班。「克里斯期望大家這麼工作,因為他就是這樣工作的,」 羅培茲表示。他和穆雷在此時已經合作了十五年,比誰都還要熱烈支持這項新計畫。「能夠有他這種天才來到這個組織,試圖改變世衛組織的慣例、成果和名聲,真是太好了,」羅培茲表示。但是,「這給我造成很大的壓力,」他回憶說。「我必須提升組織裡的人員績效,好讓大家都做出貢獻,但在同時,很難讓眾人都達到這種高水準。」
世衛組織的員工屬於國際公務員,習慣在固定時間上班,大約是早上八點半到下午五點,每周工作五天。「他們依照傳統作息在做事情, 不論是上班時間或工作成果都一樣,」羅培茲表示。「他們花很多時間在開會。」學術界與企業界常見的競爭在這裡的辦公室是很陌生的。穆雷從先前衛生統計與衛生體系研究部門接收過來的人員,很多人根本不信任他的指示。「他們跟以前一樣在相同時間上班及下班,」羅培茲表示,「他們希望克里斯趕快走,好讓世衛組織恢復到以前的美好。」
人類在緊急情況下可以做出神奇的事情,可是很少人想要在永久的危機狀態之下生活或工作。可是,他的新同事和部屬發現,穆雷是少數愛好瘋狂步調的人。一部分原因是,他是那種腎上腺素狂飆的人,又具有奇特的願景、企圖心和耐力,生理與心理上皆然。不管是住院醫生或雙黑鑽滑雪斜坡,他都不會累。但另一部分原因是,跟全人類的急迫需求相較之下,他對於個人的私生活有一種相對不重要的感覺。他對工作的沉迷,或許再加上他想要實現目標的強大壓力,已經造成他的婚姻破裂,害他不能跟子女聯絡。他不會被日內瓦的職場習俗給嚇倒的。
穆雷非但沒有因挫折而放棄,為了回應世衛組織的悠閒傳統,他找來一批臨時雇員做為地下幕僚,他們認同他的迫切感,他希望藉由他們來活化整個世衛組織。他在世界各地大學刊登廣告,提供短期職務給多種領域的工作狂,他們願意接受一年到三年的合約來到日內瓦,協助「提供各類證據的客觀評估,以影響衛生政策」。這些職位由聯合國基金會與洛克斐勒基金會贊助。
世界各地將近1000人來應徵「全球衛生領導研究員」。穆雷欽點了24人加入他的團隊。雖然有些人後來留在世衛組織,但所有人一開始都不是正式員工。相反地,如同職務說明所說的,「研究員將不會是世衛組織的員工,而只是某段期間附屬於該組織。」
做為穆雷的統計特種部隊成員,你可以在早上九點或十點到班,這比一般員工稍微晚一些。可是你的下班時間是在晚上七點、十點或者半夜,如果你可以下班的話。穆雷的高階臨時雇員是靠著夜以繼日進行特定計畫,然後再處理接下來的情況來凝聚團隊精神,從來不必跟世衛組織的終身雇員打交道。
舉例來說,曾參與穆雷在哈佛Pop 中心疾病負擔小組的喬許.所羅門(Josh Salomon),在穆雷提供他一項每個月到日內瓦工作十天的獨特職務時,他已經是衛生政策和決策科學的研究生。他的第一項任務, 是全面檢討國際間對於愛滋病的統計。「我去的時候,便會儘量工作,」所羅門回憶說。他有很多人作伴。世衛組織總部的八樓有間休息室,旁邊有個淋浴間。「到這裡為克里斯工作的一些年輕人就住在那裡,」所羅門說。「那裡就是他們的住處。」他回想,有個人吹噓他一個月都沒有踏出世衛組織的大樓。研究員計畫的關鍵,亦即它之所以可以讓大家有這麼高的工作成果,是因為大家都明白這是臨時的。
政策實證與資訊部門的一些正式人員也接受新的步調與氛圍。然而,享受世衛組織合約福利的人——「探親假,朝九晚五,舒適的周末滑雪,錢多事少,」羅培茲概括說明——不滿至極。他們以前數年才需要完成的任務,現在數周或數月便得做完,否則就交給別人去做。每項結果的證據均由穆雷和他的小朋友嚴格審查。「他無禮又大膽,」羅培茲說。「他改變了這個組織的性質,讓它更科學,更盡責。他督促人們追求卓越,他催促世衛組織提升水平。」
這種推動與反抗絕對不僅限於政策實證與資訊部的辦公室。為了成立這個新部門,布倫特蘭必須從其他世衛組織部門抽走經費。日內瓦總部許多人因而把政策實證與資訊部視為威脅。技術性計畫再也不能在未經核對、確認其邏輯合理與內部一致之前,便公開宣稱死亡或疾病人數。外部驗證工作落在穆雷的小組身上。當所羅門走進會議室的時候, 他聽到人家竊竊私語說:「喔,思想警察來了。」
在世衛組織以外,其他聯合國機構同樣很不爽。他們並不希望世衛組織對於決定援助分配、國家衛生優先事項和拯救生命或死亡人數的統計數字具有最後裁決權。「1999 年時,聯合國人口部、聯合國統計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世衛組織,對於尚比亞兒童死亡率分別做出四種不同的估計,」羅培茲回想。「氣氛極為緊張。」若想要改善兒童衛生前景,你需要對於現況有著共同的認知。舉例而言,尚比亞的死亡人數是在增加或減少,死亡率是多少?「若產生混淆,就很難取得政治及社會共識來採取行動,」穆雷同意說。可是,解決混淆的方法不是讓大家都同意錯誤的數據。「那樣可以減少混淆,可是人們會做出錯誤決策,」他表示。「你無從得知誰的工作做得好,誰做得不好。」只要布倫特蘭及法蘭克支持他,穆雷便拒絕對於衛生評量的任何環節做出讓步。
事實上,他想要擴大規模。
4. 與比爾共進晚餐
1999 年,蓋茲看到全球疾病負擔而改變人生之後的兩年,他和穆雷見面了。穆雷去西雅圖為世衛組織募款,蓋茲邀請他到位於華盛頓湖的豪宅共進晚餐。剛開始的時候,平常很不容易感動的穆雷因為目睹名人而食不知味。這個畢生都在處理巨量數據的人,正坐在資訊革命的英雄家裡。蓋茲則是毫不做作,而且相當親切。極端的數字狂熱者遇到了另一個同類。這位電腦軟體大亨向這位追求數據的科學家展示他的個人圖書館,包括萊布尼茲與牛頓的第一版數學書籍,以及珍稀罕見的達文西手抄本,那是蓋茲五年前用超過3000萬美元在拍賣會買到的。可是, 藏書當中他最仔細閱讀的是1993 年的《世界發展報告》,書頁充滿摺角,蓋茲差不多背下來了。「他大量閱讀,而且注意細節,」穆雷後來說。「他很驚訝,或許有些失望,我們在全球衛生研究的實證基礎如此薄弱。」
蓋茲是大量蒐集與精密分析數據資料的文化教主之一。微軟的經理人在做出所有決策之前都會分析數據,他們應該讓花出去的每一塊錢都能創造出可量化的結果。「花了數年時間才查明事情,還有直到全球疾病負擔之前,人們都不知道死亡的原因,」穆雷說,「蓋茲無法相信這種事情。」
蓋茲的批評者與競爭者總是說他冷酷。事實上,他是更少見的個性:冷酷理性。在穆雷的研究當中,蓋茲看到他在每次董事會要求的正確資料與全面分析。在蓋茲身上,穆雷則是看到他的理想讀者:有想像力和能力的人,決心去做改變世界的善事,對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充滿興趣,沒有先入之見和政治考量,願意並能夠隨意投入經費,來創造數據顯示出可能創造的最大成果。全球衛生的最知名權威機構,世衛組織, 一整年的預算只有大約10 億美元——「一所中等規模大學醫院的財力,」布倫特蘭寫說。相較之下,蓋茲身價接近1000億美元——而且他和妻子決定要悉數捐贈出去。《世界發展報告》為他們指出一條明路,他們後來說。失能調整損失年數和全球疾病負擔研究,則為他們指出一條正道。「我們因而展開學習的旅程,」米蘭達十五年後回憶說。可是,「不單是學習的旅程,」她接著說。「而是『你能做些什麼?』」
在見到穆雷的前一年,直接受到五年前《世界發展報告》的影響, 蓋茲夫婦已捐贈1 億2500 萬美元贊助比爾與米蘭達蓋茲兒童疫苗計畫。在和穆雷用過晚餐之後不久,他們又再捐贈7.5億美元給新成立的全球疫苗免疫聯盟。蓋茲後來說,他在開支票時,手還在發抖。他還說:「這是我所做過的最佳投資。」
根據1993 年《世界發展報告》,「大多是能預防或者是可低價治癒的兒童疾病」,仍然造成撒哈拉以南非洲43%的疾病負擔,中國以外亞洲及波灣中東大約30%的疾病負擔。利用這些分析,蓋茲可以做個精明的慈善家,就像他是個精明的企業家一樣。「成功指標是能挽救生命,孩子沒有瘸腿,」他向《富比士》雜誌表示。「這與銷售量及獲利略有不同。但都是完全可以測量的,而且你可以設定野心勃勃的目標, 看自己做得如何。」
2000 年,蓋茲夫婦將他們先前的慈善事業整合到新成立的比爾與米蘭達蓋茲基金會,總部設在西雅圖,捐贈大約160 億美元,而這只是開始而已。全球衛生是該基金會最大的補助領域,「我們在決定重點領域時的起點是開發中國家的疾病負擔,以失能調整損失年數做為指標,」該基金會表示。當時穆雷擔任世衛組織新設的政策實證與資訊部門主任,對此感到極為欣慰。「那是一件大事,」他記得。「那代表著全球衛生的推手採用我們的計量指標。」
這筆捐贈十分引人注目。比爾與米蘭達蓋茲將捐出他們的個人財富,而穆雷的方程式將是他們的指引。這個圈子的人把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稱為「全球衛生的黃金年代」,新的經費與注意力在世界各地促成衛生照護的創新。諷刺的是,在2003 年及2006 年那段期間,許多受到疾病負擔研究啟發的新計畫相繼展開,然而穆雷卻被趕出世衛組織,他想在哈佛大學成立的研究中心也胎死腹中。
2006 年6 月,穆雷正面對殘酷的任務——必須裁撤為艾利森研究所聘用的員工,他的朋友金墉和法默,在哈佛醫學院和「健康夥伴」再度共事之後,正為了一項盧安達新計畫尋找外援。《愛無國界》已凸顯他們在海地、秘魯和俄羅斯醫療工作的可觀成就。現在他們提議把盧安達當成實驗室,以改進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衛生體系。他們覺得,穆雷可以幫他們,他們也可以幫穆雷。
「歷史以極為巧妙的方式,將我們的計畫結合得天衣無縫,」金墉回憶說。他甫結束世衛組織三年的工作重回哈佛,而他在日內瓦擔任資深顧問及該組織愛滋病計畫的負責人。在盧安達及整個撒哈拉以南非洲,愛滋病已是疾病負擔的第二大原因,僅次於瘧疾。然而,非傳染病,像是心臟病、中風、糖尿病、精神疾病等等,加總起來的負擔更大。穆雷資料豐富的分析正可以著重於投資建立完整衛生體系,以統一打擊這些問題的必要性。
在全世界新聞媒體報導艾利森確定不會捐給哈佛他先前允諾的資金之後一星期,金墉、法默和蓋茲基金會領導人在西雅圖進行先前安排好的會面。「他們很想要找我一起去,」穆雷回想。他同意和他們一塊去。
以前一起當住院醫師的這三人聯手遊說,但各自訴求衛生體系的不同層面。法默談及以往在世界各地的成果,和盧安達及整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機會。金墉呼籲擴大與加強當地員工訓練,「投資於人力資源,」他說。穆雷則是發表已講了兩年的演說,強調健康計量指標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