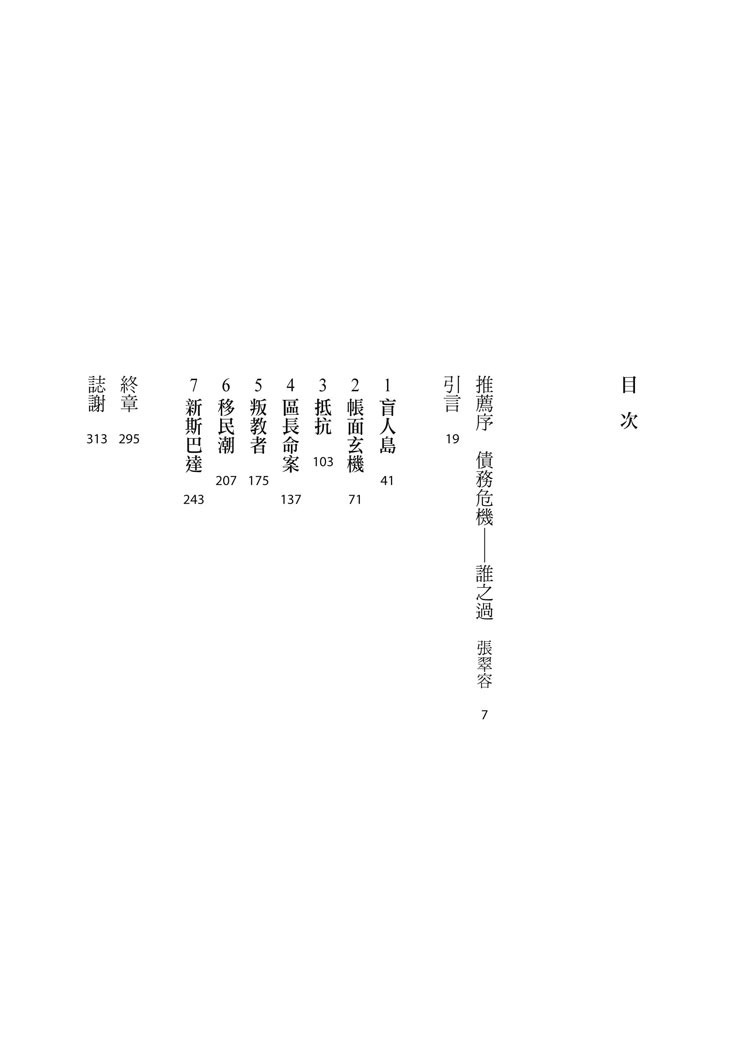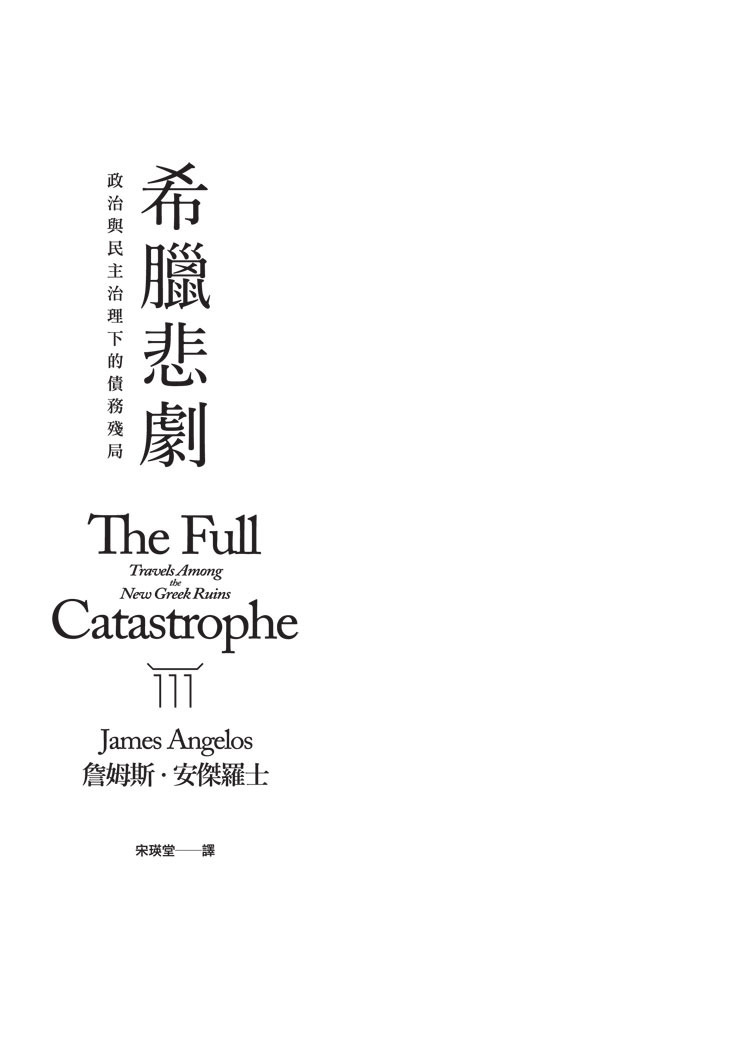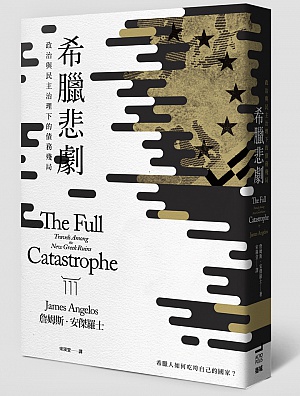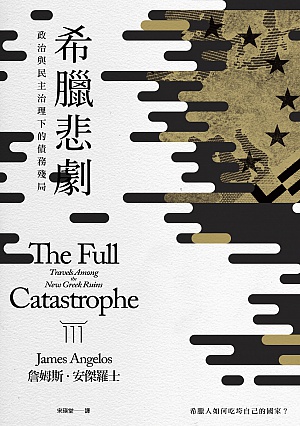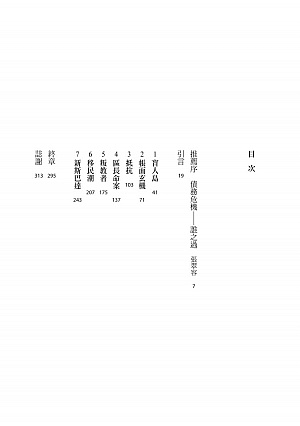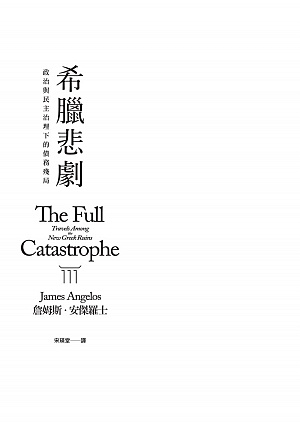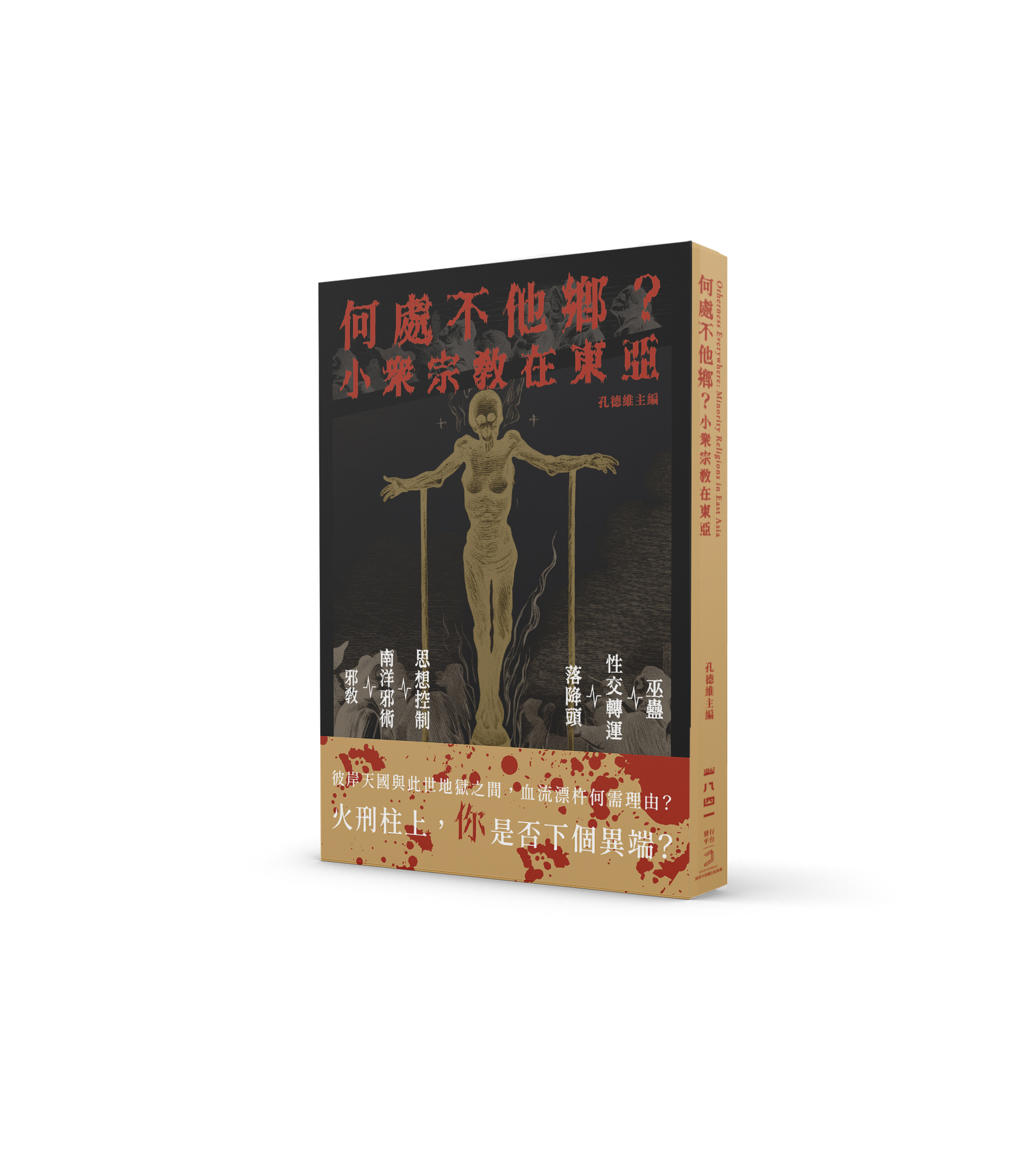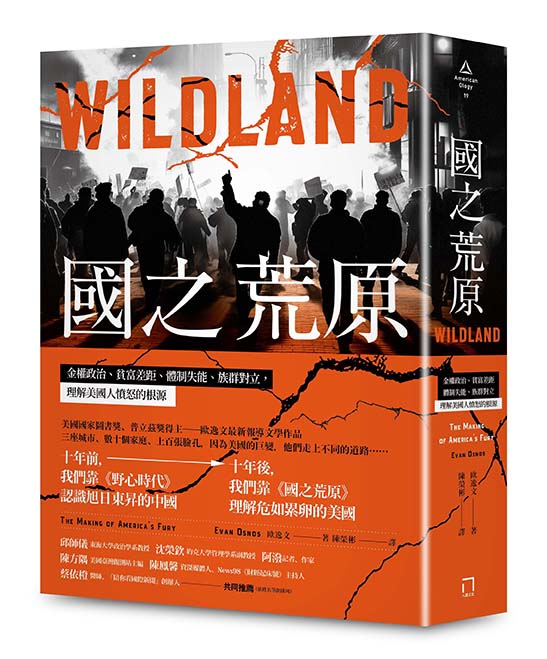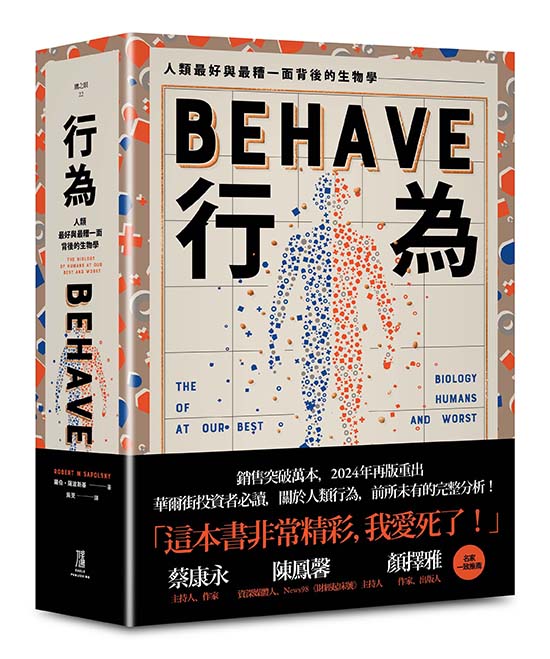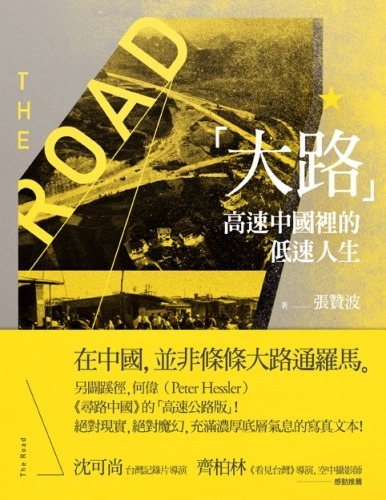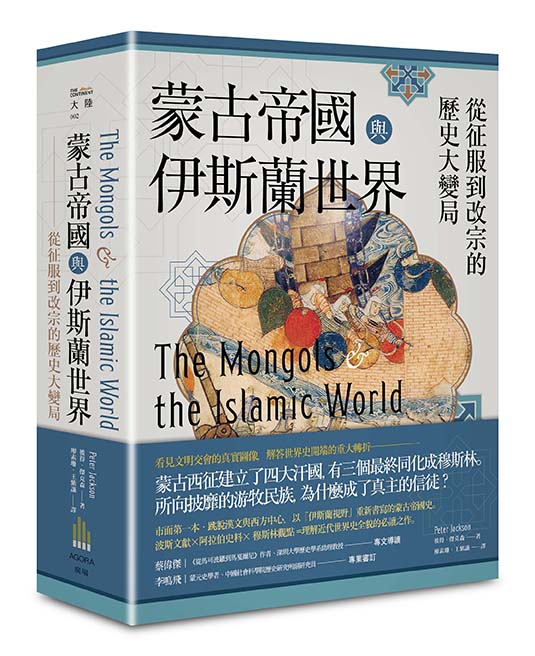【引言】
我們全是希臘人。—英國浪漫派詩人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一八二一年
三月二十五日是希臘獨立紀念日。在二○一四年的這一天,希臘人慶祝獨立革命開戰一
百九十三週年,最後如願脫離鄂圖曼帝國統治。這天,舉國上下男童打扮成山賊革命軍游擊隊員,穿著白色百褶裙和白長襪,頭戴圓筒紅氈帽,腳踩飾有毛球的木底鞋(clogs)。女童穿著傳統服飾,纏著流蘇頭巾,身上的豔麗裙裝繡著各地互異的棱角圖形。在獨立紀念日前夕,學童在學校禮堂表演話劇,重現鄂圖曼宰制希臘人幾世紀的苦難。伯羅奔尼撒(Peloponnese)半島西南角屬於麥森尼亞區(Messenia),有個山谷小鎮上演話劇,一位革命盜賊扮相的青少年從舞臺右方登臺,表達想為自由奮戰的渴望:「我能做什麼?我活不下去了!我心胸沉重,受不了土耳其人的奴役。」飾演母親的女孩裹著黃頭巾,勸他認分當牧羊人、養家餬口,但他不從。「母親,取劍予我,給我那支沉甸甸的步槍。」在愛琴海的桑托里尼(Santorini)島上,一群年紀小到連路都走不穩的幼稚園小朋友,腳步遲疑地圍圈跳著「札隆戈舞」(Dance of Zalongo)給父母看。這首民謠敘述希臘西北方的伊皮魯斯(Epirus)山區民眾在鄂圖曼的統治下集體自殺,婦女也紛紛拋嬰跳崖自盡的故事。藉著擴音器,當悲歌播到「再會了,悲慘世界,再會了,甜美人生,還有你,我悲慘的祖國,永別了」時,這些桑托里尼島的幼童幾乎跌成一堆。
每年,獨立紀念日的活動大同小異。儘管這次是我首度在希臘慶祝,但在紐約長島長大的我仍認得出許多習俗。我父母是希臘移民,他們規定我要去附近的希臘東正教教會學希臘文,上主日學班。教會是發揚祖國文化的海外據點,因此傳統毛球木底鞋、圈舞、對抗土耳其暴政的教條等,我從小就熟知了。話雖如此,這一年在希臘,顯而易見的是,尋常的慶典帶有更深遠的涵義。大約四年前,希臘瀕臨破產邊緣,而由於希臘是歐元區的會員國,希臘一倒,極可能掀起全球金融風暴。為避免災難一觸即發,俗稱「三頭馬車」(Troika)的歐盟執委會、國際貨幣基金、歐洲中央銀行,不顧德國等北方數國的質疑,決議力挺希臘,好讓希臘有能力慢慢償還巨額債務與利息。三頭馬車保證,未來幾年將提供數百億歐元分期貸款給希臘。歐盟領袖與國際貨幣基金認為,介入的性質無異於「伸出援手」,但希臘民眾普遍對此存疑。原來,金援的決策有但書,附記在希臘民眾稱為mnimonio的紓困備忘錄裡,其中許多條款讓民眾無法接受,例如薪資和年金必須縮減。國內政策幾乎全數讓給三頭定奪,而三頭也利用希臘破產在即的威脅,借力使力,強迫希臘服用改善金融體質的藥方。 奈何這帖藥效果不彰,希臘金融風暴即將陷入經濟大蕭條期的層次,因此紓困案實行不到兩年,又需要再來一帖。總計,希臘的貸款擔保高達二千四百五十億歐元,債務重整的規模之大是史上首見,它犧牲債券投資散戶的利益,打消掉一千零七十億歐元的未償債務。此外,歐洲央行為挽救岌岌可危的希臘銀行,不斷以低利短期貸款挹注。為報答紓困方案,希臘政府承諾大幅改革治國之道,上至漏洞百出的稅捐制度,下至高溫殺菌乳的販售期限,幾乎無所不包。金援的要求條件詳盡,例如希臘羊奶起司通關程序簡化、成立全國性的地籍事務所系統,這些要求顯示三頭嫌希臘欠缺自我改革的能力,必須嚴格監督。為了貫徹規定,三頭專家每季前往希臘查核進度,若希臘無法照規定改進,定期發放的款項則保留不發。簡言之,希臘人民將在被迫在持續高壓下改革。因此,對於許多希臘公民而言,金援反倒比較像又被外國強權占領。獨立紀念日一到,很適合反省當前處境。
這一天的舉國沉思大部分在教堂裡進行。並非全然湊巧的是,希臘獨立紀念日和天使報喜節是同一天,基督徒相信天使報喜節是天使長加百利宣布上帝之子將藉由聖母子宮降臨人間。建國人士認為,在救世主成胚胎的同一天獨立,最能彰顯文明古國脫胎成為現代希臘的寓意。基督教義和建國之道的共通點不勝枚舉。自古以來,希臘的主體性一直與東正教密不可分。希臘文的「革命」(epanastasis)近似「復活」(anastasis),而獨立戰爭也富含「復活」相關語—古希臘重新站起來了。因此,在獨立紀念日這天,衣著正式的希臘人,包括臉色嚴肅的高官與掛滿勛章的將領,魚貫進入全國各地教堂,聆聽大鬍子神職人員傳道闡述基督和國家化身的意義。雅典東邊小鎮司帕達(Spata)有間小教堂,一名福態的牧師披著呼應希臘國旗顏色的藍白色祭服,站在祭壇前,信眾則在他面前攤開一面國旗。牧師訴說土耳其人屠殺希臘人的往事,信眾也為之淚流,接著牧師宣讀革命英雄的姓名。科羅寇卓尼斯(Theodoros Kolokotronis),最受景仰的革命游擊隊戰士。「在此!」一名男信眾呼喊。波札里斯(Markos Botsaris),為國捐軀的革命英雄。「在此!」波柏里納(Laskarina Bouboulina),資助革命艦隊的富家寡婦,後因與鄰居吵架而中彈身亡而非戰死。「在此!」一女子回應。牧師說,這些革命烈士奮勇灑熱血,染紅了國土,冀望信仰堅貞的希臘能重獲自由。牧師接著問,今日希臘人承繼了這份聖禮,如何看待?「我們承繼了一個自由國家,卻再度把它送進奴役,」牧師以顫音說,彷彿潸然欲泣。「我們把自由掛在嘴上。兄弟們,哪來的自由。有權不得享,生活任人主宰,工作的酬勞被剝奪,哪來的自由。這種自由會奴役國家啊,」牧師說。「我們淪落至此,希臘的泥土因而嗚咽。」
慶祝紀念日的盛會在雅典舉行,氣氛也同樣凝重。希臘總統帕普利亞斯(Karolos Papoulias)年高八旬,二次大戰期間十幾歲的他曾參與抗戰,這天他坐在一小座天篷下閱兵,背後是新古典風格的國會大廈,線條素雅。一列又一列的軍人、坦克車、可移動導彈系統、大炮陸續出場。軍武場面壯闊,令人誤以為時空轉移到平壤,不太像歐洲某國首都。與歐洲其他國家相比,希臘素有狂購武器的名聲,喜歡在愛國節慶展示軍備。愛買武器並非沒道理,因為希臘持續和土耳其敵對,但縱情軍購卻也讓財政問題雪上加霜。更令閱兵儀式顯得突兀的是,到場的民眾不多。原來,政府基於安全因素,禁止民眾進入市中心大部分地區圍觀,但多數人心裡明白,政府忌諱的是大批民眾打著反撙節方案的旗幟示威。之前幾年,每逢慶典,必定引來抗議民眾鬧場。閱兵結束後,帕普利亞斯頂著隨輕風飛舞的稀疏灰髮,走向一簇麥克風,對電視機前的國民演說。「一百九十三年前,心胸宏遠偉大﹑英勇超絕的小民族展現道德勇氣,對抗鄂圖曼帝國,爭取自由,最後戰勝。今天,我們的人民也在奮戰,想掙脫債主的鉗制。歷史證明,我們終將戰勝。」
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等債主,或許期待希臘對其相助表示感激,但帕普利亞斯在演說中並未致謝。二十幾年前,歐洲國家簽訂條約,正式成立歐盟,而建立歐元區的宗旨是促進歐洲各國手足情誼,總統閱兵演說也未表達這份理念。歐陸史上各國激戰無以計數,如今經過幾十年協商,意在組成一個合作無間的政經聯盟,最後孕育出大家以為能終結戰禍的歐元。歐元誕生後的幾年間,運作情況似乎皆大歡喜,希臘人尤其高興。歐元誕生後兩年,希臘在二○○一年元旦正式採用歐元,但一年後才啟用歐元紙鈔和硬幣。為了順應希臘字母,歐元紙鈔上也印有歐元的希臘文EYPΩ。希臘版的二歐元硬幣則以希臘神話為主題,刻上化身為公牛的宙斯拐走裸胸閨女歐羅巴(Europa)的神話場景。德國比希臘富好幾倍,財政措施也比希臘審慎,全球公認德國是投資最穩當的國家之一,而在希臘初入歐元區的幾年,貸款給希臘政府的風險竟然僅比德國略高一些。進入歐元區後,希臘政府借錢容易多了,於是慷慨為公務員加高薪,提升年金福利,斥資數十億歐元籌辦二○○四年雅典奧運。輕鬆到手的錢如流水,供希臘人揮霍,造福了歐元區其他國家的經濟(例如希臘人喜歡買德國車)和希臘本身的經濟(國內餐廳、商家生意興隆,營造業蒸蒸日上)。從進入歐元區那年起,到二○○八年底金融危機殃及希臘為止,希臘的GDP以平均每年將近四%的速度暴漲,超越了愛爾蘭以外的歐元區所有國家。
我也見證到財富增加的某些現象。在一九八○年,小時候的我,有幾年去希臘祖母家過暑假,她家對面是古科林斯(Corinth)遺跡,從她家前院就看得見一座阿波羅神殿僅存的七根石柱,屹立在深藍色的科林斯灣前。祖母家所在的村莊圍繞古蹟而立,民風淳樸且多數村民以農為業,與我長住的長島郊區有相當大的落差。我祖母家最先進的科技是一臺淋浴用的電熱水器,這樣就不需為了洗個熱水澡還得用瓦斯燒熱水。祖母家附近有一位很窮的老婦人,住在搖搖欲墜的石屋裡,好像連自來水都沒有。我那時候常去科林斯灣游泳,記得有時見她拿著肥皂、戴著浴帽,以海為澡盆。老婦人的情況固然是例外,但仍足以證明,即使希臘經濟起飛了,窮日子仍屬於不久前的事。十年間,我斷斷續續來希臘,觀察到某種轉變。長久以來,很多希臘人靠僑胞親戚匯款貼補家用,一九八一年加入歐盟前身的歐洲共同體後,希臘國民像挖到新金礦。儘管希臘開發較落後,經濟也比不上歐洲先進國家,但躋身歐洲共同體後,希臘開始領到歐洲共同體的農產補助金和基礎建設資金。除此之外,當時由帕潘德里歐(Andreas Papandreou)領銜的左傾泛希臘社運黨(PASOK)新政府上臺,錢大筆大筆借,然後想辦法撒給全民,加薪連連,但也助長通貨膨脹,增加國債。當時的泛希社運黨成立不到十年,柏克萊經濟學者出身的帕潘德里歐走社會主義路線,支出毫不吝嗇,一副救世主的模樣。在這種環境下,很多家庭開始買高級車,裝修房子,也經常買不動產自保,免受希臘幣急貶的風險。就這樣,生活水準持續走高。有一年我在希臘過完暑假後,記得當時心想,希臘的物質條件改善很多,不再是遠遠比不上美國郊區了。我那時候的想法是,「脫胎成為現代國家,一定不是一件很難的事。」後來我祖母過世,我比較少進村子,但進步的速度似乎有增無減。希臘加入歐元區幾年後,我回村子一趟,發現多了幾棟別墅和時髦咖啡廳,路上有更多雙B。
入歐後,貸款變得便宜,助長榮景,與其說是反映希臘經濟基本面健全,倒不如說是顯示投資人有信心。因為投資人相信,成為歐元區國家後,對希臘財政穩定是一大保證。後來,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金融公司倒閉後,這份信心才開始瓦解,導致投資人檢討全球投資的安全性。信心動搖時,歐元區漸漸出現一種令人憂心的分歧走勢。被視為弱不禁風的歐元國家,包括希臘在內,貸款的利率攀升。反觀德國,由於投資人急著找避風港,就算把錢晾在德國生不出利息也好,德國的利率因此開始下降。
但為希臘捅出大婁子的事件直到二○○九年十月才爆發。政府該年預算赤字不是GDP的三.七%,而是大幅修正的一二.五%。隨後更陸續上修,最後超過一五%。一方面來說,二○○九年金融風暴席捲全球,各國預算赤字上修情有可原。然而,希臘上修的幅度超大,而且入歐後希臘年年上修,幅度都不小,種種跡象看在歐盟主計機關的歐盟統計局(Eurostat)眼裡,認定希臘政府在赤字和國債數字上「廣泛誤報」。在希臘,會計數字大幅修正是慣例,尤其是在選舉過後。二○○四年,選後變天,由右傾的新民主黨(New Democracy)執政,新政府指稱,甫下臺的執政黨泛希社運黨在位時胡搞數據。這也顯示了希臘申請入歐元區時提出的主計數字造假。當時入歐的條件是申請國必須符合「趨同準則」,例如年度赤字不得超過GDP的三%。到了二○○九年,泛希社運黨奪回政權,聲稱當年大幅修正的原因是新民主黨隱瞞了真正的支出。希臘政壇鬧得滿城風雨,全球不太想關心,但外界領悟到的問題本質在於,希臘的主計方式重伎倆而輕科學,金融情勢猶如垂掛在一顆急速洩氣的氦氣球下面。希臘宣布初步修正後兩天,信用評等首度遭調降,各機構緊接著也宣布降級。不久後,希臘完全無法在金融市場再借錢,想借只能忍受高利貸的欺壓。
希臘是小國,人口僅大約一千一百萬,以漂亮的小島海灘、大理石古蹟、古代哲學家聞名,世人並不重視它的經濟地位,認為它即使崩解,也不至於對全球金融產生巨浪。問題是,希臘是歐元區的會員國,這份特殊的地位足以掀起比國家大幾倍的狂濤。德法兩國的銀行是希臘最大的外國債主,在歐洲銀行體系已舉步維艱之際,希臘若突然倒債,可能進一步動搖歐洲金融。迅速明朗化的另一件事是,歐元本身的設計有幾個缺陷。例如,歐元會員國假如破產,被迫回歸國內原本幣制,情況會怎樣?創始人認真設想過嗎?似乎沒有。愛爾蘭和西班牙房市泡沫破滅後,也正面臨不少問題,迫使政府介入,搶救國內銀行。義大利和葡萄牙的財經狀況也不佳。如果希臘倒了,接著倒的是哪一國?歐洲領袖當年構思的「單一穩定貨幣」如今遭逢重大威脅,危機起始於希臘。
希臘的正式國名是希臘共和國(Hellenic Republic),當年歐洲籌備合體時,把希臘納入考量,主因是希臘在歐洲大陸的象徵意義重要。畢竟,歐洲之名Europe源於希臘神話美女歐羅巴。更何況,歐洲國家共同的傳統源於希臘,而希臘更是民主制度和西方文明的發祥地,沒有古希臘,哪來今天的歐洲?希臘在一九七○年代申請加入歐洲共同體,當時的法國總統季斯卡(Valery Giscard d’Estaing)是歐盟創始人之一,他相信希臘是「所有民主國家之母」,因此不宜將她屏除在外。可惜的是,日後希臘惹了大麻煩,似乎曝露了這種想法多麼不切實際。希臘債主有權揭開正統政權的表象,有權檢查希臘政府的五臟,所到之處發現幾乎遍地是毛病。希臘政壇根深柢固的一種傳統是,對特定團體釋放社福利益以換取選票,而最亟待援手的族群通常只有喝西北風的分。逃稅是一種全民運動,而稅捐人員竟然經常跟逃稅人串通。公務員是終身職,很多人並非資歷夠好。而是仗著姨媽或表哥認識市長或國會議員,裙帶關係導致公共行政效率嚴重低落。官僚體制不夠透明,外人無法理解其中的運作,執法也鬆散,使得政客明目張膽貪汙,也不用太擔心會被逮個正著。希臘的年金制度龐雜,財源不足。建築法規不受重視,導致違建多達一百萬戶。希臘的司法通常慢吞吞。公立中小學喊窮,希望子女進大學的家長只好掏腰包請家教。
這不是歐盟創始人當年憧憬的二十一世紀會員國。德國《明鏡週刊》(Der Spiegel)在二○一二年訪問法國前總統季斯卡時,季斯卡似乎後悔了。「我講一句坦白真心話好了,當初納入希臘是一項失策,」他表示,身旁受訪的人正是他的老搭檔,也是德國前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簡單說,那時希臘還跟不上腳步。希臘基本上是個東方國家。」談到這一類話題時,歐洲人用到「東方」一詞並沒有恭維的意思。換言之,希臘有別於水準較高的歐洲,是偏向於中東、比較落後的國家。接著,季斯卡對施密特說,「我記得你在一九八一年決議把希臘納入歐洲共同體之前,曾表達過疑慮。當年你的腦筋比我靈光。」
歐洲人對希臘的「歐洲性」具有兩極化的觀感,自從希臘獨立至今,這種觀感一直很鮮明。獨立戰爭期間,受過高等教育的歐洲人立志復興他們景仰的古希臘,以財物資助希臘叛軍,督促本國政府軍援希臘以爭取獨立成功。(因此,值得深思的不僅是「沒有希臘,豈有歐洲」,也應反問「沒有歐洲,豈有希臘」。)最後,英、法、俄支持獨立革命運動,保證貸款給初生的希臘國(後來被倒債)。英國浪漫派詩人紛紛以意識形態加油。一八二一年,也就是希臘革命戰開打的那年,雪萊寫下〈希臘〉(Hellas)一詩:
另一雅典將昂起,
如夕陽為天增色,
以盛世金碧,
遙照遠古聖哲。
若光輝無以為繼,
且留天地能授受之燦麗。
但反過來說,當時的歐洲人對希臘人通常也有恨鐵不成鋼之憾,認為現代希臘比不上前人的偉大,就連嚮往雅典復興的雪萊也對這份願景存疑。希臘革命期間,雪萊和友人崔隆尼(Edward John Trelauny)來到義大利一港口,為了認識希臘船員而搭上希臘商船,事後崔隆尼記錄過程,顯示兩人對希臘人觀感不佳。「他們三兩成群蹲在甲板上,嘶叫著,比手畫腳,抽菸,吃著東西,賭博,活像野蠻人,」崔隆尼寫道。他也記下,船長擔心生意受影響而不支持革命。
「雪萊,這符合你對希臘精神的憧憬嗎?」崔隆尼問。
「不符合!但這倒是很符合我對地獄的看法,」雪萊向崔隆尼表示。「我們走吧!這裡不見一絲古希臘氣魄。這些人無法重燃古希臘之火炬。」雪萊接著說,「我寧可守著我的希望和幻夢,不願它們再被無情的現實奚落嘲弄。」
長久以來,希臘人也飽受這種自我形象漲跌搖擺之苦。希臘獨立成功時,英國浪漫派詩人對希臘寄予厚望,對史詩般的歷史崇敬有加,但希臘農人在這方面的感受不比歐洲人強烈,因為農夫從未讀過柏拉圖或悲劇詩人尤瑞皮底斯(Euripides),而且不太崇尚啟蒙時代的理想。就歐洲人的想法中,啟蒙意識源於希臘。但如今希臘反倒比較奉行東正教的保守意識。新希臘國後來成功教育國民,讓國民對遠古懷抱無限驕傲,但灌輸這種思想也賦予國民歷史包袱。古人的成就流傳千古,拿現代的自己去相較,注定自尋苦惱,常常引來一股揮之不去的自卑,歷史壓力之沉重,世上少有其他民族能比。希臘人有句俗語最能傳達這份苦悶:「我們把光明獻給世界,自己獨守黑暗。」然而,希臘人也常自視甚高,仗勢著文明古國的背景,以上帝欽點的子民自居,高人一等。我反覆聽見希臘人如此貶損北方的歐洲國家:「我們過文化生活的時候,他們還住在山洞裡呢!」因此,希臘人常覺得,被帶出山洞、引向光明的歐洲人理應感激才對。希臘人有時拿這些觀念自我哄形象,副作用是讓國民更不滿國家屈從於債主的現勢。再怎麼說,虧欠希臘的是歐洲人。
山洞原始人不甘示弱,把希臘比擬為長了壞疽的手腳,公開探討截肢手術是否明智,是否應將希臘逐出歐元區。德國是歐洲最大的經濟體,也是希臘最大的債權國,特別猶豫該不該扶持希臘。德國遲疑的跡象一出,更加深市場的恐懼心理,認定希臘和歐元即將步上絕路。歐元區待援國家還有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賽普勒斯,但德國人最不屑的國家是希臘,原因不僅是希臘需求的金援是其他國家的總和,也因其他國家金融風暴的起源是政府為了救國內胡搞的銀行而被拖下水,希臘則是國內銀行原本運作良好,卻因政府本身的缺失而釀成浩劫。德國人比較不在乎銀行和消費者的失誤,而是苛責不知節制的政客和國民,並認定希臘政府怠忽職守,悖離歐盟成立宗旨。二○一二年二月,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與歐洲數國財長餐敘,談話內容後來由《金融時報》(Finacial Times)取得,顯示歐洲財長對蓋特納表達的感想是:「我們想給希臘一個教訓。希臘人真的很糟糕,竟敢騙我們。他們很爛,不知檢點,占盡了我們便宜。我們打算壓得他們站不起來。」蓋特納接著說,當時的態度是:「絕對要祭出重懲。」
最初紓困協議具有懲罰性質,換言之,也就是棒打債務國。如此才能稍稍緩和德國選民對於金援希臘的不安。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特意向選民強調這份協議的強硬性,同時向選民保證,希臘已受到適度譴責,而且會避免有恃無恐的道德風險。其他歐元國家也將「盡其所能避免道德風險」,梅克爾於首次紓困後如此告訴德國報紙《週日畫報》(Bild am Sonntag)。許多希臘人也盡了本分,盡量不要趁機撈錢。設想一下,假如一家公司的經營團隊宣布減薪裁員計畫,辦公室裡的氣氛會變得多麼低迷。在希臘,同樣的低迷氣氛籠罩著全國。為接受首次金援,希臘承諾大規模撙節,在國會表決撙節法案之前,希臘工會舉行全面罷工,國會大廈前聚集了大批抗議民眾。國會裡的許多議員在位時忙著散財灑福利,如今卻想收回,國會外的民眾豈能坐視?抗議者一度企圖硬闖國會大廈,場面混亂,鎮暴警察釋放催淚瓦斯,逼得身穿傳統革命游擊隊服飾的儀兵丟下崗位,棄守無名烈士紀念碑。附近有家銀行被暴民縱火,造成三名員工喪生,其中一名是孕婦。罷工示威,這還只是開端。接下來四年,全國各地發生的抗議示威超過兩萬次。
很多希臘抗議者明明知道,在希臘史上,內政被外國掌控是常態。例如在一八九三年,希臘最大出口商品醋栗在全球市場價格暴跌,國內面臨至今仍有的問題:稅收不足、軍事開銷沉重、公共行政揮霍無度,因此希臘在一八九三年倒債了。歐洲各債權國紛表不滿,德國更是氣炸了,呼籲國際接管希臘金融業,以確保希臘償清債務。為達此目的,各國幾年後在希臘成立國際金融委員會(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ommission),當時希臘剛和鄂圖曼帝國打完一場短暫的戰爭,吃了敗仗,國勢衰弱。委員會負責監督希臘金融,直到二次大戰為止,任務是徵收印花稅和菸草稅,建立海關稅制,收取火柴、菸紙、鹽等國營製造商的營收。在委員會干預下,改革有些成果,例如希臘能建立信貸信譽,因此能額外再貸款,但希臘人對外國干權感到深痛惡絕。
如今,希臘覺得國家前途再度落入債權監督國的掌握。不同於希臘人的看法,這些新的監督國家卻預測希臘前景看好。首次紓困方案規定的結構重整和減薪,勢必能修正景氣繁榮時期的不知節制,能快速提升經濟競爭力。根據三頭馬車的初步預測,改革措施在二○一二年將展現成果,希臘將再度成長,將能再向金融市場貸款,失業率最高不會超過一五%左右。預測指出,儘管希臘國債將增至險境,最終將能全數償還。當時有一份歐洲委員會報告指出,希臘必須「逆潮水而游」以符合上述目標,因為減支必須在經濟負成長期間進行。事後證明,這份報告太輕描淡寫了,三頭的預測也樂觀如癡人說夢話。很多經濟學者知道,在經濟蕭條期間縮減政府支出、降薪、增稅,很可能讓經濟更衰退。三頭嚴重低估了雪上加霜的程度。國際貨幣基金主管後來承認預估有誤。
對眾多希臘人而言,經濟衰退比預期來得嚴重,而且失業率激增,顯示首次紓困無法發生作用。因此在二○一一年秋,歐洲國家領袖和國際貨幣基金總裁在布魯塞爾深夜協商,敲定第二次紓困協議,這時希臘人已經嘖有煩言,不願再遵守另一份備忘錄。當時的總理是泛希社運黨的喬治.帕潘德里歐(George Papandreou),也是創黨人安卓亞斯.帕潘德里歐的兒子。他心生一計,希望藉公投為紓困協議增加法律效力。然而,公投的想法一宣布,歐洲各國領袖震怒,認為他們辛辛苦苦協商出的方案豈能任由希臘選民擺布。帕潘德里歐出生在明尼蘇達州,唸過安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仍保留一絲美國腔(被希臘人奚落是「小美國人」),而且因首度紓困失利而人氣跌進深谷。他禁不住國內外責難的聲浪,放棄公投的點子,被迫黯然下臺。曾任歐洲央行副總裁的帕巴德莫斯(Lucas Papademos)接著執政,領導臨時政府,執行單一任務:讓二度紓困案過關。希臘國會在冬夜裡表決通過重大縮減提案,以換取二度金援,當晚民眾聞訊,在雅典爆發激烈抗爭,罩頭青年在鬧區建築物縱火,全城宛如戰區。民主發祥地的民主如此運作,情何以堪。
二○一二年五月,希臘舉行國會改選。二度紓困案推出至今,人民首次有機會以選票表達立場。到這時候,明顯可見的是,政壇已陷入失序狀態,反金援政黨趁勢興起。希臘激烈左翼聯盟(Syriza)融合了幾個極左翼團體,誓言取消紓困協議,恢復社福支出,因此民氣暢旺。激左聯領袖聲稱,希臘已成德國新自由派政權的殖民地,誓言向德國索討二次大戰賠償金。希臘右翼選民不惜走極端,轉而支持金黎明黨(Golden Dawn)。金黎明黨擺明走新納粹路線,卻不承認自己是新納粹政黨,最初在雅典中下階級聚集的中區發跡,結夥在街頭鎖定黑皮膚移民,加以攻擊,藉此壯大聲勢。金黎明黨強調希臘民族優越感,誓言以國家利益優先,廣獲民眾支持。
五月國會選舉開票,激左聯小輸右傾的新民主黨,屈居第二,金黎明黨則順利進入國會殿堂。這次選舉中,沒有任何一黨的總票數足夠自組政府,因此六月再選一次。在二度選舉之前,希臘似乎陷入難以治理的亂局。激左聯黨魁年輕,不打領帶,曾是共產運動青年,選舉時揚言拒償希臘債務,全球唯恐激左聯勝選,金融市場因而大地震。把希臘趕出歐元區是不是上上策﹖德國政壇再次公開探討。「希退」(Grexit)成了常用詞。希臘民眾擔心提款機不久後將吐出沒價值的希臘幣,急著從銀行帳戶提款,擠兌現象嚴重,原本就不穩的信心更加動搖,創造不出適合經濟復甦的氣候,希臘的問題當然更形嚴重。
六月再選舉時,新民主黨針對希望留在歐元區的選民,以保險的選項自居,最後險勝。由於總票數最多的一黨能在國會再添幾席,新民主黨得以組成聯合政府,收編先前的仇敵泛希社運黨。新總理是薩馬拉斯(Antonis Samaras),碰巧也是安默斯特學院的校友,曾和帕潘德里歐同寢室。新總理向歐洲各國領袖保證,他將遵守二度金援協定,一反先前批判首次金援的反對黨立場。德國總理梅克爾擔心萬一薩馬拉斯垮臺,繼任人選更糟,因此禁止國內官員批評他,轉為稱讚希臘的改革魄力。
希臘獲救了,但到這階段,被千刀萬剮的希臘已奄奄一息。希臘有位旅館老闆曾以一語向我道盡國家困境:「希臘先是自己惹麻煩,然後碰到三巨頭帶來的麻煩。」我覺得這話能反映希臘危機。把希臘逼向財經懸崖的是希臘自己,但歐洲債權國和國際貨幣基金也鑄下大錯。持平而論,急著化解危機的債權國也面臨特殊的嚴峻考驗。最初歐盟面對希臘危機莫衷一是,後來下的猛藥太重,財政撙節措施弄巧成拙,結果害希臘陷得更深。儘管加稅減支的用意是改革希臘金融,國債的比重卻持續攀升。希臘原本從歐元區撈到不少好處,如今卻因身為歐元區會員國,刺激經濟成長的選項嚴重受限。由於無法掌控貨幣政策,也無法藉貶值來提升出口競爭力,希臘唯一的希望是減薪,讓希臘產品變便宜,藉此強化出口。無奈的是,減薪的副作用是殘害國內消費,出口額雖然小增,卻無法抵銷消費減少的副作用。在此同時,希臘仍達不到金援備忘錄明訂的幾項改革措施,例如督促希臘廢除只造福強勢利益團體的官僚規則,讓經濟更開放,也促進競爭力。
到了希臘慶祝獨立紀念日的時候,經濟已在六年間萎縮二五%。不久後,在觀光業幫助下,微幅成長重現,但重振經濟所需的持續穩健成長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失業率始終在二八%的高峰居高不下。很多民眾認為留在國內沒有未來,於是出國求職潮湧現。希臘報紙刊載學童上課餓昏的新聞。雅典市區和郊區出現成排的倒閉商店。教堂和市府提供糧援,饑民大排長龍,隊伍環繞整個街廓。冬天來了,雅典上空飄著有害健康的煙流,因為暖氣用油太貴,市民寧可燒柴取暖。希臘國債是危機的源頭,這時候國債大約是GDP的一.七六倍,接近巔峰。打從紓困案一開始,只有一小部分的金援貸款直接供應政府運作所需,絕大多數的錢用來應付舊債的本息,幫助銀行重組資產。金援希臘救到了歐元,但所有數據顯示,希臘快支撐不住了。
為求生存,保守派領導的政府盡量報喜不報憂。希臘除了微幅經濟成長外,也取得小小的「基本財政盈餘」(primary surplus),意思是國家收入能應付本身的支出,但不包括債息在內。巨額赤字拖垮希臘,現在這一點改善算是成果亮麗了。希臘也在債券市場客串,這是首次金援之後第一次面世,表現相對而言出色。可惜,債券登場和基本財政盈餘的概念太抽象,鼓舞希臘民心的作用有限。政府就算大幅改善了預算,但希臘家庭經濟卻變得更糟。
二○一五年初,希臘選民厭煩了經濟低潮和紓困備忘錄的宰制,把幾年前啟動的新政局徹底洗牌。一場霹靂大選過後,激左聯取得決定性的勝利—至少以小黨林立的希臘危機期國會席位而言。新任總理是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一上臺立刻誓言不再屈從於三頭馬車,並拋棄金援備忘錄,中止「撙節災難」。他領軍的政府表示,將與債主另立較有利的協議,一方面讓希臘續留歐元區,另一方面能減輕債務負擔,讓希臘有金融餘裕,足以照顧社會福利。
廣大希臘民眾將新政府的宣示視為重新伸張主權,但歐元區領袖則解讀為頑強抵抗、肆無忌憚。德國尤其不滿,德國執政黨要求希臘遵守現行紓困協議,質疑希臘政府怎能出爾反爾還敢伸手要錢或要求舒緩債務,畢竟希臘此舉影響到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納稅人的荷包。雙方談不攏,相持不下,烏雲再次籠罩希臘與歐元區的未來,「希退」又成為口頭禪。儘管激左聯面對三頭展現魄力,廣受希臘民眾擁戴,憂心忡忡的存款人則開始跑銀行,把歐元轉存國外,令人擔心擠兌風潮再起。在國家稅收方面,由於許多希臘納稅人預期激左聯能減輕人民負擔,索性不再繳稅,竟讓才執政幾週的新政府急著為了償債和避免倒債,忙得焦頭爛額。
激左聯和前任執政黨都遇到相同難題,金錢和時間都不夠用,不得不向債主低頭。希臘新政府為了換取有限的讓步,同意延長紓困案幾個月。而人人喊打的備忘錄也跟著延宕,只不過新政府的這份協議寫得模棱兩可,好讓希臘當權者事後得以抵賴。協議定案後,雙方多了一點時間,可盡量協商出一套規模更大的方案—基本上算是第三度紓困。這次金援的條件協商起來煙硝味濃。無論結果如何(按:已在二○一五年八月中旬通過),勢必對希臘的政經局勢再掀波濤,讓脆弱的希臘經濟再受打擊,還得慌忙調頭寸。第一次紓困至今五年了,希臘在歐元區的地位似乎不變,同樣是岌岌可危。
話雖這麼說,激左聯勝選後,許多希臘民眾似乎立刻拋開煩惱,歡欣鼓舞,感覺像重獲民族自主權,即使這份感覺再短暫再虛幻,也值得慶祝。「希臘不再是一直聽話的可憐夥伴,不會再乖乖做功課了,」齊普拉斯上臺不久後在國會演說表示。「希臘有聲音。她自己的聲音。」廣大希臘民眾一時之間支持認同。終於,他們覺得,國家總算掙脫債主的鉗制,重獲獨立自主。
我首度以記者身分前往希臘是在二○一一年底,當時想為《華爾街日報》寫一篇有關數百名假盲人詐領補助金的報導,而踏上了位於愛奧尼亞海(Ionian)的札金索斯島(Zakynthos)。翌年,我也盡量抽空到希臘採訪多次。我對希臘既熟悉又陌生,經常被它搞得一頭霧水。本書裡的報導展現了我所看到的的政治殘局,那種長久以來重度畸形的政治秩序。本書也展望革新的跡象,預想將來陰雨朦朧的坎坷路。英文書名The Full Catastrophe(全面鉅災)的靈感來自電影《希臘左巴》(Zorba the Greek)主角左巴(Alexis Zorba)的臺詞。這部一九六四年的電影改編自卡山札基(Nikos Kazantzakis)的小說。主人翁是活潑到出名的左巴,後來紅到被公認是最典型的希臘人,幾乎到了浮濫的程度,很多海外觀光客來到希臘,竟想從當地人之中找到左巴的影子。電影裡的左巴面對災禍,一方面感到哀傷,另一方面也視災禍為值得擁抱的轉機。歷史綿長的希臘人有數不清的災禍可喟嘆,但這次債務危機和隨之而來的經濟蕭條,在民眾心目中,其嚴重性讓希臘史上其他災難望塵莫及。在哀怨聲中,許多希臘人承認,這次危機的一大好處是讓國民醜陋面無所遁形,並凸顯對深度政治改革的需求。然而,希臘能否搖身一變,能否在促進社會公義、經濟自足的路上不至於跌得粉身碎骨,仍有待觀察。
【推薦序】
債務危機—誰之過?
張翠容
閱謮安傑羅士這一本述說歐債的《希臘悲劇:政治與民主治理下的債務殘局》後,心裡百感交集,究竟是物先腐,而後蟲生;又或是蟲先蛀,才令物腐爛?我們不自覺地陷入雞與雞蛋的陷阱了。希臘債務問題千絲萬縷,卻牽動著歐盟的命運,對全球經濟亦不無深遠影響,不過,最受打擊的還是當地的老百姓,大家都在問:哪裡出了錯?
雖然希臘債務危機已出現了好幾年,但自二○一五年希臘大選「激烈左翼聯盟」上臺,除了經濟危機之外,又再發生了政治危機,政壇動盪不安。之後又遇到中東難民湧現波及歐洲,而希臘首當其衝,對於國際媒體來說,新問題永遠比舊問題更吸引目光。
無論如何,希臘是歐債的縮影,歐債又是過去資本全球化所彰顯的問題縮影。當然,希臘本身也有其獨特的問題。這次安傑羅士親赴希臘現場,獲知了許多我們在媒體上沒有看到的事件故事,可讓讀者從微觀瞭解更多問題的來龍去脈,正所謂見微知著,這是可貴之處。最後,安傑羅士還為我們補充了難民這個因素如何影響希臘的政經發展,書中內容讓讀者可說是目不暇給。
在此,我想提出兩個疑問:一、沒有了希臘,難道歐洲債務危機便不會發生嗎?二、希臘本身的問題一直存在,為何債務危機會到二○○九年才爆發出來?而且不僅希臘,南歐其他地方也成為重災區。數年前我也有到希臘進行債務危機相關的採訪工作,或許,我在此可以對此做一些補充。
希臘在歷史上面臨太多外來強權干預,也在希臘身上留下不少歷史傷口,因此希臘人總是帶著一種受害人的情結,這種情結多少反映在這次的債務危機中,也有可能因此讓希臘人缺乏自我反省能力。但另一方面,外界對希臘的誤解又有多少?
在希臘,我訪問當地人,想知道他們是否如外界所說,是個高福利國家,由於好逸惡勞,全民熱中逃稅、四十歲就退休?被我這麼一問,他們都瞪大眼睛望著我。如果是學者,他們會搬出很多統計數字去逐一反駁外界的謬誤。所謂四十歲退休真是很大的誤會。希臘人反問,誰可能四十歲就退休呀?他們的退休年齡都在六十五歲,現在政府還要延長至六十七歲。如果公務員要提早退休,也必須服務滿三十五年才會獲得批准。只有軍中的特種部隊,才有可能早於五十歲前退休,但那是特別的個案,不能混為一談。
至於希臘人是否好逸惡勞這個問題,之前在飛機上恰巧坐在我身旁的,是雅典大學社科院研究員蘇儀(Zoi),她告訴我,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報告指出,希臘人每年工作二○一七小時,平均工時比德國要多四○%,即使撇開自雇人士的部分,希臘工時仍較德國長一○%。
至於福利,調查統計也顯示希臘的社會福利不及德國,甚至不及西班牙。事實上,希臘老百姓都希望多做多得,以應付高昂的生活指數,失業是個夢魘,誰想當長期失業者?每個國家都有懶人,希臘當然也有懶人,難道這就是債務積纏的原因之一嗎?
談到逃稅問題,希臘人就更憤怒了。因為逃稅的都是有錢人,愈富有愈想逃稅,老百姓則要負擔高稅率。有次我與一群希臘大學生喝咖啡時,其中一人拿著菜單對我說:「看!我們這裡的消費稅是二三%,幾乎是全歐洲之冠,我們老百姓的生活多難過啊!」沒錯,老百姓雖然也懂得逃稅,但有錢人逃稅則有更大的影響,這種現象到處皆是,最近「巴拿馬文件」也揭露了全球的富豪,不論是在富國或窮國都在玩這種逃稅的金錢遊戲。
在一次希臘反撙節的大遊行中,我遇上一位獨居老人,他在政府部門服務了一輩子,退休後每月能拿到八百歐元的退休金,現在一減就減到五百歐元,幾乎無法維持基本的生活。他問,為什麼外界總有這樣的誤會,以為退休者死後的退休金可由親友繼承?可能因為之前有官員收賄,讓這樣的事發生,但這是少數而不是普遍現象。老人家也不覺得希臘的福利比西歐好,甚至還不如呢!希臘人認為,有人想找代罪羔羊,卻把責任推到希臘身上,其實只不過是想轉移歐債真正原因。
希臘導演凱特琳娜.凱特蒂(Katerina Kitidi)、哈茨斯特凡諾(Aris Chatzistefanou)拍了一系列有關希臘債務的紀錄片《解放債務》(Debtocracy)。該影片有一情節,講述希臘接受德國金錢援助後,再用來購買德國的武器。而削減赤字則迫使希臘政府私有化國有資產以換取現金,德國及其他資本由此可平價收購希臘國有資產。片中盡是嘲諷希臘政客怎樣成為歐盟的買辦,出賣國家,賤售國產,而德國則是最大的受益者。
事實上,希臘在德國等歐洲強鄰的壓迫下,逐步私有化、出售國有資產,其中包括賣掉國有機場、公路、國營企業、銀行、房地產和樂透彩執照、兩個最大港口和一家自來水公司,甚至有些美麗的小島,都被政府拍賣。此舉幾乎是把整個國家出售,來滿足國際債權人的要求。
當然,希臘政府也應負責,他們未能向富有的希臘人追收稅款,而是向老百姓開刀,削減養老金。在民生方面也大幅提高稅率,例如連家用電費都調漲超過二○%,令原本生活已吃緊的老百姓雪上加霜。此外,最令人難堪的還包括,一般勞工遭到不合理的減薪,歐盟要求希臘政府把二十五歲以下勞工的最低工資調降三二%,二十五歲以上的勞工則調降二二
%。此外,勞動工時也增加,面對高昂的徵稅,人們很快便失去了消費能力,到頭來裁員之聲四起,派遣勞工首當其衝。
如此看來,僅靠撙節無助於清除銀行業界的毒瘤。這次歐債危機中,有不少是金融犯罪行為,而最大的「騙局」,當屬二○○○年美國高盛投資銀行,為希臘設了一盤局,巧妙掩飾希臘一筆高達十億歐元的公共債務真相,好讓希臘得以順利進入歐元區,以享有歐元區低廉的借貸利率,繼續借貸。
據媒體曝光的數據顯示,當年高盛利用換匯交易(swap transaction)和信用違約交換(CDS)兩項金融工具,為希臘埋下主權債務炸彈,同時也加速了歐洲的經濟危機,而他們則坐收漁人之利,單是交易佣金,三億歐元已穩穩進入高盛口袋。高盛利用所謂「金融創新」手段,讓希臘政府的債務先用美元等其他貨幣發行,之後於特定時間換回歐元債務,債務到期後,高盛再將其換回美元。據報導,多年以來,當中交易金額高達百億歐元之多。為了進一步掩飾,高盛提供希臘優惠借貸匯率,好讓希臘獲得更多歐元,並享有長達十年甚至更長的還貸期限,以迴避算入歐元區所需要統計的公共負債率。高盛這種障眼法,只會令希臘不得不製造更多的貨幣換匯交易,使希臘深陷壞帳漩渦而無法自拔。
為了維持合格的負債率水準,高盛再為希臘尋找十五家銀行達成貨幣換匯協議,其中包括德國的銀行,而且還是主要債權人之一。高盛明顯要把風險轉嫁給德國銀行業。為什麼選擇德國銀行呢?主要是因為德國是歐元區最大經濟體,此做法可將德國鎖在希臘的債務鏈內,如果德國政府袖手旁觀任由希臘違約,那麼德國銀行業也一併遭殃。
當帕潘德里歐在二○○九年上任為總理時,發現這一盤殘局已無法再騙下去,況且銀行也因全球金融危機而身陷泥淖,反而需要政府動用龐大資金救助,就在這種情況下希臘債務危機爆發了,並同時暴露了希債危機在歐洲不是單一案例。而高盛介入歐元區其他國家金融事務之深,超乎我們所能想像。除了希臘之外,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義大利等「歐豬五國」,也相繼爆出主權債務危機。
事實上,歐洲金融機構當中有不少高盛人。為希臘量身定做出一套金融工具,以掩飾希臘龐大的債務者,就是當年的高盛副總裁德拉吉(Mario Draghi),他現在竟是歐洲央行總裁。而前任義大利總理蒙蒂(Mario Monti),在二○○五年也曾任高盛的國際顧問。有美國媒體直接指出,高盛就是歐債危機的罪魁禍首,他們透過琳瑯滿目的金融商品,讓世界充滿債務,現在危機爆發,他們不僅不需負責,也沒有受到懲治,反而被挑選出來處理歐債問題。如今出面為歐債危機提供解決方案的歐洲領袖,也多是高盛出身。這不是很荒謬嗎?
高盛一手種下歐債的種子,他們對歐債自然最清楚不過。但另一方面,當歐洲也被歐債拖垮時,高盛該如何反應?高盛集團總裁兼營運長柯恩(Gary Cohn)事後向投資者表示,鑒於歐洲銀行為從財務危機解套,可能被迫出售至少一萬億美元的資產。因此高盛很可能從中獲益,他們也許會掌握有利位置,去擔任這些資產銷售的中間人。因此,面對歐洲這趟渾水,他不僅不擔心,反而還樂觀地認為,歐洲潛在的經濟危機能夠為高盛帶來營利良機。這種轉化經濟危機為生財良機的手法,高盛可是玩得出神入化,也難怪坊間對高盛抱持陰謀論的想法。人們不禁要問:高盛究竟是投資銀行,還是全球政經大戲的製作人?
有批評陰謀論者稱,高盛可能只是一個有著資本嗜血本質的金融機構,他們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是不擇手段、唯利是圖、整死對手的「企業行為」,而不是政治行為。可是,高盛這間美國投資銀行如此精明計算,會是純粹的商業行為嗎?若不是單純商業行為,難道真如外界所說的陰謀嗎?無論如何,高盛的影響力無遠弗屆,它除了擁有全球第一線政經關係,更儼如美國政府重大政策的代言人或執行者。
希臘無疑存在著政治貪腐,而習以為常的逃稅行為也的確成了社會沉重的負擔,但希臘仍有在內部進行改革的機會。試想,一個人若沒錢可借,便也不能繼續毫無節制的揮霍度日,必須自我調整了。只不過,有人卻掩飾希臘問題,並將這個問題包裝成金融產品並拚命吹捧,接著更在歐元區內如細菌般,將債務問題散播出去,另外再加上大到不能倒的銀行做為劫持者,歐債便可能惡化到威脅歐洲的整合,猶如日本恐怖片中的貞子,不時出來嚇你一跳!
說到底這關乎一九八○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帶來的資本主義金融化、金融資本全球化與去監管化的問題。對金融產業來說,有人借錢才會有人賺錢,大家都被鼓勵不斷借貸,世界遂踏入一個大債時代。金融全球化製造了信貸泡沫和資產泡沫,這才是歐債問題核心,也是全球金融危機原因所在。
試想,若不是希臘過去太過輕易借貸,希臘債務也不會如脫韁之馬。若不是因為資本主義過度金融化,銀行也不會大到不能倒,還要國家去拯救,加深了主權債務危機。若不是金融資本去監管化,得以在全球化過程中全速前進,跨越國境,不擇手段追逐利潤最大化,金融罪行便不會如此肆無忌憚。面對這樣無邊無際的金融罪行,被捲入金融全球化的小國,可能已經無法控制自己的命運了。媒體成功地把我們的視線從金融詐欺轉移開去了,一切都是歐豬五國自食其果。就好像我們一味指責那些吸毒者,卻對販毒者視若無睹,無法道出兩者如何互為因果,這正是國際社會需要回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