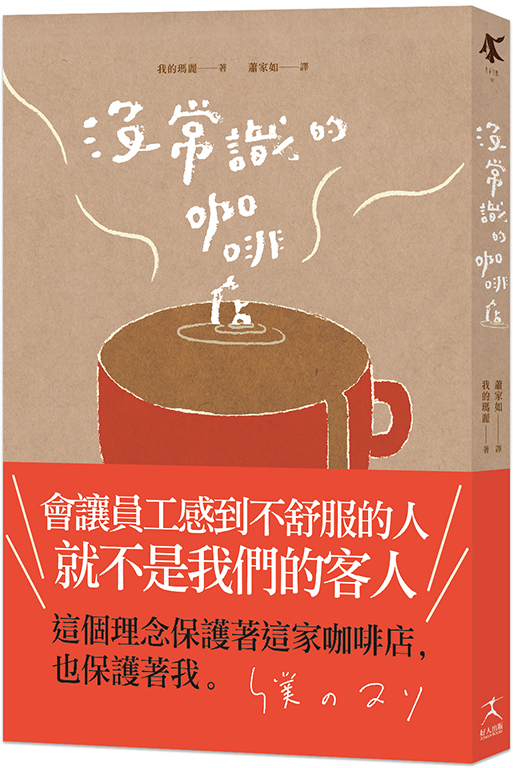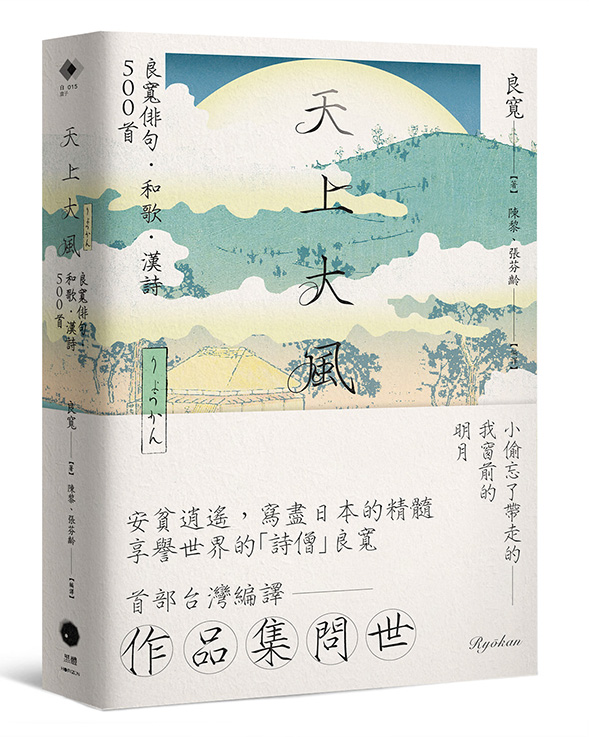◇權威日本文學教授暨資深譯者 林水福翻譯、審定、導讀、年表製作
◇資深日文系教授翻譯、篇章解析
◇國際芥川龍之介學會台灣大會•總會長宮坂覺撰寫專文推薦
芥川龍之介唯一一次出國,就是前往中國,《芥川龍之介短篇選粹•輯四》便收錄了他最重要的3篇遊記,分別是上海、江南及長江的見聞錄;遊記一度被認為對當時的中國充滿偏見,裡頭提到的淨是落後、不堪入目也令人無法忍受的中國風景。然而研究芥川的中日學者卻漸漸對這些遊記有了更現代、不同以往的觀點,除了芥川筆下的中國,讀者更能從譯者的解析中看見文本研究的變化與嶄新詮釋。
芥川龍之介在人生的短短三十五年間留下兩百餘篇文章,全為短篇,無論是幾十字的語錄、隨筆、評論,到幾百字的散文、小說,都可見作者忠實反應自身生活、交遊及對社會的思考與質疑。
以作品題材分,芥川的作品大致可分為:取材自日本古典文學的「王朝作品」、取材自江戶文學的「江戶作品」、取材自天主教聖人傳等的「切支丹作品」,以及以開化維新的明治時期為背景的「開化作品」——芥川晚年受基督教的影響很深,不論是他的隨筆亦或作品當中,都透露出濃厚的基督教思想。
在日本近代文壇,芥川與夏目漱石、森鷗外兩位文豪鼎足而立,為日本近代文學的三大家,短篇當中對於文字運用之自如,如今看來仍令人嘆服。
《芥川龍之介短篇選粹》邀集國內長期推廣日文教學與翻譯、同時也是國際知名芥川龍之介研究學者之日文系教授、副教授,連袂挑選出芥川龍之介在其創作生涯裡的重要作品,並將之譯為中文,許多對認識芥川作品及其人來說是不可或缺的,為國內目前集專業與可信度於一身的全新〔完整、精選〕譯本,且由譯者於每篇末加上簡要的作品解析,無論是專業學習或業餘欣賞,皆提供了國內讀者第一次更深入、也容易了解這位偉大作家作品的途徑。
芥川龍之介
原姓名新原龍之助,1892年(明治廿五年)生於東京。父親新原敏三在京橋以販賣牛奶為生。他出生7個月後母親即患上精神病,他被送到母親的娘家撫養,後來過繼為舅舅的養子,遂改姓芥川。
芥川一家雅好文學與戲劇,龍之介受此薰陶,養成深厚之文藝底蘊。11歲時就與同學發行手抄雜誌,並自己寫作、編輯,甚至自繪插圖。1913年他進入東京帝國大學英國文學系,期間開始寫作。畢業後以英文教學和報紙編輯維生。早在1912年廿二歲時,他已完成了處女作〈老年〉,兩年後又發表了短篇小說〈羅生門〉,但並未受到重視。
1916年芥川畢業,成績位列同屆二十人中之第二名。他在《新思潮》雜誌發表短篇小說〈鼻子〉,夏目漱石讀到後非常讚賞,對他多方關懷。這段時間他也開始創作俳句。1918年發表了〈地獄變》,講述了一個日本戰國時期的殘酷故事,通過畫師,畫師女兒等人的遭遇,反映了純粹的藝術觀。
1921年芥川龍之介作為大阪每日新聞報社的記者前往中國四個月,7月返抵日本,之後寫成《支那遊記》一書。這次任務非常繁重。在壓力和自身的壓抑下,他染上多種疾病,一生為胃腸病、痔瘡、神經衰弱、失眠症所苦。回到日本後,1922年他發表了〈竹林中〉,整個作品瀰漫著壓抑、彷徨,不定向的氣氛,反應了作者本人的迷茫。自此以後,由於病情惡化,芥川龍之介常出現幻覺,當時的社會形勢也右傾,言論自由受到從政府到普羅大眾的打壓。這使得他的作品更加壓抑,如〈河童〉。
1927年(昭和二年)芥川龍之介繼續寫作隨想集《侏儒的話》,作品短小精悍,每段只有一兩句,但意味深長。後二姐臥軌自殺,為其債務奔走導致身心俱疲。7月24日因「漠然的不安」仰藥自殺身亡,得年卅五。
管美燕
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留學生。日本國立東北大學日本文學碩士,輔仁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職臺北城市大學應用外語系系主任兼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著有《芥川龍之介の研究》、《芥川龍之介文學中的中國城市書寫》等。
徐雪蓉
政大東語系日文組畢業。輔大日研所碩士,比較文學博士班肄業。曾任教輔大日文系十年。編有《日語諺語・慣用句活用辭典》,譯有《勸學》、《遠野物語・拾遺》《日本的森林哲學——宗教與文化》等。
☆選輯策劃、召集人:林水福
日本國立東北大學文學博士。曾任輔仁大學外語學院院長、日本國立東北大學客座研究員、日本梅光女學院大學副教授、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理事長、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理事長、台灣文學協會理事長、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副校長、外語學院院長。
中、日文著作、譯作等身,研究範疇以日本文學與日本文學翻譯為主,並將觸角延伸到台灣文學研究及散文創作。
一、海上
到了終於要從東京出發 的那一天,長野草風氏 來找我,據長野說,他也打算在半個月之後到支那旅行。當時長野氏很親切地教我解暈船的妙方。但其實從門司港搭船,不到兩個晝夜就可以抵達上海,只不過才兩個晝夜的航程還需要帶解暈船藥,可見長野氏真的很膽小――當時這麼想的我,即使在三月二十一日 下午登上筑後號的舷梯時,眺望著因風雨浪大的港口,對於長野草風畫伯懼海一事不免再次感到同情。
然而,彷彿就像是輕蔑故人 而受到懲罰似的,當船航行到玄海 沒多久,大海就開始波濤洶湧了起來。我與同一船艙的馬衫君 一起到上甲板,才剛在藤椅上坐下,打在船身的浪花頓時從頭上落了下來。大海看去一片白色浪花,海浪打得船底轟隆隆地作響。此時對面不知何方的島嶼,朦朧地浮現於海上,其實那正是九州本土。不過,早已習慣搭船的馬衫君氣定神閒地抽著菸草,一點也未顯露懼色。我豎起了外套的衣領,兩手插在口袋,嘴裡不時地含著仁丹――對於長野草風氏提議要準備暈船藥的明智之舉感到十分敬佩。
沒多久,我身旁的馬衫君不知是去了吧台還是哪兒,不見人影,只留我悠然地繼續坐在藤椅上。在別人的眼裡我看起來或許很悠哉,然而我的腦海中可是極度不安。因為只要稍微動一下,我立刻就會感到暈眩。而且我覺得自己的胃也不斷地翻攪。當時在我面前有一位水手一直在甲板上來回走來走去(後來得知他其實也正為暈船所苦),那不斷穿梭的身影,也令我感到不舒服。眼前一艘拖網漁船冒著一縷黑煙在浪裡載沉載浮眼看就要淹沒。究竟為何一定要頂著這樣的大浪前進呢?看著那艘船,當時的我也感到憤恨不平。
為了逃離現在的痛苦,我開始努力地想一些愉快的事,小孩、花草、渦福的茶碗 、日本阿爾卑斯山 、名妓初代 ――之後還想了些什麼我也記不得了。不,還有,我想起來了,聽說華格納 年輕時也曾在航向英吉利的旅程中遭遇到暴風雨,據說當時的經驗對其後來撰寫〈漂泊的荷蘭人〉 有很大的助益。我也想了很多像那樣的事情,但感到頭愈來愈昏,愈來愈想吐,最後甚至覺得管它什麼華格納,統統被狗吃掉算了。
大約經過了十分鐘左右,我躺在船艙裡的床上,耳邊傳來餐桌上的盤子、刀子掉在地板上的聲音,當時我正處心積慮地克制胃裡的東西不要翻攪出來。這種時候我之所以還有這樣的勇氣,那是因為擔心暈船的該不會只有我一個人吧?!虛榮心這種東西,在這樣的時候,令人意外地代替了武士道發揮了功效。
隔天清晨,據說整個一等艙內的乘客全都暈了船,除了一位美籍乘客之外沒有半個人去餐廳。而且聽說那位不同於凡人的美國人,在用完餐之後還獨自留在船上的大廳敲著打字機。我聽到那件事之後心情突然開朗了許多,同時覺得那個美國人好像是怪物一樣,遇到那樣的暴風雨依然能夠泰然自若,簡直就是常人所不能及的絕技。如果那個美國人去檢查身體,說不定會發現他的牙齒長了三十九顆、或者是長了一條小尾巴什麼的――我依然與馬衫君一起坐在甲板的藤椅上,任憑自己天馬行空的幻想著。昨日大海的驚濤駭浪彷彿已經忘得一乾二淨似的,青翠蒼綠的濟州島的影子,橫臥在湛藍平靜海面的右舷方向。
二、第一瞥(上)
一走到碼頭外面,幾十個車夫一擁而上地把我們一行人團團圍住。我們包括了報社的村田君 、友助君 、國際通信社的瓊斯君 與我四個人。原本車夫這個名詞帶給日本人的印象決不是邋遢骯髒的,相反的,他們精力旺盛的一面甚至讓人有江戶風的感覺。然而,說到支那的車夫,那種不潔感真是一點也不誇張,而且觸目所及的每個人長相都很奇特。加上他們從四面八方伸長脖子大聲地叫喊,著實令剛上岸的日本婦女感到有些害怕。就連我被他們其中一人拉住外套的袖子時,也不由得躲到身材高大的瓊斯君的背後。
我們好不容易才突破了這些車夫的包圍搭上了馬車。但是,馬車才一起動,馬兒就橫衝直撞地撞上了街角的紅磚圍牆,年輕的支那車夫很生氣地用鞭子抽打馬兒,馬兒用鼻子頂著紅磚圍牆發瘋似的把後腿翹得很高。馬車眼看就要翻覆,大街上立刻聚集了許多看熱鬧的人;在上海如果沒有抱著必死的決心千萬不要輕易地搭乘馬車。
沒多久,馬車重新出發來到架有鐵橋的河邊。河裡聚集了許多支那的舢舨船,多到幾乎都看不到河水了。河岸邊好幾輛綠色的電車快速地行駛著。一眼望去全都是三層樓或四層樓高的建築物。在鋪設柏油的街道上,西洋人和支那人行色匆匆地穿梭著。然而,那些來自世界各國的群眾們在綁著紅色頭巾的印度人警察的指揮之下都先禮讓馬車通行。不論我怎麼偏袒,這麼井然有序的交通狀況,絕非東京、大阪等日本的都會所能及的。原本對車夫和馬車的勇猛感到些許恐懼的我,在看到這樣令人振奮的街景之後心情也漸漸好了起來。
沒多久,馬車停在從前金玉均 被暗殺的一家叫做東亞洋行 的飯店前面。第一個下車的村田君拿了幾文錢給馬車夫,不過馬車夫好像覺得不夠不肯把手收回去,嘴裡還喋喋不休不斷地嘟噥著。但村田君當作沒看到、頭也不回地逕自往玄關的方向走去。瓊斯和友助兩人對車夫的滔滔不絕好像也一點都不以為意。我對這個支那人感到有點憐憫,但又想到這種事在上海大概已經司空見慣了,於是就趕緊跟著他們一起走了進去。等我回頭再看時,車夫已經好像沒事了似的悠哉地坐在駕駛座上。我不由得想,既然如此剛剛又何必那樣吵吵鬧鬧?!
我們立刻被帶到一間光線昏暗、裝潢華麗但有點俗氣的會客室。我心裡想,這也難怪,即使不是金玉均也難保子彈什麼時候會從窗外打進來――就在我心裡暗自這麼想時,穿著西裝、外表精悍的飯店主人踩著拖鞋急急忙忙地走了進來。據村田君說,安排我投宿在這家飯店是《大阪每日新聞報》的澤村君的提議。然而,不知道是不是這位精明能幹的老闆覺得,如果讓芥川龍之介住在這裡,萬一被暗殺了也得不到什麼好處,就說除了玄關前面的房間之外沒有空房了。去到那間房間一看,不知為何有兩張床,牆壁有煤燻的痕跡,窗簾老舊,椅子則是沒有半張令人滿意的――總之,那是一間除了金玉均的幽靈、其他人都無法安住的房間。於是我不得已只好辜負澤村君的盛情厚意,在與另外三位討論之後,決定改投宿到離這不遠的萬歲館。
三、第一瞥(中)
那一晚,我與瓊斯君一起去了一家叫做牧羊人 的餐廳吃飯。這家餐廳不論牆壁、餐桌都令人感到愉快。雖然服務生全都是支那人,但是鄰近幾桌的客人都沒有看到半個黃面孔的。就連菜餚也比郵船公司船 上的菜要再好上三成左右。而且,能夾雜著一些yes或no的英文與瓊斯君聊天,多少也讓我感到愉快。瓊斯君一邊悠哉地吃著用南京米 做的curry ,一邊聊著上次分開之後的種種。其中,瓊斯君聊到了一件事,某天晚上,瓊斯君――加個君總覺得不像是朋友,他是英國人,曾經在日本住過五年,在那五年當中(雖然曾經吵過一次架),我跟他感情一直很好,曾一起去歌舞伎座買站票欣賞表演,也曾一起去鐮倉的海邊游泳,還曾大半夜跑到上野的酒店喝得杯盤狼藉。那次他穿著久米正雄 唯一一件上等的日式摺裙,突然噗通地就跳入了水池裡。稱呼這樣交情的他為君,或許比任何人都對不起他。還有一件事要說清楚,就是我跟他之所以交情很好,那是因為他的日文非常好,而不是因為我的英文很好――某天晚上,瓊斯去一家酒吧喝酒,當時店裡只有一名日籍的女服務生坐在椅子上發呆。他平常就常掛在嘴邊說支那是他閒暇消磨時光之地,而日本才是他的狂熱愛慕之所。尤其聽說當時他剛搬到上海,想必更加懷念日本。他立刻用日語跟那位女服務生攀談。「什麼時候來上海的?」「昨天剛來。」「那你不想回日本嗎?」那位女服務生被他這麼一問,立刻就眼眶泛淚哽咽地說「當然很想回去」。瓊斯說著英文的同時還一直用日文重複這句「當然很想回去」,然後就自己笑著說:「我在聽到她這麼說時心情也變得很Awfully sentimental 。」我們吃完晚餐之後就在繁華的四馬路上散步,然後再到酒吧Parijan去看跳舞。
那裡的舞池相當地寬敞,燈光配合著管弦樂音忽而變藍忽而變紅地,與淺草十分相似。然而說到那個管弦樂演奏技巧的優劣,淺草終究沒得比,雖說在上海,但不愧是西洋人開設的舞池。
我們坐在角落的桌子,一邊品嚐著茴香甜酒 ,一邊欣賞穿著紅色服飾的菲律賓少女與西裝筆挺的美籍青年翩然起舞。不知是惠特曼 還是誰的短詩裡曾寫道,年輕的男女固然賞心悅目,但上了年紀的男女又別有一番動人之處。就在一對肥胖的英國籍老夫婦跳到我的面前時,我不禁想起了這首詩。但是,當我跟瓊斯提到此事時,他對於我的感嘆只是一笑置之,據他說,他只要看到老夫婦的舞蹈,不論他們是胖是瘦,都會忍不住想笑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