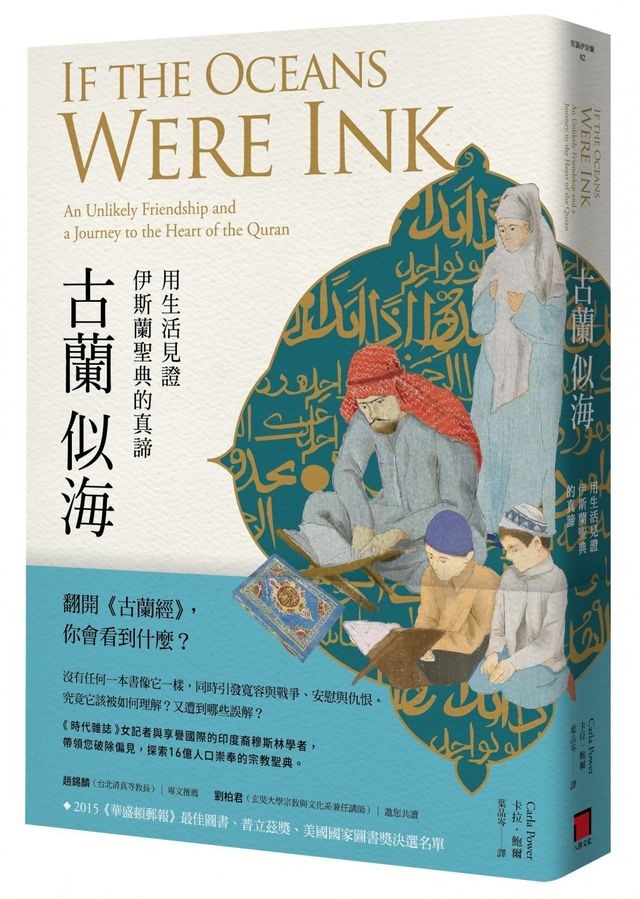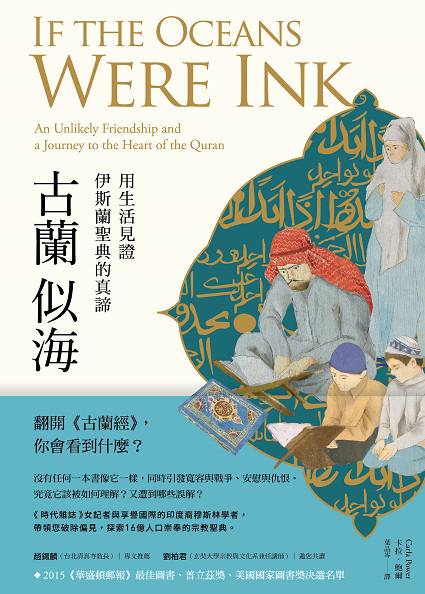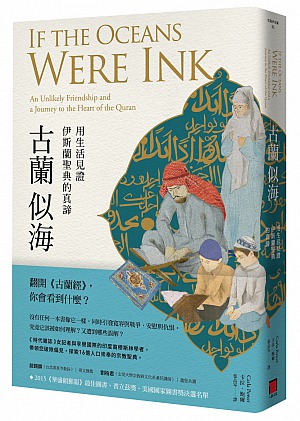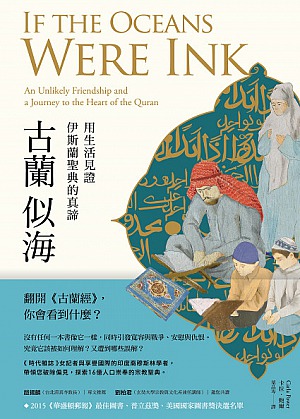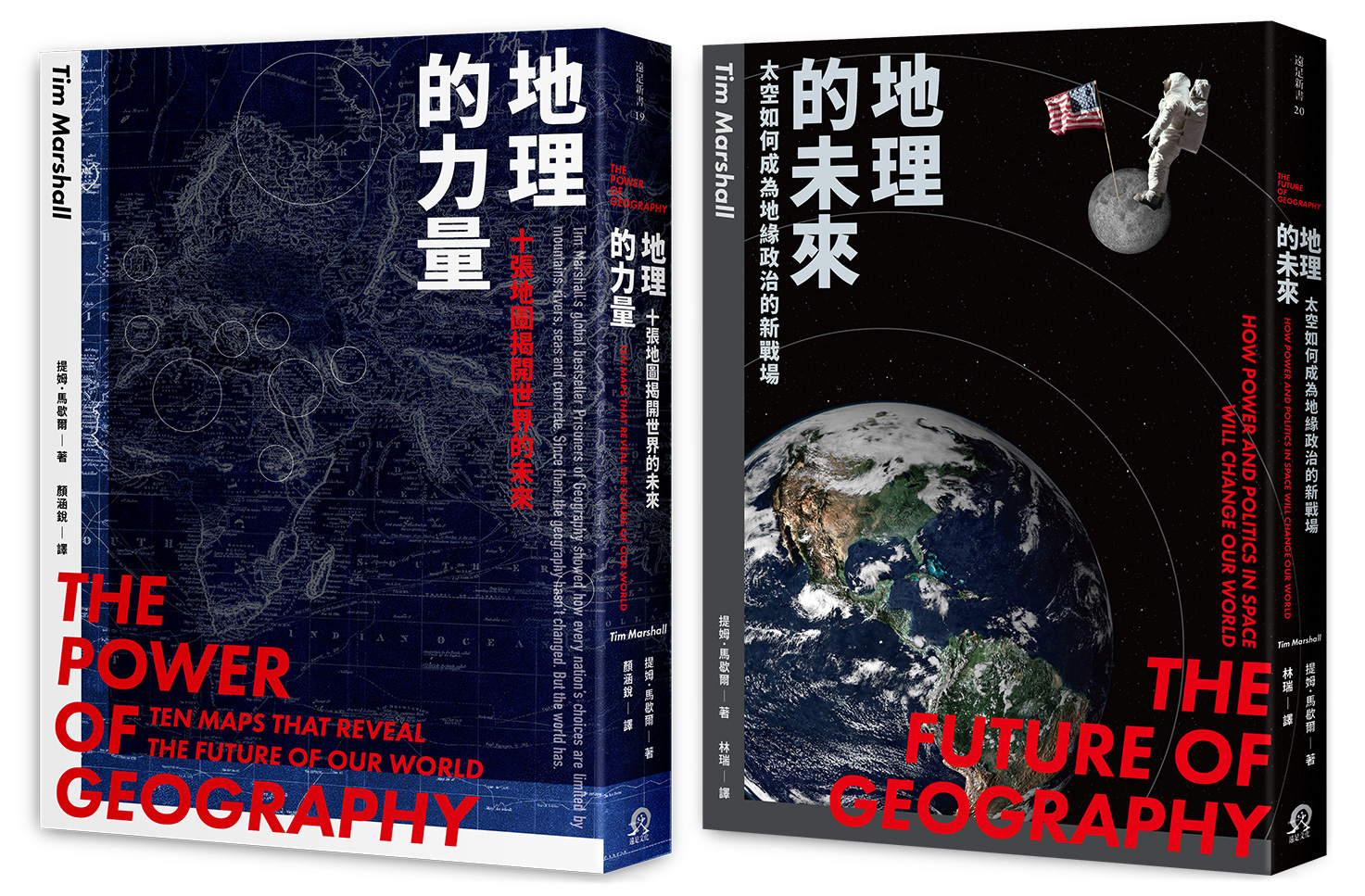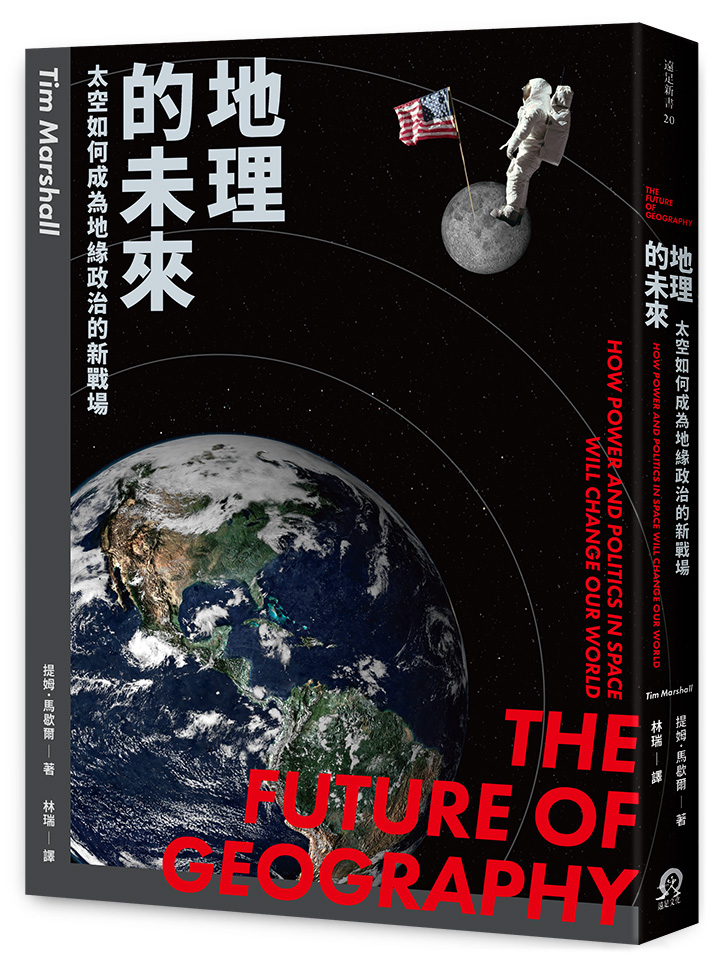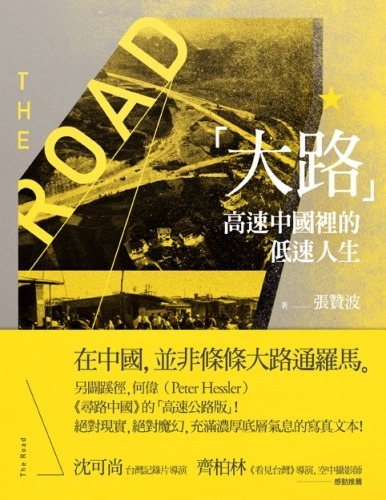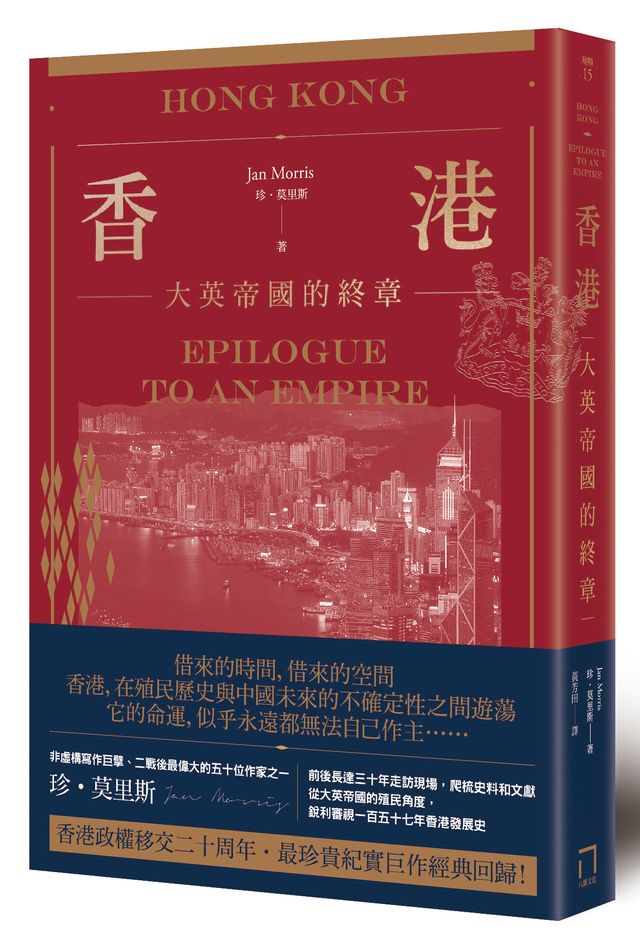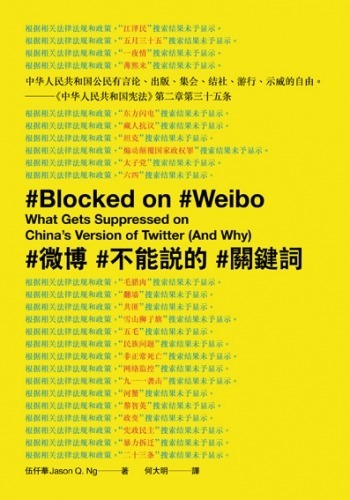※2015《華盛頓郵報》、《丹佛郵報》最佳圖書※
※2015普立茲獎入圍※
※2015國家圖書獎入圍※
世界上再沒有第二本書,能同時引發寬恕與戰爭、慰藉與仇恨。
誰誤解了它?誰能詮釋出真實的伊斯蘭?
在對立紛擾的爭辯中,一位美國女記者跟隨一位印度傳統伊斯蘭學者,
回歸《古蘭經》經文的原始脈絡,走入澄澈明亮的伊斯蘭之心。
西方與伊斯蘭世界衝突愈演愈烈之際,各式各樣關於「伊斯蘭」的報導充斥著媒體版面。狂妄暴力的極端分子成為關注焦點,深化主流輿論對伊斯蘭的抨擊與偏見,同時,為伊斯蘭平反之聲也日益顯著……
美國記者卡拉‧鮑爾兒時曾隨父親旅行伊朗和阿富汗,在她心中留下對伊斯蘭的親近之情。面臨現今西方與伊斯蘭世界撕裂衝突的局面,她決定展開行動:當瞭解伊斯蘭成為必要,為什麼沒有人願意討論《古蘭經》呢?
為此,鮑爾開始和以挖掘歷史上四千名重要的女性穆斯林而聞名全球的印度裔伊斯蘭學者阿卡蘭(Mohammad Akram Nadwi)共同研讀這本神聖經典,站上跨文明對話的最前線,找尋對話的可能。
長達一年的學習旅程,兩人走過牛津的咖啡館和印度小村莊的穆斯林學校,在茶與咖啡之間,咀嚼引發熱議的《古蘭經》經文。鮑爾聆聽阿卡蘭述說先知穆罕默德的故事與言行,還原經文脈絡,企圖接近伊斯蘭的真義。
一位西方世俗女性,和一位傳統派的印度宗教學者,似乎應該劍拔弩張的關係,卻培養出亦師亦友的真摯情誼。他們攜手從《古蘭經》洗鍊優美的文字中,挖掘出伊斯蘭崇尚和平而非屠殺的溫順性格,以及對女性的尊重而非迫害,拆解了聖戰、一夫多妻等常見的刻板印象。現今對伊斯蘭的誤解,無非是混淆了穆斯林社群中多樣的傳統文化,以及伊斯蘭信仰的樣貌。
然而,兩人的討論會不只是純真美好的文化交流。隨著與阿卡蘭的互動愈發緊密,身為世俗主義者的鮑爾不斷面臨自身思想觀念的挑戰。與異文化的碰撞是一場近身的肉搏戰,少不了尷尬、摩擦與辯論,迫使鮑爾跨越大城市居民習以為常、世界主義式的「尊重欣賞」,激盪出深刻理解的火花。
「我使你們成為許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們互相認識。」這是《古蘭經》第四十九章第十三節的經文,也是作者鮑爾翻開《古蘭經》的初衷。在真主創造的多元族群之間,不應存在衝突撕裂,而該用豐富的理解建立連結,也唯有如此,才能找到共存的解答。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見證了一段感人的友誼……《古蘭似海》貼心而細膩地重新理解伊斯蘭,並努力澄清種種對穆斯林的刻板印象與汙名……全美國52%自己認為還不夠瞭解穆斯林的民眾都應該熟讀它。」
《丹佛郵報》(The Denver Post):
──「鮑爾女士紀錄了她與一位她在倫敦智庫認識的穆斯林學者阿卡蘭共同研究《古蘭經》的點點滴滴。《古蘭似海》可以被當作是認識伊斯蘭的入門讀物,也可以作為理解阿卡蘭思想、西方人如何詮釋阿卡蘭,以及文化與宗教之對話的進階之作。
法理德.札卡瑞亞(全球百大公共知識份子、《後美國世界》、《為博雅教育辯護》作者):
──「若欲瞭解伊斯蘭對戰正與和平、男性與女性、猶太人與異教徒的看法,這本書能提供絕佳的答案。這段真誠友人之間的對話,聰穎、同理而極具啟發性,世界各地都需要有這樣的對話。」
亞薩德.莫凡尼(Azadeh Moaveni,《口紅與聖戰》(Lipstick Jihad)作者):
──「卡拉.鮑爾對《古蘭經》的親密描繪,筆調細緻優雅,記錄下關於穆斯林神聖經典之真正本質、獨特而未止的辯論。一部生氣洋溢、引人入勝的著作。」
約翰.艾斯波西多(John L. Esposito,喬治城大學伊斯蘭研究教授、(伊斯蘭的未來)《The Future of Islam》作者):
──「與眾不同、嫻熟出色、極為迷人的一本書。卡拉.鮑爾討論並發掘《古蘭經》關於和平與暴力、性別與頭巾、宗教多元主義與包容的訊息、意義以及價值,帶領讀者展開一趟跨信仰理解的獨特旅程。」
卡拉.鮑爾(Carla Power)
美國《時代週刊》(Time)作家,也曾為《新聞週刊》(Newsweek)、《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等雜誌撰稿。曾獲海外出版俱樂部獎(Overseas Press Club Award)、女性媒體工作者獎(Women in Media Award)。
鮑爾的母親是猶太人、父親曾是基督教貴格會的法律系教授,本人是生長在美國中西部的世俗女性主義者。因為父親熱愛至中東地區旅遊,鮑爾從小與伊斯蘭結下不解之緣。
葉品岑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碩士。曾任編輯,目前從事翻譯,譯作有《午夜的佩拉皇宮:近代伊斯坦堡的誕生》、《凱因斯對戰海耶克:決定現代經濟學樣貌的世紀衝突》。
第二章 一個美國人到東方
對父親而言,帶著妻小到海外住幾年,可慰藉他對美國社會長期的不滿和他的憂鬱症。他在密蘇里州當法律系教授,可是覺得在陌生國度更適得其所,若那些地方有他心目中文明社會必備的「葡萄、甜瓜和橄欖樹」時,更是如此。因此我的童年分別在聖路易郊區和穆斯林世界的幾個城市輪流度過。不消說,這份外派列表——德黑蘭、德里、喀布爾和開羅——非常啟人疑竇。媽媽的家族認為我爸是個中情局探員,狡猾偽裝成個性古怪的大學教授。他不是中情局的人。他把我們帶到國外比較是出於審美和情感因素,而非職業考量。
我們家最接近信仰體系的東西,是對旅行療癒力的堅信不移,因此宗教文本在我的養成教育中不具一席之地。我有個背棄信仰的貴格會教徒父親,以及把信念儲存在貝果和對〈陀螺之歌〉(dreidel song)模糊記憶之中的猶太血統母親,身為他們的女兒,我在成長期間不曾讀過任何宗教聖典。我們家是世俗家庭,藝廊與公園是我們的教堂,懷疑是我們的預設立場。我的雙親都是教授,不太在乎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或許曾幫助我們的祖先,他們拖著沉重腳步走在東歐猶太小鎮(shtetl)、在北美大平原上的公地(homestead)奮力求生,不過對我那雙擁有高等教育文憑和爵士樂手邁爾士.戴維斯(Miles Davis)黑膠唱片的父母卻不然。他們相信,超驗(Transcendence)存在提香(Titian)的畫作或夕陽裡,而非神聖典籍或聖人。我唯一的宗教訓練是偶爾在週日拜訪倫理學會(Ethical Society),我們在這個人文主義者集會所,彩繪世界各地的孩童的圖畫,歡唱關於簡樸恩賜的歌曲。
當母親露出猶太教的一面,是以文化而非宗教信仰的形式展現,而且一定和她的童年記憶有關,譬如鞍部鞋(saddle shoes)或吊帶。若她碰巧記得,我們會在逾越節藏無酵餅(matzo),在光明節點亮猶太教燈臺。偶爾她冷不防冒出幾句從立陶宛祖母那兒學來、記不太清楚的意第緒語:貶斥電影《愛的故事》為「沒格調」(schlock),在我和弟弟打鬧時,稱我是個「野孩子」(vilde chaya)。即便如此,我確實依稀自覺是個猶太人,雖然我所謂的猶太人自覺,充其量是一種特殊的城市世界主義,由黑色諷刺和訂閱《紐約客》雜誌所組成。極度節儉是父親貴格會文化傳統的唯一遺跡,還有關於成天「汝」來「爾」去慣用古英語的姑婆們的故事,以及隱約覺得參加貴格聚會或許不錯,前提是改天有機會的話。「我樂意信教。」父親會邊說邊張開雙臂,彷彿等待某個神祗降臨他的懷抱。神祇不曾真的來過。
父親用旅行和旅途中購買的手工藝品,填滿宗教可能進駐的閒置空間。在聖路易家裡,我們和斑駁鍍金佛像、印度迷你畫以及成堆東方地毯一起生活——這是父親用來阻擋密蘇里州入侵的防禦工事。對他而言,聖路易是鄰居要相互點頭致意的城市,是人們秉著陰森沉默加油的城市,是在冬寒中蜷縮長途步行的城市。可是為了養家,他勉強接受一份工作,在那裡教法律。他發現,只要夏天能到歐洲旅行,然後每隔幾年申請研究獎學金或無薪休假到海外住一陣子,這份工作是可以忍受的。
七〇年代初期,他首次在伊朗發現伊斯蘭文化的強效抗憂鬱成分。緩慢的日常節奏,中間穿插幾杯茶與禮拜時間,對他起了撫慰作用。中東的市集(bazaar)文化以不著邊際的閒話家常緩衝交易的爭鋒相對,讓他覺得比購物中心自然,也比較有人情味。他第一次感到自在。倚著伊斯法罕式清真寺的牆面蹲坐,或在市場與人辯論土耳其毯馬鞍袋的優點,他不再是《法律評論》交際場合上的壁花。對不曾與直系親屬以外團體產生連結的男人而言,西亞給他一種歸屬感。就連幼小的我亦看出穿梭於不同文化令他判若兩人:跨文化超越價值觀,成為一種生存策略。
我本身對伊斯蘭社會最初的認識是全然感官的,全是關於表象質感的觀察。以棕糖色沙漠為背景的綠松石色清真寺圓頂。太陽光下羊毛地毯散發灰塵和肉味。伊朗婦女一派優雅地以牙齒緊咬罩袍(從頭到腳的連身伊朗式罩布)的邊緣,以便騰出雙手抱嬰兒或提購物袋。
小時候的我為了把陌生環境變得熟悉,曾粗拙地嘗試跨文化理解。五歲時,我最喜歡的遊戲是「伊朗女士」——一個美國孩子玩德黑蘭版的扮家家酒——我把自己包進童裝伊朗罩袍,扮演伊朗女士。六年後,住在喀布爾,我幻想能有一間攤販,或許隱藏在市集的角落深處,販售美味泡泡糖(Bubble Yum)、博納貝爾潤唇膏(Bonne Bell Lip Smackers)和Levi’s牛仔褲,那是十一歲的我最渴望從美國得到的幾件物品。我腦海中的區域地圖,依照微不足道且高度個人化的比例尺所繪製。開伯爾山口是美國青少年前往伊斯蘭瑪巴德看國務院牙齒矯正科的路。白沙瓦(Peshawar)有一間提供美味餃子的中國餐館,還有一個黃金市集,客人可以試戴綴有紅寶石和綠寶石的皇冠頭飾。
住在喀布爾,我不是唯一以短淺目光想像這個區域的人:一九七〇年代期間,若西方人曾認真考慮怎麼處置阿富汗,那便是把它當作尋刺激之人與古怪孤僻之人的異國遊樂場。嬉皮為尋找比德里或果阿品質更好的大麻膏而來。牛津劍橋古典學者在鄉間四處搜索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留下的古文物。父親到阿富汗尋找卡什加地毯(Kashgai rugs)、香甜的布哈拉甜瓜,以及和聖路易大學法學院教員休息室最遙遠的距離。
儘管熱愛伊朗與阿富汗,父親對伊斯蘭文化的觀點是東方主義式的,而非身歷其境的,更著重美學欣賞,勝過承認一個現存的傳統。在他寄回家的信件中,信仰似乎不過是華麗清真寺與聖殿、孔雀藍磁磚和禮拜跪毯的源頭。我們徘徊在社會的邊緣,雖然住在當地,卻對中東正在發生的重大事件渾然未覺。我們從德黑蘭家的陽臺觀看穆哈蘭姆月(Muharram)遊行,男人用鞭子或鐵鍊鞭笞自己,唱著〈胡笙啊〉(Yo, Hussein),哀悼先知在卡爾巴拉戰役(Battle of Karbala)中死去的孫子。我父母完全不知道,將眼前遊行的能量套到對波斯國王政權的憎恨上,竟強大到足以拖動一場革命。他們也沒料到伊斯蘭會成為阿富汗戰士對抗蘇聯軍隊的強大工具。抑或提供埃及人宣洩對獨裁統治者不滿的框架。
一九七九年之前,伊斯蘭已退縮至私人領域,起碼當時的西方公眾意見這麼認為。中東的未來屬於世俗的現代推動者,像巴勒維國王或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他們是可靠的人,會向我們購買坦克和飛機,會建造道路和水壩,就算不推動民主,起碼注重國土保安。一九七七年的元旦前夕,吉米.卡特總統(Jimmy Carter)曾向巴勒維國王祝酒,稱伊朗是動亂區域的「安定之島」。西化和世俗化才有前途。伊斯蘭是鄉村婦女的消遣,或在蹲伏在清真寺庭院凋零老者的寄託。
事後我們才發現那個想像多麼狹隘。一九七九年的冬天,新聞全是嚴肅婦女穿黑色伊朗罩袍在德黑蘭街頭遊行的照片。鬍鬚蓬亂的男人呵斥「洋基佬,滾回去」。同年冬季還出現另一個畫面,同樣令人震驚:國王和他的妻子法拉赫皇后,披著毛皮,站在德黑蘭機場的柏油跑道,準備離開伊朗前往埃及「度假」,然後就一去不回了。兩週後,一架法國航空的飛機載著臉龐瘦長鋒利的何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回家,受到民眾欣喜若狂的歡迎。
當我們住在德黑蘭的時候,國王就像一個凡間的上帝,擁有孔雀王座和美若天仙的皇后。皇后的加冕皇冠比我在所有童話書上看到的都還要大。對我而言,國王彷彿全能全知,冷峻深邃的雙眼,從商店與銀行的壁掛肖像畫凝視向外。不過,一九七九年我們住在埃及時,沙達特總統給我的感覺也是如此,那年他和以色列簽署和平條約;兩年後,我仔細打量著《時代》雜誌刊載的圖片,一座閱兵臺被子彈射得千瘡百孔,一名總統遭伊斯蘭聖戰組織成員刺殺。
即便當時,我對我們的無知略感羞愧--我們和棲居之社會的疏離簡直逼近道德失敗。
「你怎能不知道?」我秉著滿腔青春期自以為是的正義感質問道。那是我們回到聖路易後,我和爸媽當時正在看六點整點新聞的伊朗人質危機新聞影片。新聞畫面中,多名美國外交官,手被綑綁,矇著眼罩,被帶到美國大使館戶外列隊展示。我曾經很愛那個大使館,因為館內的餐廳有亨氏(Heinz)番茄醬和糖包。
我以責備的眼神瞪著我的父母。「發生這麼多事,我們人就在那,但完全不知情?」
「我們知道檯面下有些腐敗的事,」母親和婉地回答,「那些房子,還有現金,還有招牌。但你感覺得到那全是虛有其表,在美麗門面的背後,一切都糟糕透了。」
我們住在伊朗的日子,外界謠傳國王秘密警察機構「薩瓦克」(SAVAK)的局長,是父親司法正義課堂上的學生。國王的影子甚至籠罩母親的莎士比亞課。講授描述暴君權力動搖的劇作《李爾王》(King Lear)是尤其棘手的任務。無論母親怎麼嘗試,她的伊朗學生始終不解寇蒂莉亞(Cordelia)不願順著父親李爾王之意加以奉承的原因。這些忠於「萬王之王、雅利安人之光」、繼承數世紀恭敬順從的國王的子民,在母親的課堂上總是困惑不已。抑或是,他們聽聞校園內有薩瓦克密探的謠言,所以才假裝困惑不解。
儘管國王的獨裁專政決定了一般伊朗人的生活,多數西方國家仍宛如追星般地仰慕他的政權。我們住在伊朗那年,他舉辦了一場慶祝波斯君權統治滿二千五百年的派對,被何梅尼指稱為「惡魔的歡慶」(Devil’s Festival)。派對籌劃者造牆隱藏一大片鄰近社區,以免國外要人們看了覺得礙眼。一名花藝師從凡爾賽宮搭機前來,在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蠍子隨處可見的沙漠中耐心照料一座玫瑰園。各國領袖在空調帳篷裡飲用拉菲酒莊(Château Lafite-Rothschild)產的一九四五年份的葡萄酒,品嚐烤孔雀。與會賓客的衣著彷彿來自五歲孩子的瘋狂幻想:就連海爾.塞拉西(Haile Selassie)愛犬的項圈都鑲有鑽石。
波斯波利斯慶典舉辦前的那幾年,來自世俗與宗教背景的政權批評者,均大力反對這類對西式表象的崇拜。許多人遭流放、監禁或被薩瓦克騷擾,但他們的話語在海外流亡圈餘音繚繞,並透過禁書流傳散播。一九六二年,伊朗作家賈拉勒.阿赫瑪德(Jalal Al-e-Ahmad)秘密出版《迷醉西方》(Gharbzadegi)。這是對伊朗菁英執迷於模仿西方的攻擊。「一個迷醉西方的人⋯⋯就像飄蕩在空氣中的一顆灰塵粒子,或漂浮在水面上的一根稻草,」艾哈邁德寫道,「他切斷了自己和社會、文化與習俗之精髓的連結。」
認識這個區域的歷史更令我看清,我們過去對當時棲居之社會的輕薄無知。個別來看,我們絕對不是「醜陋的美國人」(Ugly Americans)。可是,雖然我的父母學習波斯語且深受伊朗清真寺與地毯的吸引,我意識到,我們其實屬於一九七〇年代伊朗經歷的美國入侵的一部分。我的母親與父親尊重文化,但仍屬於五萬多名美國人的一員,他們來伊朗提供管線鋪設或刑法法典的諮詢服務,以及販售冰箱或導彈——最重要的是,驅策伊朗朝西化之路前進。
因為我們是美國人,當地法律對我們不具約束力。某個寒冷冬夜,我們一家以觀光客的身分抵達設拉子(Shiraz),那次我見證了美國人的不可侵犯。在爸媽從計程車卸下行李的同時,他們要我看著兩歲大的弟弟。我沒有照做,起碼看得不夠緊,於是他搖搖晃晃地走到街上,被一輛卡車撞倒。他生命無虞,只是受驚,但意外引來圍觀人潮,以及一雙警察。爸媽向官員保證犯錯的絕非卡車駕駛,是他們自己考慮欠周,根本不該把一個學步嬰孩留給一個五歲小孩照顧。即便如此,駕駛仍被丟進大牢,就因為我們是美國人。伊朗國王和華府簽了一份協議,美國人稱為地位協定(Status of Forces Treaty),伊朗人稱為投降條約(Capitulation Treaty),讓美國人在伊朗領土享有豁免權。父親後來整晚在警局度過,懇請他們釋放駕駛。
約莫二十年後,因為牛津的波斯語教授要我們翻譯何梅尼眾多講道內容的其中一篇,我才第一次憶起這個曾發生的事件。一九六四年,地位協定剛生效,正是這篇演講內容使何梅尼從伊朗被驅逐出境,直到國王倒臺。「一個人撞死美國人的狗,他會被起訴,」何梅尼指出,「但美國廚師輾過一國元首的國王,沒人有權利妨礙他。」
其他閱讀材料為我的記憶增添令人不安的新意涵。大學時期的我,和一九八〇年代數百萬其他學生一樣,一頭栽進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的文學與文化批評著作。他指出,千百年來,西方的東方觀點向來都是與現實不符的幻想——和西方恐懼與帝國主義的關聯,多過和東方社會本身的關聯。在薩依德看來,西方對東方文化的描摹膚淺空洞,是歐洲殖民強權在政經方面實際控制亞洲與非洲人民的一種延伸展現。研究英屬印度歷史,我從到孟加拉制訂英國法律的沙希布(sahib),抑或在旁遮普(Punjab)再現威爾特郡(Wiltshire)花園的曼沙希布(memsahib),可約略看見我雙親的輪廓。父親拿華府幫助編纂阿富汗憲法的補助金,和前朝帝國沒有瓜葛。儘管如此,他和其他許多美國人出現在喀布爾,暗示蘇聯和美國在阿富汗國內進行漫無目的的「新大博弈」(Great Game)。在俄羅斯人終於在一九七九年入侵之前,這場競賽以爭鋒相對的發展計畫形式展開。蘇聯蓋喀布爾的機場;美國人提供它的通訊和電子設備。蘇聯從興都庫什山脈(Hindu Kush)開鑿出薩朗山口(Salang Pass);美國人在赫爾曼德河(Helmand)開挖大壩。
在喀布爾當美國小孩可謂加倍地天真:高聳的院落圍牆,只收西方人的俱樂部,還有美國國防部軍營超市保護一支來自阿富汗社會的帝國派遣隊。在很多方面,我的喀布爾生活比在聖路易時更有美國味。我們用Betamax看《星際大戰》,打網球,住在一幢兩層樓高附庭院的大房,還養了一隻狗。「如果瞇著眼睛看,」母親寫道,「就像南加州的分層(split-level)式建築!」
我們和多數英屬印度的英國沙希布一樣,與當地人交情淺薄。我們喜歡我們的僕人,和偶爾來家中共進晚宴的最高法院法官與司法部官員交際寒暄。但說也奇怪,我對那裡生活的記憶,缺乏與阿富汗人的真實友誼,甚至不曾和阿富汗人多講幾句話。父親波斯語講得不錯,而且週末經常和地毯商人在一起,是我們家四人中最親近阿富汗文化的人。日後,他說喀布爾歲月是他生命中最快樂的一段。
某種程度上,他是沉溺在伊斯蘭世界獨特且自給自足的東方主義幻想的最後世代。一九六〇和七〇年代,西方人還勉強能說服自己相信伊斯蘭遠在天邊,誠如他們自一〇九五年起所相相信的,也就是當十字軍乘著馬匹去搶奪由薩拉森人(Saracen)控制的耶路撒冷。直到一九七九年之前,一個人可能在東方的大麻酒館或蘇非主義者集會處,找到屬於自己的個人天堂,抑或打造一個建造水壩、道路、刑罰制度的事業。
今天,美國和阿富汗之間的距離已徹底消失:密爾瓦基(Milwaukee)眾多母親擔心著赫爾曼德省(Helmand)的步行巡邏。坎達哈(Kandahar)是家喻戶曉的地名,喀布爾則是各國元首和將軍們例行性的公關拜訪停靠站。移民,加上戰爭,模糊了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世界的分界。父親生活的年代無疑已有穆斯林住在西方,而且數百年前已是如此。但直到一九六〇和七〇年代,來自前歐洲殖民地的移民開始在西方安家落戶,人們才覺得伊斯蘭將成為一股永久勢力。獨裁統治和戰爭造成的難民,在一九八〇和九〇年代加入外來移民的行列。巴黎與皮奧里亞(Peoria)、柏林與洛杉磯,迎來在革命中選錯邊的伊朗人;遭到海珊迫害的伊拉克人;想逃出穆安瑪爾.格達費(Muammar Ghaddafi)特勤組織魔掌的利比亞人;還有逃離內戰的阿爾及利亞人、阿富汗人、索馬利亞人與蘇丹人。他們養兒育女、建造清真寺、開始遊說並在他們的新國家投票。他們為兩個貌似迥異的時空「伊斯蘭世界」和「西方」搭起銜接的橋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