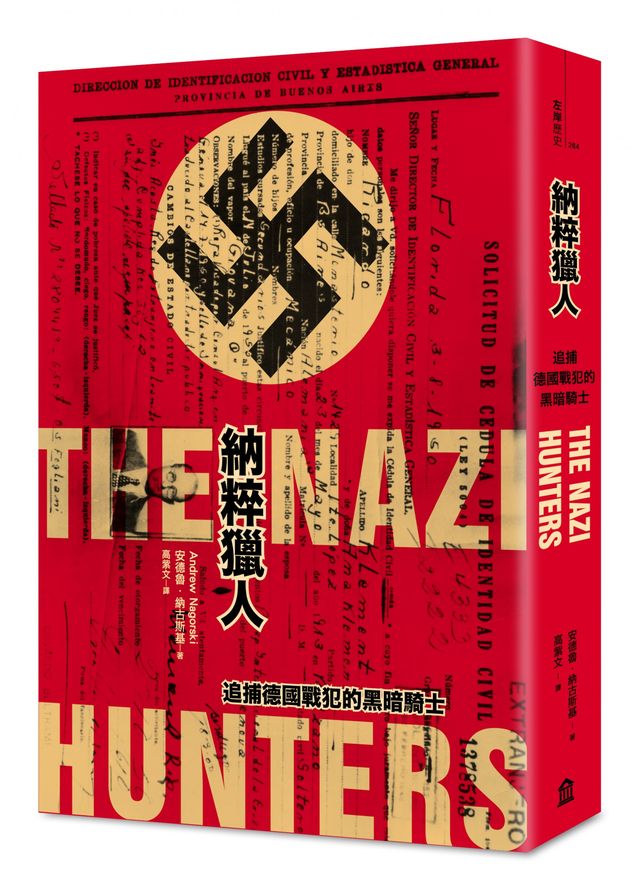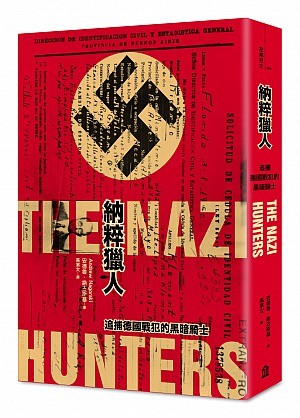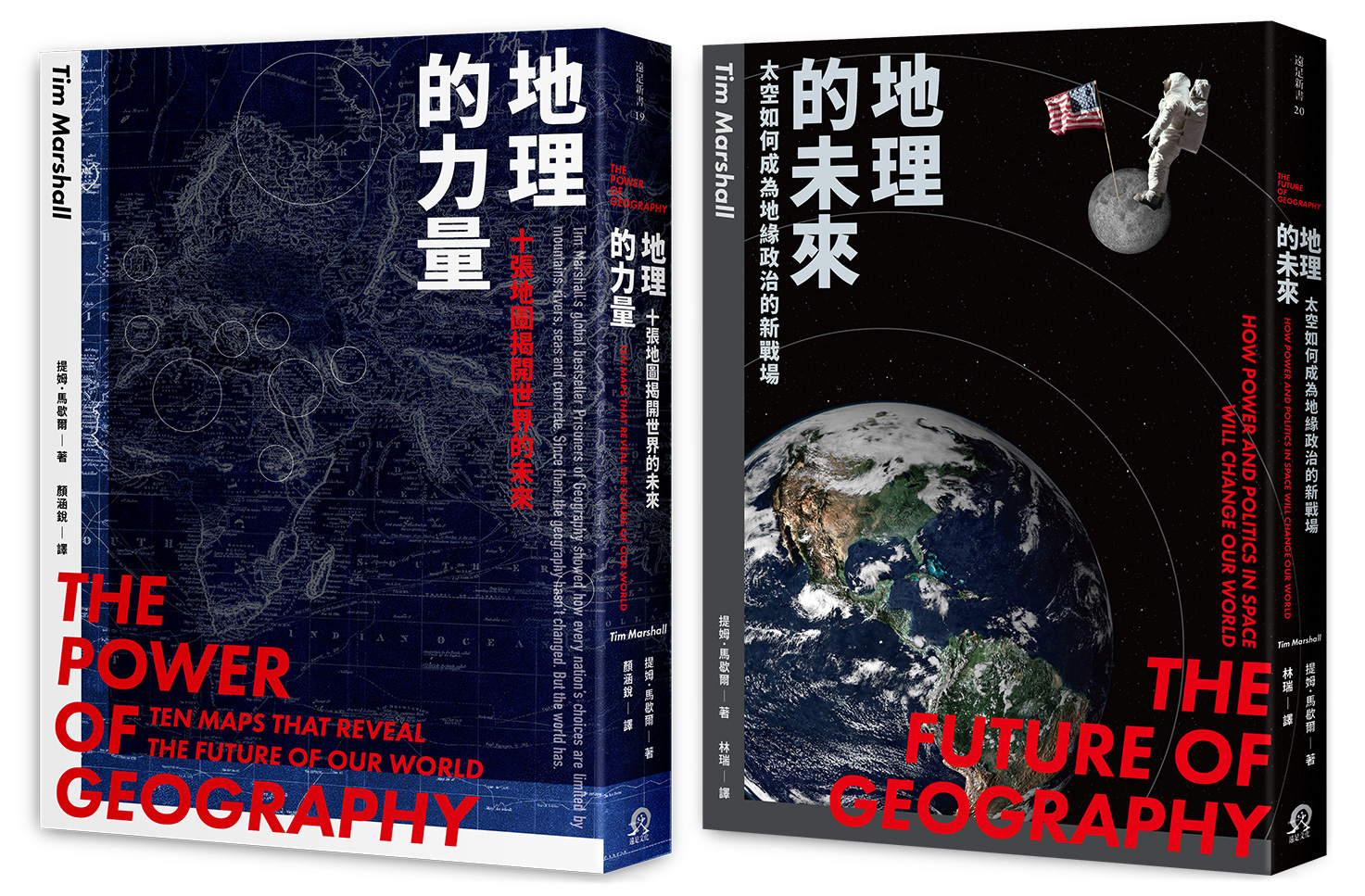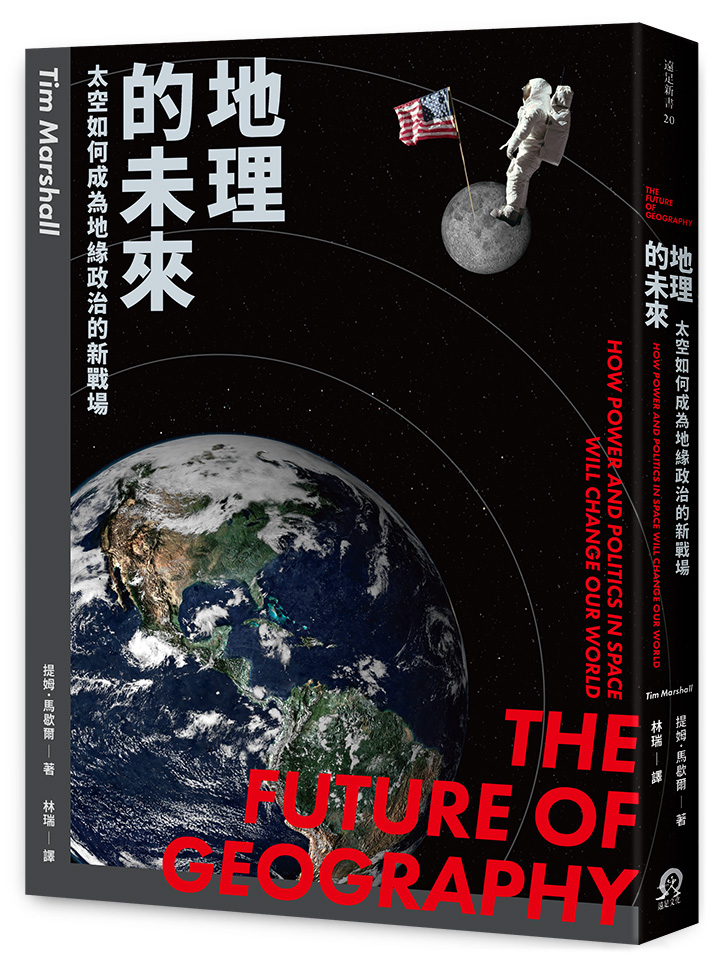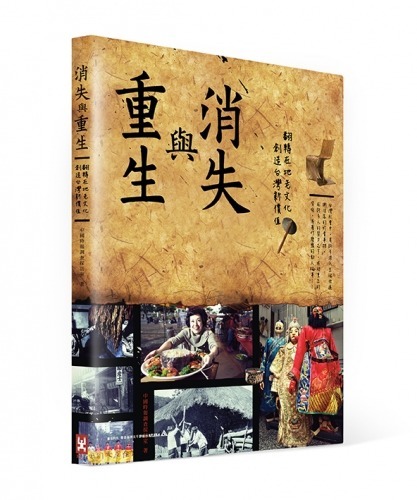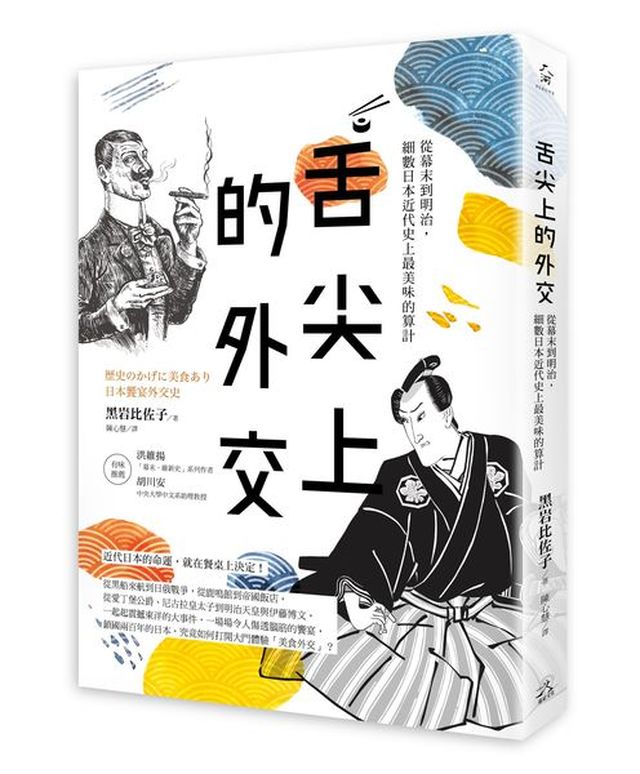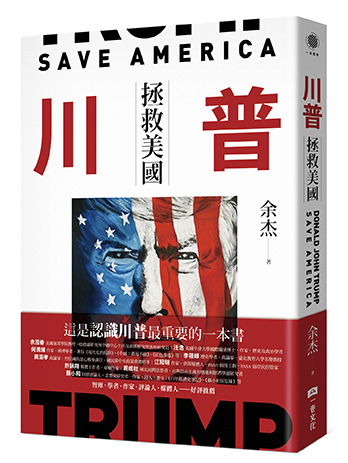1945年,二戰結束,但對另一群人來說,追尋正義的路程才要開始……
冷戰開始後,大多數二戰勝利方的人士都沒有興趣再追討納粹戰犯的罪行。許多低階的納粹戰犯很快就混入百萬人群中,在戰後歐洲重新開始生活,甚至冒險逃離歐洲大陸。本書所聚焦的這一小群人,他們不願見到納粹的暴行被遺忘,決心一步一步追蹤戰犯逃亡的腳步,就算到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人。
我們會介紹碧特.克拉斯費德(Beate Klarsfeld),她賞了曾經加入納粹黨的西德總理齊辛格耳光;波蘭檢察官傑恩.西恩(Jan Sehn),他負責審理奧許維茲的指揮官魯道夫.霍斯;還有德國法官費里茲.鮑爾(Fritz Bauer),他不斷地督促同胞去面對自己國家的大屠殺紀錄。此外,我們也會談到以色列特工局莫薩德的特務拉斐.艾坦(Rafi Eitan)與艾里.羅森邦(Eli Rosenbaum),前者成功抓到艾希曼,後者協助美國司法部特別辦公室把那些默默躲在美國境內的納粹戰犯驅逐出境。
二戰過後七十年,納粹獵人的時代也劃下句點,獵人與被獵者漸漸凋零,我們也終能完整地回顧這些人的事蹟。
當中許多案子爭議很大、事實難以界定。有些集中營的守衛活到了九十多歲才被抓到,根本就找不到目擊證人可指證他們戰時所扮演的角色。納粹獵人的故事改變了我們對於對與錯的基本認知,究竟是正義、還是復仇,世人還在爭執。但這些令人屏息的冒險故事,頑強又有決心的追獵者,其無止盡的追尋,令人難以忘懷。
安德魯.納古斯基(Andrew Nagorski),美國資深駐外記者與國際新聞編輯,自1978年進入《新聞週刊》後,在各地擔任外派記者與地區主管,三十年來,足跡踏遍全球,包括香港、華沙、莫斯科、羅馬、波昂、柏林。由於其傑出的報導,他三次獲得美國海外記者協會的表揚,也曾擔任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的董事。納古斯基著作等身,多為歷史著作,除了《納粹獵人》之外,還有《扭轉二戰歷史的最終大戰:史達林與希特勒爭奪莫斯科》(The Greatest Battle: Stalin, Hitler and the Desperate Struggle for Moscow That Changed the Course of World War II)、《希特勒之國:看著納粹崛起的美國人》(Hitlerland: American Eyewitnesses to the Nazi Rise to Power)
高紫文,臺師大工業科技教育系畢業,譯有《甘地與我》、《失控的正向思考》、《馬特洪峰》、《1940法國陷落》、《狼哨》、《美國狙擊手》、《大象先生》、《感謝您為國效力》、《垃圾天使》、《塔樓》。
第二章 「以眼還眼」
紅軍推進時,名叫屠維亞.費曼(Tuvia Friedman)的十幾歲猶太少年,在波蘭中部城市雷登的集中營當奴工,他不僅計劃要逃跑,還要為在猶太大屠殺中失去大部分家人報仇。「我越來越想報仇,越來越盼望有朝一日,我們猶太人能報復納粹,以眼還眼。」他回憶道。
趁著德軍準備撤離,費曼和兩名囚犯同伴從工廠的汙水道逃出去。他們小心翼翼穿越髒汙,逃到營區刺絲網另一邊的樹林。他們在溪流裡清洗後,自己開闢新路徑逃出去。費曼後來有記述當時他們有多麼興奮:「我們雖然害怕,但終於自由了。」
許多波蘭游擊部隊已經在該區作戰,不只對抗德國人,也對抗自己的同胞。這可是攸關波蘭在德國結束占領後的未來。在歐洲占領區,規模最大、戰力最強的反抗運動組織是波蘭家鄉軍,家鄉軍也堅決反對共產主義,效忠於流亡倫敦的波蘭政府。人民護衛隊規模小多了,由共產黨員組成,負責擔任先鋒部隊,依計劃協助蘇聯接管波蘭。
費曼用塔德.傑辛斯基這個姓名,向德國人與反猶太人的當地人隱瞞猶太人的身分,迫不及待加入亞當斯基中尉組織的共產黨民兵部隊。根據費曼的記述,他們的任務是「終結家鄉軍無法無天的行徑」,並且緝捕戰爭期間曾經「損害波蘭及其人民利益」的德國人、波蘭人和烏克蘭人。
「我懷著滿腔熱血,開始執行最後一次例行任務。」費曼報告道,「我跟幾名聽我指揮的民兵合作,摸著穩穩放在槍套裡的手槍,逮捕一個又一個榜上有名的戰犯。」
費曼和他的同志們自然有追捕到一些名符其實的戰犯,比方說,他們抓到名叫施朗斯基的烏克蘭工頭,「他打過的猶太人,多到他自己都記不得了」。那名工頭又指引他們找出另一名後來被吊死的烏克蘭人。不過有的人認為,「對波蘭最有利」的事之一,就是全面逮捕反對蘇聯在戰後統治波蘭的人,包括一些在德國占領期間英勇無比的波蘭抗戰人士。
縱使俄軍持續在跟撤逃的德軍戰鬥,克里姆林宮的主事者仍舊在華沙逮捕十六名家鄉軍的領袖,派飛機送到莫斯科惡名昭彰的盧比揚卡監獄。他們被波蘭的「解放者」嚴刑拷打,歐戰正式結束不久後,便於六月被抓去進行表演式假公審。他們對抗納粹六年換來的回報,竟然是被判「牽制俄國」的罪名,遭到監禁。
這種不公平的遭遇對費曼而言毫不重要,他不只一次受到反猶太的波蘭人傷害,因此只要有人把紅軍視為真正的解放者,費曼就會他跟在站在同一陣線。
不過吸引費曼的,不是未來波蘭新統治者的意識形態,他的優先要務是報復德國人,而共產黨給了他機會得償所願。
費曼和五名友人被派到但澤,一行人從雷登前往那個波羅的海港都,看著德軍趁著還能逃的時候趕緊西逃。「有些人看起來很可憐,沒辦法走路,頭上纏著染血的繃帶。」費曼寫道,「不論如何,我們就是沒辦法可憐他們,沒辦法同情他們。這些劊子手殺人如麻,得自食惡果。」
紅軍與波蘭警察部隊炸掉快要倒塌的建築,城市裡許多區域陷入火海。「簡直就像尼祿時代那場有名的羅馬大火災。」費曼補充道。
他們這群外來者因為命運突然逆轉而欣喜若狂。「我們感覺自己像是來自別的星球,我們來到地球,把棲息在地球的生物嚇得驚恐逃跑。」他們衝入德國人撤離的公寓;德國人倉促逃離,連衣物與私人財產都沒帶走,散落滿地。在一間住所裡,他們發現瓷瓶,根據費曼的記述,「那大概是德勒斯登生產的」。他們把瓷瓶當成足球來踢,全都踢成碎片。
後來他們變得比較有紀律,繼續執行自己認定的任務,尋找「謀殺與屠殺過人的納粹黨員,定要報仇雪恨,懲罰納粹的罪行。」新招募的人員亟欲報仇,到國家安全部報到時,受命協助圍捕十五歲到六十歲的所有殘餘德國人。「咱們把納粹人渣全揪出來,把這座城市清乾淨。」新的上級長官告訴他們。
在回憶錄中,對於猶太人第一次被逐出雷登,費曼有記述姊姊蓓拉的反應,特別是她說:「猶太人就像待宰羔羊一樣」,長久以來,眾人談到猶太大屠殺時都會如此形容。費曼在但澤審問與監禁德國人時,採取恐怖手段,他描述心中的快意時,也用一樣的動物來比喻:「現在身分對調囉,多虧帥氣的波蘭制服,我才能叫這些曾經不可一世的優等民族乖乖聽命,嚇得他們像驚恐的羊群。」
他承認自己審問囚犯時,會「毫不留情」,總把他們打到認罪。「我心裡充滿恨意,以前他們勝利時殘暴冷血,我痛恨他們,現在他們被打敗了,我一樣痛恨他們。」
戰後許久,他撰文寫道:「現在回顧那一切,我覺得有點羞愧。不過大家必須記得,當時是一九四五年春天,德國人仍舊在兩條戰線跟盟軍與俄軍頑抗到底,而且我也還完全不曉得,我的家人有沒有人在納粹集中營裡還活著。」他和其他人繼續發現更多德軍犯下恐怖暴行的證據,像是滿室的裸露屍體,屍體上還有明顯的嚴刑拷打痕跡。不過,一聽到越來越多人說他「手段殘忍」,他自己也感到不安。
蓓拉在奧斯威辛還活著的消息傳來後,費曼便辭職,回到雷登。他們覺得波蘭越來越像異邦,於是決定離開。一來是反猶太情緒引發的暴行處處可見,其次,他們也沒有其他直系親屬從集中營返回。他們原本計劃前往巴勒斯坦,加入川流不息的流亡猶太生還者;地下組織步離家協會(Brichah,希伯來文「遷徙」的意思)專門協助生還者,安排非法途徑逃離歐洲。戰後猶太人大舉遷離歐洲,為建立以色列國打下基礎。
不過費曼的旅行很快就被打斷,結果他在奧地利待了幾年。在那裡,他可以盡情追捕納粹黨員。他決定繼續清算宿怨,不過不再用波蘭新共產黨統治者鼓吹的那些殘忍粗暴、不分青紅皂白的手段。
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一輛巨大的戰車,炮塔上有一面美國國旗揮動,隆隆駛進奧地利林茲市附近的毛特豪森集中營。一名形容枯槁、穿著條紋囚服的囚犯看見後,好想去摸戰車側面的白星,但是卻提不起力量,沒辦法走最後幾呎去摸白星。他雙膝一彎,臉朝下倒了下去。一名美軍士兵扶起他後,他把手伸向戰車,碰觸到那顆白星後,便暈了過去。
西蒙.維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在營舍醒過來後,發現獨自躺在自己的床鋪上,此時他知道自己重獲自由了。許多黨衛軍守衛在前一晚就逃走了,現在每個床鋪上面只有一個人,早上還在床鋪上的屍體都不見了,而且空氣中瀰漫著滴滴涕的味道。最重要的是,美國人搬進來幾個大湯鍋。「那是真正的湯喔,喝起來美味極了。」維森塔爾回憶道。
那些湯卻讓他和許多囚犯極度不適,因為他們沒辦法消化那麼油膩的飲食。經歷過在集中營每天掙扎求生後,維森塔爾說,接下來這段日子,「雖然過得開心,卻對一切漠不關心」。餐餐都有更多的湯、蔬菜與肉可以吃,穿白袍的美國醫生還會拿藥給他服用,使他恢復了活力。不過對許多人而言,為時已晚,維森塔爾估計有三千人在獲得解放後,死於疲累或飢餓。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猶太大屠殺之前,維森塔爾就對暴行和悲劇司空見慣了。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在布恰奇出生,布恰奇是位於加利西亞東部的小鎮,當時隸屬於奧匈帝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隸屬於波蘭,現今隸屬於烏克蘭。鎮上有許多猶太居民,但是整個地區有許多民族雜居,通行不同語言,因此,維森塔爾在成長過程中,聽過德語、意第緒語、波蘭語、俄語和烏克蘭語。
不久後,當地就被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布爾什維克革命,暴行肆虐,隨後內戰接踵而至,俄國人、波蘭人和烏克蘭人互相攻擊。維森塔爾的父親是個事業有成的商賈,為奧地利軍隊打仗,年紀輕輕就戰死沙場。後來,維森塔爾的母親帶著兩個兒子到維也納,不過一九一七年俄國人撤離後,母子便又回到布恰奇。西蒙年僅十幾歲時,弟弟西樂就因為摔倒造成脊髓受傷而去世。
維森塔爾在布拉格讀建築學,回家鄉後跟高中女友希拉.穆勒結婚,成立事務所,專門設計住宅建築。求學期間以及在布恰奇時,他有很多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的朋友,他跟當時許多年輕人不一樣,從來沒有受到激進左翼的政治主張吸引,他感興趣的是另一種政治理念。「年輕時,我是錫安主義者。」他經常提醒我跟其他採訪者。
猶太大屠殺對他跟費曼以及其他生還者而言,一點都不抽象。在戰爭的第一個階段,他和家人住在利沃夫(現在改名為利維夫市)。《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又稱《莫洛托夫與里賓特洛甫協議》)簽訂後,波蘭被分割給德國與蘇聯,讓俄軍率先取得利沃夫,接著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命令德軍入侵蘇聯,迅速攻占利沃夫。
維森塔爾起初被拘禁在市內的猶太區,接著被囚禁在附近的集中營,接著又被派到東鐵路維修工廠。西蒙在那裡擔任黨徽油漆工,負責替被掠奪的蘇聯火車頭漆上納粹黨徽。這一切只不過是在集中營裡的一段插曲,他經歷過一長串的苦難、逃亡與冒險,最後在戰爭即將結束時,被送到毛特豪森。他成功安排希拉逃亡,讓希拉以波蘭天主教徒的假名到華沙躲藏。但是命運待他的母親就沒那麼好了。
一九四二年,維森塔爾提醒母親,可能會有另一波驅逐行動,她最好準備交出她還擁有的一隻金錶,以免遭到驅逐。一名烏克蘭警察出現在她家門前時,她照兒子的叮嚀做。維森塔爾痛苦地回憶道:「半個鐘頭後,另一名烏克蘭警察前來,母親沒有東西可以給他,於是他就把母親帶走。母親的心臟無力,我只希望母親能死在火車裡,不用脫掉衣服走進毒氣室。」
維森塔爾多次講述自己如何奇蹟似逃過死劫,比方說,一九四一年七月六日圍捕猶太人時,他說烏克蘭後備部隊叫他們一個接著一個排在牆前,一邊大口喝伏特加,一邊開槍打猶太人的脖子。劊子手漸漸逼近他,他茫然凝視面前的牆,突然間,他聽到教堂鐘聲,一名烏克蘭人喊叫道:「夠了!夜間彌撒囉!」
很久以後,維森塔爾變成聞名天下的名人,越來越常跟其他納粹獵人發生爭執,但是維森塔爾說的故事是真或假,經常遭到質疑。湯姆.賽吉夫寫了一本維森塔爾的傳記,引起極大的共鳴,但是,就連這位作家也提醒讀者,別輕易相信維森塔爾說的故事。「維森塔爾懷抱文學夢,喜歡天馬行空幻想,不只一次大肆添加戲劇化的歷史情節,不肯單純記述事實,好似認為真實故事的力量,不足以感動讀者。」他寫道。
不過無庸置疑,維森塔爾在猶太大屠殺期間經歷悲慘的苦難,在無數次險境中,千鈞一髮逃過死劫。同樣無庸置疑,他跟費曼以及無數生還者有著相同的想法。維森塔爾這樣寫道:「我極度渴望復仇。」費曼澈底證實這一點。他不久後在奧地利遇見維森塔爾,開始跟他合作展開一些行動,追捕納粹罪犯。「他戰後離開集中營,滿心憤恨,毫不留情向納粹罪尋仇雪恨。」費曼寫道。
維森塔爾獲得解放後的第一次經驗,並沒有刺激他做出費曼承認的那種殘忍行為。他仍舊太過虛弱,連思考怎麼攻擊人都沒辦法,而且就算他想採取報復行動,也沒能力。再說,從一切跡象看來,很快地,復仇就不是唯一他渴望實現的目標。
但是,戰爭結束後,敵我角色互換,他跟費曼一樣大感震驚,以前折磨他的人竟然一下身分就變了。他在毛特豪森恢復自由身、可以到處走動時,被波蘭營區一名模範囚犯攻擊,無緣無故被打;那個人以前當囚犯時享有特權。維森塔爾決定向美國人舉報這件事,他正準備提出申訴時,看見美國軍人在審問黨衛軍。一名格外凶殘的守衛被帶進房間時,維森塔爾本能轉過頭,希望那名守衛不會注意到他。
「每次看到這個人,我的脖子後側總是會直冒冷汗。」他回憶道。不過接下來發生在他眼前的事情,令他無法不懷疑自己是否看錯了。「那名黨衛軍被一名猶太囚犯押解入房,渾身發抖,我們以前在他面前就是那樣發抖的。」那個人以前讓人破膽寒心,現在「竟然成了驚恐又可恥的懦夫⋯⋯原來超人一旦沒有了槍護身,就變成懦夫。」
維森塔爾立刻做出決定。他走進毛特豪森的戰犯辦公室,向一名中尉主動提議想幫忙。那名美國人狐疑地看著他,說他沒有相關經驗。
「對了,順便問一下,你多重啊?」美國人問道。
維森塔爾說自己五十六公斤,也就是一百二十三磅,中尉聽到後笑了起來。「維森塔爾,去休息一陣子,等你真的有五十六公斤時再來找我。」
十天後,維森塔爾回來了,體重稍微增加了,但是仍舊遠遠不夠。他用紅紙擦臉頰,想掩飾蒼白的膚色。
中尉顯然是被他的熱忱打動,把他派給塔拉柯西歐上尉,不久後,維森塔爾就跟塔拉柯西歐上尉前去逮捕一個名叫施密特的黨衛軍守衛。他得走到屋子的二樓抓施密特,但如果施密特反抗,維森塔爾就無計可施,因為他爬完樓梯就氣力用盡,渾身發抖;他也可能是因為擔心即將發生的事而發抖。不過施密特也在發抖,維森塔爾坐下來喘氣片刻後,扶他走下樓,下樓梯時,那名黨衛軍抓著維森塔爾的手臂。
他們走到吉普車,塔拉柯西歐上尉在車上等待,黨衛軍守衛突然哭求饒恕,辯說自己只是小嘍囉,而且幫助過許多囚犯。
「是啊,你幫助過囚犯。」維森塔爾答道,「我經常看見你。你幫忙把囚犯送進火葬場。」
維森塔爾說,自己就是這樣開始幹納粹獵人這項差事。他永遠不會搬到以色列,儘管女兒、女婿和外孫現在都住在那裡,他依舊不嚮往。後來,以色列人打算要去抓艾希曼,讓這名猶太大屠殺的主謀之一受到法律制裁,那時維森塔爾有跟以色列人合作,但彼此也曾針鋒相對。
維森塔爾和費曼都說,自己幾乎立刻就開始追捕艾希曼,此人可是策動大規模將猶太人遣送到奧斯威辛等集中營。不過在戰後的初始階段,各界主要訊息焦點都是關於已經被逮捕的人或比較容易逮捕的人,以及他們被捕後的審判過程。追捕納粹和懲罰納粹仍舊主要是戰勝國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