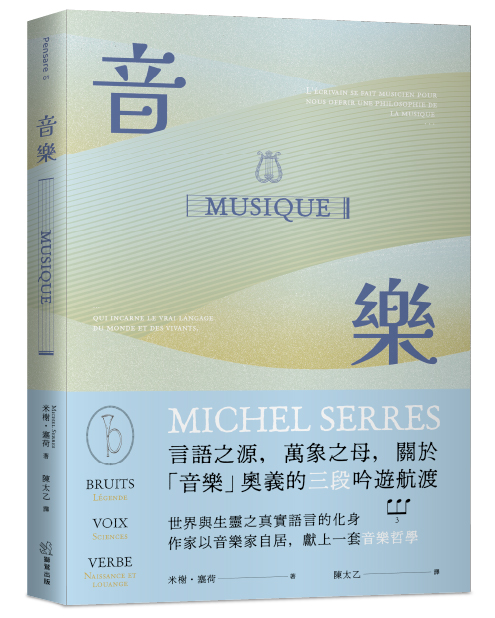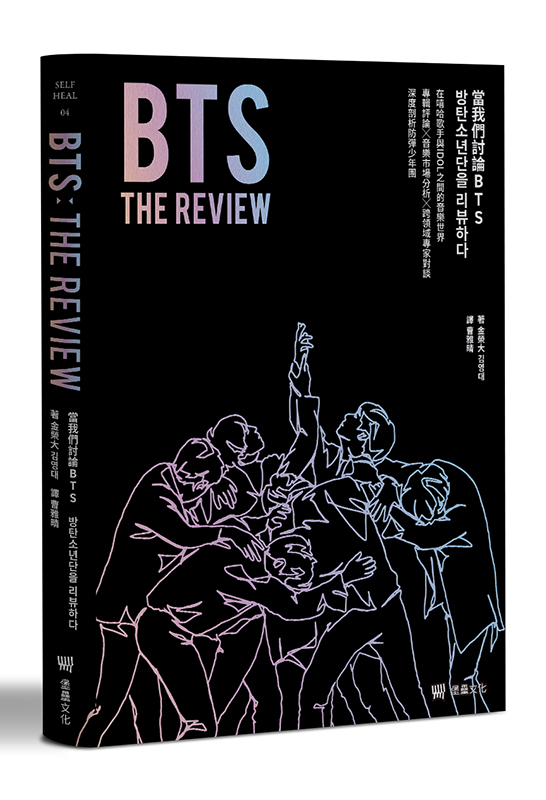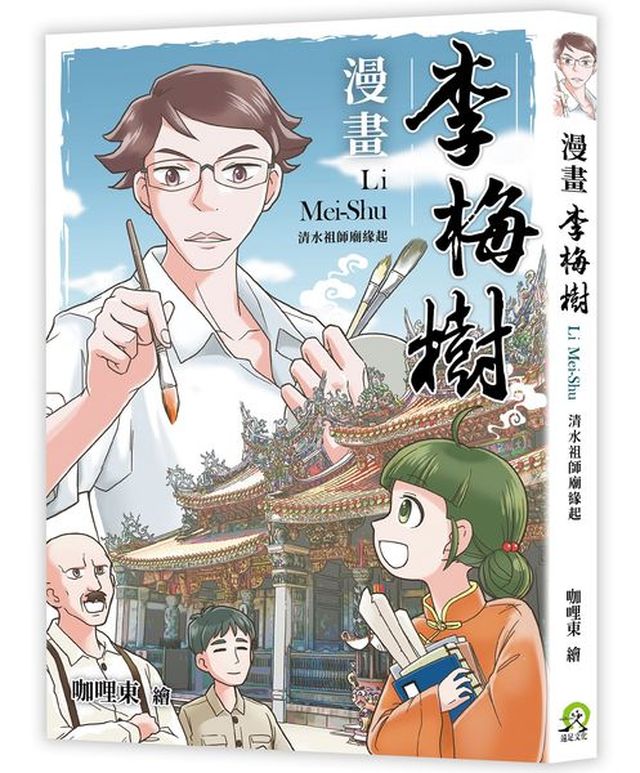★《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智生活》(Intelligent Life)雜誌最受歡迎專欄集結
作家遇上博物館——這些博物館不僅啟發了他們,甚至還改變了他們!
巴黎羅丹美術館、哥本哈根托托瓦爾森博物館、巴黎玩偶博物館、札格瑞布心碎博物館、牛津大學皮特‧瑞佛斯博物館、墨爾本維多利亞國家美術館、波士頓美術館……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博物館不計其數,唯獨這24家博物館是無可取代的。
博物館提供了大大小小成千上萬個剎那間的領悟。
博物館是我們能夠發現過去,反思對世界的了解,並能夠引領我們展望未來、重新獲得洞察力的地方。
透過本書,博物館被個人化了,更成為珍藏情感的載物——全球24位文采斐然的頂級作家(包括曾獲曼.布克獎的作家朱利安.巴恩斯、英國極富盛名的兒童文學作家賈桂琳.威爾森等)娓娓道來全世界最震撼他們的博物館和奇遇,將他們最珍視、意義最重大的啟發,分享給讀者。
編選者簡介
瑪姬.佛格森
曾任《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生活雜誌《智生活》(Intelligent Life)文學編輯。她著有兩本傳記作品《喬治.麥凱》和《麥克.莫波格:從戰火裡的孩子到戰馬》。
作者簡介
世界知名作家24人: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威廉.波伊德(William Boyd)、約翰.伯恩賽(John Burnside)、法蘭克.考崔爾—波伊斯(Frank Cottrell-Boyce)、羅迪.道爾(Roddy Doyle)、瑪格麗特.德拉波爾(Margaret Drabble)、阿敏娜妲.佛納(Aminatta Forna)、艾倫.霍林赫斯特(Alan Hollinghurst)、約翰.蘭徹斯特(John Lanchester)、克萊兒.梅蘇德(Claire Messud)、A.D.米勒(A. D. Miller)、麥克.莫波格(Michael Morpurgo)、安德魯.莫遜(Andrew Motion)、安德魯.奧海根(Andrew O'Hagan)、愛麗絲.奧斯維德(Alice Oswald)、安.派契特(Ann Patchett)、唐.派特森(Don Paterson)、艾利森.皮爾森(Allison Pearson)、艾莉.史密斯(Ali Smith)、羅利.史都華(Rory Stewart)、馬修.斯威特(Matthew Sweet)、賈桂琳.威爾森(Jacqueline Wilson)、提姆.溫頓(Tim Winton)、安.若(Ann Wroe)。
周曉峰
國立清華大學畢業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工程碩士、博士 ,普林斯頓大學研究員,在美三十餘年,擔任自動控制主管及研發主管。雖長期從事理工方面的工作,卻熱愛文學與藝術,餘暇時寫詩作畫。曾出版中英文詩合集。多首英詩發表於2014, 2015, 2016及2018年世界詩人大會詩選 (Anthology of World Congress of Poets) 。
沈聿德(Yuhder S. Odenkirchen)
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研究所畢業後,在台灣私立科技大學任教了十五年。隨後離開教職,帶著狗兒子Kodomo的骨灰和一隻活蹦亂跳、名為沈子恩的流浪犬,搬到美國舊金山北灣區,結婚定居,適姓Odenkirchen。目前為自由譯者,從事口筆譯的工作。除了本書《珍愛博物館:24位世界頂級作家,分享此生最值得回味的博物館記憶》之外,還有《管書的意外人生:監獄圖書館員歷險記》、《新譯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少女心事解碼》、《校園對話》、《低級教育》(預計2019年出版)、《如何當一個比較快樂的爸媽》(預計2019年年底出版)等其他譯著。
繪者簡介
朱疋
專職平面設計,兼職插畫,喜歡慢跑跟貓,不吃早餐。
前言 尼可拉斯‧塞羅塔(Nicholas Serota),泰特美術館館長
序 瑪姬.佛格森(Maggie Fergusson)
導讀 周曉峰
導讀 沈聿德
暗藏生命的牆壁
紐約下東區移民公寓博物館
羅迪.道爾
石中羅丹的十四行詩
巴黎羅丹美術館
艾利森.皮爾森
坐危不亂
喀布爾阿富汗國家博物館
羅利.史都華
櫃子裡奇妙的珍藏
牛津大學皮特‧瑞佛斯博物館
法蘭克.柯翠爾—波伊斯
石之畫
佛羅倫斯半寶石博物館
瑪格麗特.德拉波爾
大都會的聖殿
紐約弗利克博物館
唐.派特森
卡普里之翼
卡普里聖米歇爾別墅
艾莉.史密斯
不再被拒於門外
墨爾本維多利亞國家美術館
提姆.溫頓
戰爭的悲憫
伊珀法蘭德斯戰場博物館
麥克.莫波洛
愛,喜迎我到來
麻省劍橋哈佛自然歷史博物館
安.派契特
哥本哈根的雕刻師
哥本哈根托瓦爾森博物館
艾倫.霍林赫斯特
娃娃的宮殿
巴黎玩偶博物館
賈桂琳.威爾森
奧德薩之愛
奧德薩州立奧德薩文學博物館
A.D.米勒
微笑的水仙子
賽倫塞斯特科里尼翁博物館
愛麗絲.奧斯維德
子與母
奧斯坦德恩索爾故居
約翰.伯恩賽
如家自在
波士頓美術館
克萊兒.梅蘇德
西貝流士的沉默之鄉
耶爾文佩艾諾拉故居博物館
朱利安.拔恩斯
華玆華斯永恆之光
格拉斯密爾鴿屋
安.若
痛苦至狂喜
馬德里普拉多美術館
約翰.蘭徹斯特
心碎博物館
札格瑞布失戀博物館
阿敏娜妲.佛納
沉默的劇場
倫敦約翰.里特布賴特爵士珍寶館
安德魯.莫遜
利奧波德的先見之恩
維也納利奧波德博物館
威廉.波伊德
謝謝你們的音樂
斯德哥爾摩阿巴合唱團博物館
馬修.斯威特
格拉斯哥的夢想宮殿
格拉斯哥凱文葛羅夫藝術博物館
安德魯.奧海根
前言
尼可拉斯‧塞羅塔(Nicholas Serota),泰特美術館館長
我們可以在博物館裡,發現過去,反思自己對世界的了解,同時,還能從中洞悉你我未來將何從何去。詩人艾略特(T. S. Eliot)就曾告訴我們:
「 眼下與以往的時空
或許都存在於未來吧
他還提醒世人,我們「對過去的『理解』,理當受到當下的影響,一如當下,也步步受控於過去」。
過去五十年以來,歐美各博物館的造訪人次呈現巨幅成長,這個現象一部分是因為大眾旅遊的興起。博物館的規模變大、數量增多,一棟棟誇張的博物館新建築,滿足了我們對奇觀與新奇體驗的渴望。1997年,在西班牙的畢爾包市(Bilbao),建築師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完成了古根漢美術館分館(Guggenheim Museum Bilbao)的建造,自此建立了一個新的標竿,激勵了世界各地小城鎮也想有樣學樣的野心。
然而,從這本書裡的各篇文章裡,我們會了解到,博物館的大小,只與拍照時占去底片多大面積有關,大小幾乎從來都不是重點。2012年時,土耳其作家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在伊斯坦堡(Istanbul)創立了與他2008年出版的小說同名的「純真博物館」(Museum of Innocence),當時他想表達的理念,就是要讓世人知道,博物館不應該是浮誇的,而應該以人為規模,最重要的是,博物館是很個人的。他在《文物的純真》(The Innocence of Objects)一文裡宣示了博物館的意義,寫道:
有著大門大廳的大型博物館,向我們喊話,要你我拋卻人性,張開雙臂迎接接踵穿梭的群眾……但一般的個人日常生活故事,才更饒富涵、更具人性、更令人快慰……博物館非得規模變得更小、更具個人性,還要更便宜不可。這才是博物館以人的規模訴說故事的唯一方式。
在這本選集裡的作者當中,只有極少數的人,偏好大型或館藏浩繁的博物館的參觀經驗。這或許反映出我們會想廣邀各知名作者,以博物館為題,寫出一篇回溯個人經歷的短文的原因。然而,這無疑的也揭露了非常多人的共同看法——最值回票價的博物館遊歷,不外乎是參觀者與單一展物間建立出的特殊情感連結有關。當我站在一間展覽室,眼前面對的是一座西元前五世紀的雕像、一幅五百年前的畫作,或是某位在世的藝術家的影像裝置作品,我感受到那個共享空間中作品的形式與重量、畫布上奔放的色彩、畫筆的筆觸,或是那張紙上線條的輪廓。
這些,都是另一個人創造的作品,紀錄了他∕她對世界的感知或感動,也記錄了他∕她的信念,這些從而再轉化為我們自己的當下。就是這樣的強度,這種無法透過互聯網感受到的強度(即便Google有辦法將偉大巨作的細節放大,擁有絕對能讓人看得神迷目炫的功能,也沒有這樣的強度),驅使你我成為博物館裡人類創作作品的見證者。細細觀察,偶爾甚至還可能把展物拿在手中的那種經歷,只能意會,無法言傳,是觸覺與空間的感知。我們透過另一個有創造力的人類的視野,擺置自己於時空當中。一一加累,博物館提供了大大小小成千上萬個剎那間的領悟。
或許我們會注意到,本選集中,少數作者選定以大型城市裡最享負盛名的博物館為文。那麼,動身尋找某間地處偏遠的小規模博物館,便能以一種朝聖之旅的形式,提升參訪經歷和念想。小型博物館往往是我們得以將自己從日常生活步調中抽離出來而檢視自我,或探索他人觀點的地方。這些行為,得靠你我找出時間才可以執行,但也因為這些行為,提供了我們反省與沉思的時間。博物館,在這個被貿易與商品牽著鼻子走、被流行與新奇事物主導的世界裡,已然成為價值存續的地方。它們在族群概念或共有空間愈發罕見的現今社會中,提供了一個共享經歷的去處。博物館可以是表達各種想法的平台,能提供灼見真知,讓我們了解文化造就或因應社會變化的方式。在二十一世紀,最棒的博物館,會創造出對話、辯論和想法交流的空間,同時也會創造出指引方向的空間。就跟大學一樣,博物館可以驗證假設,但它們同時還能吸引一群衍生出某種信任感和族群性的大眾,這在學術機構中是相當罕見的。
我們也許很訝異,那些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晚期頂尖建築師手下的博物館建築作品,受到大眾如此的關注,但本選集中,卻只有寥寥可數的文章,把重點放在博物館建築的來龍去脈上。艾倫‧霍林赫斯特(Alan Hollinghurst)到哥本哈根(Copenhagen)托爾瓦森博物館(Tholvalsens Museum)的遊記,算是例外之一;不過,整體而言,作者們紀錄的是他們跟展物間的關係,而不是跟建築物本身的關係。然而,隨著博物館變成群眾聚集之地,又是反省沉思之所,建築物的形式,不可避免的也會隨之演化。博物館作為觀看的空間和社會活動空間兩者間的平衡,會有所變化。過去五十年來,透過引進教室、講堂,甚至到後來還有商店、餐廳、咖啡館、以及「舉辦活動的空間」,我們已經見證了博物館的重大改變。接下來的二十年,博物館還會進化成舉行研討會、辯論會、對話討論,還有實作活動的空間。「學習」將不會只侷限於教室或講堂裡,而是會發生在博物館建築中的各個角落,把你我,從巍峨殿堂帶向公會論壇:在這一個民主的場域,所有的人,得以從彼此,從我們的現在,乃至我們的過去當中,學習精進。話雖如此,近距離觀看展物和藝術作品的獨特經歷,依然會是博物館最重要的標準定義。也正是這種獨特經歷,持續刺激了許多作家天馬行空的想像,而我們何其有幸,在隨後的篇章裡,分享他們的點滴洞察。
序
瑪姬.佛格森(Maggie Fergusson)
有些人在洗澡時會靈光一現;提姆.德.萊爾(Tim de Lisle)則是在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想出他最了不起的其中一個點子。時值2008年春天,即將接任《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智生活》(Intelligent Life)編輯的他,陪十歲的女兒參加大英博物館舉辦的中國新年活動。雖然兵馬俑展的票已經賣完了,不過他們循著掛燈籠的步道,邊走邊看著中國戲劇團的表演,瀏覽搖身一變被布置成一個超大炒鍋的大中庭裡各式各樣的攤子,改用這樣的方式自娛。
那天是大英博物館史上入館人次最多的一天。總計有三萬五千位訪客通過票閘口,館方後來不得不關上大門,這可是繼一八四八年憲章工運暴動事件(Chariot riots)後的頭一遭。
提姆突然意識到,他小時候根本不可能發生這等情事。他回憶道,回溯到1970年代,博物館「基本上是個陰沉的地方:滿布塵埃、霉味陣陣,又密不通風。」他記得在某個下雨的週日午後,他被父母拽著去參觀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V&A)(「披在無頭人體模特兒身上單調乏味的老舊罩袍」)、帝國戰爭博物館(Imperial War Museum)(「嘈雜、混亂又無聊至極」),還有自然歷史博物館(Natural History Museum)(「天殺的一具又具的人體骨骼」)。
然而在他和女兒的童年相距的這三十餘年間,博物館吹起了改造之風。它們甦醒了過來,不再陰沉而內斂,而是變得輕快又喜迎造訪。羅浮宮(The Louvre)建起了玻璃金字塔,而大英博物館的大中庭變身為一個玻璃的甜甜圈。
被這所有的一切所啟發,提姆想出一個新的主題系列,名為「作家寫博物館」,其構想簡單,但強而有力。每一期的《智生活》都會找一位作家——而非藝評家——要對方重訪自己生命中意義重大的博物館,寫下喜歡(或不喜歡)那個博物館的事由,交織成回憶錄的一絲半縷。
幾年之後,我接下了這個系列的委任工作。我碰過一些回絕邀稿的有趣經驗。蘿絲.崔梅(Rose Tremain)解釋,她不喜歡博物館的理由,和她討厭新年的派對聚會是一樣的——「我覺得在非常緊迫的時間裡,被要求做出合宜的情感表達和聰明的回應,就像遭致囚禁一般」;理查.福特(Richard Ford)則坦承,他給自己「約莫四十五分鐘的時間逛展區,但之後地面就會變得具體,讓他的眼神無法聚焦」;大衛.塞德里(David Sedaris)承認,他就不是個喜歡去博物館的人,但他「是個滿愛逛博物館禮品店或流連博物館咖啡廳的那種人」。
話雖如此,作家們往往都還是很有意願再次造訪那些博物館,且在今年稍早、本主題系列結束之前,已經有三十八位作家撰寫了關於啟發他們的博物館的文章——當中甚至還有幾例,改變了他們的人生。各個作家的選擇包羅極廣,從莊嚴的約翰.蘭徹斯特(John Lanchester)筆下的普拉多博物館(Prado),到家庭式的羅迪.道爾(Roddy Doyle)筆下的紐約下東區移民公寓博物館(Lower East Side Tenement Museum),還有風格詭異的博物館,阿敏娜妲.佛納(Aminatta Forna)筆下,位於札格瑞布的心碎博物館(Museum of Broken Relationships)。然而,統一這些眾多選擇,同時賦予其特殊性的,是文章的品質。
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審慎考慮,要將哪些文章收錄本書中,而我們認為精選出的二十四篇都是上乘之作。希望讀者和我們一樣,也喜歡這些文章。
瑪姬.佛格森(Maggie Fergusson)
導讀
周曉峰(譯者)
本書由二十四位英美著名的作家,介紹二十四個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其中有些博物館世界知名,有些博物館鮮為人知,但都很有特色,主題包括繪畫、建築、雕塑、詩歌、文學、音樂、宗教以及文化。每篇文章都寫得精采,文筆典雅。筆者負責翻譯其中的十二篇,在此謝謝王怡文女士在翻譯過程中的多方協助和一些很好的建議。
這些文章裡談的較多的是繪畫,涉及的畫家有文藝復興時期的皮耶羅(Piero Della Francesca)、貝里尼 (Giovanni Bellini)、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十七世紀荷蘭畫派的維梅爾(Johannes Vermeer);十八世紀洛可可畫派的弗哥納(Jean-Honore Fragonard) ; 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的康斯特勃(John Constable)、透納(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ner);十九世紀寫實主義柯洛(Camille Corot);十九世紀新古典主義的昂格拉(Jean Ingres);印象派的竇加(Edgar Degas)、雷諾瓦 (Pierre-Auguste Renoir)、沙金(John Singer Sargent);到二十世紀表現主義的席勒(Egon Schiele) 、培根(Francis Bacon)、弗洛伊德(Lucian Freud)。這其中維梅爾生前清苦,死後兩百年才獲肯定。席勒生前沒有賣出一幅畫,二十八歲過世,死後五十年才被認定是天才。難以想像藝術評論家以及藝術史學者會錯得如此離譜。建議讀者在網路上查看維梅爾的《花邊女工》(The Lacemaker)和《軍官與微笑少女》(Officer and Laughing Girl)以及席勒的兩幅自畫像,《自畫像——傾斜的頭》和《自畫像——冬天的櫻桃》,都是經典之作。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畫風的變化風起雲湧,創作豐富琳瑯滿目。作者唐・派德森卻說文藝復興時期喬凡尼・貝利尼(Giovanni Bellini)的宗教作品《沙漠裡的聖・法蘭西斯》(St. Francis in the Dessert)深深的打動了他。現代畫充滿了視覺上的創新,題材千變萬化,非常吸引人。創新固然重要,但是畫要有生命,最重要的是要有深厚的信念或者信仰。貝利尼的藝術作品,無論是繪畫雕刻或建築,都感動人,是因為他有深厚的信仰。
愛諾拉博物館原來是挪威音樂家西貝流士(Sibelius)的舊居,西貝流士建造此屋時幾乎破產。西貝流士的音樂非常的冷,和同時期的阿諾・荀伯克 (Arnold Schoenberg)的音樂同樣的冷,不過前者是一種北國天寒地凍的冷,後者是心靈上的冷。西貝流士生命的最後三十年保持沉默,不再寫一個音符。1940年代的初期某一天,他將第八交響樂的草稿,和一堆未完成的作品,全都丟進火爐裡。他從此變得更平靜更樂觀。他的心裡總縈繞著家居附近的天鵝、鶴、大雁,牠們的身影和叫聲,比任何音樂文學或藝術更能打動他。創作固然是美好的事,完全的看透也是一種美。
大英圖書館的約翰・瑞布萊特爵士珍藏館,專門收原稿或者手稿,包括有披頭四 (Beatles)歌曲的原稿、希臘文新舊聖經最重要的手稿、韓國的《佛教花環經》(Garland Sutra)手稿、《英國大憲章》(Magna Carta)的原稿、史詩《貝爾武夫》(Beowulf)的手稿、湯瑪士•哈代(Thomas Hardy)的《黛斯姑娘》的初稿。原稿或者手稿,對於作者、讀者都有很大的啟發性, 甚至有某種神祕的魔力。
英國詩人威廉•華茲華斯在1799到1808年間住在格拉斯米爾的多弗小屋,這一段時期華茲華斯生活清苦簡單,小屋四面環山,他在山坡地上種菜,在附近的小溪漫步。小溪是他靈感的泉源,他寫下了很多好詩。多弗小屋已成為紀念他的博物館。華茲華斯的詩清新樸實,和他的多弗小屋一樣,是一個純淨的世界,有星辰、彩虹、蒲公英、畫眉,沒有過分複雜的情緒或深奧的思索。他是浪漫派文學代表性的人物,歌誦大自然的美。詩裡深沉的信仰和靈巧的韻腳有寧靜的美,很迷人,有點像喬凡尼・貝利尼的《沙漠裡的聖・法蘭西斯》,能安撫現代人忙亂的心境。
這些博物館有些你也許聽說過,有些你甚至去過,有些你聞所未聞。作者們都提供了豐富的資訊和深刻的見解,文字雋永,條理分明。閱讀此書,也許比你親自造訪這些博物館會有更多的收穫。如果你到歐美旅遊,建議你先參考這本書,也許安排參觀某些書裡談到的博物館,旅遊會更豐富,更有趣。
導讀
沈聿德(譯者)
《珍愛博物館:24位世界頂級作家,分享此生最值得回味的博物館記憶》一書一共有二十四篇散文,是《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生活雜誌《智生活》(Intelligent Life)的編輯群,從多篇以作家介紹博物館為題的專題文章中,精挑細選而成的作品集。名家寫作,詞情並備兼具,下筆為文,或論理、或抒情、或敘事,無一不屬上乘;筆者能翻譯其中十二篇,感到十分榮幸。
本書中,作家們挑選的博物館主題各異其趣,上自古典藝術的巨擘創作、下至大眾文化的流行音樂,應有盡有;作家們心有所屬的博物館也各自有別,從巍峨壯觀的國家型大型館件、到精巧迷你的私人收藏屋,一應俱全:還有,作家們撰文抒發自己與博物館之私密連結的理由更是不一而足:有親情、愛情、友情、對年少記憶的緬懷、對戰亂與和平的反思……等,包羅萬象。
然而,即便書裡各家羅列的博物館,規模、內容、與知名度都大不相同,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它們被個人化了;在這些名家筆下,博物館不再是一棟棟仰之彌高的冷峻建築,而館藏珍品也不再是受眾人仰望且難以親近的文物瑰寶,博物館成為某種個人情感的載物,而展品就此和參訪者有了更細微且私密的互動關係。
人們在談後現代(post-modernity)的時候,常常提到一種大敘事(grand narrative)結構的瓦解。在中文的翻譯裡,「博物館」這三個字,總讓人聯想起一種包山包海、連古串今的文物陳列方式;《智生活》的編輯當初在構思「私房博物館」這個主題的時候,就是希望能重新思考博物館的定位,重新定義參訪群眾和這龐大的文物保存與展覽制度間應該建立的互動關係。透過這些作家筆下的個人經驗,讀者得以一窺不同博物館及其館藏在每個作者心目中大相逕庭的私人意義,例如:「移民公寓博物館」(Lower East Side Tenement Museum)裡某個移民家庭深埋數十載的秘密、「皮特‧里佛斯博物館」(Pitt Rivers Museum)裡阿富汗難民用殺蟲劑空罐子做給孩子的飛機、「心碎博物館」(The Museum of Broken Relationships)裡彷若已逝戀人心跳頻率而閃著紅光的狗項圈、「墨爾本維多利亞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替鄉下孩子帶來的文化衝擊與震撼及其幾十年來策展方式與展覽內容的改變、「阿巴合唱團博物館」(ABBA: The Museum)的大眾流行音樂在文化符號學與世界政治潮流上的意義……等。
這一切,讓我們感受到,博物館連同其內的文物展品,有了生命,彷彿從展台底座上走了下來,和觀者間產生了一種無形卻有意的互動,時而短暫即逝,時而深遠雋永。在這樣的意義變動中,博物館的大敘事架構被拆解了,成為一個又一個獨立的小故事;而博物館甚至可以不需背負著必然山包海匯、蒐羅古今、專收精緻藝術(high art)的刻板印象,重新尋回其字源(古希臘語mouseion)的意思--它應該是研習、學習之處,是研習藝術詩歌之所。參觀博物館的你我,就應當看見博物館的微、小、個人化,重新打造有別以往的觀展經驗。
近年來,台灣人出國自助旅遊的風氣漸盛,而台灣本身從政府到民間,推動本地觀光的口號也打得震天價響。這本《私房博物館》裡每篇就文化底蘊上深入淺出的介紹文,除了可以作為出國旅遊安排行程時的又一參考,也能補強讀者對特定領域略嫌不足的背景知識;此外,筆者以為,本書介紹的許多博物館,還可以提供台灣推動文創與觀光的另一個思考方向——將「觀看」與「體驗」個人化,在參訪者與遊客身上,留下獨一無二且亙久綿長的深刻記憶。最重要的是,這本書收錄的每一篇散文都自成佳作,彷彿二十四件坐落書中的展品,掀開扉頁的當口,我們也就步入了你我的「珍愛博物館」吧。
心碎博物館
札格拉布市失戀博物館
(THE MUSEUM OF BROKEN RELATIONSHIPS, ZAGREB)
阿米娜妲‧佛爾納(Aminatta Forna)
我走進展間時,有一對本來在接吻的男女,迅速地分了開來。男生走到小展間的另一頭去欣賞那兒的展品;女生則仔細讀著她面前的展品說明。男生穿了一件帽T;女生則斜揹著一個紅色的包包。由於他們倆人看起來很年輕,感覺上不太可能是見不得人的第三者關係,所以,也許是我走進來讓他們不好意思了吧。
他們離開之後,我端詳了原本他們在看的展物。那是一個烘蠶豆的器具。標示上寫著:「在埃及,有句俗話說,蠶豆最好是加熱後再上菜。我們的感情,從來沒有升溫,但我們的友誼,還是像乾的蠶豆一樣堅硬。」標籤說,那段感情從1990年維持到1991年,這麼算來,跟好跟克羅埃西亞的獨立戰爭一樣長。我在想,這兩件事是不是有所關聯--建立這段愛情的原因、或之所以不再提起這段愛情,或是說,這段感情沒能開花結果,是否與戰爭有關呢。
展間另一頭的牆上,是1980年代晚期某位17歲的女孩送給她已婚愛人的刮鬍組。這位已婚男人把刮鬍組捐贈給博物館時,寫道:「我希望她不再愛我了。我希望她不曉得,她才是我這輩子唯一愛過的人。」
博物館裡幾乎所有的東西——漆成白色的一間間展廳裡打了光的展示桌上,動物布偶娃娃、瓷製的狗狗、綢緞佯裝、外套、帽子、書籍、塑膠或玻璃或陶瓷製的裝飾品、相本、手錶、時鐘和居家用品--都重複著一樣的訊息:愛情最後的結果是失去。愛情最終的結果,一定就是失去。只有那個還放在原裝盒子裡的烘蠶豆器具,告訴你我,沒有實現的愛,還可能造就某種幸福。
我第一次逛到這間失戀博物館,是去年初夏的事;當時我走在札格拉布舊城區,要穿過格拉德,我來的目的是要為自己新小說《雇來的勤雜工》(The Hired Man)裡的角色做研究,書中人物搬到了這座城市來,而且有一天她們在都柏尼克飯店(Hotel Dubrovnik)用午餐。本來我一開始是靠著這座飯店和托米斯拉夫廣場(Tomislav Square)的文字敘述,想像出書中人物在那兒看著百年樹齡的樹被砍掉的場景。之後,我跟先生來到札格拉夫,實際走一次這場景,確認我的描述屬實。廣場離飯店很近,比我想像的近得多,不過,從札達爾(Zadar)開車到札格拉布得花好幾個小時,等我們到的時候,想在飯店用午餐都太晚了。我們只好在舊城區裡亂逛,走在聖馬克廣場(St Mark's Square)下方的街上,無意中看到了這座博物館。
進來的右手邊,有一間小的咖啡聽,左手邊則是售票處和紀念品商店。在你跟前則有一連串的展廳,每一間都有自己的名字。有的展廳名字聽起來很了不起、很花俏——《距離的誘惑》(Allure of Distance)、《慾望的衝動》(Whims of Desire)。在展廳《盛怒與暴怒》(Rage and Fury)右轉,穿過展廳《時間的潮汐》(Tides of Time),你就會走進展廳《穿越的儀式》(Rites of Passage),跟著走接下來就會到展廳《家庭的矛盾》(Paradox of Home)(我就是在這裡發現那對有罪惡感的愛侶)。如果你不這麼走,而是直接穿過展廳《盛怒與暴怒》的話,會來到展廳《悲傷的回音》(Resonance of Grief),然後是最後的展間《讓歷史封印》(Sealed by History)。舊城區的這一邊,主要是市政大樓,博物館裡這些鋪設石頭地板的展間,之前可能都作為辦公空間之用。展廳《悲傷的回音》裡面牆上都是老舊的白瓷磚,看起來這兒以前搞不好是廁所。
每一件展品的旁邊,都有一個標籤,指出該段感情發生於何時,而且會提供捐贈者對這個禮物的說明。因此,在第一個展廳裡,有一雙黑皮靴,牆上的標籤就寫道:「摩托車騎士靴。1996-2003。克羅埃西亞札格拉布市。在我和安娜一起去巴黎玩之前,我買了這雙靴子給她。之後,也有其他的女生穿過這雙鞋,不過這始終是安娜的靴子。」
這座博物館的創辦人歐琳卡‧維斯蒂卡(Olinka Vistica)和德拉任‧格魯比斯奇(Drazen Grubisic),曾經是一對相愛的戀人。幾年前某個炙熱的夏天,他們不再相愛,開始劃分公寓裡屬於彼此的東西。雖然他們的分手,友好平和,即便如此,卻也沒讓人比較不難過,因此,他們開始一起整理各個房間的東西,細細分析彼此對這段感情共同的回憶。杯子、CD、菸灰缸、咖啡豆研磨機、平底鍋、地毯、書籍、徽章、還有圍巾等等:「就算是最不起眼的物品〔也有〕背後的故事。」這些是所有立意良善的朋友、每一本心理自助手冊、任何一本提供建議教人家怎麼從失戀走出來的雜誌文章,都會力勸面對像這對分手情人一樣狀況的人,要丟掉、燒毀、破壞、或捐給慈善團體的東西--無論如何,處理掉就對了。愛情結束時,絕對不要有會讓你想起這段感情的東西。但是這對男女,並不想做這樣的事。有別於心理自助手冊提倡失去對象的悲傷戀人們要破壞物品,他們他們決定提供另一種選擇,策劃一場巡迴展,展出大家捐贈出來的物品,讓大家有機會創造一場儀式--「透過創造,克服情緒崩潰的機會」,一如安娜的皮靴上方所印製的標籤說明,告訴初來乍到的參訪者那樣。在那之後,第一批收藏的展品數量已經翻很多倍,它們在札格拉布找到了一個長久的落腳處。還辦了世界巡迴展覽,一邊到各地展出一邊收集物品,讓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和柏林(Berlin)、開普敦(Cape Town)、伊斯坦堡(Istanbul)、休士頓(Houston)、甚至是林肯郡(Lincolnshire)的斯利福德(Sleaford)這些地方遭致心碎、背叛、和失去摯愛的人門,有機會分享自己物品的故事。
我第一次造訪這裡時,覺得歐琳卡和德拉任,敲到了我們心中的某個點——那些讓你我再也受不了多看一眼的物品,到底能拿來做什麼?大家的家裡滿是各種戀物情節啊:代代傳承的東西、禮物、從遠地帶回來的物品,這一切東西都充滿了情感。在我的書架上,有一把從廷巴克圖(Timbuktu)帶回來的藍色茶壺、火爐壁架上有我鍾愛的教子送給我的一塊石雕,還有,廚房的吊勾上,掛著死去狗狗的項圈。這輩子,我們把這些累積出來帶有意義的東西,從一間房子搬到另一間房子,它們便是你我活過的物質證明:我們的回憶化為實際的存在。
我認識我先生的時候,他送了我一塊壓鑄的牌子,上面是西藏動物星座的圖樣,那是他旅行時買的東西。我把這塊牌子放在鑰匙圈上,到世界各地,我都帶著它;我在馬利共和國(Mali)買那個茶壺的時候也帶著它。為了謝謝他送我東西,我也回送了他我自己的護身符,那是來自獅子山共和國(Sierra Leone)黃銅製的小塑像,直到今天,他一樣也是把它掛在鑰匙圈上帶著。在我的小說《雇來的勤雜工》裡,有一個叫杜洛年輕男孩,他從初戀對象手中收到了一個心型的小陶瓷製品。往後幾年的軍旅生涯裡,他都把這個心型的陶瓷製品放在口袋中帶著,就連他的初戀後來嫁給了別人他還是如此。交換我們愛情的信物,是所有人都會做的事。
再次回到札格拉布,是冬天的事。從街道上鏟開的雪,高高地堆在空蕩蕩的停車場裡頭。戶外咖啡屋跟街頭小販,都不見人影了。我意外巧合地訂了都柏尼克飯店,在飯店裡面的咖啡廳裡,有戴著帽子、穿著外套的札格拉布市老市民們,喝著早晨的咖啡,我想這個習慣肯定都持續一段時間了,因為,這間飯店1929年便興建完成。
用完早餐後,不確定自己能否記得路的我,帶著地圖前往博物館。地圖領著我走了有別以往的路線,穿過大教堂,我順道繞了進去快速瀏覽了裡面的聖徒雕像,接著穿過了石門(Stone Gate),城拱下有一座聖母瑪利亞的聖壇。從旁一隅,有一位女士在賣蠟燭,另一位女士則站在被裝飾性鐵條圍起來的聖母像前禱告。1731年時的一場大火,燒毀了舊的木製城門和附近的一切,傳奇的是,唯獨這張聖母與聖嬰的畫像,倖存了下來,之後,大家便相信畫像具有神奇的力量。
這些禱告的人,跟那些站在博物館裡低著頭、雙手合十,慢慢的端詳著一件又一件遺物的參訪者,是多麼相像呢。那是週間某日的上午,博物館相對來說人煙稀少。只有寥寥可數的幾對年輕情侶,另外還有幾個中年婦女,巧心打扮得頗像法國人和義大利人旅行時會穿的那樣子。聽說博物館的遊客裡,十位有七位是女性,而且大部分都四十歲以下。
在第一間展廳裡,安娜那雙皮靴旁的展品,都是逝去的愛的回憶,那種不見容於新戀情裡的物品。裡面的氛圍,是懷念。隔壁展廳的東西,則帶著痛苦回憶--應該是先前戀情帶來的痛苦遠大過於甜密吧。在展廳《慾望的衝動》裡,水晶簾幕背後的牆上,掛了一對假胸,捐贈這個物品的女性說,在她離開前夫之前,每每兩人做愛時,前夫便命她戴上假胸。另外一把從柏林寄來的斧頭,原本女主人的女同志情人為了別人拋棄了她。她的女同志情人和新歡一起度假時,她買了這把斧頭。「她倆度假的那十四天裡,我用這把斧頭,每天劈她一件家具。」她把劈下來的部分仔細排好,等她的前任女友回來收拾自己東西時,再拿給她看。
後面的展廳有一張展檯,閃著紅光,吸引了我,於是我快步走了進去。之前被我撞見在接吻的那對情侶,正站在那張展檯前。他們互相用手勾著對方的腰,女孩子還把頭靠在男生的肩膀上。不久,當他們離開繼續看其他展品時,我遞補了上去,端詳那個閃著光的物品。
那是一則讓人落淚的故事。某對夫妻在一起十三年,當彼此的愛情淡化成友誼之際,先生離開了妻子。先生把兩人養的小狗狗留給了妻子,因為他覺得,太太比他更需要狗狗的安慰。幾個月之後,先生患了憂鬱症--至於這是否出他於對太太的思念,我們並不清楚。不過,無論這位先生的感受如何,他始終沒有再回到那段婚姻裡;倒是太太很擔心先生的狀況。有一天,先生收到太太寄來的一個包裹,裡頭有幾件小東西,他說:「〔那些東西〕一件比一件更讓我心碎,大多都是她出於想要照顧我的心意才寄來的東西,即便我知道,她才是那個飽受折磨的人。」在這些東西裡,有一個閃著紅光的狗項圈,當初太太買這個項圈給狗狗,是擔心狗狗會走丟。他倆分手後的那年,先生曾跟太太吐露,覺得「自己走丟了」。兩人分手一年之後,太太在一座陌生的城市找了間飯店入住;然後在那兒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先生說,那一閃一閃的光,會讓她想起太太的心跳。
在博物館裡逛著,讓我全神貫注的,就是像這樣的故事——令人不可置信、引人目不轉睛、又讓人難過不已的故事。之後,回想起這個地方,我發現自己的思緒又回到了那個比較沒有戲劇張力的展品:安娜的皮靴,或是第一段婚姻非常可悲、但現在第二段婚姻幸福美滿的女士所捐出來的婚禮相本。想想這些東西,我戒慎恐懼地感到充滿希望。這些東西好像告訴我們,無論那個過程有多痛苦、不管花了多久時間,人們還是可以了解自己、了解愛情。
穿過舊稱共和廣場(Republic Square)的耶拉奇契廣場(Jelacic Square),我邊走邊想,這個國家,雖然經過了多年的共產統治接著又遭受戰爭,但感覺上,在很多方面,它跟我1969年第一次來的時候,都沒什麼改變。雖然我當時只有五歲,但對那次的假期,確印象鮮明--我跟姊姊站在沙灘上,而母親和她的新婚丈夫,在離岸的木船上呼喊著我,要我游泳過去。我嚇壞了:我想要我的游泳圈,可是它在船上,船與我們之間,隔著50公尺的水。船夫當時不過八、九歲的姪子,一把抓起了我的游泳圈,跳下水,將游泳圈帶來給我。那場假期接下來的日子裡,他就是我的英雄。我之所以記得這些,是因為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對男孩子有那樣的感覺。
往後人生要學的,還好多好多啊。
心碎博物館
10000 克羅埃西亞 札格布拉市西瑞羅米托茲卡街2號
(Cirilometodska 2, 10000 Zagreb, Croatia)
櫃子裡奇妙的收藏
皮特・瑞佛斯博物館,英格蘭牛津
(Pitt Rivers Museum,Oxford)
法蘭克・科翠爾-波伊斯(Frank Cottrell-Boyce)
如果你走入皮特・瑞佛斯博物館,走近詢問台的桌子,服務員知道你會問:
「風乾縮小的人頭在哪裡?」
這些人頭是博物館裡的展覽明星,令人想起哈利波特。博物館人員對這些風乾人頭的態度是非常敏感的。如果你要照相,他們會說,什麼都可以照,就是不能照這些人頭。因為無論如何他們都是人類的遺體,應該獲得一定的尊重。我帶著敬畏的心,在這裡只做文字上的敘述,沒有照片。
博物館的第一層樓零亂、昏暗,但是令人著迷。展覽櫃上貼了一些標籤,例如:玩偶,占卜的神器,簧片樂器,還有你最想看的,處理敵人屍體的方法。整個展覽廳很像耶羅尼米斯・波西(Hieronymus Bosch)光怪陸離的畫作。十幾個風乾的頭顱吊掛著,怪異的浮在空中,像是釣起來的魚。其中一個頭顱頭髮零亂濃黑有點像隻拖把,猶如經過生化工程製作出來的活生生的披頭四的紀念頭像。另外一個,鼻子上穿了一個把手,就好像托爾金(J. R. R. Tolkien)的《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裡的道具,他們的容貌各有特色。毫無疑問的,如果他們的家人和朋友看到了會很容易認出他們。
製作者多半是厄瓜多人或是秘魯人。在1960年之前,土著部落蘇瓦人(Shuar)和阿曲瓦人(Achuar)長期的處於戰爭狀態,相互獵殺人頭,然後將人頭風乾縮小。這些人頭並不是戰利品,人頭風乾縮小是必要的過程,目的是將死者的靈魂融入征服者的家族。經過這個過程之後,這些人頭就不再有任何價值,一切大功告成。蘇瓦人和阿曲瓦人很高興的買賣這些人頭,也因此有些人頭最後到了博物館。這些人頭有如時尚品一樣熱門,有人買賣假貨。皮特・瑞佛爾(Pitt Rivers)本人捐獻了一件展覽品是用樹懒的頭顱伪造的。有些頭顱的來源竊自殯儀館。有的風乾的頭顱裡塞的不是熱帶雨林的植物,而是市區裡的舊報紙,這些頭顱當然都不是土著製作的。
這類人頭的展覽引發了我的疑問,究竟這些人種方面的展覽品有什麼目的?這種種奇特的展覽,能否加深我們對其他文化的了解,或是發現人類的共通性?或只是滿足我們相對於化外之民的優越感?我第一次到皮特・瑞佛斯博物館的原因,為的就是對這些蠻族的奇風異俗充滿了好奇心。八○年代,我是牛津大學的學生。為了引起一個女孩子的注意,我帶她去看風乾的人頭。我也會展現我自己溫柔感性的那一面,帶她去看精雕細琢的象牙球,這球有十一層,每一層像絲綢般精緻,層層相套,是用一整塊象牙雕出來的,真是奇妙極了。難怪她會嫁給我。當時整個牛津大學也有一種獨特的風情。我在學校的第一年有些反叛又有些茫然,不太能融入學校的生活。我不敢相信校園裡到處都如此美麗,也不敢相信可以毫無拘束的暢遊學校任何地點。我找到一個鮮為人知的路徑通過鬧區,穿過偏僻的廣場,又穿過隱蔽的迴廊,到了圖書館和別系的學院大樓,往迷宮的深處遊走。如果運氣好,就能隨意暢遊,沒有人阻撓我。也因此我找到了自然歷史博物館後面通往皮特・瑞佛斯博物館的一扇小門。
現在校園已經有清楚的路標,學校教職員的人數也大量增加。在我們那個年代,從明亮的牛津自然博物館闖入陰森的皮特・瑞佛斯博物館,膽子要夠大,它是一個小博物館巧妙的隱藏在另一個博物館裡面。你要勇敢的穿過很多扇門。有很多櫃子也有很多抽屜:我可以打開它們看看嗎?角落裡有一個蓋上布幕的玻璃櫃,我把布幕拉開,發現一件很寬大的紅黃相間的外袍,這是1830年為夏威夷女王(Kekauluoki of Lahina)特別製作的,使用了幾十萬隻紅黃色蜂鳥小巧的羽毛,由特定專人從每隻蜂鳥身上拔幾支羽毛,然後把鳥放走。每支羽毛都固定在一定的位置,才製成這件少數僅存的外袍。目前這種蜂鳥已經絕種。
就像一層層的象牙球,每件展覽品也是有一層一層的故事。一件展覽品初始是怎麼製作的,是一個故事。有一件展覽品是一個警察的護身符,是用舊的錢幣和一段繩子做的。1883年一個名叫坎培的強盜,在巴黎因強劫殺人罪被處絞刑,繩子是吊索的一部分,坎培臨死前向神父懺悔求上帝赦免他的罪,所以他身後遺物據說有靈驗的療效。另一件展覽品是印地安人的圖騰柱,一位海達(Haida)印地安部落酋長 ,因為收養一個女孩而製作的。我可以想像這女孩站在酋長的帳幕外,面對圖騰柱上家族黯淡的歷史,先人們經由圖騰柱上鷹的眼睛,熊的眼睛和水獺的眼睛,哀戚的看著她。
這些展覽品如何到了博物館,也有故事。有的時候展覽品的標籤上的說明很動人。有一件展覽品是斐濟人(Fijian)用抹香鯨牙齒製作的項鍊。1874年斐濟國王把項鍊送給卡佛牧師(Calvert)。多年之後卡佛的孫女為了紀念她的兒子,把項鍊捐給博物館,她的兒子是著名的英國飛行員卡佛(Pilot officer James Lionel Calvert),在1939年二次大戰時陣亡。博物館收藏了美麗的奈及利亞貝南城 (Benin)的銅製浮雕。1897年英軍攻佔奈及利亞的貝南城,破壞燒毀貝南城做為懲罰,竊取並拍賣了藝術珍藏品,將拍賣所得做為戰爭的賠款,這些美麗的銅製浮雕,輾轉到了博物館。
皮特・瑞佛斯先生本人捐贈了兩萬件藏品。他1827年出生,原名是奧古斯特・連福克斯 (Augustus Lane-Fox) ,原本是格納迪爾市(Grenaiers)的低階的政府官員,因緣際會下接收了一筆龐大的遺產,變成一個具有歷史性的收藏家。依遺囑裡的繼承規定,他將名字改為皮特・瑞佛斯。一般而言,每一間博物館的收藏都有些基本理念。這個理念也是博物館很重要的一部分,可以算是博物館抽象的無形的資產。這些理念有時比博物館的珍藏品更奇特甚至更不合時宜。皮特・瑞佛斯先生的理念複雜而不尋常,除了浮雕和風乾縮小的人頭,他蒐集的興趣一般不是戰利品或是珍貴之物,而是一些平凡無奇的東西。十九世紀大多數博物館的收藏涉及種族跟國家:比如說埃及文物、希臘文物、羅馬文物、維京文物等等。皮特河展覽的題材是錢幣、武器、馬鞍、狩獵等。風乾人頭和愛爾蘭武士的心臟一起展覽,心臟被鹽醃製過,放在心型鉛製的盒子裡,旁邊還有一個一次大戰的頭盔,和一隻矛,矛上插了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9的頭像。歐洲算命用的塔羅牌和非洲剛果占卜用的骨頭也放在一起。英國約克郡葬禮上使用的餅乾,和中國死者埋葬時的頭巾也擺在一起。
一般我們對於文化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從進化的觀點來看,另一種從相對的觀點來看。就進化的觀點,文化從原始文化慢慢演變成近代的文明文化。從相對的觀點來看,文化沒有所謂絕對的進步或落後,每一個文化都有自己的信念,在自己的文化裡發揮作用。皮特・瑞佛斯先生不是文化的相對論者,他是熱忱的達爾文進化論者。有些過分熱忱的基督徒,可能會把抽象的、精神上的狂熱投射在具體、現實的生活層面上;而過分熱忱的進化論者,甚至可能把具體的進化論套用在抽象的文化層面。皮特・瑞佛斯先生屬於後者,他將展覽分類成不同的類型,提出了一個科學的理論,叫做類型學(Typology)10,是指我們日常使用物品也像生物一樣,會逐漸的演化。當然他認為物品的演化在某些地區比較快,有些地區比較慢。他說類型學也像樹的枝幹一樣演進,有主幹也有分枝,所有研究大自然所遭遇的問題在類型學裡也有。
皮特・瑞佛斯先生主觀的認為西方文化是先進的,但卻從不考慮如何去證明這個論點。他認為我們生活周遭物品的進化非常慢,而激烈的政治軍事活動往往和物品緩慢的演進相衝突。為了克服這個問題,他主張改革人類社會的種種政治革命運動。
今天我們已經聽不到類型學的論點了,它不合時宜。這些展覽的文物給我們另外一種看法。整體的印象是,無論我們到了什麼地方,無論在南北兩極或熱帶雨林,我們都有創造的動力。不只在生存上要滿足口腹之欲,另外也渴望各種生活上使用的物品盡善盡美而且賞心悅目。在阿拉斯加偏遠地方,人們把海豹的腸子做成令人驚嘆的外衣。北美的印地安人用海鴨的嘴喙做成沙鈴(一種樂器):無論在沙漠地帶或是在冰天雪地,我們都會創造音樂。在非洲辛巴威共合國(Zimbabwe)11的城市裡,有人把回收的燈泡做成檯燈。在整個博物館最令我感動的東西,是1998年來自烏干達 (Uganda)難民營的一個小盒子。原來是裝殺蟲劑的鐵盒子,在難民營裡有人用鐵絲重新加工,加上一個塑膠鼻尖,就變成黃色的玩具飛機。即使在最惡劣的環境裡,我們也還能有夢,夢想與孩子們一起飛離難民營。
皮特・瑞佛斯博物館
South Parks Road, Oxford, United Kingd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