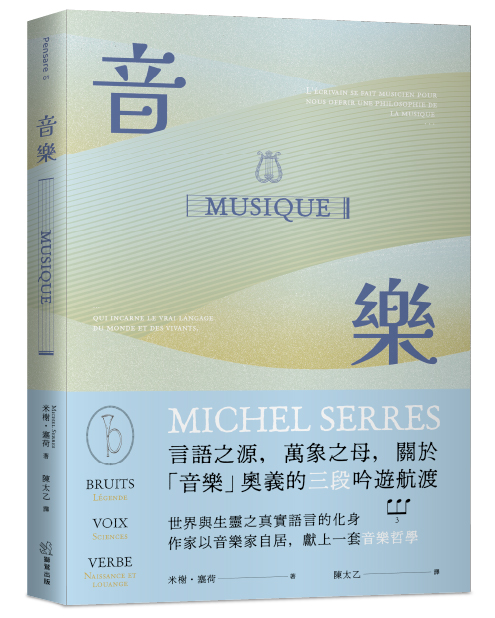兩個等待死亡的老人,兒子三十年前死於不自然,卻在強權高壓下無力反抗苟活偷生。
以前顧著生存不去抗爭,現在死亡也要來了,還有甚麼好怕的?
於是,他們決定在5月35日當天堂堂正正去那個染血的廣場拜祭兒子。
在不正常國家的陽光底下,做正常的事也是不合法。
劇本喚起的,與其說是三十三年前那個夏天無可挽回的悲劇,不如說,更是這三十三年來日日上演的,噤聲、低頭、忍辱的悲劇;與其說是「六四」的悲劇,不如說是「5月35日」的悲劇;與其說是抗爭的悲劇,不如說是失去哀悼權利的悲劇;與其說是死難者的悲劇,不如說是苟活者如何度過餘生的悲劇。
— 鴻鴻(臺灣著名劇場、電影導演)
「八九六四,五三十五,見證時代,永世不忘。謊言與禁忌,終究遮掩不了歷史與真相。」
—于善祿(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助理教授)
本書除收錄書寫八九六四的得獎劇本《5月35日》外,更記錄了劇作的創作歷程及相關評論,透過這齣「六四舞台」最後在香港公開演出的劇目,映照香港人如何以創造力和生命力,在艱難的路上堅持追尋公義。
《5月35日》曾獲「第29屆香港舞台劇獎」五大獎項:最佳劇本、最佳製作、最佳導演(悲劇/正劇)、最佳燈光設計和年度優秀創作。
由日本劇作家石原燃翻譯的《5月35日》,獲「小田島雄志.翻譯劇本獎」。
本書收錄粵語、國語、英語三語劇本,讓爭取民主自由的風箏飛得更遠。
相約在5月35日,來個光明正大的紀念
當現實荒謬,劇場卻讓人恢復正常
「草芥被擠壓到粉身碎骨前,迸發的勇敢與良善情操。」—鴻鴻
「他們的故事,也就是我們的故事。『不想回憶,未敢忘記』,是我們自身命運的呼喊。」—羅永生
本書特色
.《五月三十五日—創作.記憶.抗爭》除收錄了書寫八九六四的得獎劇本《5月35日》外,更記錄了這劇作的創作歷程及相關評論,透過這齣「六四舞台」最後在香港公開演出的劇目,呈現香港在過去幾十年來作為悼念六四的前線,如何在《香港國安法》通過後備受打壓而消亡,創作及言論自由如何遭到扼殺。
.本書通過全面的編輯工作,以《5月35日》劇作為核心,勾勒出2019以降的全民抗爭氛圍面對各式政治打壓的頑抗,本書有八九年之痛,也有香港人當下的痛。
.購買本書正是保留六四記憶,反抗打壓與抵抗遺忘的行動。
.除《5月35日》原著粵語劇本外,本書更載有國語及英語翻譯劇本,讓更多人可以認識本劇,及易於在世界各地搬演。
.本書資料詳盡,製作精明,配有上演時的彩色劇照,有助讀者想像演出情況。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與「曉劇場」將於2023年6月2-4日在臺灣搬演《5月35日》,該版本將以國語演出5場及以粵語進行1場讀劇。
.願我們一同以創作對抗強權打壓,為民主自由搖旗吶喊!
得獎與推薦記錄
.《5月35日》獲「第29屆香港舞台劇獎」6項提名,並最終奪得5個獎項:最佳製作、最佳導演(悲劇/正劇)、最佳劇本、最佳燈光設計和年度優秀創作。
.日本劇作家石原燃翻譯的《5月35日》獲「小田島雄志.翻譯劇本獎」。
.本書由八九六四民運學生王超華、香港著名文化研究學者羅永生、臺灣著名導演及詩人鴻鴻聯合撰寫推薦序。
推薦人
于善祿(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助理教授)、王丹(八九民運學生領袖)、王超華(八九民運學生領袖)、吳志森(香港資深傳媒人)、房慧真(作家)、曾志豪(香港資深傳媒人)、鴻鴻(臺灣著名劇場、電影導演)、羅永生(香港著名文化研究學者)
(按筆劃排序)
.奪「第29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劇本、最佳製作等五大獎
.日文譯本獲「小田島雄志.翻譯劇本獎」
於二○○九年成立,以藝術表演形式,介紹八九民運及「六四」事件的香港前非牟利註冊藝術劇團。曾創作劇目包括《在廣場放一朶小白花》、《讓黃雀飛》、《王丹》、《傷城記》、《5月35日》等,以期喚起人們,特別是年輕一代,對香港及中國民主發展的關注。二○二○年《港區國安法》通過,在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下,「六四舞台」於二○二一年自行解散。
推薦序一:保持憤怒,堅持想像—王超華
推薦序二:他們的故事,也就是我們的故事—羅永生
推薦序三:劇場震怒之日─讀《5月35日》—鴻鴻
出版序:六四舞台在恐懼中擇善固執—列明慧
創作.記憶.抗爭時間表
第一章:報道.原初的抗爭意志
2019年
六四的三十年經緯軸—鄭美姿
六四舞台莊梅岩:我們不能不做,香港人不會習慣那種沒自由的生活方式—陳喜艾
甚麼人訪問甚麼人:用二十年尋找一對亡魂的眼睛—譚蕙芸
2020年
《5月35日》編劇莊梅岩:我們堅持良知和真相—馮曉彤
2021年
「六四舞台」12年來首次網上直播讀劇會:劇本創作合法 勿自設限制—陳詠恩
2022年
消失的六四記憶 「六四舞台」列明慧:透過舞台劇說香港的故事—陳子非
第二章:三語劇本.向世界吶喊
粵語劇本
國語劇本
英語劇本
第三章:評論.暢所欲言的自由
首映原版
5月35日—李怡
5月35日—吳志森
母親最後不再沉默—鄧正健
《5月35日》優異的六四劇—石琪
We Cannot Forget June Fourth—Andrew J. Nathan
The Power of Theatre—Bruce Long
May 35th—Joe Frost
庚子版
6月3日響起榮光 兩年《5月35日》觀後感—Pianda
5月35日【庚子版】從苟活到救贖.從當年到當下—安徒
附錄
六四舞台簡介
創作歷程細表
首演及庚子版製作人員名單
推薦序
〈他們的故事,也就是我們的故事〉
羅永生(香港文化研究學者、評論人)
得悉《5月35日》成功面世,十分高興。不單只是因為這本書收錄了一個以「六四」為題材,寫得極為出色的悲劇劇本,也因為它從側面記載著,香港一場以悼念六四出發,三十多年來一直開展的抗爭運動,最終如何在香港本地落幕。從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而言,這段歷史本身就是一齣悲劇,它的終局尤為悲壯。
這幾年來《5月35日》不同版本的演出,筆者大都有幸欣賞,每次都隨著新的觀賞環境而產生內容不一的感動。2019年7月尾,721元朗白衣人襲擊事件發生不久,筆者坐在藝術中心的觀眾席上第一次觀賞本劇。地鐵站恐襲的場面還是歷歷在目,與舞台上呈現的三十年鬱結遙相呼應,「歷史」從來沒有如此地靠近我們。2020年六四前夕,我又透過網上直播重溫,既因為疫情爆發,也因為政局急轉直下,人人擔心這次破天荒的全港直播,能否順利完成。那是一場別開生面的「演出」,也是一件行進中的「事件」。翌日維園的集會不再「合法」,但仍有大批市民自發前往,支聯會的口號變成當中微弱的其中一把聲音。到了2021年6月3日,《5月35日》以網上直播讀劇,六四當晚,維園被龐大警力禁閉, 但附近街道滿布手持燭光的市民,翌日筆者的腦海裡盛載著這一夜壯美的街頭光影,起程離開香港。2022年6月,我和其他流亡或移居者在倫敦Genesis Cinema重溫《5月35日》的演出錄像,飲泣之聲在全院此起彼落。
戲劇是回憶的載具,可以讓我們回到被遺忘的過去,但也可以把過去帶到我們的當下。如果「八九六四」曾經被認為是關於那個日漸和我們生疏的當時當地,《5月35日》的這些演出和觀賞經驗,卻在在把我們的當下此刻,重新放置到一個不斷伸延的「八九六四」。觀眾在舞台所看到的不再只是演員們的演出,而是親身站上了歷史舞台上的自己。他們的故事,也就是我們的故事。「不想回憶,未敢忘記」的,不再是關乎日漸「陌生」的他者,而是我們自身命運的呼喊。
《5月35日》的主軸不是六四那夜發生的事,也不是八九那場民主運動的歷史篇章,而是關於六四的記憶如何被禁閉、壓抑、消滅、隱藏的故事,它們如何構成一代人的創傷和揮之不去的鬱結。直到今天,它幾乎已經被那地方的新一代徹底淡忘,可是,苟活半生的老一輩臨終的絕望,再也壓不住要到廣場去來一場光明正大的紀念—這哀悼亡者的衝動就成為對極權公然的反抗,和對未來寄予希望的象徵。
香港過去三十多年來一直維持一年一度的維園悼念,成為五星旗下唯一能光明正大地悼念六四的地方。不少人為保存這記憶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在沉淪於犬儒和冷漠的世道示範微弱反抗的勇氣,也內化為提升香港人積極精神面貌的養分。《5月35日》在剖白這段歷史鬱結的同時,也間接給予香港這份堅持悼念三十年的事跡一段充分的註解。沒有這段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言的「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也就沒有香港人長期地,在社會的微觀層次持續與親專制力量周旋的演練機會,也不會在這座以聲色犬馬見稱的商業城市,如此渾然天成地孕育出《5月35日》這部出色的劇作。
過去十年,筆者一直認為,香港人除了參加每年的六四維園悼念集會之外,更應認真整理和反思關於六四的記憶,如何進入香港本土文化和政治脈絡的經驗。原因在於,六四不單只是中國的事,相反地,它已經在香港本土播種生根,構成了甚麼是香港,甚麼是香港人,塑造著當代香港文化,涵養著香港身份中關鍵的價值認同的重要力量。就此而言,劇作《5月35日》在2019年開始,每年接續以不同形式演出,本身就是「六四本地化」歷程的高潮,也是香港劇場藝術發展的重大事件。
今日,在香港本地的悼念六四活動已經被扼殺,「六四舞台」也無法繼續在香港安排演出。然而,這只是終結了「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的一個章節。而隨著《5月35日》開始在海外演出(包括錄像放映和翻譯後的舞台演出),以及今次國、粵語和英文劇本的出版,「六四記憶」和「六四記憶的香港抗爭經驗」正在踏上新的里程。它們會更進一步,改變世界的中國想像、香港想像,介入各不同的劇場、藝術和文化脈絡,成為我們這世界的一部分。
隨著《5 月35日》的出版,筆者更期盼未來有更多的研究或資料整理,總結這些年來在教育、媒體、流行文化、音樂、視覺藝術、公民社會等領域中,關於六四記憶、六四呈現等的角力,從中我們可以重新發現香港人的生成(becoming)軌跡,立體地承傳這份無權勢者抗爭的文化與香港獨特的歷史經驗。
是為序。
出版序
〈六四舞台在恐懼中擇善固執〉
列明慧(「六四舞台」主席)
《5月35日》是「六四舞台」最後一個在香港公開演出的劇目。說是最後一個,是因為「六四舞台」被恐懼吞噬了,在2021年已自行解散。那段風雨飄搖的日子裡,民間組織解散潮一波接一波,我們懷著心不甘情不願,誠惶誠恐的混亂思緒去處理申請解散劇團的行政工作,等待警方確認社團解散的同時,一面得悉同樣申請解散的劇團及民間組織通常一星期內會收到確認,我們卻已等上三星期;一面內部討論是否如同「支聯會」一樣連網站和臉書專頁也要刪除。要麼親手抹掉過去十多年心血作品的歷史紀錄,要麼承受有成員可能會因此牽連招致牢獄的風險。我們反覆討論自己是否過度神經質,還是應理所當然地相信法律會保障創作自由?作品早已公演了,當局是否有追溯權?不斷地審查過去質疑現在,To be, or not to be,嘆息我們竟然身處一個如此荒誕的時代……(喂阿哥,做幾齣話劇啫,危害到個屁安全咩?!這可成為法庭上抗辯的理由嗎?)最終,雖然我們沒有收過一封警告信,但在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下,我們刪除了網站,隱蔽掉臉書專頁。隨著不少香港新聞機構停止運作,大部分「六四舞台」過去演出的新聞報道、評論等,在網上已無影無蹤了。
「六四舞台」的成立是本著以戲劇形式,讓人認識六四真相,反思人性。每一個製作,我們都著重要從不同的角度去回顧八九六四,從天安門廣場上風風火火的青春熱血、血腥鎮壓後內地一片白色恐怖、營救被迫逃亡人士的「黃雀行動」、流亡海外學生領袖的漂泊零落、國內維權人士被打壓逼迫牢禁、到白髮斑斑的遇難者家屬沉鬱而終。即使寫的演的是當年故事,引發出所思所想卻盡是香港的當下。香港人在這場民主運動中從不缺席,也成就了香港本土政治運動的重要脈絡,塑造著香港人在當代中國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因著香港的特殊地位,曾經享有資訊流通的自由,言論、出版及創作自由的百花齊放,香港人可以從不同題材的藝術作品中,認識人性的光明與陰暗,在反思和質疑中,發掘出真善美。
大概我們這份善意得到「戲劇之神」的眷顧,「六四舞台」一直得道多助,多年來與不少香港出色的劇場工作者合作。從2009年到2021年,我們每年都有演出,共製作8齣公演舞台劇、1次網上串流直播、2個網上讀劇會及295場學校巡迴演出。2018年,更邀得著名編劇莊梅岩撰寫《5月35日》,創作團隊花了整整18個月籌備演出。在2019年演出期間,香港發生一場史無前例的「反對逃犯修訂條例運動」,5月下旬首演6場期間,運動開始升溫,香港人高呼要維護人權,反對修訂條例,到7月重演5場,香港人親身經歷了內地對維權運動的鎮壓模式,催淚煙瀰漫的街頭接通了當年火光熊熊的廣場,地鐵站的白衣人恐襲聯繫到鄉黑片警合作執法,我們對「暴徒」還是「暴政」的爭論感到切膚之痛。
及後新冠疫症襲來,香港所有演出劇場關閉,2020年《5月35日》(庚子版)舞台演出被迫取消,我們把本劇由舞台移師到網上直播演出,反而讓更多觀眾可以分享這個故事。我們籌備庚子版演出的那段期間,中央硬推《國安法》,踐踏一國兩制,收窄我們的自由。作為創作團隊,怎會沒有恐懼?但是至少我們堅守到最後一刻,沒有出賣靈魂沒有歌頌極權沒有扭曲如蛆蟲,我們擇善固執、為蒼生說話。
2021年10月,我帶著《5月35日》的版權移居海外,在臺灣、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地舉辦過舞台劇錄影版的放映會,說六四真相的同時,也說出香港的故事。期望是次劇本集在臺灣出版,能記錄時代、見證時代,更希望將這個出色的粵語劇本,翻譯成國語及英語,有利不同地區的劇團可以搬演。讓不能在香港存在的《5月35日》,能在其他地方活下來。等風起時,讓爭取民主自由的風箏飛得更遠,讓種子飄落你家的花園,長出自由花。
內容試閱
〈5月35日〉
李怡
5月35日,幾乎沒甚麼人不知道就是今天。但這麼說的意義又跟直接講6月4日不一樣。比如你同朋友約了今天見面,你說6月4號,那就只是一個日子;你說是5月35日,那很明顯就是指六四。30年來,在大陸,六四成了敏感詞,網民就改稱「5月35日」、「8的平方」或羅馬數字「VIIV」。「5月35日」這種表述,盡顯30年來一個禁制言論、禁制人民記憶的政權的荒謬。
由莊梅岩編劇、李鎮洲導演的舞台劇《5月35日》過去幾天上演了五場。製作者是2009年成立、只有小眾關注的「六四舞台」,在藝術中心一個小劇場演出,公開售票三小時,門票即售罄。相信頗令製作者感意外。現訂在7月再加演五場。
舞台劇講北京一對困病的老夫妻,在5月35日想去天安門廣場點一根蠟燭悼念在六四中被殺害的兒子,而受到阻攔的故事。兒子死於非自然,想問個明白,想去拜祭,在正常社會這都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但在不正常國家做正常的事竟然是被強力部門壓制。結果老妻留在家中,老夫一人爬窗獨去。臨行前老妻問他:你想在被人按住的時候叫甚麼?不要叫「平反六四」那些呀,「專制政權沒有資格平反我哲哲呀!」老夫說他會叫:「我愛小林(妻名),我愛哲哲!」
沒有「愛國」,也沒有「平反六四」,愛的是妻子、兒子。
我想起美籍猶太裔學者漢娜.鄂蘭回答友人的一段話:「我這一生中從來沒有愛過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集體—不愛德意志,不愛法蘭西,不愛美利堅,不愛工人階級,不愛這一切。我『只』愛我的親友。」
早前六四遊行,參加者比去年多了一倍,而且許多往年已經消失身影的年輕人又出現。今晚六四集會相信也會如此。支聯會秘書李卓人日前在電台說,明白近年本土思潮令年輕人與六四「切割」,但呼籲出席集會者不應糾結於「愛國」與否。他多慮了。今年已經不同往日,年輕人已經不會再介意你們喊甚麼「愛國」、「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因為他們已經超離了對這些口號認同與否,變成沒有感覺了。
或許正如莊梅岩在一個訪問中說:「有時,我們被代表那件事的人,影響了對事情本質的追求。我從來不跟派別,不跟人名做事。不是因為誰支持我就支持,誰支持我就反對。我覺得件事本質才最重要。」
甚麼是件事本質?本質就是血腥鎮壓,就是連六四這兩個數字都不能提,要用5月35日代替、甚而連代替都列為禁忌的荒謬政權。而誠如莊梅岩說:「我們處身於同一個政權之下,我們不理,到最後這些待遇會落到我們身上,為何我們可以不理?」
修訂《逃犯條例》提出,香港市民已接近「最後這些待遇」了。
因此,你要愛國就「愛飽佢」啦,你要繼續乞求專制政權開恩「平反」就「平到夠」啦,反正這些口號跟我們無關,它們早就在許多香港人的意識之外了。
我們不應再介意「誰代表那件事」,我們找到的共同點就是為了反對暴政君臨而抗爭,如同話劇《5月35日》結束時一大群亡魂的吶喊抗爭一樣。亡魂體現的是一個個在親人心中不會消失的個人,亡魂呼喚的是人性,是要延續維護人的自然權利的抗爭。
(本文原刊於《蘋果日報》 2019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