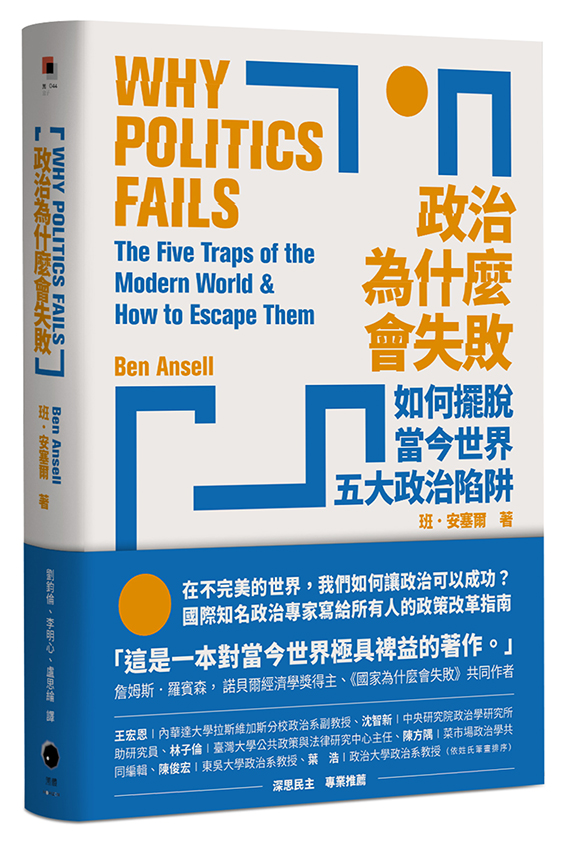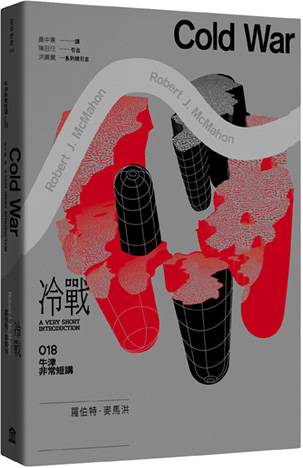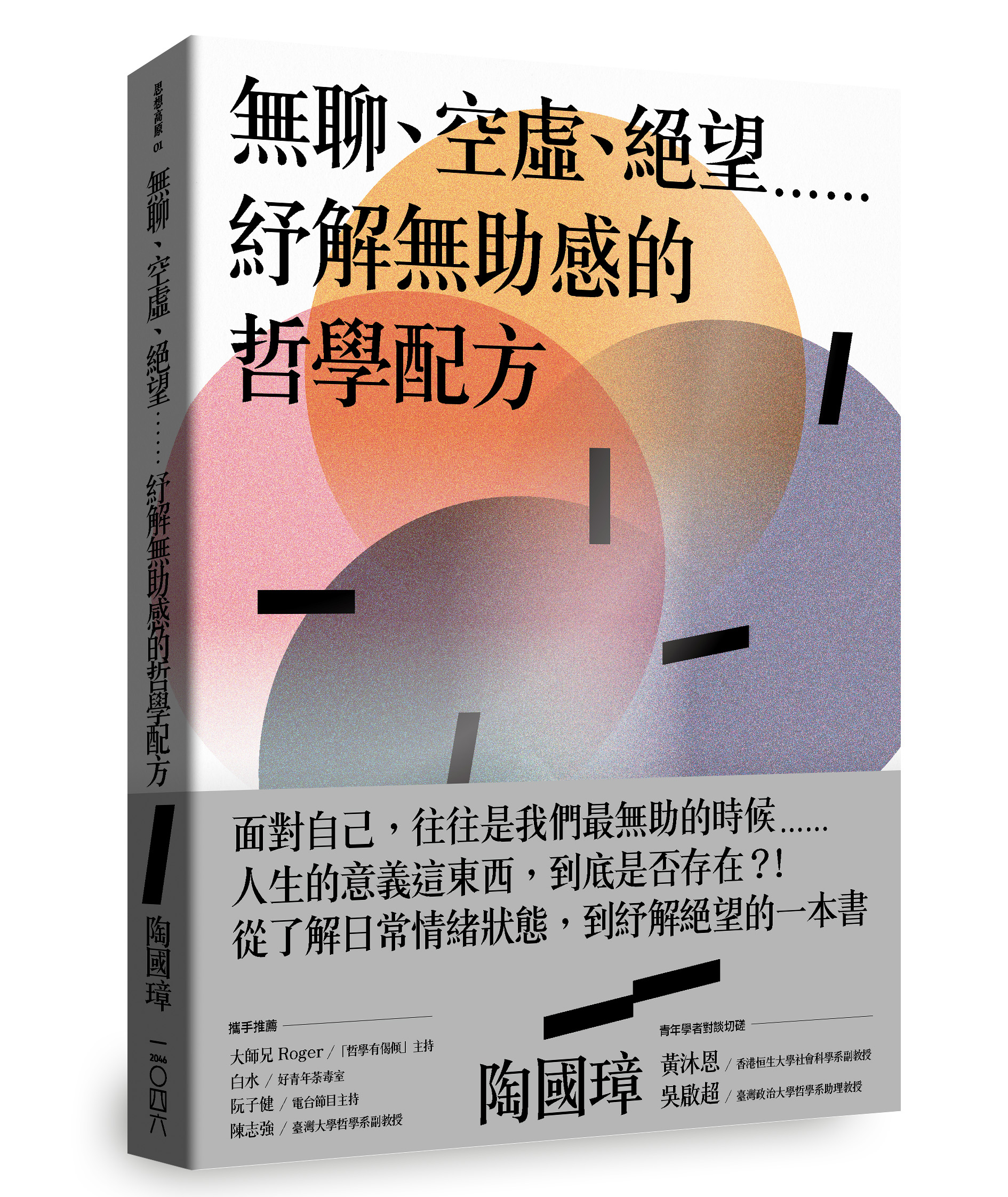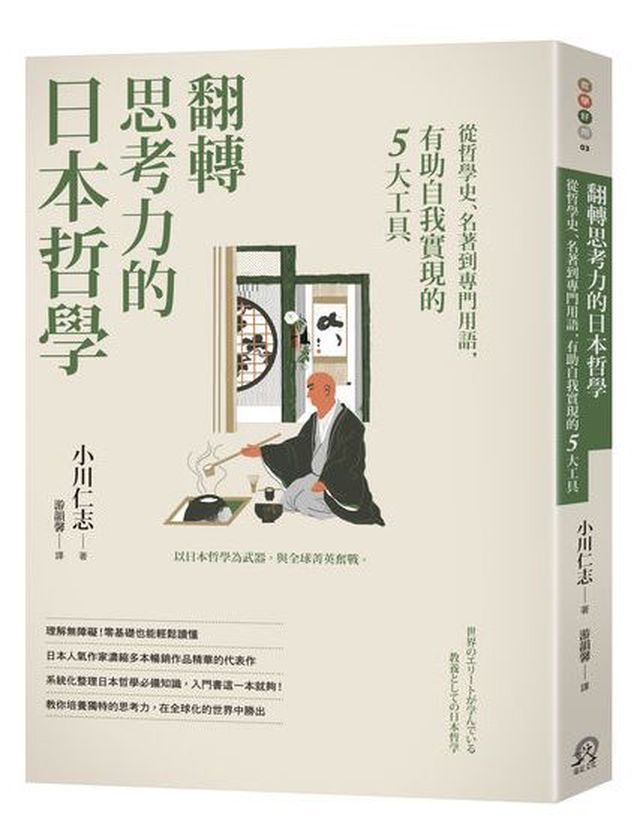法國哲學新聲,以六篇自然書寫文論,探尋萬物之「生」的核心
面對生態與人類的感受性危機
找回與萬物共存的能力
「人類的生活方式,只有與我們周遭的動物、植物、細菌、生態系所擁有的成千上萬種其他生活方式交織在一起時,才有意義。」──巴諦斯特.莫席左
法國新生代哲學家巴諦斯特.莫席左(Baptiste Morizot)曾在一次追蹤北非候鳥的行程中,撞見一隊老車愛好者途經山谷,在大自然中停駐自拍。然而,他們只關注眼前的老車,對正在他們頭頂上進行的這場地中海最熱鬧、最國際化、最多彩多姿的動物「移民」行動,卻完全視而不見。
這次經驗,引發了他的警覺:我們人類,身為社會性的靈長目動物,往往本能地更關注自己的同類。然而在當代,在政治經濟學與科學理性無比蓬勃的情境底下,我們與「自然」之間、我們與其他生物之間,卻更加成為對立的兩造、光譜的兩端。而這在巴諦斯特.莫席左眼中,不啻是當代的「感受性危機」,而亟需被重視。
巴諦斯特.莫席左作為哲學家,特別關注人類與世間萬物的關係,並試圖提出一套新的哲學角度,重思人類作為一種物種,該如何與其他物種共存。《生之奧義》由六篇哲學隨筆組成,揉合生態考察與內在思索,堅定優美的筆觸下則埋藏著生命的徬徨與溫柔。
他曾在覆雪的山地裡追蹤狼跡,並在聲聲狼嚎中感知到自己置身於地球萬物生命的共同命運之中。他也透過海綿這種原始的物種,去反省我們觀念種對於「演化」與「進化」的莫名崇拜。他甚至提出,假設人類作為一種物種的陣營,是否有可能創造出一種類似「外交官」的身分,來和其他物種打交道,並共同為了相互依存的目標而努力。對他而言,「生」的奧義,就是必須重新學習看待世界的方法,看見跟我們一樣奇妙的生命存在;而要能獲得這份「看見」,就必須改變我們怎麼活、怎麼共同生活的方法。
*本書榮獲法國在台協會《胡品清出版補助計畫》支持出版
柯裕棻(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徐振輔(作家)
黃宗慧(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黃宗潔(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蔡晏霖(陽明交大副教授、多物種人類學研究者)
共同推薦
巴諦斯特.莫席左,一九八三年生,是法國極受關注的新生代哲學家、作家。
他任教於艾克斯馬賽大學的哲學教授,主要研究人類與生物的關係,特別是透過田野調查跟蹤野生生物。
莫席左有多部著作,如《在獸徑上》(Sur la piste animale)、《生之奧義》、《讓生者之火更加旺盛》(Raviver les braises du vivant)等,並曾獲政治生態基金會(Fondation de l'écologie politique)圖書獎、弗朗索瓦墨基金會圖書獎(Fondation François Sommer)、法蘭西學院的雅克-拉克魯瓦獎(Prix Jacques-Lacroix)。他的思想受到許多當代法國哲學家、評論家的肯認,尤其在於他對法國動物哲學的突破與貢獻。
在著作之外,莫席左也積極參與各種倡議活動,捍衛環境與自然生態,實踐他的哲學理念。
林佑軒,寫作者、翻譯人。臺灣大學畢業,巴黎第八大學研究所修業中。
聯合報文學獎小說大獎、時報文學獎散文首獎等項得主,數度入選九歌年度小說選、散文選等集,作品參與臺灣文學外譯計畫,並為文學雜誌執筆法語圈藝文訊息。
著作三種:小說集《崩麗絲味》(九歌,二○一四)、長篇小說《冰裂紋》(尖端,二○一七)、散文集《時光莖》(時報,二○二一)。
法文譯作四種:《大聲說幹的女孩》(聯合文學,二○一九)、《政客、權謀、小丑:民粹如何襲捲全球》(時報,二○一九)、《世界大局.地圖全解讀》(野人,二○二○,合譯)、《在雪豹峽谷中等待》(木馬,二○二一年春)
請見:yuhsuanlin.ink。
目次
致讀者言
導論:生態危機之為感受力危機
在生物家過上一季
一株海綿的前程
與自己的野獸共居:斯賓諾沙的外交倫理學
來到夜的彼端:走向相互依存的政治
結語:隨時制宜的顧念敬重
跋◎阿蘭.達馬吉歐(Alain Damasio)
謝啟
注釋
導論
生態危機之為感受性危機
世界仰賴如此紛繁的物種,每一種都是令人顛倒夢想的原型 。
--理察.鮑爾斯(Richard Powers)
我們身處爭戰鞍部(col de la Bataille)。暮夏時分,寒意襲人;勁烈的北風於此衝撞南風、粉身碎骨。這座鞍部觸眼荒涼,時光於此滯留於舊石器時代,一小條常常封閉的柏油路從中穿行而過。然而,荒寂處並不荒寂:此處乃是身屬蒼穹的生命的聖地。確實如此,數量浩瀚、物種豐繁的鳥類動身往赴非洲、展開漫長的遷徙旅程時,經過的正是這座鞍部。此地是轉赴世界另一端的傳說之門。我們廁身於此,是為了計算牠們的數量。我們持著舞廳與劇場用來數算人頭的手動計數器,每當燕子飛過,我們就在某種歡悅的亂迷中,瘋狂地按著、按著;而燕子,燕子飛過了幾千隻、幾萬隻。三小時的點算之間,我女友就數到了三千五百四十七隻:家燕(hirondelle rustique)、毛腳燕(hirondelle de fenêtre),還有岩燕(hirondelle de rochers)。燕子從北方來,成群結伴、列隊飛行,隨而隱入鞍部下方的山毛櫸森林中,等待那對我們來說奧祕難解的訊號。燕子衡量風況、衡量氣象、衡量群燕數量,還有什麼呢,在小歇時分,牠們補充自己微薄的脂肪儲藏。而在某個精確的時刻,原因為何我們並不知曉,整群燕子在電光石火之間蜂擁前翔,在合宜的時刻,就在那合宜的時刻,群燕飛越了鞍部。牠們星羅棋布著天空。群燕一旦越過南邊迎接牠們的風牆,就抵達另一頭了,大功告成,通過了一扇門,還有其他一扇扇門。低處,緊貼地面的所在,雀形目的鳥類(passereaux)正進行匍匐的遷徙:牠們杳無形影,從這棵樹飛舞到那棵樹,像是在閒逛蹓躂;然而,這樣從一棵樹到另一棵樹的流轉,將會帶牠們到天涯海角。為了從強風下通過,某些藍山雀(mésange bleue)用走的走過鞍部這條小徑;牠們得執拗不撓走上一分鐘,才能走完這條柏油路;無有遲疑,也不匆忙擠攘,牠們開展著旅途,有朝一日將抵達非洲北部。十一公克的生命,要怎麼裝得下一整座大陸的勇敢?這裡也有猛禽──魚鷹(balbuzard),江河的祕密王者,牠把自己的爪子變成了捕魚的熊那強而有力的掌,成為了「行動」的純粹化身:一雙從空中猛撲而下的翅膀與一雙永不力竭的手掌結合在一起。紅隼(faucon crécerelle)與燕隼(faucon hobereau)成隊翱翔,獵食者與獵物共伴相隨,宛如群獅與瞪羚(gazelle)結夥漫遊。這只是從地球這端到那端的漫長隊列的一個起點:這長長的隊伍,是恐龍賸餘給我們的所有物種的遷徙行列。有些人很天真,以為恐龍滅絕了,其實牠們依然活力充沛,只不過變成了麻雀而已。這遷徙的行列中,有鷚屬 (pipit)的鳥、鶺鴒(bergeronnette)、林岩鷚(accenteur mouchet)、巨大的胡兀鷲(gypaète géant)、嬌小的金絲雀(serin)、戴菊(roitelet)、雀科鳴禽(venturon)、紅翅旋壁雀(tichodrome),還有紅鳶(milan royal),牠們就像披掛五顏六色旗幟的一個個高盧部落,各自有各自的風尚、言語、無我亦無雙的驕傲──各自有各自的堅持。這一種種生命形式,每一種都以自己獨一無二的觀點看待這萬有共享的世界,每一種都精通如此藝道:讀出其他生命形式視若無睹的訊息。
好比說,燕子必須在飛行中持續進食;牠們以專家之姿,接收氣候訊息、捕捉到一天中昆蟲群會落在牠們航線上的時刻,以便邊飛邊攝食昆蟲,同時不改道、不停佇、不減速。
忽然,引擎聲轉移了我們的注意力。下方的道路上,一隊古董車正魚貫攀登鞍部。那是古董車收藏家的聚會,他們在星期日出動,把自家的破銅爛鐵妝點得漂漂亮亮,讓它們在山路上閃閃發光。他們在鞍部上停了下來。他們下車個一兩分鐘,拍幾張馬戲團般高難度的自拍,企圖把引擎蓋、微笑與風景全都裝進螢幕中。還真有魅力啊他們,他們在這裡很開心。然後他們離開了。在我身邊,我女友分享了她之所見,震駭了狂風中的我們:「他們沒有注意到,」她說,「他們沒有注意到,他們身在地中海最熱鬧、最國際化、最多采多姿的港口這樣的地方,無數的民族正動身前往非洲 。」一支支部族與自然環境戰鬥,穿梭在能量的流動之中,為陽光而歡欣,以風的力量滑翔。
確實如此。身為社會性的靈長目動物,正如我們所深知的,他們念茲在茲就只是自己的同類,他們只看見了荒寂的鞍部、空無的環境、瘖啞的風光、電腦螢幕的布景。意識到這件事,絕非意在責難這群人。他們不折不扣就是我們自己。多少次了,生命在某處蠢蠢欲動,我們卻視而不見?恐怕是每一天。是我們的文化傳承、我們的社會化讓我們變成這樣的,這自有緣由理據。但這並非不挺身戰鬥的理由。沒有責備之意,有的只是一種哀傷,一種面對如此的盲瞽、如此盲瞽的影響規模及其天真的暴力,所生發的憂愁。至關緊要的,乃是整個社會重新學習去看見:這世界住滿了比車輛收藏與美術館展品更秀逸非凡的一個個實體;乃是去肯認:這些實體需要我們變革共同的生活與居住方式。
感受性的危機
從上述經驗出發,可以得出一個觀點。我們面臨的生態危機正是人類社會的危機:它危及未來世代的命運,連我們自己的生存基礎都因之搖搖欲墜,它還危害了我們在污染環境中的生命品質。它也是生物的危機,以如下形式展現:第六次物種大滅絕、動物消失,還有,氣候變遷損害了生物圈(biosphère)的生態活力與演化潛能。但這也是另一種更隱微、也恐怕更為根本的危機。針對此一盲點,我做出如下推論:當今的生態危機,一方面是人類社會的危機,另一方面是生物的危機,更是我們與生物關係的危機。
首先,此一危機驚心動魄地,是我們與生物世界的生產關係的危機──這從主流政治經濟學對於開採主義(extractiviste,又譯榨取主義)以及金融化的狂熱已能窺知一二。不過,此一危機也是我們集體與存有關係的危機、我們對生物界的連結與歸屬的危機;如此的連結與歸屬左右了生物的重要性,決定了牠們是屬於、還是外於我們的感知世界、情感世界、政治世界。
這場危機難以命名、難以理解。然而,人人都能準確感受到它所曉諭我們的:我們與生物的關係必須改變。
種種政治實驗讓我們的時代對與生物共居、與生物發展關係的新方式充滿熱情。群體生活形式的新選擇一樣接一樣興起了。各種生態農業(agroécologie)以及顛覆性的科學受到喜愛;它們另出機杼,重新定義了活生生的、豐盈著交流與意義的自然界。以上種種,就是我們身處的局勢裡,此一支點微弱卻有力的訊號。
不過,這場危機的另一個面向卻比較少人注意到,因為它的政治面,亦即它政治化的可能性,是較不引人注目、幾近靜默無聲的。此一面向乃是:將這場危機思考為一場感受性的危機(crise de la sensibilité)。
我們與生物關係的危機是感受性的危機,因為我們習慣與生物維持的關係,是與「自然」(nature)的關係。一如巴西人類學家艾督瓦多.維威洛斯.德卡斯特羅(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所言,我們這樣的西方現代性承繼者認為自己與人類以外全體生物世界的關係是與「自然」的關係,因為與牠們的任何其他關係都是不可能的。現代人的宇宙裡,可能的關係有兩種:要嘛是自然的,要嘛是社會與政治的,社會與政治的關係專門保留給人類。如此一來就表示,我們主要把生物視為環境布景、視為生產可用的資源庫、視為尋根溯源之所,或視為情感與象徵投射的載體。身為環境布景與投射的載體意味著,其已失去了本體論的實質。當我們失去了關注一件事物,將之視為群體生活裡占有一席之地的整全存在的能力,該事物就失去了其本體論的實質。為感受性的危機鳴鑼開道的事件正是:生物世界墜至集體的、政治的關注範圍以外,墜至「重要事物」的邊界以外。
我所說的「感受性的危機」指的是:我們感知得到的、察覺得到的、能夠理解的、得以締造為我們與生物關係的,都日漸貧乏了。連結我們與生物的那些情感、感知、概念與實踐,它們的種類減少了。我們有繁多的詞彙、關係種類、情感種類來形容人與人的關係、群體與群體的關係、組織與組織的關係、與工藝製品(objet technique) 的關係或與藝術品的關係,而用來描述我們與生物關係的詞彙卻遠少得多。我們對生物的感受性,亦即我們對生物的關注形式與我們保留給生物的關注品質,其範圍品類日漸貧瘠,這既是我們遭逢的生態危機的結果,亦是其一部分的原因。
此一感受性危機的第一個、可能也是最怵目驚心的症狀,表現在作家、鱗翅目昆蟲學家羅伯特.派爾(Robert Pyle)提出的「自然經驗的絕滅」 的概念裡:我們日常生活經歷、體驗的與生物的關係已日趨消亡。近來有項研究就揭露了,四到十歲的北美兒童眨眼間就能以專家之姿認出超過一千種品牌標誌,卻沒辦法辨別所居地區的十種植物葉片 。區辨人以外生物的形態與生存方式的能力大幅移轉到人造物上,而這又因為我們對與我們同居地球的生命極度缺乏感知而變本加厲。抵抗經驗的絕滅、抵抗感受性的危機,就是豐富我們面對浩瀚豐繁的生物時,能擁有的感知、能掌握的理解、能編織的關係。
在有科學研究為證的當代田野鳥類大規模消失,以及城市鳥類的歌聲在人耳裡產生意義的能力之間,存在著隱微卻深刻的關係。當一名操Koyukon語的美洲原住民在阿拉斯加聽見了烏鴉的叫聲,這啼鳴便深入他之中,透過成串的記憶,同時為他重建了這隻鳥的身分、講述其習性的傳說、他們共同的親屬關係,以及他們在神話時代締結的古遠盟約 。我們的城市裡,烏鴉隨處可見,牠們的啼叫日復一日傳到我們的耳朵裡,我們卻什麼也沒聽見,因為我們在我們的想像裡已把烏鴉變成了動物:變成了「自然」。我們每天聽見的十種不同鳥鳴僅僅以白噪音(bruit blanc)之姿傳入我們的腦,最多也不過喚起一個烏有意義的空洞鳥名:就好像再也沒人傳講的古老語言,其珍寶隱而不顯──令人悲傷。
我們對「自然」的信仰,其暴力顯現在:夏日,當我們遠離一座座市中心,就沉浸在鳥、蟋蟀與蝗蟲的鳴囀裡,而這樣的歌聲在現代人的神話裡卻被體驗為一種令人閒適休歇的沉靜。可是,對於願意試著翻譯它們、將它們從白噪音的處境解放出來的人,這些鳴響卻構成了浩瀚不可勝數的地緣政治訊息、領土談判、小夜曲、恫嚇、遊戲、集體的歡愉、拋出的挑戰、無字的秘密磋商。就算最小最小的一塊繁花草地,也是一塊國際的、多語言的、多物種的、活動繁忙嗡鳴的交會輻輳之所,也是一艘廁身宇宙邊緣的太空船,數百種不同的生命形式以聲音彼此溝通,於此相會並建立一套套各方都接受的模式(modus vivendi)。春天的夜晚,人們在這艘太空船裡聽見夜鶯雷射一般的歌聲,牠們以不顯暴烈、洋溢美感的努力來吸引配偶──在牠們之後遷徙來此、為了尋得雄鳥而在夜裡漫遊林間的雌鳥。人們在驚疑之間,聽見了狍(chevreuil)的啼鳴,這星系間動物的咕噥喉音兀自吼喊著欲望的絕望。
夏天的傍晚,我們所說的「鄉野」,是最紛繁多彩、最喧囂嘈雜的跨物種輻輳之地,騷動著靈巧的能量,是週一早晨非人類的時代廣場──現代人夠瘋了吧,他們的形上學足以自我實現,讓他們在這塊「鄉野」看見了令人重獲活力的寧靜、宇宙的孤獨、安詳的空間。一塊空空如也、沒有真實生命的,喑啞無言的地方。
如此一來,離開城市,就不是遠離塵囂與諸般危害、活成田園牧歌,就不是動身赴鄉野生活,而是動身去以少數族群之姿生活。一旦大自然不再是大自然──當它不再是平滑均勻的連續體,不再是一體成形的布景,不再是人類苦難搬演其前的背景──,一旦我們將生物重新詮譯為生命而不再是物品,多重物種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isme multispécifique)就來勢洶洶、萬鈞莫敵,幾乎令人喘不過氣了──我們成為了少數。這對養成了「將一切『他者』都變成少數」如此惡習的現代人來說,不啻一帖良藥。
從某種角度來看,我們確實喪失了某種感受性:都市化大規模進行著,我們的日常生活沒有接觸繁多的生命形式,這些都剝奪了我們的追蹤能力──我指的是哲學意義豐繁的「追蹤」,好比對其他生命形式跡象的感受性、為之提供的資源多寡。這種閱讀的藝術已佚失了:我們「在此什麼也看不見」;為了開始重新學習去看見,有個關鍵是去重建感受性的路徑。我們在「大自然」中什麼也沒看見,不僅僅是因為缺乏生態學、動物行為學以及演化相關知識,而且是因為我們生活其中的宇宙論預設了沒有什麼好去看見的,換言之,沒有什麼可以翻譯的:沒有什麼意義要解釋的 。這全部的哲學挑戰乃是:要讓「圍繞我們的生物界裡,確實有東西好去看見、有豐富的意義可以翻譯」為人所知所感、變得顯而易見。然而,只要踏出這一步,整片地景就會重新組織。這正是本文集首篇文章的目的,它讓讀者置身於一場考察探險裡,讀者將在韋科爾山脈的雪中追蹤一群狼。這篇文章介於「動物行為學的驚悚文本」以及「與異於我們的生命形式初次接觸的敘事」之間。
不過,「『喪失』感受性」的概念,本身的表述是模糊的。確實,對這個概念的誤解來自,它似乎暗藏了某種懷舊的原始主義之類的東西,這些東西在此並不切題。未必是「以前較好」。並不是要回到在森林裡裸體這樣的生命形式。一切的關鍵恰恰在於:必須去發明創造。
作為中介(intercesseur)的動物
感受性危機的另一個症狀──這症狀,我們已把它變得自然而然,因此幾乎無法察覺──表現在我們把動物限縮在怎麼樣的調性裡。除了牲畜待遇的問題──牲畜既非動物性的全部,更非其榜樣──,我們的文明對動物施加的隱微的大暴力,乃是我們把動物變成了給小朋友的角色:關心動物不是嚴肅的一回事,而是多愁善感、感情用事。關心動物只是「動物愛好者」(amis des bêtes)的事。是一種倒退。我們與動物性、與動物的關係都遭到了幼稚化、原始化。這侮辱了動物,也侮辱了兒童。
我們對動物的感受性,其範圍、種類已縮減到少得可憐的地步:動物要嘛是抽象而模糊的美,要嘛是童稚的角色,要嘛是道德同情的對象。夏爾.思特帕諾夫(Charles Stépanoff)筆下極北地區圖瓦人(Touvain)的人與生物關係的民族誌或是愛德華多.科恩(Eduardo Kohn)的亞馬遜地區魯納人(Runa)民族誌展現了遠為豐富、多元、細膩、強烈的繁複:動物在此充斥於當地人的夢境、想像、實踐、哲學體系之中 。
我們對生命形式的想像縮減了。在我們的夢裡,生物寥寥無幾;我們的夢沒有充斥著狼嚮導或熊導師,沒有滋養生息的森林,沒有昆蟲,沒有費盡萬苦千辛領我們走到這一步的前人類(préhumain)祖先。本文集第二篇文章正是意在鑿開一個破口,於我們的想像裡為他們設想新的位置,好比說,以沒有神祕主義色彩的儀式來呈現。
因為,動物所應得的,並不僅僅是童稚的、或道德的關注:牠們是共居地球的一分子,我們與牠們擁有共同的祖先、生命的謎奧,以及得體共居的責任。「身為一具身體,一具詮釋並活出生命的身體」,如是秘奧為所有生物共享:它是普世的生命條件;有資格召喚最為強大的歸屬感的,是它。因此,動物是原初謎奧──我們的生活方式之謎──的絕妙中介:動物展現了一種無可縮減的相異性,與此同時,動物又與我們夠相近,足以讓人感受到,人類與哺乳類、鳥類、章魚……一直到昆蟲之間,無數種對照的、趨同的形式。我們賴以重建對普遍生物的一條條感受性途徑的,正是牠們;精確地說,是憑著牠們「原初」的地位身分、憑著牠們之於我們的親密的相異性。牠們讓我們能夠逐層逐次地感受我們與植物、與細菌的隸屬關係。植物與細菌在我們共同的系譜中較為遙遠,牠們是陌生的親戚,陌生到我們較難感覺自己是與牠們一樣的生命。要覺得自己與牠們同為生命,就必須要有擺渡者:動物是擁有此一力量的中介。
然而,我們繼承了一種貶低、賤斥動物的世界觀,它在我們的語言裡昭昭可見,語言結晶了思想的反射。法文裡的所有這些說法:「沒比動物好多少」(valoir à peine mieux qu’un animal)、「跟動物沒兩樣」(n’être qu’un animal),這一切朝上的鄙視、一切有關「超越我們內在的低等動物性」的隱喻性垂直關係,都出現在我們的倫理道德、我們的自我表述裡最日常的角落──太不可思議了。然而,它們卻建立在一樁形上學的誤解上。這正是本文集第三篇文章的目的,這篇文章尋索了西方道德史──它命令我們馴服我們野獸般的衝動──之中,我們內在的動物性。
這種種之於動物性的複雜關係,一部分確實源於二元論哲學人類學從猶太-基督信仰(judéo-christianisme)一路到佛洛伊德主義(freudisme)的獨霸。如是的西方觀念將動物性思索為一種內在的獸性,人類必須超越、克服它來「變得文明」;或者,相反地,此觀念將動物性視為一種更純粹的原始性質,人類在動物性裡尋根溯源,藉此找回一種更本真的、擺脫社會規範拘束的野性。這兩種想像看似對立,其實絕非如此:第二種想像只不過是第一種的另一面罷了,它由反作用以及對稱的兩相對照所建構。但是我們曉得,反作用的創造只會永久延續那刺激我們施加反作用的敵人的世界觀,這在此即是:將人類與動物對立起來的,帶有等差階序的二元論。
各種二元論每每宣稱其已為所有的可能性標定位置,卻從來就只是同一枚硬幣的正面與反面,這塊硬幣以外的一切都遭到隱蔽、否認,甚至連想都不准想。
我們因此必須做的,就相當不得了了。二元論其中一元「以外」,從來不是與它對立的另一元,而是二元論本身以外。離開「文明」的狀態,並不是投身「野蠻」,正如揚棄「進步」並不意味著向「崩潰」屈服:反而正是脫離兩者之間的對立。是撬開被認為是對立的二元壟斷統治的世界。是進入一個沒有透過這些分類來組織過、建構過、整個變得好懂好理解的世界。關鍵在,我們必須在二元論的兩個陣營之間像刀鋒一樣璀璨爍亮,以從二元論聲稱封閉的世界另一邊出來,看看後面有些什麼。這是一門閃避的藝術,我們必須如蝴蝶一般翩飛,才能不被「自然」與「文化」、「只能在『大寫的人』(Homme-majuscule)與『遭同質化的動物』(Animal-homogénéisé)兩個爛蘋果裡選擇」、「『蠻荒自然的崇拜』與『充滿缺陷的自然之必要改良』的對立」的雙生巨石所俘虜。我們必須在繩索之間跳舞,以之閃躲「動物性是低等的獸性」與「動物性是高等的純粹」這樣的二元論。以之開闢一個仍未勘探的空間:一旦我們跨到另一邊的時候,那些尚待發明的世界。瞥見他們,展示他們,深呼吸。
那麼,在我看來,上述兩種對人與動物性關係問題的表述是錯誤且有害的:動物不比我們還禽獸,也不比我們還自由。牠們並不體現肆無忌憚的凶殘野性(這是馴養者的迷思),也不體現更為純粹的天真無染(這是上述迷思的反作用面)。牠們不比人類真實,也不比人類卑低:牠們所體現的,首先是──其他的生活方式。
關鍵正是這個「其他」。這個「其他」道盡了在擁有共同先祖的背景下,一種關於差異的自在邏輯。是一場潤物細無聲的文法革命。這場革命見證了一個小小的詞繁花盛綻、安插在所有這些日常用語裡:「人類與動物」、「與動物的差別」、「動物所沒有的」……
這小小的詞,正是「其他」。
「人類與其他動物的差別」;「其他動物所沒有的」;「人類與其他動物共有的」。
請設想所有可能的句子,然後加上其他。這是一個小小的形容詞,卻在重組世界面貌的工作中顯得如此優美:單單這一個字,就重新描繪了一套差異的邏輯與一個共同的歸屬。這個字重繪了經驗裡,彼此邂逅的生命之間那一座座橋梁、一道道開放的邊界。誰都一無所失。誠然,這個字無法讓我們深入這種種相似、種種差異。它做得到的,只有:使一套公義的邏輯成為自然,排除生物分類學的一樁嚴重錯誤,以文明之姿導入一套政治迴響久遠的心智地圖,以個體之姿再多內化一種平靜自在的小小真實(此一真實將會加入以下的行列:地圓說(rotondité de la Terre)、日心說(héliocentrisme)、演化論(évolutionnisme)、新自由主義有害論,以及「民主是最不糟糕的政治模式」 的說法)。
如果我們繼續推論,我認為我們可以說,我們與人類動物性關係的轉變因此就有了政治效應。我們與我們內在動物性的關係和我們與我們以外生物的關係息息相關。改變了前一種關係,後一種關係也隨之更易。這也許是西方現代性──無力感覺自己是生物一員、無力像生物一般互愛──的一個心理社會關鍵。接受我們身為生物的這個身分,恢復與自身動物性的連結,不把這個動物性想成該超越克服的原始性,也不把它想成更為純粹的野性,而將之視作應當接續、應當靈活調整掌握的豐富傳承,就是接受我們與其他生物的共同命運。接受人類在對自身動物性的精神支配中找不到自身的依託,只有在那值得追尋的、與我們內在生物力量的融洽相處之中才找得到,就是改變我們與外於我們的生物力量的基本關係。這就能歸納出,好比說,不再去假設「大自然」有所缺陷、必須由我們透過理性組織去改善,而是去找回對生物動能(dynamiques du vivant)的信任。去重新信任生態的、演化的如此動能,與如此動能協商出一套套各方都接受的模式的責任就落在我們身上;我們一部分也必須為了我們的需求而去影響、有時則去調節這些各方都接受的模式,但這樣的影響、這樣的調節,必須在一個共同生活的願景裡進行,這個願景留心著去發明、去創造我們對待共居地球的其他生命形式的種種合宜態度。
關鍵是,在文化與政治的層面上,把動物性的無數種形式以及與這些形式的無數種關係,化為成年人的議題。動物性真是大哉問:有了無數種動物的生命形式這些我們眼前的謎奧作為參考,人類的謎奧會更明晰、更能接受、更富活力。「在一個充滿相異性的世界共同生活」這個最道地的政治謎奧也在其中找到了其他的意義、其他的資源。
生態危機之為政治注意力危機
然而,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對生物能夠付出的關注與感受性,如此的全副注意力的藝術,往往遭到那些為了其他可能的世界而奮鬥的人輕易打發、賤斥為資產階級的、美學的或保守派的問題意識。這樣的注意力藝術其實是極度政治的。
如此的注意力藝術是政治的,因為政治隱微未顯、先於機關組織而存在的本質,就在決定「誰值得獲得關注」的門檻的移動之間發揮。近幾十年來,女性主義的問題就展現了門檻的移動,不同性別待遇差異的問題忽然就成為了吸引眾多關注的政治焦點。異化勞動(travail aliéné)的問題,也就是關注所有沒有生產工具但販賣自身勞動力的人的處境的問題,在早期資本主義裡成為自然而然的提問,從馬克思以降成為最強烈的集體關注的對象。一個人類群體,其注意力藝術的板塊變動以一個富有說明力的徵象表現出來:「能容忍的」與「無法容忍的」的感受。
一個君權神授的國王,如今已令人無法容忍:「能容忍的」與「無法容忍的」的無意識配置是一具精微靈敏的機器,它內化到每一個人裡面,受社會與文化的潮流所引導。關鍵在於,必須讓我們當今與生物的關係變得令人「無法容忍」。「田野鳥類、歐洲的昆蟲,以及更廣泛的周邊的生命形式,都因為不作為、生態破碎化以及開採主義(把一切都視作資源的開採產業的這個偏執的階段)而消失了」的這些現象對我們來說,必須變得跟君權神授的王室一樣難以容忍。而這是透過準備相遇──這些相遇讓生物能進入屬於「值得關注者」的政治空間──來達成的:所謂的「值得關注者」,就是那些「召喚人們對其小心對待、殷勤關注」者。隸屬關係讓人能擁有某種形式的擴大自我:我記得火車上,一名乘客惶惶不安望著窗外那落著春雨的天空。當他透露他憂心忡忡的原因,我一言不發:壞天氣並不會毀掉他的假期。他像談論一名親戚那樣對我宣說:「我不喜歡多雨的春天,春天多雨就苦了蝙蝠。昆蟲少了許多。蝙蝠媽媽沒辦法再餵養小蝙蝠了。」一個擴大的自我裡,其他生物喬遷入住;當然,要操心的事情又多了幾項,但奇怪的是,這也帶來了解放。只有在這之後,基本價值體系才會發生轉變,這樣的價值體系轉變並不是我們透過世界末日的宣告來讓人人都產生罪惡感所達成的;這樣的末日宣言所牽涉的生命在這些人的宇宙裡可從來不以生命之姿存在。
未來,當我們覺得對海洋生物的掠奪與授粉者(pollinisateur)的危機與君權神授的王室一樣難以容忍,當我們認為某部分採用肥料等投入物的工業化農業蔑視土壤的動物群就跟禁止墮胎一樣無可忍受,政治注意力的藝術就可說已改變了。
如此一來,某程度上,我們可以說,在大量訊息流竄的民主社會,政治位於文化的下游:這邊所說的政治,是指理想生活的表述,是指「能容忍的」與「無法容忍的」的各項門檻。因此,要改變政治,(除了挺身戰鬥、抗爭、以不同方式組織、敲響警鐘、在最靠近權力之處運用槓桿,以及發明其他居住方式之外)也必須變革留給重要事物的注意力的視野。這正是本文集第四篇文章的宗旨,這篇文章是邂逅了狼、雌羊、牧羊人、夜空與草地的戶外調查,它試圖勾勒出一種「彼此依存的政治」的輪廓。這項工作漫長但值得去做,因為我們還有幾千年的時間共同生活在這個生命雜駁際會的行星上。
我們集體政治注意力的視野要朝哪個方向開展?我們的系統性生態危機的問題,如果要從其最結構性的層面來理解,就是棲息地(habitat,亦譯棲地、生境)的問題。陷入危機的,是我們居住的方式。它之所以陷入危機,尤其是因為它對「『居住』永遠是與其他生命形式『共居』,因為一種生物的棲息地正是由其他種種生物所組成的」這樣的事實有內化其中的盲瞽。事實是,生物多樣性現今漸次死滅,一大原因正是生態破碎化,也就是其他生物的棲息地無聲無形地破碎了,毀滅了這些生物,我們對此卻渾然不覺,因為我們把我們的道路、城市、產業都蓋在一條條隱密又熟悉的路徑上,而這些路徑保障了這些生物的生存、這些生物作為族群的長遠繁榮。
生態破碎化在滅絕裡占據的分量具有不常為人關注的哲學意義:這種破碎化並非直接源於生產主義(productivisme)與開採主義的貪得無饜(雖然此兩者的貪婪是棲息地毀滅經過增強的當代面貌,召喚我們對之開展最激烈的抗爭)。生態破碎化首先源於我們對「其他生物也居住」此一事實的盲瞽:我們居住方式的危機來自我們拒斥其他生物「居住者」的身分。如此一來,關鍵挑戰在於:須讓居住者重新進駐繁衍。這個重新進駐繁衍是哲學意義上的,意指讓人能看見:組成饋養我們的環境的無數生命形式,自始以來就不是我們人類苦難的布景,而同樣是這世界理之必然、無庸置疑的居住者。因為,牠們以牠們的存在來製造。土壤微生動物(microfaune des sols,亦譯土棲微動物相)確確實實製造了森林與田野。森林與海洋植物製造了容納我們的可以呼吸的大氣。授粉者紮紮實實製造了天真的我們所說的「春天」,我們講得好像那是宇宙或太陽贈送的禮物:不,春天是牠們嗡嗡鳴響、無形無跡、遍及全球的行動以及牠們古老得無法追溯的復歸,這個行動在每年冬天終了之際,將花朵、果實以及大地的饋贈,都召喚到這個世界。授粉者──蜜蜂、熊蜂(bourdon)、鳥類──並不是四季理所當然的靜止布景上置放著的傢俱:牠們在春天的生命特質裡製造了春天。沒有牠們,三月左右日照增加時,我們也許會經歷雪融,然而雪融之處,將是一片荒漠:我們不會有櫻花,不會有其他任何的花,不會有異體受精(fécondation croisée,亦譯異花受粉)效應,而異體受精是被子植物生命周期的基礎(被子植物就是地球上所有開花植物,占了地球上植物生物多樣性的十分之九)。我們只會有一個永無止盡的冬天。授粉者這樣子的,我們可以說,「親手」製造了春天的一種存在,牠的地位並不是「布景的元素」,也不是「資源」。授粉者就是一個居住者,牠進入了各種勢力的政治視野,我們將必須與這些勢力協商我們共同生活的形式。
對生物的政治性不關心
現代性所謂的「進步」,其中一部分形容出了四個世紀的種種布置安排,這些布置安排讓我們不必去注意──不必去注意各種相異性、不必去注意其他的生命形式、不必去注意各個生態系。
我們在此針對的這個概念性人物(personnage conceptuel),我們可以呼之為「普通的現代人(moderne moyen)」(某種程度上,在號稱現代的文化區(aire culturelle)裡,我們全都是「普通的現代人」)。為了簡潔起見,我們在此將之命名為「普現人」(momo)。
既然普現人的奇特之處往往顯現於一種典型的殖民現象,就讓我們觀察這種現象吧。對一名西方殖民者來說,當他來到了非洲的叢林或亞洲的季風帶稻田,「使他落腳的空間變得文明」傳統上就是意味著去達成「能夠以『對人類以外的共同居住者一無所知』之姿活在當地」的目標,就是去消滅、控制、疏導野獸、昆蟲、雨水、洪澇。「在自己家」即是「能夠無所留心地生活著」。然而,對當地人而言恰恰相反,「在自己家」意味著不斷震顫的如是警戒、對其他生命形式之交織的如是關注;這種種人類以外的生命形式豐富了生活,雖然也必須對牠們讓步妥協,而這樣的妥協又往往要求嚴格,有時則相當艱難。在人類間的外交進退裡,和諧融洽的成本高昂,在與其他生物的關係裡也是如此。
現代人世界一大部分的技術與表述都為此服務,這就是它們的作用:豁免掉人們的注意力,也就是說,儘管在一無所知、亦即在不認識一個地方與其居住者的情況下,人們仍能無憂無慮、什麼都不在意,於任何地方作業、到處作業。這斬斷了人與周遭生物世界裡索求慷慨關注的事物──與授粉者、與植物、與生態動能、與氣候的交織──的連結。這是一種實用的形上學,其秘密但強大的功能是「可替換性」(interchangeabilité):所有地方、所有技術、所有實踐、所有本事、所有生命、馴養的蜜蜂、蘋果的種類、小麥的品系……一切種種都應該可以彼此替換。其意在透過同質化生命的狀態來達成「到處都是在自己家」的目的,免除掉認識其他生命的行為學以及一個地方的生態學──也就是居住、構成該處的各支生物民族 的習俗──的需要。而這是為了讓人能將心力投注在普現人眼中的「重要事物」:人類同胞間的關係。權力的關係,聚斂積攢的關係,聲譽威名的關係,愛的關係,家庭的關係──這一切以無生命的、由上千萬其他物種所組成的布景為背景。順帶一提,這些物種都是我們的親戚。
這是非常矛盾的一種現象,因為在某些方面,這樣的做法帶來了舒適及有利的效果。我們並不是要愚騃而極端地鼓吹往相反的方向衝刺,從耀武揚威的現代性轉變到悛悔痛懺的反現代性。我們要做的,是取其中庸:有一些生命,我們必須重新學習關注牠們。因為目前,現代性的舒適逆轉了:我們不再關注生物世界、不再關注其他物種、不再關注環境、不再關注把大家編織在一起的生態動能,長此以往,我們歪七扭八創造了一個喑啞荒謬的宇宙;從存在的、個人的與集體的尺度來看,活在這個宇宙裡都非常不舒適。尤其是,我們製造了全球暖化以及生物多樣性危機,它們具體威脅著地球對人類來說的居住條件。
矛盾因此在於,「不再受環境及其居住者要求的關注所拘束」這種現代人的藝術在某個階段帶來了可觀的舒適感;然而,一旦它超過了某道門檻或採取某種形式,就變得比不舒適還糟糕:它讓世界變得令人難以生存。問題變成了:明確說來、認真說來,那個門檻是什麼?那些形式是什麼?如何有智慧地繼承現代性,如何於我們的歷史遺產裡,在必須珍惜、保護的擺脫束縛與有害的漫蕩亂闖之間,獲致平衡?這是本世紀的一道大哉問。這個問題是航海時所須的羅盤:把穩方向,在波濤間從兩種非此即彼的立場之間穿越。是哪兩種善惡二元論的立場?一邊,是風起雲湧的反現代浪潮,一視同仁譴責所有的「現代性」這惡的化身,同時卻又享受著現代性的各種產品;另一邊,是超現代的態度,意欲乘著同一艘大寫的「進步」(Progrès)之艦加速直衝,我們如今知曉這個大寫的「進步」是最糟的航向,超現代的態度卻捍衛「別無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TINA) 這可憎的教條,這道信條讓人能夠不去思考、不去挺身戰鬥、不去質疑我們繼承的遺產裡那有害的部分。
走出密室
一個物種把構成自己家族的其他一千萬個物種、饋養自己的環境、自己日常的共居者,全都轉化為由可取用材料所組成的布景,供自身的人類苦難所用。說得更精確些,做出這件事的,是此物種裡的某個小族群,他們承載了一套歷史的、地方的文化:因為,讓其他物種隱形,是很晚才出現的地方性現象,全體人類並非皆如此。請想像一支民族來到一塊居住了其他無數民族的土地,牠們全是這支民族的親戚,後者宣布牠們並不真正存在,並沒有那麼地存在,還宣布牠們是舞臺而非演出者(啊,是的,這可不是需要許多想像力的虛構,而也是我們歷史一塊塊重要的組成)。我們是怎麼走進如此神奇的盲瞽裡,視而不見其他的生物民族?在此,為了再更彰顯我們繼承的遺產那怪異之處,我們可以大膽建構出一段述說我們文明與其他物種所持關係、最後將抵達現代境況的一分鐘簡短歷史:當生物在本體論上遭到貶低,換言之,被視為擁有較次等的、價值較低的、較無實質的存在,因而遭轉變為「物」,人類就成了宇宙中唯一真正存在者。
只要猶太-基督信仰為了讓「自然」失去宗教意味,逼得「自然」之神逃逸消失(這是埃及學家揚.阿斯曼(Jan Assmann)的假說),接著再讓科學與工業革命把剩餘的自然(中世紀經院哲學所說的phusis)轉變成沒有心智、沒有無形影響、為開採主義自由取用的材料,人類就成為了宇宙裡的獨行騎士,周圍盡是愚昧又邪惡的物質。最終的行動則意在殺死至此僅存的附屬關係:獨自面對這些物質的人類,仍與上帝維持垂直的聯繫,上帝將這些物質神聖化為其創造物(自然神學的主張)。上帝之死導致了此一恐怖而完美的孤獨,我們稱它為:人類自戀(anthroponarcissique)的密室 。
這種對我們的宇宙性孤獨感的虛假清醒,導致了全體非人類遭到泰然自若地排除於本體論認定的「重要事物」之外。如此的虛假清醒解釋了歐洲與盎格魯-撒克遜各大首都的所有「密室」哲學與文學。這詞彙可不是隨便選的:此處談的確實已是沙特劇作《密室》(Huis clos)意義上的那座密室,不過我們談的這座封閉房間卻是世界本身,是宇宙,其中居住的只有我們以及我們與人類同胞的病態關係,這種病態關係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我們與其他生物、動物、環境的多元的、情感的、積極的關係都消失了。
人類的宇宙式孤獨此一主題因為獲得了存在主義標舉而偉大,充斥於二十世紀的文學與哲學之中,其實暴力得令人困惑。這種暴力披著卡繆式荒謬的英雄主義外皮,以真理的勇氣為幌子,憑著心盲眼瞎,透過拒絕學習去看見他者的存在形式,否定了他者的共同居住者身分,逕行推定牠們其實沒有交流的能力、沒有「原生意識」、沒有創造性的觀點,沒有達成各方都接受的模式的能力,沒有政治邀請(invite)。這是西方自然主義博大精深的藝術,因此亦是其隱藏的暴力,實則意在讓「我們把自然當成唾手可得的原物料來剝削,以此襄贊我們的文明大計」變得名正言順──也就是把其他生物當作受生物規律轄制的物質來對待,拒絕看見牠們的地緣政治邀請,拒絕看見賴以為生的盟約,拒絕看見促成下述事實的所有要點:我們與生物共享一個大外交共同體,於此共同體中,關鍵將是:重新學習怎麼生活。
人類主體孤獨廁身於荒謬的宇宙裡,周遭圍繞著唾手可得的純粹物質,這些物質是人類的資源庫或是心靈上尋根溯源、恢復活力的聖殿──這是現代性杜撰出來的幻覺。以此角度觀之,沙特或卡繆成功躋身的標舉解放的大思想家,很可能已將自己的觀念深深注入法國的傳統,其實這些思想家是開採主義與生態危機客觀上的幫凶。將這些解放的論述重新詮釋為重大暴力的傳播媒介確實耐人尋味。然而,將「在一個充滿無活動力且荒謬的客體的世界,我們是唯一的主體,是自由的;我們注定要以我們的意識來為一個缺乏意義的生物世界賦予意義」的迷思轉變為晚期人文主義的基本信念的,奪走了生物世界自始擁有的東西的,正是這些標舉著掙脫桎梏的論述。維威洛斯.德卡斯特羅與德斯科拉(Descola)筆下的薩滿教徒和泛靈論(animisme,亦譯萬物有靈論)者則對互惠、交換與掠食的複雜社會關係瞭若指掌,這些關係並不是和平、消弭爭端,並不遵循以賽亞(Isaïe)的預言,它們是政治的,它們的政治性仍謎奧難解,這些關係召喚著種種形式的重獲和平,種種形式的和解,種種形式的彼此幫助、彼此尊重的同居共處。這正是本文集後記的旨趣。
因為,生物之中,處處是意義:這些意義不必由外界投射,而是要以我們自己的方法去重新發現出來,換句話說,這些意義是要去翻譯、去詮釋的。應當開展的,是外交行動。必須要有翻譯者、代言人、中介者來進行重新了解生物的工作、來超越我們不妨稱之為「李維史陀詛咒」的障礙:和與我們共享地球的其他物種溝通交流是不可能的。「猶太-基督信仰的傳統儘管噴灑了墨水的雲霧來遮掩,仍沒有其他處境對心靈、對精神而言,比人類的處境還顯得悲劇、還顯得令人不適:人類與其他活生生的物種共同生存於地球上,共享地球的好處,人類卻無法與這些物種溝通交流 。」
然而,此一「不可能」是現代人的虛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