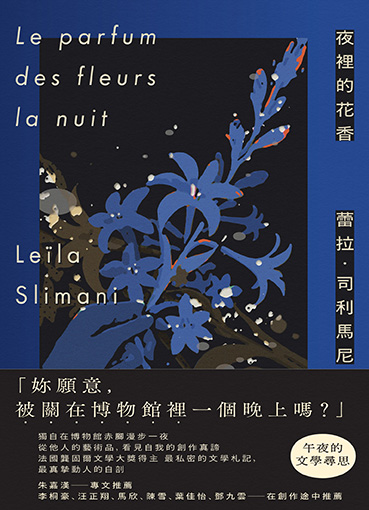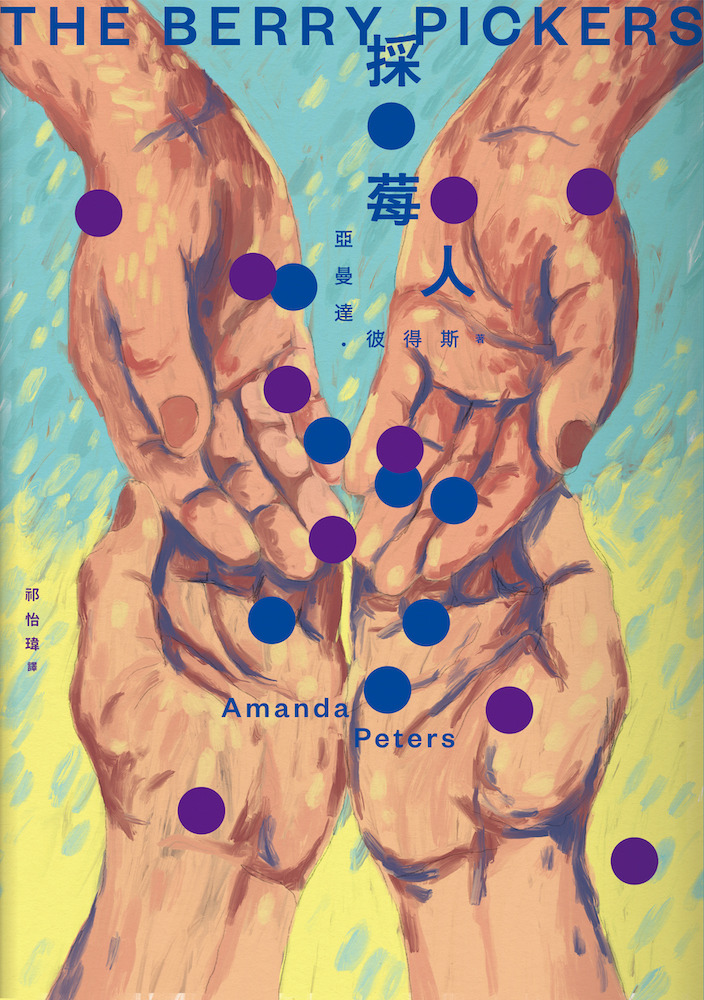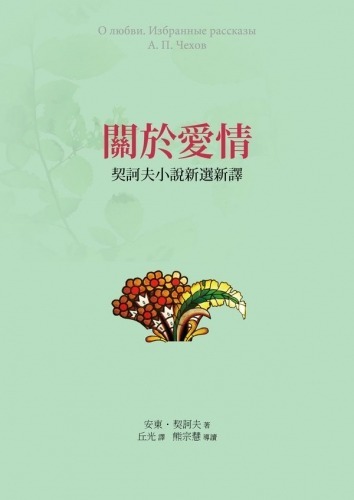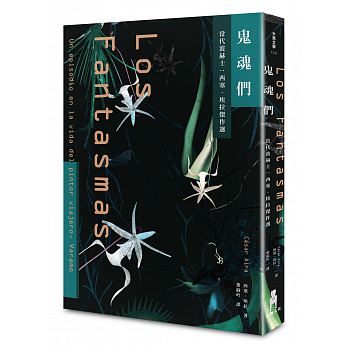法國龔固爾文學大獎得主
最私密的文學札記,最真摯動人的自剖
「妳願意,被關在博物館裡一個晚上嗎?」
獨自在博物館赤腳漫步一夜
從他人的藝術品,看見自我的創作真諦
理解創作就是開闢出自己的自由之地
龔固爾文學獎蕾拉‧司利馬尼,在開頭即陳述,寫小說的守則就是「說不」。然而,她為何最終又願意點頭,前往威尼斯的海關大樓博物館住一晚?
館中夜間打燈的玻璃溫室,種植夜來香的枝葉,讓蕾拉想起自由的氣味。由青銅、大理石、縞瑪瑙製成的雕塑,再現了扶手椅的形狀,喚起蕾拉對於父親生前坐著的記憶。
獨自在博物館的孤寂吸引了蕾拉,她漫步其中,靜觀各色藝術品,並從這些作品中反思她所極盡追求的文學究竟代表著什麼。
書中並引用許多作家的短語,從吳爾芙衍生到為何創作者需要獨處的空間;又或者2023年遭刺傷的魯西迪,他對於寫作的堅持,也啟迪了蕾拉,以文學批判自身國族時,該如何接納他人的不諒解,並且持續、不顧一切地寫下去。
《夜裡的花香》以蕾拉的第一視角走訪博物館,並從各種不同的物件中思考創作的意義,也是對於生命裡,無論傷痕或喜悅的再次記憶。
不當作家,我很可能仍舊可以活下來。
但我不確定,那樣的話,我會不會幸福。
朱嘉漢w專文推薦
李桐豪、汪正翔、馬欣、陳雪、葉佳怡、鄧九雲w在創作途中推薦
w書中金句w
「寫作,是自我束縛;然而,正是在這些束縛之中,誕生了一種無垠的、令人迷眩的自由的可能。」
「寫作是紀律。是對幸福、對日常歡樂的放棄。我們不能試圖療癒或撫慰自己。相反地,我們應該像實驗室人員在玻璃瓶裡培養細菌那樣培養自己的悲傷。必須撕開傷疤,翻動記憶,重新煽起羞恥與舊日的眼淚。」
「寫作不能僅僅只是抽離、退隱,沉湎於公寓的溫暖中,寫作不能僅僅只是築起重重磚牆來讓外界傷害不了自己,而不去直視他者的眼睛。」
封面燙上隱隱閃光的珍珠箔,呈現低調優雅色澤,
在暗夜中,引領每一位創作者找到屬於自己的花朵與芬芳。
本書特色
Ø在編輯的邀請下,蕾拉‧司利馬尼展開了在博物館住一晚的特別計畫。在短暫的一夜中,回望她生命中的起伏、創作歷程,寫下精闢感悟。
Ø蕾拉‧司利馬尼如絮語般滔滔傾訴對於創作的理想與堅持,也交織了寫作必然面臨的衝突與兩難。寫作者未必同意蕾拉的每一個觀點,但《夜裡的花香》會是一本創作者的自我提醒之書。
Ø本書沒有晦澀的藝術術語,只有從作品連結到個人生命的啟發,讓我們先是想像藝術品,閱讀蕾拉的解讀,進一步反思自己的過往。
推薦記錄
《夜裡的花香》令人耳目一新……作者以如此優雅、易讀的風格,捕捉了對於寫作的癡迷與喜悅,以及藝術與文字的力量。──英國藝術史學家、策展人凱蒂‧赫塞爾(Katy Hessel)
這位小說家從未如此坦率,《夜裡的花香》是關乎作家與文學創作的傑作。──《費加洛報》(Le Figaro)
朱嘉漢w專文推薦
李桐豪、汪正翔、馬欣、陳雪、葉佳怡、鄧九雲w在創作途中推薦
蕾拉‧司利馬尼(Leïla Slimani, 1981-)
出生於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父親是銀行家,母親是醫生。17歲時離開摩洛哥,赴巴黎求學,從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ESCP歐洲高等商學院畢業後,於《青年非洲》(Jeune Afrique)雜誌擔任記者,負責北非領域。
2011年,兒子出生後,蕾拉在報導阿拉伯之春期間被逮捕,隨後她辭去工作,專職寫作並投入小說創作。曾任法國總統馬克宏OIF(法語圈國際組織)的個人代表、2023年國際布克獎評委主席。
首部小說《食人魔的花園》(Dans le jardin de l'ogre)於2014年一出版便廣受好評。2016年,出版第二部小說《溫柔之歌》(Chanson douce);這本以紐約真實社會案件為背景所寫成的作品,甫一出版即引起巨大迴響,不僅在法國締造驚人銷售佳績,更贏得法國龔固爾文學大獎。
《夜裡的花香》不同於蕾拉的小說作品,是以非虛構的文體呈現,更加貼近作者的生命歷程,運用誠實、真摯的筆觸,直面創作的艱難與美麗。
林佑軒
寫作者、翻譯人,巴黎第八大學碩士。
聯合報文學獎小說大獎、時報文學獎散文首獎等項得主,數度入選九歌年度小說選、散文選等集,作品參與臺灣文學外譯計畫,並為文學雜誌執筆法語圈藝文訊息。
著作三種:小說集《崩麗絲味》(九歌,二○一四)、長篇小說《冰裂紋》(尖端,二○一七)、散文集《時光莖》(時報,二○二一,Openbook好書獎年度中文創作入圍)。
法文譯作六種:《大聲說幹的女孩》(聯合文學,二○一九)、《政客、權謀、小丑:民粹如何襲捲全球》(時報,二○一九,臺灣法語譯者協會法國巴黎銀行翻譯獎入圍)、《世界大局.地圖全解讀》卷二、三、四(野人,二○二○至二○二二,合譯)、《在雪豹峽谷中等待》(木馬,二○二一)、《生之奧義》(衛城,二○二一)、《零號病人》(大塊,二○二二)、《時間、欲望與恐懼:如何再現最真實的歷史樣貌,阿蘭.柯爾本的感官史講義》(臺灣商務,二○二二,合譯)。
請見:https://yuhsuanlin.ink/
推薦序:寫作與抵抗/朱嘉漢
巴黎,二○一八年十二月
威尼斯,二○一九年四月
如果想寫小說,守則一就是說不。不,我不會來喝一杯。不,我無法照看我生病的姪兒。不,我沒空吃個午餐,受個訪,散個步,看個電影。必須說不的次數多到邀約漸漸少了,電話不再響起,於是開始遺憾:怎麼電子信箱只剩廣告信了。必須說不,裝出厭惡人類、目空一切、病態孤獨的模樣。必須在自己周遭豎立一道拒絕的牆,所有的請求撞上了就粉碎。我剛開始寫小說的時候,我的編輯就是這麼跟我說的。這也是我在所有談論文學的隨筆裡讀到的,從菲利普.羅斯到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都這麼談,中間還有海明威──海明威簡單通俗地總結了這一點:「作家最大的敵人是電話與訪客。」他還說,反正,一旦紀律建立了,一旦文學成了中央,成了核心,成了生活唯一的前景,孤獨就成為必然。「朋友們死亡或消失,也許他們厭倦了我們的拒絕。」
幾個月來,我都強迫自己這樣做。我逼自己為自己的與世隔絕打造好條件。每天早上,小孩去了學校,我就上樓到我的書房,傍晚以前不出來。我把電話切掉,坐在我的桌子前或躺在沙發上。最後我總是覺得冷,隨著時間推移,我套上一件毛衣,然後是第二件,最終把自己裹在毯子裡。
我的書房寬三公尺,長四公尺。右邊的牆上,有扇窗面對中庭,餐廳的味道從中庭飄上來。洗衣服的味道,還有肥豬肉丁燉小扁豆的味道。中間呢,一塊長木板就是我的工作桌。書架塞滿了歷史書籍與剪報。左邊的牆上,我貼了顏色各異的便利貼。每種顏色對應一個年分。粉紅色是一九五三年,黃色是一九五四年,綠色是一九五五年。我在這些小紙條上寫了某個人物的名字,某個場景的想法。瑪蒂爾德在電影院。阿依莎在榲桲果園裡。有一天,我有了靈感,於是為這部我努力從事而還沒有標題的小說建立了時間表。這部小說講述一九四五年至摩洛哥王國獨立期間,梅克內斯這座小城的一個家庭故事。一幅梅克內斯的地圖,一九五二年的,在地上攤了開來。從這張地圖,我們可以清楚看見阿拉伯、猶太、歐洲三個城區之間的界線。
今天不是個好日子。我坐上這張椅子好幾個小時了,我的人物卻不對我說話。什麼都沒來到。隻字片語沒有來,圖像沒有來,能讓我開始落筆造句的音樂起頭也沒有來。這個早上到現在,我菸已經抽了太多,我把時間浪費在一個個網站上,又睡了一個午覺,還是什麼都沒有。我寫了一個章節,又通通刪掉。我想起了朋友告訴我的一個故事。我不曉得這個故事是不是真的,不過我很喜歡。故事是這樣的:據說托爾斯泰撰寫《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énine)的時候,曾嚴重感到靈感匱乏。連續好幾個星期,他一行字都沒寫。他的出版商已預付給他在那個時代相當可觀的一筆錢;稿子遲遲不來,托爾斯泰大師毫無動靜,也不回信。憂心忡忡的出版商決定搭火車去當面問他,來到了亞斯納亞波利亞納。這位小說大家接待了他,當出版商問起小說進度到哪了,托爾斯泰回答:「安娜.卡列尼娜離開了。我等她回來。」
我絕對不是企圖自比這位俄羅斯天才,也完全沒有要把我的任何小說與他的傑作相提並論。然而,纏擾我心的,正是這一句話:「安娜.卡列尼娜離開了。」我也是這樣啊,有時候,我覺得我的人物一個個逃離我,動身開展另一種生活了,只有當他們決定了要回來,他們才會回來。對我的苦惱、我的祈禱,甚至對我投注於他們的愛,他們都完全無動於衷。他們離開了,我必須等他們回來。他們在的時候,時光流逝,而我渾然不覺。我嘴裡呢喃,下筆飛快,盡可能地快,因為我總是害怕我的手跟不上我的思路。這個時候,一想到可能有個什麼東西來打壞我的專注,讓我淪為一個犯了向下看這個錯誤的走鋼索的人,我就驚懼不已。當我的人物在這裡,我整個生活都圍著這執著旋轉,外在世界並不存在。外在世界就只是個布景罷了,一天漫長而甜美的工作後,我狂亂怔忡,行走其中。我遺世而獨居。離群索居對我來說似乎是唯一真實的生活乍然臨到的必要條件。彷彿讓自己遠離世界的噪音、保護自己不受這些噪音干擾,就能讓另一種可能性終於浮現。讓一個「好久好久以前」浮現出來。在這封閉的空間中,我逃脫至此,逃離了人間喜劇,深深沉浸事物厚厚的泡沫下。我並沒有拒絕世界,相反地,我從來沒有這麼強烈體驗世界過。
寫作是紀律。是對幸福、對日常歡樂的放棄。我們不能試圖療癒或撫慰自己。相反地,我們應該像實驗室人員在玻璃瓶裡培養細菌那樣培養自己的悲傷。必須撕開傷疤,翻動記憶,重新煽起羞恥與舊日的眼淚。為了寫作,必須拒絕別人,拒絕出現在別人面前,拒絕給予別人溫情,必須讓朋友、孩子失望。對我來說,這種紀律既是滿足、甚至幸福的原因,也是我憂鬱的緣由。一個個「我必須」支配了我全部的生活。我必須閉嘴。我必須專心。我必須坐著。我必須抗拒我的渴望。寫作,是自我束縛;然而,正是在這些束縛之中,誕生了一種無垠的、令人迷眩的自由的可能。
我記得我是哪時候意識到這一點的。那是二○一三年十二月,我正寫著我的第一部小說:《食人魔的花園》(Dans le jardin de l’ogre)。我當時住在侯煦夏大道。我的兒子還小,我必須趁他去托兒所的時候寫作。我坐在餐桌前,面對我的電腦,想著:「現在,妳完完全全可以說妳所有想說的話了。妳啊,妳這個有禮貌的孩子,妳曾學著表現良好,學著克制自己,妳現在可以說真話了。妳不必討好任何人。妳不用害怕會讓哪個人難過。把所有妳想寫的都寫下來吧。」在這遼闊無邊的自由裡,社會面具脫落了。我們可以成為另一個個體,不再被某種性別、某個社會階級、某種宗教或某個國籍所定義。寫作,就是發現創造自己、創造世界的自由。
當然,像今天一樣不愉快的日子所在多有,有時候甚至接踵而至,帶來了深深的氣餒。不過呢,作家有點像鴉片成癮者、像任何受癮頭所害的人,作家忘記了副作用,忘記了反胃感,忘記了戒斷之苦,忘記了孤獨,只記得那心醉神迷的狂喜。作家不惜一切代價,就為了再次經歷這個高潮,這個人物開始透過作家說話,生命悸動閃爍的崇高時刻。
傍晚五點了,夜幕已然垂落。我沒有點亮小燈,書房沉入了黑暗中。我開始相信,在這片陰暗裡,會有個什麼翩然而至,也許是最後一刻姍姍來遲的熱情,也許是閃電般猝然臨到的靈感。有時候,黑暗能讓幻覺與夢境像藤蔓一般開展。我掀開我的電腦,重讀昨天寫的一個場景。我的人物在電影院度過了一個下午。一九五三年,梅克內斯的帝國電影院放映著什麼電影?我於是投入研究,在網路上找到了一些動人心弦的檔案照片,趕緊將它們寄給我母親。我開始書寫。我記得我的祖母是怎麼跟我談論摩洛哥電影院的女帶位員的,她們高大粗魯,硬是從觀眾嘴裡扯掉菸。我準備好要開始新的一章,電話的鬧鈴卻響了。我半小時後有一個約。這個約啊,我之前不曉得如何說不。阿琳娜(Alina)這位等著我的編輯是一位擅長說服的女人。這位熱情的女人有個邀約要提給我。我在想要不要寄一封懦弱又撒謊的訊息給她。我大可拿我的小孩當藉口,大可說我病了,說我沒趕上火車,說我母親讓我抽不開身。但我披上大衣,把電腦塞進提包,離開了我的洞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