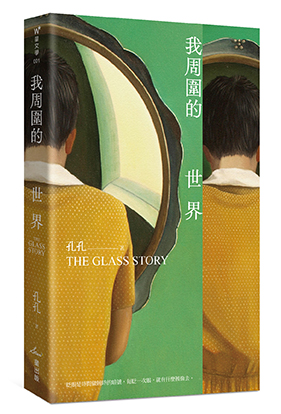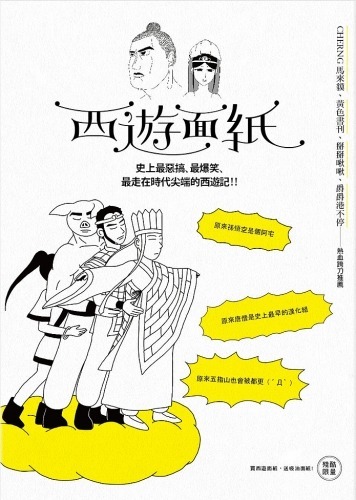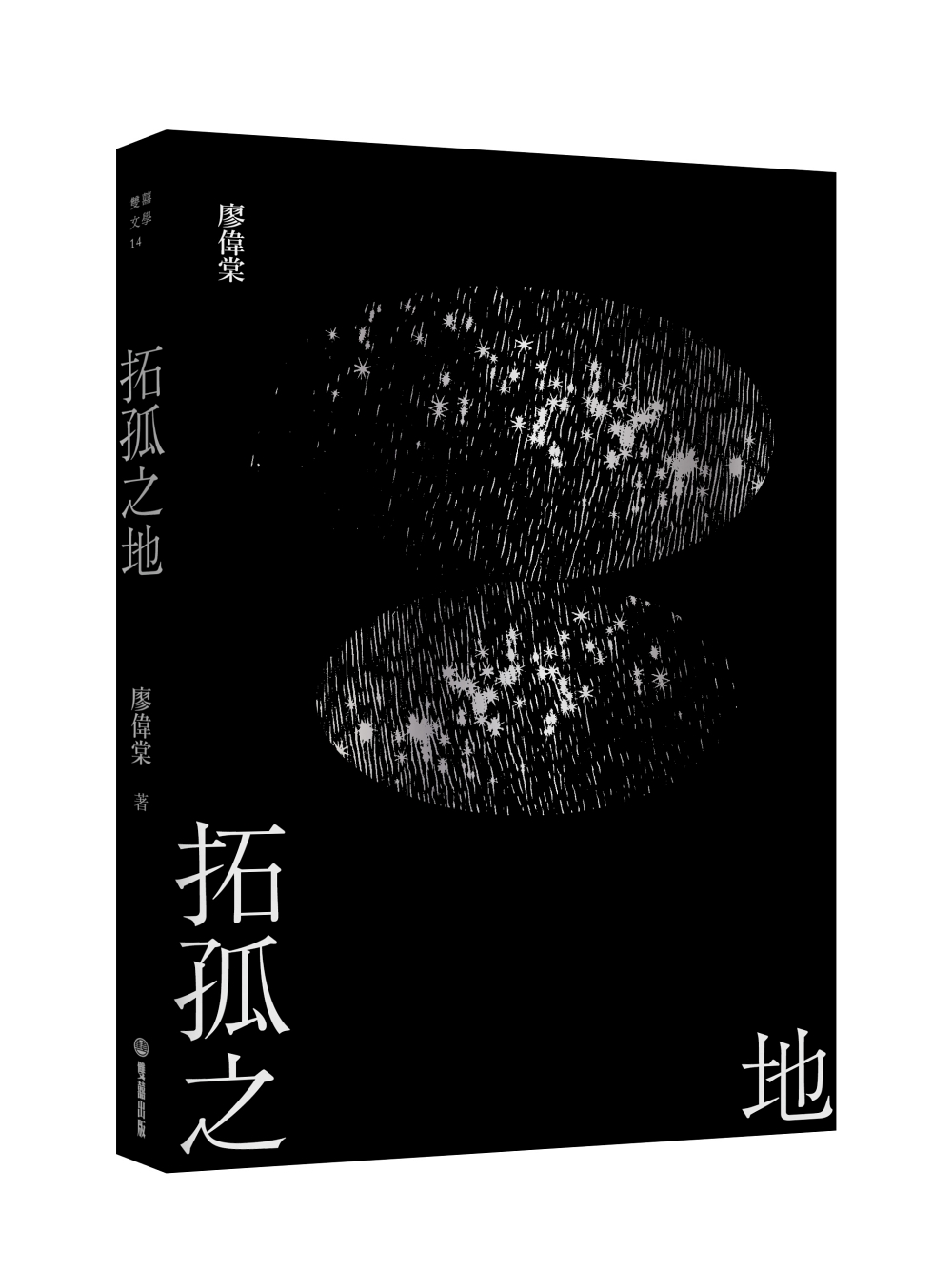第7屆台積電文學賞正賞得主孔孔首部長篇小說
姚謙、周芬伶、張貴興、鍾文音 誠摯推薦
陳香蘭恍然悔悟:「還是你小時候乖,我指鼻子,你就說鼻子,我指眼睛,你就說眼睛。」說的是周葦早忘得一乾二淨的某個童年遊戲,據說人無法保留三歲之前的記憶,陳香蘭卻堅持認為那是屬於她們母女的最好的時光。
陳香蘭不明白,她含辛茹苦、忍辱負重、全心全意養育出來的女兒為什麼最終卻變成了她的仇敵,而周葦不明白的是,為什麼她一絲不苟、戰戰兢兢、竭盡全力地向陳香蘭的完美目標靠近卻總是在快要成功時又被她一把推倒在地。
一篇一個世界,打開你的心靈之眼
|水泥盒子 |啞巴鬼魂 |皮鞋遊戲
|謊言小史 |鞋碼人生 |海的女兒
|尋人啟事 |神祕房間 |荒原宇宙
|芭比娃娃 |月球往事 |相機魔術
|災星夜晚 |魔藥時間 |光明之地
誠摯推薦
姚謙|音樂人、文字者、收藏者
周芬伶|東海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
張貴興|知名作家、2023年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得主
鍾文音|知名作家
「這是一場又痛快且有挑戰的閱讀經驗,孔孔這位年輕優秀的創作者,以她的文字強大的流動力量引我游動在她所繪製出的世界;即使這是一個已被重複描述很多次的類型,關於原生家庭、母女等某人的世界。她的筆依然有著很強烈的獨特感,不只是故事,而是她切面著手的角度和意識流的描述。讀著、讀著居然有種魔幻文學的魅力,心陷奇異無邊的境地。孔孔既主觀又當代性的審美,是這一代新文學創作者特有的氣質。她完全地說服了我,新的文學時代已經到來。」——姚謙,音樂人、文字者、收藏者
「好的小說在能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就這點而言,孔孔具備這樣的文字魔力⋯⋯在此時此刻,台灣文字走向直白與實用之際,孔孔的文字顯得特別典雅⋯⋯這本長篇,最好的還是文字,其靈巧生動更勝於〈我見夕陽與朝陽無異〉,分章節的題目也很別致⋯⋯孔孔還很年輕,第一個長篇就有這樣的成績,我想她不僅此而已,未來應該還有黃金大道等著她。」——周芬伶,東海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
「孔孔是真正的超新星,讀其小說,文字瞬即閃爍我心,常使我心跟著移位,思索,漫溢,翩飛。其人輕巧如燕,其文神采如蝶,讓我過目難忘。她的慧眼射向這荒蕪暖涼的周圍世界,既世故又純真,既老練又新手,悄悄偷渡流年,深深置換記憶,層層剝開時光,是一位埋藏豐饒詩心的小說家。」——鍾文音,知名作家
孔孔(孔曉莉)
1992年生,重慶人,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曾獲第四十八屆香港青年文學獎小說高級組亞軍,短篇小說〈動物園裡有什麼〉首發《十月》,中篇小說〈我見夕陽與朝陽無異〉獲得2023台積電文學賞正賞,《我周圍的世界》是孔孔的首部長篇小說。
目錄
繁體中文版專序
水泥盒子
啞巴鬼魂
皮鞋遊戲
謊言小史
鞋碼人生
海的女兒
尋人啟事
神祕房間
荒原宇宙
芭比娃娃
月球往事
相機魔術
災星夜晚
魔藥時間
光明之地
在我們周圍的小說世界——談孔孔的長篇 周芬伶
(內容連載)
水泥盒子
童年時,回家這件事常常讓周葦感到恐懼。
黃昏是一隻快要熄滅的手電筒,夜拿著它站在路口,拖出一截驚悚鬼影,等著將孩子、飛鳥和白日通通抓捕回去。沒有漏網之魚。蟋蟀在草叢裡發出看熱鬧的聲音,塑料瓶裡蝌蚪停止了找媽媽的遊戲。媽媽們都藏在水泥盒子裡,被手電筒照成斷章的皮影。但別誤會,那並不是無聲的把戲,相反,它嘹亮而持續。二字節和三字節交替遞進,空中落下名字的黑雨,被淋了滿身的孩子們再無處可去,除了那唯一亮燈的庇護港、安全地——水泥盒子。
一開始,水泥盒子的角落擺著張鋼絲床,那是陳香蘭從第二醫院搞到的,她總是有辦法弄到些免費的東西。等到長大一些,周葦就開始明白,它們並非真的免費,世界上一切東西都有價格,只是使用的不是同一種貨幣。每次拿到這些東西後,陳香蘭就會開心上一陣子,不是東西讓她開心,而是免費讓她開心。
「你媽我還是有點本事的吧?」
她甩出問題,卻不需要周葦的回答,東西本身就是最好的回答。有時,她又會突然被床頭的刮花、布料的抽絲或者某處可疑的污漬刺痛,意識到這些東西的廉價、粗糙,她本該早點意識到的,不該等到它們已經滿滿當當地充塞著這間屋子和她的生活才後知後覺地頓悟。它們經年累月地堆成城牆,牆上每一塊撿來的磚石都在無言諷刺:沙發上衣服堆砌的亂葬崗,過一段時間就要除冰的冰箱,一到下雨天就開始捲邊的牆紙,生拼硬湊在一起的不搭調的家具……一切都有可能引發她的無名火,而越是憤怒,人就越是感覺到無力,她可以掀翻這些家具,甚至一把火燒了這間房子,但她始終沒那樣做,她只是回過頭,將槍口對準周葦——這個與生活合謀的小偷,偷走了她的青春和生命。多年來,她反復說著一句不知從哪學來的台詞:「早知道跟周衛華借了這麼一個種,還不如把你拉到廁所裡去。」玻璃罐裡的一對母女蛾,無論如何撞擊,牆永遠在那裡,呈現出無動於衷的透明。於是,只能恨另一隻飛蛾。陳香蘭告訴周葦,是她毀掉了她這輩子最重要的機會。
「我本來可以去市裡的。」
「我本來能有一份好工作的。」
「我本來可以不生你的。」
「我本來可以……」
小學的語文作業要求用「本來」造句,九歲的周葦寫:「她本來可以不是我媽媽。」老師用紅筆畫了叉,附著二字批注:「荒唐」。周葦不懂「荒唐」的意思,拿字典查,上面寫「誇大不實」。許願為何不能誇大不實?後來周葦才弄明白,「本來」不是用來許願的詞,只是陳香蘭總愛拿它搭配夢想中的人生,使她誤會。語文老師找來陳香蘭,交出周葦的作業本,指著辦公桌前立著的一幅精心裝裱的書法,苦口婆心:「育人先育德,這是前幾年我受表彰時,部裡頒給我的,意思是讓我們做旗手,把這種教育精神發揚下去。孩子還小,不要打,好好說。」
陳香蘭沒有打,也沒有說。回到家,她只是麻利翻出一隻蛇皮袋,再更麻利地把周葦的衣服從衣櫃一股腦拽出,花花綠綠的袖子們、褲腿們你絆著我,我推著你,鬧哄哄像以為是要被帶出去春遊。可外面早已入冬,冷風把人的閒情逸致都刮乾淨了,街上每個人都縮緊脖子趕著回家,只有她們這對提著行李的母女逆著人流不知要去哪裡。
在長途汽車站門口,母女倆才終於停下腳步。周葦認得那個牌子,也認得站外的大巴和行李,鐵軌還沒鋪進這座小城的年代,要離開這裡去遠方的人都需途經此地。只不過她們到得太晚,當天最後一趟大巴的票已經售罄。車站空得像一口冷鍋,冷鍋裡零星散落著旅人,他們的厚衣服鼓起,瑟縮著脖子和面孔,是一個個冷掉的饅頭。很快,陳香蘭也成了這些饅頭中的一個,她抿緊嘴抱著臂坐在塑料椅上,袖管露出的一截手腕泛著白皮屑,看上去又乾又硬,出門時,它折疊過來一把拽住周葦時,周葦只覺得疼。但她沒開口喊疼,她知道陳香蘭在生氣,陳香蘭生氣時只會戳著她的腦袋說:「不疼怎麼長教訓?」好比不喝牛奶怎麼會長高,不吃點苦頭怎麼能成材。陳香蘭用「不」字圈出的世界,首要的就是別對她說「不」。於是,周葦什麼都沒說,沒問她們為什麼會來這裡,也沒提出想回家的念頭,即使這個念頭在她腦子裡早急得跳腳,她盡量小聲在暗地裡掩著嘴將它安撫:「別急,再等等。」其他人也在等,沒什麼地方比候車廳裝了更多的等。檢票員倚著鐵欄杆等著下班,哈欠打得下巴快脫臼,司機師傅和等著大巴出發的乘客圍在一塊吞雲吐霧,聯排塑料椅上,有人把行李鋪在身下,在睡夢中等待明日的旅途。至於陳香蘭在等什麼,周葦不知道。無事可做的她只能晃蕩著兩條腿,探出腦袋打量捲在衣服和髒被褥裡的人,他們看起來像長出了一層殼,殼裡藏著夢的軟體。沒一會兒,周葦就感到了一種傳染開的困倦,就在腦袋開始一點一點搗起蒜的時候,耳邊忽然響起了陳香蘭的聲音:「餓了嗎?」陳香蘭盯著迷迷糊糊還沒完全清醒的周葦,抬起手替她捋了捋額角的碎髮。她一度很擔心周葦不能長出好的頭髮,她嬰兒時頭髮又黃又稀,剪過幾次後才像活過來的樹苗一樣,漸漸濃密了起來,如今倒像野草似的。這個孩子和她一樣,似乎怎麼樣都能活下去。陳香蘭放下胳膊,指尖摩挲著蛇皮袋磨損得有些發白的邊緣,沒等到周葦的回答,又來了句:「餓了就去那邊小吃攤買點吃的。」陳香蘭從兜裡掏出了幾塊疊得整整齊齊的錢,先給了周葦兩張,想了想,又給了幾張,給完之後,似乎有些心煩意亂,把剩下的錢往口袋裡胡亂一塞,打發周葦趕緊去。周葦拿著錢,看了一眼陳香蘭,又看了一眼小吃攤,搖搖頭,說自己不餓。陳香蘭的臉垮下來,不再周旋,語氣變成不容拒絕的命令:「讓你去你就去。」周葦磨磨蹭蹭滑下座椅,再磨磨蹭蹭把目光黏在陳香蘭臉上,好半天終於下定決心,咬咬牙兔子一樣飛奔了出去,邊跑邊回頭,只害怕回頭得太慢陳香蘭就不在原地。
小吃攤老闆正在忙著收攤,擺擺手,說要關門了。周葦不說話,盯著他,盯到他心軟,老闆這才掀開一邊的菜罩,抬起眼:「還剩兩個肉餅,要不要?」周葦把頭點得像雞啄米,遞過去一張整鈔,老闆打開面前的抽屜,慢悠悠地在錢海裡撈來撈去,半天也撈不到想要的面額。等錢終於找到了,陳香蘭卻不見了,周葦站在只剩下蛇皮袋的塑料椅前,手捧肉餅,臉上還掛著傻乎乎的討好的笑。周葦往所有的地方看,所有的地方都沒有陳香蘭。半分鐘後,孩子的哭聲在空蕩又開闊的車站裡拉響警報,睡在塑料椅上的人只動了動腿又回夢裡去了,打撲克的打完一輪,轉轉脖子越過重重椅子看過來一眼,又被洗牌聲喊回去了,幾位好心阿姨走過來,問孩子家長呢。孩子不答,只一味地哭,彷彿壞掉的感應器,機械地歇斯底里著。
「我上廁所回來,隔老遠就聽見有孩子哭,走過去一看,結果是我家的。一堆人圍著,誰也勸不住。」後來,陳香蘭偶爾還會提起這件事,提起時她總是笑,彷彿終於在這個女兒身上發現了什麼幽默之處。「她還以為我不要她了,這孩子,從小就愛瞎想,後來老師說是有創造力的表現,這我才放心了。」
她講一遍,講三遍,講十幾遍,講到最後,話便說服了她,好比大量攝入酒精,規律注入毒品,二十一天養成一個習慣,最後成功把自己套進習慣裡,她開始相信自己所說的一切才是真相,相信她從始至終都不曾有過當初的念頭。她是那樣致命地需要著謊言,以至於願意做一具走屍,任由陳詞濫調來代替她發言。周葦發現了母親的軟弱,就像發現她身體上的某顆不易察覺的痣,先是令她驚訝,後來看久了,便覺得它是那樣的普通,所謂的肉體凡胎。可陳香蘭絕不會承認這一點的,因為軟弱從一開始就是獨屬於那個做了逃兵的男人的標籤。
「是你爸不要我們的。」
一句至理名言,掛在家裡客廳貼滿獎狀的白牆上,旁人看不見它,他們看見的是秋日碩果般閃著金粉的榮譽,只有母女倆能看見,它比獎狀更加耀眼,是始終灼燒著的太陽、不會腐壞變色的黃金。它是周葦還在牙牙學語時就開始背誦的「八字經」,陳香蘭用這句話來教導她愛與恨、孝與悌、忠誠和背叛,以及邁入人世間前所必須學會的樸素倫理。在一切表達關係的動詞之前,周葦最先學會的是「要」,然後是「不要」,一個人可以選擇要或者不要另一個人,比選擇要不要一張床還容易。
就像陳香蘭對那張鋼絲床早就一肚子意見,但始終沒將它換下。好多年裡,鋼絲床都在夜裡重彈著差不多的老調,吱吱哇哇地抱怨著自己一把年紀還要被折騰來折騰去的命運。陳香蘭只好找來一層層被褥把那張喋喋不休的嘴給堵住,可惜這沒能消滅床的聲音,它只是含糊不清了,聽上去反倒越發苦悶、委屈。那些夜晚,凸起的鋼絲透過棉織物頂上周葦的背脊,彷彿一排排老朽的牙齒,在不斷的張合中,她總覺得自己下一秒就會被吞進去。她沉溺於那種幻覺就像沉溺於童話,只不過在她的童話中,豌豆變作了鋼絲,畢竟,童話也要與時俱進。陳香蘭也懂得與時俱進,鋼絲床扎破了她原本的夢境,她便學會用一些科學方法給自己造出新的夢境。
夢境藏在一隻白色塑料瓶裡,擰開時並沒有神燈的白煙冒起,只有一顆圓頭圓腦的小白片鬼鬼祟祟地滾落進陳香蘭的掌心。起初,周葦好奇,從被窩裡擠出一雙眼睛,想要窺探陳香蘭夢境的祕密。可惜她忘了還有鋼絲床這個間諜,在她剛一行動時就用聲音將她出賣。
「要死啊?不睡覺!」
在需要造夢的夜晚,陳香蘭會變得格外暴躁,暴躁驅散雜音過後,夢境才願意緩慢地顯形。半粒白藥片是迷路的兵丁,在陳香蘭身體的燥熱雨林中小心開路,很快,他們就會落入那些驚悸不安的陷阱,更多的火力被派遣進去,白色制服的士兵前仆後繼,狹長猩紅的血管是曲折的巷道,他們等待、伏擊,二至四小時,炮火濃度攀至頂峰,然後便進入漫長的休整半衰期,每一個白日都是一片廢墟。廢墟中,一堆白色塑料瓶東倒西歪,被掏空了肚子。周葦將它們偷偷收集,藏進房間的抽屜,用筆在每一隻上詳細記錄下開封和空掉的時間,如同人們會在墓碑上所做的那樣,然而,那只是一排排空心衣冠冢,白衣士兵們都消失在夜的雨林裡。
一九九七年八月——現在。
這場戰爭曠日持久,和中東地區世代糾纏的恩怨一樣沒完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