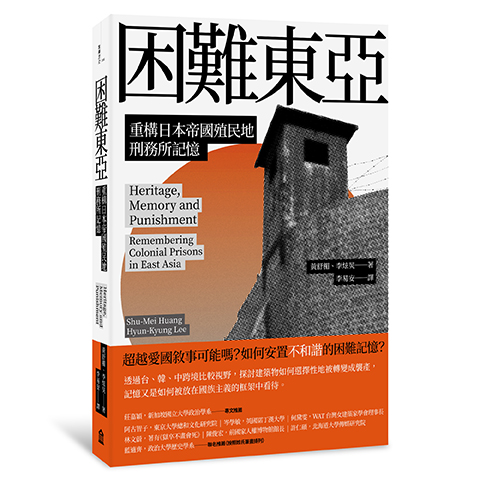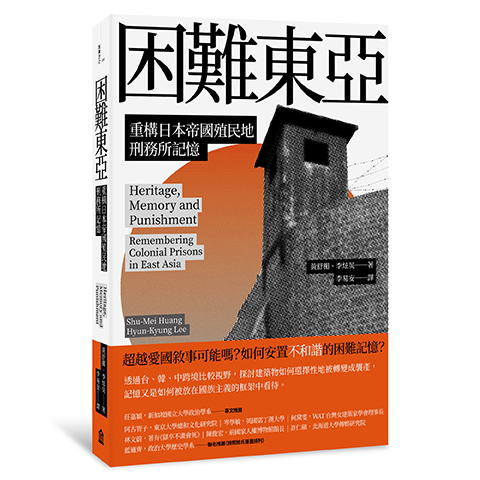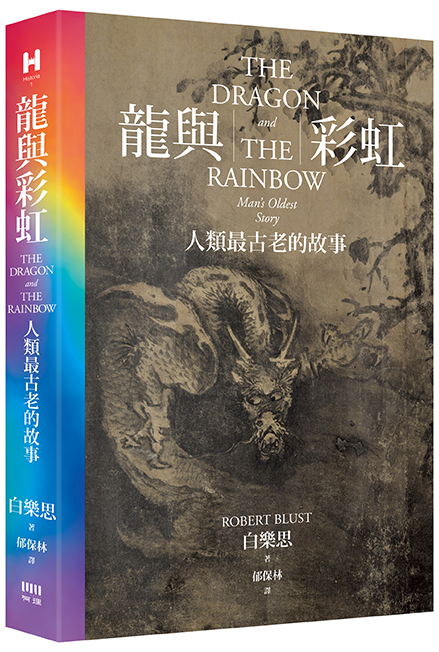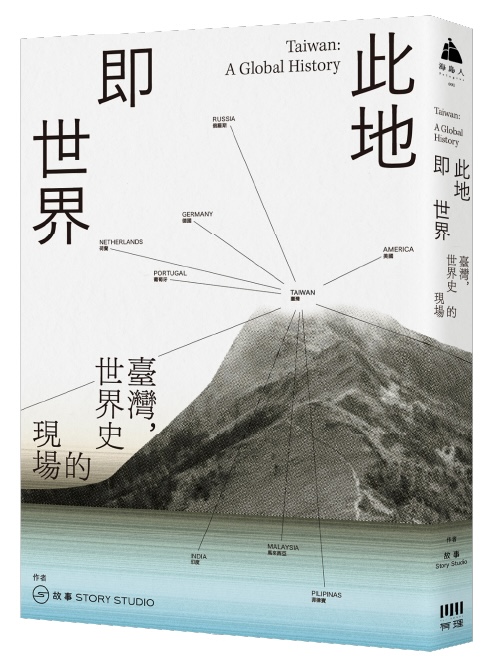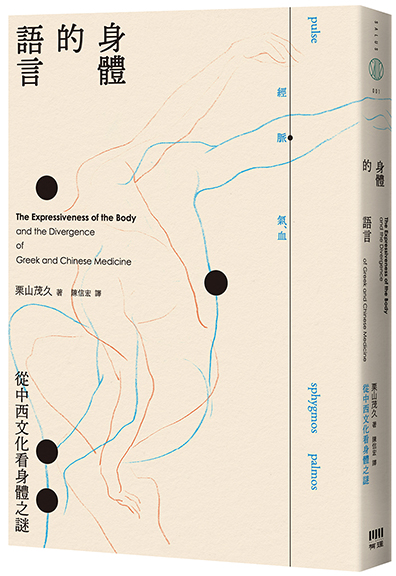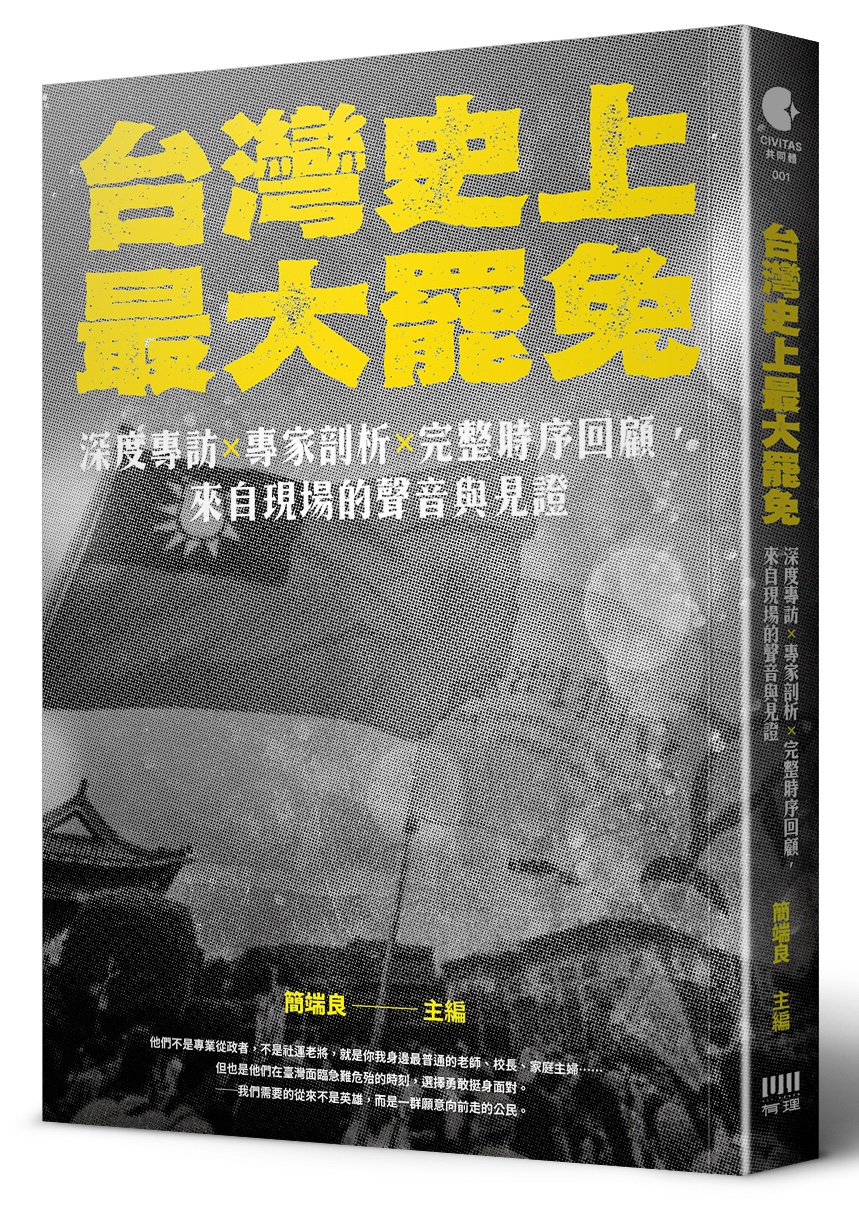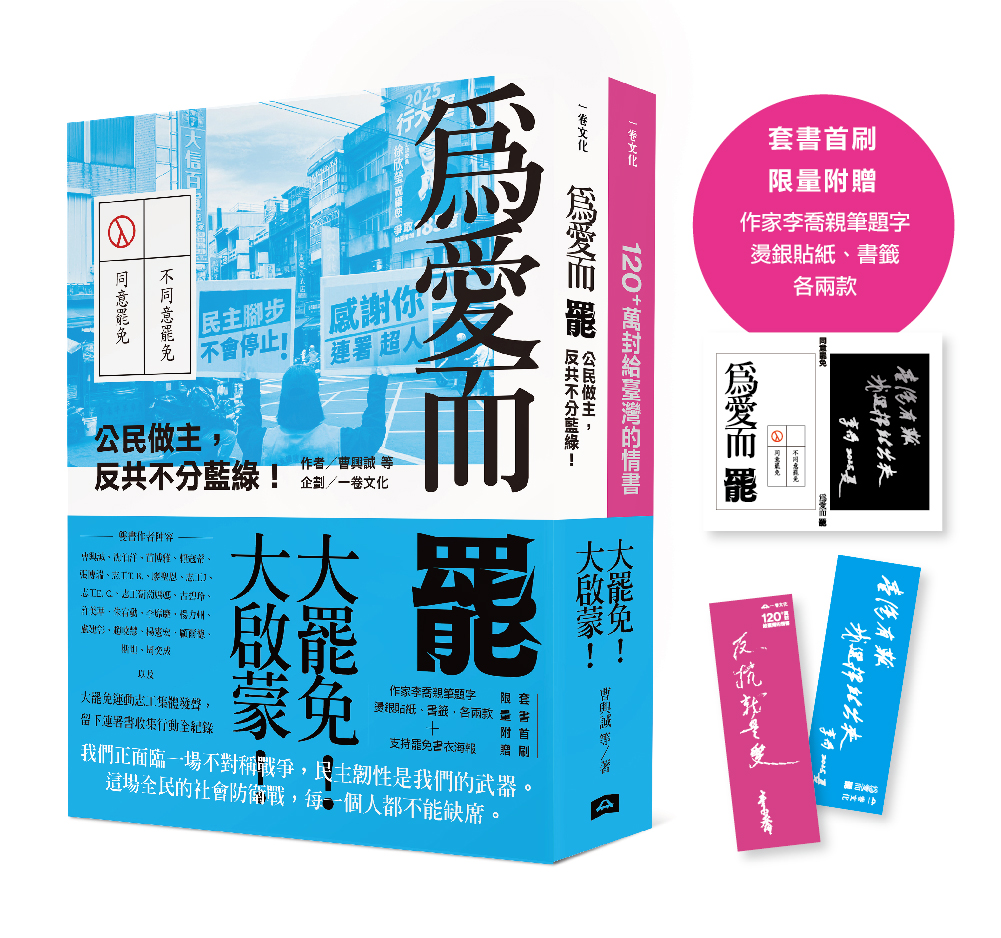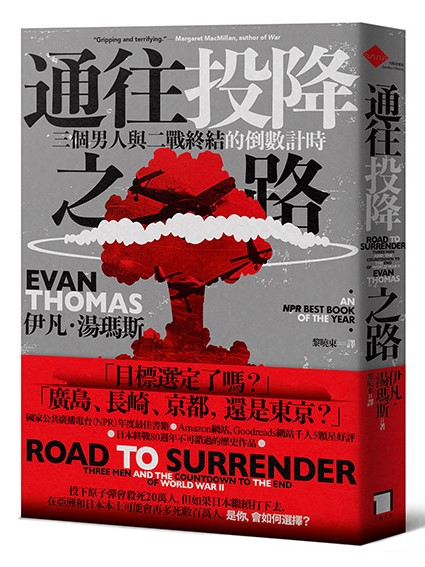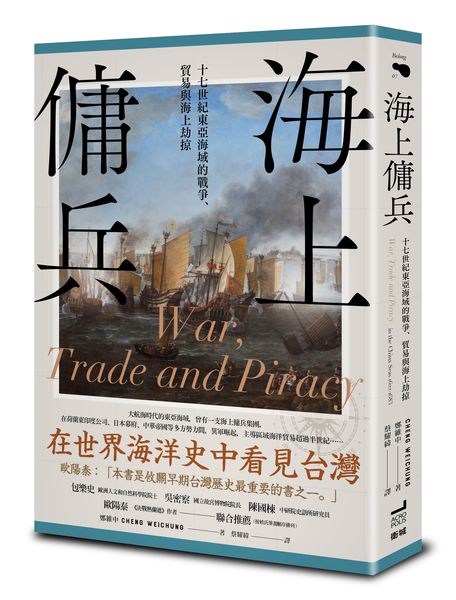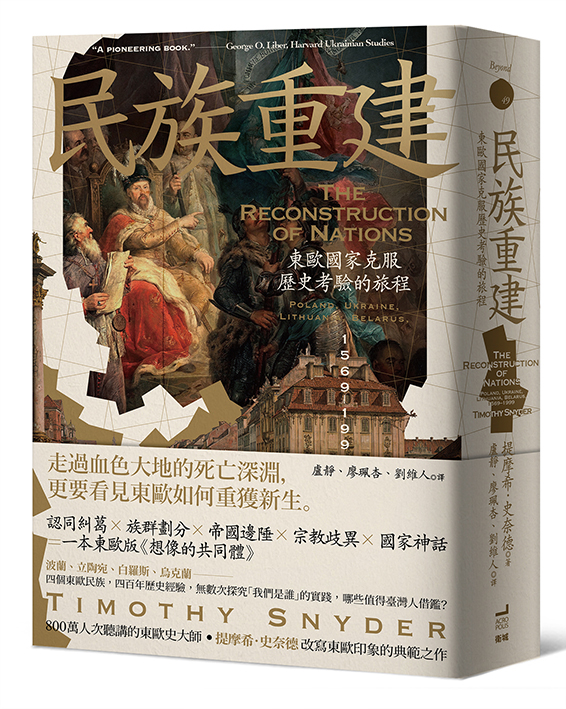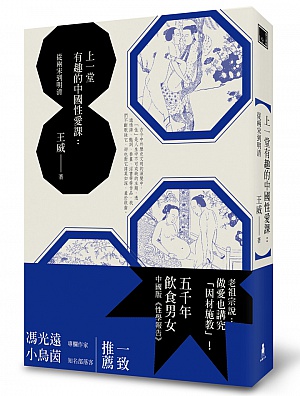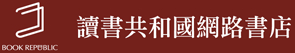超越愛國敘事可能嗎?如何安置不和諧的困難記憶?
台北監獄(案例之一)是當初日本人考察歐美監獄所興建,
戰後,我們如何看待這些殖民遺緒呢?
透過台、韓、中跨境比較視野,
探討建物如何選擇性地被轉變成襲產,
記憶又是如何被重新放在國族主義的框架中看待,
近年國際間興起一股暗黑旅遊的熱潮。在這一波浪潮裡,集中營、監獄、不義遺址成為觀光主題。面對這些不願面對的暗黑過去,東亞又有獨特的歷史脈絡。
本書聚焦於台灣、韓國、中國自日本殖民時代留存下來的刑務所。這些刑務所建造於日本帝國邁向現代化的二十世紀初,原本象徵著日本有能力追上歐美大國,以更人道的方式對待罪犯,躋身列強之林。
但二戰之後,有些案例裡的刑務所卻轉而被記憶成日本帝國殘酷、不人道的證據;有些案例的刑務所則脫離原本殖民脈絡,成為美學的靈感來源。兩位作者將監獄視為一扇窗,而我們可以透過這扇窗來理解現代東亞國家的建構和轉型。
研究發現,在選擇性記憶(或遺忘)的背後,多重邏輯彼此相互影響。如何保存這些監獄襲產取決於由哪個政治立場來進行敘事,結果往往爆發衝突和矛盾,無法增添國族共同體的光輝,這樣一種不和諧,展現了「困難」之所在。以韓國西大門刑務所為例,戰後西大門刑務所體現的韓國白色恐怖歷史經常被排除在視線之外,因為將刑務所視為單純的日本殖民產物,才能有效凝聚反日共識,打造國家認同的目的,使得「反日」成為西大門刑務所的敘事主軸。
在東亞崎嶇轉折的歷史裡,襲產也具備跨境的特質,能開啟各國外交合作的契機。以中國旅順日俄監獄為例,兩國針對「尋找安重根遺骨」展開時斷時續的交流。對韓國獨立運動來說,安重根是刺殺伊藤博文的民族英雄,對中國來說,這段歷史同時見證著中國遭受西方和日本的壓迫。不過,兩國合作並不順利,過程仍然深受現實政治的影響。
除了監獄本身的歷史,監獄周邊的居民,在都市化過程中面臨拆遷的命運,這種將記憶抹除的暴力,也再次重述了刑罰國家的運作邏輯。作者以台北監獄為例,提出我們如何可能重拾「責任地理」,讓更多衝突被看見,而非抹除?
作者期待透過跨境比較的視野,開啟更多批判性的反思:監獄如何選擇性地被轉變成襲產,而監禁的記憶又是如何被重新放在國族主義的框架中看待,結果反而再次監禁了這些東亞城市的記憶,而不是讓公民社會在民主過程中獲得解放。
各界推薦
莊嘉穎,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專文推薦
阿古智子,東京大學總和文化研究院教授
岑學敏,英國諾丁漢大學文化、媒體及視覺研究系助理教授
何黛雯,女建築家學會理事長
林文蔚,畫家,著有《獄卒不畫會死》
陳俊宏,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前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
許仁碩,北海道大學傳媒研究院助理教授
藍適齊,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近年專注於襲產、記憶、空間政治的交集,長期與韓日同儕合作跨境比較研究,近期在東京大學進行訪問研究。續此專書出版後又主編合輯《記憶前沿:困難襲產與後殖民國族主義的跨界政治》(Frontiers of Memory: Difficult Heritage and Cross-border Politics of Postcolonial Nationalism,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22)。學院外亦參與公共事務,擔任第一屆、第二屆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委員以及女建築家學會理事(2022-2026)。
Hyun-Kyung Lee
韓國西江大學批判全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劍橋大學襲產研究博士,曾在史丹佛大學東亞研究進行博士後研究。近年除了研究教學,亦擔任韓國世界遺產辦公室、文化襲產部門諮詢專家。
第六章 殖民邊緣上被錯置的記憶:
台灣的數個案例
在殖民邊緣上進行刑罰改革
曾經作為日本帝國殖民地的台灣,雖然位處帝國的邊緣,卻也是以現代性為名的殖民實驗前線。相較由西方引進的概念所啟發的其他實驗裡,刑罰改革在日本帝國的制度學習之中佔有一個特殊的地位,並出現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台灣都市地景中。日本殖民政府採納了「矯正」的概念(也就是對懲罰的現代、文明而且人性化的詮釋),藉此對監禁開始進行制度化,有趣的是,這個概念也呼應了其在殖民地實施的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在日文的漢字裡就是「都市改正」)。隨著戰後都市化的展開,這些被強行加上的刑罰地景的困難記憶,直到相關遺跡從十年前開始吸引大眾目光之前,大多都遭到了掩蓋、移除、摧毀或選擇性忽略。本章所處理的,就是這種對台灣殖民監獄相關的歷史建築漸增的興趣,我們觀察到,現在有個趨勢似乎會將刑罰地景,整合進一個全新的都市保存計畫,然而這個計畫,卻會將關於矯正和監禁的地方記憶「他者化(others)」,並可能會重新塑造殖民現代性的都市足跡。本章引用前文所發展出來的「監獄任務再造(carceral re-tasking)」以及「記憶級別」概念,檢視了四個焦點案例,藉此闡明監禁地方和殖民的實驗,如何被轉換成了一個可被利用的監獄歷史,然而「矯正」的概念卻依舊沒有被觸碰到,或者更糟的是,這種「矯正」的概念甚至可能會在未經批判的情況之下,在刑罰地景的保存過程中遭到強化。
【小標】將矯正和殖民的現代化置於脈絡之中
清帝國從一六八四年開始統治台灣,但直到十九世紀中葉為止,其對台灣的統治一直都相對鬆散。當時,在台灣興建的監獄規模相對小,而且只是用來讓囚犯在等待懲罰或處決時短暫停留的地方。一如第三章已經討論過的,現代形式的監禁懲罰,是在二十世紀初,也就是台灣被殖民之後,才由日本專家引進清帝國的。
重要的是,台灣就是在這個改革的時刻成為日本殖民地,因此和中國走上了不同的刑罰改革道路。日本是在一八九五年兼併台灣;殖民政府於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便透過台灣住民刑法(Taiwanese Residents Penalty Act),首次實施了「限制自由的懲罰」(Lin, 2014, p. 81)。就在同一天,日本殖民政府也公告了一份監獄法,而該法主要是根據日本於一八八九年公佈的一部法律所制定的。在這份新法律之下,殖民政府進行的第一個措施,就是在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六年間,將一個佔地寬闊、國有的宅邸,變成一座臨時性的監獄,亦即台北監獄(請見圖6.1)。台北監獄是台灣的第一座模範現代監獄,監獄裡有二十三個牢房、一個拘留設施,以及一些支援監獄日常運作的設施,比如辦公室、監獄工作人員的宿舍、一個診所、廚房等等。其他地方也有類似的措施。很顯然地,這類臨時監獄的容量有限,並開始出現過度擁擠的問題(以一個知名的案例為例,在一八九六年的彰化,曾有二十五個人擠在同一個牢房裡;Lin, 2014, p. 88),而這個問題,後來也讓殖民政府展開一個更宏大的計畫,建造更多的現代監獄。
【圖6.1】 台北監獄,一八九五-一八九六年間(台灣矯正協會,一九三八年)。
圖片來源: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由此,台灣監獄的現代化是由殖民政府展開的,而日本當時也正是藉由殖民統治,來邁向成為一個現代的國族國家。必須指出的是,現代監獄是無法一夕之間建造出來的;若想要建造所有的設施、滿足刑罰改革的要求,他們需要不少時間和花費。殖民政府一直要到二十世紀初的幾十年裡,可用的土地和財源才開始漸增,也才開始能在全台各地興建現代監獄。在東京的立法機構的同意之下,殖民政府發行了債券,藉此為在台灣計劃興建的三座大型監獄籌措經費(Shizuhata, 2009 [1936], p. 302)。
包括新的台北刑務所在內,日本殖民政府一共計劃在台灣興建十三座監獄,而在日本於二戰結束離開台灣之前,這些監獄最後有八座監獄完工(請見表6.1)。監獄法於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在台灣公布之後,殖民政府便正式將監獄分為三種類型:看守所、待審的被告所使用的監獄,以及用來關押被判有罪的人的監獄。一八九六年一月,台灣各地設立了十三座監獄,但它們大多都必須使用清政府留下來的簡陋設施(Sotokufu, 1916)。在西方人的刻板印象裡,日本有時會被視為不人道、殘暴的政權,而急著對抗這種刻板印象的日本,便很希望對這些臨時性、簡陋的第一代監獄進行大幅整修、改善裡頭的惡劣條件。主導計劃的監獄建築師名為山下啟次郎,我們曾在第一章介紹過他。日本殖民台灣的第一個十年裡,他曾被派到台灣來構想台灣的三座主要監獄,後來也負責監造,這三座監獄分別是:北部的台北刑務所、中部的台中刑務所,以及南部的台南刑務所(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15)(編按:日本在大正晚期,亦即一九二〇年代晚期,一律將監獄改名為「刑務所」,以去除字面的殘酷落伍意涵)。
等台灣的統治安排穩定下來之後,殖民政權便終止了比較殘酷的懲罰形式(比如鞭刑),並在一九二一年挪出一筆特別預算進行「監獄擴建」(Wang, 2015)。到了一九三八年,全台灣有將近四千五百名囚犯。台北刑務所是台灣島上最大的監獄,容納了一千五百八十三名受刑人,佔全台囚犯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請見表6.2)。現代監獄在台灣的系統性興建,不僅讓刑罰勞工制度得以取代過去殘忍的刑罰作法,同時也能支撐現代監獄的經濟運作。現代監獄的設計、以及刑罰勞動的常態化,兩者是相輔相成的,而且也讓刑罰事務變成一個展示和觀光的標的。台北刑務所就是個很好的例子。這座監獄是個大型的公共工程,很快就在這個殖民地的首府成為一個重要的地標。台北刑務所由山下啟次郎負責規劃,採用賓州模式的平面設計,監獄園區裡包括供監獄職員居住的區域、容納囚犯的主牢房,以及讓囚犯在其中勞動的監獄農園(請見圖6.2)。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如果預算允許,殖民政府便會對監獄園區進行擴建、改造,讓監獄能被賦予愈來愈多元的功能。園區裡也有日本獨特的宗教和精神空間,比如神社和演武場,讓這些日本現代監獄和西方的監獄顯得非常不同(請見圖6.3)。
一九〇八年,也就是該監獄落成不到四年的時候,來自台北刑務所的刑罰勞工就已經在支援一個重要的殖民計畫,那便是台灣的第一場貿易博覽會(台北物產共進會),該博覽會旨在慶祝台灣縱貫線鐵路的完工。日常的殖民主義,也透過這場博覽會在日本和殖民地的宣傳而得以遂行(Tsai, 2013)。監獄在支援這場博覽會上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已經在第三章討論過了:當時的囚犯,也參與了台灣博物館開館的展櫃製作,而和博物館一起於一九〇八年十月開幕的,就是這場台北貿易博覽會。此外,當時的殖民政府還有計畫,要在一九〇八年這場博覽會上展示清政府時期舊的刑罰措施,甚至還要展示一些在地的刑罰器具:「如果我們在這裡找不到,或許可以從中國買一些過來」(Taiwan Nichinichi Shinpo, 28 August 1908)。雖然沒有明文的記錄,但我們可以看出,這場展覽就是要將在殖民統治之下達成的刑罰改革,和過去的情況做個對比,但我們或許可以說,這很可能就是他們的意圖。我們或許也可以主張,我們在此找到了一些證據能證明:將刑罰事務看作適合展示、適合觀光的主題的概念,早在現代監獄於殖民地建造的最初期就已經出現了。
總的來說,和這些新監獄相關的文字記錄,處處都流露著他們希望展現出某種進步感的決心,而且這麼說不是沒有道理的。就在博覽會的一年之前,台灣爆發的一場瘟疫奪走了兩千兩百八十人的性命。我們或許可以說,當時的殖民政府很想要展示它已經達成的成就,藉此平反之前遇到的挫敗。
出於將監獄隔絕於社會之外的這個目的,現代監獄都建在郊區裡,而大門則面向市中心(Su and Liu, 2004)。不過在殖民統治的第一個十年結束後,各大城市的邊緣很快就被納入不斷擴張的城區裡,而在戰後的年代裡更是如此。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殖民政府留下來的基礎設施,被國民黨的國民政府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完封不動地接收了過來。一九四九年的內戰導致國民黨政府播遷台北。這些治理方式的過渡性狀態,解釋了為何國民黨流亡至台灣之後,台灣在至少十年之後,都和日本人當時留下的環境樣貌沒有太大的變化。
和旅順日俄監獄以及西大門刑務所不同的是,當時的人們對於將台北刑務所宿舍,和戰俘的歷史以及台灣的殖民史連結起來一事,並沒有太大的興趣,而從一九五〇年代到八〇年代為止,或可看作台灣為「流亡」政府狀態所管制,接著則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開始,開始面臨到民主化的運動。一九七〇年代和八〇年代期間,這些殖民監獄所在的位置,大多都成了一流房地產的所在地,而這也掀起了關於再開發和遷移監獄到更偏遠區域的議題。
一直要到一九九〇年代,日本人留下來的場址和建築,才開始逐漸從被視為日本帝國遺留下來的負面物件,轉變成為「記憶的場址」(Chiang, 2012; Huang, 2015)。在後殖民時期的台灣,殖民襲產一直是個備受爭議、存在很多層次的現象,在將殖民場址「紀念物化」(monumentalizing)的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層次的殖民模糊性(colonial ambiguity)(Chiang, 2012)。在這些場域之中,監獄有時是殖民襲產中特別突兀的一個類別(Huang, 2017a),很難被好好看待。在台灣,人們很少將監獄視為一種襲產,直到嘉義監獄於二〇〇四年,成為台灣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由監獄變成的博物館之後,情況才有了變化 ,台北刑務所的北圍牆則已經在台灣戰俘營紀念協會(Taiwan POW Camps Memorial Society, TPCMS)的努力之下,於一九九八年正式被指定為台北市市定古蹟。我們將在下面詳細討論這些事件。
在接下來的部分,我們將採用「記憶級別」一詞,針對存在於台灣不連貫的、非系統性的保存作法的各種記憶層級做區分。然而同樣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認清一件事:台灣自一九九〇年代——亦即台灣開始進入「地方主義時期」(era of localism)(Chiang et al., 2017, p. 238)——開始不斷變化的政治地景,也讓人們注意到歷史保存,而這個議題自此也經常成為地方政府的文化治理焦點。由於政治權力的去中心化,地方政府已經在新的政治地景之中崛起,並在透過歷史保存、文化旅遊、建立地方博物館和文化節慶等方式來提升地方認同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對襲產漸增的興趣,也帶來了一波快速的對地方記憶的重新採集,但這個過程在台灣各地,卻缺少一個必要的、彼此連貫的歷史框架。雖然這種由下而上、漸進式的記憶,能讓過去的歷史,獲得比東亞地區其他地方更多元的再現方式,卻也導致一九七〇年代和八〇年代從快速再開發之中搶救出來的那些僅存的刑罰襲產,歷經了選擇性記憶或矯正式記憶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