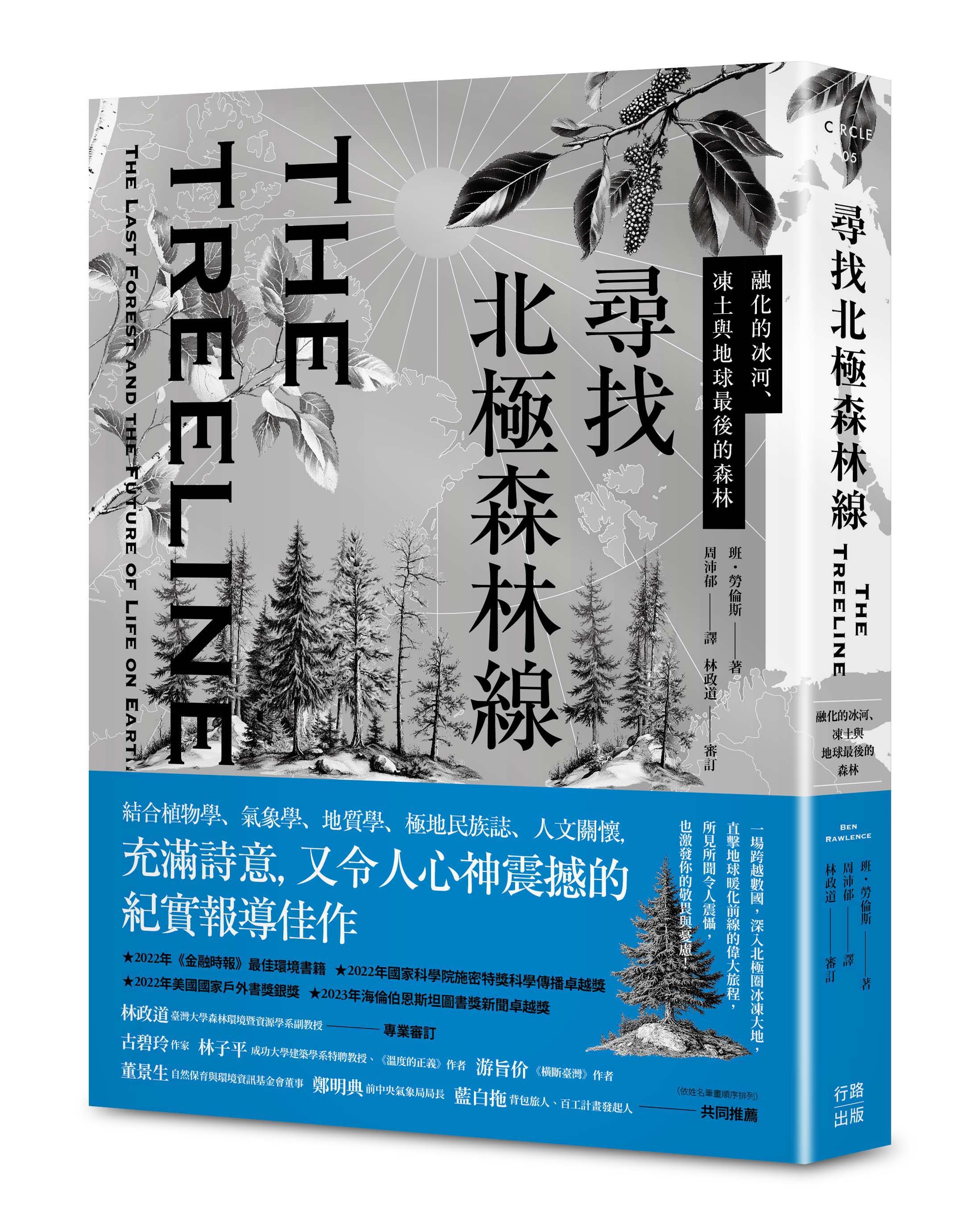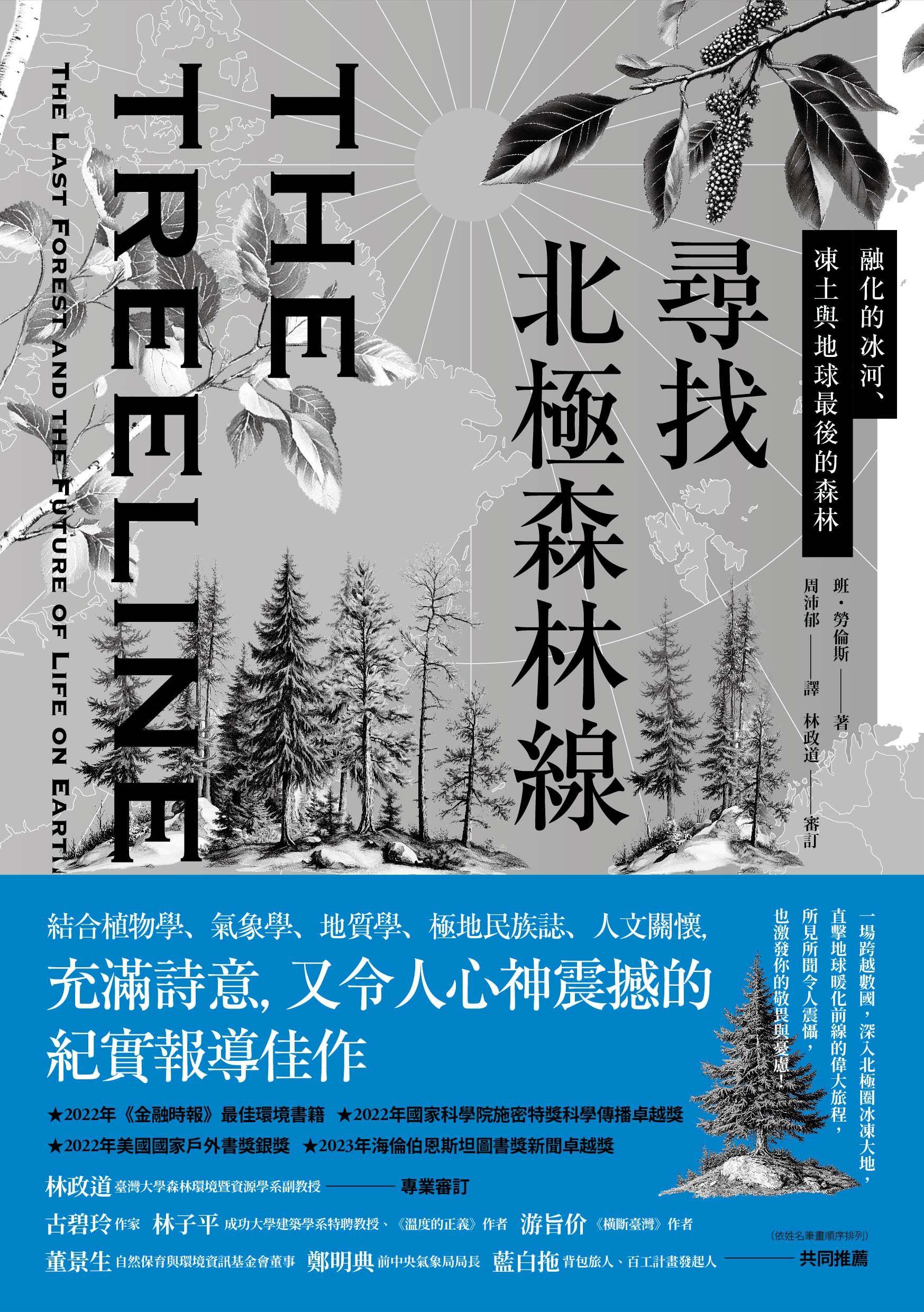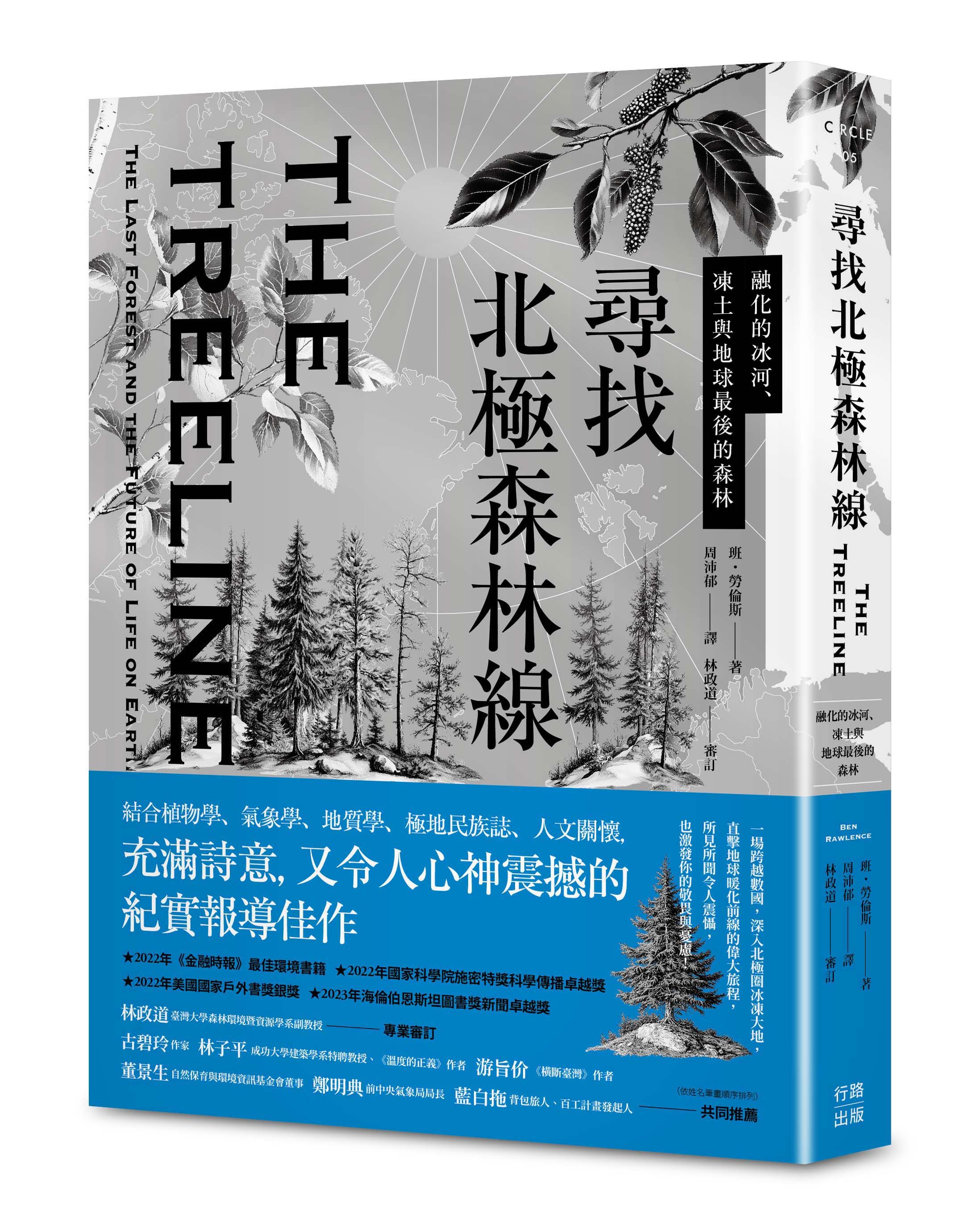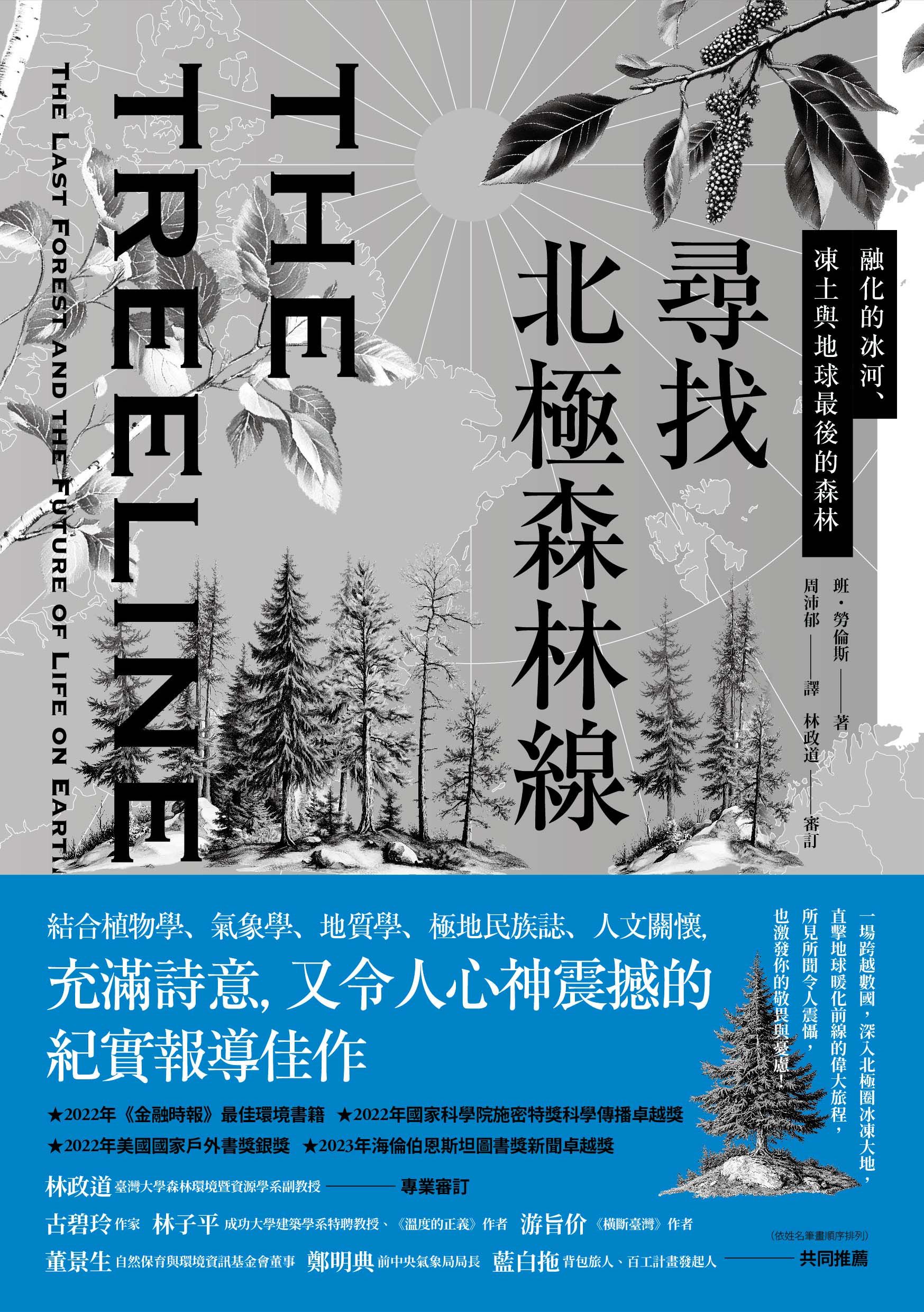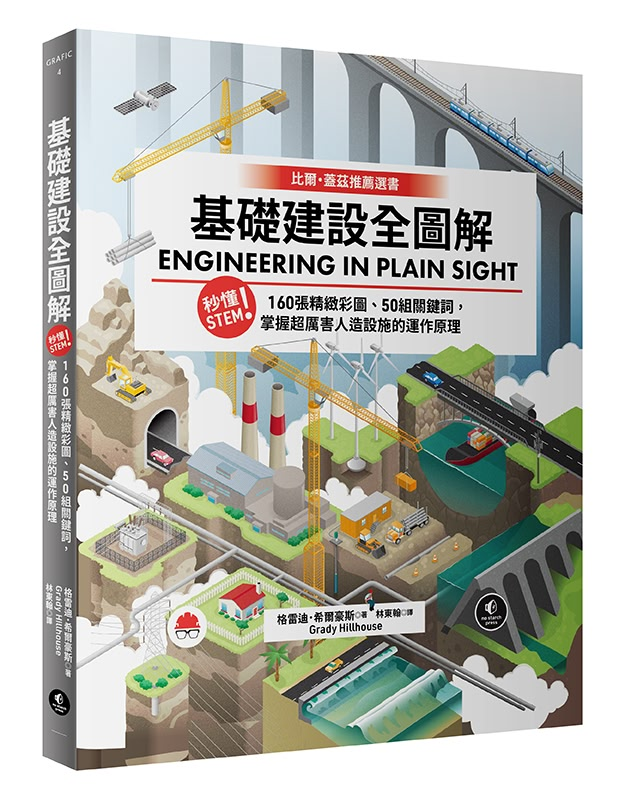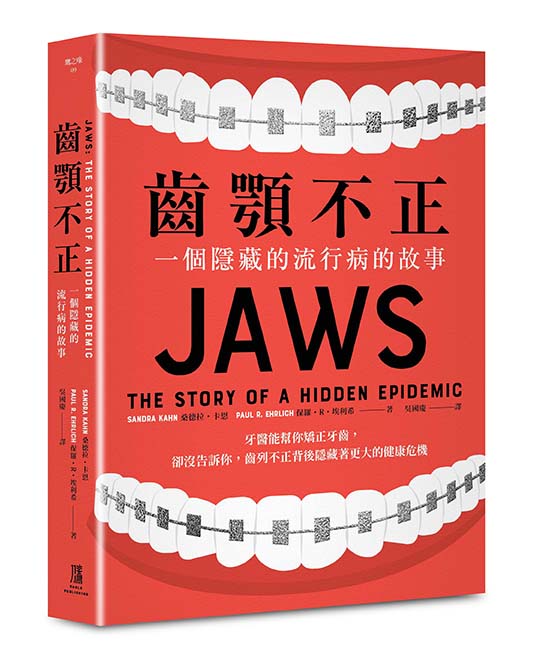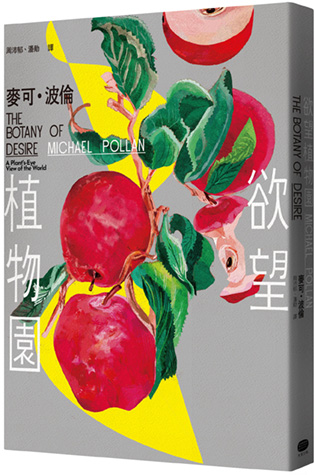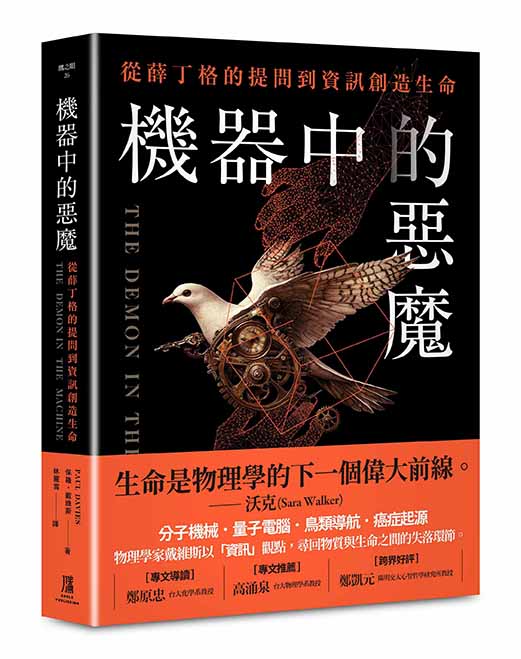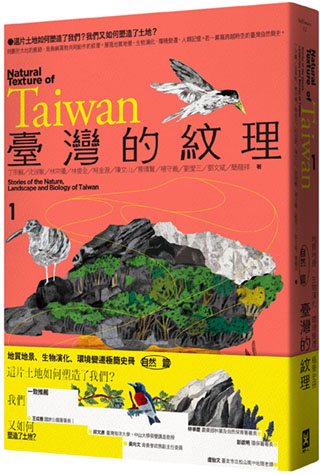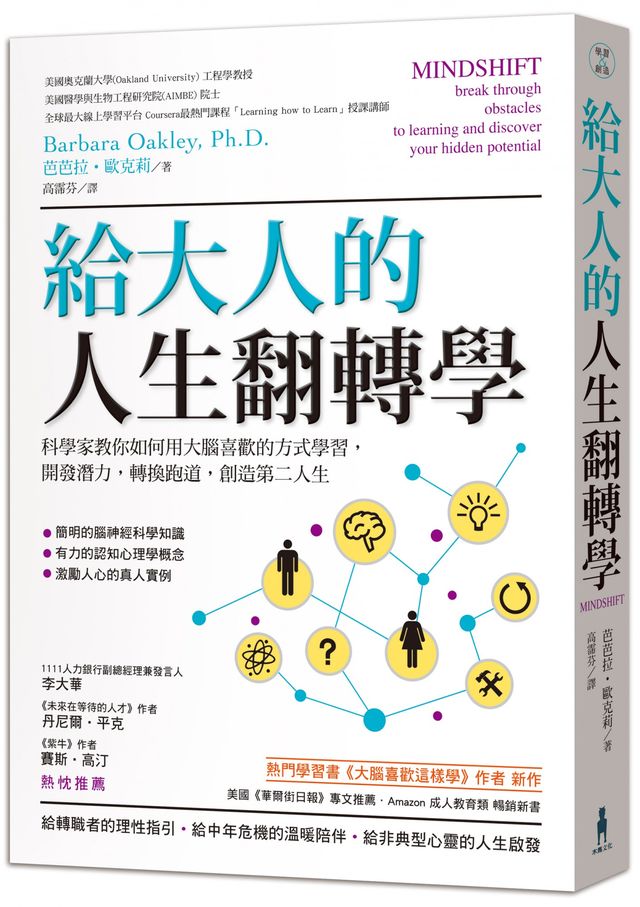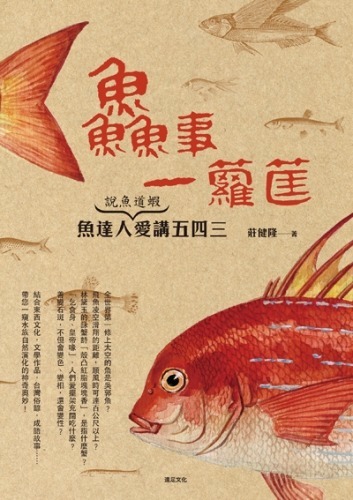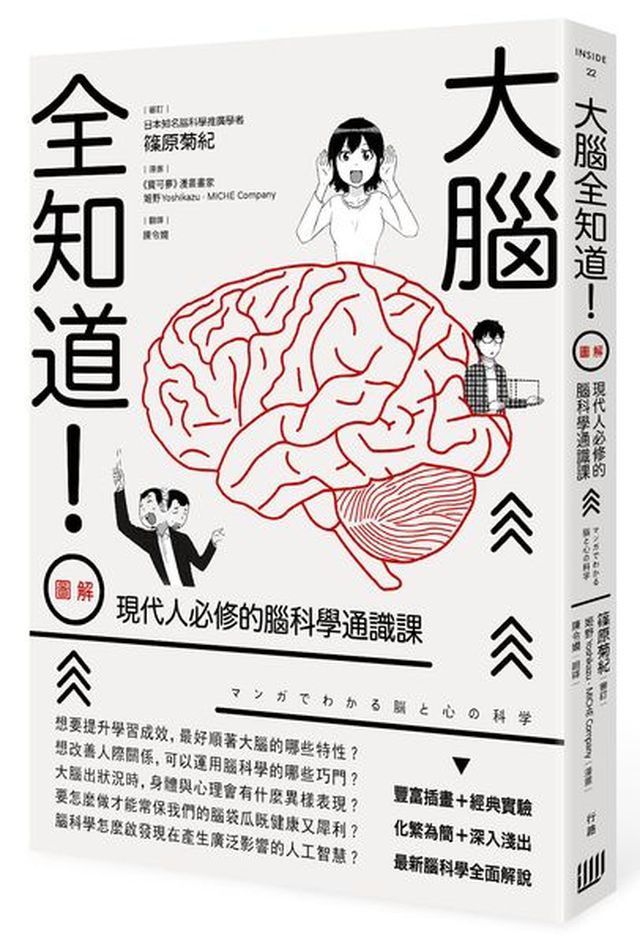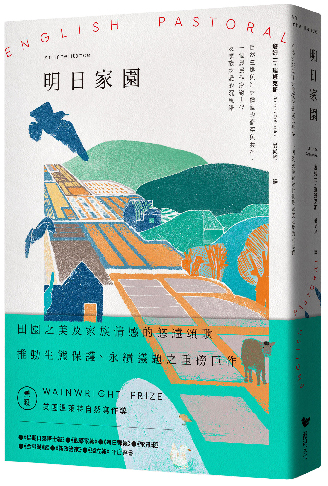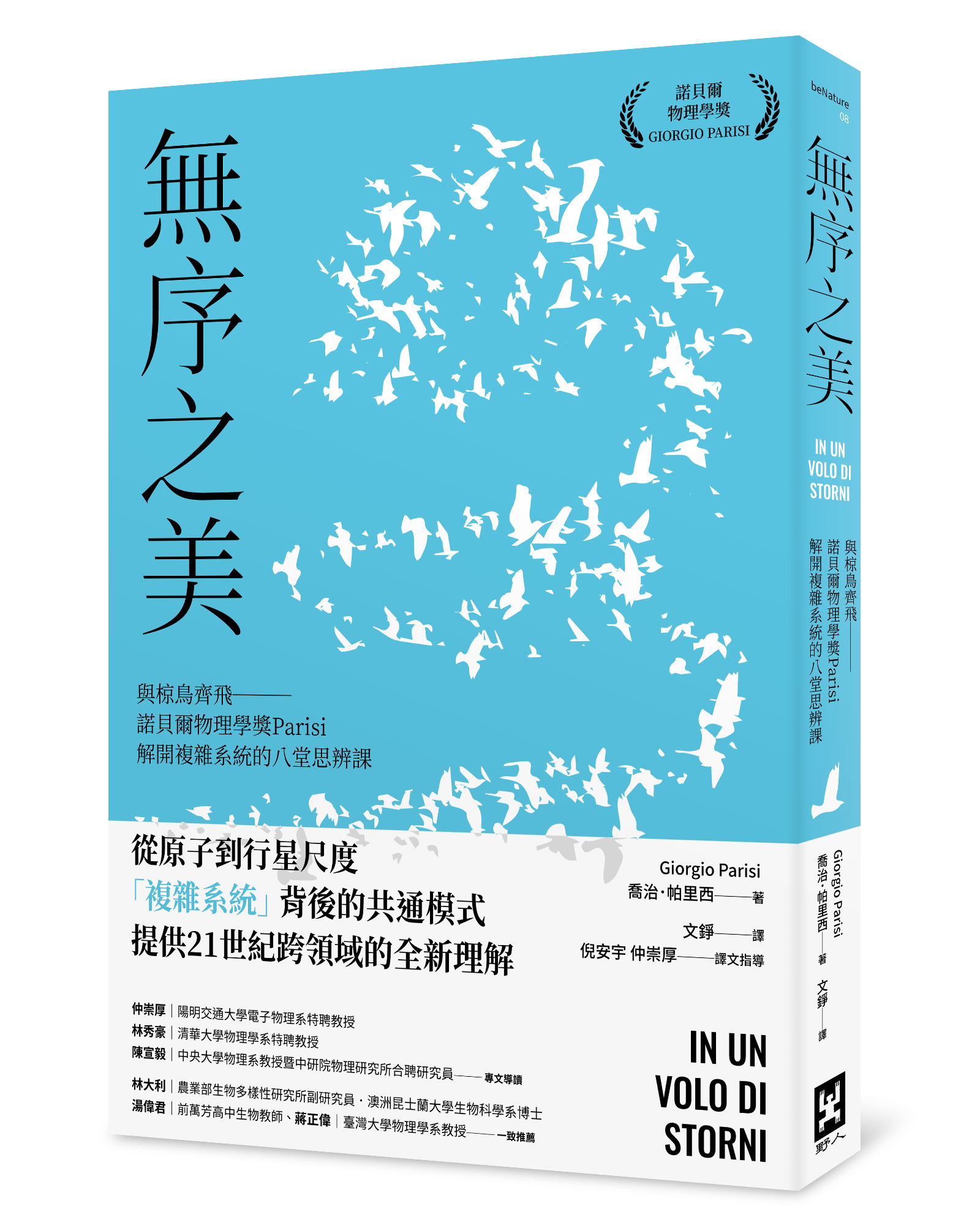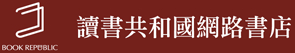結合植物學×氣象學×地質學×極地民族誌×議題行動
★充滿詩意,又令人心神震撼的紀實報導佳作★
撤退的冰河、解凍的永凍層、提早融化的海冰……
以及……向北推進的森林,與新物種的出現!
這是一場跨越數國,深入北極圈冰凍土地,直擊地球暖化前線的偉大旅程。
令人震懾,同時也激發你的敬畏與憂慮!
◆◆◆
★深入極地,追尋六個關鍵樹種
森林線是生林生長的界限,也是劃定北極圈的界線之一,若把視角放大來看,森林線其實是一個生態系的過渡帶,科學家稱之為「森林-凍原生態推移帶」。我們鮮少有人知道,和亞馬遜雨林比起來,北方的這片森林才是真正的世界之肺——這片廣袤的森林帶從北歐、俄羅斯橫跨至北美等地,覆蓋全球五分之一的面積,涵蓋地球三分之一的樹木,在地球北端環繞出一頂猶如桂冠的綠色地帶,是僅次於海洋的第二大生物群系。
然而,早在過去的五十年裡,甚至一個世紀前,暖化就已現跡於北極地區,緩緩改變著當地生態、地景以及居民的生活與傳統。近年暖化速度加劇,極地的綠化、森林的向北推進,更成為明顯可見的現在進行式。地球未來會是什麼模樣?暖化是否會有終點?作者勞倫斯決定從樹的身上去尋找答案。
在高緯度地區,往往只有最具創造力與生長力的堅韌樹種才得以生存,例如喜愛嚴寒的落葉松、能夠淨化大氣的雲杉、幾乎能治癒治百病的印第安聖樹香楊等等,這些樹木都在某一段森林線裡雄踞一方,發展出獨特的生態系,也是觀察暖化的關鍵指標。於是英國作家羅倫斯從蘇格蘭出發,走訪挪威、西伯利亞、阿拉斯加、加拿大、格陵蘭等六個地區,以六種關鍵樹種為主角,帶領我們踏上一趟深入北極圈、地理空間跨度極大的旅程,親眼見證暖化帶來的衝擊。
★科學家的隱憂與極地原住民的生命哲理
勞倫斯同時也拜訪了各地的重要研究機構,與身處研究前鋒的權威科學家對談,從他們直白或隱晦的深切憂慮,拼湊出一幅令人膽顫心驚的暖化版圖。他更跟著挪威的薩米人、西伯利亞的恩加納桑人等極圈原住民,一同進入渺無人煙的浩瀚荒野或傳統聖地,感受原住民在面對自然的變遷時,是如何抵抗或順應步伐?也或許,他們接應萬物的生命哲理能在暖冬將至時,為我們帶來啟發或借鑑。
★結合植物學、氣象學、地質學、極地民族誌、人文關懷
作為一本結合最新科學研究與豐富人文精神的紀實報導,《尋找北極森林線》記錄了一片很可能將會成為「地球最後一片森林」的故事,作者帶入豐富的氣候、生態、地質等科學語彙與知識,穿插精彩的歷史典故以及民族誌般的珍貴紀錄,深入淺出,為我們從未理解過的暖化,建構出一部視角多樣且令人深刻的樣貌,而優美而極富詩意的細膩筆觸,更是把極地的嚴寒、壯闊、神奇與脆弱毫無保留展現在我們眼前,也是最深刻、溫柔且直擊人心的呼籲。
「去年春天真的很奇怪,
我們看到以前從未看過的大隻蝴蝶。小孩子都在抓蝴蝶。」
「北半球的物種已經有向北移動的趨勢,
對於駝鹿、馴鹿等棲息於高緯度的哺乳動物或鳥類而言,移動不是問題。
但如果你紮根在一處呢?如果你是一棵樹呢?」
班.勞倫斯(Ben Rawlence)
著有《剛果電台》(Radio Congo: Signals of Hope from Africa’s Deadliest War)和《荊棘之城》(City of Thorns: Nine Lives in the World’s Largest Refugee Camp),曾為《衛報》、《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紐約時報》、《紐約時報書評》、《紐約客》雜誌和其他許多出版物撰寫文章。現居威爾斯,是黑山學院(Black Mountains College)的創辦人兼校長,這間機構致力於幫人們對不久後的變動做好準備。
譯者/周沛郁
森林系碩士,本著對語文的熱愛而投入翻譯,至今二十年,譯作以小說、科普為主。近年並沉迷解譯身體,兼職筋膜調理、太極拳教學。譯有《一日一樹一故事》、《真菌微宇宙》、《法外之徒》、《鹿苑長春》等書。
入口網站:https://portaly.cc/vampraths。
審訂/林政道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植群生態學,近年來專注於高山森林與草本植群變遷研究,並推動愛自然(iNaturalist)公民科學與在地社群培育。
第二章
追逐馴鹿
挪威.毛樺
我從阿爾塔踏上前往考托開諾的路,直直向南兩百五十公里。旅程始於一座松樹、樺樹混合的森林,林子比鄰著阿爾塔河寬闊的鵝卵石河道鋪展開來——據說阿爾塔河是世上最好的鮭魚河。接著道路迅速攀升,穿過一道狹窄的峽谷,兩側聳立著高數百公尺的陡峭岩壁,道路爬到上方的高原上,一條清澈的溪水隆隆灌入路旁的岩縫中。
薩米人的傳統會崇拜岩石、樹木、河流、山岳和其他聖地,並有奉獻魚、白化馴鹿和其他動物的習慣,以祈求打獵、捕魚豐收或單純的好運。他們和周圍的環境對話;動植物是他們的群落。薩米人的宇宙觀中心是萬眾一體,完全沒有「人」或「自然」的觀念,只有薩米人薩滿魔法鼓上描繪的一個循環系統——中央的菱形太陽放出四道光芒,由雷、風與月神統治,還有「神之犬」——熊,最底層則是薩米人,他的家、他的馴鹿和森林裡的鳥獸。神聖的力量透過神祇展現,令人敬仰,而薩米人經過聖地時,會身穿華服,唱歌或脫帽,表示敬意。現在還在世的人,有些依然記得父母叮囑過,要他們向特定的樹木或石頭道早安。
峽谷承載著精神的重量,迴盪著彷彿大教堂或森林的回聲,毫無疑問是神聖的處所。峽谷提醒我們,人類所居之地都曾有耳熟能詳的名字、故事與精神。對我們大多數人而言,這些聲音是消失於神祕過往的遙遠回響。不過對薩米人而言,那些聲音只是在聽力可及之外而已。大地並未真正沉默,只是我們不再傾聽。
水流在峽谷的上游輕輕拍打著鵝卵石,然後復歸平靜。隨著山谷像通往上界大門般緩緩敞開,河面也愈來愈寬廣。這裡的雪比海岸邊的更厚、更深,但河水還沒結凍。接著,沿著河邊左彎右拐十五分鐘左右,一道薄薄的冰線彷彿一片玻璃般,斜斜切開緩緩流動的河面。河水沖刷過冰面上下。冀盼多時、延宕許久的凍結開始了。從這裡開始,河面變得堅硬不透明。冷冽的晨間空氣裡,有白色的渦旋和藍色細碎的閃光。南方是黎明的粉紅與橙色熔爐。少了山巒的掩蔽,太陽離得更近了,不過依然靦腆地躲在視線之外。紅黃光像曳光彈一般劃過上方天際,而斑駁的山邊積雪與灌木攙雜,洋溢著暖暖的玫瑰色光線。
從阿爾塔出發的這一百公里以來,沿路都是灌木般的樺樹就近伴著車輛,一直到考托開諾。只有一次,一座顯眼的山立在開闊的河谷之上,才得以瞥一眼未被森林覆蓋的凍原——平坦無瑕的雪被一道彎曲歪扭的小小形體劃過,一大群樺樹正堅定地往上坡處前去。這裡的樹不像海邊的那麼高,很少超過兩、三公尺;銀色樹皮也比較難看——不是平滑如紙般包覆著筆直而強壯的樹幹,而是坑坑疤疤的節瘤樹皮,保護著樹木不受酷寒侵襲。白色的是周皮,粉狀的表層反射陽光,保護樹木不被曬傷,同時避免低垂的冬日太陽將樹幹內的加壓樹液解凍,使樹木爆裂。薩米人會用周皮做藥。這些樹是矮盤灌叢——矮小而生長緩慢的樹,在天然分布的外緣勉強生存。有些人質疑這些植物是否稱得上是樹。不過,半公尺高的百年盆栽難道就不是樹?還是說,不可思議的生存能力更值得敬佩呢?
離考托開諾不遠處,道路攀升到一道山脊上,下方的高原拓展成一片黑與橙的景色,黑的是樹,橙的是雪上倒映的天空。一道蜿蜒的河流穿越這片風景中央,時而有未結凍處在奔流,河面如液態的黃金般閃閃發亮。太陽不曾露臉的落日之後,就進入詭譎的近黎明時分。半片天都燒紅了。現在是下午一點。我們處於二十小時黑夜的開端。從這個制高點看去,樹木帶來的災禍清楚得嚇人。舉目所見,高原的凍原上有著斑斑的黑色條紋,有如雪鴞斑駁的前胸。這種圖案是盛行風造成的,風勢夾帶著配備薄翅的堅硬種子,在強風與氣流中翻越起伏的丘陵。風停後,種子落在山坳與窪地,長出高大濃密的樺樹群落。
這是一幅優美的風景,但其實那裡不該有樹,而且隆冬時節的河上應該結著厚達幾公尺的河冰,就像石頭一樣硬,能承受一群馴鹿或工程車的重量——因此眼前美景令人難以消受。如果我們不知道以前的模樣,如果我們能假裝僅是這一年很反常,而非處於一個加速中的模式,情況或許可能不同。這片原本未受破壞的地方,其實目前正處於劇烈的變動中;這個冬日裡,在北極圈裡的這個地方,溫度是攝氏零下一度,比過往這時節的平均溫度高了十四度,所以我們很難避免這種感覺:如果地球的氣候平衡有個臨界點的話 ,那麼臨界點早已被我們遠遠拋在身後了。
◆
考托開諾郊區一間黃色的平房裡,貝莉特.烏西(Berit Utsi)把她兩歲的兒子抱在胸前,望向戶外湖上漸濃的黑暗。湖面上覆蓋著薄如紙張的薄冰,四周樺樹環繞。貝莉特是當地馴鹿牧人協會的祕書,同意跟我談談樹木推進造成的問題。她的神情平靜,但眼中不時閃過焦躁——無法完全掩飾焦慮。
貝莉特說:「我們的文化不會大驚小怪。」這麼說太輕描淡寫了。挪威人素來以內斂矜持聞名,但若跟薩米人比起來,根本算不上什麼。對薩米人來說,情感的流露,就是一陣輕微的顫動或輕笑,或是冷峻表情中的一抹細微皺紋。
「大家的外表都雲淡風清,但內心非常擔憂。」她說起了極溫暖的冬天,不久前終於有幸下起第一場雪。然而貝莉特擔心的不只是這樣,丈夫仍在外面的某處地方——她也不知道確切的位置。他跑來跑去,手機訊號常常很差。對馴鹿牧人而言,這是個壓力很大的時代,即使豐年也一樣——必須把馴鹿群從秋季放牧地遷到冬季放牧地,將幾百平方公里內的馴鹿群聚在一起。
凍原的顏色變化導致了嚴重的後果。馴鹿是唯一看得到紫外光的哺乳類——紫外光對人類而言,是不可見光。在極地夜晚,太陽沒有升起時的低光度下,這種能力對馴鹿的生存至關緊要。地衣會吸收紫外光,因此在雪地裡呈現黑色。此外也有證據顯示,地衣會發出不同顏色的螢光,所以馴鹿可能透過雪看到地衣。馴鹿的眼睛有一片獨特的東西——脈絡膜層(tapetum lucidum),常見於夜行性動物與昆蟲,原文意思是「明亮的毯狀物」,能吸收光線,反射到視網膜,增強動物在低光度下的視覺。馴鹿的眼睛有個獨特之處,夏天的脈絡膜層是金色的,冬天會變成深藍色,吸收紫外光。在無瑕的雪中,馴鹿通常會保持平靜,習慣待在一個地方,挖掘雪地以獲取食物。但斑駁的黑白色景象讓牠們感到好奇又困惑,覺得可能有更容易取得的食物。於是牠們不再挖掘,而是嚼食樹木基部沒有白雪覆蓋的草和地衣,移動的距離大大增加,令牧人頭疼。牧人得盯著自己的馴鹿,把馴鹿聚在一起,避免牠們闖入鄰近家族群體的領地,甚至混入其他馴鹿群中。要區分一萬頭馴鹿,可能得花上兩星期。
除了上週因為貝莉特開刀,丈夫回來了幾天,否則他已經和馴鹿群在高原待了整整兩個月。他們一家的所有收入與儲蓄都投在了馴鹿群身上。一隻馴鹿在屠宰場的價值將近一千兩百歐元(一千一百英鎊),而薩米人會把全身所有部位(皮、鹿角、蹄和肌腱)用來做成衣物、工具和工藝品。然而,高昂的賭注也帶來了風險。貝莉特說:「最近發生了不少意外。」
「點檢」指的是繞行馴鹿群周圍,也是牧人每天的例行公事。在寒冷的環境下,迷途牲畜的足跡很容易在雪裡顯現出來,而雪上摩托車可以迅速穿越開闊的凍原、結凍的湖泊和河流,完成三十公里的巡航。然而,沒有結冰又長著零星灌木的地景則難以穿越。如果沒有足夠的雪讓雪上摩托車行進,同時又沒有冰層時,牧人只能駕駛越野車繞過湖、河和樹木,有時要繞個六、七十哩,花費一整天,不僅耗費許多燃料,還會壓扁大量的地衣——地衣要幾百年才會長回來。而且隔天還得再來一次。
貝莉特說:「人們都在石頭上騎著雪上摩托車,撞到樹木翻覆,最後進了醫院……也或許是冰層足夠堅固能承載馴鹿的重量,但越野車卻掉了進去。有時候得冒個險,畢竟繞路真的太遠了。去年有兩個人掉進冰層,再也沒有上來。」貝莉特還是青少年的時候,曾試著在一座小鎮裡工作,但感覺就是不對勁,她會想念她的馴鹿。貝莉特和馴鹿一同長大,每年夏天都和家人與馴鹿在特羅姆瑟(Tromsø)附近的林根阿爾卑斯山(Lyngen Alps)一同度過。她記得小時候凍原上的樹比較少,也覺得這種改變更像是一種損失,但她和我遇到的大部分薩米人一樣務實:「我們會適應,我們一向都會適應。」不過,改變中的天氣、推進的樹木,加上其他放牧的壓力(道路、礦場、風電場),使得放牧馴鹿的經濟愈來愈困難。更糟的是,政府意識到放牧的面積正在縮減,每年都要求宰殺更多的牲畜。她的家庭需要其他收入。
貝莉特希望她的孩子有機會成為馴鹿牧人——如果他們想要的話(這是很優勢的傳統),但如果孩子不像父母那樣整天和馴鹿群生活在一起,累積的傳統知識必然會少了許多。而且,他們要學的不僅僅是照顧馴鹿的方式,在野地裡的夜晚,也是述說故事、製造工具的時光。
樺樹的薩米語是soahki,對凍原上的傳統薩米生活來說,就和對馴鹿一樣不可或缺。樺樹是遮風避雨的必備之物,能製作帳篷的杆子,也能保溫——地板上會鋪著芬芳的樺樹細枝。木材是運輸必需,用於製作雪橇、滑雪板和雪鞋,同時也是燃料。秋天的樺樹和所有樹木一樣,會減少木質部(樹幹內部)裡的水分含量,準備休眠,這意味著冬天的樺樹即使沒經過風乾,也能燒得很好。其中的單寧和油脂能用於處理衣物和毛皮、製作油紙。樹皮能做成獨木舟的外皮,在海水裡發酵。單寧也用於處理傳統船隻的羊毛、麻布或亞麻船帆。到了春天,可以採集樹液做成富含礦物質的飲料,或發酵當作某種蜂蜜酒的基底。
「還有秋天的蕈菇!」在樺樹根系的棲地中,共生著超過七十種的真菌。
薩米人和樺樹的命運緊緊相連。
作為春天的使者,樺樹一向是薩米人生育力的象徵——而且不只在當地。在蘇格蘭民間傳說中,用樺樹枝條驅趕不孕的母牛,母牛就能生育。在更南方的英格蘭,傳統的五月柱是用樺木做的。「樺木掃帚婚禮」是新人結婚時跳過一捆樺木細枝的傳統儀式,直到最近,仍然是英國教堂婚禮常見的替代選擇。樺木也和純化、淨化有關,因此,當一個教區舉行「敲界標儀式」時,總是用樺樹細枝。
「樺樹是我們的朋友!」貝莉特似乎是因為誤解了這棵她依賴甚多的樹而感到抱歉。
在凍原上,樺樹讓她丈夫的生活變得艱難又危險;在廚房裡,樺樹隨處可見。貝莉特現代化的廚房裡仍然滿是游牧民族的傳統手工藝,是她夏天山中之旅時製作的。她的木湯匙和杓子都是樺木刻成——「比松樹硬多了。」架上的杯碗也是樺木刻成,而手工小刀的把手是馴鹿角和骨頭做的。馴鹿皮被鞣製做成咖啡袋,掛在水壺旁,一旁擱著一頂狐狸毛皮與馴鹿皮做的帽子。她兒子穿的靴子是馴鹿皮製成,用莖桿中空的凍原草莖隔熱。檯面上一只小鍋裡盛了樺樹皮屑,正煮著香草茶和湯藥。
「可是現在樹太多了。」貝莉特說著皺眉。她正在讀書,準備成為一名教師。
和蘇格蘭一樣,挪威放牧牲口與樹木間的平衡被打亂,人類不知所措。然而和蘇格蘭一樣的是,結局已定。大氣中的碳排放,將主導森林未來的模樣。我們現在面臨的任務和貝莉特相同——艱難地接受、適應發生中的情況。
◆
考托開諾好像休眠中的城鎮,或者根本不算是城鎮,更像是電影裡精巧的布景。對著在黑暗中的北極汽車旅館(Arctic Motel)敲門是徒勞無功的;我又來到一間青年旅舍,那是間一九七○年代的水泥建築,獨身的老婦從唯一一扇有光亮的窗戶裡往外窺視,揮手要我離開。工藝中心的大門開著,但空無一人。樓上有三位穿著寬大外套的長者正看著報紙,他們指了指樓下的工坊。工坊裡,一個男人頭戴耳罩,全心全意把注意力放在車床上;即使他看得到我,也沒打算停下手上的事。商店好像完全依喜好開張,一如阿爾塔,街上沒有行人,只有空盪盪的汽車發動著引擎以保持溫暖,還有緩慢移動的車子,煞車燈在黑暗的路上閃爍。
隔天是「挪威薩米人協會」(Norwegian Sámi Association)成立五週年紀念日,這個政治團體的宗旨是為薩米人爭取權利。也許大家都忙著為這重要場合做準備?
「什麼!才不是!」在廚房喝著咖啡的兩個女人相視大笑,口沫橫飛。「哪有人關心那種事!」
瑪麗亞(Mārija)戴著一只黑色手錶,與黑色指甲油和黑白雪紡長褲頗為相配。她的項鍊和耳環是黃金的,頭髮染紅,還剃掉了一部分。莎拉-艾琳(Sara-Irene)也穿了件黑白上衣,同樣剃掉了頭髮兩側,但瀏海則是染成金色,一耳戴了三枚珍珠耳環。莎拉-艾琳的中指戴著丈夫為她做的戒指,那是她馴鹿群的「耳號」(ear mark)——每一群的馴鹿耳朵都會被剪成獨特的形狀,代表著所有權歸屬。在畜欄裡,經驗老到的牧人在數算牲畜時,一摸耳朵就能認出自己的牲畜。莎拉-艾琳非常以她的馴鹿為榮,卻堅持不肯透露自己有多少隻。「問這種事不禮貌。」
「她的馴鹿可多了。」瑪麗亞哈哈笑著說。
「可是沒瑪麗亞多。」莎拉-艾琳說完,兩人咯咯咯笑成一團。
她們對政治毫無興趣,而且有著原住民傳統對政府的輕蔑——「政府才不在乎薩米人」。試圖透過開會來影響事務進行根本毫無意義。不過,瑪麗亞是考托開諾福利處的處長,所以她其實是為國家工作?
「「對呀!你想想看!敵人耶!」說著,她又笑到咳了一陣子。瑪麗亞的高祖父曾在一八五二年因為反抗政府而被挪威人砍頭。瑪麗亞繼承了他的耳號,那是高貴的耳號,很著名。
當我提起氣候變遷的問題時,氣氛變了。「政府只想控制我們和我們的馴鹿。那只是藉口……逼我們淘汰我們的牲畜。氣候變遷就是屁話,就十年前我母親小時候的天氣和現在沒什麼兩樣,所以我才不擔心。這我們見識過了。」
她無法解釋樹的情形。我追問瑪麗亞,她喃喃咒罵挪威政府,開了我沒聽懂的玩笑,逗笑了莎拉-艾琳,然後跑去露台上抽根菸。當她回來時,話題已經徹底轉移。
馴鹿牧人和馴鹿群密不可分,同屬馴鹿群的一分子。他們能提前幾天或幾星期感應到馴鹿群何時會遷移;他們會在馴鹿吃飽以後才開始進食;當他們面對著氣候變遷給馴鹿群帶來的威脅時,就如同想像自己的孩子挨餓或死去。悲傷的第一階段當然是否認。
莎拉-艾琳和瑪麗亞都在城裡工作。莎拉-艾琳經營一家美甲沙龍,瑪麗亞的黑色指甲就是她的傑作。不過,一年之中有些時節,她們絕不會錯過與馴鹿相聚——夏天生崽,以及冬末為幼崽上耳號的時候,那時需要全家夜以繼日驅趕數千頭馴鹿。
莎拉-艾琳說:「有時我們會覺得自己要精神分裂了!」說完,兩個女人瘋狂大笑。她們或許對自己的工作很在行,甚至引以為榮,但她們的神魂並不在鎮上,而是在外頭,在丘陵間,和馴鹿一同恣意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