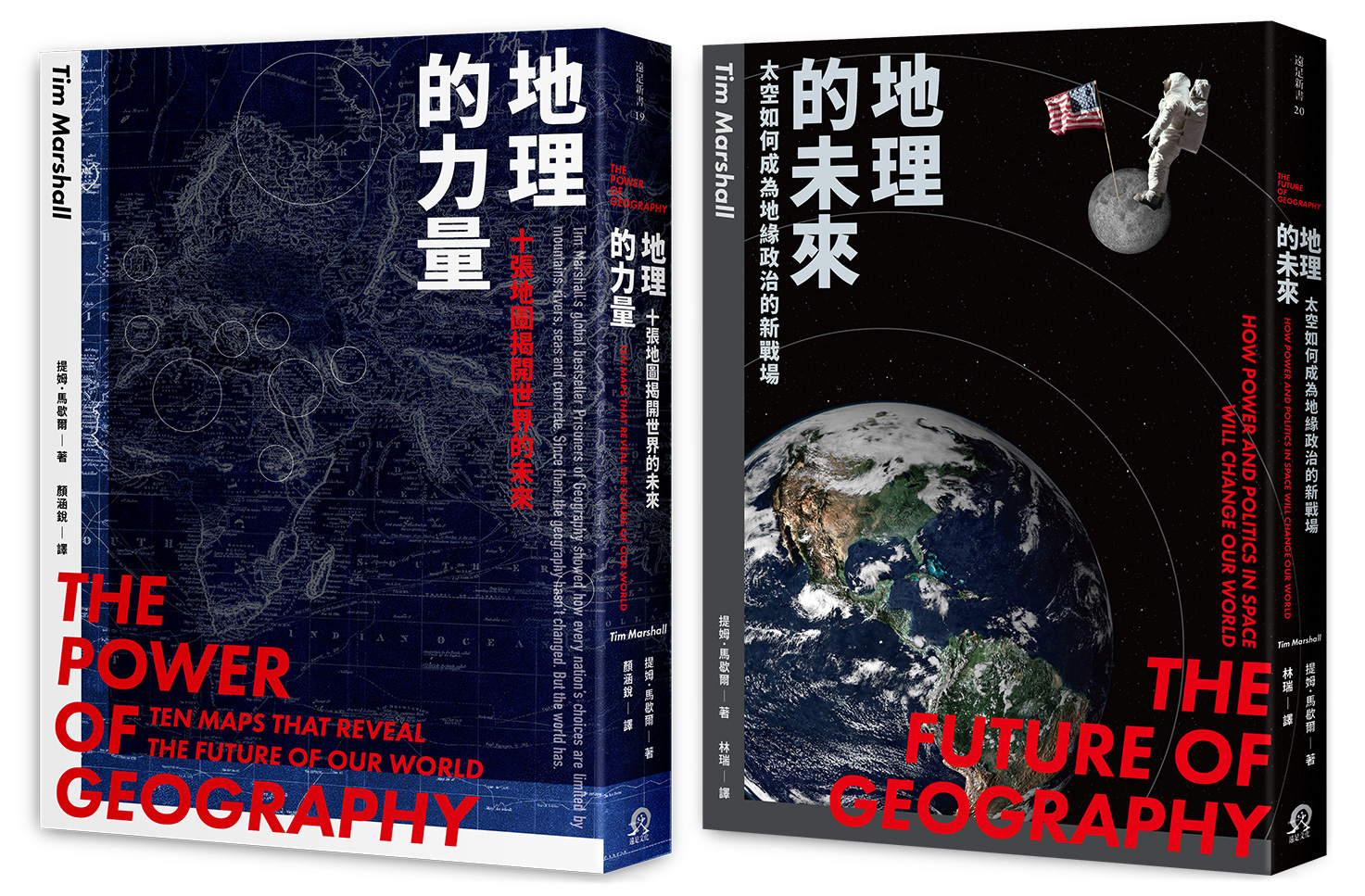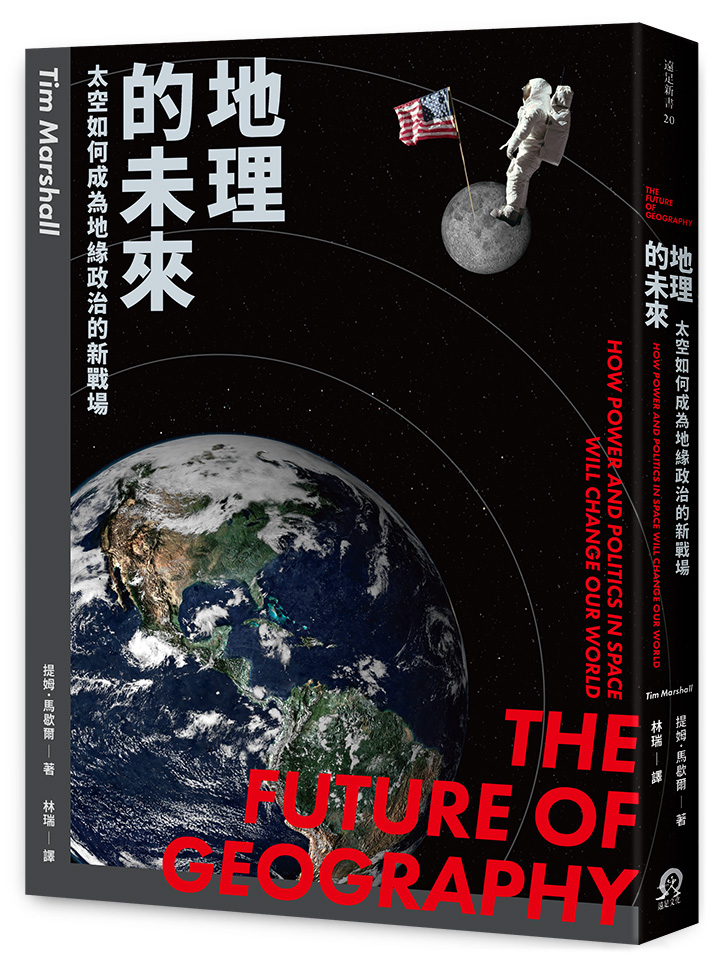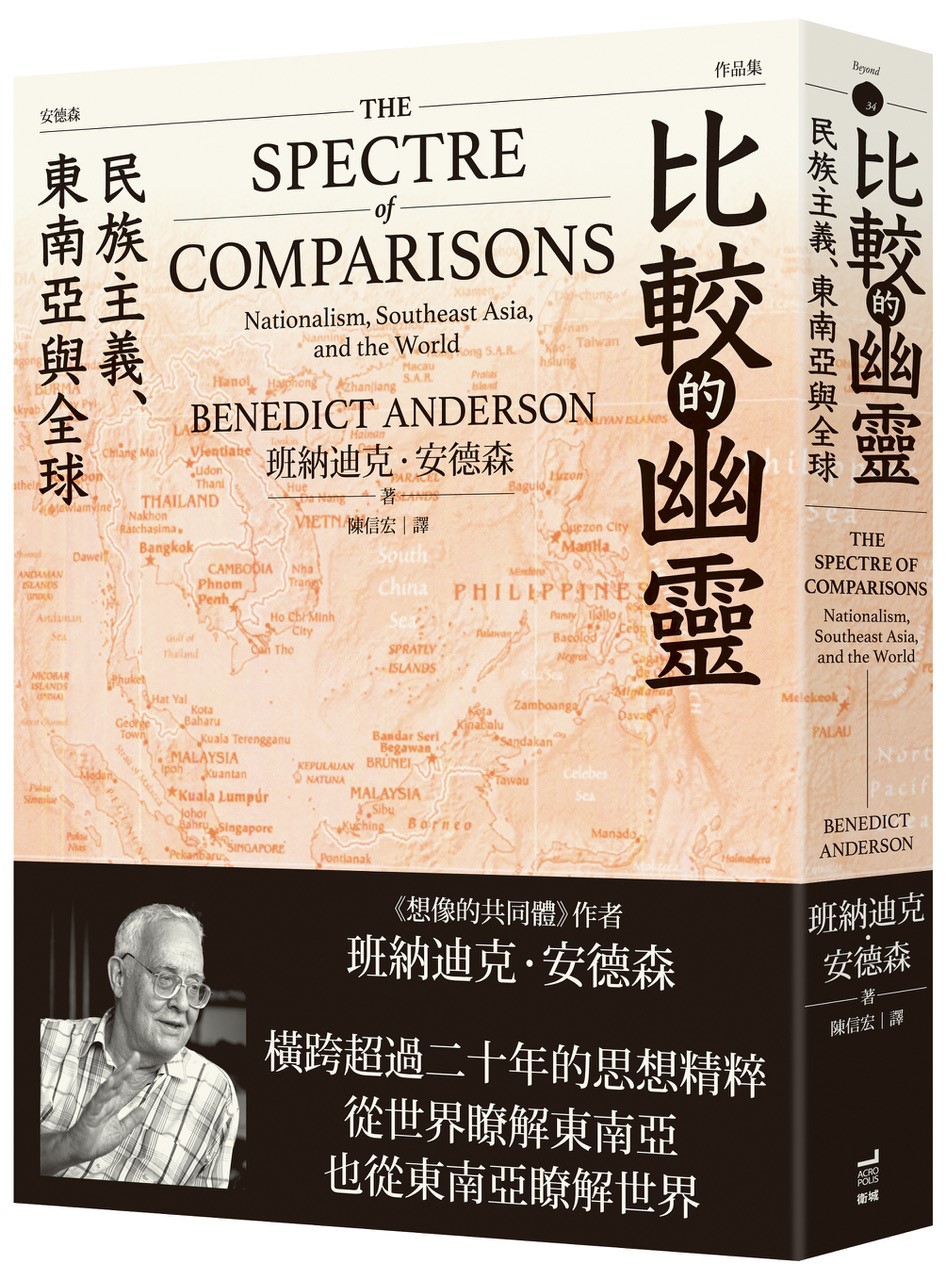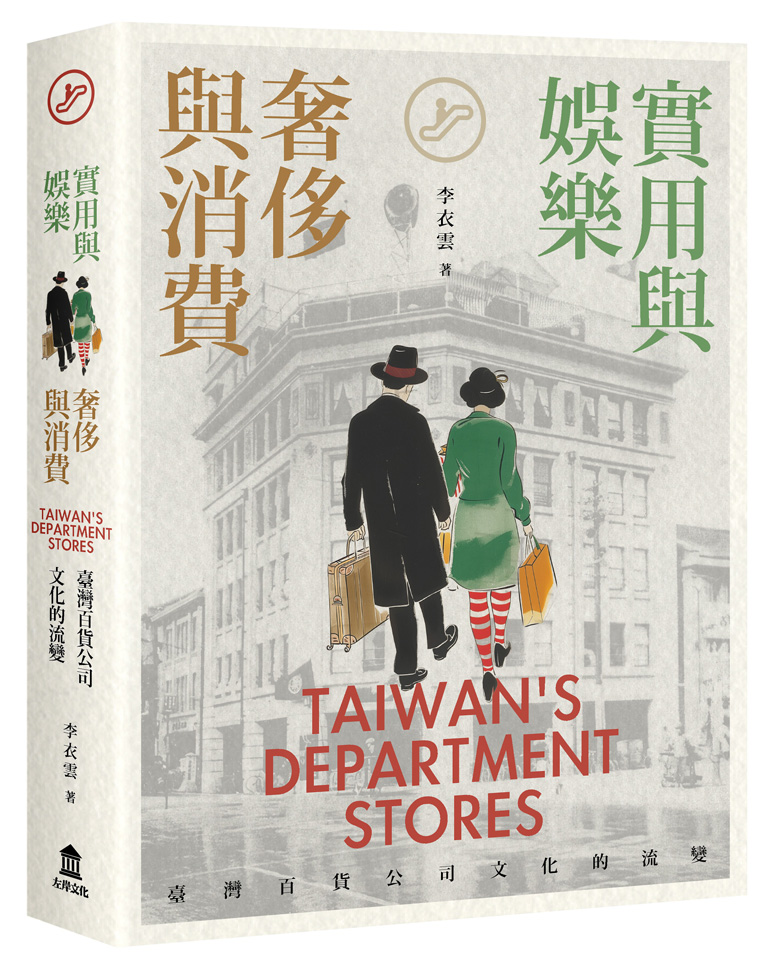從「一口飯」到餵養「不歸路」,
癡心?還是瘋狂?
牽掛與放下、救援與困境,
為什麼愛?這麼愛?
深夜橋下、堤防、廢墟、巷弄……,
愛的修羅場。
「我必須煮更好吃的肉,和籠子裡的烤鴨拼,而且一天要多餵幾餐,填飽牠們肚子,以免牠們進去籠子被捕。現在只要有空就去看,下班後也要巡一次。常常半夜一、二點,還去看籠子裏有沒有捕到狗。看到狗在裡面,如果旁邊沒人,就趕快將牠放出來。我曾帶鐵鋸鋸掉誘捕籠的門,也曾用強力膠灌籠子的鎖孔,讓他們打不開。要不是因為籠子很重,都很想把它抬走。」
不知何時,街頭巷弄角落出現了「狗媽媽」,她們有的是為發願的人生意義,有的純粹誤打誤撞,投身救援流浪犬,從「給一口飯」開始,到「無法放棄」的不歸路,她們的愛,也許源於同情,但日後為因應艱困的外在環境,自身耗盡一切,甚至鋌而走險在所不惜,她們的行徑已不是「婦人之仁」足以形容,也因為超乎常人想像,曾經讓她們無形中背負著許多莫須有的標籤,如「瘋婆子」,或者直指「不值得」、「不應該」。這種愛,不被尊重,甚至遭遇無形有形的攻擊和壓迫。
「像我住這種房子,人家會不解這種身份怎會去救狗,像瘋婆子。起初他們都反對,後來發現經過我帶去結紮,流浪犬慢慢減少,於是都不敢講話了。我要告訴那些人我做了什麼,要讓他們知道,有人在做大笨蛋的事情、不能因為女流之輩,而瞧不起我。我要勇敢,我為何要怕你們,我沒做錯事,是你們不了解。」
為了流浪的毛小孩、受難中的生命,高架橋下、堤防、深巷、廢墟……,總能找到狗媽媽的身影。她們極度低調,餵養、結紮、收容、送養,也許是張羅食物的裝備,也許是長夜埋伏的身手,各各練就「絕技」。至於她們的身分,有隸屬於團體,也有獨來獨往的個體戶;經濟上,也非偏見底下沒有生活能力、經濟生產力、佔用資源的邊緣人,她們多的是一邊工作一邊救援,或者利用網絡尋找財路,但也有可以自掏腰包提供幾百萬建設和飼料費的有錢人。
「不是我不救,而是沒辦法了。眼睜睜看牠們病死,好痛苦,哭到不行,情緒的波動好幾個星期,心疼到不行。所以朋友每次看到我眼睛紅,就會問又是哪一隻死了。然後她教我一個方法,以後任何一隻流浪犬死掉,就想說牠們一路好走,這樣就比較不會像之前哭得要死要活。我只能如此,否則根本餵不下去。」
本書作者因為相同的背景經驗,多年來近距離觀察、採訪狗媽媽,希望藉著她們的故事理清社會對她們的各種詮釋和想像,不論是過度稱頌「愛心媽媽」以推諉責任的誤解、「她們自願自受」的歧視,或者是流浪動物問題製造者的指責,關切她們的社會處境,反省牠們的福利政策……,更由這些心路歷程裡,看見人與動物的牽絆,學習愛的能力。
林憶珊
大學時期即長期投入第一線的捉狗結紮工作,之後就離不開動保圈,不但與志同道合的同學創立動保社團,東華大學族群所的論文更以狗媽媽為主題。畢業後在「關懷生命協會」服務,最欣慰的是結合大家力量,將第一線的困境轉成公共政策,成功推動「禁賣捕獸夾」法案。後期因接觸動物權,開始關注犬貓之外的動物處境,參與推動成立台大動權社。2013年與夥伴創立「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TAEA),致力推動動物平權教育,培力社會大眾成為動物守護者。
推薦文
推薦1.
你所不(想)知道的愛心媽媽
黃宗慧(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起初,只是比一般人多了點不忍,少了點過目即忘的能力,於是流浪動物受苦的影像盤據在腦海,於是想去緩解牠們的痛苦,而這再單純不過的善念,在台灣特殊的環境下,卻從此成為某一群人的緊箍咒,使她們走上「愛心媽媽」這條不歸路。《狗媽媽深夜習題:10個她們與牠們的故事》這本書,所記述的正是這些你所不(想)知道的,愛心媽媽們的心路歷程。10個故事刻畫出10種不同樣貌的愛心媽媽,但相同的是她們多半因為難以得到足夠的認同與理解,索性選擇在暗夜中餵食流浪動物。當她們的身影沒入黑夜時,她們的面貌也隨之益發模糊,還好有憶珊這樣真切關懷台灣動保議題的作者,用她誠懇的文字見證了她們與牠們的邂逅。而作為替本書寫序的推薦者,我真心的希望這一次,有更多人因此願意轉過身來,好好地看看這些對動物不離不棄的愛心媽媽。
長久以來很多人對愛心媽媽的疑問,就是不解她們何以明知餵不完、撿不完、救不完,卻還是硬把這些事情攬在自己身上?於是當她們感到心力交瘁時,多數人只會以「歡喜做,甘願受」來合理化社會對於她們困境的無視,還有些人甚至嘲諷「愛媽」根本是「礙媽」—因為太自不量力,不但沒解決社會的流浪動物問題,自己反倒成了社會問題。愛心媽媽們究竟是怎麼把自己帶進了這般孤單又艱難的處境裡的呢?透過憶珊的書寫,我們似乎可以找到回答這個問題的方向。
很多時候她們之所以背上了餵食狂或收集癖的污名,只不過是因為無法輕易轉身離開。只要一看到那些或狼狽、或病弱、或驚惶的生命,就忍不住問自己:「能力真的不行了嗎?真的見死不救了嗎?同樣是生命,為何這次這隻就該被視而不見?」,這一連串的自我質疑成了她們給自己下的緊箍咒。過不了自己這一關,就註定會伸出援手,而付出的代價,就是越來越沉重的負擔。
這樣來理解愛心媽媽的處境,並不是要美化或浪漫化她們,也不是要說「所有的」愛心媽媽都對於動保有相當程度的見解,更不是要矢口否認她們在作法上確實可能造成周遭不同立場者的困擾;而在我的閱讀裡,這也決非憶珊這本書的目的。事實上,與其說本書所呈現的故事是要提供我們「看待愛心媽媽的正確方式」,不如說是向社會大眾拋出了一連串值得思考的議題:為什麼台灣社會的流浪動物問題會長期處於無解的狀態?除了政府的不作為之外,大眾的漠不關心是否也是關鍵?當數量如此龐大的苦難生命竟是交由部份愛心媽媽來負擔時,她們的力不從心是否也就成為某種必然?當愛心媽媽決定與弱勢的動物站在同一邊時,似乎也就決定了她們同樣淪為弱勢的命運,面對這樣的現狀,如果這一切是我們所不樂見的,那我們又能為她們/牠們做些什麼?
長年在台大開設通識課「文學、動物與社會」的我,所設計的學生分組報告主題之中,有一個是「台灣動物保護運動的困境與出路」。我要求選擇這個主題的同學們實地去採訪愛心媽媽或動保團體,以便對台灣動保的特殊性能有更具體的掌握。曾經有位同學在報告時大嘆完成這項作業非常辛苦:「採訪的時候都會被愛心媽媽拖住走不了,因為她們有好多牢騷要發……」台下的同學們笑了,而我雖然可以想像同學在時間壓力下脫不了身的焦慮,但也不禁感慨,一直以來台灣處理流浪動物問題都只有捕捉與撲殺這套無效的辦法,也難怪總在第一線看著動物受苦的愛心媽媽會有滿腹牢騷吧?而如果有更多人願意聽聽她們的心聲,會不會有朝一日她們所能與人分享的,就不再是苦水與牢騷,而是生命的可貴與人情的溫暖?有著愛心媽媽靈魂的我,由衷地期盼著這本書的出現,正是為了讓那一天早點到來。
推薦2
回憶愛狗女士湯媽媽
朱賢哲(動物權益及流浪狗紀錄片導演)
湯媽媽是我當年(1996年)拍攝流浪狗紀錄片「養生主」的主角之一,情感率直真誠的愛狗保育人士。今年(2014年)三月中,湯媽媽女兒湯宜之告訴我,在爸爸的同意之下,她們將關閉已經昏迷多年湯媽媽的呼吸器,會如何沒有人知道,但醫師會協助盡量減少她的痛苦。
湯媽媽性格如同狗媽媽博士一樣會為流浪狗與人爭執、吵架,無論對方是官方、社會人士甚或動保人士。有時她也會像狗媽媽黑耳「選擇罵不回嘴,也不理睬,但多少會心酸,只能和愛媽互相取暖一下」。雖然狗媽媽們經常處在委屈、孤單,但她們從不在情感上退縮,愛狗始終如一。社會快速變遷,人與人關係複雜脆弱,狗媽媽們心靈狀態特別顯得純淨。我常覺得,對於當年一個剛出社會的我,有機會與一群對生命價值提出控訴的保育人士在一起、經歷幾場艱辛的保育事件,是我此生最大的幸運,因為我被拉到社會主流之外。從此,我不被人的觀點看待這個世界所束縛,因為世界含蓋萬物,人類畢竟只是其中一個物種。
狗媽媽另外給我的啟示是宗教的內涵,例如狗媽媽黃黃平常是花時間在參加法會的佛教徒,師兄姐會反諷她:「吃飽不去唸經、跟眾生結緣。」黃黃剛起初不應答,後來才回說:「佛祖也不是吃飽閒閒,坐在那邊唸經,佛要普渡眾生。很多佛教徒認為救動物,來世會到畜牲道裡,那他們就去好好修行,讓我來救好了。」在這對話中我非常認同狗媽媽黃黃地藏王菩薩精神。這幾年我經常反思,到底做一件善事的內涵應該放在距離多遠的心靈來感受,而,堅持、執念與覺知善意到底有無因果關係。其實,我沒答案…但我敬佩所認識的這些狗媽媽們,也感謝她們給予我的生命教育課程。
湯媽媽於今年3月25日過世,謹以此篇短文祝福她,也為這本書10位及更多正在為台灣流浪狗奮鬥的愛心媽媽致敬。
作者序
她們的故事,我們的明境
林憶珊
没錯,我就是因為狗媽媽而踏進動保界的。二十年前的我不會留意外面的流浪狗,因為認養一隻狗,我開始去花市幫忙送養流浪動物,看到不少狗媽媽為了流浪狗讓人東罵西趕,相當感動她們願意做「顧人怨」的事,因此也被感召學習一些技術以協助她們捕捉浪犬絶育。本書根據我的碩士論文改寫而來的,但其中有一半受訪人則為新的採訪對象。當初寫完論文時,自己急於讓大家都知道狗媽媽的情況,常常印製論文到處送人,沒有多想要出書的念頭,如今成真,也算了結為她們發聲的一樁心願。
狗媽媽各自的背景非常多元,本書中我沒有訪問到開賓士車的愛媽,也沒訪問到資源回收的愛媽,但受訪的狗媽媽都是超過十年以上的資深愛媽,有幾位甚至長達二十幾年。她們投注大量的金錢、時間和心力,為了孩子們的「一口飯」到處奔波,所付出的努力非外人所能想像,為此可能拖垮自己;而外界因不了解、沒機會認識或媒體強化的刻版印象,讓她們幾乎是獨自面對整個不友善的大環境,默默承受一切,卻始終義無反顧堅持下去。從她們身上,我看到溫暖與剛毅並蓄。
她們的故事就像是一面反省的明鏡,映照台灣流浪動物的問題根源──政府不積極管控源頭,就如水籠頭沒關上水一直流,導致浪犬浪貓悲歌不斷上演,也因此狗媽媽的付出永無止盡。寶寶的誘捕籠淡淡地控訴動保法的荒謬,無人陪同的狗在街上任何人皆可捕捉;芽芽的看門犬反應飼主責任教育的不足,以及公部門對動物福利及執法能力的不足;政府對殺狗違法不多加宣導,致使可卡也只能自己努力搜證,對比政府捕抓浪犬卻不需報案人舉證,顯得格外諷刺;咪咪控訴結紮後原放的狗卻被捉去撲殺;政府對繁殖場棄狗毫無作為,使得毛毛一直撿狗;像可可和呼呼自力搭檔從事救援與結紮的行動,她們曾試圖與公部門合作,卻得不到回應。在台灣這樣的環境下,因而有像黃黃、博士、可魯必須覓地蓋狗場,而嘟嘟得將浪犬送到國外認養,黒耳東遮西掩地餵食河濱浪犬,更有像阿基歐為了救出收容所中的狗,先幫狗找好主人或是去處。
記得我在碩論口試時,一位口委說我的論文被狗媽媽壓倒了,他認為我似乎過於同情愛媽的處境,也有人認為狗媽媽照顧流浪犬,也無法徹底解決台灣流浪犬的整體問題,沒錯,其實這本書也解決不了。但正如德雷莎修女創立「垂死之家」並沒有解決印度社會的貧窮問題,但她為那些貧病交加的人們無私奉獻,樹立了令人景仰的價值,感召無數人。透過這本書,我希望大家能一起加入保護動物的行列,並翻攪主流的社會觀感,讓外界看見愛媽不被看見的作為,進而以同理心對待她們,是否可以別再輕易地說,「沒有能力就別做嘛」、「喜歡養狗就帶回家」、「要餵不要在我這邊餵」?而應當試圖讓環境多點善意,鼓勵她們抬頭挺胸繼續走下去。
最後,此書獻給一位自稱也是愛媽的動保好友鄧巧玲(已於今年2014年去世),猶記得她曾說:「自己帶著收容的三十幾隻狗搬了無數次的家,就像流浪狗般,帶著一顆倉皇的心,四處為家。」也獻給所有正在努力的狗媽媽們。
「照片中的狗狗一些可能已經被人收養、一些可能已經往生或遭受不幸,別忘記他們,這些照片都證明他們曾經存在過。」
——沈怡帆
兩人騎著機車,路燈一支支地過,道路標線始終保持速度性的模糊,唯一陪伴我們的是,嗡嗡引擎聲與偶爾斷續不清的交談。
隨著前方領頭的愛媽,今天深入狗場,明天漫遊巷弄街區,她們有些清瘦結實,有些豐滿時尚,戴墨鏡或者穿短褲,可拍正面或者僅露側臉,更多時候我分不清楚那些疊字假名指涉的是誰或誰,除了擔心失禮與尷尬,只能儘量讓焦距清晰,尋找適切的構圖,或在浪犬的警戒外,停下腳步蹲身,盡全力伸長鏡頭,把持主觀與客觀的界線,克制獵奇的衝動,到底是什麼驅動自己按下快門?而反覆按下快門的自己,在浪犬與愛媽眼裡又是什麼樣子?
不安讓一個畫面從原本的五張連拍來到了十張,要走要留,或緊追或蹲點?近拍還是遠景?選擇僅在一念之間,結果可能更好或者更壞,所有關於自我的懷疑全都灌注在手中握持的相機裡,沉甸甸的,明確而無法忽視的重量,時間持續軟化一切,要保持意識清明並不容易,一不小心可能迷失在亢奮的窺視與追擊裡而不自知,卻誤認為是一種積極的狀態,也許定格的從來都不是愛媽與浪犬,反而清楚地映現了自我於種種不確定性下的心理殘跡,姑且也算是一種真實吧,不論照片好壞,如果能在時間裡保留任何純粹的意義,我希望是對這些愛媽的一種支持與肯定。
——傅翊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