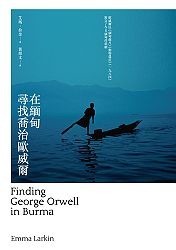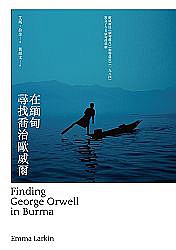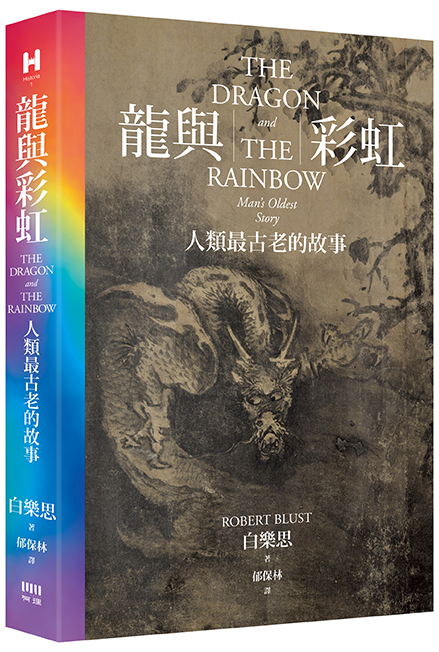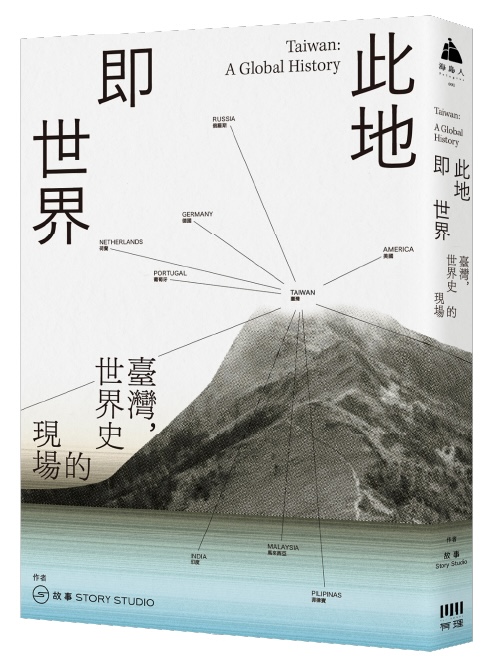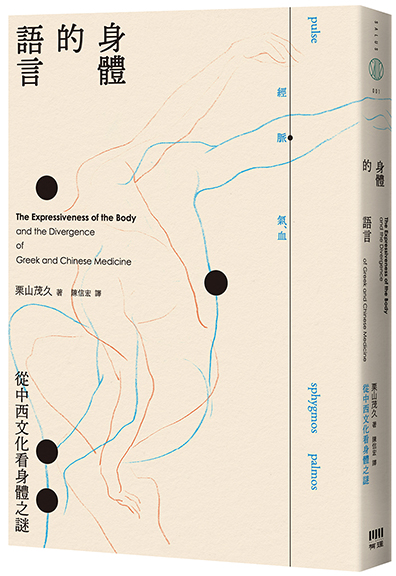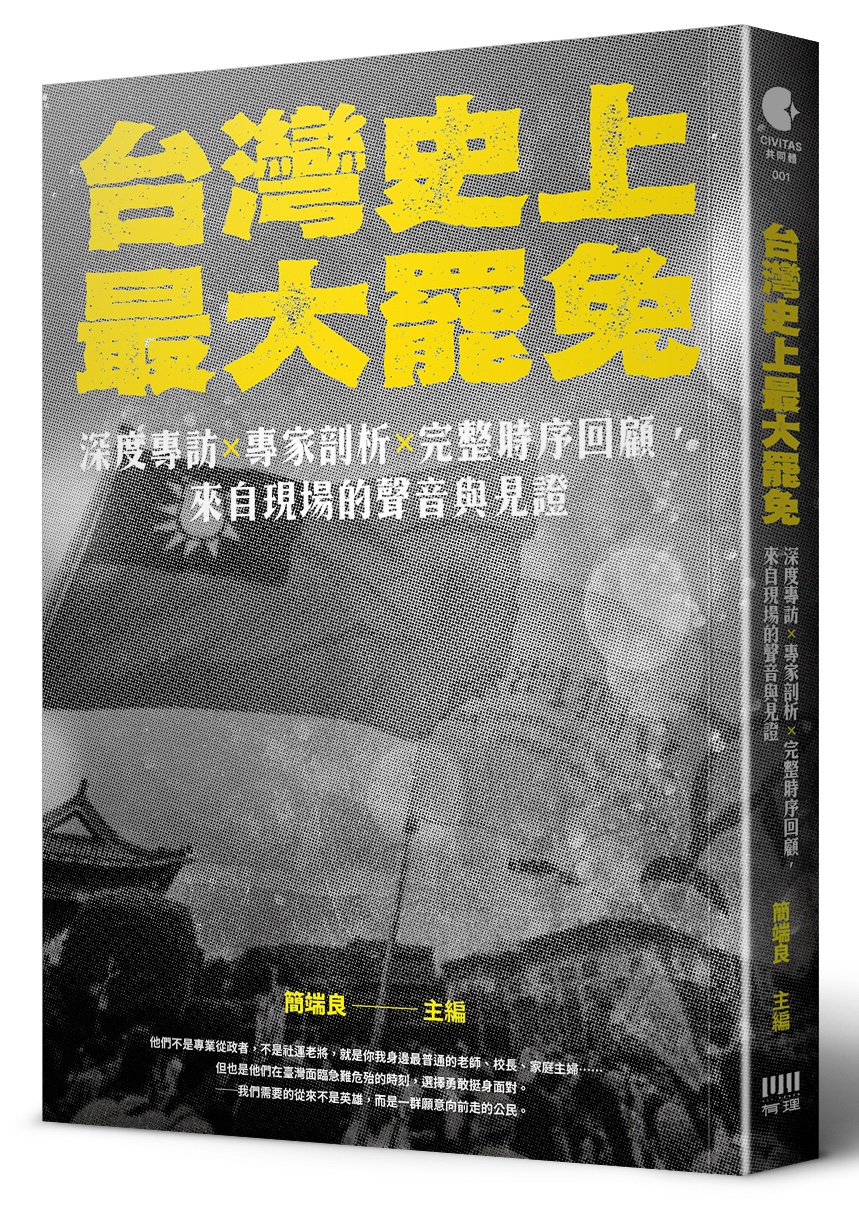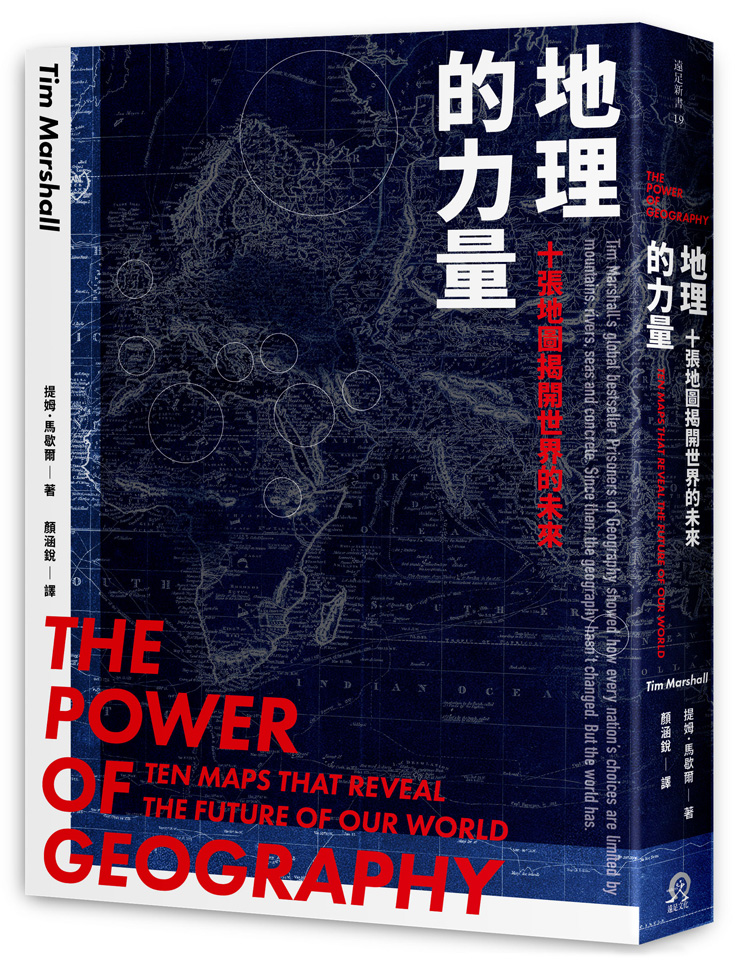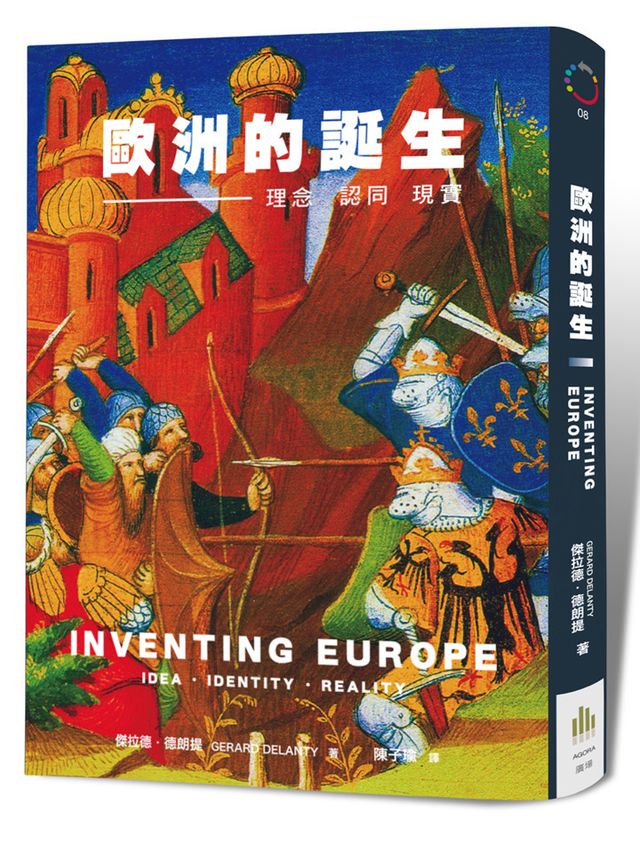序言 「喬治.歐威爾,」我緩慢地說:「喬─治─歐─威─爾。」但眼前這名緬甸老人還是不斷搖頭。 這是下緬甸(Lower Burma)一處令人昏昏欲睡的港口城鎮,我們來到老人家中,坐在宛如烤箱的客廳裡。屋內空氣悶熱難耐。我聽到蚊子圍繞著我的腦袋,焦躁地發出嗡嗡的聲音,而我的耐性似乎也即將用盡。老人是緬甸的知名學者,我知道他很熟悉歐威爾。但他已經上了年紀;白內障使他的眼睛泛著牡蠣藍的光澤。當他重新穿好身上的紗籠(sarong)#時,兩隻手還不斷顫抖著。我懷疑他是否已經失憶,而在失敗好幾次之後,我決定做最後一次嘗試。 「喬治.歐威爾,」我又重複一次,「《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的作者。」老人突然眼睛一亮。他看著我,一副意會過來的神情,然後開心地拍著自己的額頭說:「原來妳說的是先知啊!」 歐威爾於一九五○年去世,就在前一年,他的打字機遭到沒收。歐威爾住在科茨沃德斯(Cotswolds)的小木屋裡,這裡充滿綠意且舒適宜人。在養病期間,歐威爾經常整個人窩進電毯,但最後還是不敵肺結核的侵襲而離開人世。他的病床旁堆滿了各種書籍,其中有許多是討論史達林以及德國在二次大戰期間殘暴罪行的作品,有一本十九世紀英國勞工研究,幾本湯瑪斯.哈代(Thomas Hardy)的小說,伊夫林.沃(Evelyn Waugh)早期的一些作品。床底下還藏了一瓶蘭姆酒。 在療養院負責治療歐威爾的醫師們囑咐他最好不要再繼續寫作。他們說,不管是哪一種寫作,都會把他累垮。他需要專心靜養。歐威爾的兩個肺因疾病而阻塞,而且開始咳血。他的病情已到了關鍵時期,醫師對於病人是否能夠痊癒不表樂觀。即使他能痊癒,大概也無法繼續寫作,或者至少不能像過去那樣沒命地投入。然而歐威爾還是繼續搖起筆桿。他潦草地書寫信件、撰寫隨筆、評論書籍,同時還改正即將出版的小說《一九八四》的校樣。他熱切的心靈甚至正醞釀著下一部作品:中篇小說〈一則吸菸室的故事〉(‘A Smoking Room Story’),這本書打算重新造訪緬甸,這個歐威爾年輕時離開就未再回去的地方。 一九二○年代,歐威爾在緬甸擔任帝國警察。五年執勤期間,他總是穿著卡其馬褲與閃亮的黑色馬靴。帝國警察配備槍枝,是道德優越的象徵。他們巡行鄉里,即使位於大英帝國偏遠的一隅,他們也力求秩序井然。然而,有一天歐威爾突然無預警地返回英格蘭遞交辭呈。同樣突然的是,他開始了寫作生涯。歐威爾署名時不用自己的本名「艾瑞克.亞瑟.布萊爾」(Eric Arthur Blair),而另取了筆名「喬治.歐威爾」。他換上流浪漢的破爛衣裳,在潮濕的倫敦深夜遊蕩街頭,收集貧苦大眾的故事。歐威爾第一部小說《緬甸歲月》(Burmese Days)是根據他在遠東的經驗寫下的,但他真正成為二十世紀最受尊敬與最具洞察力的作家則是因為《動物農莊》(Animal Farm)與《一九八四》這兩部作品。 這是一段不可思議的命運安排,這三部小說居然體現了緬甸晚近的歷史。第一個連結是《緬甸歲月》,它記錄了緬甸在英國殖民時期的故事。一九四八年,緬甸從英國獨立,不久軍事獨裁者就阻絕國家與外界的連繫,發起所謂「緬甸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並且讓緬甸淪為亞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相同的故事出現在歐威爾的《動物農莊》裡,一群豬推翻了人類農民,自行經營農場,最後卻招致毀滅,這則寓言暗喻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最後,在《一九八四》中,歐威爾描述的可怕而無靈魂的反烏托邦(dystopia),宛如一幅精確得令人心寒的今日緬甸圖像,一個被世界最殘忍與最頑強的獨裁者統治的國家。 緬甸有則笑話,說歐威爾不只為緬甸寫了一部小說,而是三部:這三部曲就是《緬甸歲月》、《動物農莊》與《一九八四》。 一九九五年,我首次造訪緬甸,當我走在曼德勒(Mandalay)的繁忙街頭時,一名緬甸男子一邊快速旋轉他的黑色雨傘,一邊看似有所意圖地大步朝我走來。他露出開朗的笑容說道:「告訴外面的世界,我們需要民主,人民已經受夠了。」然後隨即轉身踏著輕快的步伐離開。就是這個:這稀罕而短暫的一瞥,已足以使我瞭然於心,緬甸並不像我們表面上看到的那樣。 我花了三個星期的時間在宛如明信片般完美的景致裡四處遊歷,無論是人聲鼎沸的市場、閃閃發亮的佛塔還是風華褪盡的英式山間車站,這一切都讓我無法相信自己旅行於一個世界人權紀錄最糟糕的國家。我認為,這是緬甸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地方:全國約五千萬人口遭受的各種壓迫,居然可以完全隱藏起來不被外人發現。無孔不入的軍事諜報人員與密告網絡,確保沒有人能從事或洩露任何可能威脅政權的事。緬甸媒體──書籍、雜誌、電影與音樂──受到嚴格的檢查控制,政府的政令宣導不僅透過報紙與電視,也經由學校與大學傳布到全國各個角落。這些掌控現實的方法,背後由一股不可見卻又無所不在的力量牢牢支撐著,使全國人民無時無刻籠罩在拷問與監禁的威脅之中。 像我這樣的局外人,不可能看穿軍政府粉飾的太平景象,也無力想像在這種國家生活的恐懼與朝不保夕。而就在我努力瞭解緬甸生活面向的同時,我也逐漸感受到歐威爾作品的魅力。他所有的小說都在探索一個觀念,就是個人深受環境的箝制與束縛,不僅受到家庭的控制,也受到周遭社會乃至於權力無所不在的政府的宰制。在《一九八四》中,歐威爾構思出最終極的壓迫形式,甚至創造出能描述這種壓迫的語言:「老大哥」、「一○一號房」、「新語」。 我再度閱讀歐威爾的小說──從我離開中學之後就再也沒碰過他的書──心中對於他與緬甸的關係深感好奇。什麼原因使他願意放棄殖民地的工作,選擇當一名作家?而在離開緬甸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又是什麼原因使臨終前的他將目光轉向緬甸尋求寫作的靈感?我開始想像歐威爾從緬甸看出了什麼,他也許尋出了某種觀念的線索,可以一路貫穿他所有的作品。我閱讀許多歐威爾傳記,但這些傳記作家似乎都低估了緬甸的重要性,沒有人對這個歐威爾曾經生活過五年,而且令他的人生產生重大轉折的地方進行研究。歐威爾當初駐在的城鎮就位於緬甸的地理核心位置,某方面來說,現在的我們仍有可能感受到歐威爾當初生活過的緬甸──將近半世紀的軍事獨裁統治,整個國家的風貌彷彿被凍結起來,過去的風貌許多仍完整的保留下來。然而實際走過歐威爾的緬甸,看到的卻是更陰森而駭人的景象:象徵歐威爾夢魘的《一九八四》,竟在這裡以令人不寒而慄的方式真實上演。 外國作家與新聞記者是不准進入緬甸的。偶爾有人混充觀光客而順利入境,然而一旦身分暴露,他們的筆記本與底片會遭到沒收,而人也隨即被驅逐出境。至於他們訪談過的緬甸人,遭遇的懲罰將嚴厲得多。根據緬甸一九五○年制定的緊急法令(Emergency Provisions Act),凡是提供外國人任何政府認為可能有害國家的資訊,最高可判處七年徒刑。雖然我是新聞記者,但我很少發表有關緬甸的報導,所以我仍有機會以觀光客或極少數外商的身分申請到長期居留簽證。為了把我的經驗寫入書中,我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協:我必須改變我訪談過的緬甸人姓名,有必要的話,連地點也會變更。然而在這種謹慎的過程中,我希望自己能找出一條道路,洞穿這個看似不可穿透的國家。 在我動身前往緬甸之前,我到了倫敦的喬治.歐威爾檔案館(George Orwell Archive),觀看歐威爾最後的手稿。當歐威爾於一九五○年去世時,他才剛開始著手一個寫作計畫。根據他的計畫,〈一則吸菸室的故事〉是一篇長度約三萬到四萬字的中篇小說,內容講述一名充滿活力的英國年輕人在緬甸殖民地潮濕的熱帶叢林居住之後,整個人出現難以回復的變化。翻開用大理石花紋紙張包裹的筆記本,前三頁布滿歐威爾潦草的墨水字跡,大致是故事的大綱與短篇插曲。我輕輕地翻覽整冊筆記本,發現後面的書頁空空如也。我知道,故事的剩餘部分還塵封於緬甸,等待人們喚醒。第三章 仰光權力就是把人類的心靈撕成碎片 然後依照你自己選擇的新形體 再次將心靈組合起來。 《一九八四》 抵達仰光之後,我第一個見的人是我的好友哥葉(Ko Ye),他是研究緬甸軍政府如何控制現實的專家。哥葉在仰光從事出版業已有三十年的歷史。他的出版社(連同緬甸每一家出版社)出版的每一頁的每個字,在流通市面之前都必須通過政府審查。仰光之所以能維持表面的平靜,或許是因為嚴密審查的緣故。 哥葉的出版社位於仰光鬧區車水馬龍的地帶,這裡的街道塞滿公車與汽車,攤販幾乎把人行道的每一寸都占滿了。他們販售佛教海報、草藥與盜版光碟。一名纏著腰布的印度人蹲在一只裝滿熱油的鐵鍋前翻攪著一口大小的咖哩角。一名年輕女孩揮舞著塑膠袋,好趕走覬覦新鮮柚子的蒼蠅。客人蹲坐在矮錫桌前等著湯麵端上桌,小販從大桶子裡鏟起印度香飯放進塑膠飯盒。在道路兩旁,民眾坐在人行道上的茶館裡,他們的腿整齊盤坐著,外面罩著籠基,冷眼看著混亂的車流來來去去。 我走在街道相對安靜的另一側,不久便找到哥葉位於一樓的辦公室。有人到後頭房間找他過來,要我稍等一下。我看著出版社排演流暢的芭蕾舞──一臺跟汽車一樣大小的吵雜黑色機器,一名光著上身的男子穿著勞工常見的及膝籠基,操縱著控制桿,另一名男子蹲伏在機器下方接住推送出來的印好書頁。一名女子盤坐在機器旁的地板上,她把剛印好的書頁疊好,摺進封面之內,然後用粗線將留有餘溫的書頁縫製成一本書。在她身旁,一名雙手墨漬身穿灰白色汗衫的男子把印好的書整齊地疊成一落。他將刻有出版社商標的橡皮圖章上墨,然後結結實實地在每本書的封面蓋上印章。 不久,哥葉──一名身材高大五十出頭的男子──走進房間,嘴裡還叼著一根菸。 「喝茶嗎?」他輕快地問。 「好的。」 哥葉叫一名年輕小伙子過來,他正在門口將一捆捆的雜誌綁在腳踏車的後架上,準備運送到仰光各家書局。他塞了幾張鈔票到他手裡,要他買茶回來。哥葉要我坐在他書桌前的小凳子上,他自己則坐在書桌的另一邊,用手上的菸點起另一根菸,然後談起他最喜愛的話題:出版登記與審查部(Press Registration and Scrutiny Department, PRSD)。出版登記與審查部隸屬於軍情局下,是名副其實的出版審查部隊,負責搜尋每一份印刷品(不管是學校課本、雜誌、月曆或歌詞)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每一張圖是否有反政府內容。哥葉拿起擺在桌上的生活雜誌。在粗糙、灰色的書頁上登滿了短篇故事、有關電影的文章以及流行歌手的簡單介紹。他迅速翻過雜誌,指出審查人員用粉紅色螢光筆草草畫過的某些段落、某些頁面,甚至一整篇文章。在每個記號旁邊都潦草地寫了一個字「hpyoke」,就是刪除的意思。 「為什麼是這幾頁?」我問。 「我也搞不懂,」他回答:「恐怕審查部的人自己也不知道。」哥葉解釋出版登計與審查部規定了十一個空泛的條文,概略地提到哪些主題不能寫。條文相當模糊抽象,只要扯上一點邊的,他們就會禁止: ●「有害國家意識形態」 ●可能「有害安全、法治、和平與公共秩序」 ●「錯誤觀念與悖逆時代的意見」 ●雖符合事實,但「內容不適合出現在目前的時間或環境」 「他們從不明確地說明『為什麼』某些內容會被禁,」哥葉說:「我們只能用猜的。」有些禁忌明顯是不能提的,例如全國民主聯盟領袖翁山蘇姬、一九八八年的民眾暴動事件,與「民主」這個詞。每個月,編輯都要去聆聽簡報,瞭解這個月又多了哪些不能談的話題──審查部的規定變來變去,通常要看緬甸內部發生了什麼事來決定──而在我與哥葉碰面的時候,這些規定包括了稻米(面臨嚴重短缺,促使政府必須進行配給)與黃金(金價上漲進一步顯示緬甸經濟的困境)。最近幾個月,緬甸與鄰邦泰國發生政治糾紛,審查部因此要求刪除所有與泰國有關的新聞。哥葉說,這意謂著所有跟泰國有關的東西,包括泰國人,以及泰國產品的廣告。有一本月刊不小心登了一則泰國公司廣告,結果審查部就禁止那一期的月刊出刊。審查部的命令也涵蓋了國際新聞。太密切反映出緬甸自身歷史的報導也禁止出現在緬甸的報紙與雜誌上,例如一九九八年印尼發生的群眾暴動導致專制領導人蘇哈托將軍(General Suharto)下臺。 小伙子回到辦公室,手裡提著一袋熱騰騰的茶水。哥葉在桌上放了兩只茶杯,然後熟練地把茶水倒出來,他抓著塑膠袋的一端,搖晃出最後一滴茶水。 「不只政治消息會被禁,」哥葉又說。即使是基本的公共資訊,例如就在我抵達緬甸之後,火車票價就漲到原來的四倍,也不許出現在報紙上。人們只有透過口耳相傳或到火車站買票時才會知道這件事。「這些將軍不想看到自己國家的壞事被印成白紙黑字,」哥葉解釋說。 一九一四年,一部名叫《凱絲琳的冒險》(Adventures of Kathlyn)的電影遭英國緬甸政府禁演。這部電影是關於一名白人女性在一座以印度為藍本的虛構小島的冒險故事。英國審查人員甚至不需要看這部電影。他們只要看一下廣告小冊子,就用紅色蠟筆把他們反對的句子圈起來。其中一句提到不幸的凱絲琳被賣到奴隸市場,另個句子則炫耀說:「你將看到凱絲琳被狂熱的原住民捆綁起來!」英國政府覺得白人女性在這種難堪的情境裡呈現的形象帶有貶意,可能給緬甸觀眾帶來壞的影響。當局對於媒體描繪英國人的方式非常敏感,而且把所有媒體的批評都視為對英國王室正當性的貶損。一九三三年,緬甸的英國審查人員禁止風評甚佳的電影《亨利八世的私生活》(The Private Life of Henry VIII)上映,片中描繪國王用手狼吞虎嚥地吃東西:他們不希望有人看見英國國王不用餐具吃東西的樣子,但絕大多數緬甸人至今仍是這樣飲食。運用嚴格的出版管制法(人稱「封口法」),英國對報紙、雜誌乃至於書籍進行審查與禁止。《印度愛經》(Kama Sutra)與《我的奮鬥》(Mein Kampf)同被列入禁書清單之中。只要被審查人員貼上「仇恨」、「煽動叛亂」、「不忠」或「不滿」的標籤,就會被處以高昂的罰金,最嚴重的甚至要坐牢。 從英國獨立後的短短十年間,緬甸出版業經歷了一段自由而活潑的時期。但當奈溫掌權之後,他重拾過去英國箝制媒體的法律,並且自行增添了一些限制。近年來,既有的法律陸續進行增補,對媒體的控制愈來愈嚴厲。當局持續更新所有在職作家與編輯目前的動態。與英國殖民時代一樣,只要稍稍越界,就會受到重罰或坐牢。有一名出版商正面臨三到七年的刑期,因為他未經授權出版了學生的小冊子,裡面都是一些學生的詩文與校園新聞。另一名出版商在印行某一本書時,數量超過了當初登記的兩百本,因此被處以高額罰金,公司也禁止營業半年,實際上已形同破產。「審查制度愈來愈嚴苛,」哥葉說:「隨著列入黑名單的作家數量愈來愈多,要寫東西也就愈來愈難,編輯自然而然膽子也愈來愈小。」 雜誌編輯尤其辛苦。雜誌必須印好之後才能送去審查,如果審查人員要求變更內容,編輯就必須自行吸收成本。如果一整頁都是冒犯性的內容,就會直接撕掉,如果是一整段,那麼就用黑墨或銀漆、金漆蓋住(這樣就算把書頁對著光看,也看不到上面的文字)。舉例來說,一九八四年,有一名雜誌編輯打算刊出歐威爾《一九八四》的節譯本,審查人員直接把它撕掉。現在,審查部要求的手法更精細了:它不希望民眾發覺媒體受到審查。但哥葉向我解釋怎麼樣看出內容被刪掉。因為編輯有截稿時間的限制,很難有時間重寫文章,於是就預先準備好可以塞進被審查人員刪掉的空格。他拿了一本雜誌給我,編輯用很多廣告來填滿這些空間。光數廣告有幾個就可以看出審查的力道。我把整本雜誌翻過之後,發現裡面占四分之一頁的廣告有六個,占半頁的有七個,而占全頁的有三個。 我們被印刷機傳來的巨大刺耳聲響打斷,緊接著是工人們的抱怨聲。電力中斷,機器振動幾下,最後停了下來。一名工人到外頭開啟小型發電機,幾分鐘後,印刷機咳了幾聲,又回過魂來。雖然仰光的電力供應比緬甸其他地區來得穩定,但每天還是會有停電的時候──有時幾分鐘,但更常見的是幾小時。在仰光的某些地區,例如黃金谷(Golden Valley),這處位於仰光北區的富人社區住著許多將軍,這裡的電力供應就相當穩定。仰光其他地方的夜間電力大概只能維持幾小時。對絕大多數企業來說,自備發電機是必不可少的,在大飯店與集合住宅外頭,經常可見像屋子一樣大小的發電機一天二十四小時不斷發出轟隆響聲。 哥葉從倫敦牌子的菸盒裡敲出最後一根菸來。「審查部控制出版已經有四十年以上的時間,」他說:「有一整個世代的年輕人是在審查部塑造的片面現實裡長大的。」哥葉告訴我,他兒子現在正在閱讀一九五○年代,也就是緬甸短暫享有出版自由的年代的政治小說,他很驚訝地發現過去在緬甸是可以批評政府的。當然,他知道想批評政府必須關起門來(他在家裡大概聽了太多次哥葉對政府的批評),但他不曉得也可以在印刷品上批評政府。「總有一天他們會給予我們更多的經濟自由與遷徙自由,」哥葉認為軍政府最終將會如此:「但他們絕對不會允許我們擁有言論自由。他們知道一旦我們能報導真實的事物──如果人民知道事實──完全的事實,他們不到一個月就會垮臺。」 歐威爾相信,文學不可能在極權主義下生存。極權主義政府知道它的權力來源不具正當性,因此從不允許記錄真實。想維持現狀,就必須仰賴謊言。「現代文學本質上是個人的事物,」歐威爾在〈文學與極權主義〉(‘Literature and Totalitarianism’)中表示:「文學如果不能真實地表達人們的想法與感受,它便一無是處。」簡言之,極權主義斲喪了創造力:「想像力就像野生動物一樣,無法存活於獸欄之中。」歐威爾寫道。 「鬼扯!」一名緬甸年輕作家在讀了我給他的歐威爾文章之後,用一種挑戰的語氣對我說:「走在潘索丹街(Pansodan Street)上,妳會發現緬甸的文學還活得好好的。」潘索丹街還有另一個充滿感情的名稱,叫「街邊大學」。這是一條穿過仰光市中心的繁忙大街。這裡的書店櫛比鱗次,賣書報雜誌的小販幾乎占滿了每一寸人行道。目光所及之處全是書籍,它們要不是堆置在地上,就是擺在臨時的木製書架上:滿是灰塵的古老英文經典、科學教科書、剛出版的緬甸小說、英語系學生的書籍、殖民時期的舊報紙、當代緬甸詩集與短篇小說集,以及世界各地的小說與非小說類翻譯作品。每月出版的書籍約有一百本,月刊一百種以上,另外周刊也有八十種。顯然,軍政府的鐵腕審查無法澆熄緬甸人閱讀與寫作的熱情。 在緬甸,想讀出字裡行間的言外之意是一門藝術,而緬甸的出版者、編輯與作者也發展出一套微妙的手法,足以順利逃過審查者的眼睛,將資訊夾帶進書內。我在仰光曾讀到雜誌上的一篇短篇小說,講的是狼群攻擊大象的故事。仔細思考其中的寓意,你會發現它指的分明是翁山蘇姬以奮勇不懈的力量對抗軍政府對她的政黨的百般迫害。屯林,歐威爾書迷俱樂部那位退休老師,他花了一整個下午的時間向我解釋《獅子王》(The Lion King)這部電影其實是緬甸的翻版。辛巴(Simba),那頭被迫離開家園的年輕獅子,指的是翁山蘇姬。辛巴的父親就像翁山的父親一樣遭到謀殺。刀疤(Scar),這頭邪惡的獅子奪取了王國,並且將美麗的樂土變成寸草不生的荒地,使得許多動物餓死或遠走他鄉,指的就是奈溫。屯林愉快地提醒我,辛巴最後擊敗了暴君,並且讓王國再次成為充滿彩虹與陽光的地方,不僅流著清澈的河水,所有的動物也都能在此和平地生活。 想規避審查,不一定只靠諷喻。雜誌編輯者也刊載了瑞典的醫療制度,希望讀者能比較出國內幾乎不存在醫療制度的狀況。有些出版社出版了像後現代主義與解構理論這類思想學派的入門書。「我們想用這種方式慢慢削弱他們的體系,」一名譯者對我說:「透過這些書籍,我們可以教育年輕人,幫他們張大眼睛看看四周的現實是什麼樣子。這種方法並不直接,但我們很希望人們能夠體會。」 在潘索丹街,我注意到有很多勵志書籍翻譯成緬甸文。西方最暢銷的幾本書,在這裡全找得到:《與成功有約》(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心靈雞湯》(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誰搬走了我的乳酪?》(Who Moved My Cheese?),以及續集《立志做懶人》(I Moved Your Cheese)。我曾聽過一種說法,因為勵志書籍能教導人們讓自己更有力量,因此這些看似無害的書籍其實是瞞天過海地告訴緬甸民眾要掌控權力。我問一名緬甸作家:「這些勵志書籍是否暗示一股寧靜革命正在形成?」他隨即否認:「這種書在哪個國家不紅呢?」我這才發現,有時候人們也會犯了過度解讀的毛病。 我在仰光遇見了一位著名的短篇小說作家,他跟緬甸許多作家與新聞記者一樣,曾在監獄裡待過幾年。他是一名快五十歲、說話溫和的男子,當他說話時,會用手勢協助表達他的意思,就像默劇演員一樣。「我寫的故事是以我身邊看到的一切做為素材,」他說。他的故事記錄了一般平民的生活,通常集中在軍政府統治下民眾生活的貧困上(不僅是物質,也包括精神)。雖然他仍打算出版自己的作品,但他想寫的故事絕大多數仍必須(至少目前是如此)保留在自己的腦子裡。「我有許多、許多的故事,」他說。他在坐牢時,由於不許寫作,因此訓練出記憶故事的技巧。他跟我說了一則故事,一則關於想像力的故事。 他說,監獄裡有一名老人,他的工作是將典獄長房子周圍打掃乾淨。其他犯人都不許進到這個區域,老人每天要花上一整天的時間才能完成這份工作。作家覺得他很可憐,於是決定每天從自己分配到的米飯省下一點給他。米飯很粗劣──幾乎難以下嚥,但他沒有別的東西給他。當他將自己省下的米飯分給老人時,老人向他道謝,然後一下子就把米飯吃下肚,彷彿那是他吃過最好吃的食物。「這麼難吃的東西,你怎麼有辦法吃得這麼香甜?」作家問。老人回答說,他每天掃地的時候,都會聞到典獄長太太在廚房裡煮飯的香味。他吃飯的時候,只要回想一下他牢記在腦海裡的那股誘人的香味,譬如說豬肉咖哩燉馬鈴薯,那麼再難吃的飯也能變得異常可口。 「依我看,這是如此簡單而美好的故事,」作家最後說:「但我卻不能將它公諸於世。」 我在緬甸見到的作家,幾乎每一位都至少有一本書遭到審查部查禁。結果使得緬甸存在著一個未出版圖書的祕密檔案庫──在作家腦子裡不斷徘徊的故事,以及藏匿起來的完稿。有些作家寫下他們知道無法見容於軍政府的故事。我的一個朋友每天花幾個小時坐在破舊的電腦前面,記錄他透過祕密管道得知的每天發生的事件。「我必須這麼做,」他說:「這裡的官方新聞什麼也不報導,所以,如果我不把這些事情寫下來,明天這些事情就會遭到遺忘。」我也看到有歷史學家忙著編纂緬甸東部撣邦(Shan State)的現代史。他解釋,這是一部被政府軍事占領的撣邦史。「我知道這本書無法出版,但我必須寫下來。我必須留下記錄。至少它會留下來,也許有一天……」 一名緬甸作家跟我開玩笑說:「在緬甸,我們有想寫什麼就寫什麼的自由。我們只是沒有公開發表的自由。」 《一九八四》一開始,溫斯頓.史密斯進到他破舊的公寓裡。他蜷縮在狹窄的壁龕,如此就有幾英寸的空間處於遠端螢幕監視的範圍之外。他坐在一本記事本前,裡面是空白的鮮奶油色書頁,他的手裡握著一隻偷夾帶的筆。當他在日記第一頁寫下日期時,他想著自己要寫給誰看,因為在《一九八四》的世界裡,不管給誰看都是不安全的。他開始記錄前一天的事件,然後,在幾次中斷之後,他將筆浸回墨水池裡,並且在書上題詞:「獻給未來或獻給過去,獻給思想自由的時代,當人們彼此不同且不孤獨生活──獻給真實存在與已經記錄就不會再被塗銷的時代。」 我在緬甸旅行時,經常被問到有關歐威爾的一個問題,那就是他如何能為《一九八四》想像出這樣的場景。歐威爾自己從未受到這樣的壓迫;他如何能描述壓迫?這是個好問題。《一九八四》被世界公認為對極權統治下的生活做出了極為精確的描述。這本書描寫一個被無所不能的黨統治的無靈魂社會,這個黨透過無知(所有歷史都被塗銷而眼下的事件也被改寫)與恐懼(透過無所不在的遠端螢幕與人間蒸發的恐懼)來控制人民。 那麼,歐威爾是怎麼做到的?通常,我會提供制式而不太令人滿意的答覆。有些學者認為英國寄宿學校的寒冷宿舍與頻繁鞭打給了當時八歲的歐威爾《一九八四》的雛型。有些人則相信,歐威爾在一九三○年代志願參加西班牙內戰,而且在巴塞隆納(Barcelona)遭受俄國警察追捕的經驗,使他產生深刻的體會。我自己的想法是──我愈瞭解歐威爾在緬甸的生活,愈對這個想法深信不疑──他擔任帝國警察的經驗,是他有能力描寫壓迫的主要來源。 當我把這些想法說給我認識的一名緬甸詩人聽時,他的反應並不熱烈。他告訴我一位名字他已經忘記的英國詩人的故事。這名詩人曾因一首談及俄國的詩作而獲獎。在獲獎之後,卻傳出這名詩人從未到過俄國的消息,他因此遭受嚴厲的批評。「在我看來,這種批評實在錯得離譜,」我的朋友說:「這名詩人是用她的想像在寫作,而這才是真正的藝術:去想像你從未經歷過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