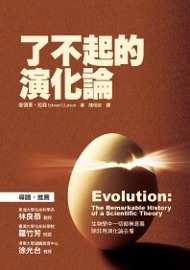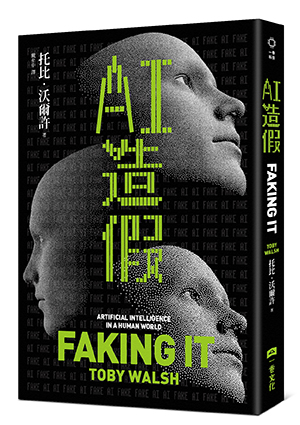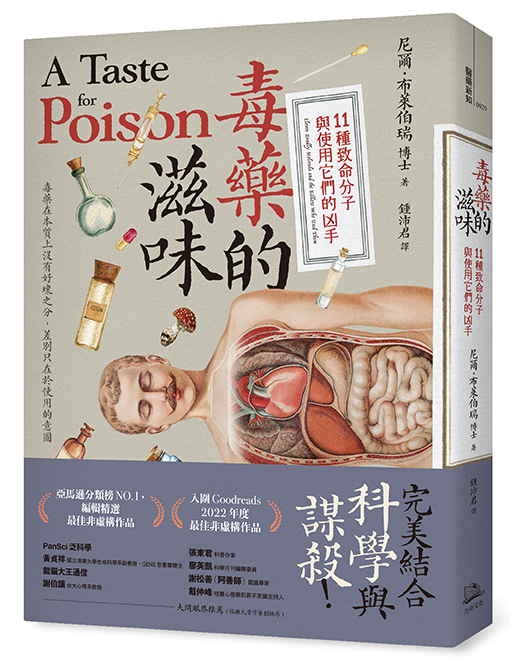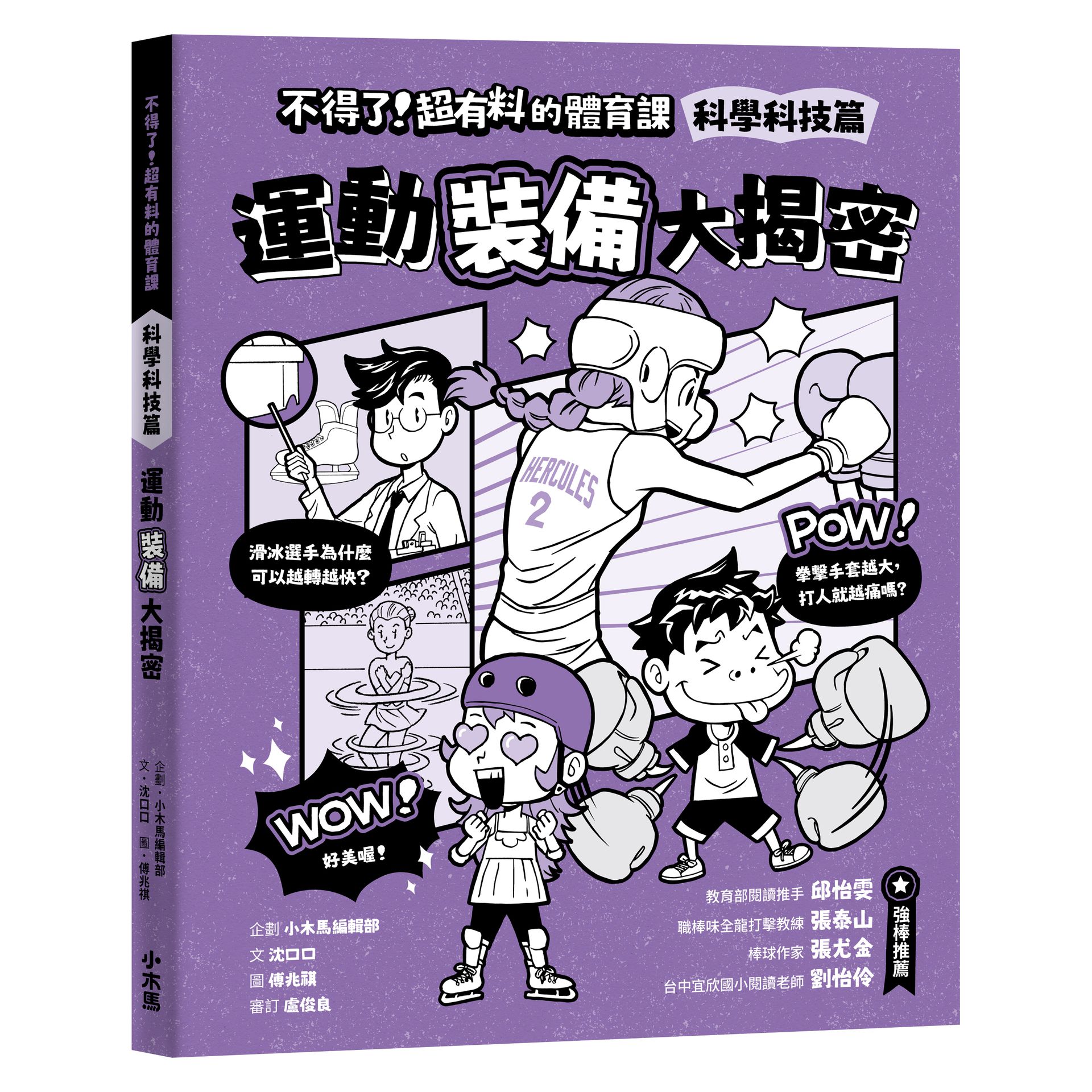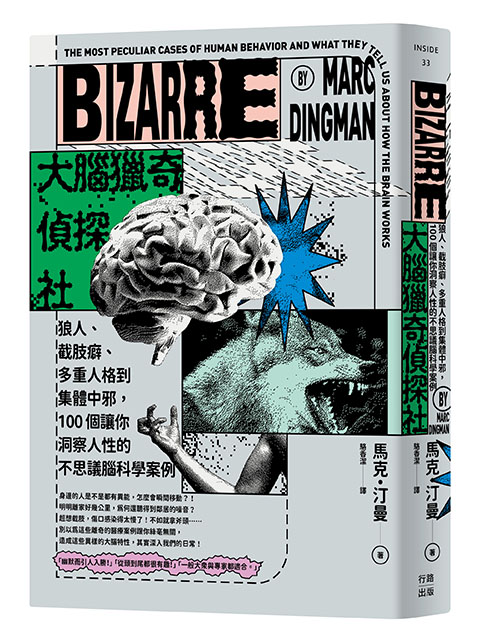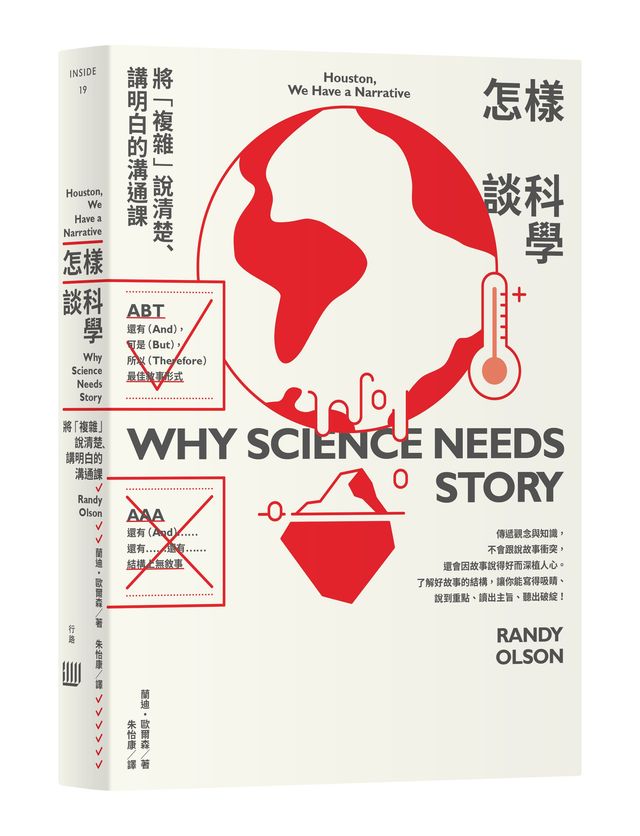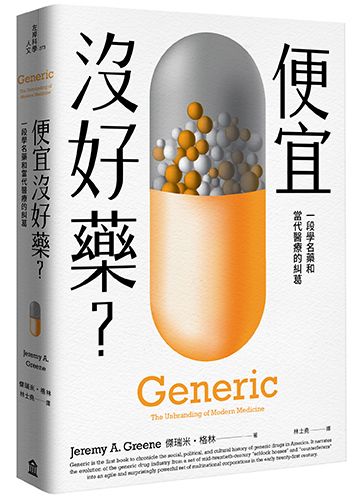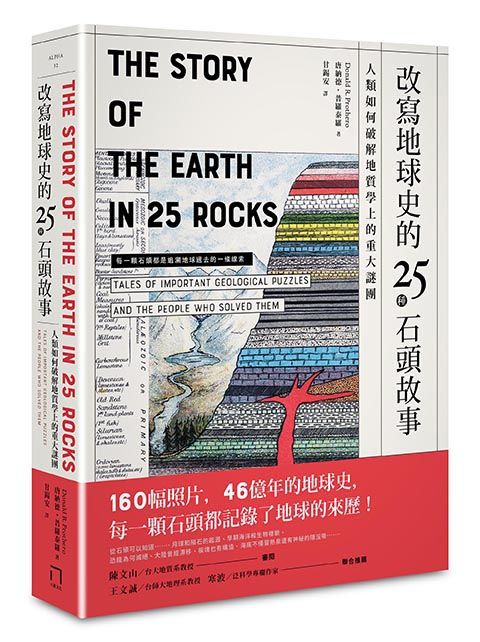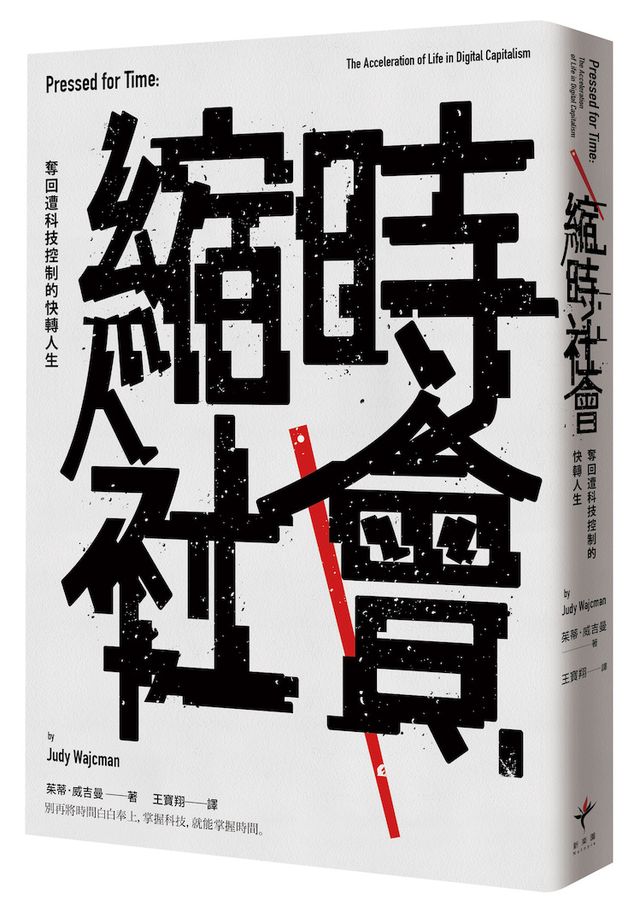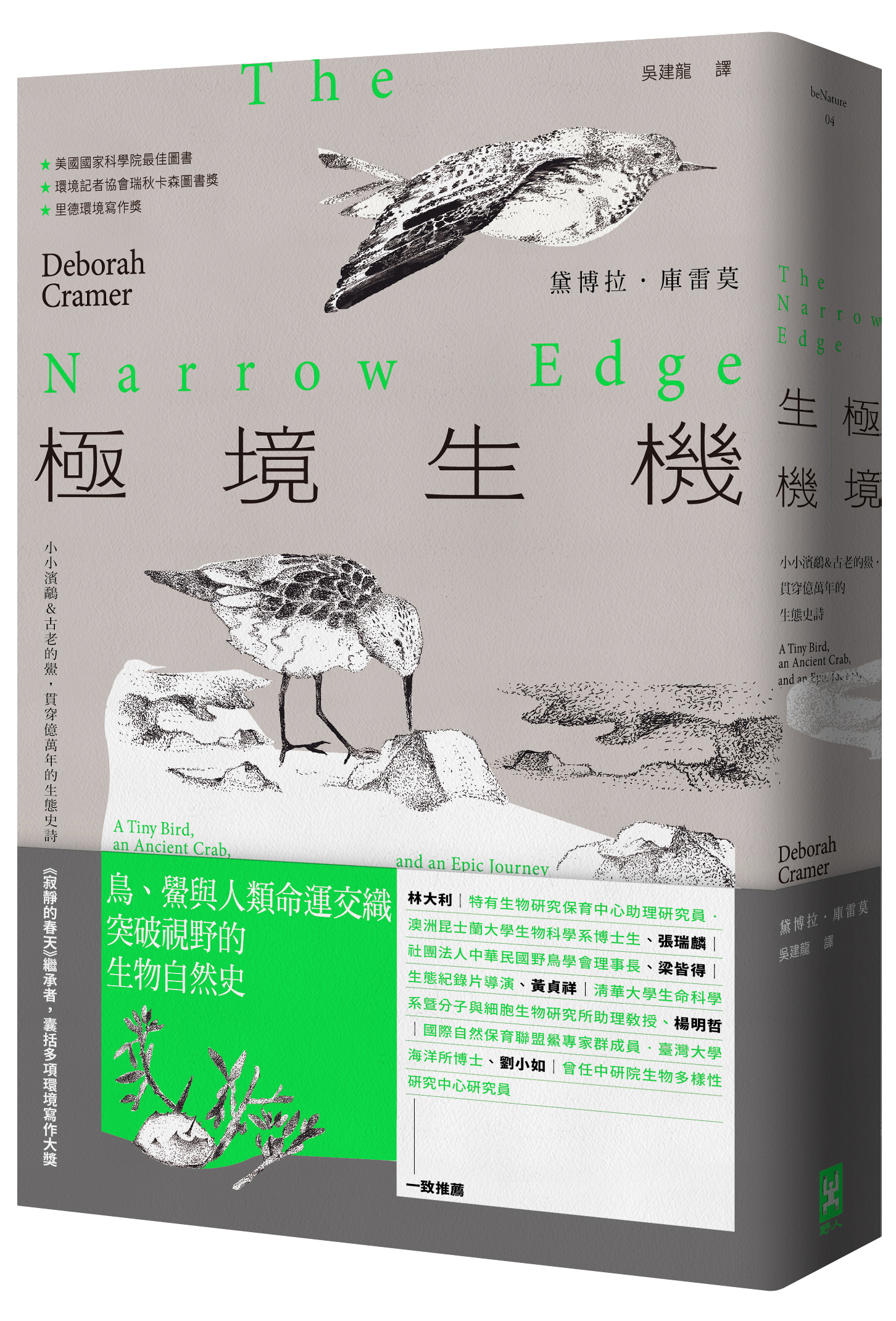★舊版原書名:雀鳥、果蠅與上帝
達爾文常回憶當年踏上小獵犬號時,「我幾乎可以確定這是一個將會令我後悔的旅程。」因為達爾文的演化理論,成了十九世紀最爭論的科學理論,到了二十世紀席捲世界,成為優生種族主義的理論根源。
這本書由普立茲獎得主愛德華.拉森執筆,探討「危險」的達爾文演化理論,如何從宗教信仰中,汲取養分,逐漸成形;「演化理論」重新衡量人類起源的問題,並破壞了人類與上帝的關係;十九世紀英國的資本主義如何與「適者生存」的達爾文演化論共舞,並加劇成對外殖民的合理化基礎;結合了文化史與科學史的視野。即便到了當代,美國基督徒對演化主義的激烈反彈,在著名的斯科普斯審判中達到頂點;今天,基督教基本教派仍在法庭爭取在公立學校中,除了演化理論外,也有教授「創造論」的權力。
那些在地層當中不連續的化石,到底代表什麼意義呢?是彼此之間有順序關係還是完全無關?這個順序關係是漸變還是突變?「人」也在這一系列的秩序中嗎?是有方向或沒有方向的演變?什麼力量促成了這樣的演變?如何傳遞一代接一代演化的特徵?
拉森,為我們導覽了達爾文的「危險觀念」(dangerous idea),從十九世紀早期關於演化這個觀念的理論、達爾文與華勒士輝煌的突破、華生與克里克令人驚訝的DNA雙螺旋發現,一直到今天新達爾文綜合的勝利,以及社會生物學的興起。整體而言,拉森將焦點置於相互合作或競爭的科學家、探險家以及其他科學界奇人的生活與事業上。這些人物包括居維葉、拉馬克、達爾文、華勒士、海克爾、高爾頓、赫胥黎、孟德爾、摩爾根、費雪、杜布然斯基、華生、克里克、漢米爾頓與威爾森等等。
這本書與現在市面上談演化學的書比較不同的地方在於,它比較系統地介紹了新綜合理論與之後的一些發展。過去的書好像都只談到達爾文的博物學傳統,很少把遺傳學、社會生物學、優生學等的互動介紹清楚。
愛德華.拉森
培普丹大學歷史教授與法律教授。在教學與寫作上均曾榮獲多種獎項,《眾神的審判》一書榮獲普立茲獎。文章散見於眾期刊,包括《自然》《大西洋月刊》《科學人》《華爾街日報》等。
陳恆安
成功大學歷史系系主任。
第三章 達爾文主義的興起 幾度因為英倫海峽狂風延宕,英國海軍所屬的小獵犬號終於在一八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從英格蘭的普利茅斯啟航,進行為期兩年的考察,計畫繪製南美洲南岸,或者南太平洋島嶼的地圖。對達爾文這位年輕的自然研究者來說,這是厄運的開始,因為它將變為五年的旅程,而且不但因此改變他的職業生涯,也將他捲入關於物種起源爭議的風暴之中。 啟航第一週的洶湧海浪,以及對在啟航前,假期裡整天酩酊大醉船員的嚴苛處罰,讓這位紳士自然研究者感到置身地獄。達爾文在他航海第一天的日記中寫著:「每天清晨都被時速八海浬的風吵醒,不久便感不適,而且持續整天……我腦海裡最不舒服的景象便是鞭打幾個因聖誕節過於放縱而犯罪的船員」。第二天,他繼續寫下:「這真是極度悲慘,遠遠超出一個未曾在船上渡過幾天的人所能想像的狀況」。具有貴族身分的船長費茲羅伊擔心,達爾文在第一次靠岸後便會放棄這次的冒險,而這樣的念頭也確曾閃過達爾文腦際。第三天,達爾文寫道:「在啟航前我常說,我不懷疑我會經常對整件事情感到後悔,也很少想過,我究竟憑著什麼樣的熱情這麼做」。「像今天一樣如此憂鬱悲觀的想法持續縈繞心頭揮之不去,我簡直無法想像會有比這更悲慘的事情」。 達爾文選擇探險並願意出航,反映了十九世紀英國的科學文化。政府贊助科學考察的航海計畫在那時是常見的事。十八世紀末期,庫克船長與溫哥華船長便已乘坐高桅橫帆船環航世界,隨船並率領一組科學家為英國進行繪製海岸圖、科學探勘以及收集自然史標本的工作。法國與其他歐洲強權國家也都派遣船隊,為自己國家進行類似的考察。甚至美國這個新國家,在一八三○年代末期也力圖準備進行考察。因為在當時還沒有正式的大學養成課程,因此許多十九世紀的優秀自然研究者,在獲得大學、自然史博物館或其他機構的終身職位之前,都只好咬牙投身海外探險。 小獵犬號的航行計畫最初並不是一個重要的科學考察,雖然後來它成為偉大的科學探險。事實上,原本航行的性質根本還不值得特別編制一位正式的自然研究者。小獵犬號是一艘船面甲板長九十英呎的三桅橫帆船,以大小來說,其實比較適合沿岸近海任務,而不適於遠洋航行。一八三○年,小獵犬號提早從測繪南美洲南端的任務返航,因為在航行途中總是獨自發號施令的憂鬱船長,在迷失於既荒涼又像迷宮般的火地島之後自殺身亡。英國南美海軍上將派遣英王查理二世未滿二十五歲的直系後代費茲羅伊,擔任指揮官,並將小獵犬號駛回英國。前指揮官自殺的兩年後,在費茲羅伊的帶領下,小獵犬號完成任務,也因此具有繼續進行環球考察的優先資格。然而,這位年輕指揮官擁有與先輩相同的氣質,因而害怕遭受相同的命運。費茲羅伊的舅舅,英國外相卡斯雷爾,就是開槍射穿喉嚨自殺的。為了小獵犬號的航行,費茲羅伊希望能有一位能與他交談的,地位相仿的人陪同出航。他獲得允許一位紳士自然研究者隨行。但一八六五年,費茲羅伊仍以同樣的手法結束生命。 雖然達爾文並不是費茲羅伊心目中最適合的人選,但是仍舊符合所有特殊的要求。一八○九年出生於英格蘭蕭布夏郊區一個富裕資本家家庭的達爾文,比費茲羅伊年輕五歲,剛從劍橋大學畢業。達爾文在劍橋時便已經發展出對自然史持久的興趣,他時常陪同年輕的植物學教授亨斯羅外出採集,也曾參與塞奇維克率領的地質學野外探勘。達爾文在畢業後並沒有詳細的生涯規劃,因此對一個像在小獵犬號上工作的環球科學航行計畫很感興趣。達爾文的父親最初反對,因為他認為這趟航行只不過又是這個不願面對就業的任性孩子的另一項昂貴興趣。不過,就像以往一般,父親很快地便又狠不下心,終於承諾支付兒子所需的,後來甚至包括一位助手科文頓的全部花費。 達爾文在寫給介紹這個工作給他的亨斯羅的信中說:「榮耀歸於主!是我所能想到的最合適的開始」。「我做的事到底有什麼差別:之前在蕭布夏沉迷於追獵狐狸,現在則在南美洲捕捉駱馬。人的命運似乎真的在冥冥中自有定數」。南太平洋的經歷特別讓他感到刺激。四天之後,達爾文在寫給大學時代密友的信中說:「訂購物品是如此有趣」,「今天我訂購了一把來福槍與兩組手槍。因為我們可能會與那些……食人族戰鬥。能射殺食人族島嶼的首領是有些影響的」。延遲啟航以及第一星期的暈船使達爾文熱情稍減,但是當小獵犬號接近計畫中的首次登陸地點,西班牙西南方的加那利群島時,達爾文便恢復他固有的那種幹勁。 他寫道:「我們看到太陽從加那利最大島嶼那崎嶇的輪廓後面升起,突然照亮特內理費島的頂峰」。「這真是令人難忘的,愉快的一天」。 不過因為霍亂檢疫,使得小獵犬號登陸加那利群島的計畫生變,他們只好繼續往南航行至地處熱帶的佛得角群島。這個航行途中在火山群島的短暫停留,促使達爾文改變對地質學的看法。在啟航時,達爾文是一個傳統的英國災難論者,仍舊受塞奇維克影響。事實上,塞奇維克曾為達爾文的航行提供了閱讀書單,明顯忽略掉賴爾那本具有爭議性的《地質學原理》。不過費茲羅伊倒是給了達爾文一本,而年輕的自然研究者也利用停靠在佛得角群島中最大島嶼聖牙哥的時候閱讀。達爾文在那裡所見的,讓他立即轉向並一輩子支持賴爾的均變論。 達爾文在《研究誌》中紀錄:「一進港,便看到海邊峭壁上一道平行白色帶狀紋路,沿著海岸線可能有好幾英哩長,距離水平面大約四十五英呎」。經過進一步研究,他發現在兩層深色火山岩石中,是一層由高溫殺死的珊瑚與貝殼所形成的淡色岩石。達爾文推測,形成白色帶的海中生物,過去一定生活在火山岩淺灘,後來被熔岩所覆蓋。之後,這些地層作為一個整體緩慢上升,一直到今天所見的高度,也因為緩慢上升,所以地層的組成型態並沒有改變。所有這些過程肯定歷經非常長久的時間,因為島嶼火山的火山口都已經因為氣候的侵蝕而無法辨識,不過發生的時間點也不能太久遠,因為白色帶中的貝殼,與海灘所發現的貝殼屬於同一類型。待在聖牙哥島的頭幾天裡,二十二歲的自然研究者以賴爾的地質活動論,而不是居維葉的災難論,滿意地詮釋了佛得角群島的地質歷史。達爾文下了一個結論,認為目前所知的地質力量只要擁有足夠的時間便能形成這些島嶼,但是過去的災難事件將會打亂地層的次序。 對達爾文來說,解讀島嶼地質學現象是令他印象深刻且影響深遠的經驗。在離開聖牙哥島的時候達爾文深受「打擊」,因為島上充滿陌生的火山地形、熱帶植物。他在日記中寫道:「這對我來說真是燦爛的一天,就好像給了盲人一對眼睛」。大約半世紀之後回想起這件事,達爾文形容聖牙哥島的海岸「清楚地向他展示出,相較於其他人,賴爾處理地質學的方法具有完美的優越性」。突然之間,達爾文對考察航行的科學重要性,以及自己作為科學家這件事,都有了更寬廣的想法。他說:「我開始了解,或許可以來寫一本書描述走訪過的這些不同國家的地質學。想到這裡我就高興地顫抖起來」。「對我來說,這真是個值得紀念的時刻,我是多麼清晰地回想起我在熔岩所造成的低崖壁下休息,陽光暖照,附近生長一些奇特的沙漠植物,腳邊那因潮汐造成的小水塘中有活生生的珊瑚」。從那時候起,一位剛畢業的旅遊者搖身變成一位自信的科學家。 接下去的一些觀察,再度確認了達爾文對地質學現實論新產生出來的信心。從將珊瑚礁視為逐漸沉澱的產物,到見證火山活動影響加拉巴哥群島,達爾文看到身邊一些例子都是自然力持續影響的證據。當然,災難論者也能藉著超出現代地質活動規模的遠古事件來說明這些現象。但是,這些解釋不再能滿足達爾文,特別是在他經歷了智利的大地震之後。一八三五年二月二十日的日記中記錄著:「這個震動使我頭暈眼花」,「世界整體來說是堅固的,卻在我們腳下如浮在流體上的硬殼般運動」。對達爾文來說,地震證明了現代地質力量具有造山的能力。兩週之後,達爾文將其他地區的新觀察記錄在《研究誌》時提到,「費茲羅伊船長發現了比高水位記錄還高十英呎的地層,上面黏附著腐敗的貝殼」。而且還不忘特別強調出「黏附在岩石」這件事。「從以下觀點來看,這個區域海拔的上升特別有趣。它是幾次巨大地震的現場,也是眾多海洋貝類登上陸地上最少六○○英呎,但我認為有一千英呎高的地層的地方」。在經歷了智利大地震後不久,達爾文寫信向一位朋友敘述這樣一個地震,他說:「對地球作為一個主題來說,地震必定是個重大的現象」。 第五章 演化主義的興起 一八七○年代的達爾文是國際名人。即使不相信自己演化自猿類,人們也會談論這個議題,或者談論達爾文。而對那些相信的許多人來說,達爾文的地位有如現世的先知或崇高的神職者。無論是否因為長期的病痛而隱居在堂村的家中,達爾文有如隱居賢者般接待幸運的訪客。他的妻子艾瑪在給兒子李奧納德的家信中抱怨,「這星期我們為了德國人忙透了」,「星期二海克爾來訪,他非常親切熱情也十分健談,不過他以那糟透的英語大聲說話的聲音實在是震耳欲聾。不過與昨天比起來那又算不得什麼。昨天科恩教授(全然聾了)與他的妻子(相當迷人)和一位R教授來訪並共進午餐,像他們那樣所弄出來的噪音是我從未聽過的」。另外幾天也有些訪客,我們接待了部分也婉拒了一些。所有的陌生人,未受邀或未知會來訪的,通通擠在大門,僕人還得一一請他們離開。看了這個景象,赫胥黎寄給達爾文一張素描,上面畫著屈膝跪拜的祈禱者,向教宗達爾文的聖地表達敬意。從赫胥黎與達爾文那打從心底對天主教的輕視來看,他們對這個諷刺肯定感到滿意。 年輕的美國哲學家費斯克在一八七三年末成為達爾文午餐宴會的客人之一,並一輩子成為達爾文的使徒。費斯克寫給待在美國的妻子的信中說:「達爾文是所有這些前輩科學家中最紳士的一位」。「他的白色長髮與白色的濃密鬍鬚讓他就像畫中人物一般。此外還有什麼事情會比看到一位無私獻身於偉大思想的紳士所表現出來的無瑕的率直、誠實與簡樸態度還要快樂?」然後費斯克又補充了一段具有代表性的評論,「我很擔心再也無法看到他,因為他的健康狀況很差,今天為了見我,我想他肯定花了精神準備。來訪英國的所有日子裡,我最珍視的就是今天了」。雖然,在擔心自己是最位一位訪客的費斯克之後,達爾文又活了十年,也又接見了無數的來賓。而且達爾文在一八七○年代,還寫下了數量驚人的私人信件,如傳記作者布朗恩所估計,一年大約有一千五百多封信。大部分的信件都是針對陌生人問題的回應,這些來信大致上都是詢問演化的問題、提供新奇的科學訊息、質問他的宗教信仰或者只是單純請求簽名。為了應付大量的來信,達爾文訂購了空白卡片以及簽名章。不過明顯地,對於大部分通信,他還是親筆完成。 在大眾的眼裡,達爾文成為有機演化觀點的化身。即使不接受天擇理論的演化學者,也都承認達爾文為他們的導師。例如費斯克,他其實是一位斯賓塞思想的追隨者,和斯賓塞一樣傾向支持拉馬克式的有機演化觀點,不過他仍然稱自己是個達爾文主義者。在艾瑪寫給李奧那德信中所提到的那位到唐村造訪的海克爾,同樣也具有拉馬克思想的色彩,不過他也把自己的研究形容為具有達爾文思想特色的科學。事實上在一八七○年代,「達爾文主義」這個字,既可以用來表示具有修改的世代相傳現象的普遍理論,也可以用來專指天擇的演化理論,雖然這兩個觀點所處理的內容差異很大。達爾文雖然在《物種起源》中支持這兩個觀點,但是卻從來沒有將兩者合併處理。一八六三年在寫給格雷的信中,達爾文強調說:「以個人來說,我其實比較關注天擇。但是我總覺得與創造或修改的問題比較起來,這似乎變得完全不重要」。 一八六○到一八七○年代這段時間,科學家越來越質疑天擇理論是否能充分解釋演化的現象。這時達爾文修訂了《物種起源》,賦予拉馬克後天性狀供給演化材料這個觀點更為重要的角色。在這點上,達爾文本身的態度反而沒那麼教條。那些抱持信念認為作用在天生變異的天擇便能夠維持演化過程的生物學家則變成著名的「新達爾文主義者」。一八八三年達爾文過世之後的幾十年,天擇理論持續失去支持,因此到了世紀之交,才會有生物學史中所謂的達爾文思想的虧蝕或讓位。話雖這麼說,但是演化理論從未蹣跚不前,反而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為了避免這段歷史造成混淆,在書中「達爾文主義」與「新達爾文主義」這兩個名詞,將專指關於演化的特殊理論,也就是天擇作用於微小隨機天生變異的演化過程。而「演化」或「演化主義」則泛指能將修飾過的世代相傳的普遍觀念。 創造論在科學中的衰退 特別創造論的教條長期主導了西方生物學思想,誰也沒預料到它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便失去上帝的恩寵。例如在美國,一八五九年《物種起源》出版之前,實際上沒有自然研究者公開為有機演化觀點背書,但是在十二年後,著名的美國古生物學家柯普推斷,地層之間具有發展的「假設是基於確定的事實」。普林斯頓大學地質學者,也是地理學者的居約,或許是美國最後一位公開反對演化主義的自然研究者。他也是最後一位仍活躍於研究工作,且具有相當崇高學術聲望的反對者。但是即使如此,也在一八八四年他過世的那年,承認除了人類之外的所有生物可能來自於共同祖先。 在英國的結果也差不多。在那裡,達爾文、赫胥黎以及他們的盟友共同接管建立科學形象的工作,他們的目的是將自然主義推舉為科學的意識形態,以及把科學推舉為現代社會的主要動因。首先,他們有意識地設法減少對達爾文主義的公開辯論,同時系統地鼓勵以提昇生物學家採用演化路數研究的興趣。透過一個志趣相投知識分子所組成的秘密團體「X俱樂部」,赫胥黎和他的朋友順利取得許多英國一流科學學會的領導權,同時安排支持者取得著名大學或博物館的職務,並影響科學期刊的編輯方針。一八六九年,他們創立了《自然》期刊,作為科學自然主義的代言,並毫不顧忌地在期刊上提倡達爾文主義。 一八七○年代,轉變在英國已經取代了特別創造論,成為多數人接受的關於物種起源問題的科學解釋。不過培里從自然中看出設計的傳統,深深盤據著英國科學的根基,因此並不會立刻消失。不過,他們的支持者要不是被邊緣化,就是被迫接受經過神學修飾的演化理論。赫胥黎不放過任何機會,不斷以計謀使歐文在論戰中挫敗,很快地他便讓這位英國解剖學元老雖然在公開場合仍享有榮耀,但是在科學上卻被孤立起來。到了科學事業的最後階段,歐文擁護的是一個定義不清的「導出」理論。這個理論假設物種突變成新物種,是衍生自事先決定的路徑或者是符合一種事先設計的原型。關於「X俱樂部」的策動,歷史學家鮑勒評論說:「極成功地取代了英國科學社群」,以至於「在一八八○年代,僅剩的反對者抱怨達爾文主義已經變成一種被盲目接受的教條,被小心地保護以防任何嚴肅的挑戰」。 在這段時期,達爾文主義也傳遍大英帝國。在英國文化的優勢區域,達爾文主義都在新建立的科學機構中紮下了根基,特別是在澳洲、紐西蘭以及加拿大等地。然而在英語世界之外,它的傳播速度便慢了許多,對羅馬天主教勢力範圍下的南歐與拉丁美洲更是沒造成什麼影響。居維葉的傳奇讓演化論在法國陷入絕境達一個世代,當它真正進入法國科學時,明顯地是帶著拉馬克思想的特色。 《物種起源》出版之後接下去幾年,演化論的主戰場便轉至德國。這個國家,雖然在當時才從眾多獨立的小國統一起來,但是便已經成為優秀的研究中心,研究領域包含了形態學(或植物或動物結構)、生理學(或機體功能)、細胞理論以及實驗室生物學的種種問題。從一八六○年代開始,形態學者海克爾,他是一位政治激進者與科學唯物論者,在那裡以他自己的偽達爾文演化理論作為撞牆槌,向主導德國生物學的形上唯心論的堡壘進攻。這個具有豐富創造力的國家傳統,提出了包含停滯以及預先存在自然中原型的想法,不過與海克爾心目中經由自我驅動發展的自然過程相互牴觸。當越來越多的學生追隨海克爾的時候,他嘗試根據演化系譜而不是原型來了解生物。海克爾將演化的進行視為達爾文式的天擇,選擇了適應力較高的拉馬克式的後天性狀,而與他同時代的魏斯曼則提倡一個比較純粹的達爾文主義,一個完全依賴存在於個體之內的可遺傳「種質」產生遺傳變異的天擇過程。由於海克爾、魏斯曼以及他們的支持者,達爾文主義(出生於英國,養成於美國)在德國也找到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