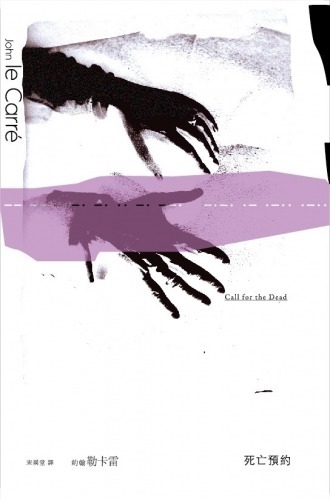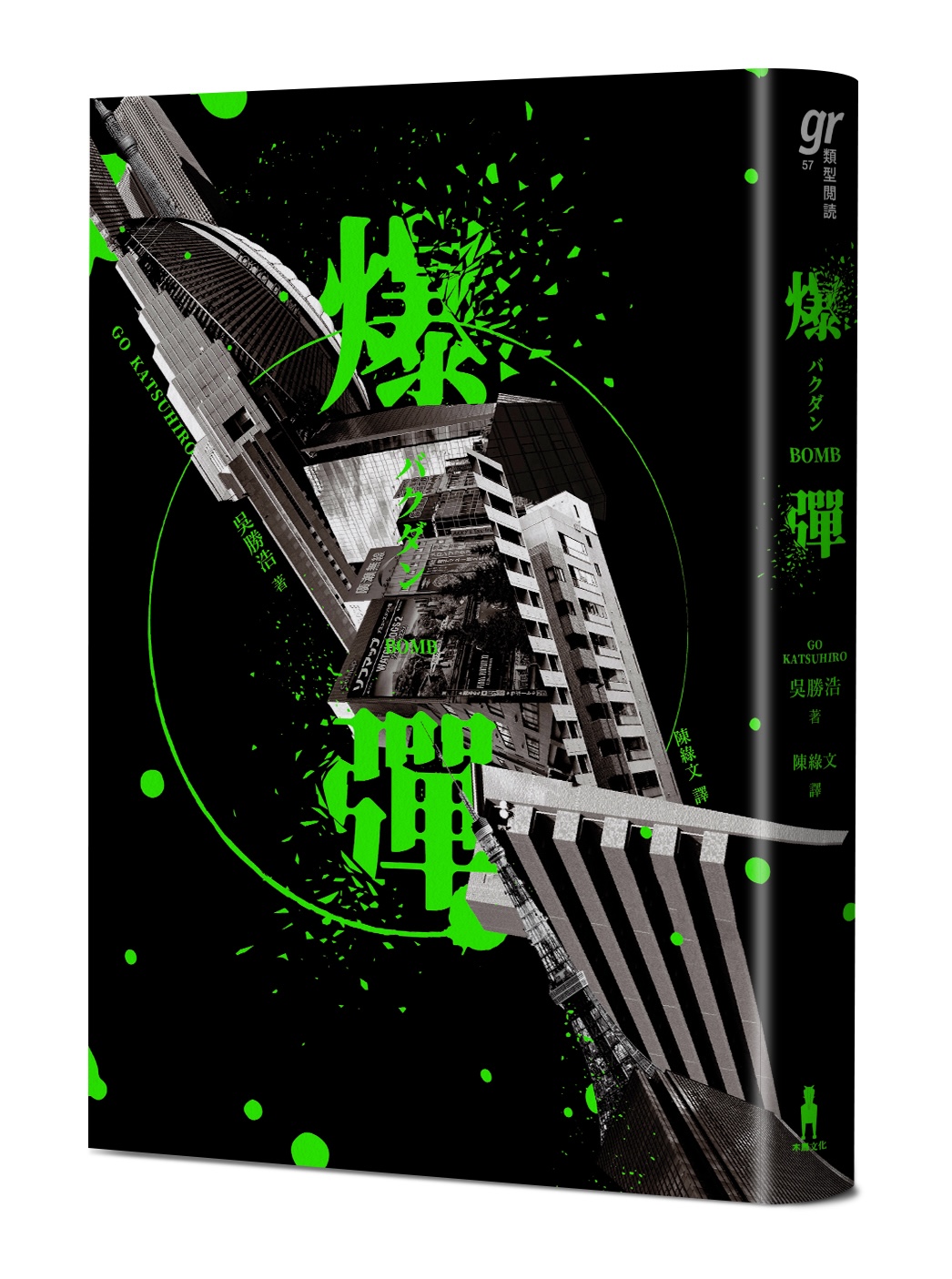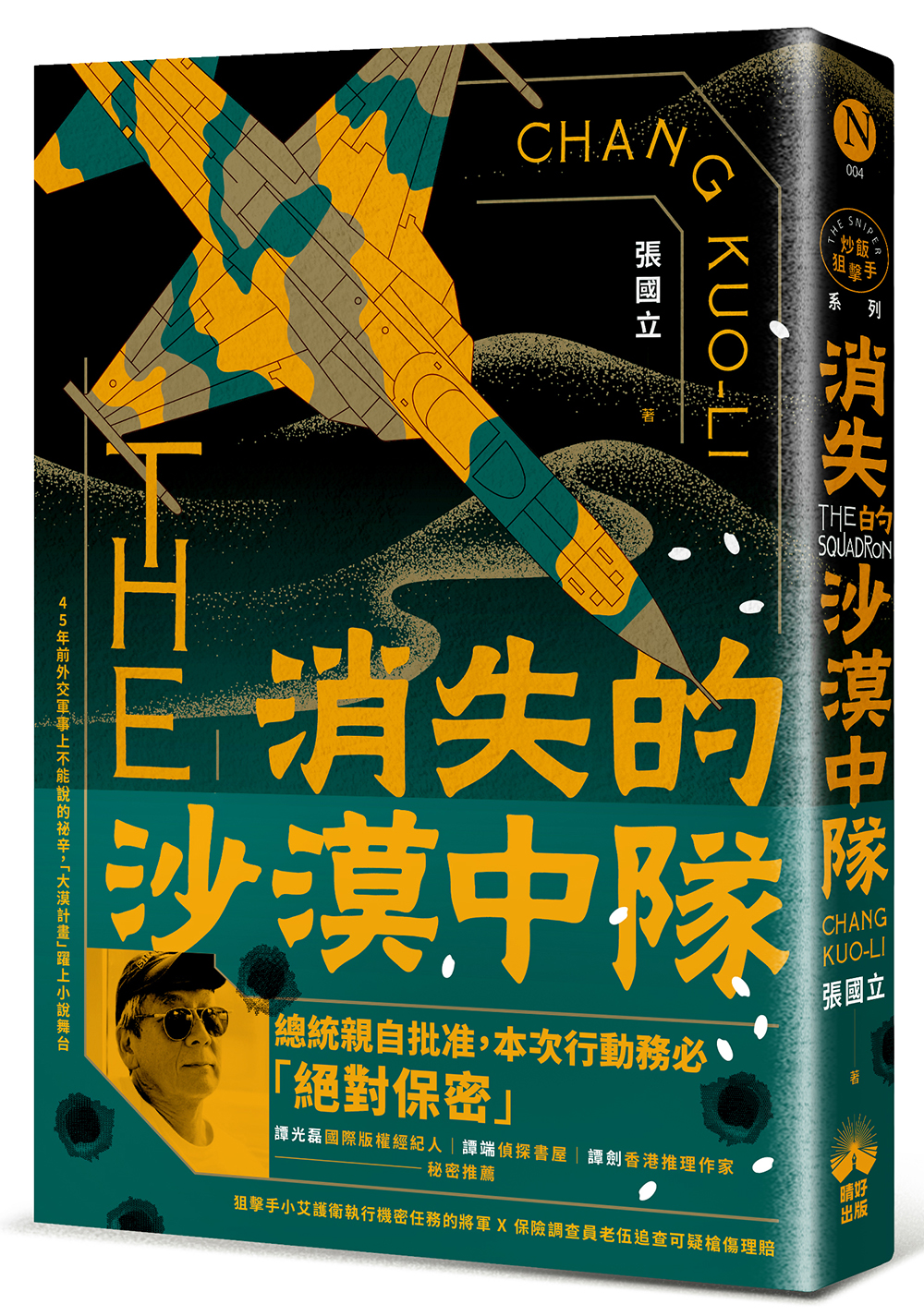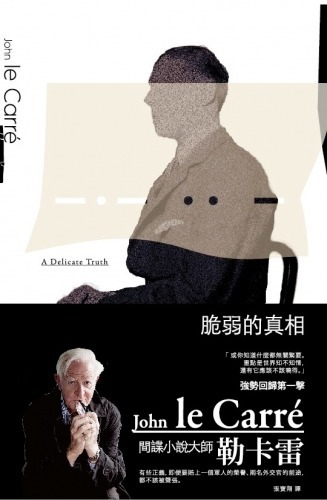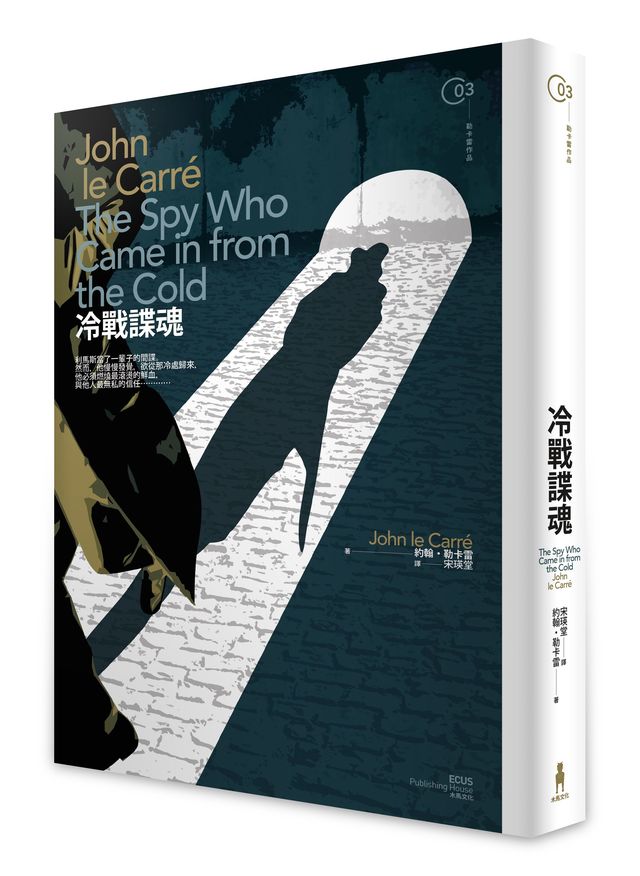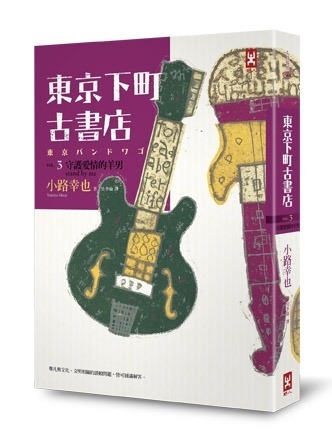史上唯一獲頒英國犯罪推理作家協會(CWA)「金匕首獎中之獎」的大師!
毫無疑問,這個類型的小說沒有人會比勒卡雷寫得更好,即使是已故的格雷安葛林也比不上 ----- Library Journal
勒卡雷絕對是全球小說圈的最佳間諜頭目 ----- News Weekly
高明……寫實。懸疑不斷,筆法傑出 ----- The Observer
高明、驚悚,令多數間諜文學相形之下索然無味 ----- Sunday Telegraph
詹宏志、唐諾、羅智成、韓良露、楊照、傅月庵、劉森堯、南方朔、李家同 推薦
執行這項工作時,他感到五味雜陳,難以調適。
他必須從他所學、在超然的位子上評估一個人的「情報員潛能」。
他的這一部分無情而殘酷——在他的生意裡,史邁利扮演的角色是國際傭兵,
不講道德,無關動機,只求滿足私慾。
甫出場,勒卡雷筆下這個全球知名的人物,史邁利,就已經步入中年了。他看起來不像○○七或傑森‧包恩,他只鍾情於美麗的妻子安,唯一的興趣是研究冷僻的十七世紀德國詩作。但在大戰期間的地下工作、為組織挑選合適的間諜,加上他自身極佳的智力,有些任務——比方內部調查——唯有喬治‧史邁利足以勝任。
原本只是一個簡單的約談工作,約談後的結論也並無可議之處,史邁利的約談對象亞瑟‧芬南卻在隔周自戕身亡,並留下激烈的指控信。拜訪芬南遺孀的那天,史邁利接到被害人前一天預約的晨呼電話;決心自殺的人,為何要預約隔日的電話通知?這樁自戕案果真如表面上單純,只是為求清白的激烈手段?
史邁利不這麼想。
(本書於2007年曾以書名《召喚死者》於木馬文化出版。)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
原名大衛‧康威爾(David Cornwell),1/931年生於英國。18歲便被英國軍方情報單位招募,擔任對東柏林的間諜工作;退役後在牛津大學攻讀現代語言,之後於伊頓公學教授法文與德文。1959年進入英國外交部工作,先後於英國駐波昂及漢堡的大使館服務,同時開始寫作。1963年以第三本著作《冷戰諜魂》(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一舉成名,知名小說家葛林如此盛讚︰「這是我讀過最好的間諜小說!」從此奠定文壇大師地位。
勒卡雷一生得獎無數,包括1965年美國推理作家協會的愛倫坡大獎,1964年的英國毛姆獎、James Tait Black紀念獎,1988年甚至獲頒CWA終身成就獎(另外分別在1963年與1977年獲頒金匕首獎),以及義大利Malaparte Prize等等。2005年C.W.A更將象徵最高榮譽的「金匕首獎中之獎」頒給約翰‧勒卡雷。至今已出版19部作品,不僅受到全球各大媒體矚目與讀者歡迎,更因為充滿戲劇元素與張力,已有11部被改編為電影與電視劇。
勒卡雷以自身真實的經驗,加上獨一無二的寫作天賦,細膩又深刻地描寫漫長間諜生涯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兩難的道德處境、曖昧的善惡定義,內容富含哲理,情節引人入勝,閱卷愈罷不能,不愧為享譽全球的大師級作家!
宋瑛堂
台大外文系學士,台大新聞所碩士,曾任China Post記者、副採訪主任、Student Post主編等職。譯作包括《蘭花賊》、《本壘的方向》、《非關男孩》、《發現eBay》等書。
第一章
簡述史邁利
當社交名媛安‧瑟孔姆在大戰近尾聲時下嫁喬治‧史邁利,她對她震驚的上流友人形容他「極其尋常」。兩年後她為了一個古巴賽車手離開他,她神祕地宣稱,倘若她當時不離開史邁利,將再也不可能那麼做;索立子爵則專程去了他的俱樂部一趟,確定消息走漏。
在短短的一季裡,這句有如警語般的聲明,卻唯有那些認識史邁利的人才能理解。粗短、肥胖,性情恬靜,顯然會花大錢在極差勁的服裝上,它們披在他矮胖的軀幹,彷彿縮水蟾蜍身上的皮膚。事實是,索立曾在婚禮上表示「瑟孔姆嫁給了一隻灌滿西南風的牛蛙。」而史邁利沒聽見這番批評,他正啪答啪答地步上教堂走道,尋覓能將他變成王子的一吻。
他是貧是富、是莊稼漢或是神職人員?她是從哪裡認識他的?新娘無庸置疑的美貌只是更強調了這一對的不協調,而男人與他新娘的落差則引起神祕的聯想。只是,八卦中的角色必須簡單而絕對、必須裝備他們以罪過及動機,方便在言談間交換傳遞訊息。於是,史邁利成了沒受過教育、無父無母、非軍非商、不貧不富,在社交特快車中的警衛車廂裡,身上沒有標籤、轉眼間淪為遺失的行李,注定在離婚消息來了又走了之後,待在昨日舊聞、生灰塵的架子上,依舊無人認領。
當名媛安追隨她的星辰前往古巴時,她想到過史邁利。她不太情願地對自己承認,如果此生她只能有一個男人,這人非史邁利莫屬。而她滿足地想起,自己已經透過神聖的婚姻證明了這件事。
名媛安訴請離婚對她的前夫有何影響,社交圈並不感興趣——他們本來就不關心轟動事件的後續發展。然而,知道索立那幫人如何設想史邁利的反應,也不失趣味;圓滾滾、戴著眼鏡的臉在認真專心研讀冷門德國詩人之際皺了起來,肉乎乎的汗濕雙手在鬆垮的衣袖中緊握成拳。但索立僅微微聳肩以法文表示「只是離開小個子罷了」(partir c’est courir un peu),顯然沒注意到,名媛安儘管只是離開,喬治•史邁利這人確實有一小塊隨之死去。
史邁利身上倖存的那個部分,與他的外型格格不入,一如他的愛情,或偏好藉藉無名的詩人,那就是他的職業:情報官。他喜歡這份工作,因為它讓他有幸與品格、來歷同等晦澀的人共事。這份工作也提供他過去人生的最愛:透過有條理地、實地運用他自個兒的演繹能力,就人類行為的奧祕進行科學研究。
二○年代期間,史邁利自不甚起眼的學校畢業,接著懵懵懂懂地進入他那同樣不甚起眼、陰暗而封閉的牛津學院,曾夢想著成為研究員、畢生致力於研讀十七世紀德國晦澀的文學。然而指導教授更瞭解史邁利,以睿智的手腕讓他偏離他無疑將獲得的榮耀。一九二八年七月一個清新的上午,疑惑又年輕紅潤的史邁利坐在一張桌前,接受海外學術研究委員會面談,而他居然沒聽過這個單位。傑布帝(他的指導教授)莫名含糊地帶過這個引介:「史邁利,跟這些人談談,他們或許會用你,薪水低到保證你有一群正經的同事。」但史邁利被惹惱了,也照實說了。讓他擔心的是,傑布帝說話一向明白清楚,此時卻閃爍其詞。輕微惱怒的他同意暫緩回覆牛津大學的萬靈學苑(All Souls),先等見過傑布帝的「神祕人物」再說。
他沒有被介紹給委員會,但他光用看的就認出其中半數成員,包括劍橋的法國中世紀學者菲爾丁、東方語言所的史帕克,以及某晚傑布帝邀史邁利在高桌(High Table)餐廳用餐時,也出現在那兒的司第—艾斯培。他得承認自己對此印象深刻。至少讓菲爾丁離開研究室,而且離開劍橋,本身就是一種奇蹟。事後,史邁利總把那次面試想成一種扇子舞;一系列計算過的開誠布公,每個人各自揭開一個神祕實體的不同部分。最後,司第—艾斯培——他似乎是委員會主席——掀開最後一層面紗,呈現在他眼前的真相赤裸得令他目眩。這個——由於想不出更合適的名稱,司第—艾斯培難為情地形容它為特務局——機構,將提供他一份職位。
史邁利要求給他時間考慮。他們給他一個星期的時間。沒人提到待遇。
那晚他住在倫敦一間相當高級的旅館,請自己看了一齣戲。他感到反常地頭重腳輕,令他煩惱不已。他很清楚自己會接下這份工作,他在面試時大可就答應。這麼做純粹出於本能的警覺,也阻止了他想玩弄菲爾丁那情有可原的念頭。
他同意之後開始受訓:沒有名字的鄉間住宅、沒有名字的指導員,大量的旅行,以及愈來愈明朗化的、完全獨立作業的美好前景。
他的第一個指派任務相對輕鬆:到德國的地方大學擔任英語講師兩年,講授濟慈的作品、與一群熱心而認真的各種各樣德國學生至巴伐利亞的狩獵小屋度假。每次長假尾聲,他會帶其中一些認定有潛力的學生回英國,並透過祕密管道將他的建議傳送至波昂的一個地址。在那兩年間,他不知道自己的建議是被採納了或置之不理。他也無從得知是否有人去接近他所提名的人選。確實,他沒辦法知道自己的訊息是否寄達他們手上;在英國時,他也與軍情科沒有往來。
執行這項工作時,他感到五味雜陳,難以調適。他必須從他的所學、在超然的位子上評估一個人的「情報員潛能」,得就人格及行為設計精妙的測驗,以提供他該人選的品質參考。他的這一部分無情而殘酷——在他的生意裡,史邁利扮演的角色是國際傭兵,不講道德、無關動機,只求滿足私慾。
相反地,目睹他內在原有的樂趣逐漸凋萎則令他悲傷。總是置身事外,如今他發現自己會在友誼與人性忠誠的誘惑前退縮;他警醒地避免自己做出自然反應。由著他的智識之力,他強迫自己以客觀的學術角度觀察人類,然而他既非神明也非聖賢,對自己人生中的虛假感到既痛恨又畏懼。
但史邁利本來就是感性的人,長時間離鄉背井更增強了他對英國的深愛。他以牛津的往事餵養飢渴的心靈;它的美、它理性的安逸,以及它在下判斷時的成熟穩重。他夢到秋天哈特蘭碼頭(Hartland Quay)多風的假期,夢到在康瓦爾郡懸崖上跼跼長行、風吹得他的臉又平又燙。這是他的另一個祕密生活,而他則愈來愈痛恨新德國齷齪的侵略舉動、制服學生的叫囂跺腳、帶疤的傲慢臉孔與他們廉價的回應。他也憎惡校方竄改他課程——他心愛的德國文學——的那種手段。有那麼一個晚上,在一九三七年的冬天的某個可怕夜晚,史邁利站在窗前,望著大學中庭升起營火:數百名學生圍繞著它,臉龐在跳躍的火光中亢奮閃爍。他們把好幾百本的書丟進這異端的火焰中。他知道都是哪些書:托馬斯‧曼、海涅、萊辛與其他多名文人。而史邁利,他汗濕的手捏著菸屁股,旁觀著,痛恨著,並勝利地想他已認清他的敵人。
一九三九年他在瑞典,是個瑞士知名小型軍火商的代理,與該公司的關聯自是即刻生效。自然,他的外型也出現某些改變,因為史邁利發現自己在這方面的天賦,不僅止於基本的改變髮型與蓄道小鬍子。四年期間,他盡責扮演角色,往返於瑞士、德國、瑞典三國。他從未料想到,一個人可以擔憂受怕這麼久。直到十五年後,他一緊張仍會刺激左眼的神經;壓力在他圓滾滾的臉與額頭上鑿出線條。他知道什麼叫永遠無法安枕、永遠無法放鬆、不分晝夜無時無刻心悸不休的感受;瞭解孤單與自憐的極限,來由地突然渴求女人、酒精、運動、任何藥物,只求帶走他生活的壓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執行他值得信賴的軍火商生意以及他的間諜工作。情報網隨著時間擴展開來,其他國家也修正了他們缺乏遠見、缺乏準備的毛病。一九四三年,他被召回。六個星期不到,他開始渴望回去,但他們不肯放他走。
「你的任務結束了,」司第—艾斯培說:「訓練幾個新人,休個假。去結婚之類的。放鬆一下。」
史邁利向司第—艾斯培的祕書安‧瑟孔姆求婚。
大戰結束。他們資遣他後,他帶著美麗的妻子回到牛津,繼續投入冷門的十七世紀德國文人。然而兩年後,安去了古巴,渥太華一名年輕俄羅斯密碼員的供詞使具備史邁利這樣經歷的人頓時炙手可熱。
這工作很新鮮,威脅難以捉摸,起初他做來得心應手。可惜更年輕的人陸續進來,想法也許比較新穎。史邁利不是升遷的料,而這時他才緩緩悟出,進入中年的他從未年輕過,因此他——最好的可能做法就是——被晾在架上。
滄海桑田。司第—艾斯培走了,從北美投奔印度,尋找另一個文明世界。傑布帝死了。一九四一年,傑布帝在里爾(Lille)與他年輕的比利時無線電操作員搭上一班火車,兩人從此音訊全無。菲爾丁埋首撰寫羅蘭(Roland)的論文——只剩馬斯頓還在。馬斯頓是職業外交家、戰時的招募官、各部長的情報顧問;「他是第一人,」傑布帝曾說,「玩權力溫布敦網球賽的第一人。」北大西洋公約聯盟,以及美國人深思後的迫切手段,徹底改變了史邁利服務單位的本質。司第—艾斯培的時代一去不復返,那時你非得去他在牛津莫德林學院(Magdalen)的研究室裡、喝一杯波特酒,才能接受指令;原本高度稱職、薪資低迷,接受指點後能發揮業餘水準的人手,讓路給了講求效益、官僚作風、勾心鬥角的大型政府部門——事實上是受衣著昂貴、頂著爵位、一頭顯眼的灰髮與繫銀色領帶的馬斯頓所擺布;馬斯頓,這人甚至記得祕書的生日,行為舉止卻被登錄處的小姐當作笑柄;馬斯頓,帶著歉意擴展他的帝國,並充滿遺憾地往更高處爬。馬斯頓,喜歡在亨里(Henley)舉辦光鮮宴會,並踩著部屬的成就前進。
大戰期間,他們延攬他,這個傳統部門裡的專業公僕,一個處理公文並能將部屬的聰明才智與笨重的官僚機器加以整合的男人。大英帝國多麼慶幸能找到一個他們熟知的人,一個有辦法將任何色彩淡化成灰色的男人,而這人也很清楚他的主人,能與他們平身進退。而他表現得可圈可點。他們喜歡他為了自己的交遊圈道歉的吶吶模樣,他為部屬的奇想辯白時的不真誠,以及他在考慮新承諾時的柔軟身段。他也不肯放棄斗篷與匕首人malgré lui(除了他自己)的優勢:為主人穿上斗篷,為僕人保留匕首。表面上,他的職稱怪異:名義上他不是特務局長,而是各部長的情報顧問,司第—艾斯培總喜歡稱他為宦官長。
對史邁利而言,這是個新世界:亮晃晃的走廊,精明的年輕人。他自覺平庸、過時,對著最開始在騎士橋區(Knightsbridge)那棟破敗的連棟雙層屋犯起思鄉病。他的外表似乎也以一種生理上的退化反映出這種難以調適:他的背更駝了,比以往更像隻青蛙;他的眼睛眨得更頻繁,並得到一個「鼹鼠」的綽號。但初出社會的祕書欣賞他,老是叫他「我親愛的泰迪熊」。
史邁利現在已經老得不適合放洋了。馬斯頓說得很清楚:「不管怎麼說,親愛的老兄,大戰期間地下工作做多了,身分也曝光得差不多。最好還是待在家裡吧,老兄,延續家族的香火。」
由此或可說明喬治‧史邁利為何坐在倫敦計程車的後座,時間是元月四日星期三的凌晨兩點,在前往劍橋圓環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