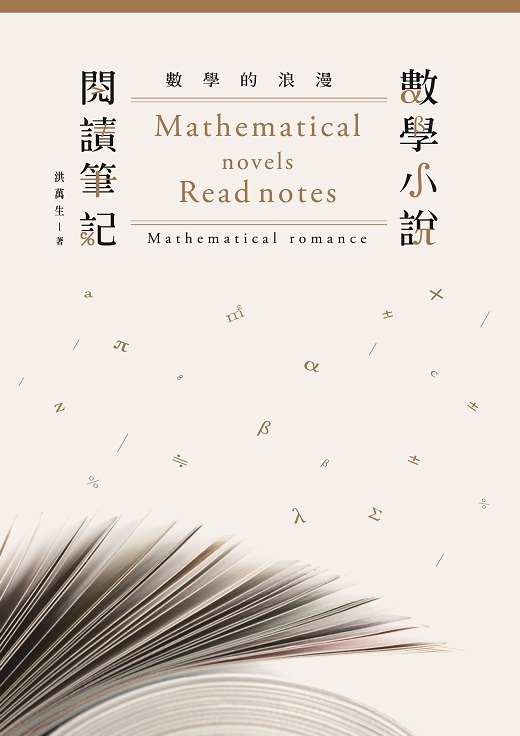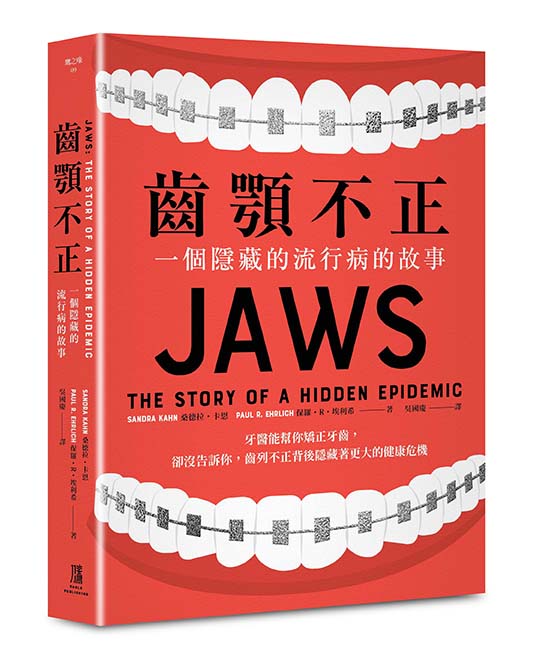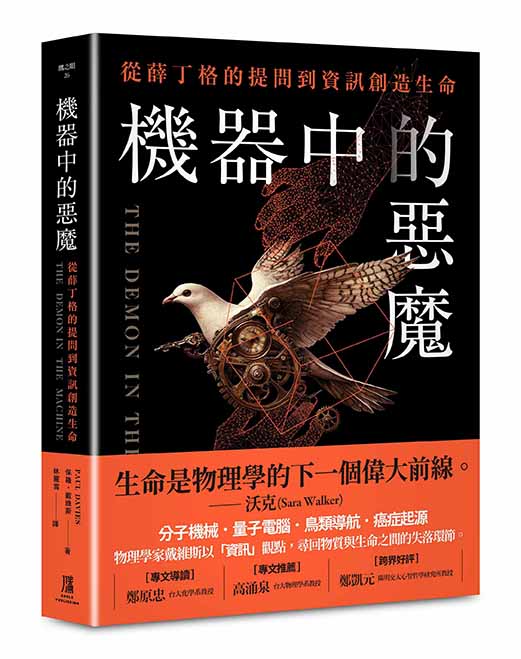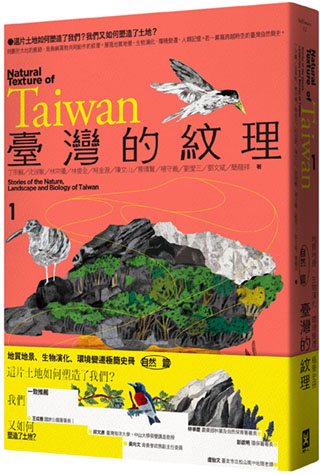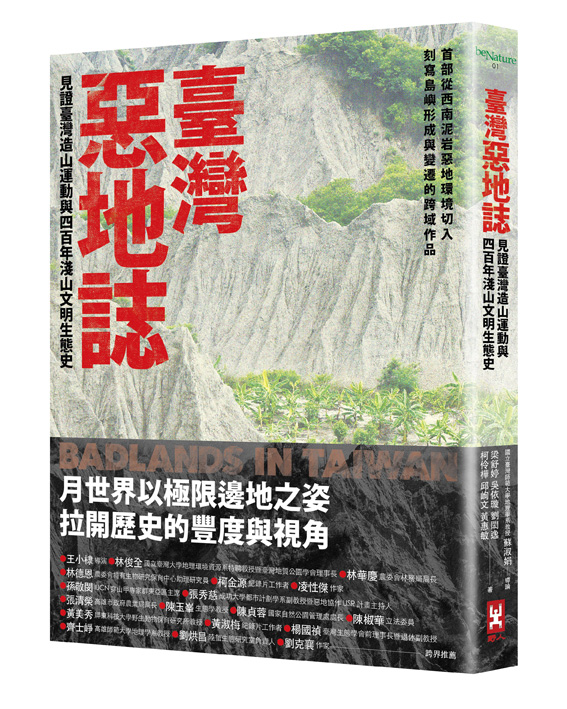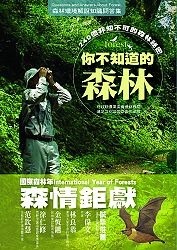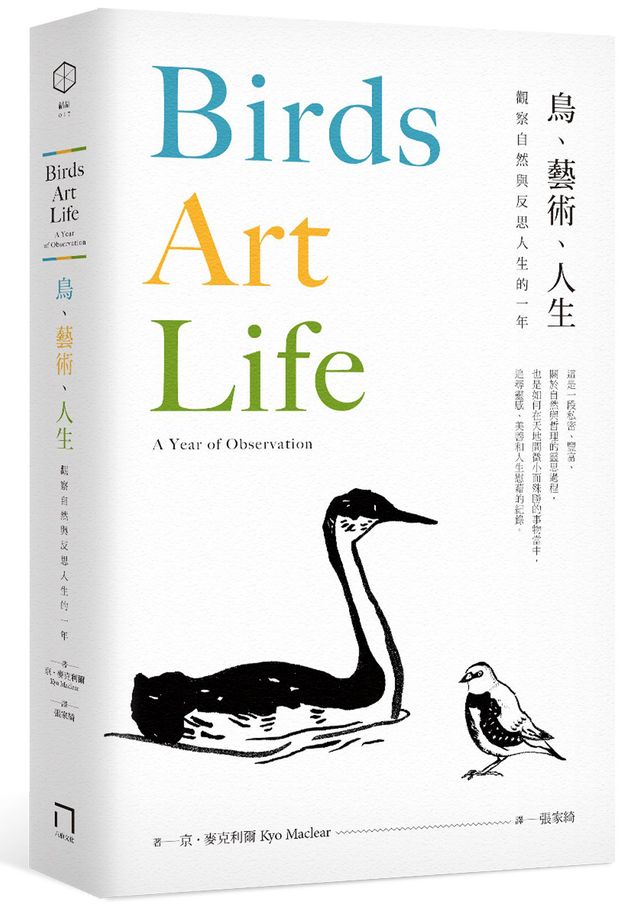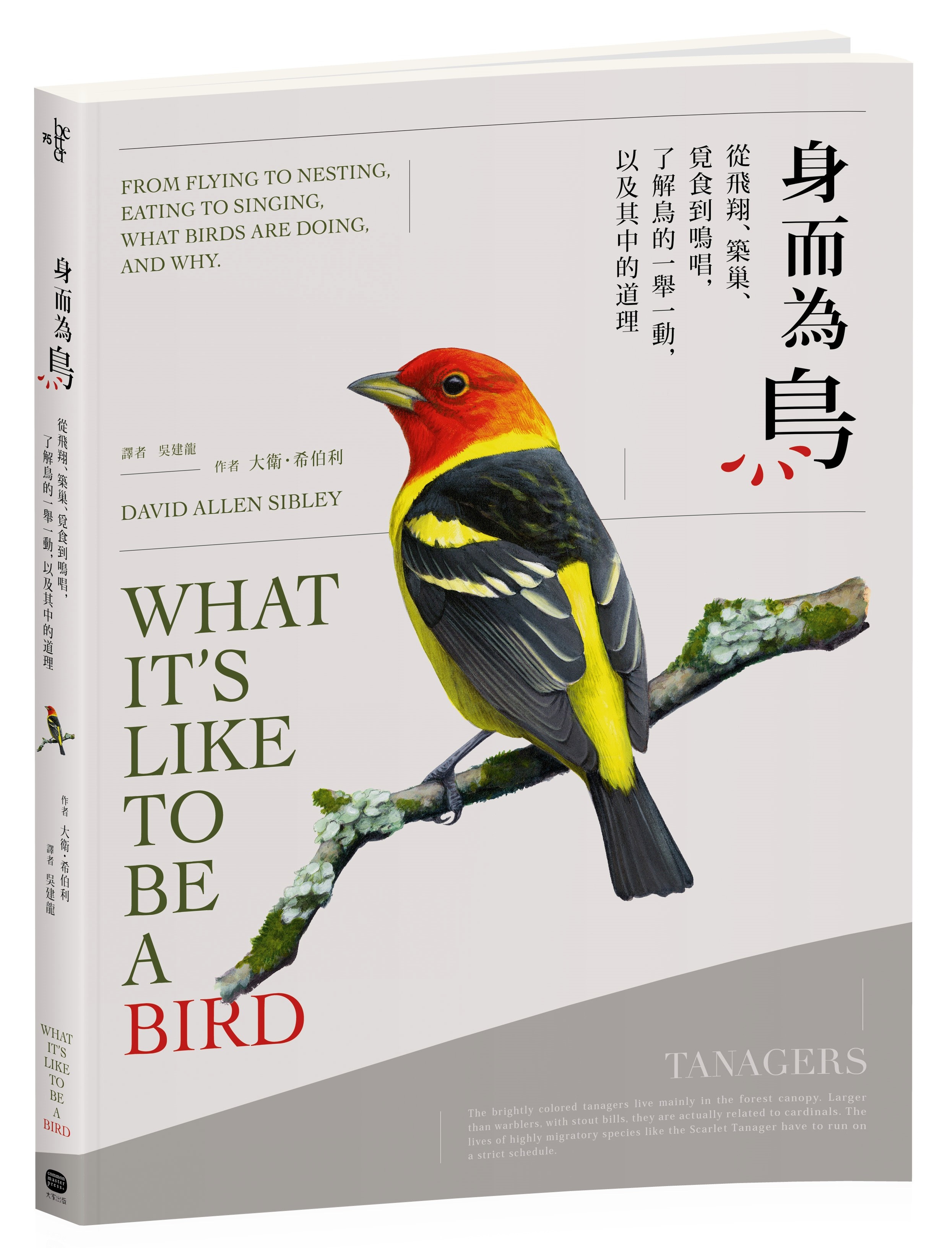當數學的學習只是變成一個篩選的標準,「背公式」、「解大量習題」就成為進階的唯一方式。那大多數的學生對數學的反應就會變成:
「數學 我的天啊 !」
「我恨數學」
「數學令人討厭」
數學不再『冏』
洪萬生老師指出另一種數學學習的方法:閱讀數學小說。
洪老師帶領讀者走入數學小說的世界。從不同的角度對照欣賞數學的邏輯與美感。「數學的證明就像在說故事,題目中的元素就是人物角色,情節要合乎邏輯,還必須要簡明而優雅」。
傳統的數學學習方式容易讓學習者覺得數學是中立的、冰冷的,因此,學習者不容易燃起對數學學習的熱情與認同感,透過敘事的形式,反而容易將要傳達的數學「精神」與概念包裝在故事中,讓學習者在輕鬆的心態下,自然地吸收所要傳達的價值觀。
洪萬生
台灣彰化人。他早有數學普及之夙願,基於大學時代所累積的數學經驗,中壯年時期戮力數學史專業及其在數學教學之應用。在逐漸退出學術研究行列之後,又有幸在大學的通識教學以及中學教師的研習活動中,分享數學小說的閱讀心得。不過,他試圖不斷地賦予數學知識活動之價值與意義,則始終如一,無論身份是學生、教師或是數學史家。
摘文
諾貝爾桂冠小說家孟若的《太多幸福》
艾莉絲・孟若 (Alice Munro) 是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她有一篇短篇小說〈太多幸福〉創作於2009年。根據她的自述,「有天我在《大英百科全書》裡找資料的時候,發現了索菲亞・柯巴列夫斯基(〈太多幸福〉的女主角)。這既是小說家也是數學家的身份,立時勾起我的興趣。」
現在,輪到我們對她的作品發生興趣。孟若是在榮獲諾貝爾桂冠的前一年創作這一篇小說。她究竟如何將這位女數學家的傳記,轉化成為一篇小說,或者她如何將數學史敘事轉化成文學敘事,是本文所關注的主題。我們希望藉此說明,文學家對於數學家及其知識活動的敘事,的確有助於我們認識數學的多元面向。因此,數學普及閱讀的範圍,理應將這些文學作品納入才是。
太多幸福
《太多幸福》(Too Much Happiness)是一本短篇小說集,其中有一篇與書名同銜的短篇小說,就是根據索菲亞・柯巴列夫斯基的傳記創作而成。根據孟若的自述(〈謝辭〉),她主要參考的傳記是唐・甘迺迪(Don H. Kennedy)的《小麻雀:索菲亞・柯巴列夫斯基傳》(Little Sparrow: A Portrait of Sophia Kovalevsky)。由於甘迺迪的妻子妮娜是索菲亞表親的後裔,因此,孟若認識這一對夫妻之後,得以接觸「索菲亞的部分日記、書信與無數的文字記錄」。
孟若將本篇小說的時間背景,集中在索菲亞過世(1891年2月10日)的前幾天,其中也穿插她早年生活的回顧。由於小說是虛構的,但其中的主要人物(尤其是數學家及其相關親友)都是真實的,因此,本作品可以說是一部歷史小說,同時,也由於其情節涉及數學 -- (女)主角索菲亞是俄國傑出數學家,因此,我們也將它歸類為數學小說。
目前的科普市場中,數學小說是一個極風行的文類,也因此,數學小說顯然負擔了數學普及的功能或任務。《太多幸福》出自諾貝爾桂冠作家,顯然是文藝創作,我們著實不應對號入座,討論它是否具有數學普及功能。儘管如此,由於主角是數學家,因此,孟若在小說敘事情節中,結合了數學知識活動的特殊趣味,還是非常值得我們注意。
底下,就讓我們來介紹並討論這樣的一個插曲。
數學的理性 vs. 文學的感性
索菲亞名字的英文拼法,除了上述的Sophia Kovalevsky 之外,還有Sonya Corvin-Krukovsky Kovalevsky,以及Sofia Kovalevskaya或Sofia Kovalevskaia。在《女數學家列傳》中,英文原版的名字是Sonya Corvin-Krukovsky Kovalevsky,因此,我們當年翻譯該傳記時,將她的名字中譯為桑雅・卡巴列夫斯基。不過,在本文中,我們主要使用索菲亞這個名字。
1850年1月15日,索菲亞・柯巴列夫斯基出生於俄羅斯的一個陸軍將領家庭,有姐姐安妮塔(Anuita)、弟弟費依達(Feyda)各一人。她父親卡魯卡夫斯基(Vasilii Vasilevich Korvin-Krukovsky)在她六歲時退休,不過,家道殷實,兩姊妹甚至因為文學早慧,寫作投稿並結識了後來成為大文豪的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而有機會進入當時在莫斯科活躍的「歐洲知識份子」菁英圈子。
索菲亞也在幼年時即展現不凡的數學才華。由於俄羅斯大學拒絕女生入學,因此,她只好設法到歐洲留學。不過,除了她父親強烈反對之外,當時俄國文化習俗也不容許未婚女子到海外留學,除非她已嫁做人妻。於是,索菲亞與姐姐安妮塔就與閨密商量,一起物色一位願意與她們假結婚、而且打算出國深造的年輕人,在人選決定之後,索菲亞自告奮勇,不顧父母的極力反對,堅持要「嫁」給他。如此一來,除了她自己可以出國讀書之外,她的閨密也可以名正言順地跟隨「她」一同出國。
索菲亞的「丈夫」名叫維拉第米爾・柯巴列夫斯基(Vladimir Kovalevsky)。這一對「新人」先到海德堡,維拉第米爾主修古生物學,索菲亞則研讀數學與物理學。後來,經由威爾斯查司(外爾斯特拉斯,Karl Weierstrass)的徒弟之推薦,她決定前往柏林大學,投入威爾斯查司門下。可惜,礙於柏林大學的規定,她不能正式入學,於是,威爾斯查司只好讓她私下參加他的書報討論班(seminar)。四年後,索菲亞完成博士論文,由威爾斯查司向哥廷根大學說項,而從該校榮獲博士學位。
1874年,索菲亞與維拉第米爾回到俄羅斯,雖然「丈夫」馬上獲得莫斯科大學的聘任,然而,她卻找不到任何大學教職或研究單位的位置。事實上,有一所小學歡迎她去教數學,結果她以無法熟背九九乘法表而拒絕!此時,過去的交友圈十分歡迎她的歸來,以及她帶回來的異國見聞,於是,她開始為報紙撰寫小品文、詩歌、戲劇、文學評論以及小說,並且得到極高的評價。「她為爭取教育機會所做的奮鬥,促使她成為強烈的女權鼓吹者;而且,她多數的文學作品也都集中火力在這個主題上大家發揮。」
由於索菲亞在文學方面的創作,受到文化圈內同儕及讀者歡迎,因此,她在小說《虛無主義女孩》(A Nihilist Girl,又名維拉・波隆佐夫Vera Vorontzoff)中,(註1)特別答覆那些讚美她多方面才幹的來信:
我瞭解你們會覺得奇怪,為什麼我能一邊創作文學,一邊研究數學。很多人由於從來沒有機會通曉更多的數學,都把數學和算術弄混在一起,而認為它是一門枯燥乏味的科學。事實上,它倒是一門需要大量想像力的科學呢。本世紀一位數學家領袖就曾非常正確地陳述這種情形。他說:任何人要想成為數學家,不可能不是心靈上的詩人。當然,為了領悟這個定義的精確性,我們必須拋棄古代人那種認為「詩人總是無中生有,且發明與想像乃是同一回事」的偏見。對我來說,詩人只是感知了一般人所沒有感知到的東西,他們看的也比一般人深。其實數學家所做的,不也是同樣的事?
就我自己來說吧!我這一輩子始終無法決定,到底哪個偏好較大些,是數學呢?還是文學?只要我的心智逐漸為抽象的玄思所苦,我的大腦就會立即偏向人生經驗的省察,偏向一些美好的文藝作品;反之,當生活中每一樣事開始令我感到無聊而提不起勁的時候,只有科學上那些永恆不朽的律則,才能吸引我的興致。如果我能心無旁騖地專注於一門科學,我應該可以在這一門上超越目前的水準,然而,我卻不能完全地放棄這兩項中的任何一門。
儘管如此,根據數學史家安・寇布立茲(Ann Koblitz)的研究,索菲亞的文學很難與十九世紀俄國大文豪如杜斯妥也夫斯基、普希金(Pushkin)及托爾斯泰(Tolstoyan)等人相提並論。畢竟文學正如同數學一樣,是需要專精的一種「技藝」(expertise),更何況她從未接受文學的專業訓練。不過,由於她的筆鋒所洋溢的基進與自由主義風格,大大地衝擊了閉塞保守的俄羅斯社會文化,因此,她的文學創作(有些如《虛無主義女孩》還被列為禁書)就十分風行,而造成廣大的迴響。
數學 vs. 詩篇:小說家如何敘事?
孟若將索菲亞有關數學 vs.文學的這一段自白,安排在威爾斯查司(外爾斯特拉斯,Karl Weierstrass, 1815-1897)第二次在家接見索菲亞的場合。原來在索菲亞第一次求見威爾斯查司時,他交給她一些問題打發她,要求她解出來之後再回來找他。小說家對他們第一次的會面描述如下:
「以妳這種情況,我能做的是,」他說:「給妳出一串題目,請你解出來,一個禮拜以後把答案交給我。要是結果我還滿意的話,我們再談。」
當然,正如後來故事的發展,威爾斯查司「詫異不已(這點他後來也跟他說了) -- 每題不但都解了出來,而且有些還是用完全原創的方法解的。」於是,威爾斯查司決定「小心栽培她,讓她學會怎麼管好自己腦裡不住爆發的火花。」
緊接著,在這個語境中,小說家讓威爾斯查司自述他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喜悅,不過,卻連結到前一節所引的索菲亞之自白。威爾斯查司先是表達他感受到無上「幸福」:
他這輩子(他始終對「熱過頭」這情況非常小心,所以他坦承,要他講出下 面這句話並不容易)-- 他這輩子就是在等這樣的學生踏進書房。一個能處處挑戰他的學生;一個不僅有能力跟上他的思路,更可能大幅超越他想法的後進。
接者,他指出直覺的洞察力對於數學家與詩人的同等重要,而且也強調直覺之外的「十分嚴謹、一絲不苟」:
他在說出自己真正相信的事情之前必須三思 – 那就是,在一流的數學家的腦袋裡,必定有什麼類似直覺的東西,某種一瞬之光,能揭露始終存在的奧秘。這種人必須十分嚴謹、一絲不苟,但偉大的詩人也是如此。
針對數學家 vs. 詩人的強烈對比,小說家認為威爾斯查司不無掙扎:
他終於有勇氣對索菲亞把這些和盤托出時,也對她說:有一些人一聽「詩人」 這詞和數學連在一起便怒不可遏;也有人忙不迭附和這種觀念,卻解釋不了自己的想法何以混亂鬆散。
在這一段敘事中,小說家可能考慮過但又覺得不適合提及的插曲,應該是威爾斯查司學派(或柏林學派)所主導的「分析算術化」(arithmetization of analysis),至於其代表作之一,就是函數極限 (lim)┬(x→x_0 )〖f(x)〗=L 的 ε-δ 定義:
對於所有的正數 ε,存在有一個正數 δ,使得
若x滿足 0<|x-x_0 |< δ,則 |f(x)-L|<ε 成立。
這個經典的定義出自漢內(Heinrich Eduard Heine, 1821-1881)-- 威爾斯查司的另一名高徒,標誌著數學分析學(Mathematical analysis)的邏輯基礎從此確立。(註2)而所謂的「算術化」,是指在此定義中,只涉及邏輯量詞(logical quantifier)如「所有的」和「一個」,邏輯連詞(logical connective)如「若…則」,以及算術(絕對值)不等式。如此一來,極限中的無窮小量(infinitesimal)所引起的邏輯含混及謬誤,即可一掃而空。
威爾斯查司學派的貢獻當然不僅止於此,然而,直覺與嚴謹並重,無疑是他的學風。而在這個關連中,小說家按照她對詩人的技藝(expertise)之想像來對比數學家,的確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敘事。
不過,索菲亞描述她自己如何依違在數學與文學之間,如何從「永恆不變的律則」 vs. 「人生經驗的省察」得到心境的平衡,有其自我解說(self-explanatory)之功能,小說家倒是棄而不用,實在有一點可惜!因為索菲亞的這個「現身說法」,對任何人(尤其是數學或科學的學習者)來說,都相當具有啟發意義,值得我們參考。
結論
本文第二節引文出自Lynn M. Osen的《女數學家列傳》(Women in Mathematics)。在這一篇傳記中,歐森只是單純引述那兩段文字,用以說明索菲亞擁有多面向的才華,譬如她既能從事抽象的數學思考,也能從容出入極端感性的世界。正如本文第三節所述,相對於此一「白描」,小說家孟若的敘事,就豐富深刻多了。小說家顯然考慮到威爾斯查司(外爾斯特拉斯)的「分析算術化」所代表的嚴謹學風,因此,她特別在他們師徒第二次會面後,指出他收徒條件之「嚴謹」,以及他如何珍視數學才識在嚴謹之外的「一瞬之光」,正如同詩人不同凡響的感知能力一樣。
總之,小說家孟若為索菲亞的自白 -- 任何人要想成為數學家,不可能不是心靈上的詩人 -- 提供了最動人、最貼切的敘事。(註3)事實上,這也是目前科學文化人最渴求的博雅本事版本。然而,如何將這句話融入故事情節,當然考驗文學敘事功力。孟若在這個語境中為我們解說嚴謹 vs. 直覺,其手法別出心裁,值得我們欣賞與借鏡!。